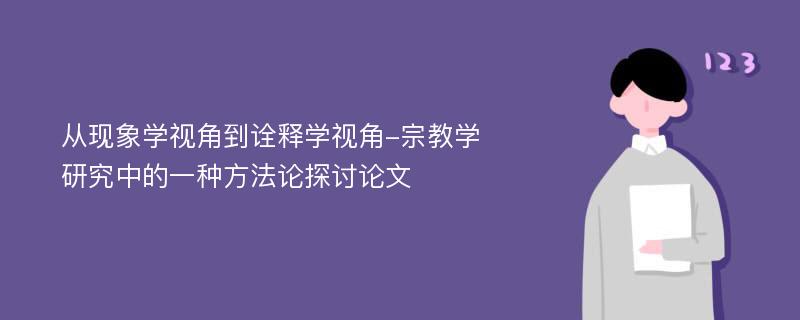
从现象学视角到诠释学视角
——宗教学研究中的一种方法论探讨
宗喀·益西丹佛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摘要: 本文首先从现象学入手,考察宗教学研究中的局内视角(Insider)与局外视角(Outsider)及其两者的互动与融合,提出宗教学研究的方法和立场应当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由此形成客观、公正、理性对待宗教的取径与态度。其次从诠释学出发,考量文本原义和读者释义的互动与融合,主张诠释学的立场应当是读者本位、本土化位格以及现代化视域。从此双重视角的交汇中自然引申出外来宗教中国化的必然性与合法化。
关键词: 诠释学;视域融合;局内人与局外人;佛教中国化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宗教现象是最为复杂的,因为它涉及到人们的精神世界与终极关怀。对此,笔者试图借助现象学与诠释学的方法,以便尽可能探寻宗教现象的“事情本身”并发掘其隐微的意义。胡塞尔通过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对纯粹现象达到本质性的理解,而海德格尔则将“理解的前结构”或曰“前见”引入现象学视域。在他看来,我们在理解和把握现象时与我们自身的社会文化传统密不可分,因为我们永远无法超越自己的文化传统。“所谓文本意义的发生,其实是主体与文本之间的‘视域融合’。这是一个主体与文本之间不断流动、相互生发的过程,我们由此进入‘诠释学的循环’。”[1]本文即是在这样的视域下探寻宗教学的研究视角与方法。
一、“局内人”与“局外人”两种视角的视域融合
宗教学研究仅仅依靠“局外人”的视角来诠释“局内人”的状况是否已经足够?回答是否定的。人们都知道 “只知其一,便一无所知”(He who knows one,knows none)的道理。用当下流行的话说,就是没有他者的观照,便无法了解自我,此所谓“揽镜自鉴”也。我们穿着别人的鞋子究竟能走多远?1○在美国小说 《杀死一只知更鸟》中出现过这么一句话:“You never really understand a person until you consider things from his point of view…until you climb into his skin and walk around in it.”2○此句可译为“你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一个人,除非你从他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直到你深入他的内心,走进他的世界,在其中徜徉。”这个说法引申到宗教的学术性研究中,便关涉到“回到事情本身”与“观察的客观性”问题。对此,可称其为“局内人”与“局外人”(Insider and Outsider)。根据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还原的第一步即是悬置,“它不仅包括对现象以外的外部世界的实在性暂且存而不论,更重要的是必须彻底搁置前人的判断以及自身的偏见。”[2]这也是我们在对某个宗教研究前放弃一切所谓“前见”,力求成为局内人的愿望,即“Can You Climb Out of Your Own Skin? ”3○此时我们能悬置自身的立场吗?换言之,我们能使主体自身的情感还原到研究对象的客体中吗?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感同身受而充当一个客串者?
经过7天朝夕相处,两人的感情更加火热,郭启明提出,让关小美和他一起到北京去。他说:“小美,我是公司里的储备人才,现在公司就已经给我分了公寓,配了雅阁小轿车,公司领导承诺,将来还要给我股份,那时,我就可以每年带着你到海滩度假,带你游历世界……”郭启明的话让关小美心潮澎湃,但她还是犹豫着摇头说:“启明,我们的事我还没来得及给我爸爸妈妈说,如果我现在丢了工作跟你到北京去,他们肯定会反对……”
因麦克斯·缪勒在1873年出版的 《宗教学导论》一书中的首倡,这门学科被命名为“宗教学”(The Science of Religion)或曰 “比较宗教”(Comparative Religion),“强调所谓宗教学就是对各种不同的宗教进行比较性的说明和研究”[3],这样宗教学就作为一种学科体系而形成,意味着人们将宗教现象作为一个客体对象予以考察。这表明宗教研究开始摆脱单纯的神学视域,以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探究,但其中亦存在不少学术难题,因为许多宗教学者“既不主张涉及宗教现象的本质,也闭口不谈宗教发展的规律。”[4]这不是人文社会科学视角下的宗教学研究。后来,日本宗教学者岸本英夫把宗教研究的立场和方法分为两种,即“主观的立场”和“客观的立场”。“主观性的研究是从信仰的角度或批判信仰的角度出发的研究,是探讨宗教应该怎样存在或批判这种存在的研究;客观性的研究与此根本不同,是所谓如实地用实证的和价值中立的方法来研究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宗教;主观立场的研究包括基于信仰的‘神学’和基于理性以批判性地探求宗教本质的宗教哲学;客观立场的研究则包括宗教史或他所了解的宗教科学。”[5]这样,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宗教学研究形成了所谓的“局内人”和“局外人”两类观察者。在现当代很多学者看来,尽管不作为广泛的特权,学术研究中有一个传统的假定即经验在所有人类存在中可被分享,就是人类通过学习共有的经验达到“局内”(inside)4○。 对宗教的理解并不意味着唯有信仰或依赖于某种特定的思维过程才能达成,而关键在于能否对他人的经验、思想、情感、观念等做到悬置与移情,在此前提下,这些学者认为“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的差距是可以被克服的。
尽管如此,仍有很多人持反对态度,在他们看来“信仰是对尚未实现或尚未证实观念与境界的确信与追求。”[6]有关人的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后者的研究对象都是可以直观接触或感知的,而人的状况要复杂得多,不同于这些物质甚至是动物。“宗教最本质的特征就在于它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有限性,以及有限的人对无限的终极神圣的一种永恒的追求和向往。”[7]人类的行为和信仰往往受到情感和精神层面的巨大影响,故此,宗教信徒对具有超越性的彼岸世界的确信与向往以及终极关怀的神圣导向等层面,恰恰是“局外人”(outsider)最难以企及的部分,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具有规律性与必然性。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公式,如 “W will do X,will say Y,and think Z”5○,可通过外部条件推导出固定结果,尽管这在自然科学甚至是部分社会科学学科中是探求结果的重要手段,但恰恰人类的行为往往不能够通过外在表现而推导出来,更何况是涉及到精神与内心感受的信仰活动。
那么,难道在宗教研究中“局外人”就永远无法与“局内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了吗?事实上在以往的研究中,从外部建立理论以沟通Insider与Outsider并非完全不可能,因为人类的行为终归有客观性的表现,这些都是可以基于观察与经验层面来研究的,而其中的挑战是工具和手段上的发展,这样能够帮助Outsider在经验和意义上进入他者,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建立桥梁。如英国的著名宗教学家尼尼安·斯玛特,他从单一的绝对主义的定义形式出发,提供了一个更具动态的维度定义。在早期的讨论中他提出了七种不同的维度来定义宗教的边界,即“实践和仪式的维度”、“体验和情感维度”、“叙事或神话的维度”、“教义和哲学维度”、“伦理和法律维度”、“社会与制度维度”、“物质的维度”。尽管这七个维度的讨论无法囊括所有数据,但这种方法相较传统定义更具开拓性。这些维度有助于描述各种文化形态在世界上的存在,我们可以对那些活跃于人类精神的运动进行一个平衡的描述,并在社会的形成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不忽视任何想法或实践。6○
易门县农业局大胆创新,打破过去一站一所或多站所同时进行一种作物的技术推广模式,从局下属的种子、农机、经作、农技等站所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技术组,集合各专业之长,形成综合技术优势,发挥专业特长,在油菜生产中全程提供优质服务。经过五年实践,积累了一套主推技术措施,锻炼了一支科技队伍,筛选出了1-3个主导品种,实现了思想观念、管理经验、体制机制的突破与创新。
在Insider与Outsider之间沟通,方法的不可知论(Methodological Agnosticism)是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即不要假装结论的必然性7○,或曰不要假装自己的中立客观。此时我们不禁要问:怀疑论者与信仰者之间能相互理解吗?如果研究者不参与到Insider中,一个可能被赋予完美意义的意图和动机的世界,那么研究者通过什么手段才能评判其中的对与错、准确或妄想呢?如果研究者的目标不是价值判断,只是简单的描述人类行为和信仰文化的多样性、相似性与复杂性,那么他们所谓的宗教研究又与社会学和人类学甚至是经济学的田野调研或考察报告有何区别呢?8○当然,方法的不可知论并不是要求你成为一个有神论者,但无可厚非的是,它会要求我们在某一刻处在此位置上,即当没有确实足够的信息去作出关于事实问题的决定时,不要轻易地下结论。宗教与其他各种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虽然宗教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对于世界的认知有很大差异,但它们各自作为一种世界观,都对人类的基本问题予以关注并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社会发展,所以应当形成一种既相互碰撞又相互促进的状态。事实上,“信与不信”的问题存在于很多讨论之中,这预示着即使我们不同意对方,也有必要理解对方。宗教学家罗伯特·A·西格尔(Robert Segal)认为宗教信徒一般采取两种主要策略抵御来自社会科学领域简化论的威胁:一种是消除社会科学,另一个是包容他们。这两种策略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是不一样的,但它们都假定社会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威胁着宗教。前者具有一定的防御性,认为社会科学对宗教的本质有一种曲解,因此实际上不会对宗教领域构成威胁。社会科学只能给出一些关于宗教的基本问题的答案,诸如起源、功能、意义和真理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社会科学给出的答案是一致的,甚至更确切、更具体的来说,社会科学只能回答关于功能和起源的问题,即以更简化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更苛刻的来讲,社会科学不能回答任何关于宗教的问题,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是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而不是宗教本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米尔恰·伊利亚德。而“包容社会科学”比第一种更具讽刺意味,但却更加隐伏。它认为社会科学的威胁虽然曾经是真实存在的,但现在却已经没有了。宗教主义者与社科学者现在用同样的路径分析宗教。宗教主义者并不是以社科学者的路径来研究宗教,而是社科学者向宗教主义者那样,以他们的方式来研究宗教。这与传统的社会科学学者形成了对比,当代的学人将宗教视为宗教,而非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这样他们对宗教的分析就并非是化约主义的结果。9○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五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后期,学界无有可能采取汤氏这种对待宗教的态度与立场。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拨乱反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落实,此方法逐渐为不少学者所接受,如著名宗教理论家吕大吉先生提出“学术需理性,信仰要宽容”[9]的原则,著名宗教史家牟钟鉴先生提出研究宗教“要处在信与不信之间”,并比照前苏联对宗教采取“战斗无神论”的态度和方法,提出“温和无神论”的主张,以达到研究宗教时的客观与中立,后来还有些学者提出宗教研究要采取“感性体验与理性审视”的态度与方法。这些研究方法总括起来讲,对于宗教的研究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这样一种方法论和态度,看似是站在了一个价值中立的位置,但从本质上看,他们这些话语背后的思想动机或曰“底色”仍然受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与近代科学主义有意无意的支配,后来又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我们以当代两位研究宗教学理论的代表性专家为例,牟钟鉴先生出生孔孟之乡,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早年在北大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训练,后又研修中国哲学史,毕业后研究方向转至宗教学理论与道教文化。吕大吉先生早年在北大专修西方哲学史,后期专注于宗教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他研究宗教史与宗教学理论的思想底色。比照世界宗教学术史,中国的宗教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有三方面的转向,即“‘视角’上,从教内信徒宣教式的宗教研究转向兼具教外视野的、客观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宗教研究;‘方法’上,从论证性的‘神学’式宗教研究转向描述性的‘史学’式宗教研究;‘态度’上,从区分优劣差等的宗教研究转向平等对待的宗教研究。”[10]这些都说明中国学者中真正信仰宗教者并不在多数,再加之近代以来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以及唯物主义的教育在中国学者中深入人心,因此更不可能有严格定义下的纯粹信仰者。他们只是将研究视角的价值最大程度的靠向中立,因为“之间”、“宽容”、“同情”这些词汇,显然不是insider的语境与语法。诸如吕大吉、牟钟鉴二位先生,就自己的世界观而言是唯物主义者、理性主义者以及人文主义者,但他们对宗教及其信仰者抱着同情的理解、包容的态度,这不可谓不是对待宗教问题的一种价值中立。故此笔者认为这可视作一种积极的实证主义,即“局外人”在不能调和的立场对立状态下,做出的一种“乐观”妥协,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客观性。因为科学的宗教研究不接受宗教纯粹是人类生物性、社群性、精神性或经济性的衍生作用和结果的看法,但接受宗教有它自存而又独特的文化意义世界[11],即以科学的方法对宗教现象进行研究的同时,必须呈现出其内在所蕴含的宗教意义,这是宗教学研究成其所是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视角必须进行动态转换的原因。并且,这种价值中立的视角也不应是固定不变的,而应当始终处于一种运动状态,以应对来自Insider与Outsider面临的共同或相异的现实问题。这也许是宗教学研究中一个最佳的解决途径。伽达默尔说:“在异己的东西里认识自身,在异己的东西里感到是在自己的家,这就是精神的基本运动,这种精神的存在只是从他物出发向自己本身的返回。”[12]这说明如果没有一个有差异的他者,也无法借助差异来认识自我。这可能也是麦克斯·缪勒在对宗教学研究定名时所用“比较宗教”的初衷。
综上所述,立场、视角、方法这三个问题在宗教学研究中是如何体现的,它们三者之间有怎样的联系?从广义来讲,Insider和Outsider就是立场的区别;视角则是在不同的具体情况与讨论范畴下,一个观察者所处的位置;而方法来源于众多的分支学科,为不同的观察视角提供理论支撑与研究方法。但通过实践我们可以发现,所谓宗教研究中的“价值中立”在立场的维度中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立场不存在中间道路,在立场上宣称中立实际上就是一个Outsider,因为Insider是不需要也不认同这种中立的。所以,宗教研究的价值中立更多的是研究视角的中立,在这个维度中,中间立场也更具可行性。我们从中国学界研究宗教的诸位学者所谓“价值中立”的立场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如著名中国佛教史研究大家汤用彤先生在1938年出版的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的题跋中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中国佛教史未易言也。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深弘。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8]汤用彤先生的这段经典论述说明了宗教研究者对其对象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陈迹之搜讨,文字之考证”上,而要对宗教本身怀有“同情之默应,心性之体会”,并须身体力行之,否则“必不能得其真”。真可谓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矣。
我们关于信或不信的讨论应当建立在分享、对话的基础之上。那些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不能完全分析宗教的“局内人”们,认为它们只能对某些特定的方面进行探讨,比如功能与起源,而非意义和真理。意义与解释有关,并且要对比得出解释的原因。其中一种解释了宗教的意义和原因,但是什么又定义了这种解释与说明本身呢?10○这时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视角来暂时悬置我们的本位立场,变成能够移情或者解释的观察者。例如,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哲学家在探讨哲学问题时,他的结论推理或通过经验实证,或通过逻辑理性,而不应当作信仰主义式的宣教。这样,方法的不可知论意味着研究者在研究中能够选择更多工具或方法,在无法确定从观察处获得更多的事实或证据存在时,有意识的避免提出价值判断或事实的问题。这是作为一个“局外人”在回答“理解何以可能”的时候可以给出的答案。对研究宗教的“局外人”而言,关键不是用不用“局内人”的视角,而是用得好坏与深浅问题。我们当然不能只以“局内人”的视角为标准,但必须要进行参照与融合,这是每一种文化传统与宗教思想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可见对“局外人”来讲,“局内人”的处境及视角不仅不是负能量,反而是正资源。当然,从另一角度讲,“局内人”也应对“局外人”的处境和视角有同情的理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也。也许“局外人”的视角让“局内人”跳出“局内”又反观“局内”,通过了解他人的视角来看到更好的自己,达到一种对话的境态。
情境教学的目的就是千方百计地促使学生带着好奇心理解教材,但是每个人的认知心理又有一些差异,所以要有相应的策略和优化方法。简单来说,教师要把握一定的技巧来激发学生的感悟和思考,鼓舞学生大胆想象,享受审美的乐趣。
二、文本原义与读者理解之义的视域融合
首先,作为诠释学的三大要素,文本原义、作者原意与读者接受之义是任何诠释学理论都无法忽视的部分,实践证明在这三者之间,没有高低主次之分,只有各自侧重点的不同。所以,现代诠释学研究是要在上述三要素之间找到一个立足点,这个点即是某一诠释体系的特征。任何一种诠释学体系都有其合理性与片面性,而后者早在从三要素中择其一点之时就已产生,故诠释学理论中此三种向度的关系就不可能是截然对立的,应当是互补、交流与融合的。“在当代诠释学家的思考中,作者原义的因素,因其事实上难以求得,已逐渐淡化,基本上退出了人们的视野。”[17]诸如海德格尔、利科尔等学者,在他们的诠释学理论体系中,基于作者方面的考虑已经若有若无,乃至于全然不关切。但实际上这并非毫无意义,尽可能深度把握文本原义与作者原意对于文本的理解仍然是一种积极因素,“准确的重构文本的作者原意虽不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作者原意,也不意味着理解作者原意的尝试根本无助于对文本的理解。”[18]故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一切在理解活动中产生的意义都不会是文本原义、作者原意与读者接受之义三者当中的某一种单纯结果,而应当是它们的综合,换言之,人类理解与解释的历史,基于理解过程中此三要素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产物。
故此,理解(Understandings)与解释(Explanations)这两个词在开始讨论上述两种可能性的时候变得都非常重要。对于Outsider来说,他们需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从外部观察、理解到的关于信仰和行为的意义进行解释,并从不同的世界中得到相同的认可。人与人的理解力尽管各有不同,但研究人的信仰与行为并不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产品,他们只需要把握意义与道德价值观,把宗教看作是自然界中的一种复杂事物,可辨别以及被描述和记录等。如果不是来自宗教信徒的认可,就没有理由证明宗教学者的正确性与有效性,这样的规则被接受,那么最终信徒判定的对与错将成为唯一权威。但如果按照这个规则,人们在对宗教进行考察研究的时候就会变的单一化,并很难发现信徒在宣扬与行为之间的差距,因为有时连信徒们自己也不详细了解自己行为的复杂意义,所以我们在进行宗教研究的时候,不能被动的只从一方面接收信息。这样从整个宗教学研究理论的发展来看,就不会有任何一种宗教性的唯一视角能够左右研究结果,我们从每一个外部的特定系统中寻找标准,以便于比较,最终一起阐释它们。
其次,我们以诠释学的视域看宗教学研究中的“局内人”与“局外人”论题,也是属于文本原义、作者原意与读者接受之义讨论的范畴。无论“局内人”与“局外人”,在面对宗教文本时,他们都是不同的读者,而对于“局外人”来说,宗教文本与“局内人”本身,有时都是“文本”和理解对象。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诠释学的视角就是读者的视角,因为“理解并不是更好理解,……如果我们一般有所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19]所以局内与局外两种不同读者的互动交流,概括起来讲就是要“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是指我们对所研究的宗教要给予同情的理解、同情的默应,要深入宗教,尽可能的对信仰者感同身受,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的理解他们,尽可能真实的还原信仰者的内心世界,即他们的所思、所想、所行、所为。也就是所谓现象学的还原性研究,而“出乎其外”是指作为学术研究,这也就是诠释学的读者本位和读者立场。我们“入乎其内”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出乎其外”,在“入乎其内”的过程中最终成为了某种宗教的信徒,尽管对这种现象不应当做价值判断,但已经丧失了作为学术性研究的读者立场。在研究过程中对某一宗教的认识深入到一定程度,我们就需要“出乎其外”,站在客观的立场,理性审视我们的研究对象,这应当是宗教学研究者所秉持的立场与态度。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当观察宗教时,应与宗教最近;当研究宗教时,应离宗教最远。也就是与宗教既近又远,近是指进得去,远是说要跳得出,唯其如此始可跳出皮相,获取精髓。
鉴于研究内容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及发表文章语言的局限性,为使更多的国内读者及时了解竹藤研究前沿进展,本刊将及时跟踪GABR成果,对原文内容进行精简、提炼,以中文形式呈现给读者。本期介绍全球首次报道的棕榈藤基因组的情况。
应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使用单变量分析来筛选出与预后有关的因素,在单变量分析中显示与预后有关的因素再被纳入到多变量分析中。K-M分析及LOG-rank检验用来分析二分类单变量和描述生存曲线。多分类变量及多因素生存分析采用COX生存分析及LOG-rank检验。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依次筛选出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
三、现象学—诠释学视角下的宗教学研究方法
西方诠释学理论发展为一种哲学思潮,经历了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它要解决“理解何以可能及如何实现”的问题,并以哲学诠释学的方式进行了回答。这是哲学诠释学的逻辑起点所在。理解是一种此在的存在方式,人们在进行理解或者价值判断的时候从来就不会有一种绝对、纯粹的客观中立视角。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所有的理解行为都是一种处境化的理解,即读者在当时所处的时空条件下对文本进行的本土化、在地化诠释。“一切的理解都与自我理解相关,而自我理解乃是被抛的筹划;这意味着理解开始并结束都在主体之外——在它所不创造的过去和它对之没有控制的未来之内。”[13]存在是我们理解的存在,是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这就意味着理解永远无法超越它自身的历史境遇,其所能获得的知识总是具有局限性的,且可修正,而我们恰恰不能将其看作是它客观上的局限。
事实上关于文本与理解的问题,在西方哲学的领域里有不同的讨论,如施莱尔马赫认为要“还原和重建”,而黑格尔认为需要“综合创新”。那么究竟是要原汁原味的“还原和重建”抑或是历史视角与当代视角、他者视角与自我视角、文本视角与读者视角的“综合创新”?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对施莱尔马赫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且赞同黑格尔的观点。在黑格尔看来,理解和诠释是历史—当下、主体—客体以及自我—他者的整合,“因为历史精神的本质并不在于对过去事物的恢复,而是在于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14]这是黑格尔在文本的理解和诠释问题上超越施莱尔马赫之所在。故如果将宗教作为一种文本对象的时候,我们的理解和诠释就应当回归到读者(研究者)的立场,并且是读者当前时空条件下的处境化阐释。但是,在这种处境化的理解过程中,我们并不是完全要抛弃文本原义,绝对的遵从读者原意,伽达默尔认为,“我们要对任何文本有正确的理解,就一定要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和某个具体的境况里对它进行理解,理解在任何时候都包含一种旨在过去和现在进行沟通的具体应用。”[15]想要理解文本的意义,我们必须首先得到某种视域。
综上所讲,如果将现象学上的“局内”与“局外”,“还原”与“释义”转换成诠释学便形成了文本原义与读者之理解、诠释之间的互动与交融,其结果便是回到了以读者为主的立场,而读者的立场也就是处境化的,因为读者作为“在世存在”总是已经处于理解境遇之中,这种理解境遇便决定了此读者的立场和态度必然是当下的,即现代性,本土的即是民族化,此为诠释学的两大重要特征。这是说“任何理解都绝不是一种复制性的原样理解,而是理解者根据自己的当前语境和现实问题对一直传承到自己的传承文本的把握,这里既有理解者的具体境遇和效果历史前理解,又有传承物本身经历的效果历史,因而我们的理解本身就是一种具体的效果历史事件。”[20]由此所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对任何文本的理解、诠释,都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而这种理解与诠释行为包含着一种旨在将过去和现在进行沟通的具体应用与实践落实维度,这便决定了中国佛教,乃至于任何一种外来思想文化或宗教的本土化、现代化的必然性、合理性与合法化。
在这种既包括理解者、解释者“前见”又与文本自身相融合的“视域融合”中,前者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决定性作用。正如伽达默尔所言:“企图在解释时避免运用自己的概念,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显然也是一种妄想。所谓解释正在于:让自己的前概念发生作用,从而使文本的意思真正为我们表述出来。”[16]这是外来思想本土化的内在因素。中国学者方立天先生的一番论述道出了此本旨:“我研究佛教秉持的是‘中国本位’立场,······也就是说,我是在中国文化、思想、哲学的演变、发展的历史背景下,研究中国佛教文化、思想、哲学的流传、兴衰。”⑪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前见”是他理解中国佛教的思想根底,中国人的实际需要和精神需求是他面对佛教的态度,本土的儒、道等文化自然而然的与佛教交流、交往、交融。因此方立天先生研究佛教的成果是中国传统思想视域与印度佛教思想视域的融合,即佛教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且更是其内在根据与必然结果。
注释:
对分离出的7株产蛋白酶菌株的菌落形态进行观察鉴定。通过革兰氏染色和霉菌的乳酸石碳酸棉蓝染色,观察菌株的个体形态,并确定有6株菌为革兰氏阳性菌,观察结果见表4。
①③④⑤⑦⑧⑨10○Russell T.McCutcheon,The Insider/Outsider Problem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CASSELL:London and NewYork,1999),general introduction,pp.2.此书无中文版,上述引文内容为作者译,如有错误还望读者海涵,下文中不再赘言。
②Lee,Harper 1982(1960).To Kill a Mockingbird,New York:Warner Books.p29-30.Russell T.McCutcheon,The Insider/Outsider Problem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CASSELL:London and NewYork,1999),general introduction.
⑥Ninian Smart(1989),The World's Religions,Cambridge:Canbridge University Press.参见Throries of Reigion--a reader,Edited by Seth D.Kunin with Jonathan Miles-Watson,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Brunswick,New Jersey.
⑪参见《方立天文集》总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参考文献:
[1][2]谢爱华.还原与诠释:宗教田野经验的现象学考察[J].宗教与民族,2006,(10).
[3][4][5][9]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2.13.14.5.
[6]金泽.略论信仰作为宗教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J].世界宗教文化,2014,(5).
[7]孙亦平.西方宗教学的历史回溯与未来展望[J].江苏社会科学,2002,(3).
[8]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87.
[10]刘贤.陈垣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宗教研究的现代转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3).
[11]黎志添.宗教研究与诠释学——宗教学建立的思考[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9.
[12][14][15][16][19]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6.247.x.401.420.
[13]乔治娅·沃恩克.伽达默尔——诠释学、传统和理性[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50.
[17][18]潘德荣.西方诠释学史(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8.
[20]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4.
From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to Hermeneutic Perspective--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Religion
ZongkaYixidanfo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art with phenomenology and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internal perspective (Insider)and the outside perspective (Outsider),and their integration,and puts forward that the method and position of religious research should be"inside and outside".Thus to form an objective,fair,rational approach to religion and attitude.Secondly,starting from hermeneutics,considering the interaction and fusion between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text and the reader's interpretation,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position of hermeneutics should be reader-based,loc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From this dual perspective of fusion,further extended to adhere to the inevitability and legalization of foreign religion in China.
Key words: Hermeneutics;Fusion of Horizon;Insider and outsider;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中图分类号: C958.12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681(2019)02-0030-06
本文系笔者参加的由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孙悟湖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和现状研究》(批准号:18BZJ024)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9-01-22
作者简介: 宗喀·益西丹佛(1993—),男,藏族,青海湟中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藏传佛教研究。
[责任编辑 先 巴]
[责任校对 徐长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