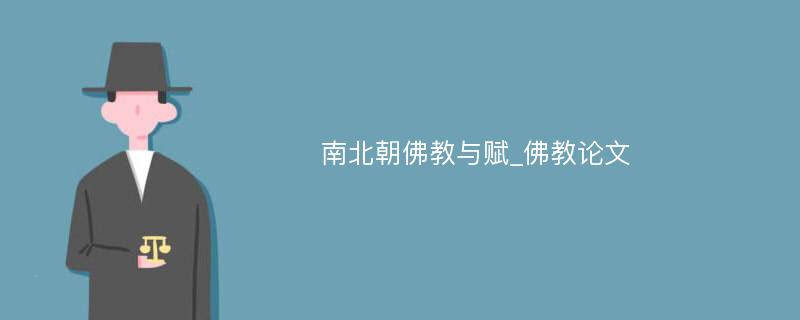
佛教与南北朝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教论文,南北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154(2006)05-0109-04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我国,在与本土的儒家、道家思想融合过程中不断中国化,逐渐成为中国人的重要心理力量。佛教在中国真正风行是在西晋以后,至南北朝时期尤为兴盛。南朝各代的帝王及一般文人学士大都崇信佛教。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南朝佛教兴盛景象的生动写照。北朝除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其余历代帝王都较为扶植佛教。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潮,佛教对汉魏六朝赋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选取南北朝赋作为主要文本来论述佛教对赋体文学的浸染,而为了考镜源流,间或也论及南北朝前后的一些赋作,尤其是东晋和隋的赋作。
一 佛教题材之渗入
(一)佛教题材的直接入题
佛教思想对赋体文学浸染的最为显著之体现莫过于相关题材的直接入赋,这一般从赋的题目即可判定。从现存文献来看,南北朝赋直接以佛教题材入题的作品有:梁武帝萧衍的《净业赋》①(《全梁文》卷一)、北魏李颙的《大乘赋》②(《全后魏文》卷二九)、陈江总的《修心赋》(《全隋文》卷十)。
作为梁朝的开国皇帝,武帝萧衍笃信佛教,为了表示对佛教的虔诚,他还多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萧衍以帝王之尊力倡佛教,使得佛教盛极一时,他在位期间把佛教几乎抬高到国教的地位。据何小莲《宗教与文化》记载,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人,仅建康就有大寺700余座,僧尼信众常有万人。梁武帝一生撰写了大量的佛教著述,其中就有以赋体写成的《净业赋》[1]。从赋题来看,此赋是以铺叙清净善业的修习为主旨的。“净业”乃是佛家之语,指清净之善业,是往生西方净土的业因。《观无量寿经》一云:“凡夫欲修净业者,得生西方极乐国土。”修净业,即净修,就是净业的修习,也就是清眼境、净心尘,明心见性的功夫。从赋的长序看,它在交代为赋缘起的同时,也表现了梁武帝向佛之心的极端虔诚,其中描写自己即位以后坚持素食的一段尤为感人:
及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羞,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莫不毕至,方丈满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辍箸,对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温清,朝夕供养,何心独甘此膳,因尔蔬食,不啖鱼肉,虽自内行,不使外知。至于礼宴群臣,肴膳案常。菜食味习,体过黄羸,朝中班班,始有知者。谢胐、孔彦颖等,屡劝解素,乃是忠至,未达朕心。[2]
为了清除“杀害”和“欲恶”二障,梁武帝不仅“不啖鱼肉”,而且“亦断房室”,不与嫔侍同处四十余年,虔诚之心,可谓至极。赋的正文则着重阐发自己对于如何修净业的体悟。赋中首先铺叙人的各种欲望对趋向善道的障碍,所谓“至如意识攀缘,乱念无边。靡怀善想,皆起恶筌。如是六尘,同障善道”。赋家极力阐述了因果轮回思想:人类以“眼、耳、鼻、舌、身、意”六识,追逐“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情欲无节,患累无穷,在现世就会“殃国祸家,亡身绝祀”,而死后将会“轮回火宅,沉溺苦海”。在阐明净业障碍的基础上,赋家又尽力描述修净业的正确途径,所谓“皇天无亲,唯与善人。外清眼境,内净心尘。不与不取,不爱不嗔”。佛教以为欲望由六根六识生起,所以要灭欲,只有清净六根,明心见性,才能脱离苦海。不难看出,梁武帝不仅有向佛的虔诚之心,而且对修习佛教清净善业的体认也是非常深刻的。
江总一生历梁、陈、隋三朝,入隋五年而卒,故而一般将其纳入南朝赋家来论述。又据《修心赋》序言,该赋作于太清年间,当为仕梁期间的作品。据《陈书》本传记载,此赋当作于侯景之乱之时。太清二年(548)朝廷曾经准备派遣江总和徐陵出使东魏,以病未行。不久,侯景反。次年台城失陷,“总避难崎岖,累年至会稽郡,憩于龙华寺,乃制《修心赋》,略序时事”。可见,此赋作于遭乱困乏之中。赋以“修心”名题,佛教主旨很明显。心,梵语为citta,佛教谓心为真体,是心性,不变之心体。《传心法要》曰:“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一念离真,皆为妄想。”所以说,赋的主旨是参悟佛教的明心见性之法。
读赋文亦可感知赋家由于遭难困乏而滋生的伤时之痛,佛家修心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其心灵的慰藉。其赋有云:
岂降志而辱身,不露才而扬己。钟风雨之掩蔼,倦鸡鸣之聒耳,幸避地而高栖,凭调御之遗旨。折四辩之微言,悟三乘之妙理,遣十缠之系缚,祛五惑之尘滓,久遗荣于势利,庶忘累于妻子。
赋家以佛教作为心灵苦痛的解救之方,力图达到一种宠辱不惊、遗荣忘累的超脱境界。
李颙的《大乘赋》也是直接以佛教入题,其主旨是铺叙大乘佛教。佛教有大乘和小乘之分。在序言中,作者着力阐释了大、小乘含义,所谓“大乘者,盖如来之道场也;故缘觉声闻,谓之小乘”。而“言法驾之通驰,如舟车之致远也”之句,则言明了“乘”的运载及传送之义。序言还在比较之中推阐了大、小乘两者之分野,所谓“无无以畅,则乘斯小矣;有有以通,则乘斯大矣”。赋的正文,则是着重敷衍大乘之要旨。由于赋作以推阐佛理为务,故而甚为抽象。
(二)佛教题材的间接引入
佛教对赋体文学题材的影响,除了直接入题这种最为直观的方式之外,以佛教故事、语汇、典故间接渗入赋的本文的方式也较为普遍。这种类型的赋作一般以描摹山水自然或世俗生活为主要内容,结合佛教题材内容的间接进入,表现对佛法的体悟,尤其是对佛教人生境界的向往。东晋僧人支昙谛的《庐山赋》和《赴火蛾赋》已经表现出这方面的特点,延及南北朝则尤为普遍。例如,谢灵运《山居赋》的本文以描写山水风物为主要内容,间或也插入一些佛教的内容。其中有这样一段与佛教相涉的铺叙:
苦节之僧,明发怀抱,事绍人徒,心通世表。是游是憩,倚石构草。寒暑有移,至业莫矫。观三世以其梦,抚六度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指东山以冥期,实西方之潜兆。虽一日以千载,犹恨相遇之不早。
这里描叙的主要是对于佛教思想的感悟,既有“寒暑有移,至业莫矫”的修佛恒心表露,亦有对“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人生境界的企羡。其中嵌入了诸如“三世”、“六度”、“西方”等佛教词汇,此外还有佛教的典故。对这段文字赋家自己还作出了解释,其自注曰:
谓昙隆、法流二法师也。二公辞恩爱,弃妻子,轻举入山,外缘都绝,鱼肉不人口,粪埽必在体,物见之绝叹,而法师处之夷然。诗人西发不胜造道者,其亦如此。往石门瀑布中路高楼之游,昔告离之始,期生东山,没存西方。相遇之欣,实以一日为千载,犹概慨不早。
与此同时,一些以佛教场所为创作背景和以佛经讲诵传播为内容的赋作,也是佛教对赋体文学题材的一种扩展。梁朝王锡的《宿山寺赋》和后梁宣帝的《游七山寺赋》就是以佛教寺院为创作环境的赋作。萧子云的《玄圃园讲赋》和萧子晖的《讲赋》描绘的都是梁朝法会讲经之盛况。《玄圃园讲赋》极力铺叙了当时讲经的场景,既人气旺盛而又不失庄重肃穆,可谓一派佛国气象。赋中有云:
于是清宫广辟,宿设宵张,华灯熠曜,火树散芒,敛闪六尺,笼丛九光。颖若流金之出沙屿,粲若列宿之动天潢。朝曭朗而戒旦,云依霏而卷簇。轻辇西园,齐宫北郁(囿)③;文卫济济,僧徒肃肃。法鼓朗而震音,众香馝而流馥。……扬散华之飘飖,响清梵於林木。灯王归而赠筵,香积来而献熟。似众圣之乘空,若能仁之在目。(《全梁文》卷二三)
在赋中萧子云还言明了时间是在梁武帝天监十七年,亦即公元518年。讲经的场面如此壮观,当时佛风之盛可以想见。萧子晖的《讲赋》其文已佚,然从《梁书》和《南史》的有关记载来看,其创作缘起亦在于听讲佛经。《梁书》卷三五《萧子恪传》附其子《萧子晖传》说他“尝预重云殿听制讲《三慧经》,退为《讲赋》奏之,甚见称赏”④。
二 僧赋与赋僧
研究佛教对赋体文学之影响,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那就是自东晋以来僧赋与赋僧的出现。谈及僧人与文学,学界对于僧诗与诗僧关注甚多,而于僧赋与赋僧则相对忽视。僧人作赋的源头最早可追溯至东晋。东晋以降,文人崇尚佛教,僧人雅好文学,渐成风尚。此种时代环境,有利于激发僧人参与赋体文学创作的热情。
现存最早的僧赋当始于东晋高僧支昙谛⑤。支昙谛,本康居(古代西域城市国名)人,居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县)之千秋里,后徙故鄣之昆山(今山东诸城县)。义熙七年(411)卒,年六十有五。《隋书·经籍志》列有“晋沙门《支昙谛集》六卷”。严可均《全晋文》卷一六五录其赋作两篇:《庐山赋》和《赴火蛾赋》。《庐山赋》描写自然之美,从题材而言属于山水赋范畴。《赴火蛾赋》是一篇短小精悍的咏物赋,取“愚人忘身,如蛾投火”之意,以蛾喻人,托物言志,寓佛理于咏物之中。其赋有云:
翔无常宅,集无定栖。类聚群分,尘合电移。因温风以舒散,乘游气以徘徊。于是朱明御节,时在盛阳,天地郁蒸,日月昏茫,烛耀庭宇,灯朗幽房,纷纷群飞,翩翩来翔,赴飞焰而体焦,投煎膏而身亡。
南朝僧人赋现存惟有释真观的《愁赋》、《梦赋》。真观,字圣达,俗姓范,吴郡钱唐(今属浙江)人。陈时,住泉亭光显寺。入隋,住灵隐山天竺寺。隋炀帝大业七年⑥(611)卒,年七十有四。严可均将其作品辑入《全隋文》卷三四,然而,真观一生跨梁、陈、隋三朝,其主要活动时间当在陈,故而本文将其赋作纳入南朝来考察。
《愁赋》这篇描写人的心理情绪的赋作,无论从题材还是从创作手法来看,显然都受到了江淹《恨赋》、《别赋》,以及简文帝萧纲《悔赋》之影响。其中对于一种情绪的细腻感受和精细区分,所谓“若夫愁名不一,愁理多方”,可以与江淹之“故别虽一绪,事乃万族”(《别赋》)两相媲美。
比较而言,《梦赋》则含有更多的佛教因子,尤其是渗入了佛教的人生态度。从结构而言,设为梦境,采用问对主客形式展开,在“客”与“余”的问答之中阐释佛教人生境界。其中有对出家之道的阐述:
戒忍双习,禅慧兼修。天人师范,豪庶依投。若夫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则道业逾高,益之则学功逾远。故形将俗人而永隔,心与世情而悬反。所服唯是三衣,所餐未曾载饭。从师则千里命驾,慕法则六时精恳。濯虑于八解之池,怡神于七净之苑。
通过潜心修佛,双习戒忍,兼修禅慧,超越世俗情感,无为无欲,不惧不忧,进而达到“法眼不窥其色,天耳不听其声。恶言不能加毁,美誉无以为荣”的超脱境界。其中“三衣”、“六时”、“八解”和“七净”等均为佛教的专门语汇。
北朝的僧人赋,现存有释慧命的《详玄赋》和释慧晓的《释子赋》,严可均将其辑入《全后周文》卷二二,其中《释子赋》仅残存两句。慧命,俗姓郭,太原晋阳(今属山西)人,住河阳仙城山善光寺。慧晓,俗姓傅,生平不详。《详玄赋》纯粹是一篇阐述佛理的赋作,通篇几乎都由佛学话语体系建构而成。然而,赋家在行文时讲究形式之美,骈偶甚为精工,音韵极为和谐,在阐述抽象的佛理之时,善于使用多种修辞技巧。如赋的最后一节:
道莫遗于始行,暗弗拒于初明。拟六贼其方溃,冀十军之可平。昏云聚而还散,心河浊而更清。性海无增减,行月有亏盈。疑兔足之致浅,惧鸿毛之见轻。为山托于始篑,庶昆仑之可成。(《全后周文》卷二二)
由于综合运用了对比、对偶、用典和比喻等修辞手法,尽力将抽象的佛理形象化,力图达到深入浅出的效果。因此,从文学价值来看,此赋也不无成就。
三 佛经译传对赋体创作艺术之沾溉
佛教对赋体文学之影响不仅表现在内容上,也表现在形式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的翻译和传播的广泛普及,为丰富赋体文学的创作艺术提供了新的契机。诚如程章灿所言:“佛教与赋尤其是南朝赋在表现手法上的联系虽然比较间接,却是客观存在的。”[3]我们认为,归结起来看,佛经的译传分别从音韵学和修辞学两个方面丰富和提升了六朝赋的表现手段。在声韵学方面,集中表现于对骈赋形成所产生的促进作用;在修辞学方面,则主要表现于佛教典籍中的比喻、典故和词汇等对赋的表现手段的丰富。
通过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传播,中国佛徒广泛接触印度的语言文字学,尤其是其中启蒙入门的字母之学,从而推动了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据《异苑》和《高僧传》记载,最早在研究佛经音律方面作出贡献的当为曹植,而学界以为此说恐多附会⑦,故难以为凭。我们认为,在南北朝以前,文人虽然也讲究声音和谐,但终究还停留于“始判清浊,才分宫羽”[4]的层面。有关声律的比较细密的理论,是南朝齐永明年间沈约、谢脁等提出来的。四声作为中古汉语的客观存在,何以恰在南齐永明得以倡明呢?这一方面得益于前代音韵学成果之积淀,另一方面与佛经转读带来的启示不无关系。诚如《高僧传》卷十三云:“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5]由于汉语语音与梵音迥异,佛典翻译除了达意之外,还需语音上的转读。这一点对音韵学带来了影响,也对赋体创作有所沾溉。
南朝的时候,赋体文学之中还出现了专门描写佛经诵读的作品,南齐萧昭胄就曾作有《经声赋》,虽然其文已佚,但是足以看出佛经诵读对赋体文学之影响。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二《齐竟陵王世子抚军巴陵王〈法集〉目录》著录有萧昭胄《经声赋》,而僧祐《齐竟陵王世子抚军巴陵王〈杂集〉序》亦说萧昭胄“雅好辞赋,允登高之才”,“观其搞赋《经声》,述颂《绣像》,千佛愿文,舍身弘誓。四城九相之诗,释迦十圣之赞,并英华自凝,新声间出”(《全梁文》卷七二)。这里写到萧昭胄对于佛经之诵读达到了“英华自凝,新声间出”的境界,足见佛经转读给当时带来的音韵学之影响。
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明确提出四声源于梵文的命题[6],指出四声说的确立缘于建康的“审音文士”和西域来的“善声沙门”相互交往和切磋。沈约《谢灵运传论》中的“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即是借用梵文诗律中的“轻重”来指汉语的声调。永明声韵说促进了包括赋体文学在内的各体文学走向格律化的进程,四声理论确立后被迅速运用到文学创作实践。《南史·陆厥传》说:
时盛为文章。吴阉沈约、陈郡谢脁、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为了铺排的需要,赋本来就是一种比较注重骈偶的文体,四声说的倡明无疑加快了赋的骈偶化进程。台湾学者黄水云以为骈赋萌芽于曹魏,成长于两晋,茁壮于刘宋,成熟于齐梁陈隋[7]。其实,在贾谊、司马相如、张衡等汉赋作家的赋中,骈丝俪片已然可见;延及魏之曹植,晋之成公绥、陆机、陶潜等人,骈赋规制初备;再到刘宋之谢灵运、谢惠连、鲍照、谢庄,骈赋茁壮成长,而至齐梁陈隋时期的沈约、谢脁、江淹、萧衍、庾信,骈赋全面成熟;庾信《哀江南赋》出,尊为骈赋典范。在这一嬗变历程中,永明年间声律运动的推行对于骈赋臻于成熟具有划时代意义。
以上从题材内容、创作主体和艺术手法三个层面论述了佛教对南北朝赋的影响,其实,佛教对南北朝赋体文学之熏染尚可从其他角度切入。此外,玄释合流对南北朝赋存有综合影响,在这一时期的赋坛之上,玄风佛影时常交织闪现。对此将另文专论。
收稿日期:2006-07-03
注释:
①据方立天考证,《隋志·集部》录梁武帝撰《净业赋》三卷,今已不全。又现存赋中,自“小人道长”至“各至权轴”的中间一段,系道宣所加。参阅方立天论文《梁武帝萧衍与佛教》(《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第194页).
②李颙,生平不详。严可均据《广弘明集》将此赋编于北魏高允《鹿苑赋》后。然,检《魏书》、《北史》,未见其人。疑此赋亦东晋李颙所作。东晋李颙,字长林,有赋论诔等文八篇,在《全晋文》卷五三。
③“郁”当作“囿”,据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广弘明集》卷三七改。
④程章灿《先唐赋存目考》辑录萧子晖《讲赋》。参见《魏晋南北朝赋史》附录二。
⑤《隋书·经籍志》列昙谛于慧远之前,《释文纪》有丘道护所作《昙谛诔》,以为义熙七年五月卒,春秋六十有五。道护与昙谛友善,必不有误。《高僧传》七《神僧传》三作宋元嘉末卒,恐未可据。《隋书·经籍志》将《昙谛集》、《丘道护集》皆列于晋,不列于宋,足以明之。
⑥曹道衡、沈玉成《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中华书局1996年出版,第329页)以为真观卒于隋炀帝大业十七年。大业年号凡14年,似笔误。疑为“七年”。
⑦晋刘敬述《异苑》卷五中说,曹植“尝登鱼山,闻岩岫有诵经声,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高僧传》卷十三重复这一传说并增重其贡献之分量,强调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此说可能出于附会,但却反映了“梵唱”本土化这一历史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