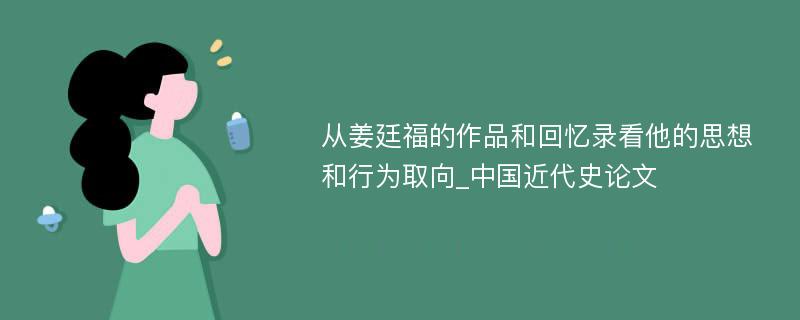
从著作和回忆录看蒋廷黻的思想和行为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忆录论文,取向论文,著作论文,思想论文,看蒋廷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9月,湖南岳麓书社在大陆出版了《蒋廷黻回忆录》(以下凡引此书,均迳称《回忆录》或仅注页码)。这部回忆录原是1965年蒋廷黻退休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口述实录,1979年曾由台湾传记出版社在台湾出版。尽管此番口述仅及抗战,以后诸事因蒋廷黻的突然去世而付之阙如,但由于蒋在中国现代政治史、思想史和外交史中的特殊地位,且他平时无论行文还是口述,都是删繁就简,句短言略,留下的东西不多,在大陆就更难得见到,所以,其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蒋廷黻初为学者,先后执教于南开和清华,以治外交史知名于世,编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卷)两册,治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外交史都是筚路蓝缕;以后,蒋廷黻以学者身份从政,他和地质学家翁文灏可以说是继另一地质学家丁文江之后自由派学者从政的典型。而正是1935年受蒋介石征召加入国民党系内阁以及入阁之前与胡适等人就“民主与独裁”展开了论争,使蒋廷黻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颇受争议。在笔者看来,这两件事不是孤立的有关蒋廷黻的私事,它反映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论认知状况和政治参与的方式。
一、学者参政:理想抑或现实
蒋廷黻被大陆史学界重新认识,缘于他那本《中国近代史》。此书初版于1938年。1987年在大陆重版,并编入湖南岳麓书社“旧籍新刊”中,以后,先后收入海南出版社的“人人袖珍文库”、上海书店“民国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出了新版。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篇幅很短的小书,在大陆中国近代史学界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被誉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注:见沈渭滨:《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载〔上海〕《复旦学报》1999年第4期。)。
蒋著《中国近代史》的特色,主要在于它的表述非常个性化,臧否人物,品评事件,一仍其所见。在他的书中,一切仿佛都是客体,他永远是站在超然的立场之上,所以他冷静,所以他的叙述和评论不失一针见血的锋芒。他的书中,没有绝对的英雄,也没有绝对的败类,林则徐可以批评,李鸿章可以表扬,全凭他们在当时当地的行为表现。这样看,个性化只是表象,理性化才是内在。
蒋廷黻的思想底色就是理性化。这首先与他接受西方教育比较早有关。据《蒋廷黻回忆录》记载,1906年11岁的蒋廷黻便进入湖南湘潭的长老会学校,期间深受美国传教士林格尔夫妇的影响,17岁赴美留学直至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在国外共计11年(其中在法国一年),如果加上国内的6年教会学校,所受的西方式的教育达17年之久。尽管蒋的朋友以及台湾的一些研究者,在分析蒋的思想时,多强调其中华性,强调其受到乡贤魏源以及曾国藩经世致用思想的薰陶(注:参见吴相湘:《蒋廷黻的志业》,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卷第6期,1965年12月1日。),甚至以蒋之湖南乡音始终未改,说英语时亦有湖南味来证明其思想和意识完全是中国的(注:参见吴相湘:《蒋廷黻学以致用》,载《民国百人传》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本,第259页。)。但这些研究、评价或回忆多是在台湾主流意识形态一直认同传统的语境下作出的,更多地还是出于同代人或后来者的“好意”。
蒋廷黻思想中的理性之所以很西方化,是因为他非常重视价值,与中国人之讲关系正好相对。重价值其实也是现代中国西化的自由派的共同取向。然而,蒋廷黻所秉承的价值和理性,均有自身的特点。这个特点在现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不能说是唯一,至少也是与众不同。
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都知道,新文化一代人曾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约定。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新青年》,有人希望他们直接批评现实政治,陈独秀的回答是“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注:1915年9月15日《答王庸工》,见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然而两年后,同样是读者要求谈时政,陈独秀的答复已经有所变化,他说:“愚非迷信政治万能者,且以为政治之为物,曾造成社会上无穷之罪恶。惟人类生活,既必经此阶级(即今之所说的阶段——引者),且今方在此阶级中,则政治不得不为人类生活重要部分之一。”而颇能反映前后反差的还是陈独秀所说“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注:以上均见1917年7月1日《答顾克刚》,同上书,第179-180页。)1932年,新文化的另一代表胡适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讲演时,谈到了他们践约的原因。他认为“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约定“不容易做得到”,原因是“我们虽抱定不谈政治的主张,政治却逼得我们不得不去谈它。”(注:《陈独秀与文学革命》,收入《胡适全集》第1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既然新文化一代人抱定不谈政治而不得不谈政治,甚至直接参与现实政治,那么,对政治有很大兴趣和相当研究的蒋廷黻的关心政治,进而参与现实政治,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蒋廷黻从政前,是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在清华,他与校长罗家伦是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倡导者,收集资料,锲而不舍;他也是典型的自由派,放言论政,毫无顾忌。据时任教清华大学且为《独立评论》同人的陈之迈说,蒋廷黻离开清华,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消息传出,“许多朋友劝他多多考虑是否应当接受。有的人对于政府‘求实’的诚意表示保留;有的人以为政治是污浊的,党同伐异,倾轧排挤,弄得不好会身败名裂,劝他不应跳入这个‘火坑’;有的人以为他应当保持学者清高的地位,以在野之身议论政事,鞭挞政府;更有人心存嫉妒而说出许多难听的话来”(注: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生平(六)》,载〔台北〕《传记文学》第9卷第2期,1966年8月1日。)。这“难听的话”当指“清华园太小了,他不会感觉过瘾的”之类的流言(注:参见吴相湘:《蒋廷黻的志业》,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卷第6期,1965年12月1日。)。但自由派以及《独立评论》同人中间的异议并没有想像得那么大。曾倡导“好人政府”的胡适虽一贯不干涉别人的选择,但在此问题上他还是寄予了希望的。在给蒋廷黻以及先期从政的翁文灏、吴景超的信中他引用了丁文江的诗《麻姑桥晚眺》作为寄语,诗的后两句是“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胡适期待他们做“‘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并希望他们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以教育和改造政府(注:见《胡适全集》第24卷,第288-289页。)。
就思想层面言,导致蒋廷黻同意入阁的原因就是上面提及的理性化。这个理性,与新文化一代有根本的区别。因为新文化一代本质上说都是理想主义者。陈独秀和李大钊虽然组建了共产党,倡导反帝反封建,但那是信仰使然,胡适论政,却不愿轻易从政(抗战时的驻美大使可以另当别论),也是出于自由主义理想。蒋廷黻1923年才回国,他不属于新文化一代,他也有理想,他的思想也是属于自由主义的,所以他与胡适等人一起创办《独立评论》,各自发表独立的见解。但与新文化一代相比,他实在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的理性也就是现实的理性。在《回忆录》里,蒋廷黻谈及他与胡适的分歧时,说胡适“对自由议会政府的想法太天真。”这个评价,不完全像蒋所解释的,是因为“胡适几乎忽略了经济问题。”而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是原则问题,乃是轻重缓急问题”(以上均见第147页),根本上说,体现的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分野。
蒋廷黻的现实主义理性,总体上看,是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蒋著《中国近代史》中论述国际关系的一段话,可以作为一个注脚。他写道:“国际关系不比私人间的关系,是不讲理,不论情的。国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结合为友,为联盟;利害冲突就成为对敌。”(注: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页。)当然,我们不能依此说法,来断定生活与朋友中的蒋廷黻就是专讲利益不顾情谊的人。因为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在蒋廷黻那里并不是一回事。蒋廷黻的现实主义理性是诉诸于公共领域的,这是他的职业理性,他的国家利益最大化也是在当时国际环境下,从民族利益出发的一种现实选择。
对政治感兴趣的人进入政府乃顺理成章,由书写历史到创造历史,往往容易志得意满,所以蒋廷黻终身不悔。这倒未必是传统的官本位在作怪,它与蒋廷黻对政治和知识分子的基本认知及其现实主义职业理性有很大的关系。1947年,蒋廷黻发表过一篇题为《漫谈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的专论,文中不仅论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特点和基本取向,而且自觉不自觉地为他这样的出仕的“士大夫”的行为方式进行了辩护。蒋廷黻写道:“谈政治,最忌凭空创设乌托邦或假定某一部分的人是天生圣贤。”在分析了中国的情况后,他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在于作官,教育官、行政官、事业官。名义虽不同,靠公家薪津吃饭则是一致的。所以在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是切身的。”他进一步指出,“事实虽是如此,知识分子却不肯充分承认。他们中间至今尚有人在作梦。一种梦是教育清高而作官不清高。另一种则以为惟独作官是光荣。其实教学可以清高,普通也是清高,但作官也可以清高,应该清高。作官可以得光荣,也可以不得光荣,并且教书,作工程师,行医,当律师,都是光荣的。”蒋廷黻最后的一段话,更值得玩味。他说:“中国官僚百分之九十来自知识界,却是知识分子最喜欢骂官僚。在朝的知识分子和在野的知识分子形成两个对垒。其实在朝的与在野的,无论在知识方面,或在道德方面,是不相上下的。”(注:以上均见蒋廷黻:《漫谈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南京〕《世纪评论》第1卷第24期,1947年6月14日。)
将知识分子与官员、在朝的学人与在野学人之间的隔断拆除,从主观上讲,自然是为了自身选择的辩解,但客观地看,却也不乏卓识。因为虽然二者社会角色不同,认识上和行为上会有明显的差异,但基本的道德要求却有着一致性。这似乎与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或依附性,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晚年蒋廷黻对此依然是坚信不疑。他在《回忆录》里说:“我对政治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认为政治并不是专为金钱和荣耀。对我说,政治只是一种工作,我认为它和教书一样的清高。”(第151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日渐严重也是催化剂,促使先前即有划分军阀等级的蒋廷黻做出选择(注:蒋廷黻在《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中就多次提到破坏统一的是“二等军阀”。载〔北平〕《独立评论》第83号,1933年12月31日。)。而此时在蒋廷黻眼里的“一等”军阀蒋介石正有组织专家内阁的设想,蒋廷黻受此礼贤征召,也正是机缘凑巧了。对蒋廷黻来说,这样的选择也符合“两害相较取其轻”的现实原则。
但应该看到,即使受召入阁以后,蒋廷黻在国民党政府任内,也还是把公共理性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1936年,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固然因时事所迫,且他对苏俄外交史有所研究,所以用其所长,但从《回忆录》看,也与他先前在行政院政务处长任上所推行的政府改革计划重实效而不重关系,得罪了某些当朝权贵有很大的关系。
尽管从1935年开始直至退休,蒋廷黻一直担任国民党政府公职,但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客。蒋廷黻的朋友自由派学者陈之迈从性格上着眼,以为蒋廷黻“可以做一个政治家,他绝不可能做一个政客。他有坚强的自信心,不敷衍、不苟且、不逢迎、不妥协,因此他在处事上开罪了不少人,使人一时不能了解他、原谅他。”(注:参见《蒋廷黻其人其事》,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卷第6期。)如果硬要给蒋廷黻定位的话,“技术型官员”(“行政官员”容易引起误解)也许比较合适。他自己似乎也无意成为政客,无意完全受意识形态的左右,这从他身居要职而一直未入国民党,或可得到佐证。而蒋介石本人似乎也无意要这类技术型官员(类似的还有翁文灏、蒋梦麟等)过多介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纷争,所以,蒋廷黻所任的职务,无论是行政院政务处长,还是驻外大使,与意识形态的联系都不是太紧密。
二、“新式独裁”论:学者的纸上谈兵
不能说,蒋廷黻与现代中国的自由派在一切问题上都有分歧,在“民主与独裁”论争前,他们的共同处远大于分歧。即使是以后发生了争论,彼此还是朋友,也还有共识。蒋廷黻1965年去世后,毛子水在纪念文章里披露,晚年蒋廷黻曾有与胡适共同组建一个新政党的意愿(注:毛子水:《蒋廷黻先生二三事》,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卷第6期。)。而就在蒋廷黻率先鼓吹“新式独裁”前几个月,即1933年4月,胡适还在《独立评论》第45号上为蒋廷黻《长期抵抗中如何运用国联与国际》一文所作的跋文中,大赞蒋对国际关系的分析以及中国对策的见解,且有英雄所见略同之叹(注:参见《跋蒋廷黻先生的论文》,载〔北平〕《独立评论》第45号,1933年4月9日,收入《胡适全集》筹21卷,第611-615页。)。
既往的研究中,对现代中国自由派中一些人出而鼓吹“新式独裁”的基本语境叙述得较全面的是美国学者易劳逸(Ltoyd E.Eastman),按照易劳逸的归纳,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拥有“双重遗产”,即专制的传统和20世纪初的民主主流;孙中山的早期民主信念和晚年的独裁倾向。而从当时的国际思潮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民主热情已经在战后面临“崩溃”(注:参见易劳逸:《流产的革命》中译本,陈红民等译,钱乘旦校,〔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176页。)。加上来自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威胁所引发的严重的民族危机,使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意识陡然增强。这些语境的影响都可以从当时鼓吹“新式独裁”的蒋廷黻、钱端升、丁文江的文章里找到。可以这样说,从近代以来,中国的任何思潮都以民族主义为其出发点或基础。丁文江、蒋廷黻、钱端升等自由派的“新式独裁”鼓吹自然也不例外。抽象地看,民主与独裁,孰是孰非,一目了然,丁、蒋、钱也不会等闲视之。但实际选择上,却远较理论为复杂。很显然,外在环境只是促发因素,真正的原因还要从他们对民主的基本认知以及自由派所处圈子的总体倾向中去寻找。
现代中国的自由派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虽然因人而异,但基本上是以承认其合法性为前提的。对政治不太关心,但隶属于胡适一派的历史学家顾颉刚的说法也许可以反映其中一部分人的心态。他在致胡适的信中称他本人“深感到国民党是一个有主义、有组织的政党,而国民党的主义是切中于救中国的”(注: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26页。)。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胡适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最为激烈,他从维护新文化运动基本价值的立场上,批评国民党的保守倾向,并把国民党排除在了新文化的统系之外(注:参见《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载《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1929年9月10日,收入《胡适全集》第21卷,第436-450页。)。尽管他的批评已经激烈到令国民党几乎无法容忍,不得不发出“警告”的地步,但基本倾向却还是属于建设性的。他也自认要做政府的“诤臣”和“诤友”(注:语见《致汪精卫(稿)》,1933年4月8日,《胡适全集》第24卷,第161页。)。而国民政府授权对胡适发出“警告”的正是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另一位自由派教育家蒋梦麟。正因为自由派的圈子里没有完全与政府势不两立的意识,像蒋廷黻这样的自由派学者就没有必要以鼓吹“新式独裁”为手段,标高以立异,曲意引起蒋介石及其政府注意,最终达到出仕做官的目的。
虽然说从近代以来,中国的任何思潮都以民族主义为其出发点或基础,但落实到每位历史人物身上,也有着相当的个体差异。蒋廷黻对民族主义的认识源于他长期所受的西方式的教育,其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老师海斯(Carlton J.H.Hayes)的思想对他也有直接的影响。蒋廷黻在研究院读书时海斯是他博士论文实际的指导教师,1930年他又将海氏的《族国主义论丛》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尽管直到晚年蒋廷黻还是坚持早期的观点,以为海斯对民族主义的批评不妥,因为“我们当代的中国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如果实行高度的民族主义,对中国人一定是有好处的”(回忆录,第83页),但海斯所倡导的国际交往的前提却是蒋廷黻坚守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个原则实际上摒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归纳起来说,就是在爱国主义的问题上,要相互理解;在国际交往上,要取得双赢;“总之,欲想建立新中国,中国人就必须吸收全世界的资源,精神方面的和物质方面的”(参见回忆录,第84页)。
开放的民族主义当然也还是民族主义,在外来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形下,蒋廷黻像许多知识界人士一样,对彼时中国现实的确显出了无奈和急迫。蒋廷黻在他第一次明确鼓吹“新式独裁”的文章《革命与专制》中对近代以来的诸次革命的失望情绪已经表露无遗。他说:“我们中国近二十年为革命而牺牲的生命财产,人民为革命所受的痛苦,谁能统计呢?”“在中国近年的革命,虽其目的十分纯洁,其自然的影响是国权和国土的丧失。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国的奢侈品。”(注:《革命与专制》,载《独立评沦》第80号,1933年12月10日。)但需要注意的是,蒋廷黻在这篇文章里所指责的“革命”也包括孙中山和国民党领导的革命,可见,他也还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发言的。
其实,蒋廷黻出于民族主义意识而产生的无奈和急迫心情,在半年前发表的另一篇文章《知识阶级与政治》(注:《知识阶级与政治》,载《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中已经显露,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在《知识阶级与政治》中,蒋廷黻是从救国的角度检讨知识阶级的政治参与问题的。他讨厌纯粹的武人政治,自然也看透了一些依附军阀的学者,他也反感知识界的一些人士越出自己知识的范围,又在完全不了解现实的情况下去任意发言,或任意以西方理论来界说中国问题。他称后一种情况为“口头洋”。然而也许是救国的意念过于急切,他几乎将知识分子特有的通过舆论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式全盘否定了。而他将近代以来国家出现的种种问题全归总到知识阶层身上,也未免过于绝对。但之所以会有此认识,还是和蒋廷黻所体会到的知识阶层在现实的民族危机面前的无力感有关。
对文人失去信心在常态社会可能只会导致检讨和批判文人的不足,但在危机时代就容易转而寄希望于武人。在一篇论述统一方法的文章里,蒋廷黻就认为“武力统一自较民意统一为优”,“较国民会议统一为优。”(注:见《统一方法的讨论》,载《现代评论》第65期,转引自文星杂志编委会:《蒋廷黻和他走的路》,〔台北〕《文星》第6卷12期,收入朱传誉主编:《蒋廷黻传记资料》(一),〔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影印本),第58页。)蒋廷黻将“国家统一”看作第一要务自然是为了抵御外侮。但从思想渊源看,它出自其老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家邓宁(William A.Dunning)的政治学理论。在邓宁看来,政治学的最终问题是政权的性质,“政治家的最终目的是保护政权”。由此,蒋廷黻得到的启发便是在最低限度的稳定都做不到的国家,“稳定政权、建立秩序乃是一国政治的基点”(《回忆录》,第79页)。有评论说,蒋的“新式独裁”论反映了他的“效率第一”的思想,“‘新式独裁’的重点似乎是效率第一的”(注:参见《蒋廷黻和他走的路》。)。但“讲效率”只是一种期冀,内心急迫才是原因。可与另两位“新式独裁”的鼓吹者钱端升、丁文江相比,蒋廷黻的急切心情还是收敛的。他所提倡的“新式独裁”也还是向自由主义过渡的一个特殊阶段,不像钱、丁,一旦论起来便有把“新式独裁”推向极致的味道(注:这一点钱端升更明显一些,他崇信的是德意式的“极权国家”(参见《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1日);而丁文江则比较偏重于渡过“空前的外患”和“不久或要遇上的经济恐慌”“这双重危机”(参见《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载〔北平〕《独立评论》第133号,1934年12月30日)。)。蒋廷黻在《回忆录》里所说的“我向《独立评论》的读者保证,尽管自由主义推行困难,有些地方不合时宜,但是最后胜利还是属于它的”(第177页)一段话并非是后来的辩词,因为就在当时,游历了俄、德等国,亲身体会了两种类型的独裁体制,但从他给胡适的信中看,他还是证明不了自己的鼓吹是否正当(注:参见《蒋廷黻致胡适》,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64页。)。
从对民主的认知上看,蒋廷黻这一代自由派大多是将民主诉求与民族富强联系在一起的。但不能因此而笼统地推论,民主既然是一种富强的手段,为了富强采取任何手段都是顺理成章。就蒋廷黻言,作为权宜之计而鼓吹的“新式独裁”论,也时时与他所信仰的自由主义发生着价值上的冲突。在《回忆录》里,蒋廷黻谈到了他的矛盾心态。他在实地观察了俄、德、英等国的现状后,以为:“纳粹的极权主义思想对我似乎太积极,相反,自由主义又太松懈。有一段时间,似乎全世界都倾向自由主义。……迨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人们突然认为自由主义是一个卑鄙的陷阱。”(第176-177页)彼时,欧美政治思潮的波动的确是影响到了一贯以西化为参照系的部分中国自由派成员的信心。但特定情形下的表现,也很难成为蒋廷黻一生的概括。后来蒋在《回忆录》里只字不提“民主与独裁”论战之事,而他的朋友陈之迈对此轻描淡写(注:《蒋廷黻的志事与生平(六)》,载〔台北〕《传记文学》第9卷第2期。),也多少说明了问题。
最后,不能不再提到蒋廷黻的现实理性。应该说,正是隐藏在民族主义意识背后的现实理性和他独有的思维方式直接引发了蒋对“新式独裁”的提倡。治外交史的蒋廷黻的研究思路从来都是现实化的。刘崇鋐关于蒋廷黻“是运用政治家头脑运用政治家远大计划来从事学问”(注:参见《蒋廷黻先生的治学与教学》,载〔台北〕《文星》第12卷第6期,收入《蒋廷黻传记资料》(一),第90页。)的说法,固然有些言辞上的夸张,但也有相当的道理。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蒋1931年所写《琦善与鸦片战争》与1938年所著的《中国近代史》对琦善和林则徐的评价“显然换了调”(注: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2页。)。而1931年,蒋廷黻正在主张和谈避日,1938年他当然已经是主战派的一员了。
现实状况影响学术研究,反过来说,学术研究也反作用于现实判断。在蒋廷黻1933~1935年发表的文章中,外交上的现实主义原则的影响可以说是随处显现。而典型者是《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一文。谈到国家统一,蒋廷黻说:“我们必须有一个中央政府。”“我只求中央能维治全国的大治安,换句话说,能取缔内战与内乱;……有了这样的政府,我以为我们的环境就自然而然的会现代化。”他之所以提倡“个人专制”,也是因为他“所提倡的是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这一些小专制。”(注:以上均见《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载《独立评论》第83号,1933年12月31日。)这正是上面提及的“两害相较取其轻”的现实理性。
蒋廷黻在他所提倡“新式独裁”的诸文中,始终没有明确谁是可以担负起统一使命的人和政党。但三十年代的现实大有“时不待我”之象,似乎无法重新选择,也无暇重新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从蒋廷黻的现实原则看,国民党和蒋介石当是首选。而如果按照蒋廷黻的思维逻辑推理,应该是这样:蒋介石及国民党的“统一”已经既成事实,如果取而代之,不仅暂无可能,即使有可能也必然要经过一场战争,现在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虽然不尽人意,但经历一场战争不仅于中国十分不利,其本身的代价也太大,就是战后成立的新政权是否随人所愿,也还是个未知数。因此,唯一的可能就是承认这个政府,并将作为过渡方式的“新式独裁”的权力赋予它。但让蒋廷黻没想到的是,这一过渡期太过漫长,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完结。
当然,“新式独裁”论也仅止是蒋廷黻等人的纸上谈兵,是他们所想象中的拯救国家和民族危机的良方。“民主与独裁”的论战,按胡适的说法,没有产生多少实际影响(注:胡适1934年日记中附录1935年1月2日所写《一九三四年的回忆》,其中说到“民治与独裁的讨论,继续了一年,没有多大影响。”参见《胡适全集》第32卷,第409页。),他之所以参与驳论,也主要是担心“其效果将有‘教猱升木’之患”(注:见1934年1月8日胡适日记,收入《胡适全集》第32卷,第265页。)。这一担忧到1934年底似乎又深了一层。在此时所写的《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一文中,胡适指出:“学者立言,为国家谋福,为生民立命,在这种紧要关头,是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岂但是‘教猱升木’,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注:载《独立评论》第133期,1934年12月30日。)。从以后的历史看,胡适的担心也未必全是杞人忧天。应该看到,学者所提出的重大政治主张,大多有纸上谈兵的特点,本身可能只是诉诸理想,未见得真要发挥多大的实际作用,蒋廷黻等人的“新式独裁”论虽极力咬定为现实服务,作现实抉择,但也不能脱此一路。前引蒋给胡适的信中,多少显露了这种纸上谈兵的心态(注:参见《蒋廷黻致胡适》,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364-265页。)。但问题是,学者之理论主张为政治势力所利用后,其效力往往不随人愿,结果亦很可能与初衷相违拗。这大约也是前人所谓“学者立言须谨慎”忠告的指向之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