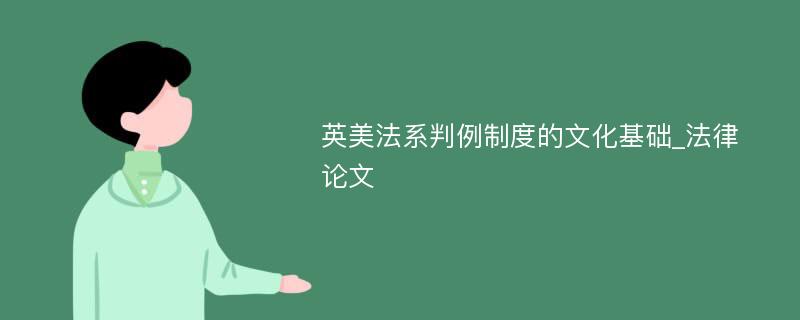
普通法系判例制度的文化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系论文,判例论文,制度论文,基础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3/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28(2006)06-0086-06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法律的文化从形式上也可以表现为三种形式:静态的法律制度、动态的法律行为、精神性的法律观念,笔者暂且将这第三种形式称为“法律文化”。①这也是对“法律文化”概念采用的最狭义的理解,它基本是与“法律制度”相对应的精神领域的上层建筑,是“共同制约法律制度并且决定法律制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地位的价值与观念”,②它涉及法律机构、人员和制度本身的内在观点的群体性的观念模式,体现了对法律态度、信仰、评价、思想和期待等方面的观念。关于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布莱克曾指出,“在文化稀少之处,法律亦少;而在文化丰富之处,法律亦繁荣。文化越多,法律也越多;法律的变化与文化成正比。”③可见,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是双向互动的关系,法律制度需要一定的文化依托,法律文化也成为法律制度的存在依据并引导法律制度的发展方向。作为判例制度运行的“软环境”的文化传统,笔者认为包括判例制度的基本法治理念基础、判例制度下人们的社会心理基础以及判例制度本身蕴涵的职业伦理基础,这三者又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整体上构成了判例制度运行的文化基础。
一、判例制度的法治理念基础
(一)法律神圣
孟德斯鸠认为:“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就是: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风俗、习惯。结果就在这里形成了一种一般的精神。”④孟德斯鸠的“一般精神”,其实指的是维持社会一般秩序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力量,其中社会规范在型构社会形态的样式及其决定其发展方向方面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作为秩序观念存在形式的规范不仅在习惯上被遵守,而且在内心深处被信仰,才能达成社会的整体性秩序。秩序的基本特征在于稳定性,任何社会的人们都采取“自己的”某种方式来实现稳定。而西方世界社会的“一般精神”是二元化的:即一个是宗教;一个是法律。二者的关系是:法律被当作宗教来信仰;宗教被当作内在的法律来遵行。“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它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他的信仰。”⑤在普通法领域,严格的诉讼程序、开放的陪审制度、抽象的法律符号足以使得法律在普通法国家成为人人得信仰的“法律宗教”。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法律的理想和人的意志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统一。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成为国家的治理模式,通过法律的交往行为成为个人的生活方式。这种信念的存在反过来又有助于法律秩序的建立,正如加塞特(J.Ortegay Gasset)所说的,“秩序并非一种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压力,而是一种从内部建立起来的平衡”。⑥
普通法系的判例制度是一项形式主义色彩浓厚的制度,烦琐的判例汇编、错综的备选判例使得这一制度实际运行起来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高效率。但是判例制度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遵循先例原则将使普通法对于任何一个进入这一领域的人都不偏不倚。在观念上,判例制度不被认为是令人头疼的繁缛末节,而恰恰是一个得到尊崇的创造。庞德认为,美国的“司法系统几乎将全部精力用于找出一个连贯的、具有逻辑性的、详细精密的判例体系。”⑦这样,法律的神圣不仅体现在法官通过神圣的仪式来创造法律,也体现在人们以神圣的心态来看待这一过程。如果说以弘扬个人主义为特征的早期清教传统在普通法中还留有余迹的话,那么判例制度通过对个案的尊重来体现对个人的尊重,使判例制度观念与法律神圣的理念相得益彰。作为判例制度的运行结果,“判例法是法官制定法,因此,往往融立法思想与法律规则于一炉,使得人们对法律制度背后的观念性东西一目了然。”⑧
(二)司法至上
普通法演进的历史表明,它是在司法实践中生存和发展的。因此法官不是议会法律的诠释者,而是制定法反倒成了法官判决的注疏。分权原则使立法和司法分别获得相对独立的空间,但是判例制度法官造法的理念使得司法权在普通法国家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与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的情况不同,在英国有一个真正的‘司法权’,就其重要性与地位的崇高讲,不下于立法权与行政权。……一个完全独立与高度受到尊重的司法权的存在,是英国各种制度充分发挥作用所必不可少的,为了这些制度的建立与巩固,法院在历史上曾作过有力的贡献。”⑨司法至上则表现为法院的独特地位和法官的受到极大的尊重。每当遇到重大的社会问题需要法官做出决断,大多数普通法国家(尤其在美国那样典型的三权分立国家)的法官都能挺身而出,做出毅然决然的司法判断,以至于有人对司法权在政治问题上的扩张趋势表示疑义,如在Webster v. Reproductive Healthy Services一案中,斯凯力(A·Scalia)大法官就提出法院不应该超出案件事实本身去回答任何宪法问题,这也从反面说明普通法国家司法优位的理念。
具体说来,普通法上一个重要的观念是认为真正的法律是通过判决被创造出来的,而实证主义者更进一步认为法律不过是对法院判决的预测。“如果所有的法律规则都包含以一种以不变形式在神圣的经文、十二铜表法、法典或公认的法令大全之中,或者包括在其原则被权威地证明为一个习惯法王国之中,那么,不仅在注疏的伪装之下通过推导和类推延伸必然遇到新的情况,而且所有法律的不可避免的变化也必定会隐藏在相同的伪装之下。”⑩在这样的传统下,司法判决是法律的出口,法律神圣的必然逻辑是对司法的重视,进而是对法院和法官的尊重。特别是在涉及基本人权和国家制度的重大问题上,法院和法官成为解决问题的焦点。如在美国影响深远的1973年罗伊判例问题、1984年焚烧国旗事件、2001年戈尔与小布什的总统竞选选票之争,都由我行我素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裁决而一锤定音。司法途径成为息事宁人的最终选择。至于解决社会冲突的过程,卡多佐法官指出,“法官作为社会中的法律和秩序之含义的解释者,就必须提供那些被忽略的因素,纠正那些不确定性,并通过自由决定的方法——‘科学的自由寻找’——使审判结果与正义相互和谐”(11)判例主义的方法是司法空间拓展的主要方式,在这里,法官凭借他们的经验和才智庖丁解牛般地处理案件。判例制度不仅在于确认每一个具体关系的属性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而且通过日积月累形成了判例法体系。
二、判例制度的社会心理基础
对法律制度来说,其获得持久的生命力的条件之一就是社会成员对于该制度有相应的社会体验和感受并持有一贯的、恒常性的心理倾向。任何良好法律制度都不可避免地在完善之中裹挟着不完善之处,这样面对判例制度的缝隙,普通法国家人们的普遍心态是宁愿接受错误和保持传统倾向。
(一)接受错误
判例制度在案件的判决结果上存在着一个悖论:遵循先例是避免错误的绝好方法,但是如果被遵循的先例本身是错误的或者一个正确的先例被合乎理由地规避,那么当前案件就有可能是延续错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前提是对法律问题是否有一个唯一正解的追问。在大陆法系国家,理性主义的传统决定了人们认为制定法提供了或能够提供正确的行为准则,法官是在狭小的空间里适用法律的,因此,犯错误的空间也同样狭小,而且所谓的“错误”通常是法官的错误而不是法律本身的错误,这样,法律问题的答案基本上是唯一的,“错误”应该很难出现。在普通法国家,其实也并非否认法律问题答案的唯一正确性,因为遵循先例原则本身就隐含着上级法院或自己已经做出的判决是正确的意味,但是这种“正确”的结论来自于程序上的拟制而未必是实质上的确认。这样,被识别为“正确”的判决往往由于某些情况的出现而成为“不正确”,这使得正确与否在很多时候具有不确定性。具体来看,判例制度运行的过程中,无论认为法官是在宣布法律还是制定法律,法官都成为获得法律文本的通道,法官的错误也就是法律的错误,而法官并非是一些永远不犯错误的人。而且,判例法是由判例形成的法律体系,一个后来被认为是错误的判例一旦被推翻,至少在观念上将产生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影响整个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因此,判例制度需要法官和公众对错误要保持适度的宽容。法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他认为是错误的判例而不能轻易推翻,公众需要理解法官坚持某些可容忍的错误的做法,并且不必要在“错误”发生的时候轻易对法律产生怀疑。由此看来,经验主义的判例制度在实现个别正义问题上的优势并不能掩盖其由于对逻辑的轻视和因具体争议问题的鲜明个性而在实现普遍正义上的不足,两种正义观念在某些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对判例的尊重就是对法律的尊重,错误的判例也往往需要被“模糊化”,这也是一种对错误能够接受的心理状态的体现。
当然,笔者并不认为也无意渲染判例制度是一项容易犯错误的制度。如果任何的判决都有一个唯一正解,那么大陆法法官犯错误的几率也许并不比普通法的法官少,只不过大陆法法官的错误很容易被一部部理性化的法典吸收了,而普通法法官的错误却为一个个判例轻易暴露出来。人们能够平静地接受这样的许多错误,这是判例制度的一个特色所在。
(二)传统倾向
大陆法是面向未来的,普通法却是面向过去。大陆法对人的行为模式进行普遍的概括,普通法却从传统中寻求法律的根源,“法律并非是一系列定型化的权威设定的明示规范,而是‘由传统、应用和经验流传下来’的隐含在一堆实践和实践观点的若干形式中的规则和方法”(12)普通法是历史的延续,法律规则的有效性和约束力不在于谁在什么时候创造了它,而在于它被实际上接受和证实。普通法的根源其实是习俗,而习俗只有在法院并且通过法院的活动才能获得法律的身份。这种法律不是纯理论化的,它们的实际创造者不是哲学家或理论家而是实践的法律从业者。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关注的是问题的解决而不是理论的阐述,因为法律的实践中往往并没产生这种具体的需要。因此,对普通法来说,“法律不是来自于规则,而是从既存的法律(即被确证的意见和决定)中获得规则”。(13)
总的说来,法律是传统的体现或者说法律代表了一种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法典法和判例法分别代表了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传统。“我们(普通法)法律传统的基本经验就是从特定例子的应用中得出一般性的结论。”(14)而笔者此处的“传统”的涵义是指一种回溯过去的倾向,它反映出一种对法律中的传统极度珍视的法律生活态度。英国法学家认为,“只有透过一个案件的事实,并缩小到解决一项纠纷所必要的范围,才有真正的法律规范”。(15)而“在一个普通法国家,对于不是来自判例的规定总认为是不完全正常的”。(16)在普通法中,不仅越是被认为是过去的传统的东西越受到尊重,而且传统成为现实存在形式,对现实的理解的前提是对传统的认识。而判例是法律的传统表现形式,是维系传统的纽带,也体现了传统的精神,正是传统才使法律得以延续并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因此,普通法下的人们对于他们的传统总是津津乐道,这使得直接面向传统的判例制度能够始终如一地运行,而大规模的法典化运动也必然屡屡受阻。同时,传统也深深影响着法官的行为,“一个有关人的明显而确凿的事实是,他们身处传统之中,并对传统做出回应,特别是对他们一直以来就研习的技艺的传统更是如此。传统控制、塑造、限制和指引他们;我们可以不为什么就谈到比如工作或思想的根深蒂固的方式,经验丰富或是定型僵化的人们,思维的习惯。而且,传统还将这些影响强加于人们身上……”(17)卢埃林认为,美国上诉法院的法官们首先是活生生的人,传统对普通法的法官是最重要的“现实”,因为法官的现实处境是要做出不脱离传统的判决。
三、判例制度的职业伦理基础
在普通法上,法律活动具有鲜明的职业性,它的运行是一个职业共同体的行为过程。这一职业价值意义上的伦理性在于实现正义,其过程的伦理性在于行动的合理性、健全的判断力。普通法的判例制度通过司法过程中行为选择的合理性来实现法律的最终目标,行为的合理性要求“选择行为时,能够用适当的方式,使目的、手段、对象、时间、地点等行为的契机,在同状况的相互关系中统一起来,并使之与行为的人伦性一起作为行为的伦理性。”(18)判例制度的职业伦理体现为采用其特有行为方式,伴随独到的精神气质来实现具体的“善”。
(一)保守与创造之间
普通法的事业是保守的事业,普通法的判例制度同样具有保守性。制度的保守性首先来自于人的保守性,“英国法官都无一例外地具有‘保守’的倾向,心理学家可能会说:从事法律职业的年轻人都具有墨守成规的陋习,总是津津乐道于既定的规则。他们都是现行体制的坚决维护者,而非改变这种体制的激进派。……这便使得英国法官远离了社会的主流,担任法官的时间越长,便越有可能脱离常人所面临的问题。”(19)保守性体现为对历史的态度、对变化的态度、对法律的态度。由判例制度所产生的判例法本身就是历史的积淀,因此从历史中去寻找答案是判例制度的基本方式。法律自身以及司法判决是面向过去,而不是欲说未来,固然判例制度使得当前的判决对未来案件具有拘束力,但是任何一个法官在做出判决时的基本出发点是为当前案件提出一个具有正义性的解决方案。正是通过个别具有时代精神的法官的判决,法律得到发展,这样“无心插柳柳成荫”。拉德布鲁赫认为,法律的安定性优于正义性。那么如何实现法律的安定性?普通法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法典,因此,只能在法律的动态发展中实现稳定,而判例制度使这种要求成为可能。保守意味着对激烈的变化持克制的态度,试想,如果先例常常被轻而易举地推翻,那么判例制度其实也就不存在了。标新立异并不是普通法法官的风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判例法体系内部的动态稳定。
需要指出的是,保守不等于僵化。保守倾向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对既定法律的认可。卡多佐大法官认为,判例制度是一项可以让普通法的法官流芳百世的事业。法官只有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才能促进普通法的发展。普通法的许多原则的产生,正是一些伟大的法官顺应时代的要求,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法律结论。面对法律的缝隙之处,即便存在制定法,也要求发展法官的创造空间,正如丹宁勋爵所说:“法官应该向自己提出这么个问题:如果立法者自己偶然遇到法律织物上的这种皱折,他们会怎样把它弄平呢?很简单,法官必须像立法者们那样去做。一个法官绝不可以改变法律织物的编织材料,但是他可以,也应该把皱折熨平。”(20)实际上,普通法的法官往往就是在保守的情绪下发挥其创造精神的,如在Michael David Jaensch v.Vicki Lorraine Coffey((1984)155 CLR 549)一案中,考菲太太的丈夫发生了交通事故,在事故发生的稍后,这位太太在医院看到丈夫的痛苦状态并且受到极大的刺激,以遭受精神损害要求被告予以赔偿。以往很多先例都判决,被告对他人造成人身伤害后,被害人的亲属因为出现在现场目睹被害人的惨痛情景而受到精神损害的,被告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先例使考菲太太存在因为不是在“当场”受到刺激而得不到赔偿可能,而这对她来说是不公平的。审理本案的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布莱能大法官认为,并不存在要依据先例而区分有关刺激是在医院里还是在马路上发生的特殊原则。他果断地对被告的上诉予以驳回。这并非是一个特例,在很多情况下普通法的法官们并非一味墨守成规,而是经常能够在先例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法律的原则,创造体现时代精神的规则。这反映出普通法的法官们在保守与创造之间进行的既维系又超越的尝试,同时也成为判例制度的基本存在方式。
(二)贵族传统
“贵族精神既然崇尚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首创精神,就本能地拒绝接受固定、刻板、统一的行为规范的制约。这就使贵族精神天然地喜欢判例法而讨厌成文法。在贵族法官心中,人是法的主人而不是法的奴仆。一个具有独立判断能力和创造性精神的贵族法官,宁愿运用自己的良心智慧和经验,经过苦心熟虑对哪怕是十分疑难的案件做出令人信服的裁断,而不愿意像成文法时代的执法之吏那样,把案情和法条排在一起,像做加法一样容易地得出结论。”(21)这种太白遗风在中华法系中的痕迹已经让人难以捉摸了,但是对于普通法的法官职业来说,却是真实、现实、确实的写照。早在1834年,托克维尔就指出:“如果人们问我美国贵族在什么地方,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贵族就在法院和律师界。”(22)这里的贵族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仅是指普通法法官的地位,而在更大程度上是指法官群体的整体精神气质。古往今来,正是爱德华·柯克爵士、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曼斯菲尔德勋爵这些著名的法官通过对法律的解释为法律改革铺平了道路,同时也形成自己独特的判案风格:写作的风格、讲演的风格和做出判决的风格。那么什么是普通法的贵族传统?笔者认为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美德、超脱、自主。如果说司法独立在政治体制上为法官的职务行使设置了屏障,那么普通法的职业传统则在精神领域培育出了法官贵族气质,使法官的职业行为进一步神圣化。法官的职业是追求正义、张扬美德,做到这点的前提是法官要具有美德。不过,贵族的传统是以家族为单位而具有的超越平民家族体系的文化底蕴,普通法则以法官的职业群体为单位,尽管法官来自不同的阶层(当然大部分亦是社会的有产者阶层),但是在这一职业团体的内部却整合成一个“法律家族”,他们以落实人间的正义为圭臬,用另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考虑社会问题,划清了正义和非正义的界限,成为正义和法律的化身。同时,“英国的审判制度仰仗于社会对司法的尊重,仰仗于司法的独立性和整体性。在某种程度上,这就要求法官有不同于一般人的尊严,在言行方面,法官必须谨小慎微,适当节制”。(23)而实际上,贵族化的精神传统使得普通法的法官能够超然于一般的社会事务,而专心于他们的法律创造活动,在那个自由的空间里,没有人能够无端地涉足,法官在象牙塔中以判例为基石营造了他们引以自豪的普通法。他们使法律成为贵族化的事业,这样的法律又反过来服务于所有的民众。
注释:
①张文显教授在《法哲学范畴研究》一书中提到关于法律文化的解释或定义有5类,并指出:“法律文化没有先验的内涵,其意义是给定的。但是,给予法律文化什么释义,则取决于研究者的认识和理论前提,特别是研究者为自己的工作设定的价值目标。”(见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页。)笔者此处主要着眼于对与法律制度相对应并对法律制度有深刻影响的思想上层建筑而言,关于“法律文化”的认识也未必科学,这样解释的目的在于研究判例制度的精神方面的基础条件。
②L.Friedman,Legal Cul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Law and Society Review,6(1969),p.19.转引自[美]H·W·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M],贺卫方、高鸿钧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③[美]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M],唐越、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④[法]孟德斯鸠:《沦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5页。
⑤[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8页。
⑥转引自[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3页。
⑦[美]罗斯科·庞德:《普通法的精神》[M],唐前宏、廖湘文、高雪原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
⑧张乃根:《论西方法的精神—一个比较法的初步研究》[J],《比较法研究》1996年第1期,第19页。
⑨[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M],漆竹生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385页。
⑩同前注[7],第120页。
(11)[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6页。
(12)Gerald J.Postema,Philosophy of Common Law,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of Law,edited by Jules Coleman and Scott Shapiro,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590.
(13)同前注(12),p.597.
(14)[美]卡尔·N·卢埃林:《普通法传统》[M],陈绪刚、史大晓、仝宗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15)同前注⑨,第396页。
(16)同前注⑨,第462页。
(17)同前注(14),第59页。
(18)[日]小仓志祥:《伦理学概论》[M],吴潜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页。
(19)[英]马塞尔·柏宁斯、克莱尔·戴尔:《英国的法官》[J],李浩译,《现代法学》1997年第2期,第107页。
(20)[英]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M],杨百揆、刘庸安、丁健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21)武树臣:《贵族精神与判例法传统》[EB/OL],http://www.chinalawinfo.com/research/academy/details.asp?lid=1175。
(22)陈力铭:《对中国建立判例制度的探讨》[A],江平:《比较法在中国》(第二卷)[C],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