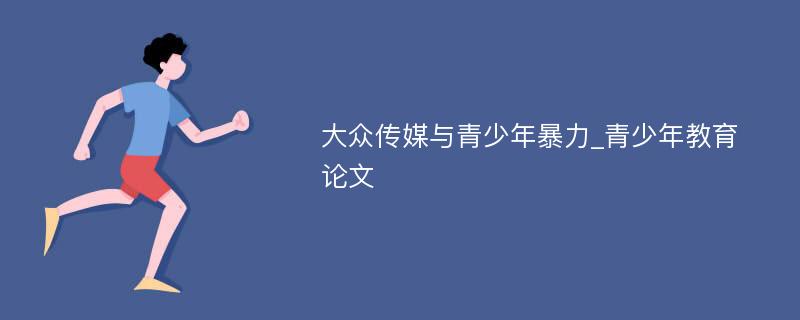
大众媒体与青少年暴力行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青少年论文,暴力行为论文,媒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众媒体,包括电视、电影、广播及报纸、杂志,其传播内容完全足以影响整个社会,并对该社会的国民行为起着不可低估的重塑作用,这似乎已经成为国际理论界一个无须再争论的公认事实。然而,长期以来,犯罪社会学界最具争议性的问题则是,大众媒体有关暴力行为的渲染和过度报导,是否会对其国民,特别是对其国民中的青少年群体产生影响,从而导致其行为变异,使暴力犯罪率上升呢?
部分持“媒体暴力无害论”的学者认为,青少年暴力行为的出现是一个涉及到多种变量的复杂问题,单单将大众媒体视作暴力产生的源泉不仅有失公允,而且还有寻找替罪羊之嫌。青少年任何行为的产生均与其生理、心理和外部社会环境有关,单一的某种因素是不可能起决定作用的。虽然这些人也承认攻击性行为是经由模仿而习得的,但他们却认为这一些并不十分重要,因为与其他相关因素相比,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持这种观点的人甚至认为,媒体对暴力行为的渲染只会对情绪异常者发生作用,而对那些人格健全的青少年,对暴力行为的了解却不会引起他们的行为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观点是以一个无根据的结论为基础的,即暴力行为仅仅是个体情感异常的产物。然而,众所周知,犯罪性的暴力行为并非是由内部病理所引发的病态行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不管青少年的人格如何,导致他们实施暴力行为的真正原因并非情感失常,而是对暴力行为的模仿和认同。对于那些采用暴力行为的青少年,实施暴力是希望通过暴力手段使他人屈服,从而让自己获得某种心理和物质的满足。虽然青少年的暴力行为并非由单一的因素所决定,但大众媒体的影响无疑十分巨大。在现代社会之中,大众媒体对青少年的教育作用显而易见,通过媒体对信息的传播,青少年可以受到许多正面影响,他们不仅可以增长知识,学习技能,而且还可以确立正确的思想和道德观念,以指导自己的生活实践。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随着媒体普及程度的加深和传播面的扩大,媒体已深入青少年生活的各个领域,改变着青少年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因此,既然媒体能将积极的正面行为灌输给青少年,那么,有何理由认为,媒体所传播的负面信息,如暴力,色情和攻击性行为就不会对他们产生消极影响呢?
事实上,媒体传播与青少年暴力行为之间,的确有着一定的潜在联系。早在1890年电报首次出现之时,法国社会学家塔德就曾意识到,犯罪行为会随着这种新型的信息传输方式扩散,以至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犯罪率。塔德认为,犯罪行为是随着电报线路传播的,向公众公布暴力会使部分人重复暴力行为,使犯罪行为向着更广泛的层面蔓延。从本纪世60年代开始,无数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又对影视暴力及青少年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过较为系统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影视暴力与青少年攻击性行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例如,从1969年开始,美国影视及社会行为科学顾问委员会就曾耗费巨资对影视与青少年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为期10年的跟踪研究,研究对象涉及世界几十个民族中的10多万青少年,相关课题一共23个,研究内容为影视内容,青少年特点,暴力行为对青少年态度,行为、道德的潜在影响等等,大量事实表明,影视暴力对青少年的行为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他们在与人相处时易出现非友善的攻击性行为。研究还指出,青少年喜欢的影视节目与其闹事行为有关,三年级男孩对暴力节目的偏爱与他10年后的犯罪行为有着极高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幼年时所观看的暴力镜头,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产生有很大影响。
那么,为什么大众媒体对暴力的渲染会对青少年的行为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呢?归纳起来,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原因之一:青少年期是个体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特殊时期。在这一阶段中,个体在生理和心理上迅速发展。一方面,由于他们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迫切希望获得新知识,了解新信息,成为社会所认同的一员。因此,他们很可能成为影、视、广播及报刊最大的受众群体,充当所有媒体最热心的读者、听众和观众。媒体所传播的信息无疑会对他们产生极大影响,成为导向他们思想和行为的一股无形力量。然而,另一方面,由于青少年人生经历太短,是非观念比较模糊,加之自我控制机制的建立尚不够完善,因而容易受媒体传播的负性信息,例如暴力和攻击性行为的影响,错误地将暴力视作可接受的行为模式。当然,对媒体传播的任何信息,多数青少年不会不加思索地全盘接受,他们会认真加以识别、选择,然后再决定其取舍。对于那些粗制滥造、明显让人反感或由反面人物实施的暴力行为,多数青少年会断然拒绝接受,更不会对其加以仿效。但是,那些由所谓英雄人物或由青少年所崇拜的明星角色所表现的暴力行为,却比较容易为青少年所认同,并有意或无意在现实生活中重复。换言之,由英雄人物或明星角色所实施的暴力会变得合法化,很可能为青少年学习、模仿。部分人甚至会将暴力视作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在现实生活中反复使用。
原因之二:有关研究表明,对暴力的过渡渲染会滋生新的暴力现象,提高青少年对暴力的适应度并引发更多的暴力行为。暴力滋生暴力的观点是70年代中期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托马斯·霍滕等人提出来的。托氏及其同事通过对青少年行为的大量研究,认为不断接触暴力信息,会使青少年对现实生活中的暴力现象反应迟钝,增加他们对该现象的忍耐度。对暴力忍耐度的提高会改变他们的观念和行为,使他们将暴力视作可接受的行为模式。托氏等人还认为,经常接触媒体暴力会减少青少年以前对暴力现象耳闻目睹时的焦虑感,使他们对暴力行为产生适应和习惯的感觉。因此,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面临暴力情境之时,他们不仅不会产生激动情绪和抑制动机,反而会产生司空见惯和麻木不仁的态度。不仅如此,与暴力信息频繁接触者在现实生活中会比不常接触暴力信息的青少年暴力冲动更多,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也会更多地选择暴力手段。换言之,暴力信息的经常接受不仅会降低青少年对现实暴力的敏感程度,而且还可能改变青少年的态度和行为,滋生更多的暴力现象。托氏等人还对青少年进行过一次情绪唤起的对比试验。他们将参加试验的青少年分为两组,一组观看暴力电视,另一组观看会令其兴奋但没有暴力行为的电视。电视节目结束后,他们又让被试者观看了现实生活中的暴力行为,然后再对其进行生理测量。结果表明,与观看令人兴奋,但不含暴力行为节目的青少年相比,观看暴力电视的青少年在目睹现实暴力之后的情绪唤起水平较低。该项研究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接触暴力会使暴力行为的情绪唤起迟钝,从而使暴力成为可以接受的行为模式。
近年来社会心理学家们认为,暴力不仅可以滋生暴力,而且,暴力行为还可以传播、扩散;一个地方的暴力行为会波及移动到其他地方,引起相似的攻击性行为的产生。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伯克维茨曾对美国联邦调查局统计的犯罪案件进行过研究,他发现60年代初发生的几起具有哄动效应的暴力案件(如肯尼迪谋杀案、理查斯皮克系列谋杀案、惠特曼袭击案)与60年代中期全美暴力案件的剧增有关。伯氏抽取了全美40个城市1960~1966年间暴力犯罪的统计数据,发现在以上案件发生的前3年,即1960~1963年的各日中,40个城市的暴力犯罪率均低于1960~1966年间各日犯罪的平均数。而在以上重大案件发生之后,40个城市的暴力犯罪率均有所增加。特别是案件发生后的第二、三个月,所有城市的暴力犯罪案件剧增,以至形成了一个暂时的暴力犯罪高峰。因此,伯氏得出结论:暴力犯罪的增加与暴力事件的发生及媒体的广泛报导有关,过分渲染会使暴力扩散,最终导致暴力行为的增多。
原因之三:暴力行为是一种习得性行为,是经由模仿、学习过程获得的一种后天行为。而大众媒体则是当今青少年行为习得的主要途径,媒体所传播的信息,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均有可能为青少年所接受,并经由学习、模仿内化为其行为机制的一部分。众所周知,个人行为的习得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个体的直接体验,二是通过间接方式获得。在第一种情况下,个体会以不同的行为方式应付所面临的各种情境,如果行为结果是圆满的或是令人感到愉快的,个体则可能从中获得某种经验和知识,并在相同的情况下重复这一行为模式。相反,如果行为结果令其失望或感到不满,个体则会从中汲取教训,并不再重复这一行为。但是,在现实生活之中,个体没有必要必须事事亲身经历,他们可以找到替代性的学习途径,从他人经验或媒体信息中间接获得所需要的知识。在现代社会之中,大众媒体无疑是青少年间接学习知识的最重要途径,它所传播的信息对青少年知识的积累起着极重要的作用。由于青少年时期是学习社会知识和社会规范的主要时期,青少年比任何年龄段的群体受媒体教化的机率更高,媒体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也更大。媒体扩散的正性信息有利于青少年身心的发展,会对其产生良好而积极的影响,而媒体对暴力行为的不适当报导却会在青少年中形成模仿效应,让青少年不知不觉地习得暴力行为。社会心理学家班图拉认为,青少年的暴力行为是通过模仿机制而习得的,而其学习榜样的提供既包括实体性的,也包括象征性的。象征性的榜样即通过影、视、录像、文字和口述所提供的学习内容。与实体性的学习榜样相比,后者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前者。按照班氏的观点,只要观察学习榜样的青少年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榜样所提供的攻击性行为就有可能被习得。尽管青少年所习得的攻击性行为不一定会马上表现出来,但个体对攻击性行为的学习机制已经产生,因此,一旦青少年遇到挫折或产生愤怒情绪,其攻击性情感很可能被唤起,从而使他们从媒体中模仿、学习的暴力行为在现实生活中重演。
原因之四:媒体暴力可能成为青少年攻击性行为产生的情境线索,导致青少年攻击性行为的条件反射。社会心理学的观点认为,青少年攻击性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遭受挫折后形成的巨大愤怒感。一般说来,当个体有目的的活动受到阻挠时,即会产生一种受挫心理,而如果个体将其挫折原因归之于外部环境或他人的蓄意破坏而不作内在归因时,他们很可能会产生一种愤怒感觉,这种愤怒感会成为暴力行为发生的中介,最终使部分人实施攻击性行为。按照社会心理学家巴伦的观点,让已经具有潜在愤怒意识的青少年观看影视暴力,会增长他们实施攻击性行为的可能性。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青少年的攻击性行为尤如对情境刺激的一种条件反射,影视暴力的刺激会煽起个体已准备好的攻击性情绪。换言之,如果某一已经具备了愤怒的个体缺乏唤起其攻击性行为的环境线索,其攻击行为不一定会得以实施。但是,如果其愤怒反应恰好与类似的情境刺激相结合,即会强化其攻击意向,促进或助长其暴力行为的实施。有关研究表明,青少年暴力冲动情绪的唤起在很大程度上受情绪线索的影响,甚至被认为是情境线索的条件反应。遭受挫折产生愤怒情感的青少年,其愤怒感会与影视情境相结合,从而产生强烈攻击动机,催化其暴力行为。
不仅如此,大量的犯罪调查和个案研究还发现,在实施暴力犯罪的青少年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犯罪技术和犯罪手段来自于大众媒体所传播的信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大众媒体所传播的信息一经扩散,就会被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兴趣爱好和不同收视动机的受众有选择地加以接受,并在他们中产生不同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反应。一般说来,正常的青少年在收受某一特定信息时,其注意力大部分集中在对信息内容和意义的了解上,而具有暴力犯罪倾向者则会对其中的攻击性情节、手段、作案工具和作案技术特别敏感,以至印象深刻地留下特别记忆,并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重复这类情节。由于大众媒体具有效果增强和意境创造的作用,因此,在青少年对某一问题了解甚少或态度暧昧的情况下,媒体所扩散的有关信息尤其会促进其态度的形成,并直接或间接地左右青少年的行为。
笔者认为,要使媒体对暴力的报导不至产生消极后果,首先对暴力行为的报导和描述必须正确、适度。假如暴力行为是作为一种在道德上应受惩罚或在法律上必须付出昂贵代价的形式出现的,那么,当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诱惑时,青少年也许不会模仿其攻击性手段。然而,对媒体信息,特别是对影视节目的分析表明,暴力行为通常是作为一种被容忍的,甚至正面的英雄行为出现的。即使在部分节目中实施暴力的是反面人物,但对他们的惩罚也显得过于软弱,实施暴力者比不使用暴力者生活得更好,只在剧终时他们才会受到惩罚。换言之,在节目中,对实施暴力者的回报或奖赏及时而慷慨,对他们的惩罚却显得迟缓或根本不存在。节目并未反映出“犯罪的代价是法律的严惩”这一主题。相反,实施暴力者反而趾高气扬或成了不败的英雄。然而,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这类节目非常有助于青少年暴力行为的习得,因为及时的奖励无疑对行为是一种有效的强化,而拖沓的惩罚却会使铤而走险者认为此类行为值得一试。因此,为了净化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媒体对暴力行为应作适度报导。对于一些暴力镜头过多的影视片,播放前应预先提出警示,公布其暴力行为的数量、内容、节目各称、播映时间及频道、影院,以便青少年有选择地观看。
当然,如前所述,青少年攻击性行为的产生原因非常复杂,并非完全源于媒体对有关信息的渲染、报导。但是,媒体暴力信息的过度扩散毕竟是引发青少年攻击行为的重要原因,它不可否认地对青少年的行为有着潜在影响,会直接或间接地让青少年习得暴力行为。因此,为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防止青少年暴力犯罪率的增高,有关方面应促成媒体改进其暴力行为的报导方式,限制那些肆意渲染暴力行为的文化产品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