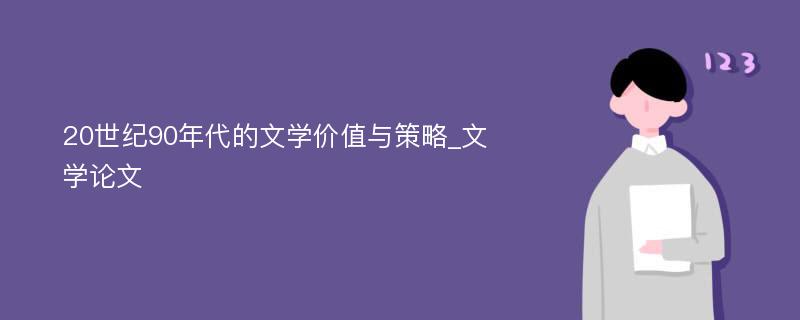
九○年代的文学价值和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策略论文,价值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间:1994年6月10日
地点:北京建内5号社科院文学所
李洁非:1985年以来,有一类话题,是文学界越来越少谈及了,也许还可以说,有点不肯谈及,似乎这类话题业已死去。比如说,文学和社会的关系,文学能否或应否有助于社会,特别是文学的人本主义(相对于这些年比较热闹的“文本主义”)和人格、良知对于文学的意义,等等。但是,自去年以来,情况正在改变,一些人士通过他们的文章开始重新看待这些问题。究其原因,倒也是迫于社会本身的跌宕和变异,终于使得一部分有责任感的人文知识分子“潇洒”不下去,而不得不去关心社会,重新思考文学价值体系的完整含义。那么,社会现实究竟是怎样触动了文学?当前文学创作与现实的差距究竟体现在哪里,以及文学又该如何来对当下中国做出它的反应?这正是我们亟待探讨和解决的一些问题。今天在座的诸位,有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也有从事纯理论研究的,正好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就此发表见解。
张德祥:现在流行着一种说法──我们的社会正处在“转型期”。“转型期”的概括,既准确,又模糊,“准确”的是原来的价值体系,原来的格局被打破了;“模糊”的是要往哪里转?似乎是要转向“市场经济”,但又不尽然,因为人们对于“明天”心里越来越没底,由困惑、迷惘到失落,尤其是精神的失落,没有了寄托,因此,只能拼命地抓住“现在”,抓住“当下”,而“当下”能抓住的唯有“钱”,唯有用钱来“消费”。挣钱与花钱,成了人的全部意义。之所以失去了“明天”的关怀,还在于“当下”的失落,其核心是“道德”的失落。田中禾的《枸桃树》里的主人公说:“日子好像到了头一样让人凄凄惶惶。”道德沦丧,人与社会的腐败是不言而喻的,精神价值寄托转化为肉体快感享乐,物欲和情欲在最本能的意义上膨胀和泛滥,拜金主义和及时行乐淹没了良知而激发了兽性。也许是时间与社会的宿命般的巧遇,没有哪个概念能比“世纪末”更准确地概括出“当下”的社会特征,亦即一种放逐了道德良知和人欲疯狂,“过把瘾就死”!
面对这样的现实,文学的价值选择,一方面关系到怎样理解中国社会的“转型”以及这种“转型”的历史走向,另一方面,更关系到怎样理解文学的价值和走向。
许明:我是主张重塑“偶像”的。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人的本性当中有宗教神性的一面,有了这,才有几千年的宗教史与精神发展史。一个缺少精神的时代无论如何从何种角度讲都是荒谬的。这种时代只能产生“癫狂”而不诞生“文明”。我承认,由于中国近代以来的特殊的历史际遇,使得这种历史要求若隐若现,使得担负社会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变得猥琐和平面。西方社会学家所关注的“进步”引起的人的精神的贫乏与感觉的退纯,正在我们这里以沙漠化的速度演进。产生不了大作,是因为没有大贤;没有震撼力,是因为良知的麻木和理性的丧失。
人文知识分子应当在任何历史条件下,前导和创造精神发展的历史,而不是仅仅顺适社会潮流。当有人以过来人、聪明人的口吻说现在已经是什么“潮流”了的时候,我正在默默地回想写出了《罗亭》、《悬崖》、《卡拉玛卓夫兄弟》、《安娜·卡列尼娜》等巨作的俄罗斯文学的世界时代。沙俄时代的外在条件的困顿与在这种条件下生存和为俄罗斯命运奋斗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令人崇敬,那些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流放地仍在讨论着黑格尔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面临着社会和文化的转型,同样面临着新的历史前景的创造,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格局是否该大些、该强些呢?
钱竞:这几年,离当下的文坛远了。不知是自己冷淡了文学,还是文学疏远了自己。只是,也还算名义上搞文学的人,才和当代作品保留着若即若离的联系。要说对这些作品的感受,也许只有三个字:无所谓。恐怕是再也没有激动可言了。回想起来,自己曾把文学阅读作为生命的不可缺少的部分。《牛虻》激动过我,《马丁·伊登》令我振奋,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浩瀚中领略了什么是崇高,从欧·亨利的短篇中得到了无穷的欢笑。这大约是60年代文学读者的共同的阅读经历。
至于这几年,则判然有别,甚至缺少了当初看到“新时期文学”创作的那种久失而复得的欣喜体验。声势浩大的陕军东征,对我并没有带来广告式批评所宣布的那种轰动效应。至于那些以调侃、戏拟,拿无聊当有趣的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作家们,时兴当令并不真正证明他们的强有力。在消解权威与神圣的时候无意中也消解了自己,搞不好,自己反而沦落为弄臣、优伶──在当今文化市场上供人消遣作乐的丑角。是不是文学的创作和批评都莫名其妙地进入了“失重”的状态?我想,尽管这些作家扮演的角色和作品的挡次有所不同,而导因则是一致的。这便是几年来人文界及其工作者心灵中的价值资源的枯竭。自以为摆脱了责任,纵情于游戏,可以宣称世事与我无关涉,而实际上只能促使原来完全枯竭的更枯竭,尚未崩塌的化作一阵泥石流。
李洁非:作为当代文学创作的观察者,除了肯定它经过10余年的探索而在艺术表现能力和方式上取得某些进展的同时,我的不满和忧虑在于,它同我们的现实、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公众(同时也是我们的读者)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深深陷入某种偏狭、呆滞、空虚的境地。关于这一切,此地我显然不能展开来谈,不过,提到以下一种现象应该说也就足以说明许多其他的相关问题了,这个现象就是我曾经在一篇题为《“当代”小说重“历史”》的文章中谈到过的:当前文坛上许许多多最有才华的作家,都丧失了表现当代生活的兴趣,也丧失了这种能力,而把他们的聪明才智纷纷投入到历史题材创作之中,远及唐宋,最近的年代也是在民国。他们特别热衷于家世小说,对旧式簪缨之家的兴衰枯荣、妻妾争宠这类故事爱不释手,或者,是对发生在后宫的权力倾轧、秽闻丑行、恩恩怨怨玩味再三,以至于发生了几个作家为著同一个题材撞车的事情。我还听说,有些作家现在专门到书肆搜求那些逸闻野史一类的书籍,从中寻求创作灵感,编造作品。如果只是有个别或极少数以历史题材创作见长的作家这样做,例如法国的特罗亚和台湾的高阳那样,我并不会感到有何异常之处,但是,很明显,在我们这里这种做法却是一股风,是一种普遍的趣好,以至评论界不得不为之起一个名称“新历史小说”。
张德祥:面对现实,文学应当怎样?这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学是没有逃路的。是合着“潮流”推波助澜,还是对现实作道德批判?文学的价值支点应当建立在媚俗的欲望挑逗上,还是应当建立在人的精神、人格关怀上?是认同“末日”的情绪,还是反抗这种情绪?
李洁非:我认为,文学创作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失衡,显然是跟这些年文学的价值观念上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加以排斥分不开的。我们知道,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排斥,理由在于,八十年代中期许多人认为社会层面的因素是非文学的,与文学的艺术属性无关,或者说不能在美学方面有益于文学。基于中国当代文学前40年的负面事实,人们很自然地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一逻辑──问题就在这里,实际上,当我们将社会学及其相关的字眼从文学辞典中剔除出去时,我们并不是处在无利害的科学的心境之中,相反,我们心中残留着过去的经历形成的某种恐惧,于是像是躲避瘟疫一样急急忙忙抛弃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我们的结论是成熟的和理智的。今天,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至少我个人认为,所谓社会因素、社会内容、社会功能无助于文学的美的形成,仅仅是文学的外在价值这种看法,是武断的。更何况,对“善”的排除,只能使文学的“美”变得苍白、小器。
许明:这当中有个今天的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自我放逐”的问题。和70年代末以前的情况相比,由于精神饥渴已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被填平,以至于今天的知识分子的任何“说教”和对历史真谛的掌握,在当代读者讲,似乎都是多余的。回想70年代末,当我们这些“老三届”还是毛头小伙子时,精神饥渴驱使我们排通宵的长队去争购一本《契诃夫短篇小说集》或在当时看来是天外奇书的《红与黑》。十几年后,现在什么书买不到?读不着?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信息和知识爆炸何止以几何级数增长?
在这种令人振奋、令人迷乱、令人惶惑的阵势前,“知识者”贬值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知识者被真正抛向了“边缘”。这个剥夺过程是很残酷的。公众不再将你视如神明,你的话语的神秘性、专有权被消解了。于是,你自己或公众都感到了:当年作为启蒙者的崇高的社会角色,如今已变得可怜巴巴、自艾自怜;你环顾四周,猛然发现人们行程匆匆,无暇顾及你的存在。你的草呀、花呀、闲呀,什么再造历史呀,语言的新实验呀……一切一切,显得多余和无聊。无聊者如庄之蝶(《废都》),一个50多岁的中年作家,你可以想象他有过多少奋斗和磨难,有过多少激情和责任,有过怎样的被鲜花和掌声拥簇的生活,而现在,他统统失去了,锐气荡尽,他的“平面化”表面上是一种堕落,其实是自我心理治疗,一种知识、话语权被剥夺后的自我放逐。
钱竞:我看贾平凹是努着劲儿想在《废都》里说一次真话。作家竭力挣脱掉各式各样被迫或是自愿戴上的面具,拼命在作品里显示一个赤裸的自我。在抽象意义上,我尊重贾平凹主观的真诚。但是又无可奈何地看到了一个事实:作家身上并没有出现一件“皇帝的新衣”,而只有那早就被铸就塑定了的文化灵魂。至少在庄某人身上,是弄权而无方,归隐而不得,从半是玩世半是麻木中突现的,是深入骨髓的无聊感。
许明:另一种方式是以公众话语面目出现的,比如说王朔就典型地构成了知识话语权力被大众消解的现实。他自己很清楚这一点,一个写了百万字的“作家”竟然在各种场合渲泄对“知识分子”的嘲弄和仇视,他嘻笑怒骂,对责任、良心、历史、理性……这一切“陈腐不堪”的人文精神遗产极尽讽刺之能事。“庄之蝶”之流或许尚有自我放逐的失落感,而像王朔恐怕并没有边缘化的感觉,恐怕还在为此沾沾自喜,他不会去唱挽歌,不会去吟花、弄草、消遣、寻古,而是跳动着活泼的感受,与“卖浆贩水者”厮混在一起。另外还有一些人,在主张着清闲。这些人不过是在过着大锅饭的余瘾。他们的肩膀太懦弱。他们被理性、责任、理想吓得战战兢兢,被历史的脚步吵得精神不安,你无法指望他们对付常以恶与善为双轮的历史之车。文坛上述种种情形,用米歇尔·福科的话来讲,都将成为我们分析这个时代的精神病史的病例。
钱竞:目前价值资源枯竭,文化信念残破的局面,肯定是一段时间里逃不了避不开的现象。但社会中的理性力量,终究会也应该负起文化调整的功能。在这项调整工程中,作家、批评家,大而言之,人文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最灵敏的感官,自然会传递出大量的信息。如果我们接受话语即权力的看法,那末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知识分子客观上就是具有相当权力的文化调节集团,其作用即在于此。但是,又不止于此。如果展开我们的视野,就会立刻看见一个可以称之为“沉默多数”的社会主体,知识分子的文化调整职能,必须体现在与之沟通上,所以,时下议论正多的价值重构、文化再建,肯定不能再是知识分子的在其书斋里完成的工程,我们的灵感、激情和观念,必须来自于作为“沉默多数”的社会主体。
李洁非:艺术对现实的关注,对社会的关注,归根结底,实际上是对人的关注。当然,有人也许会争辩说,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同样做到关注于人。但是,我很难想象,如果一个人首先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和自己周围的人的生活状况失去兴趣,那么,他的人道主义热情从何而来?在中国,这个问题尤其不容回避,因为我们很清楚,人道主义思想远远没有真正深入到文学艺术的基本价值体系中去,八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中期,我们一度接触过这种价值观念,但由于诸多的原因,内在的和外在的,有关人道主义思想的探寻和建设只是浮光掠影地喧闹了片刻,复又被人遗忘。
张德祥:“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普遍来看,都体现出“物”的价值对一切非物化价值的排斥和挤压。正是在这种价值机制的畸形状态之下,才更需要一种人文精神和道德理想的矫正功能,更需要唤醒“人”的意识,“人”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思想家和艺术家对社会的强烈批判,无论是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还是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无不是对人的“物化”的一种反抗,而强调“人”、“人道”的价值。文学正是在这种“反抗”中显示了自身的存在。
事实上,文学对社会的这种艺术批判,是社会进步、人类进步不可缺少的参与,也是文学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一方面以“金钱势力”而对文学造成了挤压,另一方面却也为文学提供了新的契机,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你或者是放弃文学自身的意义和使命,认同“商品”属性,以庸俗的艳情的乃至色情故事去媚俗、迎合精神堕落的需要;或者是坚持文学的“人”的理想,坚守艺术信仰,与世俗抗争。“抗争”也有两条道路:一是在“纯文学”意义上进行叙述操练,把文学理解成技艺的表演,在语言游戏的结撰中炫技自娱,获得个人智能上的快乐,这是一种躲入“象牙塔”式的“抗争”。另一种“抗争”,便是站在“人”的立场上,以人的价值、理想、精神对非人道的“物”的抗争,对现实的不合理的批判。就此,应当重提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意义。批判现实主义并未过时,也许正逢其时。
李洁非:近年,文学回避社会似乎有一个很充足的借口,亦即像我前面提到过的,这当中有着把文学重新和政治拴在一起的危险,某种意义上,这个担心也是有道理的。不要说前30年,即便80年代中期,作家尚颇具社会责任感的时候,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也过多地和狭隘的政治情结纠缠在一起。可以说,我们还从未真正理解,艺术人道主义的内涵是远比一时一地的政治情结深刻得多的“善”。也正因为未能达到这种理解,至今,一旦有人提出文学艺术应该运用人道主义介入社会、介入现实时,人们就会担心,这将重新迫使文学艺术与政治“复婚”。据我所知,具有强烈社会精神的19世纪作家及其作品,绝少与政治发生瓜葛,相反,像巴尔扎克、陀思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这些人还受到政治家们的指责或抱怨。我相信这样的说法:真正的艺术对于现实永远是一种主权,它在现实面前所做出的反应、它介入现实的方式、它从现实看到和提示出来的东西,既不会混同于政治家,也不会混同于经济学家或者法学家,因为它所焦虑并努力维护的,是比现实所承认和允许的人的更高的幸福和权利,这也许可以用“永恒正义”的概念来表述。我想,这也就是雨果别出心裁做出的那个区分:“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我认为,这应该成为90年代新文学基本尺度。
钱竞:如果作家、批评家、研究者真的身体力行,不求速效,致力于文化沟通和重建的话,我想,我们的文学就不至于疏远人,而能够让人亲近自己。文学与社会也就会从无序纷乱的状态进入一个相对亲和的时期。
许明:我所谓的重建“偶像”,其实就是重建我们的精神发展史。现在在精神方面,工具性资源已丰富得令人目不暇接了,而恰恰是在丰富之中才显出我们的贫乏──那不是知识的贫乏,而是人格力量的贫乏。在这个时代,穿透历史所缺乏的正是人格力量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一百年后,也许文学可以真正成为把玩的消遣品,但至少在现在,多变的中国需要各种精神支撑、导引的时候,文学是难辞其责的。盛夏,北京的文学理论界开始热闹起来了,“文学与道德”、“新意识形态批评”、“开放的现实主义”、“后以后是什么”等等话题,均指向精神现象的深处。一批中青年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将学术热情投向社会与人文科学的相邻领域,密切关注着变动中的社会历史进程。这一切都是好兆头,历史总是呼唤着它需要的东西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历史与社会的召唤呢?依我看,现在的理论要走到创作前面去了,作家的权力意识被凝固了,以至太不关心理论界正悄悄发生的变化。
李洁非:显然,大家都逐浙意识到并且赞成这样一点:在90年代已经到来时,我们必须重新检讨自己的文学价值观,使之从偏废达到健全。这一方面,是为了使文学对得起它面临的社会现实和民众,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要将文学从颓势中拯救的需要。关于文学命运的悲鸣,我们已听了太多,但这些悲鸣几乎一致把文学生存处境日益恶化的原因归之于金钱和市场经济的压迫。这肯定是有一部分道理的,然而要说它是全部,却大错特错。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当我们把文学从民众手中夺走塞进象牙塔封闭起来时,我们又有何理由要求读者对这样的文学产生“需求”呢?也许,我们不应急于下结论,试试看,把文学还予社会,还予人性、正义和善,从它们那里汲取历史的必然真理的力量,然后,我们再来讨论文学的前途和命运,亦不为迟。
标签:文学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作家论文; 道德论文; 李洁非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