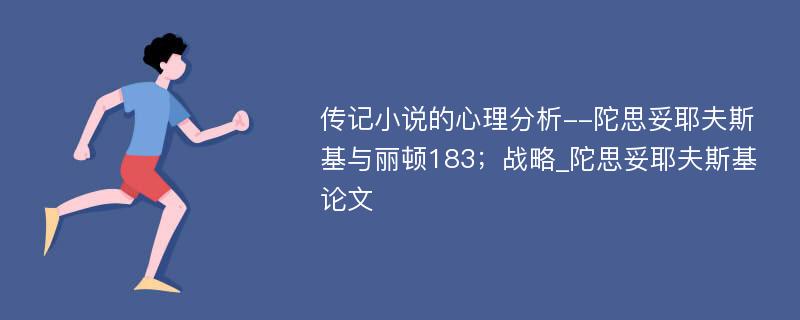
传记中的小说化心理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利顿#183;斯特拉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特论文,斯基论文,传记论文,耶夫论文,心理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的传记写作强调全面展示传主的个性,还原历史真相。斯特拉奇提倡运用“揭露法”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既写传主的亮点,也写传主的暗处。在传记艺术手法上他主张兼收并蓄,包括小说化描写、戏剧性冲突、绘画式光影设计、科学定量(如强调缩短篇幅)等等,其作品被伍尔夫称作“新传记”,①至今仍有一定影响。讨论利顿·斯特拉奇的传记写作,心理分析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但是对于他的传记中使用的具体心理分析方法,多数评家尤其是那些从宏观语境进行研究的学者倾向于认为他是受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响。②但也有学者特别指出,斯特拉奇的《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心理分析的源头是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③对于后者,我们不禁要问:纪实的传记何以从虚构的小说中借鉴心理分析模式?这二者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本文拟通过比照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和斯特拉奇的《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对此作一考察。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欧洲19世纪描写现代性最卓越的作家。学界往往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文学成就的原因归结为一点,即对人物心理的准确把握和深入剖析。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拒绝承认他与心理学有关联。④俄罗斯学者卢纳察尔斯基认为,准确的说法似乎应当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含有“极丰富的心理学材料”,但作者称不上是心理学家。心理学家是指那种能够通过分析人类心灵,“得出某些心理学规律的人”,而“这一层,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未做到。”⑤而事实上,无论文学大师还是广大读者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心理分析和心理描写给予很高的评价。⑥
对照阅读,我们发现斯特拉奇的《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中的确藏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的影子,小说家透视人物心理的手法固化成了传记作家解析传主的语法,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双重人格”;二、忏悔行为;三、幽默视角。
“双重人格”的概念并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发现,但他将这一主题发挥到极致,被誉为描写“双重人”的大师,“几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主要人物……(都)具有双重性。”⑦追溯历史,重视分裂人格和幻想化身的描写一直是欧美的文学传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的欧洲作家中,德国的E.T.A.霍夫曼、俄国的果戈理都写过“双重人”主题的小说。因此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总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如《双重性格》)中感受到果戈理的《鼻子》、《狂人日记》或霍夫曼的《跳蚤师傅》的影响,联想到爱伦·坡的《威廉·威尔逊》或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等等。⑧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到之处,除了巴赫金认为的叙事策略不同之外,⑨主要是他对人物的心理挖掘建立在道德关怀之上。由于这种道德关怀的支撑,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叙事充满同情与理解,叙事口吻往往以幽默平衡了残酷无情的人性剖析。
《双重性格》(The Double,1846)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双重人”概念的代表作。主人公小职员高略德金已届不惑之年,但一无成就。表面上看是高略德金不善交际,不会应酬所致。高略德金每日极度紧张的心理终于幻化出一个“同貌人”替身,与他自身性格迥异,能言善辩,曲意逢迎,两面三刀,在社会交往中游刃有余。替身甚至用其频频获得的世俗成功奚落、嘲笑主人公。高略德金最终受到这个幻影的报复,他发疯了。
在其他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双重”主题的扩展形式。在《白痴》中,梅什金和罗戈任是一个复杂矛盾体的两个面,出国归来的梅什金高尚而显愚蠢;结拜兄弟罗戈任粗野而显精明。用基督教的眼光看,罗戈任就是梅什金的原罪化身,因此他必将在小说中与梅什金同来同往。有学者解释说,双重人概念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寓言,即在知识的大门口,恶必定在场。也可以说,“没有黑暗,我们怎么会理解光明”?⑩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主要人物伊凡的“双重人”是其父的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斯麦尔佳科夫卑鄙、粗俗,心中充满邪念。而这些都可看作伊凡性格的另一面体现。也许伊凡的邪念只是在心中半隐半现,但在斯麦尔佳科夫身上则外化得淋漓尽致,谋杀父亲的过程就表现为伊凡鼓动,斯麦尔佳科夫实施。
对于斯特拉奇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概念不只是谋篇布局、贯穿全书的叙事技巧,更是洞悉人心的角度和剖析人心的路径。《双重性格》中的高略德金之所以最终精神错乱,是因为“其他成年人那种毁灭性的眼神,是他们的拒绝、蔑视和嘲弄,更是他们的反应中所表现出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11)换言之,高略德金先幻觉,后疯癫,看起来是他人造成的悲剧。这种观点显然并不足以解释高略德金的个性。统观高略德金的表现,我们倒是看出,他的悲剧之源固然有来自社会和他人这些外部因素的成分,更多的却来自他自身性格的内部因素,如约翰·赫德曼(John Herdman)所指出的,“他的疯癫之根源不仅是他周围社会环境的限制、折磨和压迫,还有他自己的虚荣心、野心、妒忌心和受到伤害的傲慢之心。”(12)高略德金的故事说明,人的个性、行为和无意识三者之间常常缺乏一致性,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活动与他的外在行为并不完全吻合。表面上高略德金没做什么坏事,而他的内心深处却可能是一片滋生邪念的良田沃土。
沿着这种追寻人的内在心理和外在行为之间关系的路径,斯特拉奇在《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13)中的《曼宁传》开篇就申明他准备探索传主外表之下的情况:“当代探索者对其[曼宁]一生的兴趣主要取决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他的一生反映出的他那个时代的精神,二是他的心路历程反映出的心理问题。”这种思考导致了关于“双重”主题的一系列疑问:人的外部成就与人的内部思想情操是否同样伟大?人的外貌是否与其人品相符?
曼宁可归于杰出教士之列——这绝对不是一个小行列——这类教士之所以出众,不是因为他们多么圣洁高尚、知识渊博,而是因为他们社会能力高强。……看他一生的奇特经历,好像是昔日教士擅长外交与治理的老传统几乎在他身上复活了。要是没有他,人们真会以为这个老传统已随红衣主教沃尔西(14)一去不返了。所以在曼宁身上,中世纪似乎再度来临。这个又高又瘦的人,苦行僧般的脸上露着微笑,身穿长袍,头戴四角法帽,气宇轩昂,从奥拉托利会的大弥撒到埃克塞特市政厅的慈善募捐会,从港区的罢工委员会到上流女士跪见红衣主教的贵族之家,哪里有他,哪里的事情就肯定不同寻常。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他身上的威严气势震住了敌对的气氛呢?还是19世纪的敌对气氛本来就没有那么强烈呢?19世纪分明是一个崇尚科学、追求进步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还会胸怀热忱欢迎代表古老传统和坚定信仰的人吗?也许可以这么说:那个时代在内心深处给曼宁这样的人留有一席之地——宽容地留给他们一席之地?或者,从另一方面看,是曼宁这样的人会曲意逢迎、善于妥协?他们这种人是靠耍手腕获取了以实力绝对获得不了的成就?也就是说,他们这种人能成功地成为领袖人物,并不是因为他们人有多优秀,而是因为他们有巧妙地挤进领袖行列的高超才能?不管怎么说,是怎样的机缘,怎样的回合与奋斗,怎样的客观环境与个人条件的结合,使得这位老人爬上大主教高位的呢?(15)
纵观斯特拉奇笔下曼宁的一生,我们看到,这位道貌岸然、德高望重的大主教经常表里不一,前后矛盾,判若两人。他任副主教期间,工作极其认真,对人极其热忱。然而,“他的事业越有活力,越幸运,越有前途,他的内心深处便越频繁地看见那个可怕的场景——燃烧着硫磺圣火的湖。”他一面对天主教和英国国教的争执心存怀疑,但又不愿意在教友面前承认自己和他们的认识别无二致。于是他陷入痛苦,宛如“一个士兵发现自己对正在为之战斗的事业已失去信仰时,不打是背叛,打下去也是背叛。”当《泰晤士报》上登出他拒绝罗马天主教廷提升他当红衣大主教的消息时,他的忧虑几乎和高略德金一样沉重。
……他害怕了,就像从前屡屡害怕一样。当然让他害怕的危险并非子虚乌有。一般情况下,没有他的允许,这样的文章怎能刊登出来?其结果不就是让他丢人现眼吗?大家会以为他断然拒绝了压根不想拒绝的荣誉,还故意闹得纷纷扬扬,让天下皆知他见荣誉就让。这不是等于说他轻率地拒绝了一项他其实满怀感激的任命吗?一旦这要命的消息被罗马方面读到,会不会导致这个红衣主教的称号干脆压下不给了?(16)
“曼宁传”里也有另一种形式的“双重”主题:曼宁主教的另一个自我纽曼主教。本来在传记中表现传主的对立面在相当程度上是受了传记传统的影响。古罗马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著名的《双行传记》(Parallel Lives)以成对的方式为希腊和罗马的英雄人物立传,对后人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20世纪初英国文人爱德华·库克(Edward Cook)认为,一个传主一生某个阶段中如果恰好有其对立面,这对传记作家是最幸运的。(17)而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概念让斯特拉奇在传记中给曼宁的生活描述增添了更大的戏剧性。曼宁一生中的几个关头都有与他截然不同的纽曼主教衬托他。如果说纽曼是崇尚理想、注重思想的艺术家;曼宁则是擅长营私、热衷实利的政治家。纽曼是著名的牛津运动的发起人,他怀抱着复兴基督教真谛的信念,主张恢复宗教信条的严规戒律;但曼宁则是想把牛津运动当作实现自己向上攀爬的阶梯。纽曼1840年代从英国国教改信罗马天主教,致使他在英国从声名显赫骤然落到一名不闻。曼宁改宗较晚,当时纽曼已经得罪很多国人,出任天主教在英格兰的牧首已经十分困难。这倒成全了曼宁,他爬到了天主教在英格兰的领袖地位。几十年后,当纽曼的《自辩书》出版引起轰动,已处英国绝对天主教领袖地位的曼宁却害怕了,于是给纽曼设置障碍,制造麻烦,阻止纽曼实现他的宗教理想。高略德金的幻想双重人凸显了他的荒唐可笑,而曼宁的现实“双重人”反衬了这位英雄的反英雄品质。
陀思妥耶夫斯基另一个重要的心理分析手段通过表现人物的忏悔行为实现。在他的小说中忏悔处处可见。与圣奥古斯丁和卢梭不同的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忏悔包含多重含义。如弗朗西斯·R.哈特(Francis R.Hart)所说,有“寻求表达自我的本原和实质”的忏悔,也有“寻求展示或力图实现自我完整性”的自辩书式忏悔,还有“寻求说出历史性自我”的回忆录式忏悔。(18)这些忏悔离不开人物自身的个性,也离不开西方宗教传统。在基督教中,忏悔是免罪行为中的一个环节。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曾经专门讨论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忏悔和双重人主题。在库切看来,免罪行为有四步:犯有罪孽、忏悔、悔罪和免罪。他举出中世纪圣奥古斯丁的例子,说明忏悔目的之一是检讨自我。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记录了他因偷梨所作的忏悔。“过去我一贯……为我知道自己做错事而忏悔;现在我要为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事而忏悔……我不了解自己,这种状况将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在您的光明之中‘我的黑暗变成日上中天’”。(19)也就是说,偷梨事件是奥古斯丁的罪过,检讨自我是他的忏悔,他既因为自己是个罪人(带有原罪)而忏悔,又因为自己过去对自己没有清醒的认识(意即自己竟然能受诱惑干出偷梨的勾当)而忏悔。通过深刻反省和真诚的忏悔,奥古斯丁在行动上悔罪了,从而得到上帝的宽恕而得以免罪。(20)
因此美国理论家保罗·德曼如是总结忏悔:“忏悔是以真理的名义克服罪孽和羞耻;是对语言认识论的运用。”(21)但是忏悔的虔诚意义在卢梭那里被解构,人的罪过以忏悔的名义被拿来炫耀。最有名的例子是女佣玛丽永事件。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所述自己诬陷玛丽永之事在保罗·德曼看来实为“辩解”,而并非忏悔;在库切看来卢梭是炫耀过错,以此耍酷,出风头(exhibitionism)。忏悔的庄严意义在卢梭这里发生了颠覆性变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忏悔对象发生了变化。(22)奥古斯丁向上帝忏悔,卢梭向读者大众忏悔。忏悔对象由万能的神降成普通的人,忏悔者却随之从谦卑上升到主位,掌控着忏悔的导向,忏悔的意义由此走向反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奥古斯丁式的真诚忏悔比比皆是,卢梭式的炫耀式忏悔也星罗棋布。而其中最多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对卢梭式忏悔的延伸,即忏悔怀有极其实用的世俗目的。
以小说《白痴》中的一个场景为例。凯特勒找到公爵梅什金推心置腹地向他忏悔。“他的话几乎刚开头,就突然跳到了末尾,他声称,他已经‘道德败坏,不可救药’……到了偷东西的地步。”(23)但是凯特勒自我贬低的忏悔让公爵听起来有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感觉,公爵因此怀疑凯特勒的忏悔另有目的。凯特勒就势耍了一个“阳谋”,把自己打算向他借钱的计划和盘托出,但仍不忘以忏悔的形式炫耀自己多么无耻。显然,凯特勒的忏悔因为不真诚,使人怀疑他有比炫耀卑鄙更加世俗的借钱目的,他是“想用眼泪骗点钱花”。(369)库切认为,凯特勒的忏悔固然因炫耀卑鄙而越显卑鄙,但公爵的自白更具有戏剧性。公爵听了凯特勒的“阳谋”式忏悔,安慰他不要为自己的卑鄙想法而自贬,因为卑鄙邪念和高尚道德并存的“双重”思想人皆有之,他自己也经历过“双重”思想的斗争。(24)貌似高尚的公爵和卑鄙的凯特勒竟然在人格上不分上下,这瞬间瓦解了读者心目中公爵的高贵形象。
对斯特拉奇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忏悔不在其花样繁多,而在于它是表现人物性格的有效手段。凯特勒向公爵忏悔,一波三折,先是“闯”进公爵的住处,强行迫使公爵倾听他的自我败坏诉说,以致“要轰走他是根本办不到的”。然后他佯作真诚,却显然看得出在编故事,使得公爵萌发对这只迷途羔羊“施加好影响”、使之“改邪归正”的念头。然而在凯特勒设置的借钱计谋中,慈悲为怀的公爵料想不到,凯特勒的忏悔是有实用目的的。当公爵试探性地点出凯特勒想“借钱”的真实意图时,凯特勒顺势忏悔自己打着忏悔的名义行借钱之实质有多么卑鄙。公爵安慰他不要为自己的心理斗争惴惴不安,因为此情此景人皆有之,这时凯特勒明白他的目的基本已经达到。
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忏悔成了斯特拉奇观察传主的角度和表现传主心灵的一个方便入口。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龌龊的主人公不同的是,斯特拉奇传记里的主人公都是现实世界里高尚伟大的英雄人物。他们的忏悔公正堂皇,日记往往是他们检讨自我、跟自己对话和反省自我的场所。赫里尔·弗劳德在日记里向上帝检讨自己学习和实践《圣经》不够认真。(25)曼宁的日记袒露出日记主人的犹豫、怀疑和真实心迹。因为这些19世纪的传主当年写日记时,未曾想过要发表,所谓读者可能永远是他们自己,所以这些日记就多了些真心的忏悔,矛盾的流露,而鲜有以过错为荣的炫耀。德高望重的红衣大主教曼宁在日记里承认他喜欢世俗凡人的追求,“我确实喜欢荣誉,爱当头,一心往上爬,热衷与名流为伍,但喜欢这一切真是太卑鄙可耻。”(26)如此种种的心迹袒露映射出一个与万众瞩目高高在上的大主教不同的曼宁——这是一个饱受矛盾心理煎熬的两面体。他身在神职,但渴望世俗的成功。他对《圣经》中的某些教义心有怀疑,但在信徒面前却表现出坚定不移的信仰。因为虔诚,他拒绝了送上门来的重要职位,但此后
他的心绪远未平静下来。首先,他想起此事便耿耿于怀,老觉得“撒旦说我只是为了给人留个克己圣洁的好印象才拒绝这个职位的”;其次是他深感失望,也很懊悔,挥之不去,越发耿耿于怀。他失去了一个好机会。但一想到自己在慎思、自诫、谦恭、自律、苦修以及赎罪等方面,可能做对了,便又感到一丝宽慰。(27)
斯特拉奇还注意到,忏悔固然是当事人为了自己而对自己实话实说,用自己的怀疑跟自己交谈,因而能够有力地表现传主的心路历程,但一如库切所看到的,与环境和性格的神秘而又无情的力量相比,说什么,想什么,甚至祈祷与最后的事实结果可能还是有出入。也就是说,忏悔只能表现传主的一部分心迹,而不是全部。(28)所以,斯特拉奇的历史叙事告诉我们,尽管曼宁在谋求当英格兰天主教威斯敏斯特大主教时,曾在日记里不断检讨自我,发誓“不想靠拉关系,造舆论来追求这个高位”,(29)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发誓高位送上门来时不接受。换句话说,想坐高位是他一直未变的本性。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幽默,巴赫金的评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再现双重现象时,他总是在保存悲剧成分的同时也保存了喜剧成分”。(30)面对凡俗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心是苦的。他笔下的人物挣扎在与自我的搏斗当中,通过这种搏斗,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物内心深处的种种丑恶一展无遗。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超凡脱俗,他对芸芸众生充满了同情,正如约翰·赫德曼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洞悉他小说里的主人公弱点的眼力是无情的,其冷漠的叙事语气可能残忍冷酷,模仿的叙事视角可能很有嘲讽力,然而他在想象力中进入人心理中具体的低下卑微、犹豫不决和疑心的状态,却与对人的深刻同情与理解不无平衡的关联。”(31)在《群魔》中,我们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美国百万富翁处心积虑,贪得无厌,甚至在谋划遗嘱时仍想竭尽全力占有这个世界:
他把自己身后的全部巨额财产都留下来办工厂和办实用科学,把自己的骨骼留给当地医学院的学生,把自己的皮留下来做成一面鼓,在这上面日日夜夜敲响美国人的国歌。(32)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幽默甚至带有恶作剧的“恶毒”性质。《白痴》中有一个场景,女主人公之一纳斯塔西亚邀请了一群客人到她的客厅,在一位房客的建议下,同意众人一起玩一种沙龙小游戏,要求在场的每个男人说出自己平生干过的最坏的一件事。包括阿法纳西在内的三个男人展露了自己丑陋的灵魂。于是纳斯塔西亚借着游戏规则的掩护,巧妙地提出即将发生的事将是自己“平生干过的最坏的一件事”:解除由阿法纳西做媒要她嫁给加夫里拉的婚事。读到此,读者方才明白,原来纳斯塔西亚这次邀请众人聚会别有目的。(第170-182页)如果说其他陀氏幽默是悲中有喜,这则故事对加夫里拉则是悲从喜来。
斯特拉奇尤为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幽默,认为我们至少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其价值。第一,幽默激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各种才能:恶魔般透视人心的洞察力,不厌其烦地表现奇闻怪事和对人性中高贵品质的特殊挚爱。正是这种幽默感使他的作品具有非凡的感染力,让读者带着恐惧直面他对人的灵魂的剖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剖析入木三分,赤裸裸,血淋淋,如果没有幽默的调节,这种对人心的透视很可能变得十分恐怖。而有了幽默,那些描写“就像高高举起的火把或划过天际的流星放射出的光芒,”(33)有助驱走恐惧之心,舒缓紧张气氛。第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物充满同情心,他的幽默在犀利中带有理解,在挖苦中并没有仇恨。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嘲笑不像斯威夫特那样狠毒,没有伏尔泰那样尖刻,也不是简·奥斯丁那种裹着爱意的恶作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幽默是带着怜爱的嘲笑。斯特拉奇赞美陀氏幽默“不贬低被嘲笑对象,而是使他们更加高贵,更加可亲。这一点在他的全部特点中最令人称奇。”第三,陀氏幽默的讽刺是全方位的——在他笔下全部人性一览无余,“一会儿是愚不可及,一会儿是神圣无比,一会儿是卑鄙无耻,一会儿充满尊严,一会儿是极端利己主义,一会儿是极端克己主义。”(34)
可以说,斯特拉奇在传记中也把幽默用到了极致,以致幽默成了他的传记的一大特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斯特拉奇的幽默没有感官的刺激,而是一种旁观者的超然。由于传记与小说的差别,斯特拉奇的幽默不是全方位地揭露人性恶,而是向事实逼近,企图展示现象背后的那个本真。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透视人物灵魂一样,斯特拉奇透视英雄传主的“泥腿”时眼力也很犀利。在他看来,英雄是人不是神,因此不可能没有缺点。不写缺点的传记,是不完美、不真实的历史纪录,而且读者有权知道一切。对英雄一味采取例行公事的歌颂手段,将所有英雄描绘得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也是对英雄的不尊重。但在当时社会主旋律道德风气的影响下,英雄已经被套上各种光环,要还英雄的真实面目还需要极富洞悉力的眼光和具有相当表现力的技巧。斯特拉奇幽默的特点之一就是在英雄的庄严之中洞见其不合理的渺小之处,在伟大的背后袒露卑微,在和谐之下洞察其自相矛盾之所在。因此他往往使用对比手段表现这种幽默。在《曼宁传》里,不只是曼宁大主教是斯特拉奇重新审视基督教的靶子,整个19世纪英国基督教都在他的拷问之中,因此他虽然对曼宁的对手、牛津运动中的基布尔和纽曼主教有所同情,但对基督教本身的质疑仍然毫不留情。他认为,基督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高尚,没有办法解释世俗生活,却企图联结世俗社会与理想彼岸。所以基布尔和纽曼发动牛津运动其实基于一种特别的危机感:
但别的人把基督教只看做生活中的一种摆设,用起来方便,也有较高的档次;有了它可以给人灌输一套健康的道德观念,信仰它便有望得到永久的幸福。纽曼和基布尔则不然。他们看到的则是古往今来神力超乎寻常的显现,如浩浩流水,连绵不绝。是神圣的教士,通过躬身行按手礼的神秘象征,与上帝通灵。是普天下信众通过圣饼与上帝交流。是卷帙浩繁的玄奥理论,一度莫测高深,也看不出有何重要意义,但最终不容置疑地确立下来。他们看到,随时随处都有超自然的现象,如一股看不见却能感觉到的强大的力量,隐藏在天使身上,启发着圣人的心灵,并赋予最普通的有形物质以产生奇迹的特性。难怪他们发现,从亨利八世的离婚案、伊丽莎白时代的议会阴谋、1688年的革命演变而来的社会制度,很难与他们理想中的奇迹景观合拍。(35)
上帝的无边神力仅是通过简单的“按手礼”和“圣饼”通达信众,与信众交流。而且虽然基督教理论高深玄奥,卷帙浩繁,神职人员们花费大量时间研究讨论的却是纠缠在奇迹、无边的法力和围绕着这些问题的“真理的谬误”。斯特拉奇似乎是说,个中的奥妙不是很具有讽刺意味吗?不只如此,斯特拉奇向我们展示,高尚与卑微共同出场的机会在基督教生活中并不少见。纽曼由英国国教改信天主教了,让人确信他改宗的仪式性标志竟是他换了条裤子。而且导致纽曼改宗的,也并非是他能站在“真理”的立场上思考良久的举动,不是他的理性驱使他,而仅是他的感性使然。斯特拉奇感叹,“可惜真理与谬误取决于众多因素,单靠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见得一定探得真理。一个人实事求是的态度可以一丝不苟,完全彻底,然而他[纽曼]对真理的尊重程度——不容否认,也许是不够的。他也许像疯子、恋人、诗人那样,满脑袋全是幻想。那些‘奔涌之思’,那些‘天马行空的乱想’,重在心悟神解,而非理性冷静之识,其中点滴足可使人或誉或毁。”(36)纽曼高尚的信仰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演成了一场闹剧。虔诚的纽曼不知道,这种闹剧式的背景本身就给他的悲剧和曼宁的成功埋下了伏笔。通过对比的手法,斯特拉奇的幽默告诉读者,纽曼的热情、激情和虔诚奉献给基督教这样一个理论上至高无上、世俗生活中见微知著的事业,其真才实学,著书立说,不过使他最终沦为曼宁的手下败将,原因是,世俗背景本身的蒙蔽性更易使曼宁这类实用主义式的人物“靠耍手段玩策略获得了用实力绝对获得不了的成就”,结果“此类人能成功地成为领袖人物,并不是因为其人多么优秀,而是因为他们钻营的才分高超”。(37)
文学性是以斯特拉奇为代表的“新传记”的特点之一。评家们注意到传记中文学性的刀锋特点,但是人们往往忽视斯特拉奇传记中文学性的本质,即,在强调传记艺术性的同时,更注重对小说技巧的理念而不是纯形式的吸收。因此,吸取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表现技巧之一心理分析的理念让斯特拉奇既把传记写得栩栩如生,使传主生动活泼地立于纸上,又使之与小说保持了文类上的距离。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斯特拉奇的追随者们没有达到斯特拉奇的艺术高度的原因。
注释:
①Virginia Woolf,"The New Biography," in Leonard Woolf,ed.,Collected Essays,Vol.IV(London:Chatto & Windus,1967).
②例如下列文献:John A.Garraty,The Nature of Biography(1957; New York:Vintage Books,1964)122; Reed Whittemore,"Biography and Literature," in Sewanee Review 100.3(1992)383; Paula R.Backscheider,Reflections on Biography(Oxford:OUP,1999)127。
③保罗·莱维(Paul Levy)断然肯定斯特拉奇《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的影响源有二:一为伏尔泰,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见Paul Levy,"Introduction," in Lytton Strachey,Eminent Victorians(London:Continuum,2002)xxviii-xxix。传记作家霍尔洛伊德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斯特拉奇的传记写作至少有两种影响,一是瞄准人物内心世界;二是采用幽默叙事技巧。见Michael Holroyd,Lytton Strachey:A Critical Biography(London:Vintage,1994)247。彼德·凯的研究发现,斯特拉奇“旁征博引,从欧洲文学传统的高度准确地评价了陀氏小说,”是当时极少数真正理解陀氏小说艺术的学者之一。见Peter Kaye,Dostoevsky and English Modernism,1900-1930(Cambridge:CUP.1999)21。
④著名的例证是学者经常引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881年1月的日记:“他们叫我心理学家,这不对。我只是个更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我描写人类内心最深处的灵魂。”例如:Marina Kanevskaya,"Smerdiakov and Ivan:Dostoevsky's The Brothers Karamazov," Russian Review 61.3(2002)372。
⑤转引自陈思红:《心理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载《北京大学学报》(外国语言文学专刊)1999年,第160页。
⑥详见Rene Feuloep-Miller,"Dostoevsky's Literary Reputation," in Russian Review 10.1(1951)46-54。
⑦Mikhail Bakhtin,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Caryl Emerson,ed.& trans.; Wayne C.Booth,intro.(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217.
⑧见马尔科姆·琼斯:《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幻想现实主义解读》,赵亚莉、陈红薇、魏玉杰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7、70-71页。
⑨巴赫金探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双重人”主题上对其他作家的学习与仿效,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效仿中有个人独到的特点。见Mikhail Bakhtin,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49。
⑩John Herdman,The Double in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90)17.
(11)马尔科姆·琼斯:《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幻想现实主义解读》,第69页。
(12)John Herdman,The Double in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15.
(13)《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是天主教在英格兰的首席大主教曼宁、护士南丁格尔、教育家托马斯·阿诺德和军事家戈登少将四位维多利亚时代名人的合传。斯特拉奇声称其立传目的是用这四位象征维多利亚时代精神支柱的人物揭示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真相。见Lytton Strachey,Eminent Victorians,1918(London:Chatto & Windus,1945)ix。
(14)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1475-1530),英格兰枢机主教和政治家,曾协助英王亨利八世处理外交内政事务,取得很大权势。1529年被指控犯有侵害王权罪。
(15)利顿·斯特拉奇:《维多利亚时代四名人传》,逢珍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16)利顿·斯特拉奇:《维多利亚时代四名人传》,第92页。
(17)Edward Cook,"The Art of Biography",in National Review April(1914)282.
(18)Francis Rt.Hart,"Notes for an Anatomy of Modern Autobiography," in New Literary History 1(1970)485-511.
(19)St.Augustine,Confessions and Enchiridion,Book X,trans & ed.Albert C.Outler(London:SCM Press,1955)205.
(20)J.M.Coetzee,"Confession and Double Thoughts:Tolstoy,Rousseau,Dostoevsky,"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37.3(1985)194.
(21)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64页。
(22)J.M.Coetzee,"Confession and Double Thoughts:Tolstoy,Rousseau,Dostoevsky," 206.
(23)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臧仲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年,第366页。后文凡出自同一小说的引文,随文标出页码,不再另注。
(24)J.M.Coetzee,"Confession and Double Thoughts:Tolstoy,Rousseau,Dostoevsky," 223.
(25)Lytton Strachey,Eminent Victorians,10-11.
(26)Lytton Strachey,Eminent Victorians,38.
(27)利顿·斯特拉奇:《维多利亚时代四名人传》,第36页。
(28)J.M.Coetzee,"Confession and Double Thoughts:Tolstoy,Rousseau,Dostoevsky," 215.
(29)Lytton Strachey,Eminent Victorians,62.
(30)Mikhail Bakhtin,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117.
(31)John Herdman,The Double in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15.
(32)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臧仲伦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329页。译文有所改动。
(33)Lytton Strachey,Characters and Commentaries(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36)183-184.
(34)Lytton Strachey,Characters and Commentaries,186.
(35)利顿·斯特拉奇:《维多利亚时代四名人传》,第14页,译文有所改动。
(36)利顿·斯特拉奇:《维多利亚时代四名人传》,第25页。
(37)Lytton Strachey,Eminent Victorians,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