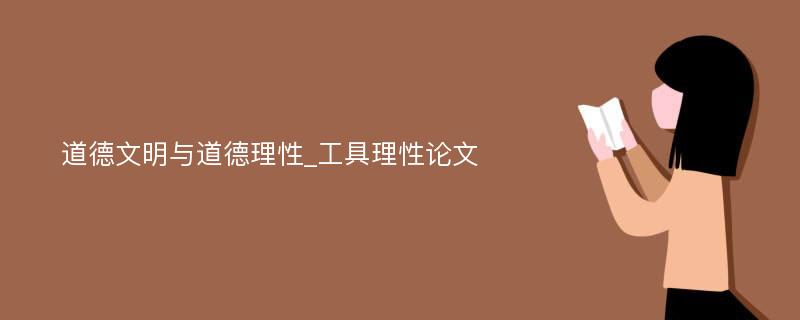
道德文明与道德理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理性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近来学界有关经济与道德关系问题讨论很热烈,提出了许多很值得深思的问题。不过大家似乎过于强调道德对经济的依附关系。当然,我们尽管不能否认经济对道德的影响,但道德在更大意义上有赖于价值理性的建构。具体说,就是道德理性或道德形上学的建立。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指责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道德滑坡,也不能指望经济繁荣会自动带来新的道德文明。因为道德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财富与道德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如果只在经济与道德间作经验的分析,势必会陷入理论上的二律背反。
道德不能建立在经济这一工具理性行为基础之上。工具理性只为追求功利的目的所驱使,其着重考虑的,是手段对达成特定目的的能力或可能性,而并不顾及善恶。因此,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感受性要求。它是从经验出发,与人的得失,愉快和痛苦感觉相联系的一种行为。但是道德却不能简单地从经验中引出,它蕴涵在人的理性之中。经济发展必然与幸福、利益等相联系,而道德恰恰不能从幸福和利益中引出,它是从原则出发,进向概念,随后才进到现实的层面。它永远意味着对意志的一种关系,并不直接指向事物的对象或性质,与人的苦乐等感觉无关。因此,道德文明必须指向一种价值的形上学。现实情况表明,往往并非经济状况决定人的道德水平,而是人的道德自觉决定了人对义利关系的不同取舍。在这里,道德理性具有优先性,而人们对义利关系的判断、抉择只是一种价值判断与抉择。价值判断虽然体现了人们道德意识,但只是道德意识的一种外化,而不是道德本身。道德本身是从道德理性中涌现出来,与他物无关,具有自律性。只有当它落实到现实的层面,在与事物的交道中,才表现为价值判断行为,这就要求我们把道德与价值概念作出适当的区分。经济发展直接作用于价值,但不直接作用于道德。这一不同也警醒我们,在思考经济与道德关系问题时,必须充分顾及道德自身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二)
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发展似乎可得出这样的启示:国民道德的建设须仰赖于超越的道德理性重构。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道德理性对于知识理性的优先性,道德的成立必须仰赖于天理或根系于心性,这种道德形上学的建立,旨在从先验的依据中,寻找道德的合法性和普遍有效性。这点与康德实践理性,可谓暗若符契。但中国传统哲学在建构道德形上学的过程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没有在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进行合理的分层。尤其没有对知识理性的适用范围进行合理的规定和批判的鉴定,往往轻率地以道德律统摄自然律,以德性之知消解见闻之知,把一切道德化。在传统文化中,圣人同时是宇宙的智者,这样,传统哲学体系中,就没有给知识理性的独特价值和合法性充分关注,没有能在道德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建立起合理的张力。
于是,一旦西方的船坚炮利叩开中国的国门,工具理性创造的工业、经济文明席卷东进,人们就很容易不加思索地抛弃固有的道德形上学,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泛道德主义走向泛科学主义,泛价值论走向泛工具论,表现出对工具理性文明的狂热崇拜。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许多事实,可以充分说明这点。
勿庸置疑,近现代以来,中国对西方的工商业文明和科技文明的引入,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扫除了传统中国文化只言心性,一味务虚的作风,为中国文化社会走向现代带来了光明和生机。不过,由于传统文化没有发达的工具理性,也缺乏对工具理性严格的批判反省机制,所以,使得人们无论是在反传统,还是吸收西学的问题上,都陷入种种误区。一方面,把传统的道德形上学看作不切实际的迂腐之学而加以激情式的(不是理性的)批判和根除,如吴稚晖调皮地讲,所有中国文化,都不过是向古传下来的木石蛇鼠献一些虔诚而已的盲动和迷信。于文江嘲笑中国传统心性理论,认为这只会产生一种虚幻的优越感,疏于实事。另一方面,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也大多倾向于工商、科技或至多是政治文化的层面,很少关注西方形上学的发展。胡适向国人广泛介绍实用主义哲学,却偏偏不讲詹姆士的形上学和宗教哲学。人们崇尚实证主义的穆勒、赫胥黎、斯宾塞,却恰恰遗忘了穆勒对“道德科学方法”和“物理学方法”的严格区分。忘记了斯宾塞说的“终极的宗教和科学概念,同样都只是现实的符号”,“如果精神总是存在着超越知识的可能,那么就永远不会没有宗教的地盘”等等这样一些对形上学的眷顾。
西方近代文化自休谟、康德以来,一直对人类理性认识的能力与科学方法的适用范围进行批判的囿定,这使得他们在承认科技、工商等工具理性文化发展合法性的同时,又始终限定它的无限澎胀,没有完全忽视人类价值生活的独特意义和超越性。而中国近现代以来文化思潮的一个主流,就是在反传统的同时,无限夸大工具理性的意义,以工具理性消解价值理性。例如,对待科学问题,通常把科学作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科学,如有学者所说,已不再是作为一门学科,而是“作为一种规律教条来接受”,这正是雅斯贝尔斯所批判的现代“科学迷信”(Supersition of Science)。目前,社会上对待经济问题的看法,也颇类似,值得注意。
有人寄托于科学来建立新道德,也有人主张通过发展经济来改进道德,认为贫困就是罪恶。事情并不这么简单,近现代发展的历史似乎表明,科技与经济在带来福祉的同时,并不必然地带来善。各种不道德的,甚至丑恶腐败现象仍然大量存在,道德问题没有因为科技经济的发达而减少。但我也并不同意有些人因此而旧梦重温,追怀往昔,指责财富增长带来了罪恶和道德滑坡。我只是要说明,科技,经济等工具理性活动,是中性的,它不应该对道德问题负责。道德的善恶只能从自身的文化理性中去寻找根据。近现代中国反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过失,就在于它对传统进行嘲弄和勘落的同时,截断了返回道德形上学的文化言路。
尽管如此,仍让我们感到一点欣慰的是,近现代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一批心系道德,忧虑人心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重建道德形上学,来挽救时风,洗新民心。如章太炎认为,要匡正劣败黑暗的社会道德风气,应建立一个超绝的,“上契无上”的价值体系。现代新儒学、新佛学的许多思想家,都在这方面作了努力的尝试。他们也克服了中国传统道德形上学的不足,希望通过对知识理性的再反省而上升到道德理性的建构。梁启超认为,道德建设一方面要升华到心性学的层面,另一方面又要“建设于极隐实,极缜密的认识论之上”,“专用科学的分析法,说明‘我’之决不存在”,他提出佛教最适合于作为中国道德形上学建立的依据:“释迦很有点像康德,一面提倡实践哲学,一面提倡批判哲学。所以也可以名佛教为‘哲学的宗教’”。
可惜,这些思想往往被认为不切实用而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人们还不容易跳出对工具理性的过分膜拜。我认为,这些思想,恰恰是我们道德文明建设应该寻找的文化结合点。
三
基于这些理论和历史的反思,我认为,当前道德文明建设至少应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强化对技术、经济等工具理性的反省。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建立起工具理性的一极,近现代文化又走向对工具理性狂热崇拜的另一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文化体系中,缺乏对工具理性反省与批判的向度。有人认为,中国近现代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技术、经济,因此,不应参照西方现代文化中反文明、反异化的文化批判。我认为这种看法是短视的,它忽视了文化理论研究应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反思功能。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发展中,则有一批较清醒的思想家,能以出乎现实之外的高度而又入乎现实之内的使命感,承担起批判、纠正社会发展道路的义务。这些批判,不仅没有使西方道德文明走向现代化的反面,反而使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更臻圆熟。使西方文化在技术经济现代化的躁动之中,保存了一块人文精神的绿洲。
现代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经济的工具理性文明。不过,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中西近现代以来,文明发展的历史教训。一意孤行地片面发展工具文明,忘记价值理性的再构,已使我们的许多道德理想在强大的经济大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中国许多人的一种普遍信念是,道德文明与经济原则是一致的,只有经济上去,道德文明才能挺立。这种幼稚的幻想,唤起了多少人对技术、经济乌托邦式的幻想,认为技术经济原则可以解决一切人生问题、社会问题,从而丧失了对技术、经济文明的反省。
2、合理地重构道德信念。信念是现代文化发展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道德信念的建立需要形上学,也可从宗教中吸收其合理成分。道德既然不能从技术、经济生活中直接引出,而应考虑道德自身的理性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思考道德文明的建设中,充分注意中西学者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许多有益探索,在信念和迷信之间作出正确的区分,真正建构出合于社会进步的道德信念和道德形上学。
3、建立社会进步评介的多维参照系,改变以往以技术经济作为衡量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标准的单一化模式,真正全面理解现代文明的丰富内涵。技术经济是标明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但不应成为唯一尺度。马克思在这方面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虽然反对以道德的评判原则来评介历史的进步,但他始终并不完全排斥必要的道德评介。马克思一直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是人作为主体不能不把自身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和标准,如何理解、寻求人的全面发展,充分关注人的价值和命运,为人类提供更多的“合乎人性的环境”和精神空间,就成了马克思评介历史进步的不可缺少的一面。
历史和现实的许多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必须相辅而行。孙中山说:“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缺乏文化准备和心理准备的前提下发生的。应该看到这是出于迫不得已的现实原因,但绝不能因此而忽视文化精神、道德理性和思维方式等在社会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现代化的社会模式是一个以技术、经济发展为中轴的综合化模式,它离不开掌握技术发展的人的观念形态的文明。“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在我国当前现代化的建设中,道德理性的建构已势在必行。
①康德著,关文运译:《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②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等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③李向平:《救世与救心——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