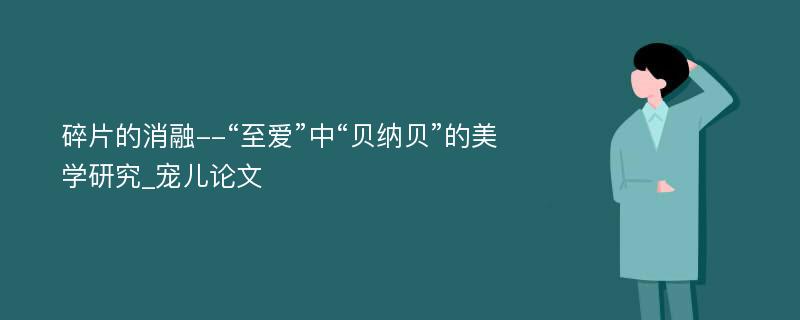
碎片的消融:《宠儿》的“百纳被”审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宠儿论文,碎片论文,百纳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62(2012)03-0093-04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是美国当代一位著名的黑人女作家,其作品享誉世界。她的第5部小说《宠儿》(Beloved)于1987年出版,并于1988获得了美国普利策奖。这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也历来被美国作家们视为一种崇高的荣誉。1998年,《宠儿》被搬上银幕(香港译名《真爱》,大陆译名《宠儿》),由美国著名电视主持人奥普拉·温芙蕾饰演的美丽的主人公赛丝成为家喻户晓的银幕形象。2005年《宠儿》又被改编为歌剧《玛格丽特·加纳》,在底特律歌剧院举行了首演。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宠儿》已跻身于现代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西方许多大学文学系的现代派文学、意识流小说、黑人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课程均将其选入必读书目。[1]
创作这部揭露美国黑奴制不尽的精神残害的小说的灵感,源自于莫里森为兰登书屋编辑《黑人之书》时接触到的一个真实故事:19世纪50年代,一个叫玛格丽特·加纳的女奴在逃亡途中被奴隶主追捕。为了避免女儿重蹈自己做奴隶的悲惨命运,她抄起斧子砍断了不到两岁的女儿的喉管。当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莫里森便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希望通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探究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为饱受奴隶制摧残的美国黑奴们著录一部心灵史。但在创作手法上,莫里森对过去故事片段的兴趣不只是谴责美国白人奴役黑人的罪恶,而更多的是希望揭开黑人破碎的过去,将之缝进非裔美国人以及美国人自己的“文化之被”。这部小说的创作技巧与黑人民间传统的百纳被缝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百纳被的表现形式下蕴涵着深刻的百纳被的美学意义。作者独特的题材选择、多重的叙事视角、非线性的叙述手法以及多变的叙事话语蕴藏着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融洽的整体与局部关系,从而使小说具备了百纳被的美学效果。正如非洲祖先们用不同颜色和尺寸的布料缝制百衲被一样,莫里森运用零散的、破碎的知识,以多层次、多样化的艺术技巧缝合了自己多彩的百衲被。
缝制“百纳被”的民间传统源自英国和非洲,后来流行于北美殖民地。这是一种将不同颜色、不同形状、不同材质的碎布拼制成被子的手工工艺。当时的女性一般将旧衣服或其它废旧布料剪成碎片,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设计好图案,再将这些碎片一块一块地缝制到一起。由于当时物资匮乏,所有的女孩子从小就学习缝制百纳被。缝制百衲被一般是社区的妇女们聚在一起集体完成,这种活动融洽了妇女间的情意,成为她们彼此学习、交流思想的重要渠道。在历史上,百衲被的缝制在美国社会、家庭和文化传统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既有实用性也具有审美意义,在获得保暖效果的同时,百衲被还是当时妇女传递信息与情感、延续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百衲被是叙述的而非抽象的,他们是直接源自于他们用来传递文化、保存历史的讲故事的口头传统。”[2]由于整个“百纳被”的制作过程与文学创作过程有相似之处,“缝制百纳被(quilting)”也就被女性主义批评家们视为美国女性主义写作实践的一个重要隐喻。它的美学意义在于打破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因为任何一块碎片都是整个被子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碎片的选择——精挑细拣
“(莫里森)用无处不在的物体碎片、身体碎片、精神碎片、家庭碎片以及社区碎片展示了美国社会种族、文化的断裂。”[3]《宠儿》这部小说安排了很多碎片的意象。赛丝的身体因为受到鞭挞、强奸、被人强行吸掉奶水等暴行而失去其完整性。她的背上留下了一棵像结满了肉瘤的树的烙印;在“甜蜜之家”被“学校老师”(奴隶主)用皮鞭抽打得皮开肉绽;被奴隶主的侄儿无耻地吸走她哺乳婴儿的奶水,疯狂地践踏她作为一个女人最神圣的母性;鬼魂总是在向她提醒过去的伤痛,使她的灵魂得不到片刻的宁静;母爱、悲伤与内疚在她的内心深处纠结着,使她的精神饱受煎熬,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赛丝的家也是破碎的:丈夫在发疯后神秘地消失了;大女儿宠儿被母亲割喉而死;两个儿子因为不堪鬼魂的骚扰而离家出走;婆婆萨格斯也已经去世。赛丝和黑人社区之间的联系也是破碎的:人们抵制萨格斯的宴请和林中布道;邻居们的冷漠使得“学校老师”带人来抓捕她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来与之通风报信。她和女儿丹芙住在人迹罕至的124号,由于闹鬼,周围的邻居都对她们家疏而远之。通过这一系列的意象,莫里森不只是在揭露奴隶制与种族压迫给黑人带来的伤痛,同时更多的是在表现个人与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的冲突、白人与黑人之间存在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莫里森在《宠儿》的扉页上写道:“献给六千万甚至更多”,以纪念在科学和民主光环笼罩下的美利坚的黑奴亡魂,以历史回顾的方式抨击了100多年前被废除但阴魂不散的奴隶制。正如莫里森自己所说,“这是黑人不愿意回忆的,白人也不想回忆……这是国家的记忆缺失症。”[4]这部美国百年历史的画面就如同百纳被,作者将这段历史分成了不同的碎片,每一块碎片都讲述了不同的故事。瑟曼(Judith Thurman)曾指出:作家如同将灾难性事件的场面画到一块黑色玻璃上,“她把这些玻璃打碎,然后以互不相连、令人迷惑的现代形式将其重新组合”。[5]从小说一开始,莫里森就叙述了一系列发生在不同时间段的故事,这些故事的片段就像百衲被的碎片一样被拼接在了一起。这里有萨格斯临终前的情形,有赛丝为了给宠儿碑上刻字而不得已与刻字工人以出卖肉体进行交易的无奈,有保罗·D来124号找赛丝的情形,有赛丝回忆她跟黑尔结婚的甜蜜,有赛丝如何在逃亡的途中在白人女孩的帮助下生下丹芙的艰辛,有赛丝和保罗·D、丹芙一起参加狂欢节的情形,有赛丝、黑尔、保罗·D他们在昔日的农场“甜蜜之家”遭受的种种磨难,有回忆贩奴船的片段,有赛丝逃到辛辛那提后与萨格斯相聚的幸福,有“学校老师”追来要抓走赛丝和她的孩子们时赛丝情急之下将宠儿杀死的惨状,有赛丝带着丹芙坐牢的痛苦,有杀婴事件发生后124号的闹鬼。这些过去的事件与现实的事件交织在一起,使得故事在琐碎的碎片的拼接中显得扑朔迷离。“(莫里森)用叙述片段为她的人民求声音、求存在、求在场;用历史片段为他们求自尊、求自信、求未来”[6]“过去”是之于非洲传统、美国南方、奴隶制、“甜蜜之家”以及不可言说的伤痛的“过去”。隐瞒任何一段“过去”都意味着历史的残缺,而所有“过去”的集合将谱写成一部非洲裔美国黑人的史诗。
二、碎片的拼接——精湛的技艺
“叙述充当的是将故事碎片缝进大文本的缝纫行为”[7]在《宠儿》这部小说中,莫里森并没有遵从传统小说的写作方式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来讲述故事。故事的情节简单,不具有明显的开头、高潮和结局,而是将过去与现在纷繁地交替在一起。小说中1873年的现状与18年前的弑婴惨剧交织起来,又不时地闪回到遥远的过去:贩卖奴隶的时代;昔日“甜蜜之家”劳作的时代;“学校教师”对奴隶残酷迫害的年代;赛丝逃亡的历程、丹芙的出生经历;儿子出走的情景;萨格斯的去世等等情形纷繁复杂地交织着。
小说正是这样穿梭于时空之间。时而回到过去,时而又讲述现在。作者的用意在于突出相对独立的故事片段,这种错乱颠倒的时间顺序深化、突出了主题:过去没有消失,也不能被遗忘,现在源自于过去;人们要想发现和形成完整的自我,就不能割断与过去的联系;应当重新整理和审视历史而不是沉迷于过去的成功或失败,喜悦或痛苦,而应在历史中确认自我,从而在现在的生活中重新塑造和把握自我。“同样,只有健康的社会才能面对历史,正视历史,不管历史曾经多么黑暗;只有真正面对过去,才能拥有未来”[8]。
托妮·莫里森的这种故事叙述模式挑战了西方文学理论关于线性时间的概念,而这种非线性时间的概念更贴切地表现了美国的历史及其黑奴生活。这使得读者不仅能感知到奴隶制对奴隶身体的严重戕害,还能感受到奴隶制给奴隶带来的严重的心灵创伤。这种非线性的时间顺序也造成了最复杂难缝的百纳被,只有技术高超的缝补者才能够缝合出这样一条复杂多变的百纳被,而这也正是《宠儿》这部小说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在尼采看来,“对于世界的诠释没有限定的方式”[9]。现实依赖于不同的感知者的再现,多重叙述角度比单一的叙述角度更富于表现力。莫里森采用多变的叙述视角,颠覆了传统的一元叙述视角的模式。《宠儿》之所以成为经典,与小说中多变的叙述视角有着重要的关系。多重叙述视角扩大了叙述的自由度,因而能全方位、多角度地叙述故事,拓展了小说的叙述功能,也使得小说展现出碎片的模式,蕴含了百纳被的美学意义。《宠儿》中许多重要事件都是通过多重视角来表现的。小说中赛丝杀死婴儿以及丹芙的出生等这样的故事都是由多人从不同的角度讲述的:在“学校老师”的眼里这些故事是血淋淋的,毫无人性的,“里面,两个男孩在一个女黑鬼脚下的锯末和尘土里流血,女黑鬼用一只手将一个血淋淋的孩子搂在胸前,另一只手抓着一个婴儿的脚跟。她根本看不见他们,只顾着把婴儿摔向墙板,没撞着,又在做第二次尝试。”(178)赛丝对于这一情节的回忆基本上都是一闪而过,她认为“我把我的宝贝儿们带到了安全的地方。”(195)保罗·D则认为赛丝的“爱太浓了”。(196)塞斯背上的伤疤也是通过多角度的描述一次又一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保罗·D认为塞斯背上的伤疤“简直就像一个铁匠爱得不愿示人的工艺品,”(21)或“一堆令人作呕的伤疤”(26)。对于白人姑娘爱弥来说,伤疤“是棵树,露。一棵苦樱桃树。看啦,这是树干——通红通红的,朝外翻开,尽是汁儿。从这儿分杈。你有好多好多的树枝。好像还有树叶,还有这些,要不是花才怪呢。小小的樱桃花,真白。你背上有一整棵树。正开花呢。”(93)祖母贝比则认为那伤疤是“鲜血的玫瑰”。(111)
莫里森用多重视角讲述故事这一方式填补了黑人尤其黑人妇女缺失了的话语权,淡化了白人主流话语对黑人历史的干预。比如在对杀婴故事的叙述中,读者首先被迫接受白人奴隶主的话语,在这个话语中,赛丝表现出疯狂的动物般的特征,其行为似乎背离了正常的母性。实际上,这个带有种族偏见的话语在明显地否定和歪曲黑人的价值体系。然而,长期以来,黑人的历史总是通过这种话语被歪曲地再现。只有当赛丝打破失语症似的沉默,直面惨痛的过去,参与叙述时,这个故事才获得了完整的叙述,它的深层意蕴才显现出来。黑人女性的话语体现了黑人女性这个特殊群体的特殊心理,也使得小说更加丰满和完整,深刻反映了美国社会不同种族、不同阶级迥异的、复杂的个体心理。如同用不同质地和不同颜色的碎布缝合的百纳被,小说也更加彰显其层次性与丰富性。
在小说中,莫里森采用了灵活多变的叙事话语—叙述性话语、间接形式的转述话语和意识流。在得知是赛丝亲手将自己的婴儿杀死的时候,保罗·D这样说:
“你的爱太浓了,”他说道,心想,那条母狗在看着我;她正在我的头顶上穿透地板俯视着我。
“太浓了?”她回答道,又想起了“林间空地”,贝尔·萨格斯的号令在那里震落了七叶树的荚果。“要么是爱,要么不是。淡的爱根本就不是爱。”
“对。它不管用,对不对?它管用了吗?”他问。
“它管用了。”她说。(196)
这种叙述性话语扩张了读者与人物对话的时间与空间,让读者能更加客观地把握人物不同的价值取向。
当保罗·D感受到塞斯在袒护丹芙时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母爱的时候:“危险,保罗·D想,太危险了。一个做过奴隶的女人,这样强烈地去爱什么是危险的,尤其当她爱的是自己的孩子。最好的办法,他知道,是只爱一点点;对于一切,都只爱一点点,这样,当他们折断脊梁,或者被胡乱塞进收尸袋的时候,那么,也许你还会有一点爱留给下一个。”(54)在这里,间接叙述话语有利于把保罗·D的心理活动展现在读者眼前。这段间接叙述话语直接指出了奴隶制体系下一个黑人妇女浓厚的母爱所产生的危机。在奴隶制下,奴隶主夺取了黑人的一切,包括财产、象征身份的名字、婚姻,以及爱,父母子女之间的爱。而赛丝正是在和这种黑暗的奴隶制度进行着不屈的抗争。作为这种残酷制度的见证人与受害者,保罗·D深知强烈的爱潜在的危机,对他心理的描写也成为不同碎片联结的丝线,为故事的发展进行了恰当的铺垫。“语言的活力在于描述讲述者、读者和作者现实的、想象的以及可能的生活。”作者在1993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感言很好地诠释了自己的写作实践。
《宠儿》也有较多的典型的意识流成分。由于人物回忆过去的内心独白都是立足于现在,使得历史与现在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在小说的第二章,赛丝、丹芙和宠儿先后进行了内心独白。赛丝的独白洋溢着对宠儿的母爱,表达了对女儿归来的喜悦,夹杂着自己童年缺乏母爱的痛楚以及在“甜蜜之家”的辛酸。丹芙的独白则充满了对拥有姐姐做伴的渴望,对从未谋面的父亲的思念,糅杂着对母亲杀死姐姐的恐惧。而宠儿的内心独白形式则别具一格,是由大段的文字堆砌的,中间没有一个标点符号,纷杂的意象混合在一起。前一部分描述了黑人从前在非洲摘花的幸福的田园生活,后半部分则是黑奴被贩卖、被挤在贩奴船舱的惨绝人寰的遭遇。最后,宠儿、赛丝和丹芙既独白又对话,组成了一段诗歌般的文字,变成了不同的心灵的交汇。它既是生活在奴隶制及其阴影下的黑人女性共同感受的横向交流,也是分别代表过去、现在、未来的黑人女性心灵的纵向体验。
三、百衲被的完成——走向融合
莫里森用高超的技艺将故事碎片缝合成了一条多彩的百衲被,在被子里面缝进去的不仅是故事,更有她的梦想和期待:将断裂的过去与现在乃至将来缝合成了一个整体,期待黑人族群与美利坚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未来的理解与融合。
“你是说我从没给你讲过卡罗来纳?没讲过你爸爸?你一点儿不记得了,我的腿脚怎么变成了这副样子?不记得你妈妈的脚,更甭提她的后背了?……记住它,然后走出院子。走吧。”(291)。这个来自过去的萨格斯的声音鼓励和指引着丹芙走出自己的家,走到外面向邻居们寻求帮助。邻居们给了她善意的关怀,也讲述了更多过去的故事。在他们的帮助下,鬼魂被驱散了。最终丹芙不但获知了赛丝的过去,还了解了整个黑人社区的过去,接着在黑人的历史中发现了自我,在黑人这个群体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使她满怀勇气、信心和希望去面对现在和未来的生活。
作为“甜蜜之家”最后的一名男子,保罗·D与赛丝的重逢与结合是偶然中的必然。故事在保罗·D与赛丝的重逢中拉开序幕,他的到来实际上是来帮助赛丝重现回忆。只有等他们清理好记忆的残片,将所有的故事连成一个整体之时,赛丝沉重的记忆之门才被缓缓打开:人性、屈辱、心灵的扭曲、爱与暴力的错位——各种复杂交错的心理在沉默、回忆、停顿、诉说中得以深刻展现。
百年前美国奴隶制的废除并未能彻底解除黑人民众的苦痛,也未能使他们在这个自诩为“民主、自由、博爱”的国家中免于生存的灾难。残酷的私刑、嗜血的三K党、靠出卖肉体来维持生计的黑人姑娘、处于社会底层被剥夺政治和教育权利只能忍辱偷生的黑人大众……莫里森无时不在地向人们警醒奴隶制残留下来的对黑人的压制与迫害。莫里森竭力肩负起拯救黑人同胞的责任,并在小说这一艺术形式中探索着他们的救赎之道:黑人应该象萨格斯林中布道所宣扬的那样,“黑人应该自爱、爱自己、爱自己的肉体……”,做到自爱,爱自己的身体,爱自己的社区,爱自己的历史,爱自己的文化,爱自己的民族;要象保罗·D和宠儿的出现唤起了赛丝对于过去的痛苦的回忆一样,黑人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超越时空,找到真正的自我;要象丹芙勇敢地走出来寻求邻居的帮助一样,整个黑人民族只有团结友爱才能找到出路;要象爱弥那样的白人及时地伸出援助之手,黑人和白人才能凭借超越民族、肤色界限的最崇高的爱告别过去,面向未来。通过富于张力的艺术表现与对救赎之道的不懈探寻,《宠儿》这部小说达到了一个崭新的艺术高度与思想深度,并因之而被喻为美国黑人历史的一座纪念的丰碑。
本文引文均引自潘岳、雷格译:《宠儿》,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