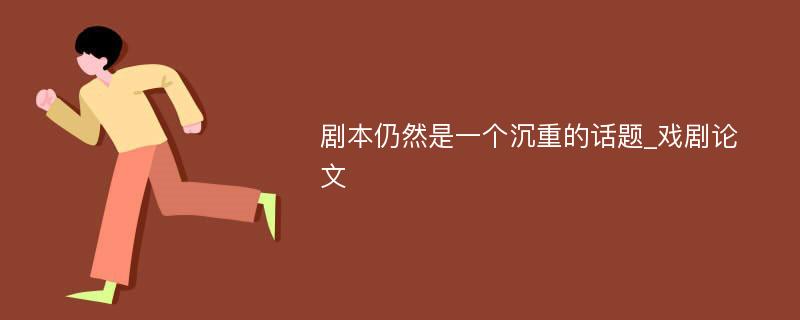
剧本,依旧是沉重的话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本论文,沉重论文,话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剧本,是一剧之本,已是个相当陈旧且沉重的话题了,然而却又不得不直面之。近半年以来,就这个话题,已在不少的报刊上,一些圈内圈外的人士纷纷表示关注,分析结症所在,提出了不少的真知酌见。譬如,剧作家又是北京人艺当家的副院长刘锦云认为,使他最愁的就是剧本。他说:“这是近几年来的最困难的时期。优秀的、可以传世的剧本,我们不敢奢求,退而求其次,就连能够上演的本子实际上也很难找。”(1996年10月28日《北京晚报》)评论家刘平的一篇述评中认为,北京’96话剧舞台的热闹红火之中感觉到了一种一哄而起的浮躁,“概括地说,这种感觉大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非艺术家的商业性演出的‘炒作’;二是戏剧创作者的浮躁情绪及某些剧本的‘急就章’创作。”“‘急就章’式创作的后果必然是艺术上的粗糙。有的戏虽说凭借一些手段使演出场次不少,但整个创作并没有进入艺术的层面。”( 1997年4月5日《文艺报》)
我多年来接触过不少的演出团体,我也深有感触。普遍现象是,演出团体寻找不到过硬的本子,“等米下锅”。或者也是“急就章”式的将不甚成熟的剧本推出。再加上演出市场也不景气,还不能算是正常运转,即便是偶尔露出的一线亮色,多数也是戏外因素所为,形成并不理想的运行机制。因而我依旧认为,这种现象的关键之一在于剧本,还是应该抓“之本”的东西,才能治本,使艺术生产纳入正规的轨道,使戏剧文化创立自己真正的、健康的、繁荣的市场。
纵观这一二年的话剧舞台,我认为这个问题显得更为突出。首都主要的几家剧院,如上面已提到的刘锦云所言,收到的初有水准的剧本愈来愈少了。我在青艺工作时期,从80年代中期,能收到上百出剧本。打从那个时候以来,就呈每况愈下的势态了。而今,一个剧院每年能收到十来出新创作的本子就相当不错了。这里,影坛上也如此。在北影工作的剧作家苏叔阳也“家事外扬”,前期对记者坦陈说,80年代的北影文学部,一年总要收到三四百个剧本。但现在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一年也就几十个剧本,大部分还都是业余作者写的。而其中可谓优秀的电影剧本更是廖廖。这种情况与话剧舞台可以互相印证。同时,从舞台上推出新的生产剧目也不多,同样也能窃视到创作数量减少的结果。近年,一个大剧院每年演出的大型剧目只有二出左右,与应能生产的水准是不甚相称的。可见,大剧院们所面临的“剧本荒”的课题是一样严峻的。
那么,从已经被推上舞台的演出剧目来看,“一剧之本”的剧本是否都已达到了令人满意的境界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也需要从“治本”着手。例如,近期正在演出的一出反映当代生活的话剧,叫《找不着北》,讲述老哥俩的一段生活经历。他们不同的人生境遇,不同的价值观念,造就了哥俩的差异和不同形象。可以看到剧作者创作的初衷是不错的,也看得到剧作者对周围生活的一腔热情和对普通人生活的关注。然而,细究起来,剧本经不起推敲。虽然,它不是常规的演出团体的演出,有自己特殊的难度。但是从剧本上来看,戏剧情节过分简单、直白,人物色彩也显单薄、苍白等,因而,在舞台上尚欠火候。看得出来,演出者想在二度创作上设法弥补,但颇有“无米之炊”之势,弥补是极其有限的。如那位泥瓦匠的老哥人物,我觉得他的感情脉络显得不够合理和清晰,表演者越投入就越让人感到别扭;又如那位徒弟的角色,把握也不够准确,随意性过强,让人出戏。尽管演出者起用了成熟的老演员乃至人们喜爱的“大腕”。可是终因“之本”之因,我认为不能视为成熟之作,外在的因素、包括流行的包装,并不能带来好运。又例如,前期还有一台演出,剧名《漂亮女人》,起的剧名也是挺惹招人的,演出者也是一些响当当的、有知名度的人物。然而,我觉得同样也没有达到“包装”宣传中的预期效应。名曰“喜剧”,但让观众可笑可喜的地方并不多。当然,写好当代生活的喜剧,其难度会更大些。要将观众逗乐、导入特定的当代生活的喜剧情境,也不是依赖戏外因素所能凑效的。该剧写当代两个女性的命运,视角倒是较新的,毛病却出在对人物命运的把握与定位。其性格、其语言、其动作等,缺乏喜剧的因素。剧作者还没有大胆地“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鲁迅语);更谈不上“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的那种“妙境”了(李渔语)。因此,“漂亮女人”在舞台上并没有达到“漂亮”的效果。上面例举的两出剧目,我无意作更多的褒贬,我更不否认演出者的勇气和执着,我深有体验要推出这种方式的演出,已付出了相当艰辛的劳动了。我只是想说,提供的本子未达到较为理想的基础,从而使二度创作不能有更大的作为。
不过,这类演出的舞台面貌和情况,并不只出现在“制作人”制作的舞台上,在大剧院“正规军”舞台上也不尽人意,同样能见到因剧本不“达标”而捉襟见肘的窘境。如青艺演出的《关东大集》是部火辣辣、热闹闹的当代生活戏剧。从剧本上去挑毛病的话,其戏剧情节显得散而不聚,人物性格形于外而未动于衷,缺乏内在、有机的扭结和张力,看个热闹而已。又如,目前已被人们普遍看好的北京人艺演出的《古玩》,应该说在近期的舞台上,已属姣姣者了,包括上座率。假如苛刻地去审视的话,假如本子更为成熟的话,这台演出将会更有自己的历史色彩。该剧讲述历史时空跨度达三十多年的故事,又趋在风云变幻的动荡岁月,要牢牢地抓住人物命运的主调,并准确主动地编织起一幅幅历史画面的缩影,是有相当难度的。年轻的剧作者付出了更大的艺术劳动的汗水是不容置疑的。从演出来看,偶有“走失”、“变调”之感,在拨弄近代历史的音符中,还夹带着一些杂音。譬如,剧中贯穿全剧始终的、已被人格化了的那只鼎,对它的泼墨浓写还不够;对它的“命运”还可以更关注。这样更能搅动起金鹤鑫、隆桂臣等“玩古者”们心灵的波澜。可见,剧本的整体结构中所显露的散淡、游弋等弱点,淡化了理应更可以生动有趣的历史世俗景观。不过,人艺的艺术家们为本子作了一定的调整,或者说校正,使之弥补了不少剧本本身的一些不足。再如,实话今夏上演的《生逢其时》,倒是相当贴近生活——面临下岗和下岗工人的生活。这是当前十分现实、十分尖锐的社会问题。剧作家敢于大胆地碰撞这个严峻的课题,敢于干预这个紧迫的生活,剧作家的勇气和社会责任感是令人羡佩的。在当前现实里尚在摸索、尚在解决过程中的问题,要在舞台上得到回答,显然是不现实的,更不是剧作家应担的责任。正因为过分逼近生活,与生活同步的舞台生活,让观众一下子与舞台人物融置在同一种生活的节奏里、氛围中,给人以直观性强的愉悦,但同时因缺乏一定的审美距离,而产生不了应有的、带有陌生化的、理念的审美效果。如剧中主人公、厂长崔建立自告奋勇、走马上任后所遇到的一连串的问题,以及他的思考、困惑、无奈、喜怒哀乐等,同时也是台下观众所遇到和思考、关注的课题,几乎是同步行进的,还来不及“品味”而被翻了过去,划不下生活的印迹而失之肤浅。尤其是戏剧的结尾的过分理想的色彩,反而使这个人们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削弱了思辩的魅力。或者说收尾显得“急就”了。然而,这既可以说是剧作家的无奈,更应该说是生活的无奈。该剧的作者是善于把握生活脉络、善于营造舞台氛围的。他捕捉的生活气息和时代色彩是能够被普通人所接受的,包括生活细节的描述、人物心理世界的透视、喜剧化的情节架构等,都已相当到位的了。我想强调的是剧作家还可以从更高一点的视角,就会迈上更高一个艺术层面了。
因此,从当前不同团体、不同类型的演出舞台上,运行成败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需要挑剔的毛病,主要是在“一剧之本”上。当然,舞台艺术是综合性极强的艺术,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但其他因素再多,先“治”剧本是首当其冲的。“治”剧本或者说抓剧本,也存在抓主要矛盾的问题。我从当前演出剧目的现状来看,抓不出或抓不住好的、较好的本子,有一些明显的结症,也存在一定的误区。有的是客观的、外在的,有的是主观的、内在的,也可以谓之“大气候”与“小气候”。例如,有文化市场的运行机制的问题,有创作队伍的素质和流失的问题,也有经济上分配的问题,等等。我在这里想说两个方面的问题,依旧是老话题,沉重的老话题:一是抓什么样的题材内容;二是怎么样对待生活。
一,剧本的成败,它的题材内容虽然不能起决定的、绝对的作用,但是轻视和忽视题材内容的因素也是不可取的。近年,人们对“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有了更准确的把握,也出现了不少的好作品,应该说是个必要的导向和可喜的现象。如果剧作家没有为自己的时AI写作出时代的强音,没有为身边的纷繁多姿的生活谱写新曲,那么至少可以说,剧作家尚未完全尽到自己历史的、社会的责任。但如何对待“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及其关系,在创作中又如何把握,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我认为“主旋律”与“多样化”是整体性的一个话题,不能分割开来加以思考。近几年来,有一些剧目的创作就缺乏整体性的视角,往往分而言之。常说这个剧是“主旋律”的,那出戏是“多样化”的;或者说,眼下先抓“主旋律”的,而后再弄“多样化”的;云云。试图将“主旋律”与“多样化”截然分开来界定戏剧的方位,将前者看作是思想内容上的,后者视为形式样式上的,我认为是形而上学的观念。譬如近年内上演不少讴歌英雄模范人物为题材的纪实性的戏,有配合某项活动和政策的戏,还有为了参与评奖或得奖的戏,就冠之属于“主旋律”的戏。于是,方方面面就十分投入。假如说是一出英模戏,选材上是“好人好事”式的,人物是正面的色调,不能染上点灰色,表现结构往往是串“冰糖葫芦”式的。这已是十分省劲、已被模式化了的创作思路了。我觉得这个模式本身并不坏,可以运用,也可以创造出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80年代早期有《陈毅市长》,近期有《孔繁森》等,但这并不等于所有这类模式的戏都能成功的。不动脑筋,不投入真正的情感和激情,“轻车熟路”去套用它,是唱不响真正“主旋律”的。内容陷入概念,形式一旦僵化,艺术的生命力就大打折扣了。这里,从“主旋律”的视角看,是忽视了“多样化”的存在。这样的戏,思想性上是无需怀疑的,但是否能被观众乐意接受,就值得怀疑了。可以说它的大幕一闭上,戏的生命也就结束了。这类的戏,还有在发展的趋向,是值得思索的。从这些舞台上,进一步看到了剧作家的心态是浮躁的,创作是“急就章”式,甚至是应酬、应付式的。还远不如60年代初期的一批剧作。如《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青松岭》等。抛开当时特定的因素之外,它的艺术上的“多样化”是下了功夫的,也是有成就的。而今天的这类作品很少达到这个水准。模式的滥用,又泛滥开去,不是对“主旋律”的弘扬,而是一种虔诚的“捧杀”,适得其反。我想,这也不是剧作家的初衷,也会让观众产生逆反的观赏心理。
反过来,走向另一个极端,一说它是属于“多样化”的剧目,就一下子用“艺术”的标准去要求,去衡量了。这同样是十分偏颇的、形而上学的观念,掩盖了另一种缺乏整体性的创作倾向。勿庸置疑,“多样化”不是无内容、无思想的多样化,不是脱离历史、时代、现实和生活的多样化。如果是这样的“多样化”,就是没有“根”、没有“源”、没有“魂”的多样化,也从根本上失去了“多样化”的意义。恩格斯当年在“席勒化”还是“莎士比亚化”的天平上,并没有倒向哪一边。他说“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这段话,依然是今天“主旋律”和“多样化”之间关系的最好注释。
因此,处理好“主旋律”和“多样化”的关系,使我们的戏剧舞台才能创造出有生命力的作品。“伟大艺术家永远是自己时代的眼睛,时代通过这只眼睛来看自己,并且见到了自己。”(罗曼·罗兰语)戏剧家如果不睁大自己的“眼睛”去洞察、认识世界和生活,一味地追求某种功利性的创作,是短视行为。虽然,这并不完全是剧作家的责任,或者是出于无奈,但是我仍然希望剧作家要有勇气和主见,排除非艺术因素的干扰,用自己的“眼睛”,写出充满自己热情和真诚的作品。近年,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少结合好的、比较成功的剧作。如前期演出的《商鞅》、《地质师》等话剧,便是例证。
二,如何对待生活,是剧作家毕生的课题,也是一再探讨的课题。我仍然很欣赏歌德的一句名言:“生活之树是常青的。”他说:“依靠体验,对我就是一切;臆想捏造不是我的事情:我始终认为,现实比我的天才更富有天才。”“天才”的歌德对生活抱着虔诚的态度,当代剧作家、哪怕也是“天才”型的,恐怕也不能背离这个艺术的戒律。眼下仍有不少剧作,尤其是在视屏上看到的千篇一律、矫娇二情的冗长电视剧,无疑是对生活的一种亵渎。生编硬造的情节,虚假的标签式的人物,以及硬侃的语言等。即便是被定为“主旋律”的纪实性剧作,也显示出生活“贫血”的症状。有人揶揄地将这类作品归纳为几种套路。如一位普通干部奉公敬业,工资低住房差,但整天忙于工作。妻子体弱多病但贤良无比,女儿聪明伶俐但无人照管而学习较差。于是纠葛出一堆矛盾。如忘了给孩子过生日,孩子提醒下才想起;又因囊中羞涩只买个很便宜的礼物,却又接到紧急任务或因病倒无法赶回家一起过生日,令人“扼腕叹息”一番。这是“家庭”式的。又如写一位改革者,奋力改革但阻力重重,其阻力来自上级的副级,而动力则来自更上一级的领导。同时,顶头副级往往还有市里或省里的更大靠山。这样显得矛盾一环套一环、一级压一级。待矛盾到可以人为收场的时候,让更高一级的领导出场了,一切迎刃而解,随之结尾的主题歌悠然而起……这是“改革”式的。还可以有“情爱”式的。如主人公(他或她)有胆有识有貌有财,是个大情种。有几位很不错的女郎都喜欢他,但他发乎情也止乎礼,绝不过分不能影响自己的形象。只是说明他“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而已。于是,三角四角,死去活来闹腾一番,表现“人性”或“现代意识”。这些套路还可以举出更多,里边的人物也可以换成老板、公关小姐、洋职员等。
出现这种创作倾斜,如此浮躁,如此媚俗,如此概念,正是反映了剧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有人认为,戏是可以“侃”出来的,这倒不必急于否认。只要有生活,有对生活的真切感悟和真知酌见,也是“侃”得出好戏的。只怕是闭门造车、胡编乱造,以“东施效颦”之举,去创造出一个“西施”来,是近乎天方夜谭的。说得苛刻些,这是对生活的嘲弄。如果剧作家嘲弄生活,那必将遭到生活的嘲弄。
我们也有一批剧作家历来是相当重视生活的,开掘着生活的“深井”,找到了永不枯竭的创作甘泉。远的不说了,我想到的是一位大庆剧作家杨利民。他不久之前推出的话剧《地质师》,令人震撼,给我们一股沉思的力量。其成功的最根本的因素,是生活的恩赐。
杨利民是土生土长的大庆油田的剧作家,他的每一部剧作都可以让人闻到石油味,油田生活贯融、维系着他整个创作生命。他的每一出戏,已是一幅幅当代油田生活的画卷,成了当代油田的艺术代言人了,礼赞着油田的生活火花,颂扬着油田之子的衷情。《地质师》正是一曲油田之子的赞歌。剧中以洛明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为开发油田作出了惊天动地的奉献,所付出的血和汗的代价,令人震颤。贯穿演出所高唱的《勘探队员之歌》,把所有的人拉回到如火如荼的岁月,那么亲切,那么扣人心弦。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90年代的《年青的一代》,而只是换成今天的视角,呼唤着当代仍需要的奉献精神。洛明象征着“骆驼精神”,谱写了悲壮的、地质学子所特别拥有的世界。杨利民正是拥有了自己的生活世界。他的厚重的生活基础和底蕴,并不是朝夕之间淀积起来的,是杨利民长期浸泡生活的结果,是全身心地慕拜和拥抱生活的结果,顺其自然地流淌到舞台上的。在他身上,创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是疏理不清的“源”和“流”的关系。所以,《地质师》的舞台是一曲生活和生命的交响诗,它的每一个音符的背后,都凝聚着剧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崇拜和付出。左拉曾动情地说过:“我在艺术里只有一个热烈的欲望——生活。我用我的爱情忠实于现代的生活,忠实于我的整个时代。”剧作家杨利民的作品正是这样的“爱情”结晶。
戏剧离不开生活,尤其是话剧舞台及时、鲜活地表现生活,是它的一项强项,与生活更为密切,更似鱼水之间的关系。我相信,既然是生活之树是常青的,那么,我们的戏剧艺术之花也永远不会凋谢的!
总而言之,当前的戏剧舞台仍是要关注剧本的问题,需要进行“综合治理”。道理很浅显,说来也容易,但做起来不会轻而易举。我看到如戏剧剧本问题上存在的这些现象,也只是一孔之见,开的不是一张包治百病的方子。对具体的创作问题作具体的分析和观照,作一些理性的思考,“间离”一下,使之疏导得更清清晰晰。这就让我想起戏剧家黄佐临先生生前对当时舞台状态的评说。他对90年代初的状况认为,舞台趋于一种“沉积状态”,要打破这个状态还需要一个时期。那么,时至今日,这种“沉积状态”是否已被打破?我觉得从剧本创作状态来看,还要走一段艰辛的道路,一段谁也迂回不了的路。然而,我想,只要按艺术的规律去行进,只要坚持不懈地去打好剧本的基础工程,“沉积状态”之后,必然会勃发、涌动出新的艺术生命。我期盼着剧本创作喷发出新一轮的曙光,去照亮新世纪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