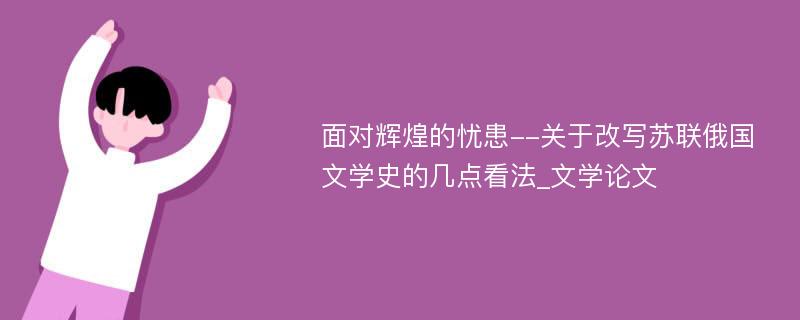
面对辉煌的忧思——关于重写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史的意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维埃论文,忧思论文,俄罗斯论文,重写论文,文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苏联文学曾在世界文坛占有举世瞩目的地位,给人类留下许多文学瑰宝。苏维埃时代的结束并不能抹煞苏联文学的辉煌,只是引起人们更深入的思索,重新认识与评价这段文学历程。这是摆在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者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鉴于苏联文学研究界认识上存在分歧,笔者提出几点个人意见,期望文学史家重新思考:如何看待苏维埃历史时期,什么是文学的性质与功能,何谓真正的作家与不朽作品等几个重大的问题。
【关键词】 成就辉煌 重新评价
从十月革命胜利至苏联解体,七十多年构成了一个特殊时代,它在历史长河中不算短也不算长,更重要的是它给整个人类历史造成了巨大影响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在这七十四年里也经历了一段曲折、艰难、痛苦,然而却是辉煌、悲壮的发展历程。
我们说它辉煌,是因为在这一历史阶段的的确确产生了批震人心弦、发人深省并具有高超艺术性的作品,包括小说、诗歌和戏剧。数量惊人的各种体裁的作品被翻译成各国文学。随着这批作品在世界上影响的不断扩大,一批作家也在各国广为人知,赢得世界性的知名度,为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人民所敬仰、所传颂。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就不断翻译、介绍、学习并研究苏联文学,它对我国几代人的思想成长发生了影响,无怪乎许多上年纪的同志谈起时,都感慨地说:“我们心里都有一个苏联文学情结。”然而,现在却有人企图否定苏联文学的功绩,以为随着苏联的解体,苏维埃时代的文学也就消亡了。其实这是两个问题,一个历史阶段的终结,决不意味着一时代的创造与成就不再发生作用了。有人象十九世纪的虚无主义者那样,跳起脚来,咒骂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称他们为政治的“奴仆”甚至“魔鬼”,否定他们在文学上做出的杰出贡献。还在苏联解体之前,有人(如叶罗费耶夫之流)就要为苏联文学送终,高喊“追悼苏联文学”。然而历史是开不得玩笑的,也不会因少数人的歪曲和随意涂抹而改变其本来的面貌。肤浅的人企图贬低高尔基的《母亲》,可是前不久根据这部小说重新改编的电影在世界电影节放映后,又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发现从新的审美角度去认识这部作品,能够更深刻地发掘小说的潜在内涵,更进一步理解这位伟大作家。苏联文学界曾为《静静的顿河》的作者真伪争论数年,但谁有力量否认《顿河》的不朽价值?又有哪位作家能达到肖洛霍夫写作《一个人的遭遇》这样的思想与艺术境界?苏联文学不会因苏维埃时代的终结而失去自身的价值,它给世界文学宝库留下了一笔别具特色的宝贵遗产,这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过去我们习惯于叫“苏联文学”,其实这种叫法不够科学,既显大又太窄。因为我们实际上着意研究的还是七十多年来的俄罗斯文学,并不能包括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各民族的所有文学创作,而且又不是仅仅服务于苏维埃政治的作家和作品,还应包括这一时代各主要流派和方法的作品。有人试图改称为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我也以为不妥,倒是“苏维埃俄罗斯文学”这个叫法更为贴切一些。这一称谓所指的是苏维埃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主流及其他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学现象。其中不仅包括早被历史公认的优秀作家,而且包括曾因政治原因遭受过禁止、贬斥,然而历史终究遗忘不掉的文学珍品。
1986年以来,苏联文学界出现了一股“回归热”,在各种文学刊物上开禁了一批长期被埋没的佳作,比如布尔加科夫的《狗心》、普拉东诺夫的《地槽》、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们》、特里丰诺夫的《消逝》、格拉宁的《野牛》……它们的问世为我们全面认识苏维埃时代的文学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我们似乎突然发现,原来文艺百花园里还别有洞天,珍藏着如此绚丽、灿烂的鲜花。其实,在以往的漫长、曲折的道路上,许多作家、诗人何尝不是逐渐被承认并得到公正评价的呢,象叶赛宁、阿赫玛托娃等。只不过八十年代“文学回归”浪潮,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重新认识、重新界定、重新评价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尖锐而迫切的问题。
苏维埃时代的文学经历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南京大学余一中教授把它概括为“多元——一元——多元”,苏州大学陆肇明同志则引用一种说法,叫:二十年代的动乱,三十年代的悲剧,四十年代的胜利,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转折,七十年代的停滞,八十年代的改革。无论怎么说,它走过的也是一条曲折、艰难的道路。十月革命后各种流派纷呈,一批朝气勃勃的年轻作家、诗人张开双臂迎接一个崭新的时代,革命前就已登上文坛的作家发生了痛苦的裂变,许多人经过困惑和踟躇而转向革命,工人阶级中也开始成长文学新人,这欣欣向荣的景象到二十年代以后即被瓦普、拉普、伏阿普们破坏了,扫荡了,从此就开始了棍子、帽子满天飞。且不说“没有同路人,不是同盟者便是敌人”这一臭名昭著的口号,即使承认文学的“同路人”就对吗?“同路人”是个什么性质的概念?只能说是政治的,而不是文学的。可是我们有些人至今还在津津乐道所谓的“同路人”文学。“拉普”虽然被取消,曾经一时还被基本否定,但它的阴魂又何曾离开过苏联的文坛?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和理论上的庸俗社会学倾向,不是为苏联作协领导层长期沿袭或曰“边批边犯”吗?位居领导的著名作家亚·法捷耶夫在临终前致苏共中央的信(“绝命书”)中说:“文学界的优秀干部(沙皇的暴吏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有这么多),或肉体被消灭,或死去,而这都是掌权者们无法无天的罪恶行径所致。最优秀的文学界人士过早夭折,其余的人,那些多少能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的人也都活不过四五十岁。”①这个时代的诗人、作家们正是在痛苦的挣扎中,非人道的迫害中创作出辉煌作品的。仅活三十岁的叶赛宁、三十五岁的古米廖夫、三十六岁的马雅可夫斯基都给我们留下了壮丽的传世诗篇。但是,许多作家的英年早逝,另一些文学家毫无道理的被捕入狱,在囹圄中消磨年华,还有一批流亡国外,在苦苦思念祖国的心境中继续自己的创作,这些不能不说是现代文学的悲剧。逆境出人才,悲愤出佳作,苏维埃时代的一代代有才华的诗人、作家在继承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学习并措鉴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欧现代派的创作方法,经历了革命的变革、战争的硝烟、新思想的洗礼、饥饿与苦役的磨炼,各种政策的更迭以及突如其来的荒唐事件、紧张和政治斗争、无端的流言蜚语的打击,或在热情激荡或在愤懑抗争中奋笔疾书,或通过痛苦的思索、冷静的分析和精心雕琢,那些激动人心的短篇、发人深思的巨著便诞生了出来。苏维埃这特定时期的文学,虽然不断受到各种政治、社会因素的干扰,时左时右,有起有伏,但依然沿着自己的轨迹,顽强地求得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真正的文学家“既不畏惧屈辱,也不希求桂冠,赞誉和诽谤都要处之漠然,更不要与愚妄之徒争辩”。他们都天然地具有历史使感,并对历史的公正抱有充分的信心。他们所满足的就是:“我将长久受到人民的爱戴,因为我用诗歌唤起了善良的感情,在我们严酷的时代我讴歌自由,为苦难的人们呼吁同情。”(普希金语)②以往的文学史家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全面地、公正地、实事求是地总结评论这一别具特色的时代的文学发展道路以及它的全部成就和悲哀。他们受到历史的局限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不可能公正评价每位杰出作家、每部确有价值的作品,并且删除那些无价值或平庸的作家及作品,这需要时间。只有当这一时代结束了,人们站得离它远一点,不再受各种非文学因素、错误历史观的干扰,才能看得清楚、真切。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国的福克纳等人,都是在去世很久以后才被文学评论界发现其宝贵价值的。维·卡维林说得好:“当然,只有时间才能让一切都各就各位,而且安置得既客观又准确。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已非一次了。”③现在正是其时,应该着手做这件工作了。因为时间久远了,这个时代的人都已不在人世,写文学只的人就将缺乏真实的历史体验,那就象当代人写秦始皇、唐明皇那样胡编乱造了。
以前所编写的各种苏维埃文学史著作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病,这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较为普遍的问题就是往往以苏共中央在各个历史阶段作出的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决议、指示作为依据,来进行文学发展阶段的划分、素材的取舍甚至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它们在文学批评的标准上往往混淆文学与政治的概念,在文学批评的方法上常常以偏代全,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排斥不同的艺术流派,压制具有不同文学观念的作家。其结果是,一部史著成了少数作家的生平与创作介绍,使读者无法对这一时期人文学历程形成一个起码的总体印象,似乎苏联文学就是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富曼诺夫、格拉特科夫……的文学。近年来维霍德采夫教授主编的文学史包容量较大,不仅续编了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部分,而且将散文、诗歌、戏剧分章编写,对各个时期有贡献、有成就的文学家尽可能地加以介绍,可谓前进一大步。但是正如其前言所说:“然而,苏维埃时代文学过程的许多现象、问题、观点和规律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由于该书第一版距今将近二十年,补充修订版问世也已八年,材料上仍未包括“回归文学”和“侨民文学”,在观点和视野上均存在局限,譬如,一如既往,过高推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现代主义持否定态度,仍未站到时代的高度,更冷静、客观地分析苏维埃时代全部文学的历史存在。
重写苏维埃时代的俄办斯文学史是当务之急,这是认识、研究的需要,也是教学的必需。等待俄罗斯的新版本,已不大现实。原苏联解体之后,特别从提倡“公开性”、“民主化”以来,思想界与文学界开始出现了动荡和混乱。一些人企图否定自高尔基而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只承认那些曾经长期被埋于地下、被禁锢的“历史沉渣”;另一些人变得迷惘了、退缩了或消沉了。当然,也还有一些文学宿将,他们虽然暂时有点沉默,却进行着更为深入的思考。然而,数十年形成的文学史基调仍然是个羁绊,是难以冲破的惰性气层,加之目前俄罗斯所处的政治、经济、思想环境,恐怕近期内不大可能产生理想的新版本文学史。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研究人员当仁不让,大胆地着手进行这项艰巨而光荣的工作,这是值得钦佩和赞赏的。应当说,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积累了一些经验。我国的苏联文学研究界近十几年硕果累累,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写了许多有份量的评论、专著。不过,透过这些文章与著作,通过我们平时的讨论和交换意见,总感到尚有一些原则性的分歧没有得到解决,这将影响新文学史的顺利编写。笔者不揣冒昧,愿就几个重要问题发表点个人意见,仅供重写文学史时参考。
关于文学史主线的问题是争论最多、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苏 维埃时代是一个工农兵在联共(布)领导下举行起义、夺取政权击开创的革命时代,是在两千二百四十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土地上进行社会主义实验的时代。这个时代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革命变革,历史事件,战争与斗争,运动与变迁,轰轰烈烈而又可歌可泣。这些事件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每个阶层、每个家庭、每个人,决定着他们境遇与思想的演变。也正因此,苏维埃时代的文坛才产生那么多内涵丰厚、题材文学的作品。所有反映这些历史事件及各阶层人民在革命变革中的思想感觉的作品,加在一起构成了这一时代的文学主旋律,其他题材的作品只能算作副调与和声。如果把少数创作方法或流派叫做主旋律,必然失之偏颇。
还有几个不容忽视的总理,也需要尽量统一认识。首先是对苏维埃时代各个主要历史事件,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进行实事求是的反思,既不可为所谓的“历史定评”所束缚,也不为“时髦”观点所左右。这将牵涉到对许多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也决定着素材的取舍。例如别洛夫的《巨大转折的一年》和肖洛霍夫的《新垦地》几乎取材于同一时期同一事件,而立足点和着笔处却大相径庭,谁是谁非,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其次要解决对文学的性质和功能的认识问题。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个普通常识,尤其对文学史家来说,几乎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其实不然,往往就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出现分歧。比如,我们在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时,常把一些艺术上很有创新的优秀作品也否定了。须知,文学作品不仅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特征,还具有它本身的艺术使命。诚然,文学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灵,起到“道德净化”、培养新人的作用。但是,除了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外,它还应具有审美功能和娱悦功能,否则就不成其为文学。第三个相应的问题就是关于真正作家的概念了。有些作家(包括上过文学史的作家)确也真诚地创作过,但他们是出于一时流行的信念和追求,写出反映当时表面现象的作品;另一些作家只是完成“社会定货”,写些应景之作。这都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早期的富曼诺夫、别德内等,后期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索尔仁尼琴等,都是各自政治观点的鼓吹家,语言与艺术都相当粗糙,称不上优秀作家,不值得在文学史上大书特书。一个好作家,首先应该是有远见卓识、对生活具有深邃洞察力的思想家,其次当是语言大师和有独特造诣的艺术家。尤·特里丰诺夫说得好:“文学具有一种强大的净化力。真实地再现生活——过去的和今天的生活——可以起到医治、帮助、劝导、拯救的作用。……但是,起作用的绝非仅仅是文学,也不是所有的文学,而是存在于文学、艺术作品、外形和美之中的那个东西——真理的核心。”④谁抓住了、表现了真理的核心,谁才称得起是个好作家。特里丰诺夫本人就是个生动的榜样。拿这样的标准去衡量,我们就能辨出真伪。
重写一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史是一件不易之事。尽管近些年陆续公布了一些过去封存的秘密材料,发表了部分被禁的作品,研究者在探索过程中仍会遇到不少暗礁险滩。以前的史料和评论中,往往夹杂着谎言或捏造。正如美国学者马克·斯洛宁所说:“一个研究者尽管充分施展其才干,也不容易在这种自相矛盾的评价、秘而不宣或者赤裸裸的谎言的基础上找到一条安全的道路。如果要了解真正的文学情况,他就得慢慢研读数量惊人的小说、诗歌、散文、论文、党的决议、官方评论文章——这决不是一桩有趣的工作,而且需要大量的时间、耐心和特殊的鉴别力,从字里行间探求其隐藏的意义。”⑤面对如此大的困难,我国从事苏联文学研究的一批专家学者,毅然决然拿起了笔,踏上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我们只能支持、鼓励,拍手加油,预祝胜利,并翘首期待新一部史著的诞生。
注释:
①亚·法捷耶夫致苏共中央的信,载《苏联文学联刊》1991年第2期。
②《普希金作品精粹》第3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③费·梅德韦杰夫:《详察过去,洞晓未来》,载《俄苏文学》1989年4期。
④尤·特里丰诺夫:《真理的核心——创作扎记》,载《苏联文学》1986年第2期。
⑤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史》前言,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