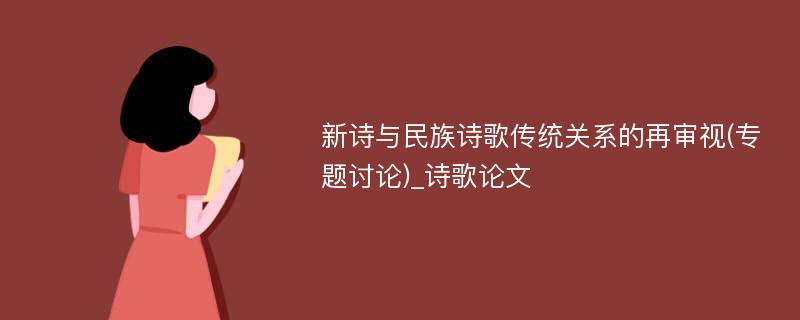
重审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专题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题讨论论文,新诗论文,诗歌论文,民族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方长安
[主持人语]近百年来的中国诗歌因其发生机制、传播途径,特别是其内在生命体验、思想意蕴和书写方式所呈现出的与民族古典诗歌极为不同的新质,故而被命名为新诗。这一命名,使得它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在特定历史时期不断地被人提起。特别是以世界性眼光评说其特征与成就时,有人责难它因切断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而失去民族个性和汉语独特的张力,有人则认为它的现代性活力正是由于摆脱民族诗歌传统束缚后向外国学习的结果,也有人看到了它与民族诗歌精神之间难以言说的关联所带来的复杂性。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确实是考察、言说新诗最重要的角度与话语平台,然而,这一关系因长期以来许多言说者过于激动的情绪而一定程度地被扭曲或膨胀了。言说者个人的许多情绪性话语被阐释到了这一关系之中,不仅使这一关系在评说新诗时的有效性没有被充分利用,而且关系本身也因情绪化阐释而变成了一个问题。
所谓对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的重审,就是要剥离长期以来积淀、附着于这一关系上的多余话语,回到关系本身,以新诗既有的历史与现状为依据,以未来发展为目的意识,用现代眼光对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重新追问。诸如,新诗发生之初,诗人们到底是以怎样一种姿态面对、审视民族诗歌的?他们言说、择取民族诗歌传统时遵循的话语逻辑是什么?这种逻辑导致新诗与民族古典诗歌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给新诗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应如何评说这些影响?回望新诗历史,用今天的眼光看,新诗究竟应与民族古典诗歌建立一种怎样的新型关系?新诗能向古诗学习什么?在全球化语境中,新诗为什么要学习民族古诗艺术,其意义何在?新诗与民族古典诗歌关系对于新诗自身传统的形成有着怎样的意义?等等。我们这组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这些相互缠结的问题展开讨论。其中,著名诗人郑敏的文章尤其值得关注。传统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是“现代”使“传统”成为一个问题的。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在根本上还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对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的重审,将诗歌现代性讨论引向更为具体而深刻的层面。
在传统中写新诗
郑敏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在革新求强中形成了一种传统与创新对抗的心态。在20世纪初,当反叛行动达到最高潮时,所有的对国家、民族衰落的仇恨都集中在方块字和它所承载的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上,因此才有“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样的“革命”造反的口号。今天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在读书看报时,大约都不知道今天你所面对的这些我们深深热爱的祖国文字都是劫后余生。它们曾经在20世纪初的文化革命中,遭受到多少先锋革命家的咒骂和凌辱,又曾被多少文字改革家建议将它们字型的方块砸烂,使它们永远不得直立行走,而变成横着爬行的拉丁化文字。理由是,20世纪强大的西方列强的文字无不是横着的拼音文字,而中国要强盛就非得使汉字拉丁化不可。所幸,在几次革新尝试后,人们终于清醒过来,认识到除了在帮助幼儿学习和查字典时拼音符号确实有用之外,汉字是注定要保持它的方块结构才能传达文字交流时的各种文化信息的。它的形、声、义有机结合是如此的独特,以致单单以音为主的西方拼音文字是万万无法替代的。经过这近百年的汉字改革的折腾,在今天先进的语言学的帮助下,我们终于认识到古老的方块字确实是祖先传给我们的无价之宝,可以说是世界上有惊人的生命力的、举世无双的古老文字,历经数千年而不衰!所以,要使新诗能在世界诗歌家族中再现唐宋诗词为世界公认的光彩,我们首先要重新找回对汉字的审美敏感。当你写下一行新诗时,你有没有自问这些汉字是不是个个都传达了你内心的感觉?它们的声音、色彩、姿态和神情,是不是能在人们的联想里唤起你要传达的信息?我们的古典诗词做到无一字不在声、形、色、义上给读者带来丰富的信息,使人在读时有一种强烈的感性审美和灵性的醒悟。新诗在诗歌语言上,可以从古典诗词中学到很多。虽说我们已经走出古典的格律,但字的四声仍在诗行中有它的音乐效果,需要诗人用自己对汉语音乐的敏感去选择。诗行的顿数也与汉语的词句结构有关。古典的词又叫长短句,对新诗的诗行节奏感会有很大的启发。我们如果经常朗诵宋词,在自己写作时,对如何安排诗行内的词组长短句,以及长短诗行间如何呼应、对称,形成起伏跌宕的建构美,都会有新的想法。总之,仔细研读古典诗词及古文,都会增加我们对汉字之美、之深、之富内蕴的鉴赏力,在写新诗时也自然会在选字遣词及诗行的安排上形成对新诗的审美要求。经过一段潜心的追求,我们的新诗在艺术表述及形式审美方面一定会有提高。
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诗人只有当他/她能自由地驾驭“艺术的不自由”时才能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很多喜爱古典诗词的老人们对新诗的批评往往是:“这也算诗!这不就是一段大白话分段写吗?”当我们理解了“艺术的不自由”时也就明白批评者确实击中了白话诗的要害,这就是在打破古典诗词的格律后,并没有找到自己“艺术的不自由”,也就是新诗的审美规律。在心态上往往以“革命”的自豪感掩盖了自己的艺术懒惰,造成新诗艺术的发展迟缓。在任何艺术创作中,无论你的主题多么进步,多么崇高,它都必须通过“艺术的不自由”,对现实及理念加以转换,才能成为艺术。今天媒体的商业广告似乎比诗人更意识到艺术对现实转换的必要性,虽然广告的实用利益与诗歌的追求是不能相比的。
新诗除了在用字时应当学习古典诗词对每个字的声、色、形、义的审美和整首诗的音乐性与造型美之外,还应当珍惜中华五千年文化留给我们的一件精神珍宝,那就是对精神境界的崇尚。评价古典诗词的最高审美指标就是“境界”。无论是陶渊明的“此中有深意,欲辨已忘言”,陈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还是李白的“今人不见古人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杜甫的“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都是在有限的生命和现实的狭小世界中感受到宇宙的浩渺无穷,而获得一种融入无限的精神超越感。这种无神的心灵超越比西方的宗教升华更是一种“无待”的自由,它更富有老庄的玄思。因此,也更是一种东方的超脱文化,充满了我们先人的古老智慧。它融合了儒、道、释的最高悟性,在后现代的历史阶段是人类用以平衡人性中精神和物质需求的杠杆。一旦这二者间失衡,小则可影响个人的品德,大则可影响世界的和平,破坏多国、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人类国际内的“和而不同”的和平、平等的共存。更有甚者,一旦人类失去对人性中物质欲望与精神境界的平衡,人类就会愚蠢地剥削自然以满足自己膨胀的物欲,直至人类与被他所破坏的自然同归于尽。而这种敬天顺时、善待自然的品德,正是中华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在我们的文、史、哲古籍中俯拾皆是,也是传统诗词中一种天人合一的超越境界。一些不曾接触多少中华传统文化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专业的学生,还以为“环保意识”是当代西方文化的先进部分,这真是天大的误会。如果我们打开《史记》(约写于公元前104—前91年),赫然在目的就有这样的记载:帝喾“顺天之意,知民之急”,“取地财而节用之”。可见,顺从自然、节约使用自然资源的环保意识早已是我们五千年文化的古老智慧了,岂能视之为外来的当代西方的先进思维呢?
作为当代新诗作者,我们的血液里应当有高质量和高数量的自己民族文化的红血球,才不会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成为商业利益驱使下消费文化的随波逐流者。由于篇幅之限,笔者无法在此展开中国古典诗词是所谓“当代西方先锋诗歌”的诗艺的源头的论述,这在今日西方诗论史中已有不少论述。笔者仅建议青年诗人将李商隐的《锦瑟》细读一遍,你会在那首写于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古典律诗中找到今天西方先锋诗的诗艺,而那时中世纪英语还要待一百年才诞生,乔叟也要等四百年才来到这个世界。因此,中国新诗走向高峰,走向世界,不应当忽视和疏离中华古老而充满智慧的文、史、哲文化传统,恐怕是理所当然的了。否则,岂非有揣着金碗要饭之嫌?最后,我想说,一个全球化时代的诗人总是在世界多元传统的互动中,发展和丰富自己这一元传统的独特性,因此没有所谓的“回归”传统。传统的昨天和今天都向明天走去,因此我们应当总是在传统中写新诗,就好象鱼儿只能游在水中,大树只能长在泥土里。所以,脱离了传统,我们还能从哪儿创新?
作者简介:郑敏,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
新诗择取民族诗歌传统之启蒙逻辑反思
方长安 翟兴娥
新诗虽为现代白话诗,与古典诗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野,但新诗并没有真正切断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对传统诗歌稍有了解的读者不难从现代新诗中发现传统诗歌时显时隐的影迹。这种影迹是如何留下的呢?人们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主体无意中的承传,因为传统根深蒂固,不是任何主体能够轻易摆脱得掉的;然而,考察新诗萌动、生长的历史,又不难看出,传统并非完全是无意识的自然留存,而主要是创作主体的自觉沿传。那么,现代诗人究竟是以怎样的态度、立场自觉审视、择取与延传民族诗歌传统的呢?
一
总体而论,现代诗人是遵循启蒙逻辑以审视、择取民族诗歌传统的。所谓遵循启蒙逻辑,指的是诗人们在西方现代启蒙思想浸染下,以思想启蒙为诉求革新中国诗歌,努力使诗歌走向民众,成为启蒙利器。是否有利于启蒙是他们审视、择取民族诗歌传统的基本原则。早在晚清诗界革命时期,黄遵宪就曾在《杂感》一诗中宣称:“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主张摆脱古典诗歌陈旧范式的束缚,以当代俗语为诗,使诗歌走出泥古迷津,成为传播维新思想之利器。到五四时期,胡适、傅斯年、刘半农、俞平伯、康白情、郑振铎、郭沫若等更是自觉持守启蒙立场以审视、择取古典诗歌传统。
那么,究竟什么是启蒙逻辑呢?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说到底就是要将人从封建蒙昧状态中解救出来,赋予人以尊严与自由,崇尚自然,强调人的自然本性,而启蒙的一个重要依据和思想武器是西方的进化论。所以,“自然”与“进化”构成了现代启蒙逻辑的核心。
胡适等人以启蒙眼光审视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将中国诗歌史阐释成为不断走向“自然”的进化史。1919年,胡适在《谈新诗》中说:“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方可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而诗体进化也就是诗体“解放”,走过了几个漫长的时期,一个时期向另一时期转换遵循的便是“自然”的法则,如“骚赋体用‘兮’‘些’等字煞尾,停顿太多又太长,太不自然了。故汉以后的五七言古诗删除没有意思的煞尾字,变成贯穿篇章,便更自然了”;“五七言诗是不合语言之自然的,因为我们说话决不能句句是五字或七字。诗变为词,只是从整齐句法变为比较自然的参差句法”[1](P14—15)。
古典诗歌这种向“自然”“进化”的历史,给胡适最大的启示就是以“自然”为基本尺度审视、择取古典诗歌资源以建设现代新诗。换言之,就是择取古典诗歌中那些他认为“自然”的因子,舍弃那些束缚情感、精神自由的非“自然”的传统,使中国诗歌进一步向“自然”进化,完成“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那么,哪些是非“自然”性的传统呢?在他看来,五七言诗体、词调曲谱、格律、平仄等均属于非自然的因子,应统统打破,用他的话说,就是“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1](P15),使新诗创作真正做到“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2](P381)。
既如此,古典诗歌中是否有在他看来属于“自然”性的传统资源可以利用呢?在《戏和叔永再赠诗却寄绮城诸友》一诗中,他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作诗如作文”,就是他从古典诗歌中挖掘出的一个以“自然”为诉求的诗学传统。这一传统来自宋诗,“由唐诗变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我那时的主张颇受了宋诗的影响”[3]。不只是胡适接受了宋诗这一传统,那一时期绝大多数诗人都以“作诗如作文”为依据,追求诗歌创作的“自然”境界。1920年初,宗白华发表《新诗略谈》,认为“新诗的创造,是用自然的形式,自然的音节,表写天真的诗意与天真的诗境。新诗人的养成,是由‘新诗人人格’的创造,新艺术的练习,造出健全的、活泼的,代表人性、国民性的新诗”[1](P29)。运用“自然”的形式,目的是为造出“代表人性、国民性的新诗”,诗与人的启蒙联系起来了。同年,康白情亦认为“诗要写,不要做;因为做足以伤自然的美。不要打扮,而要整理;因为整理足以助自然的美”;“最戕贼人性的是格律,那么首先要打破的就是格律”[1](P35—38)。“自然”的便是人性的,格律就是戕害人性,成为他面对传统言说诗歌的基本逻辑。1922年,俞平伯在《〈冬夜〉自序》中写道:“我不愿顾念一切做诗底律令”,“我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出自我”[1](P61)。在他看来,“当代的语言”才是“自然”的语言、人性化的语言。同年,郑振铎也主张:“诗的主要条件,决不是韵不韵的问题。”“诗之所以为诗,与形式的韵毫无关系了。”[1](P48—52)古典诗歌所尊崇的韵成为与诗无关的形式。“作诗如作文”是他们从民族诗歌传统中获取的一大资源,成为那一时期他们共同的诗学立场,难怪胡适称当时大多数诗人“都属于‘宋诗运动’”[4](P214)。
除宋诗外,他们还将视线转向“元白”诗派和民间歌谣曲调,从中挖掘具有“自然”属性的资源。“元白”诗派强调“歌诗合为事而作”,“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力求“言直而切”,通俗平易。这种诗风深受胡适等早期白话诗人欢迎,成为他们倡导白话诗歌的重要资源。废名在《谈新诗》中就曾明确地道出这一现象:“胡适之先生于旧诗中取元白一派作为我们白话新诗的前例。”[5](P28)与此同时,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等人于“五四”前后曾大量征集、编辑歌谣,研究歌谣艺术,并以歌谣形式进行创作。后来,“中国诗歌会”在新形势下亦将视线转向民间歌谣:“我们要用俗言俚语,/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的一个。”[1](P232—241)由俗言俚语、民间歌谣等挖掘诗学资源实际上已衍化为新诗的一个重要传统,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解放区的诗人均不同程度地开掘过民间诗歌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大跃进民歌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随着新诗探索的深入,也有不少人开始意识到这种启蒙逻辑的危害性。1923年,陆志韦针对自由诗的“自然”化取向指出:“自由诗有一极大的危险,就是丧失节奏的本意”;“文学而没有节奏,必不是好诗。我并不反对把口语的天籁作为诗的基础。然而口语的天籁非都有诗的价值,有节奏的天籁才算是诗”;“诗的美必须超乎寻常语言美之上,必经一番锻炼的功夫。节奏是最便利,最易表情的锻炼”;“节奏千万不可少,押韵不是可怕的罪恶”[1](P66—70)。他意识到,“口语的天籁”不一定有诗意,诗美生成于“超乎寻常语言美之上”,所以节奏、押韵这种古典诗歌经验对于现代诗美的建构非常重要。1926年,闻一多以更强烈的语气表达了自己对白话诗人择取古典诗歌、创造新诗的自然化启蒙立场的不满:“诗国里的革命家喊道‘皈返自然!’其实他们要知道自然界的格律,虽然有些像蛛丝马迹,但是依然可以找得出来。不过自然界的格律不圆满的时候多,所以必须艺术来补充它。”“偶然在言语里发现一点类似诗的节奏,便说言语就是诗,便要打破诗的音节,要它变得和言语一样——这真是诗的自杀政策了。”[1](P96)他认为诗是靠节奏激发情感的,而节奏就是格律,所以诗不能废除格律。同年,穆木天、王独清等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穆木天说:“现在新诗流盛的时代,一般人醉心自由诗,这个犹太人发明的东西固然好;但我们得知因为有了自由句,五言的七言的诗调就不中用了不成?七绝至少有七绝的形式的价值,有为诗之形式之一而永久存在的生命。”[1](P77—82)认为新诗应朝“纯粹诗歌”方向发展,认为古典诗人所创造的格律艺术是新诗创作的有效资源。而胡适的“要须作诗如作文”则是一种非诗主张;王独清与之相呼应:“求人了解的诗人,只是一种迎合妇孺的卖唱者,不能算是纯粹的诗人!”[6]否定了新诗求人了解这种启蒙主义逻辑。
周作人、梁实秋、陈梦家、何其芳等人后来均表达了对新诗审视、择取古典诗歌这种“自然”化立场的不满,他们对于传统诗歌资源的挖掘、实验也一定程度地改变了新诗过于自然化的趋向。然而,由于胡适的观点是在新诗发轫期提出来的,实际上成为“五四”新诗建构的“金科玉律”,其影响相当广泛、深入,加之中国现代社会历史更适宜于口语化、“自然”化诗歌的生长,如穆木天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诗歌主张就发生了变化,由“纯诗”立场转为倡导大众歌调,所以启蒙逻辑及其给新诗所带来的“自然”化、口语化倾向,在总体上并未真正改变。
二
迄今为止,新诗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说这一启蒙逻辑呢?诗贵自然是诗歌史给我们的一大启示,诗人们在创作中确实应持有一种自觉的“自然”意识,努力将诗歌写得自然而富有诗意。中国新诗在草创期及其后来不同历史阶段强调诗的“自然”性,对于中国诗歌走出泥古倾向,走进“现代”,拓展新的诗歌空间,创造“现代”话语,确实非常重要,其积极的诗学意义不可低估。然而,我们更不应该低估其深远的负面影响。胡适等人是在现代启蒙语境中言说“自然”的,他们的“自然”已经不是传统诗学中的“自然”,而是涂上了浓厚的启蒙色彩,是一个与封建“腐朽”、“落后”性相对立的具有“进步”内涵的概念。他们以为古典诗歌中那些具有“自然”特点的传统必然具有历史“进步”性,所以择取它们是一种合历史潮流、目的的“进步”行为,而那些非“自然”的传统则是封建反动的,必须摈弃。这种启蒙逻辑使他们将“自然”性与现代诗性等同起来,以为“自然”的就是诗的,将“自然”视为评判诗歌的一个基本标准,一味地追求“自然”化。然而,自然的不一定就是诗性的,诗性的也不一定是“自然”的,这是常识。而启蒙逻辑的“进步”陷阱使他们在言说新诗与传统关系和评判诗歌时往往不顾常识,反常识性是现代启蒙逻辑常犯的一个通病。
那么,以“自然”立场审视、择取古典诗歌传统,创作中一味追求“自然”性,其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答案是,其根本在于对古典诗歌“自然”诉求的语境、现代白话诗与“自然”关系等问题缺乏一种真正学理性的考察与诗学层面的反思。一方面,古典诗歌以“自然”为诉求的革新是在文言写作这一言文分离的基本语境中进行的。文言是一种被提纯的知识分子话语,具有“贵族”化、非“自然”的特点,格律等艺术又是在文言语境中逐渐建构起来的,它们在催生诗意的同时又不同程度地制约着诗人的自由,并使诗歌艺术不断地朝贵族化、人为化发展,这一诗歌语境导致古代诗歌史上不断兴起以“自然”为诉求的革新运动,以制约贵族化倾向的发展。所以,古典诗歌的“自然”化诉求是非常必要的,正是因为这种不断向民间、向诗之外求“自然”的行为,中国诗歌才在总体上避免了陷入言语封闭的象牙之塔。另一方面,虽然文言语境中这种不断强调自然性的经验,对于倡导白话诗以取代文言诗是一个有力的依据,但当真正以白话进行诗歌写作时,古典诗歌以“自然”为诉求的经验就不一定有效,起码不能一味地强调自然性。因为白话本身就是一种极其自然的语言,用这种语言写出的诗歌有一种天生的自然属性,而这种自然性总体上看又有一种非诗性的倾向或者说特征。所以,运用白话创作诗歌时应有意识地吸纳古典诗歌的审美经验与形式艺术,将其化入现代白话之中,丰富现代白话的表现力,使白话这种自然化的语言获得尽可能多的诗性成分,以改变白话诗歌因固有的自然性所导致的非诗性倾向。
然而,启蒙主义使胡适等人在拟构新诗发展路向、想象新诗未来时,考虑的仍是诗歌如何自然化、大众化的问题,对古典诗歌“自然”诉求的文言语境缺乏应有的考察,误以为现代白话诗歌创作完全可以照搬古典诗歌“以文为诗”这种散文化、自然化之经验,忽略了“以文为诗”发生的文言语境,特别是文言转换为白话所带来的诗性问题。他们择取古典诗歌中那些具有“自然”性的传统,而坚决摈弃“雅致”的传统,使白话这种自然的话语失去了必要的“雅化”处理,变得越发“自然”,也就是在“自然”路径上走向了极端,于是所谓的白话诗歌在许多人那里事实上成为一堆大白话。
这种启蒙逻辑给新诗发展带来的后遗症非常严重。由于古典诗歌中许多雅致的传统被视为非进步的因子,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诗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老年)只热衷于以流畅的白话口语作诗,缺乏自觉吸纳古典诗歌形式艺术的意识。他们不读古典诗歌,不研究古典诗歌艺术,以至于今天绝大多数诗人不懂古典诗歌中那些优雅的艺术,几千年的汉语诗歌资源对于他们来说在相当程度上变为无意义的存在,新诗自然化、口语化倾向愈演愈烈。一些人也意识到这种自然化的非诗性问题,他们往往借用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某些创作经验,如通过颠覆现有语法规则制造陌生感以生成诗意,这类探索当然不是没有成效,但仅靠这种方法显然是不够的。
白话新诗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它的许多艺术因子来自西方,或者是由自体不断再生出来的,它与民族古典诗歌已经不是近亲,而是相当疏远了,从优生学角度看,新诗也确实到了应自觉吸纳古诗艺术的时候了。所以,新世纪诗人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有效地发掘、吸纳古典诗歌艺术,以改变新诗要么过于口语化、要么过于晦涩的倾向,使新诗真正成为极具诗意、诗味的诗。
作者简介:方长安,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翟兴娥,德州学院中文系讲师。(山东 德州 253000)
标签:诗歌论文; 胡适论文; 西方诗歌论文; 读书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古典语言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 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