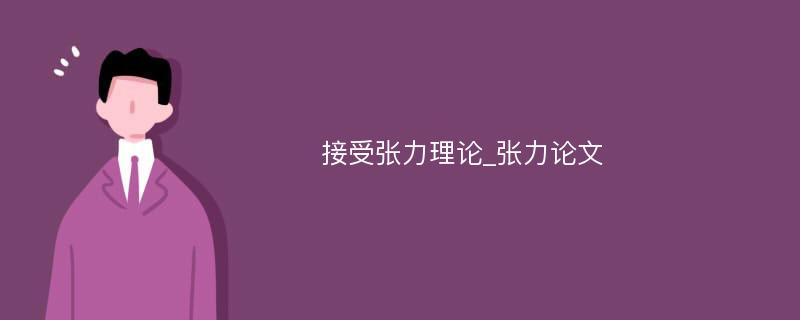
接受张力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张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力(tension)原系自然科学中的一个术语,指事物之间与事物内部存在的力的运动造成的一种紧张状态。“新批评”派将此术语率先引入文学批评领域,用来分析文学作品的本体结构,退特在《论诗的张力》一文中认为,诗歌语言有两个相互作用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诗歌语言的外延(extension),指语言的字典意义或指称意义,第二个因素是诗歌语言的内涵(intension),指语言的暗示意义或联想意义,这两个因素形成相互冲突而又彼此依存的紧张关系。退特主张去掉extension和intension的前缀,合并为一个词——张力(tension)①,自称创造了一个“假博学的双关语”,但并未对这一术语作出详实解释。后来英国的罗吉·福勒主编的《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将它释为“互补物、相反物和对立物之间的冲突或摩擦”,“凡是存在着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力量、冲突和意义的地方,都存在着张力。”②如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之间,一篇作品的几种意义之间,以及作品的特殊与普遍之间均存在艺术张力。从张力的角度去研究文学作品的内在构成无疑具有辩证的合理因素,它强调了作品内容各种要素的矛盾统一和对立面的平衡。但是由于“新批评”派对作品语言本体的崇拜,仅对张力作静态的分析与凝固的考察,未能将作品张力纳入作者——作品——读者的系统中作动态观照。事实上,张力不仅存在于文学作品内部,而且更存在于作者的创作心理和读者的接受心理中,作者充沛的写作心理能量与动力正是依靠强劲的心理张力得以维持的,而且作品的张力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作者心理张力的外化形态,是静中寓动。与此相适应,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又会将作品的张力由静转动,将作品的张力内化为心理张力,感受到多种心理驱力的交叉互补。同时,读者自身的心理期待在与作品的碰撞与互渗过程中,也充满了既统一又矛盾的心理张力,维持阅读心理的动态平衡。
一
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是读者心理期待与作品总体结构之间形成的张力关系,分析这一张力是研究其他张力的前提与基础。如果读者不去阅读作品,就不会将作品中的张力结构内化为心理张力,因此,读者的心理期待与作品之间的张力具有先在的意义。
接受实践表明,读者往往是带着一定的期待视野进入作品内部,将作品纳入自己的审美心理结构之中。根据朱立元先生的研究,读者的期待视野是由定向期待和创新期待构成的,一方面,长期的接受习惯使他按既定的期待去审视作品,如果合他的胃口,就会满意、肯定;另一方面,求新的欲望也开始上升,它不满足老一套的成规,它要搜索新的东西来刺激自己,这样,原有的习惯就成了障碍,只满足原来兴趣的东西反倒被排斥了。这种定向期待与创新期待既矛盾又统一,从静态的角度说,两者互不相容,一个要守旧,固守早已习惯的阅读模式,一个要创新,趋向新的模式。从动态的角度说,旧的阅读模式又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与新的阅读模式达成统一,旧模式是新模式孕育和产生的基础。如果将它们看作读者心理上的两股力量,那么它们就构成了对立统一的心理张力。进一步看,这一心理张力是在阅读过程中得以拓展延伸的,一般来说,读者既有的定向期待是在以往的阅读活动中逐渐积淀而成的,与以往阅读过的作品基本统一,当一部新作品摆在面前时,读者的心理会显得躁动不安、无所适从,失去了心理平衡,难以找到与作品的契合点和进入作品的突破口,只能徘徊于作品的外围和枝节,不能驾驭作品整体和勘破作品内蕴。这就意味着读者的定向期待遭遇到来自作品顽强的抵抗力,无法展开顺畅舒适的阅读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懒惰的以追求消遣为能事的读者会丢开作品不去阅读,严重的甚至会产生“酸葡萄”心理,一方面否定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在内心竭力解脱作品给予他的心理压力,恢复失去的心理平衡;另一方面,就是退回原来的作品并极力夸大其价值与意义,由此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把二、三流作品与经典之作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后者远不及前者的种种笑料,这些均属于读者心理中的防御机制所导致的非正常的接受行为。而一个具有探索兴趣和开放心态的读者可能会在经历一阵心烦意乱之后,主动调整与作品的关系,在作品的激发下唤起顽强的反抗力,调动自己全部的心理能量去顺应作品,按照作品提出的问题对定向期待作出反思,重新建构新的阅读模式。这种反思和建构并非一朝一夕或一两次阅读所能完成的,而是一个艰难曲折、波澜起伏的过程。
对旧的期待作出调整不是全盘抛弃,而是突破与扬弃,追踪作品新的规范与特质也非全盘接纳,而是读者与作品经过碰撞搏斗后作出让步形成新的契合,用皮亚杰的话来说,就是“同化”和“顺应”的辩证统一,绝对的“同化”是对作品的排斥与漠视,绝对的“顺应”又会失去根基,二者都不符合接受的实际情形,因此,在二者之间维持必要的张力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鲁道夫·阿恩海姆对知觉过程的描述对于正确认识以上问题不无启示意义。他认为:“知觉活动所涉及的是一种外部的作用力对有机体的入侵,从而打乱了神经系统的总过程。我们万万不能把剌激想象成是把一个静止的式样极其温和打印在一个被动的媒质上面,剌激实际上就是用某种冲力在一块顽强抗拒的媒质上猛剌一针的活动。这实质上是一场战斗,由入侵力量造成的冲击遭到生理力的反抗,它们挺身出来极力去消灭入侵者,或者至少要把这些入侵的力转变为最简单的式样。这两种互相对抗的力相互较量之后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最后生成的知觉对象。”③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论述尽管带有格式塔心理学的一些弱点,但对知觉过程的解释则是非常透辟的。我们完全可以将作品对读者的剌激当作一股外力对读者心理的作用,这股力又会唤起读者来自固有的期待的顽强的反抗力,两股力斗争与较量的结果就是彼此退让,达成融合与统一,生成审美对象。这种融合与统一决非天衣无缝,因为两股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完全消除,仍然留有回旋的空间和余地。
二
由读者的心理期待与作品的刺激形成的张力不仅存在于读者与作品的总体结构之间,而且存在于读者与作品的部分之间,它们之间构成了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互补关系。
阅读实践又表明,读者的阅读心理总是呈流动状态的,随着作品的语言和情节等线性要素向前伸展。罗曼·英伽登将它描述为不断唤起期待和解决期待的动态过程,读者接触作品的语言并由此唤起进一步向前阅读的期待。“阅读过程就是以这种方式不费力地发展着,但是,如果下面的句子间没有无论什么明确联系的话,那么在思想流中就会出现一个阻碍,这种中断同某种多少是主动的惊奇或义愤相关联。”④也就是说,读者指向未来的心理期待之力与来自作品局部的阻滞力之间形成了对立与冲突,萌发了一种焦躁不安和无所适从的心理经验,心理功能发生紊乱,不知如何去化解阅读中的障碍,开辟走向未来的通道。
这里我们不妨引证一下美国“读者反应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斯坦利·E·菲什对弥尔顿《失乐园》中一句话的分析来简要说明这一问题,这个句子是“他们并非没有看到罪恶的深渊”(Nor did they not perceive the evil plight)。菲什分析道:“读者刚看到句中的第一个字(Nor),必定会产生一种相当确切的(尽管是抽象的)期待:这个句子必定是一个否定的陈述,后面必定是一个主语+动语的结构结束全句。读者心中这时存在两个‘假想’的空白等待填补。由于句中用了助动词did和代词they,这种期待也就更加强烈(或者说,由于句中用了助动词did和they,这种期待没有受到挫折,因而变得更加强烈)。读者估计动词一定不会相隔太远。但是,在动词应该出现的地方,读者发现的却是又一个否定词not,与他预料中的句子形式并不相符。读者这时的思路遇到了障碍,不得不屈服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因为读者并未预料到)not。事实上,读者此时做的,或者说不得不做的,是问一个问题:他们究竟是看到了,还是没有看到?”⑤这个句子并非如否定之否定那样简单明确,而是以其曲折变化的形式动摇读者的期待,强化读者的疑惑与悬念,激发“他们究竟是看到了,还是没有看到”之间的冲突,这样,读者就感到自己的思维陷入两种力量的挟裹而难以得出确切的结论。从菲什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读者即使在读解一个孤立的语句时也会感到期待力与阻滞力之间的心理张力,那么,在理解作品的语段和语篇时,这种心理张力将会更加普遍而多样。
如果说语言内部的张力需要读者细致耐心的阅读才能感受和发现,那么情节内部的张力则比较容易把握。情节内部的张力往往是由省略和悬念促成的,作者在情节发展到高峰或决定人物命运与归宿的关键时刻突然停止叙述,造成了情节的中断与延宕,没有形成完满无缺的完形结构,读者的心理流程被猛然切断,紧张的期待顿时被化为虚空,积聚了强劲的心理能量。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瞌睡》颇能说明这一问题,它写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瓦尔卡在朦胧的瞌睡中掐死了主人家的孩子,因为她发现使她不能入睡的原因是那孩子的哭声:
瓦尔卡笑着,挤了挤眼睛,向那块绿斑摇一摇指头,悄悄走到摇篮那儿,弯下腰去,凑近那个娃娃。她掐死他以后,就赶快往地板上一躺,高兴得笑起来,因为她能睡了;不出一分钟她已经酣睡得跟死人一样了……小说结尾用省略号代替,她掐死孩子后会招致怎样的命运与结局,作品并没交待,也许作者不知道怎样为人物设定一个最后结局,抑或是作者心中有数而故意留下让读者想象的空间,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读者的心理期待被这一虚空切断,形成了两股相互冲突的张力,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读者的心理潜能,在想象世界中将这个不完全的结构趋于完整。
我们不妨援引格式塔心理学理论对这种心理现象稍作分析与解释,格式塔心理学认为,当一个不完全的形状呈现于眼前时,会引起视觉中一种追求完整的强烈倾向,会激起一股将它补充和恢复到应有的完形状态的冲动力,使知觉的兴奋度大大提高。“这种感受有点像竭力猜出一个谜语时的情况,注意力高度集中,潜力得到充分发挥,整个身心全力投入。这是伴随任何一种创造性知觉活动或创造性思维活动的特有的紧张,这种适度的紧张及解决问题后的松弛,是产生审美愉悦的重要源泉。”⑥只是文学接受中对空缺与省略的补充比对“不完全”形状的知觉更为复杂,由于读者难以找到确切的答案和恰当的填补方式,由冲突形成的张力并不最终消失,读者被截断的心理流程会多向辐射,有的鸢飞鱼跃,峰回路转,活跃异常。小说中悬念的艺术功能也应如是观。读者的心理张力也是由定向期待和情节的延宕的反差所维持的,悬念一旦解开,心理张力会自行消失,阅读兴味也会减弱。这就提醒作者在创作中要运用相应的文学策略去调配与控制读者的情绪,产生最佳的艺术效果。
三
读者在阅读作品时期待心理与作品整体及部分的阻滞所构成的心理张力是在读者的心理时间中得以维持的,随着接受向纵深拓展,读者将会感到来自作品不同层次之间的艺术张力,它建立在“新批评”所说的作品张力结构的基础上。如前所述,由于“新批评”派只是静态考察作品的张力结构,忽视了它与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因此,具体分析一下作品的张力与读者接受的关系就显得很有必要。
“新批评”派认为:张力存在于作品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各个要素之间,作品就是由众多要素形成的一个复杂的张力结构,但这些力的结构只有在读者的接受活动中才能复活,才由潜在的力转化为现实的心理力,在读者的心灵世界中撞击出生命的火花。由于这种张力是多种多样的,本文不可能——解析,只是对其中几种样式作出考察,以期收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我们首先看一看小说中叙述层与故事层间的张力。叙述层是指小说的叙事话语,故事层是叙事话语投射的一系列前后关联、具有因果关系的事件。从符号学的角度说,叙述层是能指,故事层是所指,两者的有机统构成了完整的小说文本。优秀小说中的叙事话语这一能指从来就不是单纯指向故事层这一所指的工具和媒质,达到使读者只意识到语言所描述的事物、情景和人物,而不知有所谓语言文字的叙事效果。它除了叙述故事之外,还要凸现自身的审美功能,积极开掘语言本身的潜能与意味,用它那抑扬顿挫的音调、起伏变换的节奏、新鲜奇异的句式给人以美感。有时,故事反倒成了它利用的手段,它在对故事实行消解的过程中,成为指向自身的艺术符号,能指转化为所指,巴尔特的观点极具代表性,“他认为,一般作家写的是某种东西,真正的作家就只是写,区别全在于此。真正的作家不是把我们带向他的作品之外,而是为了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写作活动本身。”⑦这样,貌似天衣无缝的小说文本就充斥了叙述层与故事层之间的矛盾,二者构成了颇具张力的艺术空间。与此相适应,读者在接受小说文本的过程中,就应向两个方向伸展自己的心理能量,一方面,读者受接受惯性的影响,往往将小说当作故事来读,力求将作品的叙述层转化和还原为因果相续、前后贯通的故事层,从中寻找事趣,事实上,一般小说也能满足读者追逐事趣的心理。另一方面,作品的叙述层又要张扬自己的艺术功能,往往又抗拒读者的转化和还原,固守其艺术营垒,读者被它吸引,产生惊奇感,不得不在其中徘徊穿梭,留连再三,领悟其艺术旨趣,延长阅读。小说文本就这样在读者的接受中被一分为二,由于这两股心理流不可能得到最终融合,读者就时刻感受到两股或强或弱的心理力的搏击。我们阅读当代小说怪杰莫言的部分小说会强烈感受到此种心理经验,他的短篇《球状闪电》与路遥的《人生》在题材上十分接近,二者都讲述了一个落魄回乡的秀才与两位异性间的感情纠葛,但《人生》的叙述层是与其动人的故事紧密结合的,后者的其大起大落过于惹人注目,消解了前者的艺术能量,二者间的张力空间较小。而莫言的《球状闪电》的故事尽管不乏诱人之处,但多少被叙述层掩盖,读者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将那诡谲的奇异的语言消解成故事。正如很多论者指出的,它向读者打开了一个感觉化的世界,对读者的审美感觉构成强烈的剌激,获得直觉的、故事所不具备的美感,这种感受与读者从故事层中获取的感受由于难以协调统一而留下了可资游戏的张力空间。
完整地看,接受小说的趣味正是由叙述层与故事层之间的张力所构成,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故事层的趣味并非小说独有,接受者也能在戏剧与影视艺术中享受故事的乐趣,而叙述层则为小说所独具,小说中的故事层可以从作品中抽出转化为其他艺术形式,而叙述层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转化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承认萨丕尔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小说中交织着两种不同层面的艺术,“一种是一般的非语言艺术,可以转移到另外一种语言媒介而不受损失;另一种是特有的语言艺术,不能转移”⑧。因此我们可以说,阅读小说的过程,就是徘徊于叙述层与故事层之间的过程,就是充分感受二者艺术张力的过程。
随着读者对作品语言和故事等表层要素的理解和感受,逐渐深入到对深层内蕴的领悟,读者将会感受到来自作品意义内部的艺术张力。孤立的意义当然不可能形成艺术张力,但如果我们把意义分解为意思和意味两个层面时,就不能不感到它们之间互补性冲突的艺术魅力。文学作品的意义是渗透在形式结构之中的,不可能从中完整地抽象剥离出来,正如布拉德雷所说:“对一首真正的诗来说,除了它自身之外,根本不可能用别的语句把它的意义传达出来。”⑨当年有人问托尔斯泰《发娜·卡列尼娜》表现了什么思想,托尔斯泰巧妙地回答说:“思想一旦从赖以生存的联结中抽出,特地用语言表达出来,就会失去其意义,它的价值也就极大地降低了。”(10)布拉德雷与托翁都巧妙维持了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观点。但事情往往有另外一面,假若对作品意义作出层次划分,其中的意思是可以用另外的语言大致转述出来的,如果转述得好的话。更何况,读者在接受过程中,总是期待从作品中发现什么思想,有一种发现思想的期待,试图用简洁明确、条理分明的语言去概括作品的基本意思。鲁道夫·阿恩海姆在谈到形体知觉时就分析了人的大脑领域中存在那种向最简单结构发展的趋势,使知觉对象看上去尽可能的简单,这种简化的趋势当然包括对知觉对象所传达的意义的简化。这种心理规律无疑也是适合文学接受活动的,除了那些单一贫乏的作品外,一切优秀作品的意义都是丰富复杂的,蕴蓄着难以穷尽的底蕴,为理解设置了重重障碍。读者为了总体上驾驭和统摄作品,就不能缺少对贯穿作品血脉的基本意思的把握,将复杂的作品纳入一个多少有些干瘪的简化模式中。但问题在于,读者对作品意义的简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作品相吻合,在多大程度上传达了接受过程中那种鲜活跳动、丰富多彩的审美感受和文学意味。所以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简化与拒斥简化的紧张的心理张力的产生,作品以其意蕴的丰富多彩性阻滞读者的简化倾向,因为意蕴的深层显得精微莫辩、神秘难测。十七世纪英国的拉潘在《关于亚里士多德讨论的思考》中曾这样说:“同其他艺术一样,诗歌中也有某些东西是不可言传的,它们(仿佛)是宗教的玄秘。诗的那些潜藏的韵致,那些觉察不到的魅力,以及一切神秘的力量,都注入心中。”(11)它们只能用心去感受和体验,不可能用语言去描述,因此,作品的意蕴总是介乎“可解不可解”、“可言不可言”之间。康德对此也有深入认识,他认为,艺术作品的审美意象“能引起许多思想,然而,却不可能有任何明确的思想,即概念,与之完全相适应。因此,语言不能充分表达它,使之完全令人理解。很显然,它是和理性观念相对立的。”(12)这表明,读者在观赏和玩味审美意象的过程中,获得了多种思想的暗示,没有什么明确的思想让读者用概念化的明晰语言去表达,因此,任何概括都是一种简化,都和作品有较大距离,都会造成与作品的紧张关系。
四
分析文学接受中的心理张力,不仅要充分注重心理张力的各种典型形态,而且要弄清心理张力产生的条件及其美感效应。首先,张力来源于读者的审美心理与作品这两种异质因素之间,正如鲁道夫·阿恩海姆说:“任何非同质性的剌激物都会招致张力的出现”(13)。也就是说,作品必须与读者的审美心理维持一定的差距,对其作出一定偏离,心理张力才能产生。如果作品一味投合读者稳固的习惯心理,就会心生厌倦,失去兴趣,不能激发内心深处的紧张感,这正如人生活在一个非常熟悉的环境中就会心安理得,而一旦身处陌生环境就会本能唤起一种紧张情绪一样。美国的乔治·桑塔耶纳说:“顺心而单调的环境所产生的快感,往往不能使环境显得美,道理很简单,就是这环境未受到注意。同样,我们习惯了难看的东西,例如风景上的缺点,我们的衣服或墙壁的丑处,并不使我们难堪,这不是因为我们看不见它们的丑处,而是因为我们习焉不察。”(14)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说,过于熟悉的作品会导致读者心理的钝化与保守,而新奇的作品则可能使之改弦更张,发生嬗变。正因为如此,什克洛夫斯基才提出了文学的“陌生化”理论,主张用反常的文学形式去瓦解读者的习惯经验,用新奇的眼光去关注对象,让钝化的审美知觉复活,在与作品的碰撞中产生心理张力,激发心理潜能。“陌生化”的程序与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如前面分析的,有对读者熟识的艺术规范的总体反叛,颠覆读者的期待视野,有对日常语言规范的打破,使语言多义化和模糊化,菲什对《失乐园》诗句的细读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有对情节的省略与延宕,进一步强化读者的心理期待;可以加强作品语言潜能和形式意味的开掘,使作为交际手段的日常语言上升为艺术目的,打破读者对故事的期待,等等,均属于“陌生化”的程序与方法。
当然,文学的“陌生化”无论怎样新奇,都应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要符合读者心理嬗变的基本规律。心理学中的“差异原理”认为,介乎旧与新之间的偏离与变异最能唤起人的新鲜感,激发人从已知探索未知的兴趣,并非作品越新颖,接受张力就越大,超过了限度,作品难以构成读者的接受对象,张力也就不存在了。
在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为什么不满足于那种安闲宁静的欣赏,而去追求新奇的刺激所唤起的艺术张力呢?首先,追求张力是一种生命的需要,它能打破生命的单调和平庸,体验到生命的丰富与圆满。在现实生活中,人为了功利的需要,利用各种手段去克服人与外部世界的张力,将各种剌激尽量缩简为最简化的式样,建立一个有利于身心平衡的和谐世界,正如阿恩海姆所说:“人类在追求某种目的时,总是力求达到一种张力最小的圆满结局,他将力求使自己个人的需要与周围环境的需要达到平衡。”(15)但这种消除张力的功利活动往往会导致人的心理功能的萎缩和片面化,过于简化与单调的世界使人的生命丧失了丰富多彩性,因而人又需要那种紧张的生活体验去激发、唤醒人的生命活力,而那些新颖奇特、与读者心理异质的作品则是激发生命活力的最好形式之一。同时,在现实行为中,人们往往重视目的而轻视过程,目的一旦实现,过程就失去了意义,而文学接受并不是指向一个外在目的的手段,接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读者更注重由张力激发的生命力释放的快乐和紧张情绪的体验。其次,张力能激活读者的审美注意,唤起人的探究欲望。如前所述,过于熟识的审美对象会使人的注意力麻痹与涣散,而新奇的对象则往往会使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审美感知和情感等处于活跃状态,创造力充分发挥,穷尽对象的奥秘与内蕴。第三,张力能刺激人的想象力。文学作品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空白,如情节空白,语言空白,意义空白,它们作为接受过程中的障碍与读者流动的心理期待形成了紧张关系,等待读者的填补与克服,这就极大调动了读者的艺术想象力,思维处于兴奋活跃状态,多向辐射,获得创造的愉悦与自我实现的满足。
注释:
①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第1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②罗吉·福勒主编《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第280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③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第5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④英伽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参见杜夫海纳主编《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第262页,朱立元、程未介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
⑤菲什《文学在读者:感情文学体》,见《读者反应批评》第97页,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
⑥《视觉思维》中译本前言,《视觉思维》第16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
⑦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第11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⑧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⑨布拉德雷《诗就是诗》,转引自H·G·布洛克《美学新解》第31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⑩参见尤里·苏特曼《艺术文本的结构》,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作品系统)第3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1)拉潘《关于亚里士多德讨论的思考》,转引自艾布拉姆斯《镜与灯》第3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2)康德《判断力批判》,转引自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第113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13)(15)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觉》第607页、60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
(14)乔治·桑塔亚纳《美感》第7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