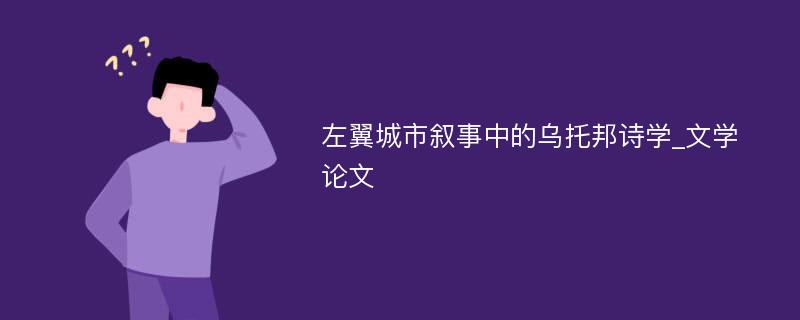
左翼都市叙事中的乌托邦诗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诗学论文,左翼论文,都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293/Z(2003)04-0044-05
左翼女作家丁玲在写于1930年6月的中篇小说《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中对上海都 市景观作了如下一段概括性描写:
这个时候是上海最显得有起色,忙碌得厉害的时候,许多大腹的商贾,为盘算的辛苦 而瘪干了的吃血鬼们,都更振起精神在不稳定的金融风潮下去投机,去操纵,去增加对 于劳苦群众无止境的剥削,涨满他们那不能计算的钱库。几十种报纸满市喧腾的叫卖, 大号字登载着各方战事的消息,都是些不可靠的矛盾的消息。一些漂亮的王孙小姐,都 换了春季的美服,脸上放着红光,眼睛分外亮堂,满马路的游逛,到游戏场拥挤,还分 散到四郊,到近的一些名胜区,为他们那享福的身体和不必忧虑的心情更找些愉快。这 些娱乐更会使他们年轻美貌,更会使他们得到生活的满足。而工人们呢,虽说逃过了严 冷的寒冬,可是生活的压迫却同长日的春天一起来了,米粮涨价,房租加租,工作的时 间也延长了,他们更辛苦,更努力,然而更消瘦了:衰老的不是减工资,便是被开除; 那些小孩们,从来就难于吃饱的小孩们,去补了那些缺,他们的年龄和体质都是不够法 定的。他们太苦了,他们需要反抗,于是斗争开始了,罢工的消息,打杀工人的消息, 每天新的消息不断地传着,于是许多革命的青年,学生,××党,都异常忙碌起来,他 们同情他们,援助他们,在某种指挥之下,奔走,流汗,兴奋……春是深了,软的风, 醉人的天气!然而一切的罪恶,苦痛,挣扎和斗争都在这和煦的晴天之下活动。[1]
上述引文最吸引我们目光的莫过于它那对都市生活既具体又富于概括性的总体展现。 它和穆时英笔下那种浓得化不开的感性画面有着天壤之别,和《子夜》开头那段对黄浦 江、苏州河交汇处的鸟瞰式描绘也不尽相同:这段文字展现的是一幅让人感到既熟悉又 陌生的都市全景图,它包蕴着某些感性的元素,但又不沉溺于其间,而是深入到了社会 的表象之下,深入到了对社会结构的内在运动奥秘的探究之中,深入到了对各个阶级间 的冲突的剖析之中,深入到了对现实世界的否定性评判中。从细部而言,它有些模糊, 但整体的轮廓却分外鲜明。它是一种复合的话语,将都市景观的描绘、对各阶层人物生 活的概述和爱憎分明的政论揉为一体。阶级斗争、革命等大写的主题词赫然在目,里面 有对旧世界的诅咒,有对上层阶级奢靡生活的揭露,有对在死亡线上挣扎、食不果腹的 劳工的深切同情,有对反抗和斗争的衷心赞美,还有对一个在地平线上崭露头角的新世 界的殷切渴望。
然而,最为重要的是,人们从中可感悟、窥视到它所蕴含的启示录式的话语。所谓启 示录,本是犹太—基督教文学中的一种特殊体裁。启示(apocalypse)一词源自古希腊语 中的apokalupsis,有显示、揭示(disclosure)和默示(revelation)之意。最早的启示 文学作品是收入《旧约》的《但以理书》。在随后的数百年间,一大批启示文学作品先 后问世,它们主要是《以诺一书》《西番雅启示书》《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战争》《 亚伯拉罕启示书》《亚当启示书》及收入《新约》的《启示录》。(注:有关犹太—基 督教文学中的启示文学,梁工、赵复兴在《凤凰的再生——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文学研究 》中有详细论述,参见该书第254-286页、417-445页、688-701页,商务印书馆,2000 年1月。)林林总总的启示文学作品尽管在风格、文体、意象上各各不同,但它也有一些 共同的特点:它们是先知式的人物或圣徒对深陷在现实世界苦海中而无力解脱的民众的 抚慰,是对这个被罪恶、痛苦、不义纠缠的现世的彻底否定,是对一个神恩眷顾的新世 界的吁求,“启示文学的作者们娓娓动听地告慰正在苦海中挣扎的同胞:莫因眼前的不 幸而沮丧,黑暗、混乱、疯狂、是非颠倒的日子即将过去,上帝赏善罚恶的时刻就要来 临,由救主弥赛亚永远统治的光明国度终必建立”。[3]
末日审判之际令人惊怖的景象是启示文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在《新约·启示录》 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当末日审判的号角吹响之际,上帝将以各种灾祸无情地惩罚作恶者 和邪恶者,而与这阴惨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新天地体现的“新耶路撒冷”则是 壮观无比瑰丽异常,它是一个令所有人心驰神往的理想国度。显而易见,在启示录的文 本中,时间划分为两大段:即“现存的时代”和“将临的时代”。它们之间已不单是时 间维度上的先后之分,而是染上了鲜明的伦理色彩:黑暗与光明、邪恶与纯洁,天使与 恶魔……追求正义的激情在字里行间呈波浪型跳荡,对现实已不抱任何希望,投向它的 只是轻蔑,毫不容情的诅咒;对未来,则满怀渴慕向往之情,那是人们全部价值寄寓的 光明璀璨之地。在上面所引丁玲的这段文字中,洋溢着的正是这种启示录式的激情。但 从整篇作品而言,《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对此表现得不够充分,而《子夜》的深 层结构中正蕴含着这种启示录式的激情。
也正是在这里,人们看到了以《子夜》为代表的左翼都市叙事文本与新感觉派作家、 张爱玲等人最内在的分界线。如果说在新感觉派作家、张爱玲那儿,理想主义、神圣的 超验价值被无情地嘲讽,进而被支解,世俗的欲望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辖制权,并进而导 致对现实秩序有意无意的顺从与认同,那么左翼都市叙事的一个最大特征便是表现在它 对现实社会毅然决然的否定姿态,而这种否定姿态正是衍生于启示录式的激情。在《子 夜》中,人们看到了现代都市癫狂的繁华喧嚣,看到了金融股票市场角逐中的惊涛骇浪 ,看到了日益凋弊的农村乡镇中的骚乱,看到了年轻人在乱世中的向往与无所解脱的迷 惘,看到了工人贫苦艰窘的日常生活,看到了工头、工会领导人与普通工人间复杂微妙 的拉据战,看到了工人与企业主之间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看到了在商贾间如鱼得水般 游走周旋的交际花,看到了年轻女性在性爱上的苦闷与无措,看到了威严的传统伦理准 则在人欲横流的世界中如何不堪一击倾刻间土崩瓦解,看到了薄如纸的人情,看到了声 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活动和处于燎原之势的革命运动,看到了显赫一时的财富和权势如何 在刹那间化为乌有,但这一切丰富的表象并不具有自足的意义,作者将它们汇总起来, 凝聚起来,串接起来,目的是要展示现实生活总体秩序的不合理,揭示它的衰朽,并进 而否定这一令人厌憎的现实。而对萌生中的革命运动(在作品中具体表现为工人的罢工 和双桥镇的暴乱),茅盾无疑倾注了他全部的热情,它们是这个丑恶现实世界的反面, 是代表着未来的力量和希望,是改造这个世界的桥梁。
虽然在具体的意象与表达方式上与上述的启示文学作品不同,但《子夜》全篇浸润的 正是这一启示式的激情。正如茅盾自己所说,他在作品中想表述的中心思想是,“打倒 国民党法西斯政权(它是代表了帝国主义、大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是当 前革命的任务;工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革命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共产党手中”,[3] 他实际上向往的是这样一种情形,这和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柏林对革命渴望的论述不 谋而合:通过解放运动,工人们“步调一致地离开他们的工厂和车间,然后万众一心奋 起一击,让那个该死的制度,那个使他们陷进涂尔干或孔德的囚室和等级制之中、完全 丧失人类本性的制度、遭到总体的、粉碎性的、永久的、‘拿破仑式’的失败。这就是 人类的伟大起义,光明之子反抗黑暗之子,自由战士反抗商人、知识分子和政客——资
本主义世界那群可悲的主子、平民中的得志者、被人收买和接纳到等级制中的人、专业 人员和社会计划人员、右翼或左翼中的权力和地位的追逐者、鼓吹以贪婪和竞争为基础 或以合理组织的压迫为基础的社会的人——的起义。”[4](P382)
这一对世界的大拒绝的启示录式的精神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曹禺的话剧剧本《日出》 中同样得到了鲜明的反映。据曹禺自述,他之所以写作这部左翼色彩极浓的剧作,缘于 现实生活的强烈刺激:
这些年在光怪陆离的社会里流荡着,我看见多少梦魇一般的可怖的人事,这些印象我 至死也不会忘却;它们化成多少严重的问题,死命地突击着我,这些问题灼热我的情绪 ,增强我的不平之感,有如一个热病患者,我整日觉得身旁有一个催命的鬼低低地在耳 边催促我,折磨我,使我得不到片刻的宁贴。
我忍耐不下去了,我渴望着一线阳光。我想太阳我多半不及见了,但我也愿意我这一 生里能看到平地轰起一声巨雷,把这群蟠踞在地面上的魑魅魍魉击个靡烂,哪怕因而大 陆便沉为海……冲到我的口上,是我在书房里摇头晃脑背通本《书经》的时代,最使一 个小孩子魄动心惊的一句切齿的誓言:“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见《商书·汤誓》 )萦绕于心的也是一种暴风雨来临之感。我恶毒地诅咒着四周的不公平,除了去除这群 腐烂的人们,我看不出眼前有多少光明。诚如《旧约》那热情的耶利米所呼号的,“我 观看地,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感觉到大地震来临前那种“烦躁不 安”,我眼看着地崩山惊,“肥田变为荒地,城邑要被拆毁”,在这种心情下,“我已 经听见角声和打仗的喊声”。我要写一点东西,宣泄这一腔愤懑,我要喊“你们的末日 到了”!对这帮荒淫无耻,丢弃了太阳的人们。
腐肉挖去,新的细胞会生起来。我们要有新的血,新的生命。刚刚冬天过去了,金光 射着田野里每一棵临风抖擞的小草,死了的人们为什么不再生起来!我们要的是太阳, 是充满了欢笑的好生活,虽然目前是一片混乱。[5](P374-377)
在上列引文中回荡着的正是这种启示录式的激情: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现实无比 的憎恶与对光明的急切渴求。《日出》卷首有作者精心选择的八段引文,除了一处来自 《老子》外,其余都源自基督教的《圣经》,有的直接取自启示文学篇章。(注:引文 中的两段文字可视为启示文学篇章:一段直接摘自《新约·启示录》,另一段摘自《旧 约·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向人讲述上帝耶和华向他展现的耶路撒冷被毁时的凄凉场 景,这是犹太人不敬神、沉溺于荒淫生活所致。虽然《耶利米书》就全篇而言不能算作 启示文学,但它部分段落在意旨与描写手段上与启示文学有相通之处。)在作品展示的 都市空间中,一切都糟糕透了:这里有依靠富人钱袋撑持的高级交际花陈白露,有在陈 白露身边不时打转、靠榨取人们血肉为生的潘月亭、张乔治、顾八奶奶、胡四等鬼怪, 有一心往上爬、孤注一掷而落得惨败的李石清,有任人践踏的失业职员黄省三,有不堪 凌辱而悬梁自尽的小东西,还有就是虽没有公开出场、但却操纵着人们生死予夺大权的 黑社会老大金八。在这幅都市生活的全景图中,一切都在腐烂,败落,没有希望,没有 救赎的曙光,像方达三这样书生气十足的人物并不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他的 那些举动是“多么可笑又复可怜”。[5](P378)
但要注意的是,《日出》中展现的都市的世界并不是漆黑一片,给人以安慰的便是被 作者视为“最主要的角色”——太阳,它成了这个憋闷凝滞的世界中“唯一的生机”。 [5](P380)太阳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方面它是自然力的精粹,“象征伟大的将来蓬蓬 勃勃的生命”;另一方面又是理想的新世界的标记。[5](P379)由于作者没有直接塑造 出体现光明世界的人物,他只是让它成为陪衬物,成为一种背景,与那些哼唱着“哼哼 唷”的工人融为一体。在工人们的哼唱中,充满着“他们的忧郁,痛苦和奋斗中的严肃 ”,那首《轴歌》中的歌词更是有着明确的政治内涵:“日出东来,满天大红!要想得 吃饭,可得做工。”[5](P235、371)通过这一方式,在初升的阳光中辛勤劳作的工人成 了创造未来新世界的主人,这与当时风行的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不谋而合。陈白露 这些人则没有前途,只能被淹没在黑暗中,这点她自己也明白,她再三吟咏的诗句清楚 地表露了这一点:“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5](P338)
显而易见,只要将《日出》中的劳工形象进一步明晰化,涂抹上更为鲜明的政治色彩 ,它便和为左翼评论界尊崇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相差无几。周扬当年在谈到 这部作品的弱点时,便认为它的结尾部分虽然乐观,“但却是一个廉价的乐观”,作者 应该提供“一个不致使观众模糊的明确的暗示”,而不足的原因在于作者“还没有充分 的把握:只有站在历史法则上并经过革命,这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才能根本改 变”。[5](P338)但这种评论太过苛刻了。实际上,只要把它和同属都市叙述文本的《 子夜》比照一下便能发现,《日出》中体现的启示录式的精神更为鲜明,更富于象征的 诗意。单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都市文学文本中蕴藏的启示录精神并不是《子夜》这部作 品的专利,而是许多左翼文学作品共享的特点。相同的意识形态倾向孵化出了极为类似 的欲望书写方式,而在都市叙事中所体现出的这种对现实的否定姿态成了茅盾等左翼作 家与新感觉派作家、张爱玲等人最为重要的分界线。
潜伏在这一巨大差异背后的则是各自意识形态倾向的不同。在刘呐鸥、穆时英构造的 都市空间中,个人的欲望追逐是作者关注的焦点。在竞争趋于白热化的都市生活中,欲 望与其说经常如愿以偿,不如说是不时受挫,跌入痛苦、绝望的困境。那些人物对现实 世界怀有种种牢骚与不满,但他们欲望受挫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社会体制所致,各 种个体心理、经历的偶然性使他们滑入了迷惘的窘境。都市社会尽管在他们眼里有时显 得面目可憎,但他们并没有毁灭它的冲动和力量;相反,它是这些人物活动的恒常的舞 台,他们与它是共存共荣的关系。施蛰存部分涉及都市题材的作品也有这一特性,而他 以心理分析手法写成的历史题材作品则从心理学的维度上解构了一切神圣的价值,将它 们从高不可及的神坛上拉回到俗世,一切神圣的光环背后都隐伏着极为世俗的因素。而 以描摹都市空间中平实生活见长的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更接近于生活的原生态,他们在不 那么夸张、浮华的外表之下却隐伏着她本人刻意展现的以日常生活经验为根基的“人生 安稳的一面”。[7](P378)它具有不可移易的恒常性:在这种恒常的人性面前,任何变 革的企图和冲动不是烟消云散,便是沦为毫无必要的瞎折腾。
茅盾等人左翼都市叙事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出发点。那是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 ,一种与日常生活哲学对立的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冲动,它力图超越现实,改造现实,甚 至依照理想的模式重塑重造一个新的现实。乌托邦就其本义而言,在社会学家曼海姆的 眼里,“只能是那样一些超越现实的取向:当它们转化为行动时,倾向于局部或全部地 打破当时占优势的事物的秩序”,它“打破现存秩序的纽带,使它得以沿着下一个现存 秩序的方向自由发展”。[8](P378)
在这种意识形态话语中,没有所谓恒常不变的人性,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秩序,一切 都在流动、变易、衰败、新生之中,他们想以动外科手术的方式摧毁不可救药的新世界 ,在打扫清地基后矗立一个晶莹剔透的新世界:一个消除了现代文明滋生的所有罪恶和 弊端,又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基础的社会,一个消灭了财产私有制、对生产和分配过程进 行社会化公共管理的社会,一个消除了人对人的压迫与掠夺的社会,一个个人与社会处 于和谐状态、个人潜力最大限度得以发挥的社会。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千载难逢的高潮 瞬间:在那一刻,历史运动与集体的意愿、个人的欲望水乳交融地合为一体,达到前所 未有的和谐,人类在必然王国中实现了其自由王国的梦想。
这一革命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怪物,它与人类自古以来有关完美社会的 理想息息相关。在先秦时代,孟子的仁政学说中就包含着建立一个完美社会的想法,尽 管那还只是一个自然经济的理想构图。(注:有关孟子的仁政思想,参看任继愈主编《 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相关论述,第302—31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 到了近代,康有为在《大同书》中阐述的大同社会的诱人图景更是涂抹上了浓烈的乌托 邦色彩,那里物质文明高度昌盛,劳动和财产公有成了社会的基石。(注:有关康有为 的大同思想,参看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127—14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7 月版。)而这儿论述的左翼的革命意识形态则是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思想的孪生儿。从古到今,西方思想中有关完美社会的设计方案林林总总, 源远流长,就拿柏拉图的理想国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伊甸园来看,它们的信念便互不 相容;但在柏林看来,不管它们之间存在着多少歧异,它们分享着一个共同的假设:“ 即完美的社会是可以设想的,不管它是一个祈祷和向往的对象,或仅仅是对人类尚未实 现且不可能实现的潜能的一种幻觉,或是对真实或想像中的过去的一种怀念之情,或是 历史必然遵循的目标,或是只要有足够的能力、精力和道德纯洁,从原则上说就可以实 现的一个实践纲领。”[4](P145)
在这一旨在建立世俗乌托邦(即人间天堂)的革命意识形态的驱使下,茅盾等左翼作家 似乎是禀得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他们觉得惟有将个体的生命融入集体的革命运动、以 及由这种运动所体现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自己的生命才能获得最高意义的价值实现 。因此,在都市叙事文本中,他们对原先的叙事模式作了修正,以适应革命意识形态的 要求。在这种非人格化、以启示录精神构建的叙事框架内,个人的欲望追逐不再是文本 发展的动力,集体的意愿和对历史规律有意识的展示成了作品的内核。在某种意义上, 作者自己便成了某种不可置疑的真理的代言人,像有学者所言,“作家不仅自信获得代 言‘真理’的权威,而且获得再现‘现实’的辩证方法。”[9](P378)革命的意识形态 、现实主义的方法与社会学的透视角度成了这种方法中最重要的因素,构成了三位一体 的结构,它对日后包括都市文学在内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下,个 体及其欲望的消泯成了势所必然的结果。
收稿日期:2003-0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