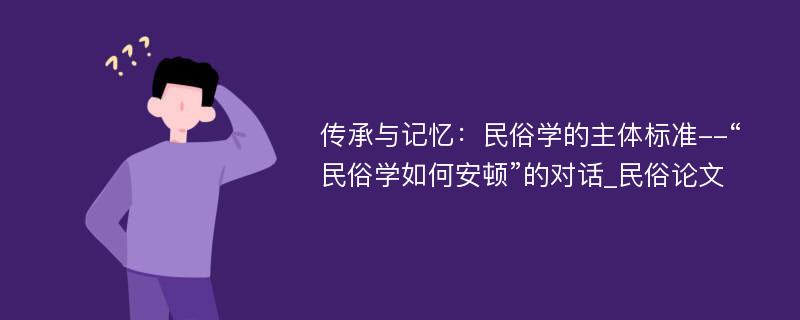
传承与记忆:民俗学的学科本位——关于“民俗学何以安身立命”问题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俗学论文,安身立命论文,本位论文,学科论文,记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士闪教授给我们一个命题作文,题目就是“民俗学何以安身立命”?① 我想这个问题是出自一种对民俗学现状的强烈地不安定感,至少是不确定感。民俗学现在不再是一花独放,有了许多博士点、硕士点,还有“非遗”保护的助力,热热闹闹,人丁兴旺,国家也开始重视,似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但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是张教授居安思危,觉得民俗学似乎有点无以安身立命或者无处安身立命的危机,否则就完全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的必要。我觉得这种危机意识是难能可贵的。
刘铁梁教授说到他准备了一个题目,叫做“感受生活的民俗学”。他是从高丙中的博士论文开始讲起的。较真点儿说,我不知道有没有不感受生活的民俗学。民俗学不就是感受生活的吗?如果说到民俗学这三个字,我们应该想到的就是感受生活。难道还有一个专门感受生活的民俗学的意义,就是说以前或者现在或者将来还有一个不感受生活的,无论是感受或者生活这两个关键词都没有的那样的民俗学吗?如果说本来民俗学就是感受生活的学问,那这个命题的意义在哪里呢?我想刘教授是有所指的,也是对民俗学的现状有感而发,民俗学“安身立命”的问题也就有意义了,刘教授的讲题和张士闪的命题作文也就联系起来了。
一、“生活”及其“感受”之后的学科问题
讲到民俗学是感受生活,就涉及到了民俗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你不能说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甚至文学就不关心或者感受或者剖析人的生活。那么民俗学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即使是在今天的学科目录里,民俗学如果是作为一门学科,不管是一级学科还是二级学科,不管它是什么意义上的学科,你就不得不从学理上说明它与其它学科有什么样关系,是怎样的交叉,或者有哪些共同的关注。即使你自己的研究需要涉猎非常多的学科,你还是要回答你自己学科的本位是什么。如果学科本位不清楚,或者不能坚守,这个学科就很难存在。也许就不一定叫民俗学,叫某某学都可以,甚至干脆就是人类学或者是文化研究(culture study)的一个分支,专门研究民间文化等等。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学科有没有持久生命力的基本保证,否则的话,你没办法存活;你可能出现一时,但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消失了。
回顾一下学术史,民俗学在诞生之初还是很轰轰烈烈的,很多人都已经写过文章、写过书讲北大歌谣运动或是讲中大的《民俗周刊》。我们知道那是与“五四运动”前后那样一个大的意识形态背景、大的社会浪潮有关系。到中大时期有些学理上的讨论,当然现在看来还是初步的。到后来差不多学术上的探讨就停顿了。顾颉刚、容肇祖回头研究他的历史,周作人写他的小品,刘半农不在了,江绍原、黄石等人的境遇也不太好,没有一个好的研究环境。大概只有钟敬文写了一些民间文艺学的理论文章。到抗日战争时期以及以后,民俗学的思想有时被利用为意识形态的工具,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差不多都处在比较低潮的状态下,大学没有这个学科,也没有多少专业人才,因此是名副其实的先天不足。直到今天,好像又才缓过一点劲来。但这种形势的好转也不完全是学科本身努力的结果,一方面是人文学科都有所好转,另一方面是客观上有个遗产保护的大环境。仔细想想,如果没有两个这样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背景,民俗学是否能产生或存在都的确是个问题。我们一去梳理这个学术史,就知道它就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并不能盲目乐观。所以学者们提出这个“安身立命”的问题是缘于这个环境。问题的实质是,民俗学如何凭借学科自身的学术努力获得它的繁荣?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高丙中教授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是17年前系统地讨论民俗学学科基本问题的著作,② 多年后,吕微教授撰文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该书在民俗学的学术范式转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引领作用”,即在欧美学界的同行中,这样的理论思辨性著作也不多见。他也指出,对这部书,学界一直没有给予充分的讨论和研究,颇有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之感。③ 对此,我也颇有同感。在这里,我不想对高丙中教授的大作展开正面讨论,对吕微教授文章中的延伸议论也基本赞同,但民俗学的本位问题现在已经不再是何为“民”、何为“俗”的问题——这些问题已逐步取得共识,也不能只限于抽象地指出民俗学的意义在于其关注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因为这是所有人文学研究的基本取向,大量“传统民俗”的消失也不再是民俗学研究存在的障碍和令人恐惧的危机——因为民俗学并不是历史学,而且我们从来都承认民俗一直处在变化之中,即使是“传统民俗”也是“层累地制造”的,就像我们常说的“老北京”民俗,不过只是清末民初的生活现象罢了,距离明清乃至更早的民俗不知改变了多少。
吊诡的是,吕微教授认为民俗学科的学科危机源于民俗学从人文学术向社会科学转移这样一个重新定位(reorientation),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人对自身存在形式即存在本质的理解。据我的知识,这恰恰体现了人文学术经历了20世纪社会科学化之后对学科人文性的回归。这种人文性又恰恰通过高丙中教授及其所援引的萨姆纳教授所高扬的“人的生活”、甚至是“个体的生活”得到彰显。在较早的研究中,高丙中教授亦把民俗学的人类学倾向与人文学倾向(神话的、历史的或文本的研究)对立起来,似乎认为田野调查这种人类学方法属于社会科学的倾向。④ 问题在于,将此种强调归结于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或者在高度抽象的意义上强调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在于“人的生活”,或许体现出民俗学者在当今学术界社会科学的强势存在的情况下不甘自弱、“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心魔。
高丙中教授强调了“生活”甚至先验意义上的“生活世界”,刘铁梁教授则强调对这个“生活”或“生活世界”的“感受”,这个“感受”也许既是经验的,也是先验的。但分别是前者注重民俗学的客体,后者则注重主体。尽管刘铁梁教授增加了研究者主体认知在民俗学认识中的比重,但总的来说,他们二人对民俗学对象的本质具有一致的结论。问题是,这虽然解决了以往对“民”、“俗”的狭隘理解的问题,缓解了“传统民俗”逐渐消失给研究者带来的困境,也强调了把握民俗学研究中outsider与insider之间的复杂关系,将民俗学方法提升到新的高度,但并没有区分开民俗学在这些问题上与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其它人文学之间的学科差异,反而有进一步模糊这个学科差异的趋势,使民俗学学科本位的问题更加凸显。
二、民俗学科的学科本位问题之我见
在日益强调多学科互补互动(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的今天,强调学科本位是否不合时宜呢?事实上,即使我们申明了民俗学的对象是“生活世界”,而方法就是“感受生活”,并不能阻止我们用人类学来取代民俗学,甚至可以用历史学来取代民俗学。我们不能说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不包括民俗,也不能说历史学不研究历史时期的民俗。格尔兹研究的巴厘的斗鸡不是一种民俗吗?我们为什么不声称它是民俗学作品?列维·施特劳斯研究亲属关系,民俗学者也研究姻亲关系、拟亲属称谓等等,历史学者研究宗族,这中间有什么区别?萧放教授对“历史民俗学”有长篇专论,简言之就是研究历史时期的民俗,但如果历史学者同样研究历史时期的民俗,这项研究属于(历史)民俗学还是历史学呢?⑤ 如果民俗学者不能清晰地意识到这些问题并且能给出确定的答案,民俗学就无法以一门独立学科的身份与其它学科平等对话,不能以知识、理论与方法层面上的独到贡献为其它学科所看重和共享,“安身立命”的问题就依然存在,学科危机就没有得到缓解。
相对于人类学,我对历史学的了解应该更多一些。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相对于民俗学、人类学这些后起的学问来说,其学科地位更稳定一些。但是它也需要变化,也经常遭遇危机。19世纪历史学是一个“科学”的时代,兰克认为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对史料加以考订之后,就可以得到客观的事实。但到19世纪末这个结论就开始遭到质疑。不过在20世纪前大半的时间里,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很大,历史学还是坚持它的社会科学方向,于是像经济史、统计学的方法,性别史、种族史、工人运动史等等与现实相关的主题还是颇为风行。到20世纪后20年,这个方向也在改变,微观史学或小人物的历史开始得到青睐,人类学的影响日益增大,⑥ 多学科的倾向十分明显。但无论是社会史、文化史或者历史人类学,都始终坚守其历史学的学科本位,即关注历史时期的社会、人的生存状态及其变化,在方法上以文献学的方法为圭臬。在具体的研究中,“定时”(timing)是所有工作的前提。
高丙中教授在稍近的一次对话中也已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将民俗学的学科本位表述为民俗学的“核心传统”。他说,“学科史上,可能有一个时段是要借助‘轻视’学科传统带来更多的开放,但是有人斗胆开放一段之后,重建对于学科根底的信心的需要和能力都会自然形成,这就是我近年认为‘激活学科传统’应该在当前成为民俗学界的自觉意识的主要考虑”。“所谓民俗学的学科危机,有两种相反的因由。早先是封闭造成的危机,近些年是开放造成的危机。封闭的危机是不断边缘化的危险,但在最后的结果发生之前尚能固守自我;开放的危机是太多作为异质的新质湮没自我的危险,但好处是开放带来的活力提供了大发展的机会。”⑦ 我们今天需要认真思考的,与其说是他上世纪90年代中叶提出的问题,不如说是他在10多年后的新思考。而这个问题,即我所谓民俗学的学科本位问题,实际上回到了学科内部更为本质性的“元问题”。
但是,高丙中教授并没有进一步引申,在其它场合的谈话中,他似乎也颇犹疑不定。比如在谈到人类学的民族志与民俗学的民俗志的分别的时候,他的表述是:“一个是我对我群的参与观察与文化书写,一个是我对他群(国外社会和国内的其它族群)的参与观察和文化书写。”但他同时也说到,这样一个区分“可能很难把这两个东西区别开”。⑧ 的确,要区分何为“我群”、何为“他群”,实在是太困难了。“国外”和“国内”的“国”多半是指近代以后的“民族国家”,并不适合像中国这样一个概念不断变动的文化实体。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无论从面积、人口,还是从族群及文化多样性来说,“中国”可能要与整个“欧洲”做比较才合适;即使是在所谓汉人社会中,是否都是“我群”?如果不是,如何区别哪个是“我群”,哪个是“他群”。用讲河北或江苏或广西的某个地方的事情来说这是中国的事之误人匪浅,自从施坚雅的文章问世以来便已然清楚了。
民俗学要做田野工作,人类学也要做,甚至历史学也可以做,研究民间音乐、戏曲、美术的都可以做。事实上最早做的是地理学和考古学,人类学最早还可以是书斋里的学问(armchair scholarship),但地理学和考古学可不行,没有田野他们就没饭吃了。所以做田野是不能把民俗学和人类学分开的,民族志也同样,我从来不认为非得叫做“民俗志”不可,叫民族志就不行,就是高丙中教授说的“哪个学科都可以用民族志”。但因为“民族志”是人类学的发明,还是要尊重人家的专利。你可以用,但你不能换个类似的名词,内容也差不多,就说是你自己的发明了。注重感受和体验一样不是民俗学的专利,我相信刘铁梁教授也是同意这个看法的,现在我们叫感受的民俗志,除了文本的书写本身这个技术方面的问题以外,从它的学理来讲,你说它完全是民俗学的吗?我以为这是基本的人类学立场。我们要说清的是,什么是民俗学的田野工作,什么是民俗学的民族志,什么是民俗学感受。
这些问题当然是讨论民俗学学科本位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前提是,民俗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学问?我还是坚持一个“古老”的说法,民俗学是一门“传承”之学。换句话说,“传承”是民俗学的核心概念,高丙中教授的所谓“核心传统”就是围绕“传承”被历代民俗学传人构建起来的,这就是民俗学在学界的“应有份额”。
说这个说法“古老”,是因为如柳田国男等老一代民俗学者便写过《民间传承论》这样的经典作品,将“传承”作为民俗学的基本概念确立下来。直至今天,在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还是对“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说明这个概念本身就代表了民俗学的传统。但是,这里强调“传承”,是强调一个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动态的过程,而不斤斤计较于何人传和传何物。因为强调了这个动态的过程,何为“民”及何为“俗”的问题就不言自明了,这是由于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民”和“俗”。
强调传承,意在强调民俗学与历史学及人类学重点关注的差异。过去钟敬文师曾强调民俗学不是“古代学”而是“现代学”,意在说明与民俗学以往的“遗留物传统”的不同。我在与先生讨论时提出,虽然民俗学不是“古代学”,但可以是“历史学”。当然这不是把民俗学归入历史学学科范畴的意思,而是强调研究对象的过程性特征,而与人类学强调研究对象的结构性特征区分开来。但历史学研究是针对“过去”的,它是这个“过程”的一端,它可以研究过去的“结构化”(structuring)过程;人类学是这个“过程”的另一端,它关注的是这个过程结束后的结果或现实状况。民俗学的现实着眼点与人类学相同,它的主要精力并不放在过去,它参与观察的全部对象都是此时此刻存在的;但不同的是,它关注的核心在于此时此刻存在的东西从何而来,为何得以存在,其得以存在的深层机制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民俗学打的是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时间差”。
明白这个道理,才能明白“非遗”保护的学理基础。为什么要保护“非遗”呢?为什么要强调传承人的保护呢?关键是这些遗产是否在当下社会还有生命力。如果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就是由于现代生活迅速变化,民俗生活的载体消亡了,许多遗产就没有生命力了,这时的保护是因为它具有历史价值,像文物一样,可以放进博物馆。对它的研究就多半是历史学的研究了。但另一方面,是它还有生命力,它还跟着现代化的节奏走,这些东西还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进步,但因为某种原因被故意摧毁了,比如“文化大革命”就摧毁了许多不是被日常生活自我发展所抛弃的那些东西,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建设、商品大潮也造成了类似的后果。我们要保护它,是希望它还可以继续传承。这个传承不是始终需要靠国家的力挺,而是可以靠自身的活力传承下去,我们的保护工作就是要发现这个传承的文化、社会机制,我们现在的保护才有意义。这部分工作就是民俗学承担的了。
强调传承的民俗学,就要强调作为方法的“记忆”。这一点已得到日本学者岩本通弥的申明。⑨ 我在研究三月十九日太阳生日及洪洞大槐树的传说中也使用了这一概念。在探索传承机制的过程中,记忆的机制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因为传承得以实现主要是凭借集体或个人的记忆。由于记忆是现实人的记忆,这个记忆不等于历史事实,但由于传承人的身份,这个记忆就成为传承的最权威依据,使他人难以质疑,故而传承下来。所以岩本通弥说,“如果我们不使用民俗、传承、常民这些惯用的词汇给民俗学下个定义的话,它可以这样表述:民俗学就是不借助记录,而是以‘记忆’为对象,通过‘访谈记录’的技法,通过人们的‘叙述’、‘对话’来研究人们的生活和意识的学问。按照这个定义,对民俗来说,记忆成了最本质性的存在”。但这样的以“记忆”为核心概念的表述,并不能将民俗学与历史学区分开来,因为在我看来,历史学所使用的大部分文献记录也同样是“记忆”或“历史记忆”,关键在于作为民俗学方法的记忆是服从于“传承”的,是关于“传承”的“记忆”。岩本通弥所说“口头传承并不是‘错误记忆的结果’,而是‘新创造的产物’。我们的民俗学,就是从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发现意义,并以此为起点而成立的”,就与我的主张完全合拍了。⑩ 在民俗学学科本位的问题上,“变化的过程”即传承过程,是一个铜板的一面,记忆或记忆机制是另一面;记忆是关于传承的记忆,同时记忆又造就了传承。
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俗学的田野工作及建立在其上的民族志书写,就是对民众生活文化传承机制和记忆机制的观察、理解和解释,对民众生活文化的感受和体验是为这种观察、理解和解释服务的。
三、民俗传承的变与不变
我们说民俗学是传承之学,并不是说传承就是不变,其实没有不变的传承。但其中还是有不变的因素,有可能是精神不变,内核不变,形式变了;也有可能是形式不变,但所表达的意义变了。因为记忆的特点就是有选择性的记忆,有些东西被记忆,有些东西则被忘却。探讨传承的机制,同时也是探讨变。
比如说拜年,我们过去有许多拜年的礼俗,现在都废弃了。但是两个熟人在见面的时候,还有可能说声“新年好”!但拱手作揖、邻居串门拜年的习俗至少在城市里比较少见了。但是现在有新的拜年方式。过去相距遥远的时候是很难拜年的,过节的时候也很难相聚,所以才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诗句,可是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电子邮件,或者打电话,甚至视频的方式来拜年。过去陌生人之间很少相互拜年,但现在在春节联欢晚会上,主持人可以向全国人民拜年,国家领导人可以在春节团拜会上向海外华人拜年。这不仅是形式变了,拜年的范围也扩大了,亲人之情、邻里之谊被扩大到整个社区和族群。但是,拜年这个民俗事象还存在,只要还有年节,拜年的习俗就会存在。西方人过圣诞节,也会发个贺卡说Merry Christmas,有的还自己制作卡片把一年来自己的生活大事写下来或画下来,告诉亲友,这也是拜年。这种人类的文化根性就是一种传承的机制。
刘铁梁教授讲到民俗学的身体感受或者身体性,对骑马民族的理解,只有感受到马背上的生活,才能理解骑马民族的民俗特点。他说按过去的规矩,人类学者要到那里去骑一年、半年的马。落到我们的话题上,大家知道,澳大利亚或新西兰,他们是以养牛或养羊来著称的。他们虽然也经历了现代化社会,城市化水平也比较高,但他们还是有很多畜牧业。过去养牛或养羊,像美国西部牛仔一样是骑马的,他们有骑马的感受;但现在不骑马了,很多人驾驶着摩托车,开着越野车来放牧。小时候我们唱他们的一首歌,很有民俗的味道,叫《羊毛剪子咔嚓响》,现在剪羊毛可以用机器了,不都是人工用剪子了。但放牧还在,剪羊毛还在,这个是不变的东西。所以骑马有骑马的感受,开越野有开越野的感受,与骑马有关的生活改变了,但不一定完全改变,因为骑摩托、开越野还是离不开草原,离不开放牧,对后者的感受对于我们民俗学的意义是与感受骑马一样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不能说骑马的没有了,民俗就没有了。民俗还存在于开越野放羊的人身上,畜牧方式的改变不等于畜牧不存在了。这就是改变中的传承,这就是我们说的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
华南宗族的情况颇能说明传承与变化的一些复杂情况。关于华南的宗族,人类学者是率先关注的,国内学者林耀华的《金翼》和《义序的宗族研究》、许烺光的《祖荫下》都可以说是代表作。但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弗里德曼。(11) 不过现在国内研究宗族最有影响的却不是人类学者,而是历史学者。我们在广东、福建看到祠堂林立,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活态的存在,不像江西、徽州也有很多祠堂,湖南也有很多族谱,但祠堂里已经没有活动了,所以感觉是从过去、比如明清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据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历史学者告诉我,这其实是一种错觉。那里的宗族发展也是经历过一个断裂的,并非是连续不断的传承。毛泽东从当年井冈山时期就说族权是束缚中国人的四大绳索之一,经过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大家已经不知道宗族的事情应该怎么搞了,族谱怎么修、祠堂如何建,祖先的神主牌怎么放,祭祖的仪式怎么做,统统不知道了。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传承的机制是多么奇妙和如何起作用的了。大家知道,从晚明开始,特别是到了清代中叶以后,广东、福建沿海有许多人都迁居到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地区。他们到那里去了以后,就把家乡的传统带到那边去了。包括在我国的台湾,清代中叶以后闽南人、客家人、潮汕人去了那边,把家乡的信仰传统和宗族传统都带过去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家回来寻根问祖,同时投资搞建设,看到家乡的祠堂、寺庙破败不堪,就出钱重修。因为在台湾、东南亚这个传统没有断,所以人家知道怎么做,于是告诉你要把原来的碑刻、族谱找回来,要怎么摆神主牌,怎么做仪式,这个传统就重建起来了,传承就被接续起来了。什么叫“礼失求诸野”啊?就是传统如何接续的机制。可能从“野”求来的“礼”已经变了,已经不是庙堂上原来那个“礼”了,但八九不离十,即使相差较远别人也不知道了。其实几乎所有的传统都有断裂,也都是这样接续起来的。所谓“传承”就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这个传统接续的机制又不仅限于宗族组织的重建。因为宗族组织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联宗等方式,形成了日益壮大的族产。宗族中的各个房支的族产成为宗族族产中的各个股份,宗族就是这个控股公司。在华南,这些宗族的房支在不同的地方经营着宗族的族产,可能在香港,可能在东南亚,也可能在北美,各个房支对宗族做出贡献,也就在宗族组织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经营宗族也是经营生意的方式,不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而是在明清时期就是如此。有人将此理解为一种传统与现代性的结合,事实上这是传统的接续。如果这是现代性,那么在传统中就有“现代性”了。正是由于这样的机制,所以“传承”是有内在动力的。
所以,民俗学既是传承之学,也是变动之学。“变”是“传承”的题中应有之义。过去把传承理解得过于狭隘,好像现在古建筑修缮讲究的“修旧如旧”一样,就是把过去的东西完全承继下来,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生活中除了古董以外就没有这样的东西,只要它有生命力就必然是变的。刘铁梁教授最近很强调“身体性”(实际上我认为古人讲“体悟”这个词更好些,把切身的体验与其后的感悟都包括进去了),他也承认代际的社会在变化,每个人在用文化来参与生活的过程中,就必然就会有自己的独特的东西进去,于是这就变成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传承。
总之,“生活是一条河”,它本身是一个流动不居的过程。任何一个事物,可能很短暂,白驹过隙,但也是一个过程。一个人有他自己的生命历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变与不变构成了这个过程的主旋律。民俗学所研究的就是这个生活传承过程及其机制和意义。
四、民俗学研究实践中的学科本位
现在回到民俗学的研究实践。
张士闪教授为我们这个“民俗学何以安身立命”的讨论主题拟出了四个可以发挥的话题,一是当前国家制度中民俗学的危机与机遇,二是当代民俗学的学术视野与自我定位,三是反思目前国内的区域民俗志或民族志的热潮,四是学术理念与分析工具:民俗学研究如何操作。第一个问题中的“国家制度”我猜包括学科目录上的民俗学和“非遗”保护中的民俗学,我在这里没有正面讨论;我前面所讨论的主要是第二个问题,都相对比较宏观;后两个问题是比较技术性的,第三个问题我虽然有所涉及,但主要还是刘铁梁教授近年所做的工作,由他讨论比较合适;下面我只稍微论及第四个问题的后半句话,涉及民俗学研究的具体实践。但是民俗学涉及的研究课题很多,我没有能力做到全面。
过去在论文答辩等一些场合,我经常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民俗学研究的个案要看是否有助于回答民俗学是什么,或者说是民俗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在民俗学的学科本位问题没有理清之前,这个问题还不好回答。但我们如果心里没有这个学科自觉,不清楚自己做的研究对民俗学有什么贡献,这就会使研究意义大打折扣。我经常担心的是,我们的研究,特别是前面说的“区域民俗志”研究,稀里糊涂地找了一个点,下去做田野,然后挖了一堆资料,不管是文献的,还是访谈的,就拿回来写论文。反正别人也没有去过,你这里说的张三、李四、王五,某某庄,某某村,别人都没听说过,写出来你就是最厉害的了,反正别人也没有你这个经历。你这样研究了一个点,他也这样研究了另外一个点,往往只是个案的累积而已。如果没有学科本位,缺乏问题意识的自觉性,不清楚自己要和谁对话,不明白做这个个案对民俗学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研究是没有太大价值的,这个学科也是没办法进步的。
这个问题强调的是民俗学者要修炼内功,它的繁荣不能太依赖外力。外力可以借助,但不能被它忽悠,否则就会有损于这个学科的生存。我可以用别的学科的例子来说明。比如地理学也是个传统学科,与历史学一样古老,但这个学科现在颇有一些挣钱的机会,其中最大的一个机会就是帮助各地的政府做规划,旅游规划、详规、总规,做一个规划的费用就数十上百万,导致现在变成一个产业。一些学者花大量时间、精力做这个,研究生都跟着打工,每个月都能多拿几千块,很有诱惑力。慢慢大家就没心思思考本学科的学术发展,老师们都在耗费他们当年学问的老底子,不去研究什么新东西了,学科的思想进步就停滞了。现在我们也热衷于评这个评那个,外在的东西占了太多时间、精力,该去想的东西也不去想了。等时过境迁,当国家、社会、人民需要我们民俗学贡献聪明才智的时候,却拿不出新的东西,拿不出真才实学给他们,这个时候民俗学就真的难以安身立命了。
我前面提到过关于亲属关系的人类学研究。我们知道山东大学刁统菊博士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一个村里的姻亲关系的。从理论框架来说,我觉得它总体说来没跳出人类学的亲属关系研究框架,至少是这样一个人类学问题意识的延续。带着前面申论的理念,我比较关心的是,今天村落生活中的亲属关系或姻亲关系,与他们所知道的、还能记忆的,或者他们在生活习惯当中形成了惯制的关系是如何勾连的;如果有关联,哪些是变化了的同时哪些又是未变的;达成这样的现实生活样态是因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说,或者都这么做,这样的一种惯制是怎么样存留到今天的,在这样一种过程中起作用的机制究竟是什么,也就是传承的机制是什么。目前的民俗学研究不是完全没有这样的追求,但是不多。
刘铁梁教授的另一位博士张士闪教授研究的是小章竹马,刘教授说这篇博士论文是比较传统的民俗学。不管传统不传统,我说还是比较像民俗学的研究。为什么说比较像?是因为他做得也还有大大改进的地方。小章竹马是一种民间的仪式性表演,过去可以把这样的研究划入秧歌之类民间小戏的研究那一类,可以是民间文艺的研究,所以刘教授说它看似比较传统。但我们看到,它实际上是一种民间仪式,而民间仪式就多多少少带点宗教性。这样的主题其实也是人类学所关注的,不一定就是民俗学的研究。但张士闪教授告诉我们——虽然没有着力强调,这就是说要大大改进的地方——小章竹马这种民俗传统是如何传承下来的呢?这个传承的过程是与马氏家族的发展过程有关的。它提炼出来的是,西小章村的竹马表演是靠着会点武术又挺厉害的马氏家族的活动来传承的,所以他探讨的是民俗生活传承的机制,这就落在我所谓的民俗学本位上了。当然这个提炼还不够自觉,分析的力度还不够,但他还是尽力把落脚点放在了马氏家族的活动这里,而不是局限于铺陈这种表演。
所以如果我们的学者、我们的研究生能通过我们论文的具体个案,对这个民俗学的学科本位问题都做出哪怕是一丁点儿贡献,大家集腋成裘,民俗学研究就进可攻,退可守,即进可服务于现实社会,退可专注于学术本身。在一定的时间内,安身立命就是可能的了。
说到最后,我顺便提及民俗学作为传承之学的资料问题,这也是个实践或操作层面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可以拓宽民俗学资料学的范围,也可以打通所谓“一般民俗学”和“历史民俗学”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界限。
一般来讲,民俗学搜集资料的方式是参与观察,其结果是获得访谈记录和观察感受。我们过去说25年或30年可以形成一个新民俗,是表示我们可以有一个能观察到的、或者能有记忆的一个时间范围。但我们考虑传承过程的时候,也许不能只获取这样一个时间范围内的资料,我们获取资料的时间范围,要看我们研究的对象所需涉及的远近。无论如何,我们可能需要注意两类材料:一类材料是在现实生活中直接面对的、或者是正在变或已经变了的生活,另一类是现实生活之前的资料。但在后者中,有许多和现在的生活没有直接的联系,已经变得很间接,对这类资料感兴趣的是历史学者,不是民俗学者。民俗学者要的是与现实生活有直接联系的那部分材料。这两类材料要并重。
但民俗学研究必须把重点放在前一类,只是对后一类不能偏废,因为我们要思考的是传承和变化的问题。这样我们面对的资料就不仅是口头叙事,也包括文献,包括仪式表演和其它身体性的文本,还要包括图像和声音文本。文类(genre)多样化了有个好处,就是可以超越单一文类的局限和误导。因为任何文类和文本都有它的局限性,都是特定人群的产物。比如口头叙事文本的特点是生动、鲜活,但是它有非常易变、不确定、意义模糊的特点,所以研究口头叙事的传承更要注意对“变”的分析。但面对不同文类的资料,需要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即解释和分析的方法。材料种类丰富了,研究的难度也增大了,但它的学术价值就更大了,距离接触到相对真实的东西就越来越近了。
基于此,强调传承的民俗学研究就不会排斥其它学科的方法,因为不同学科对于特定材料的分析、解释手段是有专长的,比如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历史学的考据学方法、心理学研究记忆的方法,以及美术、音乐、戏曲等艺术学科的专门方法,这些都可以为我们研究传承之学的本位服务。也许我们也就可以因此发明出一种关于解释生活文化传承与变化的方法,即学科本位的方法,可以给别的学科贡献出他们可以参考借鉴的东西。所以,当我们的学科本位问题明确了以后,对资料的认识和对方法的思考,都可能会随之有一个新的开拓和提升。何以安身立命的问题,就是在下一轮学术转型之际需要再度面对的问题了。
注释:
① 这个问题似乎语出吕微在《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上的文章,他在文中以此来思考高丙中著作中引入胡塞尔现象学理论的动因。此外,《民俗研究》编辑部召开的关于民俗学之人文学术与社会科学性质的座谈会,似乎也是吕微文中涉及的问题。这使我们的讨论不得不略略涉及两位教授的思想。在这里,尤需对张士闪教授邀请我和刘铁梁教授到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与师生座谈表示感谢,并特别感谢谈话记录的整理者山东大学2010级民间文学专业硕士生井长海、赵容、宫慧珉,本文就是在这份记录基础上改写而成的。
② 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③ 吕微:《民俗学的笛卡尔沉思》,《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
④ 高丙中:《中国民俗学的人类学倾向》,《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
⑤ 参见萧放:《中国历史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感谢萧放教授在该文中将拙著《狂欢与日常》列入“历史民俗学”研究中,但我个人以为它还是一项历史学研究,与另一本《眼光向下的革命》不同,后者是民俗学的学术史。
⑥ 对这一过程的归纳可参考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9年,及其《20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中译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⑦ 高丙中:《核心传统与民俗学界的自觉意识》,《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
⑧ 高丙中:《“民俗志”与“民族志”的使用对于民俗学的当下意义》,《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
⑨ 岩本通弥:《作为方法的记忆——民俗学研究中“记忆”概念的有效性》,中译文见《文化遗产》2010年第4期。
⑩ 加粗的重点词为笔者所加,特此说明。
(11) 参见林耀华:《金翼》,三联书店1989年;《义序的宗族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Francis L.K.HSU,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Kinship,Personality,and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