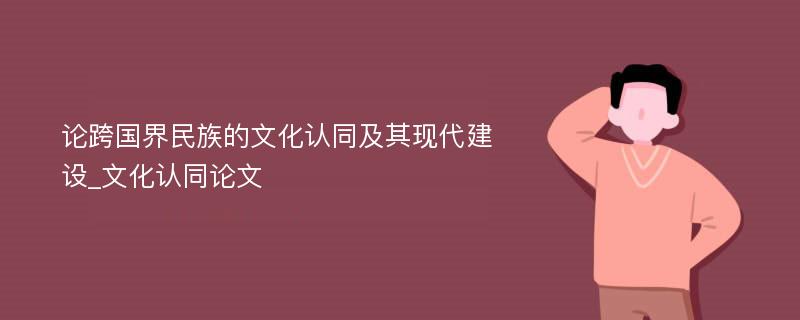
论跨界民族的文化认同及其现代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文化论文,论跨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的跨界民族,专指分布或居住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疆域里的族体。由于这类族体的生活和行为跨越了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政治边界,使得“民族”与“国家”出现了不完全重合的形式,加之涉及相关国家的现实政治利益和管辖权利,因此,这类族体自形成起,便与现实的族际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纠缠在一起。事实一再表明,如果当事国之间不能妥善处理跨界民族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历史与现实、自身和外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就极易引发国家间的关系紧张。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的跨界民族问题一再印证了这种判断(如中东地区的库尔德人问题、中亚地区的俄罗斯人问题等)。有学者指出,由跨界民族问题引发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冲突不单纯是一个政治或经济问题,它还是一个文化问题,其深刻的根源往往是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感情基础的裂痕所引发”,其中“文化是一种深层次的决定性力量,一些表面上看来是政治上的冲突,实际上都反映了深刻的文化分歧。”①显然,对跨界民族而言,这里的“文化”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而是指复杂而重要的文化认同。
一、现代语境中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culture identity),通常被理解为个体或群体对自身所属的文化体系自发形成的一种内在情感,表现为一种归属感或文化情结。文化认同行为是在跨文化交流中,社会精英敏锐地捕捉到自身文化与异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别,自觉地反思自身的文化特性及发展动向,并藉此来实现或强化其文化理念的社会行为。已故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认同(identities)由自我界定,但又是自我与他人交往的产物”。②文化认同的形成与维系主要取决于认同主体自身的体认和坚持,以及认同客体的默许和接受,这是一个建立在自身条件和外在条件之基础上的现代建构行为,其最终结果是在社会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社会区分。
文化认同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文化体系,③它包含了族群起源、部落所属、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文明形态等社会因素,这些社会因素是社会群体进行历史记忆的主要凭借物。从功能属性上看,可以划分为表层结构因子和深层结构因子。属于表层结构的生活方式、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等社会因子,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相当强的适应性,即发生变化与转型的可能性相对较大;而宗教信仰和族群起源等社会因子则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发生变化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也就是说,尽管社会群体进行文化认同时,表层结构因子更为凸显,但实际上,深层结构因子在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分量。
从社会属性上看,文化认同是现代社会建构的产物,天然地具有现代性。首先,文化认同是现代社会背景下不同族群之间进行跨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时派生的,由于不同族群在接触过程中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中心—边缘”、“主体—非主体”、“主流文化—亚文化”等社会群体文化模式,那些处于从属或受支配地位的族群往往会进行自我认同。其次,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化认同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一方面全球化使得各族群大规模、远距离、多层面、宽领域的接触和交往以及各种身份的体认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因来势凶猛的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同质化发展趋势而形成的压力,部分处于弱势地位的族群通常会通过强化自身文化认同,以在社会化过程中体现自我存在。由于文化“是广义的社会化的结果”,④在现代社会背景下,随着族群之间的频繁接触和跨文化交流的深入,形成了文化的“区分”与“认同”,最终“在‘各种文化的民族’中,每一个自我都是在与‘他者’的关联中被界定的”。⑤
二、跨界民族的文化认同:逻辑、功用与影响
在现代社会中,跨界民族作为一种特殊的族体,从形成的那一刻起,本身就兼具政治性与民族性、社会性与文化性等多重特征。因此,跨界民族在进行认同时就呈现出形态各异的取向,即政治认同是清晰化还是模糊化,民族认同是单面性还是多向性,社会认同是适应状态还是对抗状态,文化认同是总体上稳定还是趋于变动。这些多重认同一方面受到文化的影响,即文化因素是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基本元素;另一方面,这些复合认同的取向与性质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族群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并通过跨界民族的历史记忆行为和社会文化生活来体现。本文将通过对跨界民族文化认同的演变逻辑、基本功用和主要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入的考察,以此来理解当下十分复杂而敏感的族际关系。
1.跨界民族文化认同的演变逻辑。跨界民族无论是由于自然迁徙还是由于政治分割,其始终生活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环境之中。这种特殊的文化情景常常使得跨界民族面临文化生活方面的冲突(culture clash),特别是涉及诸如传统文化或宗教信仰等深层次问题时,文化层面的冲突尤为凸显。这类冲突行为实际上是指在社会生活中跨界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异文化遭遇时,两种文化之间的互不包容或互不适应的情形。当两种渊源甚远、形态各异或取向不同的文化相遇时,如果其中一种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对另一种文化采取根本性的排斥,那么两种文化之间就必然出现剧烈碰撞。跨界民族的文化冲突就在这种碰撞的过程中发生了。
从文化、文明交流史的角度看,文化碰撞后通常会发生两种基本情形:(1)处于强势地位的文化凭借自身的优势,通过不断深入接触来影响或同化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同时,强势文化在影响相对弱势文化时,通常也或多或少地吸收异文化的一些有益的文化成分。⑥(2)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在遭遇异文化时,会自发地进行自我反省,往往表现出对自我文化的一种批判与反思,以及围绕异文化与自身文化何去何从或两种文化如何相处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对跨界民族而言,他们身处两种文化包围之中,这种反思更为直接和真切,尤其是当少数群体遭遇强大的异文化裹挟时,社会精英们要么主动融入异文化的主流之中,要么通过社会行为方式唤起本族群的祖先记忆以强化本族群文化的完整性与稳定性,这种行为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记忆”。⑦
对于跨界民族而言,文化反省后随之而来的是在文化层面进行适应性调整。这种调整是对被强势异文化包围的必然回应。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国家疆域相对稳定,民族跨界而居已成常态,无论是处于和平跨居的状态,还是处于抗争分裂的状态,绝大多数跨界民族必须接受这种基本现实,并在文化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与适应。跨界民族在文化层面上的调整,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其目的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在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更好地起到族群凝聚与社会动员的作用。跨界民族文化层面上的调整通常分为表层与深层两个层次,涉及日常生活、传统习俗、语言文化、心理适应等方面。表层的调整或是应对异文化压力之需,或是在基本适应的情景下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而深层的调整旨在通过强化的行为方式以增进本族群的社会凝聚。
跨界民族在经历上述文化层面的冲突、反省和调整之后,形成文化认同。可以这样概括跨界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逻辑:文化碰撞(冲突)→文化反省(批判)→文化调整(适应)→文化认同(自我与他者)。文化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经历相应阶段之后的行为方式,诚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文化认同性的动态性及其变形表现在不同文化群体的交往之中以及随后的涵化过程。”⑧
2.跨界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功用。跨界民族由于身处两个或两个以上文化环境之中,在同其他族群发生联系时通常会形成一种模糊的族群边界,这种族群边界的巩固与发展通常取决于“地方性知识”和社会情境的交互作用。在此过程中,族群基于自身文化的符号和历史记忆,通过“自我”(我族)与“他者”(异族)等区分类社会行为来强化身份认同。“‘族群自称’常是最有效的族群认同与族群边界的符记,有共同称号的为同一族群,以区别于使用不同自称的人群。”⑨由此可以推论,认同是建立在区分之基础上的社会行为,跨界民族的文化认同亦是如此。
在现实中,跨界民族通常是所居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有时其中一部分在一国是少数民族,有时都是所在的国少数民族,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形,跨界民族在进行文化认同时,都伴随“区分”的社会行为。这种“区分”一方面体现在跨界民族作为少数民族与所在国主体民族之间的区分,另一方面还体现在这些特殊的少数群体对自身身份的确认。中东地区的库尔德人就是最好的例子。作为中东的古老民族之一,库尔德人由于诸多原因至今仍然没有自己的国家,而是作为少数族群分布在土耳其、伊拉克等国家,与所在国其他族群的关系在总体上呈紧张状态,他们的身份一直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以致库尔德人在这些国家一直试图通过社会区分来强化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⑩
跨界民族文化认同的第二个基本功用是,通过认同行为的实现以增进族群内部的凝聚力。尽管凝聚力始终是每一个民族都在刻意弘扬与维系的重心,但在实现形式上却有很大的不同。前现代民族是靠“共同的名称、共同祖先的神话、共享的历史记忆、某些共同的文化因素、与故土的联系、社会精英的心理意识”(11)等形式来强化,而现代民族则是由其“共同文化和共同法律来界定”。(12)当跨界民族自身文化遭遇来自异文化的强大压力时,跨界民族中的精英分子会选择文化认同方式,以唤醒本族群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以及文化所赋予、联系的身份与权利,这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社会过程。当跨界民族完成这一社会化过程之后,经由文化认同而实现的族群内部凝聚力也就得以增强,从而保证本族群在身处异文化的包围之中能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跨界民族文化认同还具有社会动员的功用。在一些存在跨界民族问题的地方,跨界民族中的精英分子通常会运用历史解释、教育感化、传媒影响、宗教联系和政治参与等方式来增进本族群的文化认同,这些方式或多或少地都包含文化的元素。精英分子之所以采用文化认同来进行社会动员,是因为文化认同作为一种集体行为,其“形式是由个体或集体的经验创造的,由习惯、风俗和记忆来教授的,它们往往受过了经久的考验”。(13)
3.跨界民族文化认同的主要影响。跨界民族的文化认同及其相应行为通常会影响到族际关系甚至相关国家之间关系,原因在于跨界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其政治认同、民族认同、社会认同和地域认同的重要基础,(14)它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其他认同的走向与发展。可能也正是由于文化认同的重要性,人们对跨界民族文化认同的认识往往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因此,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要千方百计地采取一些强制措施,诸如在文化层面强行推行主体民族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或行为规范,对处于弱势地位或边缘地位的跨界民族之文化采取压制性措施或忽略的态度,企图实现强制同化,但这类做法通常收效甚微。比如上面提到的库尔德人问题,在土耳其,库尔德人是仅次于主体民族的第二大群体,但自1923年以来,土耳其政府并不承认该族群,禁止在学校和公开场合使用库尔德语,企图以强制同化的政策使库尔德人丧失其认同,进而建立一个族群同质化的国家。这些政策没有取得成功,反而激起库尔德人的反抗。(15)直到今天,库尔德人问题一直是土耳其政府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跨界民族文化认同的影响主要通过族际关系互动来发挥作用。跨界民族文化认同所表现出来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可以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族际关系乃至国际关系中表现出来。在一个存在着跨界民族的国家里,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基本适应还是完全对立,是和谐发展还是相互隔阂,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跨界民族进行文化认同时的基本走向;而且在此基础上,相邻的两个国家如何处理这种关系,是采取措施鼓励跨界民族积极融入所在国的社会生活中,还是鼓励跨界民族采取分离行为,也必然影响到跨界民族文化认同发展的走势,因为“受刺激的各方不仅强调本文明的认同,而且强调对方的文明认同”。(16)同时,跨界民族的文化认同又影响到本族与其他族群之间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因此相关国家间的关系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因此,跨界民族与族际关系、国际关系形成了一种交互作用的关系。可以中国和泰国的例子来加以说明。许多分布于中国、越南、老挝和缅甸的族群,可能称谓有所不同,但其中的许多族群却是同根生的民族,属于典型的跨界民族。(17)这些跨界而居的族群,长期以来由于建立了良性的族际关系,加上其所在国家都推行相对积极的民族政策,所以他们在文化认同、族际关系和国际关系方面呈现出良性互动的态势。可是,对于泰国南部马来人穆斯林,由于泰国当局长期以来对他们采取了边缘化政策,其文化认同也变得异常复杂。受此影响,泰国的族际关系以及泰、马两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跨界民族而变得十分微妙。一方面是泰国的防范,另一方面是马来西亚的关注,最后加剧了泰南马来人对泰国的背离以及认同的转向,而这种对其邻国的认同又因他们与邻国的穆斯林兄弟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而得到强化。(18)
三、跨界民族文化认同的现代建构
自近代以降,随着世界性的社会转型的深入演进,民族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敦促国内各族群在最高层面上进行认同,以此来加强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从而强化社会的稳定。在这些措施中,文化认同是民族国家的主要关切之一,因为文化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关涉了国家认同、族群认同和社会认同,因此民族国家通常会通过赋予文化认同的现代性来强化其他层面的认同。这一复杂的社会过程,实际上就是民族国家对文化认同的现代建构过程。由于现代性(modernity)是现代社会转型的衍生物,所以现代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会建构来体现的,这种行为特征在跨界民族的文化认同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跨界民族进行文化认同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且包含了多重现代性因素的行为选择。民族国家应该推行包容和宽松的民族政策,正确引领跨界民族进行文化认同。由于建构文化认同的基点是对“既有文化的认同”和“新的因素的注入”,(19)所以跨界民族的文化认同事实上是一个包含了历史与族裔文化的特定的现代建构过程,其中伴随的“连续性与对历史的尊重内在于民族—文化身份之中”,这是因为同族群密切相连的文化与民族归属,“既是被选择的也是建构性的”。(20)若想解决这一问题,跨界民族的精英分子还必须从自身原生的族群文化入手,通过引入现代性的因素,进行现代建构,因为“族群文化基于内在特征和历史过程,可以建构其合法性和自主性”。(21)
从本质上讲,这种文化认同的现代建构,其实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费老指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22)因此,对跨界民族来说,建构文化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践行文化自觉的社会行为,并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与所在国的其他族群建立和发展良性的族际关系,这是因为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包含了基本的意识问题,即:“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究竟应该确定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发展目标?怎样实现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标?”(23)体现在跨界民族身上,就成了他们对自己的过去(历史记忆与族群文化)、现在(族际关系)和未来(实现路径及发展取向)的反思性行为。
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来说,在多元社会建立互信、消除隔阂、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在处理好权力、资源、制度等问题时,也不应该忽视文化认同问题。(24)跨界民族文化认同的现代建构即文化自觉,正是费老所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种现代建构要求民族国家、社会和族群相互适应,理性地进行身份认同,尤其是民族国家要采取积极行动引领族群进行良性族群关系的建构,最终形成相互包容、彼此适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多民族国家尊重和保护作为少数民族的跨界民族的身份、历史和文化,乃至接受其正当与合理的诉求,并在社会经济方面采取宽松和扶持的政策,促使跨界民族尽可能地融入所居住国的主流社会中去;处于弱势地位的跨界民族也要接受社会现实,即当今民族国家之间的疆域总体上是稳定的,他们应该放弃分离诉求,不要将自身隔离起来,避免出现从“想象的边缘”走向“事实的边缘”。同时,与跨界民族有关的国家不应该过多地卷入对方的内部纷争,更不应该鼓励和支持跨界民族采取分离的行为,否则,由于跨界民族引发的族际关系可能会最终会影响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发展。
世界是多元的,文明是多样的,各民族文化应该相互包容、共存发展。民族国家要采取平等、积极和务实的民族政策,通过建立良性族际关系来引领跨界民族进行理性和正当的文化认同,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跨界民族问题,促进跨界民族在认同方面进行现代建构,在多元一体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自觉,最终形成“和而不同、共存共荣”的理想格局。
注释:
①马曼丽:《中国西北跨国民族文化变异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09-210页。
②〔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4页。identities本身具有“身份”、“认同”、“特性”、“同一性”等含义,本文使用的是“认同”之义。
③〔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2008年。
④〔美〕乔纳森·弗里德曼著、郭建如译:《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4页。
⑤〔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33页。
⑥〔美〕罗伯特·墨菲著、王卓君译:《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60-261页。
⑦类似的表述还有“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祖籍记忆”,这些表述用语适用的语境和内涵可能并非完全一致,但有许多内容是交叉的,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文化认同概念的多维性与动态性。详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等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杨晋涛、俞云平:《东南亚华裔新生代的“祖籍记忆”——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个案比较》,载《世界民族》,2007年第6期。
⑧〔黎〕萨利姆·阿布著、萧俊明译:《文化认同性的变形》,载《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文化认同性的变形: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5页。
⑨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72页。
⑩陈建民:《当代中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5页;辛旗:《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中的宗教根源》,海南出版社,2002年,第111-117页。
(11)Anthony D.Smith,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Oxford:Basil Blaekwell,1986,pp.22-30.
(12)Anthony D.Smith,The Nation in History:Historiographical Debates about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Hanover: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2000,p.65.
(13)〔法〕马克·富马罗利著、萧俊明译:《“我是他人”:对于同一性的误解》,载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文化认同性的变形》,第34页。
(14)由于族群的认同关涉诸多方面,所以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不同表述方式,如政治(国家)认同、族群(民族)认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以及地域认同等。它们之间是有着内在联系的,甚至还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如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所强调的高层次认同,族群认同则是在国家认同的前提下进行的群体认同。可以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的精彩论述为例。他说:“中华民族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高层次认同,对本民族的认同是低层次认同,不同层次的认同可以并行不悖。”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页。著名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则认为,认同包括了“合法性认同”(legitimizing identity)、“抗拒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和“规划性认同”(project identity)。详见〔美〕曼纽尔·卡斯特著、曹荣湘译:《认同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6页。这些论述为理解跨界民族的文化认同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路径。
(15)咎涛:《被承认的问题》,载《读书》,2009年第2期,第42页。
(16)〔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306页。
(17)我国共有31个跨界民族,占我国民族总数的55%。这些跨界民族成为我国和邻国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是中国在处理与邻国关系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详见葛公尚主编:《当代国际政治与跨界民族》,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二十六、二十七章;刘稚:《中国——东南亚跨界民族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五章;范宏贵:《同根生的民族——壮傣各族渊源与文化》,民族出版社,2007年;周建新:《和平跨居论——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
(18)陈衍德:《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7页。
(19)郑晓云:《文化认同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32页。
(20)〔以〕耶尔·塔米尔著、陶东风译:《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18-22页。
(21)常宝:《试论全球化与族群文化的自主性问题》,载《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第51页。
(22)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载《费孝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48页。
(23)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载《文艺研究》,1999年第1期,第5页。
(24)王建娥:《民族分离主义的解读与治理——多民族国家化解民族矛盾、解决分离困窘的一个思路》,载《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第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