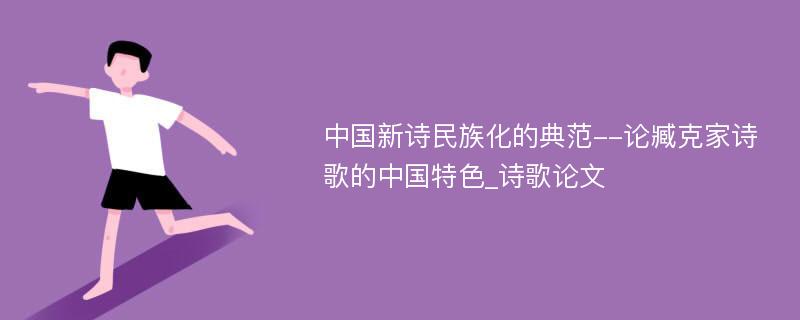
中国新诗民族化的典范——漫论臧克家诗的中国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新诗论文,典范论文,臧克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臧克家在他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从诗才焕发的青春年少,到诗情不衰的耄耄高龄,始终是在诗的轨道上驰骋,“新诗旧诗我都爱”,表明他是传统诗歌与新诗之间的传棒接力者。时至今日,还有人竭力把中国诗写得象翻译成汉语的外国诗,而三十年代初的臧克家,却是入手便将新诗写成道地的中华民族的诗,中国农民的诗,出身于中国农村,有一身泥土味的知识分子的诗,以至闻一多先生在为他第一本诗集《烙印》写的序言中,将他与唐代的孟郊相比,因为《烙印》中所表现的“生活”正是中华民族持续了数千年的艰难生活,“这可不是混着好玩”的生活。臧老的诗,从一开始,其内在的意蕴便是中国的,有着民族化的深深烙印;在诗的形式方面,臧老又写的是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式的新体诗,并且多是与传统形式大相异趣的自由体诗,他不写与传统形式较为接近的齐言体或民歌体或词曲体的新格律诗,更不仿作西洋的格律体诗。我们将他的作品置于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乃至稍后出现的艾青等诗人的作品之中细细品味加以比较,便会感到他的诗中国味特别足,绝非传统诗词又令人联想到古典诗词的韵味,既是不受任何固定格律约束的自由体但又没有丝毫洋化迹象,是确确实实地彻里彻外地中国化了、民族化了的中国新诗。六十余年后我们回首检阅一下中国诗坛的芸芸众生,可否这样说:臧老的诗是中国新诗民族化最突出的典范,或者说,是最早树立的典范。当然不能说他在中国现代诗坛一枝独秀,但谁也不能否定此人此诗唯在“国花”之列。
这不足怪,因为臧老从他写第一首诗始,就是非常自觉地走新诗民族化的道路,有着非常清晰的民族的审美意识,他自己说过:“我很喜爱中国的古典诗歌(包括旧诗和民歌),它们以极经济的字句,表现出很多的东西,朴素、铿锵,使人百读不厌。我在初学写诗的时候,就有意地学习这种表现手法。”(《臧克家诗选》1956年版序)臧老没有出国喝过洋墨水,但他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对中国古典诗歌知之甚多,研之甚深,品之甚精,在当时,有如此功底之人多入写作旧体诗词之圈,流连风雅,但臧老却不,他心中最爱却不从事所最爱,毫不保守地拼弃他所最爱的旧诗的形体,吸取传统的营养,营造新的形体,终于使他的心血创作免于成为传统诗史的“回光”(他晚年创作的旧体诗,其功力及作品的优秀程度,使他置身于梁启超、柳亚子、陈衍之列毫不愧色),成为了中国新诗史上杰出的一大家。
臧老的诗之所以最具民族化特征,“化”里且“化”外,我品其诗之精华,觉得最主要之点就在于:其里曰“意境”,其外曰“炼字”、“炼句”。里外结合,交融契合于一,其民族的气质、气派、风格、韵味等等,便不可移易了,犹如一个孩子在中国母亲的腹中孕育,出生之后说的又是母语,便只能是一个中国孩子。
记得我还是读初中时,初次读到《难民》中“日头坠在鸟巢里,/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陌生的道路,无归宿的薄暮,/把这群人度到这这座古镇上”等诗句,我们眼前立即展现出一幅古镇黄昏难民满街的图画,我好象也身临其境,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诗的艺术境界之魅力。臧老初写诗时,就是自觉地着力地追求并创造诗的意境美,他说过:“诗人饱和着思想感情,把客观事物的感受造成优美的意境。”又说,炼字炼句都是为造成诗有意境,“如果意境不高,徒然在字句上下工夫,那只会显现匠气,却不能创造出动人的佳句来”。(《学诗断想·推敲》)诗的意境说在中国古典诗学中可谓源远流长,汉代《淮南子》就有“览物之博,通物之壅,观始卒之端,见无外之境”的发明,唐代“诗境”说已经成熟,为唐诗走向诗艺高峰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诗家夫子”王昌龄将诗境分为三种类型三个层次,即“物境”、“情境”、“意境”,后者高于前者。读臧老的诗,我觉得他很少模山范水、状景写物的去“造成”物境,他更多是触物、触事生情而呈现情境,或是经思想的升华、表现生命的体悟而上升到意境。以他的早期诗言,《难民》、《洋车夫》乃至脍炙人口的《老马》,表现的都是一种特定的“娱乐愁怨皆张之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的情境,难民沉默的场面,洋车夫“呆着象一只水淋鸡”,老马的“有泪只往心里咽”,实际上都是诗人“深得其情”而有此悲怆的笔墨。臧老是一位情感丰富但又富于理性、有很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诗人,更多的是“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而“得其真”,于是《天火》、《不久有那么一天》、《生命的叫喊》乃至写人物的《炭鬼》等篇章,皆显示诗人“捣碎这黑暗的囚牢/头顶落下一个光天”的愤世之意,从而落得了壮美的意境。这种情境与意境的创造,恰恰是诗人深深植根于中国农村土壤之中结出的诗葩,臧老自己说过:“对于出现在我的诗篇里的那些人物,对于乡村生活的景象,我不是偶然遇到他们,或是过眼云烟地接受一点浮薄的印象,然后凭想象去把它创造成诗的。不是的,活在我诗里的那些农民形象,几十年就活在我的心上;展开在我诗里的那乡村生活的图景,几十年来从没有淡忘过。”这就是臧老诗的意境之本,铭刻在心上的东西自然也就凝定于作品之中,“深厚的生活才是诗歌最肥美的土壤”,这是臧老的艺术真言!
不只是写农村生活的诗,其他题材的诗作,臧老同样注意创造或壮美、或优美、或博富、或深邃的意境。他写军旅生活的诗,使我联想古代的军旅诗或边塞诗,《从军行》的激昂,《壮士心》的悲慨,《兵车向前方开》的英武,《匕首颂》的冷峻,无不是爱国抗日志士的心境坦荡表现。《运河》、《血的春天》以及《大别山》、《马耳山》等较长的篇什,则展开从诗人壮怀激烈到祖国壮丽山川的雄浑之美。诗人运用多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境和创造诗的意境,长诗《自己的写照》更多的是直抒胸臆,感情的直写;而《春鸟》则以春鸟为一个活跃的生命的意象,映衬自己有“早醒的一颗诗心”可是“喉头上锁着链子”的痛苦心境;《依旧是春天》则以纯净优美的景物描写而“感时”,蕴含国难深重的忧愤于字里行间,却不着迹象,完全符合古代诗人所追求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境在象外”,从而使此诗大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这样的诗,在臧老的诗集中常常遇到,令人品味不尽。他在1956年写的被著名诗人张光年赞为“真正的艺术品”的《海滨杂诗》,首首短小精炼,首首都以有悠远的意境取胜,如《会合》仅三句:“晚潮从海上来了,/明月从天上来了,/人从红楼上来了。”此种境界简直就是司空图所激赏的“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廿四诗品》),不着意营造,而最美的境界宛然天成。又如另一首《一瞥》也只有四句:“海水蓝,天色蓝/一片蓝色分不开边,/它作了一个少先队员的背景,/她的红领巾红得比虹还鲜艳!”大自然与人、静与动,对比分明的色彩,经诗人妙手融合,其境之美完全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这样的典范之作,在《凯旋》组诗中也有,读之感到美不胜收。臧老不少有关人生思考的诗篇,具有大科学家钱学森所标举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最高的台阶,那是表达哲理的、陈述世界观的”即有很高的哲理境界,建国前写的《忧患》、《无名的小星》、《星点》、《星星》等,已颇富哲理意味,诗人对于星星的连贯思索,后来终于来了一次飞跃,强度的升华而写出了家弦户诵的《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有的人》不是物境,不止于情境,而是达到了意境的高层次--哲理化境界:“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这首佳作曾选入中学语文课本,铭刻在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少年心中,它激励着多数人“更好地活着”,以至在1976年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诗潮中,有两位青年女工把这首诗抄在黑板报上,引起了革命群众热烈欢呼和“四人帮”爪牙的极大恐惧(见《学诗断想·〈有的人》的遭遇》)。哲理化境界的呈现,使这首诗超越了纪念鲁迅的具体事件,超越了对鲁迅个人人格的评价,获得笼括一切空间和时间的悠久的普遍意义。
追求意境美,有着营造高层次艺术境界的非常自觉且警醒的审美意识,带来臧老的诗一个更豁目的异常出色的特征,以至不看署名便可准确判定:这是臧克家的手笔--这就是臧老诗有高超的“炼字”、“炼句”之功,从而有他人与之不混淆、不可仿造的独特的语言风格,用现在很时髦的术语来说,臧老有纯属他个人的“话语”系统。
谈到意境创造与诗的语言的关系,臧老在《新诗旧诗我都爱》中说过一段很精当的话:“我们向优秀古典诗歌学习,当然要学习古代诗人那种体物入微、传情入神,善于把自己的生活经验造成美丽动人的意境,用以少胜多的极为高强的概括力,使笔下的诗句成为色香俱全、铿锵动听、永不凋谢的艺术花朵。可是这就不能不涉及造句遣词等等具体问题,这两者是不能分开的。只有具体体会、学习了古人造句下字的艺术功力与独到的手法,才能使我们自己的作品得到提高。”为创造好的意境而炼字炼句,“意境虽美,表现力不强也是徒然,字句的推敲在这里起着很大的作用。”他还说过:“对于自己的诗创作,我是相当严格地要求它的字句精炼的。我坚决地认为,以经济的字句去表现较大的思想内容,这是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草率、罗嗦,是诗的致命伤。诗的寿命在于思想深刻、感情饱满、表现简炼含蓄。含蓄才能吸引人百读不厌。”这是深得诗之三昧的经验之谈,至理真言,可惜当今大多数诗人尤其是年轻的诗人,没有高度重视臧老六十余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
“炼字”云云,出自托名白居易的《金针诗格》:“炼字、炼句、炼意、炼格。炼字不如炼句,炼句不如炼意,炼意不如炼格。”后人评曰:“世俗所谓乐天金针集,殊鄙浅,然其中有可取者,‘炼句不如炼意’,非老于文学者,不能道此。又云:‘炼字不如炼句’,则未安也,好句须有好字。”臧老反复言此,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是不容置疑的“老于文学者。”臧老诗歌的语言特点一言难尽,我就自己感受到的,且有深刻印象的略述三端:
(一)炼字以传“神”。臧老学习古代文人炼字,炼有动感的字,已为广大读者熟知的如《难民》中“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黄昏爬过了古镇的围墙”,以“溶”字和“爬过”传黄昏景色之神;“螺丝的炊烟牵动着一串亲热的眼光”,“牵动”传难民眼睛之神。《神女》中“她会用巧妙的话头,敲出客人苦涩的喜欢”,一个“敲”字,尽传一个强作欢笑的妓女阅世颇深观人颇精之神;“记忆从头一起亮起”,一个“亮”字,又传她无可奈何之神。《场园上的夏晚》里“蝙蝠翅膀下闪出了黄昏,蛛网上斜挂着一眼热闷”,“闪出”和“斜挂”使黄昏和闷热都有了质感,有了神气;“用拔不出来的耳朵听红毛的鬼怪”,绝妙地描写小孩对鬼怪故事痴迷的神情。写大别山,“眼光投出去,山头又给碰回来”,一个“碰”字又传大山高峻庞大之神。写长安东面的形势:“压一座潼关,在风陵渡”,不用“立”而用“压“,出人意外地暗示了潼关“一夫挡关,万夫莫开”的沉重份量。……这样一字之炼的例子太多了,不胜枚举,臧老称此为“诗眼”,他举古人“沾衣欲湿杏花雨”说:“一个‘欲’字多少情味;一字之差,关系非浅,这是‘诗眼’,确有画龙点睛之妙。”(《学诗断想·推敲》)“欲”字是虚词,炼虚字而“点睛”难度再大,可臧老也有出色的范例,那就是前面已提及的《依旧是春天》,题中出“依旧”二字,诗的最后两句是“东风留下了燕子的歌,碧草依旧绿到塞边”。此诗的“韵外”、“象外”之意,完全是靠“依旧”来传导。后来他自己谈到此诗时说:当时国难当头,蒋介石却不准人民抗日,“春天来了,大自然景物依然,静谧柔美,好似东北没有沦亡,山河没有变色,大敌没有压境,人民没有反抗……。绿草仍旧绿到鸭绿江边,绿到塞外,而我们的主权已经达不到那些疆土了!静境中,包括着激动,柔弱中满含着义愤!”可以这样认为,“依旧”是此诗的“诗眼”,此中含多少情味,诗人巧用一个虚词,无异于化腐朽为神奇。
(二)炼句以造境。炼字实质上也在炼句,句中有眼,不但全句且往往使全诗为之生色。但也有相对独立的炼句,比如臧老自己谈到过的《不久有那么一天》的结句:“象黑夜过去了就是光明这样一个意思,如果平白地直说出来,会令人觉得淡然无味的,我反复寻思,把它写成:‘黑暗的长翼下/伏着一个光亮的晨曦。’”这两句诗,论炼字并无神奇之处,但它从整体拓展了全诗的意境,承前面“不久有那么一天,/宇宙扪一下脸,来一个奇怪的变”的预言,意象化地喻示光明即将到来。再如《自己的写照》中有:“八叔手中的剪刀绞断了我的小辫,/大清的江山也叫我那条辫子摔开。”这里既炼了动词“绞断”、“摔开”,但使诗的境界豁亮的是摔掉了“大清的江山,”时间空间瞬刻一变。《春鸟》的诗情之所以如行云流水,不能不得力于诗中出色的炼句,如“你的口/歌向青山/青山添了媚眼;你的口/歌向流水,/流水野孩子一般;……”同样《大别山》中的:“日月从石头上出没,/天地把人心挤得放不宽;/青峰随意乱排起阵势,/峭壁要耸耸身子飞上天。/水色不让山光姣好,/把媚眼的瀑布挂在山腰,/流泉到处卖弄清响,/把石子冲洗得光滑剔亮。”经过诗人反复锤炼的诗句,本来并不奇特的寻常山景,因诗人传情入神而充满灵趣,诚如王昌龄所说:“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臧老诗中炼句的妙句佳句,亦是不胜其摘。如果说,炼字主要是炼动词,那么炼句主要炼形象与意象,“意象欲生,造化已奇”(司空图《诗品·缜密》)。我还想举《在毛主席那里作客》,写领袖的召见和谈话,表现如此庄重的场面,诗才不逮者很容易陷入平板和呆滞,可是臧老的生花之笔,处处从谈话之外写谈话创造的一种和谐的氛围,畅美的境界:“我们谈诗,谈百花齐放……/话题象活泼的小鸟/它不停留在一棵树枝上”;“他的心象海洋/他的话是轻快的波浪;把地毯变成了一片草地-/窗外透过来雪后的阳光,/大块玻璃屏风上那银白鸟儿,/倾听我们谈话听得出了神”;“你听见过,站在天安门上/他那震动世界的呼声,/闲谈的时光,他的音流象春水溶溶”,“在握手告别的时候,/许多话题突然来撞心胸,/走出这庄严温暖的厅堂,/白皑皑的雪色诗意一般浓。”从引录的部分诗句,足见臧老的“炼句”(也包括炼字,如“撞”)之功,他终于将这次作客和谈话,幻化为“活泼的小鸟”、“轻快的波浪”、“春水溶溶”等生动的意象,酿造出了一个诗意浓郁的纯美境界。
(三)炼意以求精。臧老常说:“诗贵精”,强调“一行优秀的短句,可以胜过一万行陈言滥调。诗的价值和它的大小不成正比例。有时适成反比。”炼字炼句是诗求精之一途,但是此二炼都从属于炼意,为炼意服务。意愈精粹,才有真正的句简字精。他还说,宁可把长诗的材料压成短诗,压缩得越强,概括力越大,诗小,含量可不小,咫尺具万尺之势(《学诗断想·诗贵精》)。“短小精美”是中国诗歌的好传统,臧老创作过不少短小精美的诗,以意蕴深永又语简字精而广为传布人口。《老马》一诗只有八句,刻划一匹拉车老马的形态神态,隐喻和象征中国农民累世百代的苦难境遇,它不会让人“只就它本身来看,而更多地使人想起一种本来外在于它的内容意义”(黑格尔《美学》论象征语)。另一首《三代》仅六句:“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葬埋。”同样是写农民的命运,较之老马虽直白一些,但在“洗澡”、“流汗”、“葬埋”三个词中隐含了多少没有说出来的东西,真正达到了意精、语精、字精!在今年第5期《诗刊》上读到臧老一首近作,只有十个字:“我,/一团火。/灼人,/也将自焚。”我以为这十个字描述了臧老的一生,概括了臧老的一生,他的秉赋,他的人格,他的追求,他的痛苦与欢乐,都压缩在这十字之中。曾风行一时仅用一个“网”字而以《生活》为题的诗,彼精则不能再精矣,但较之臧老的《我》,何其苍白和萧索!臧老曾在一篇短文《一首短诗的构思过程》中,介绍他在写作《凯旋》组诗中的《联系》时是如何炼意的:蛰居医院之中,躺在病床之上,“黑夜来了白天去,/天花板象一页读腻了的书”,但通过收音机耳机天线与沸腾的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到祖国工业、农业等各条战线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他的诗心大大活跃起来,想写“那些动人心魄的大事件”,但事件很多,从那儿下手?“什么都写,不等于什么也没有写吗?”踌躇再踌躇,最后否定了“非写三四十行莫办”的初衷,“决定把工业、农业、国防……等等的形象和意义放到幕后去,终于写成这样八行。没有说出的那些东西,叫它包涵在最后两句里,让读者自己去体会。不把诗行放在读者眼底,把它们放在读者的心上。”(最后两句是:“耳边有一条长长的线--/是一条心呀在紧紧联系。”)这首诗,我不敢说它是臧老最好的作品,时过境迁的读者,是否还能体会到诗人当时激动的内心感受,仅是这则谈构思过程中如何炼意的短文,把诗行“放在读者心上”的精警之言,就有永恒的意义。“感受得极丰富,字行却极吝啬,越嚼水分越多,越噗咂越甜”,臧老摄住了中国古典诗歌所以深入人心的“魔力,”并使“魔力”发挥于自己的作品之中。
臧老常常琢磨“诗味”,他得出结论:“是诗人把深切的生活经验,鲜明的思想倾向性,浓烈而真挚的情感,独特的艺术手法,酝酿、熔炼而成。注入的东西越多,诗味也就越浓。”本文之所以特别标举臧老诗的“中国味”,是因为他在上述这些原则性要义之下,特别追求中国式的意境,运用中国式的艺术手法炼字以传神,炼句以造境,炼意以求精,真正达到了“情与景会,事与心谐,含蕴沉湎,百炼千锤”的艺术至境!
臧老对中国新诗民族化的毕生努力,在当今的诗坛还具有典范的意义。中国诗人到底应该写“美国诗”、“法国诗”……还是应该写中国诗,看来当今诗界不少作者尤其是青年作者对于理所当然的事情尚缺乏自觉的意识。诗歌文体、形式、表现手法尽可多样化,但最终成果必须有中国味道,尽管这种“味”或不是当前的常味,为所有中国人都习惯的口味,悠久的时间终将品出此味唯此一空间才独有,与彼一空间之味绝不会混同。诗须有意境,字精句炼,似乎凡为诗、愿成为优秀诗人、愿把诗行放在读者心上者,应当视为创作实践中的应有之义!说中国诗学中的意境理论是孔夫子中庸哲学的产物,是“反映封建主义理性精神、中和原则的诗的批评标尺”,实质是不懂中国诗歌精神、精义真谛的妄语。以芜杂的或尽量洋化的语言来掩饰诗的意蕴之浅薄,诗情之贫乏,更是对中国民族化诗歌好传统的践踏和亵渎;在中国新诗向21世纪迈进之时,我们完全应该放眼世界,但要立足本土才能不丧失自我,不丧失家邦之感。与此同时,我以为切实研究臧克家等从“五四”时期走过来的、认真对待生活、认真对待诗、且有深厚国学和艺术功底的老诗人们的优秀作品,吸取和升华他们的创作经验,方能造就出新的典范!
1994年10月12日-14日
写于江西师大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