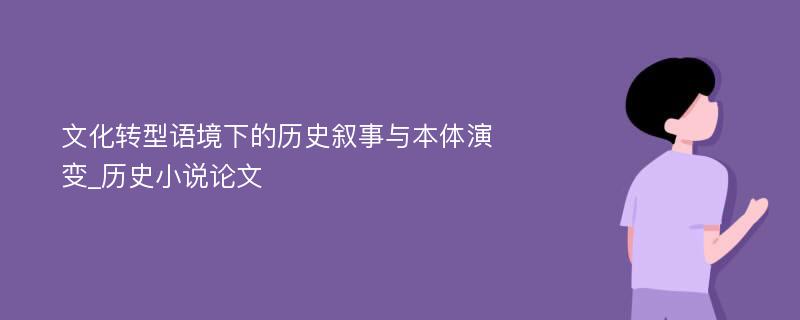
文化转型语境中的历史叙事与本体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本体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2)01-0062 -07
中国拥有丰厚的历史遗产,世界上的几个文明古国如埃及、印度、巴比伦,都没有像 中国这样保存了将近五千年的编年史和历史人物传记,拥有如此发达的史官文化。这些 都为我们作家的历史题材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由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原 因,自五四新文学以来,历史小说的创作一直处于冷寂境地,偶尔虽也有一些精制的短 章出现,但终未能形成气候。真正繁荣发达、引人注目则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事。在这 二十多年间,涌现了姚雪垠的《李自成》,端木蕻良的《曹雪芹》,徐兴业的《金瓯缺 》,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蒋和森的《风萧萧》,杨书案的《九月菊》、《孔子》 ,鲍昌的《庚子风云》,凌力的《星星草》、《少年天子》,顾汶光的《大渡魂》,刘 斯奋的《白门柳》,唐浩明的《曾国藩》、《张之洞》,二月河的《雍正皇帝》,黎汝 清的《皖南事变》等一批颇有影响的佳作,成为当代文学名副其实的一个重镇。这也说 明,历史小说只有尊重自身的创作规律,不再搞简单的影射比附,才有可能寻找到自己 恰当的位置。当然,在当今日益开放而无序的文化转型语境中,为了重铸中华文明的辉 煌,也为了在横向的民族交流中不至于失语,客观上也需要我们进行纵向的“寻根”或 “寻祖”。这种情况也为历史小说的崛起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和有利的外部条件。
何为历史小说?这当然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国人通常的解释即指以一定历史事实为 基础加工创造的这类特殊的作品,它与历史真实往往具有异质同构的姻缘关系。20世纪 80年代至90年代以来,在新的文学观、史学观尤其是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下,有人开始把 文本叙述中,只有“虚”的历史形态而无“实”的史实依据的作品也包括进来。这就使 原本比较复杂的历史小说在概念扩大的同时,也显得更为复杂。笔者倾向于历史小说的 文本叙述应遵循“基本事实和基本是非”要有所规范的原则,其所包含的内涵也不宜过 于宽大无边,以尊重历史小说有别于一般文学的特殊审美属性。但为了避免歧义和扩充 论述容量之需,在这里姑且沿用比较宽泛的概念来进行概括,即将只有“虚”的历史形 态而无“实”的历史依据的纯虚构的作品如《红高粱》也视为历史小说引进视野,同时 ,把它与革命历史小说如《遵义会议纪实》、《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等一起归属到“历 史题材小说”(而不是“历史小说”)这一整体概念上来,并分别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 的概念。这也就是说,我们在此所说的“历史题材小说”,从内部构成上看,实则包括 了“传统型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三大板块或曰子系统。这 个概念也许太宽泛了,但却可以在更大的视野范围内,对世纪之交二十多年来客观存在 的多元复杂的历史题材创作作出回应;而同时又不至于对多数人认同的历史小说概念进 行弃置,保持其合理合法的存在。在没有更好的命名之前,这样的划分也许是一个折衷 的办法,至少可聊备一说。
在界定了历史题材小说的概念内涵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对其展开具体创作的探讨了 。显然,这是一个相当烦琐的工作,可以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深入探讨。本文主要从历 时性的角度归纳、梳理其创作走向与发展轨迹。在笔者看来,新时期以来的历史题材小 说尽管错综复杂、良莠掺杂,在演进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但在时代之风和文学大 格局的影响下,总体而言是不断地走向成熟的,并以其沉稳和厚重彰显出自我存在的独 立意义。就纵向而论,其具体的创作过程大体经历了“爆发期”、“过渡期”、“多元 复合期”三个发展阶段。
一、爆发期:与反封建的新启蒙契节相符
新时期的历史小说是以姚雪垠的《李自成》为发端的。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该作前 两卷的问世,当代历史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爆发性的新阶段。与之相应的 对民族政治历史的反思,自然地成为广大历史小说作家普遍的自觉意识。作为“文革” 的过来人和“反右”运动的受害者,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给我们民 族和人民带来怎样的灾难性后果。因此,在“归来”乍初,他们就毫不迟疑地把情感指 向和主体价值追寻活动定位在对封建主义思想,尤其是作为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的儒家 思想的政治批判上。基于自己的切身感受,也是受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催动,作家们普 遍涌动起一种强烈的政治激情,他们关注并愤怒鞭笞的是封建传统文化中的君权独裁、 愚民政策、盲目崇拜、伦理至上、扼杀人性等方面的内容,就像当时涕泪交流的伤痕文 学、反思文学怀抱强烈政治忧患意识倾全力批判极左思潮一样。
翻看那几年反映农民起义或反抗外侮的《李自成》、《金瓯缺》、《星星草》、《风 萧萧》、《九月菊》、《庚子风云》、《义和拳》、《神灯》、《天国恨》、《天国兴 亡录》、《陈胜》等一批长篇历史小说,我们便会深切地感受到作者胸臆中那份浓浓的 政治情结,其文本叙事写得最投入、最感人、最具深度的莫过于揭示封建主义的这一部 分内容。姚雪垠曾不止一次地说他在写作《李自成》的过程中,“常常被自己构思的情 节感动得热泪纵横和哽咽”,以至于“不得不停下笔来,等心情稍微平静之后再继续往 下写”[1](P.5)。其他众多的作家如徐兴业、任光椿、肖军、凌力、顾汶光、李晴等也 都有类似的情形。正因为如此,这批充满政治激情叙事的作品也就平添一种特别的艺术 感染力和亲切感,一问世就处于颇高的思想艺术起点之上,与反封建的新启蒙思潮契节 相符,并成为这场新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反封建恰恰正是包括历史小说在内的 新时期整体文学走向“现代性”的起点。为此,历史题材小说的成就和影响自然也就远 远超出了自我本身,而在事实上成为当时整个时代的“文学经典”。这是历史小说最辉 煌的时期,它甚至可以说是继明代中叶首次高潮之后,在五百多年间中国历史小说所仅 见的又一次高潮。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时代之风,所以,《括苍山恩仇记》的作者吴越在一篇题为《历史 小说与反封建》的笔谈文章中,不仅公开声言“每一个从事于编写或创作历史小说的人 ,都应该在自己的作品中把反封建这个主题放在第一位”,甚至进而认定“一部历史小 说,如果反映不出这个主题来,就不是优秀的历史小说,就是没有完成一个有觉悟的作 家所肩负的任务”[2]。后来,有些人在回顾这段文学史时,对此多有贬斥,似乎写政 治就是公式化和概念化,这是片面的。其实,在思想大解放时代,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 表现出的热切关心之情是可以理解的,也不乏积极的意义,更何况中国历史本来就是一 部高度政治化的封建史。所以,即使从求真角度讲,历史小说作家也不应在文本中排斥 对政治的描写。过分地非政治或反政治,将政治排斥在文学之外,往往导致作品的浅显 和单薄。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数不少的新历史小说从局部看颇有意味,而就整体观照 却普遍缺乏思想艺术内涵而显得很单薄,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当然,这是今天的认识,在粉碎“四人帮”初期的历史时期,人们并不这么看,也不 可能这么看。那是文学与政治高度结盟的时代,也是作家政治激情高扬的时代。那时, “现代性”淡出,“政治性”高于一切,它往往成为人们创作和评论的最主要、最根本 的价值标准。这样的结果,就使得社会历史全部的丰富性有意无意地被抽象为一种两极 对立的简单形式。于是,这些卷帙浩繁的作品大多思想价值和艺术取向趋向比较单一, 其文本构造很难跳出农民/地主/、我军/敌军、革命/反革命、前进/后退、真/假、善/ 恶、美/丑、正/邪这样二元对立项的格局。人物的区分也是泾渭分明的,并相应组成“ 我方”和“敌方”两套话语系统:“我方”系统使用的是一系列美好的词汇,他们通常 是出身贫苦、英勇善战、光明磊落的人,具有超人的意志、崇高的品格、献身的精神, 甚至连相貌都高大英武,光彩照人;而“敌方”系统则由一系列丑陋的语言构成,他们 一般生于恶霸官僚地主家庭,生性贪婪好色,凶残阴险,愚蠢自私,身上还有人民的血 债,而且长相鄙琐。在实际创作中,这两套话语系统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 所有的描写都呼应着“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惟一动力”的经典论断, 而很少甚至不敢旁涉非阶级性的、纯人性方面的内容。即是说,这是国家的、民族的、 阶级的、神性的话语,而不是个人性的或大众通俗性的话语。反映在题材选择上,基本 都局限于暴力革命范围,阶级的、民族的战争或斗争受到高度的推崇而成为当时作家创 作的普遍体式。这种现象的出现,既与刚刚粉碎“四人帮”时社会文化处于戒备紧张的 现实境遇相吻合,同时更有其现实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在原因。
上述论及的历史小说中,比较特殊的是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在这部60万字的长 篇中,作者一反传统惯见的思维作法,热情歌颂了以谭嗣同为首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 改良主义,多方面地表现他们“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的先进思想和明知 不可为而为之的革新精神;相反,则把自下而上的农民起义——义和团运动作为戊戌维 新的陪衬,对其挖铁路、砍电杆、信奉神灵符咒等盲目排外、反科学的暴力行为给予笔 裹毫霜的严厉批判。这在历史小说中是不乏突破性意义的。在同时出版的周熙的《一百 零三天》中,我们也同样窥见到类似的创作意向。不过实事求是地看,这一类小说尽管 在思想内核上有创意,但它主要的价值还是政治进步性意义,而不是文化开放性意义。 故其文本中的戊戌变法及谭嗣同形象的描写,也明显具有两极对立的特征,其政治翻案 要大于艺术审美,以至政治激情化的叙事程式潜移默化地取代了文化冲突,遮蔽了文学 的审美原则。
也许正是在这一定位问题上把握不准,加上政治反思的创作动机与艺术实践在经过数 年以后,矛盾抵牾的现象日趋明显,作家们慢慢地发现,他们的政治历史反思虽可直接 “今用”于当代中国人的思想启蒙,但它离丰富、丰润和丰厚的历史本身毕竟还有相当 一段距离。当作家们一旦认识到这个问题时,他们对历史介入的态度也就不知不觉地发 生了转换。尤其是一批后起的作家,他们不得不放弃原先那种不堪重负的启蒙任务以及 自以为可以洞穿历史的理性判断力。这样,历史小说创作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第二个阶 段。
二、过渡期:非政治性的内容逐渐浮出水面
所谓过渡,是指从A到B的一个过程。它既是对前面“爆发期”的一种修正和调整,同 时,也为下文将要讲到的“多元复合期”进行必要的铺垫和转换。时间上大致从1983年 起始,延至20世纪80年代末,先后有七八年之久。
不必讳言,在整个过渡期,历史小说创作相对显得沉寂,成就和影响也不及在这以前 的“爆发期”。但是稍加细心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其间的历史小说仍顽强地搏动着要求 变革的节律。这种求变的推动力,首先来自历史小说界的内部。1984年、1986年,花城 出版社和中国作协分别在广州及湖北黄冈召开“历史题材小说研讨会”(花城出版社还 同时在1984年独家创办了《历史文学》刊物),便显示了历史小说圈子内的作家和评论 家要求突破、创新的强烈呼声。尽管此时大多数作家尚未形成明晰的创作思路,他们更 多的只是不满而不是构建,但是,那些对文学与历史有深刻理解的新锐作家,却在时代 精神的感召下切切实实地进行着思考和探索。在这两次讨论会上,《大渡魂》的作者顾 汶光等提出了对《李自成》、《金瓯缺》创作模式“超越突破”的问题[3],这其实寄 寓了作家对历史小说一体化模式的不满及要求革新的殷切之情。随着政治意识形态逐渐 淡出和思考的深入,过去被历史小说所遮蔽的非政治性内容逐渐浮出水面,慢慢地,革 命历史小说(如黎汝清的《皖南事变》)、新历史小说(如莫言的《红高粱》)也开始出现 了。另一方面,受波及到整个人文各学科“文化热”的影响和“观念创新”的驱动,历 史题材小说在整体上又明显表现出了由一般政治历史反思向文化历史反思转换的趋向。 愈来愈多的作家特别是年轻作家突破过去惯见的单一模式,自觉采用宏观的大文化视角 ,笔力所及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以及由此凝结而成的内隐和外显的观念系统,包括物质 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潜文化等方方面面。这就给作品在思维层次和艺术向度上带来了 两大新的变化:一是艺术重心已不再满足阶级论、农民革命动力说的概括和反映,而是 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把艺术思考的笔触投向朝代兴亡、文化人格、心理结构、人性冲 突等历史的纵深,从中开掘题材所固有的启人警世的思想意蕴;二是描写对象开始广泛 地由农民扩大到知识分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等各个领域,并且其创作热情也由单一的 价值倾向评判转移到对审美价值的把握上,写人叙事按照审美的需求来进行艺术处理, 因而,这些作品显示出了较高的艺术魅力和艺术品格。
就前种创作走向而言,顾汶光的《大渡魂》和已故著名老作家巴人(王任叔)的《莽秀 才造反记》比较典型。这两部作品都取材于农民起义失败的一段悲剧历史,然而,由于 它们没有简单地摘取某个流行的概念,而是透过历史的表象,深入揭示其中最本质、最 有意义的东西,因此,较之以往同题材作品,更具有一种耐人咀嚼的深沉意蕴。关于反 映农民革命悲剧的作品,我们至今见到的,大多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敌我力量的悬殊, 敌人暗中破坏等外部客观条件;从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苟安短视、争权夺利等内在主观 上寻找原因的,便是其中最深的一个层次了。《大渡魂》和《莽秀才造反记》对农民革 命悲剧的描写,可以说又更深入了一个层次。《大渡魂》主要从封建文化道德观和农民 思想内在联系的角度来感知、透视农民革命的悲剧根源。小说通过石达开在天京内讧后 率部西征入川,被清军围困大渡河畔惨遭全军覆灭的描写,富有见地地为我们开启出一 个令人怵目的深刻主题:农民革命的失败,不是败在天时、地利不好,也不是单单败在 人不和,更为主要的还是肇祸于石达开头脑中的以“忠义”为特征的因袭旧道德文化的 思想。而《莽秀才造反记》则主要是从民族和土地的“文化惰性”,如保守、循矩、沉 滞、古板、迷信、偏见、狭隘、陋习给人民精神心理带来严重损害的视点,来观照农民 起义的失败。作者深邃地揭示,由于它的存在、蔓延、恶性膨胀,致使发生在浙东的这 场“反洋教”的农民暴动,从义军领袖王锡彤到普通将士都普遍沾上了浓重的“小康安 命的思想,分散互轧的精神,疟疾似的痉挛的症状,时冷时热时辍时息的不能坚持到底 的行动,爱小利而忘远景的眼光”,而最终只能悲壮地走向毁灭。
与《大渡魂》、《莽秀才造反记》的艺术走向相并,过渡期历史小说在题材领域的扩 大特别是在审美意识的觉醒方面也有明显的拓展。先前政治性、阶级性的因素大大减弱 ,艺术性、审美性的含量不断得到增强。刘斯奋的《白门柳》就很具代表性,有必要引 起我们的重视。这倒不尽是这部三卷本的历史长篇在1997年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更主要的则是它领时代风气于先(这恐怕与作者所在的岭南文化的开放性有关),早在20 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整个社会文化尚处在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严格规范的情况下,按 照艺术规律,也根据对历史的认识,作者率先在这部反映明末清初士林斗争生活的作品 中进行了“审美”加“文化”的尝试。立足现代的写作立场回眸过往的这段王朝更替的 历史,刘斯奋敏锐地发现:真正体现人类思想和社会进步的,既不是爱新觉罗氏的入主 中原,也不是功败垂成的李自成农民起义,而是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我国早期民主思想的 诞生。这种不以阶级定性而以历史进步为标识的艺术取向,使作品对东林、复社名士群 体知识分子的描写有效地避开了是非曲直、忠奸正邪的评判模式,既有独到的新意和深 度,又获得了较高的审美价值。于是,我们看到,即使像钱谦益这样一个历来被视为十 恶不赦的“民族叛徒”,也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形象生动、具有多层立体的文化 符号。更不要说柳如是、董小宛、冒辟疆、黄宗羲这些名妓名士了,他们的悲欢离合远 远超出了阶级论的框范而充盈着丰富鲜活的文化信息和审美内涵。反映到具体的人事描 写,就是将历史的真与艺术的美有机地统一起来,始终坚持用审美的眼光观照历史,从 情节、场面的选择到细节、语言的处理,均按历史小说的审美规律予以造型。
《白门柳》外,本阶段还值得一提的是王伯阳的《苦海》。与侧重从传统文学那里寻 找可资借鉴的审美资源的《白门柳》不同,它承续三四十年代施蛰存及冯至的作法,在 创作上明显取法于西方非理性主义、存在主义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并以此观点 重新解释和处理民族英雄郑成功,在作品主人公身上抉发了与英雄、伟岸、崇高、理性 、完整、完美等一类截然相抵的鄙琐、阴暗、丑陋、荒诞、孤独、本能欲望。这样一种 审美观或人学观,与西方非理性主义、存在主义对人的理解是颇为一致的,而同新时期 以政治理性为核心的新启蒙主义主潮则相去甚远。公平地说,《苦海》在思想艺术上的 圆润丰满不及《白门柳》,作品中的中西艺术融合也存在着不少不尽人意之处,但它的 意义和价值却不在《白门柳》之下,且至少为当下历史小说艺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展示 了不同于《白门柳》的另一条新路:这就是大胆地走近西方,从它们那里寻找异质的审 美和文化资源。
三、多元复合期:个人化写作造成“众声喧哗”的复杂景观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历史题材小说从政治性向文化性、审美性转换的过渡 期,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它则进入了更加丰富驳杂也更为混沌无序的多元复合期 。如同其他文体一样,在转型步履的急剧催动下,历史题材小说整体格局又一次发生了 全面的刷新和嬗变,原来相对统一的艺术理想被日趋鲜明的个人化写作所取代。20世纪 80年代后期,寻根小说、先锋实验小说、新写实小说所开始发生的转向,加上后现代主 义和新历史主义的登堂入室,对本阶段历史题材小说的多样化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 家们不再按照对历史的共同理解来进行创作,而是以个体的生命体验与独特的方式,来 描写自己心中的历史。在这种情形之下,历史题材小说看似丧失了20世纪70年代至80年 代的那种“轰动效应”,但坚持个人独立性的结果,倒是使它有可能回到文学本体的起 点,在总体上获取更加真实的艺术效果。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题材小说仿佛是一个令人 眩目的万花筒,新的、旧的、洋的、土的、雅的、俗的,各种各样的“主义”和“形式 ”都有。以前从未有过的,现在有人在写;以前比较幼稚的,现在愈来愈趋向成熟。其 间的成就不可小觑。特别是1993年,短短的一年中推出了凌力的《暮鼓晨钟》,唐浩明 的《曾国藩》,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李锐的《旧址》, 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等一批佳作,几可称为“历史题材小说年”。从某种意义上 看,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题材小说已走向一种集体性的“众声喧哗”。这种“众声喧哗 ”当然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固有的创作直接有关,但更为主要的还在于它体现了20 世纪90年代更加自由开放、也更为纷繁庞杂的时代新变,是时代新变的一个曲折的反映 。
那么,对于多元复合期的历史题材小说来说,它的个人化写作所带来的“众声喧哗” 到底是怎样表现的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形态或模式:
首先,是主旋律范畴的“革命纪实历史小说”。作者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往往 专注于中共党史、军史和共和国史,着重描写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领袖人物,题材下移 ,力图通过对那段刚逝去的创世纪辉煌历史以及那些创世纪伟人的回忆,以说服和引导 读者认同现实秩序和自我的社会位置。如石永言的《遵义会议纪实》,陈敦德的《毛泽 东、尼克松在1972》,权延赤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走下圣坛的周恩来》,毛毛 的《我的父亲邓小平》等。其次,是以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为主旨的“政治历史小说” 。如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王火的《战争和人》,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黎 汝清的《湘江之战》、《碧血黄沙》,邓贤的《大国之魂》、《日落东方》。特别是老 作家姚雪垠的《李自成》第四卷、第五卷,他用经典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思维方法 ,严格按照现实主义文学编码所应遵循的理性主义的逻辑规范,在近百万字的续作中, 深入地揭示了李自成这场农民运动盛极而衰的全过程。第三,取法西方异质文化的“现 代主义历史小说”。这些作品在一定的历史框架内,直接注入作者的现代思想和对历史 的主观理解,如女性意识、女权观念和弗洛伊德的泛性论等,以古喻今,反过来也以今 拟古,重新解释历史。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赵玫的《高阳公主》、《上官婉儿》,苏 童的《武则天》等。第四,固守本土民族之根的“文化历史小说”。如杨书案的《孔子 》,唐浩明的《曾国藩》,韩静霆的《孙武》,熊召政的《张居正》,王顺镇的《竹林 七贤》等,作者们希望通过文化溯源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用名人先哲的伦理精神和 人格魅力来教育后代,将人物史传的叙事巧妙地转化为现实民族本位文化的支撑和承传 。第五,与新历史主义密切有关的“新历史小说”。这些作者不再将匡时救世、重塑民 族魂魄作为自己不能承受之重的使命,而是袭用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的某些理论, 在随意、无奈乃至颓唐的叙事中,将历史由过去庄重严肃的阶级或阶级斗争层面转向世 俗卑琐的纯人性、纯生存、纯生命的层面。像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叶兆言的《半 边营》,格非的《敌人》,刘恒的《苍河白日梦》等作,都明显地体现了此种意向。第 六,模仿鲁迅《故事新编》的“新故事新编”。如李冯的《另一种声音》,朱文颖的《 重瞳》,张伟的《东巡》,张想的《孟姜女突围》等,用滑稽戏拟的超常叙述,将古今 的人事杂糅在一起,给人以有别于传统的怪诞美和新奇感。第七,崇尚娱乐消遣的“游 戏历史小说”。街头书摊上这类作品颇多,它们大多按照市民的趣味来编排历史,用商 业规则来突出其感官刺激功能,将历史题材小说变成纯文本的游戏操作。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上述诸种模式形态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并始终占据主导地 位的,还是对本土民族和传统文化进行阐扬的作品。尽管存在主义伴随商业物质主义价 值观念的发育堂而皇之地进入了社会文化,进入了历史小说文本尤其是年轻作者创作的 历史题材小说文本,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它并不能取代启蒙主义固有的理性原则和民 族情感。不仅不能取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主义与以民族理性为本位的启蒙主义 事实上是共存的。而且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标“新”立“后”的语境中,历史题材小说 在价值层面上,仍顽强地表现了古为今用“启蒙”的目的和功能,其现代性中注入了颇 浓的民族传统内涵。因此,这就造成了此一阶段历史题材小说思想艺术取向特别丰瞻也 特别矛盾复杂的特殊景观:一方面,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有关的非主流、非 理性、非功利的价值观,有关人类爱欲是历史文明“动力”的认知观,有关种族记忆、 集体无意识对民族心理结构的影响的文化观等等在这里大行其道,产生了深刻的辐射作 用;另一方面,与之对应的是,因上述两方面挑战激发的新保守主义反而形成了有利于 历史题材小说发展的背景。出于对西方殖民文化和文化殖民的警觉,也是为了使历史题 材小说现代性接上民族文化这根精神血脉,不仅是一般的精英作家,就是主流意识形态 也大力关心支持有关这方面的创作。
于是,我们看到,在多元复合期的今天,才有那么多的作家置身历史题材小说领域, 且文本中的民族内涵明显凸现,以至成为左右现代性的主导精神力量。特别是传统型历 史小说文体更是如此,对传统文化认同与批判兼得而以认同为主,已成为普遍的主题模 式,历史温情迅速弥漫开来。这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历史题材小说相比,不说是 截然不同,起码是大相径庭,且与国内兴起的“国学热”是一致的。此种情形,正好应 合了余英时有关文化“激进”、“保守”的基本判断:“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 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相反的,在一个要求安定的时代,‘保守’常常是思想的 主调”[4](P.216)。
收稿日期:2001-07-01
标签:历史小说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小说论文; 李自成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白门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