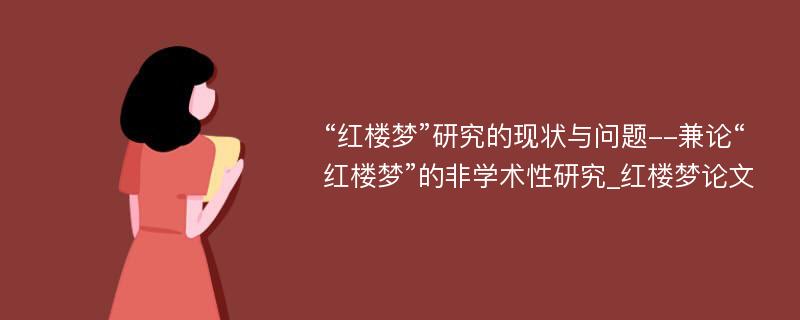
红楼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兼论红学非学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学论文,红楼梦论文,现状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06)03—0015—006
李贽是这样论述“童心”的:
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1]
对于好的文学作品,必须以似懂非懂之童心读之,不可刻板求真,过于求真“全不复有初矣”。读《红楼梦》亦如此,将《红楼梦》颠来倒去地玩弄,必失童心,《红楼梦》“全不复有初矣”!“初”(原著)是最有意义的,后人对《红楼梦》的说辞则不如原著价值高。“红学家”都承认《红楼梦》这部书好在没有说教,耐人琢磨,原书的这一优点实在珍贵。
我对“红学”评价不高就是因为它离不开附会。附会乃天下第一易事。以《红楼梦》之博大之精深之包容,评说它何需练字度句、搜根寻据?集长舍短自立一家,意随笔生不假错意,可矣。俗话云“《易》无达言”,套用这句话可以说“红(学)无准谱”,怎么说都有理。有人说东你说西,有人正说你反说,可矣,反正贾府门朝南或朝北无关宏旨,薛宝钗美于林黛玉或林黛玉美于薛宝钗也绝不会影响大局,永远没有标准答案。
红学中粗浅的附会,在考证曹雪芹创作动机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秘笈的《红楼梦》尚且让人糊涂,比“秘笈”更奥妙的创作动机自然更让人糊涂。所以各种动机说五花八门,无所不有。我们都知道,司马迁创作《史记》是为完成父志,但丁创作《神曲》是为写给心仪的姑娘——贝亚德。曹雪芹为谁创作?除去刨坟问尸,别无他法,因为曹雪芹没有像司马迁、但丁那样直率地吐露写作初衷。如果非要究其动机,在我看来,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2] 就是为了愚弄“红学家”的:一人藏物,百人难寻,我藏珠匿璧,让你们翻箱倒柜——这不是一种愚弄吗?曹雪芹造疑的水平实在超乎常人,诚如戚蓼生所说:
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两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不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两牍,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3]
左比不失其当,右附正合其宜——这正是曹雪芹的独具匠心之处,若是一歌一声,一手一牍,也就无需考证了。
也如霍国玲所说:
曹雪芹伟大,他的伟大不仅现在,即使是将来,也难于被人们全面认识。……顽石坠地,标志曹公出世;黛玉进京暗隐着贾府被抄;贾雨村复出,比附雍正帝登基……[4]
也如王蒙所说:
《红楼梦》本身就可以像生活一样成为某些作家进行再创作的素材,尽管成功的是这样少,但这种诱惑是永远不能消失的。……多么好的《红楼梦》啊,它会使那么多人包括我一辈子有事做。[5]
“成功的是这样少”说得不准确,应该说“没有成功的,而且也永远不会有成功的”。
也如俞平伯所言:
我尝谓这部书(指《红楼梦》——引用者)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糊涂。[6]
以上诸论,余独高俞公。“越研究便越觉糊涂”,妙,一语道破天机——所谓研究红楼梦,不过是使作品更“糊涂”些罢了,因为小说正是为“糊涂”读者的。在某种程度上,研究“红学”是在续写《红楼梦》,是“小说创作”之继续。这不正说明“红学”非学术吗?若以为从《红楼梦》中能够研究出正学来,除非重新定义“学”与“学术”。学术不会与小说混同,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
雪芹布香饵,后人争食之!现在,直接、间接吃红学饭的车载斗量,还不断有新人加入到“胡适之先生之流”(鲁迅语)中来,然而绝无一人成功。因为只有做有“效益”与“意义”的事情才可能成功。效益与意义是人类做事情的两个要旨,缺一不可。考证或变相考证一部小说究竟有什么效益与意义呢?寻它千百度却寻不到。“红学家”所作所为游离于社会之外,不干第三人事。不是吗?就在中国深入研究、考证《红楼梦》主题,为贾宝玉的“反雍正精神”高唱赞歌之时,电视媒体却反其道而行之,大演电视剧《雍正王朝》,为其歌功颂德,“红学家”与电视人各自为饭碗而忙碌,对互相撞车无暇顾忌。不由得想象出这样的一种场面:一部分人负责往地上贴小广告,另一部分人负责清扫,各干各的,形成完美“配合”。双方都在“为稻粱谋”,从社会效益上看,这样的事不干也罢。我并不一概反对这种“撞车”(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反对的是给予干这个行当的人以过高评价,让做着一般事情的人洋洋得意到以为自己在做一种伟业。
红学考证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
考证学(即考据学)本用来研究古书(至少数百年之前的书)的,一般采用以此书证彼书的方法,考察有破绽的地方,确定真伪。乾隆曾大力提倡考据学,鼓励优秀士大夫到这个领地耕耘,为的是转移学界视线,让士大夫注意力集中于鸡零狗碎,免得写出于朝廷不利的文字。清朝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律——本朝人不言本朝事!不言本朝事,可做的自然就剩下考证“前人事”了。最早的考据书可举钱大昕的《二十四史考异》、顾炎武的《日知录》。顾炎武有考据癖,每见古物必考之。由于顾炎武名大声响,在他带动下,中国的治学迅速朝考据学转向,以至于许多人认为“学问即考据,考据即学问”(此风至今未泯)。中国典籍有14万种,汉字书写起来又易出错误,考其万一,一辈子就吃喝不愁了。但是,古人终究不像今人这样惟利是图,虽然许多士大夫加入到考据行列,清朝考据书总计也不过百部,而我所收罗到的红学考据书(与长文)已逾三百种!看来说清朝最时兴考据已经有失偏颇了。
“红学家”不会不明白考证是怎么回事,所以近年“考据派”、“索引派”一直遭受“红学界”批评,“索引派”被讥讽为“笨伯猜谜,附会大家”。按照王国维的思路,研究分析《红楼梦》的内容、艺术风格与思想性,固然比考证、索引好,然而即使这样做,也不能谓之“红学”,更不该将其升格为“显学”。只要把小说当“学”对待,提笔必落言筌,想摆脱也难。因为凡“学”都是真实的,一部小说,无论怎样好,都是虚构的,不存在标准答案。
不是吗?“红学”正宗的研究绝大多数并不比考证派、索引派强多少,很难见到让人信服的论文。不是“红学家”水平不够高,实在是因为路子不对。“索引派”、“考据学”不好听,可是离开“索引”、“考据”又实在无文章可做。所以,那些坚决反对索引、考据的人只好翻来覆去地论证《红楼梦》主题精神,颠来倒去地分析贾宝玉、林黛玉的人物性格,不厌其烦地讨论曹雪芹的创作手法。重复来重复去,老调被传为滥调子。
冯其庸一向正说《红楼梦》,然而其说词亦经不住推敲,论点一捅即破,如以下一段话:
《红楼梦》是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思想和艺术的高度综合和结晶,从《红楼梦》的时代来说,这部书既是对传统优秀文化思想艺术的继承,又是对它的飞跃和发展。[7]190
《红楼梦》中确实蕴含传统文化,但实在说不上“飞跃”和“发展”,如果中国的诗歌飞跃成《葬花词》,我宁愿唐诗宋词不再“发展”了,如果读书人不再读四书五经,而改读《西厢记》,我宁可不读书了,如果贾宝玉成为士大夫之楷模,我宁愿种地而不当文人了……说实在话,与唐诗宋词相比,《红楼梦》中的诗词充其量只能算是三流的(何况曹雪芹之诗并非纯粹创作,借鉴了古诗,尤其借鉴了杜诗)。至于思想,《红楼梦》恰与儒家正统思想反对,《红楼梦》中含有佛家、道家与一些新潮思想(如追求自由),就是难以找到“中国传统”的正统思想。《红楼梦》作者对中国传统思想基本采取否定态度,将经书讥讽为“劳什子”,怎么能说“《红楼梦》是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思想和艺术的高度综合和结晶”呢?!这一论断太离谱了。
还有这样一个论断:
《红楼梦》这部书,不仅是对两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社会(包括它的意识形态)的一个总批判,而且它还闪耀着新时代的一线曙光,它既是一曲行将没落的封建社会的挽歌,也是一首必将到来的新时代的晨曲。[7]62
《红楼梦》所处的时代与“封建社会”风马牛不相及。中国的封建制早在公元前221年就寿终正寝了。 就算“封建社会”指的是秦始皇之后的大一统皇权社会,《红楼梦》又在何处对其“意识形态”进行了“总批判”?如前所述,作者确实对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持否定态度,但作者没有能力对其进行“总批判”,“总批判者”的头衔应该戴在胡适头上,胡适有“总批判”的能力,曹雪芹不具备这个能力。如果曹雪芹做了“总批判”,就没有必要让胡适来发动“文学革命”了。
有人认为《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挽歌。此说更离谱,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死亡两千年了,那里有死两千年才为死者写挽歌的?!
周汝昌在许多问题上与冯其庸观点不一致,但在《红楼梦》代表中华文化传统上却高度一致:
每当与西方或外国访问者晤谈的时候,我总是对他们说:如果要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特色,最好的——既最有趣味又最为便捷的办法就是去通读《红楼梦》……《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文化小说。[8]
“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特色”就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传统(其他民族没有形成如此悠久的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化传统)。《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却都是儒家文化的叛逆,我读《红楼梦》,怎么也读不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特色”。如果改成以下表述还讲得通:读《红楼梦》可以了解佛家文化与自由主义思潮的萌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红楼梦与人生”是红学家热衷的话题。有人分析作品之后总结出人生的三条道路:一条以贾雨村为代表(科举之路),一条以贾赦、贾珍、贾琏为代表(袭祖恩荫之路),还有一条以贾宝玉、林黛玉为代表(有人说是自由之路,有人说是游手好闲之路),多数“红学家”断定,只有第三条道路才是人生正途。读来绝倒,我宁愿当芸芸众生而不愿意作贾宝玉,因为我怎么也爱不起来这个专爱惹逗裙钗的人。被“红学家”看好的第三条路恰恰最要不得。第一条路有缺失,但那是正途。评家皆云贾宝玉是才子,读《红楼梦》却不知道贾宝玉才从何来,莫非厮守女子可以成才?贾宝玉反对八股固然含有“反叛精神”,然而做八股也强似成天与女人厮混。贾宝玉反对文死谏、武死战,他哪里知道,文不死谏,武不死战,他哪里能优哉游哉地吃女人胭脂?有人将贾宝玉与李贽、顾炎武、戴震同论,这是只知其表、未见其里。李贽、顾炎武、戴震皆反传统,这没有问题,但李贽、顾炎武、戴震皆立于传统之内反传统,他们一边读书、写文章,一边反传统;贾宝玉则不读圣贤书,不写道德文章,徒反传统而已。中国人若个个都是贾宝玉,文化传统早就断香火,也就用不着反了。
凡歪说歪理必然愈演愈烈。焦大醉酒之后骂出“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博得许多“红学家”喝彩,以为焦大喊出了豪言壮语,殊不知这句“名言”现在已经成为黑道上盗贼的习惯用语,这个口号是盗贼行凶时的壮胆剂。这个帮助恶人做坏事的口号不知断送了多少无辜的性命!在“红学家”那里,这句话却每每得到称赞!
类似的“胡批”数不胜数,比如有人对“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的诗句喜爱有嘉,捧为“向往理想世界”之绝唱,实际上这句禅诗表达的是人生短促无常。佛家认为: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复如电,应作如是观。[9]
此诗告诉我们的是:人生短促无常。葬花词也是表达此意,只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
《红楼梦》后四十回一向是评家喜欢议论的话题。张爱玲主张删掉后四十回,任其残缺,这样就可以避免“无日无光,百样无味”了。周汝昌同意此说,他把后四十回批评得一无是处。同是“红学家”,冯其庸认为后四十回还可以。对于后四十回,喜欢的读,不喜欢的不读就是了,实在想不通有什么可讨论的。说高鹗狗尾续貂的为什么不用自己的“狐尾”“续一续“貂”,谅无此能。
对好作品评头论足是必要的,如若总是“假语村言”、“贾假甄真”那一套,久了,令人生厌。
《红楼梦》已经评了一二百年,话差不多已说尽,继续评下去断难再出彩章。举两例前人点评,即可断定后“红学家”超过前人否。
其一:
真可拍案叫绝,足见其以兰为心,以玉为骨,以莲为质,以冰为神,真真绝倒天下之裙钗矣。[10]
其二:
林颦卿者,外家寄食,茕茕孑身,园居潇湘馆内,花处姊妹丛中,宝钗有其艳而不能得其娇,探春有其香而不得其清,湘云有其俊而不得其韵;宝琴有其美而不得其幽,香菱有其幽而不得其高,凤姐有其丽而不得其雅。询仙草为前身,群芳所低首者也。[7]2
笔力简括,蕴义怀文。读这样如诗如画之妙论,我实在不忍心节外生枝妄言宝钗,论凤姐,说宝琴,道香菱,不想以我之庸论覆盖前人之妙言。
近年社会上刮起一股歪风,肆意夸大《红楼梦》研究的作用,欲将“红学”升格为显学,让“红学”内涵越来越深,外延越来越广,纵无底线,横无际崖,茫茫荡荡,无所不容。甚至有权威将“红学”提升至“国学”,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为“三大显学”,说甲骨学是研究上古历史的,敦煌学是研究中古历史的,“红学”是研究近代历史的云。真是越扯越远了。请问:《红楼梦》是历史书吗?“红学”研究中确实有时涉及历史,然而一旦涉及历史,必然远离作品从而脱去红色。事实正如此,一位“专家”将《红楼梦》与《圣经》并列。还有一位专家将《红楼梦》与《周易》并提:在汉语语言文化历史上,我认为有两本书是天书,一本是《周易》,一本是《红楼梦》。[11] 将《红楼梦》与《周易》并提,与把体育与哲学归于同类有何差别?
红学确实很热,但那完全是人为造势的结果。《红楼学刊》1979年创办,一年四期,每期约25万字,至今已出一百多期,约有近3000万字的“研究成果”。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单门“学科”研究成果之最,只知道这三千万字成果,不到一天可以读完,因为重复的实在太多。
为什么形成“红学热”是“红学家”热衷的又一个话题,真是自爱得可以。一位“红学家”解释说:
“红学”为什么热?热源在哪里?……就是因为《红楼梦》这部作品丰富、深邃、精妙,还带几分神秘。说得稍微复杂一点,也可以这样表述,是因为这部小说作品的原创性,思想意蕴的多义性,成书过程的复杂性,文学思想的开放性。[12]
明明“红学热”是人为加温造成的,偏偏将其归于作品本身。有一本“红学专著”第一章标题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避难所”[13],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莫非中国知识分子吃女人胭脂心灵就找到避难所了?搞不懂小说何以能如此神通广大。经、史、掌故、义理、词章被称为传统“五学”,虽然小说与掌故沾点边,终究不是独立一项,正统士大夫从不以治小说为务。“红学热”绝不仅仅是因为《红楼梦》作品伟大,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比《红楼梦》伟大的不下20部,除去《论语》都没有成“学”,惟《红楼梦》成为“显学”,原因必须从更深处寻找。一切都是“现代性”在搅局。现代性迫使中国人的审美兴趣发生巨大转变,一言以蔽之就是由雅变俗。高雅的诗词歌赋被低俗的小说取代。审美载体由美文转移到小说。俗文学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小说中的佼佼者《红楼梦》自然成为俗文人的追逐对象,他们用《红楼梦》来附和现代性,用小说来填补空虚的心灵,为此不惜将《红楼梦》“研究”请上学术殿堂的高阶,将其“金玉其外”,造成学术繁荣的假象,一方面遮掩无聊文人的偃蹇狭陋与喜新厌旧的浮躁心理,另一方面无需劳神,通过炒《红楼梦》冷饭而将自己留名于中国文学史。算盘打得虽好,却坑害了不明就里的读者,把他们引向歧途。从胡适提出“科学的考证”至今已80年,“红学”早已不“红”(不再与《红楼梦》有任何关联),该收场了!
《红楼梦》是中国优秀古典章回小说,作者的想象力与表达力都是异乎寻常的,对此我丝毫不否认。我想强调的是,《红楼梦》仅仅是一部小说,小说是可以评的,但必须把它当小说评,而不能当历史评、当自传评,更不能把评小说当作单独的一门学问看待。
有人认为,英国有“莎学”(莎学也很热,《莎士比亚大典》已再版40多次),中国为什么不能有“红学”?
英国可以有“莎学”,中国不该有“红学”。理由有三:
其一,英语产生于14世纪,只有700来年历史, 不存在类似汉语文言文那样的能够久传不失其意的书面语,英文随口语呈周期性变化,莎士比亚死后不到百年,其作品已难为后人理解,所以需要后人整理之,研究之,诠释之,以保存其原意。后人研究莎士比亚,不是为了附会,而是为了让其作品流传下去。《莎士比亚大典》重印40多次就是为此目的。“莎学”从来没有钻进考证索引与重复评论的死胡同,也没有自诩为“显学”。
其二,莎士比亚是英国第一文豪,适当赞美甚至神化其作品是可以理解的。曹雪芹不同。他在中国文学史上进不了前十名,过度赞美甚至神化他的作品令人费解(曹雪芹也是相当伟大的文学家,只是因为中国古典文学太辉煌了,他才进入不了文学宝塔塔尖)。专门为一名排名十多位的文学家建立殿堂,而置那么多文学成就高于他的文学家于不顾,实为不妥。
其三,英国文学史比较简单,以小说类作品为主(莎士比亚戏剧应算作小说),谁的小说写得好谁就可以坐第一把交椅。中国文学史比较复杂,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打文体。按照传统审美标准,小说根本上不了台盘。之所以20世纪20年代《红楼梦》这条鲤鱼独跳龙门,是因为那时中国的崇洋媚外风已起,胡适借助“红学”让西风更进一格,益使风力遒上。胡适的目的基本达到了,随着“红学”走红,诗词歌赋已渐渐被国人忘记。如果中国文人的注意力尽被小说(无论这部小说怎样好)牵扯,无须百年,中国古典文学将彻底断其统续(无人会写诗词与韵文),那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啊!
中国文学宝库中,有无数优秀作品值得华夏后裔吟诵之,评论之,继承之:《诗经》诗之发轫,后振其步;《庄子》意态风神,不知何在;《楚辞》花草情景,种种具备;《左传》滔滔莽莽,点笔立就;《史记》文史谐鬯,诙诡不羁;《三国志》轻重缓急,小笔望尘;《古诗十九首》浑朴莽苍,暗合前古;《曹子健集》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陶渊明文集》丽藏于淡,采蕴于拙;《文选》广征博引,淹贯古今;《文心雕龙》篇篇高妙,句句神工;《古文观止》博采散韵,叹为观止;《全唐诗》吟写性灵,流连光景;《八大家古文选》字惊文曲,力敌造化;《聊斋志异》化狐为姬,化鬼为人;《红楼梦》野马尘埃,任人遐想……哪一个不是国宝,哪一个不让洋人羡慕?何必一棵树吊死,贵其一而贱其余,强分伯仲叔季而徒心血耗乎?
本文意不在否定《红楼梦》,也不在否定《红楼梦》研究者。《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王国维、冯其庸、周汝昌、王蒙等是文学功底深厚的文学评论家。本文意在说明:“红学”一词可以用,但它不是学术,《红楼梦》研究应纳入到“文学评论”之中;“红学”不是显学,也不应该成为显学。
学者李贽曾批评道学家“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又与焦弱侯》)。李氏所言,实为笃论。不管口谈什么,“穿窬”,必然原形毕露。
收稿日期:2006—03—15
标签:红楼梦论文; 贾宝玉论文; 曹雪芹论文; 红学家论文; 红楼梦评论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封建社会论文; 顾炎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