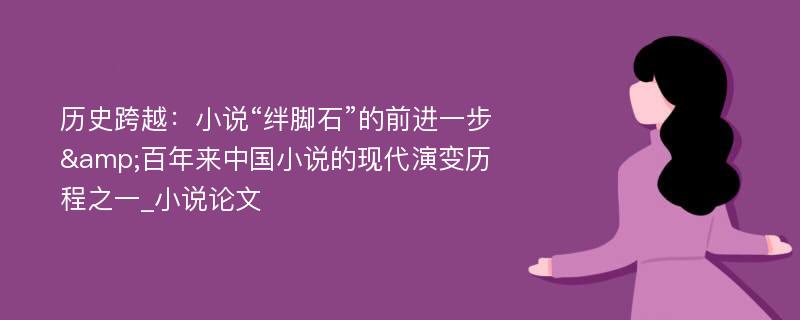
历史跨越:长篇小说“蹒跚”迈步——近百年中国长篇小说现代演进过程探讨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小说论文,中国论文,过程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动的世纪。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于结束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建立共和体制的反复迂回和政治动荡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更加推动了社会的科学、民主氛围的出现。这是中国历史的一次重要跨越。 在这样重大的历史变动中,作为一种特殊文学体裁的长篇小说,并没有像诗歌和短篇小说那样,随着历史闸门的打开,就立刻倾泻而出,而是经过了一段的回流、一段沉寂过程才“蹒跚”起步的。所以我们的研究也就不能用简单的办法,仅以“辛亥”为界、或以“五四”为界来左右我们观察文学的眼光。 一、辛亥前后:长篇小说创作“哀情”的泛起 进入20世纪后,在辛亥革命风潮前后的若干年间,长篇小说领域大量涌现的并非是配合革命呼风唤雨的政治小说,而是一批以描写“哀情”而风行一时的作品,它们在当时动荡的社会中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批长篇小说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民国初年先后在《民权报》连载的徐枕亚的《玉梨魂》(1913年9月出版单行本)、吴双热的《孽冤镜》(1914年2月出版单行本)、李定夷的《霣玉怨》(1914年7月出版单行本)等,更值得注意的还有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1912年5月至8月在《太平洋报》上连载)和漱六山房(张春帆)的《九尾龟》(1906年在上海的《点石斋画报》上连载)等。这批长篇小说,在以往一些现代文学史、小说史中,往往把它们归入“鸳鸯蝴蝶派”而受到笼统的批判,或因它们运用文言或骈文写作而被排斥于“现代文学”之外。但是,作为长篇小说演进的研究,对这个时期所出现的这种创作现象,却是需要作认真分析的。 应该怎样来认识这样一种现象?为什么在辛亥革命前的晚清末年,长篇小说创作虽然也有言情,但大量出现的却是对社会种种腐败现象发出“谴责”之声,可是一场划时代的革命爆发后,却没有带来创作领域格调高昂的革命音响,反而泛现一片“哀情”? 在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中,已经注意对这种复杂现象进行比较客观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两方面的看法:一是从文学功能的角度分析,认为自变革维新以来,小说被提到社会生活的重要位置,被要求担负起开发民智、改革政治的重任,可到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封建帝制的倒塌,共和民国的建立,一般认为,革命任务已经完成,小说还是应该回到自身的功能,抒发个人情感,作“遣情之具”,而不必去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了。因为他们看到了小说的政治化,并不能使腐败的社会起死回生,民国初年,小说家、翻译家包天笑也就是这么慨叹的:“则曰群治腐败之病根,将借小说以药之,适盖有起死回生之功也;而孰知憔悴萎病,惨死堕落,乃益加甚焉!”“以为小说之力至伟,莫可伦比,乃其结果至于如此,宁不可悲也耶?”①研究者认为,这种言论,正是代表了当时在实践的挫折中对小说社会功能所产生的怀疑。另有一些研究者则是从社会思潮变化的角度来分析,认为辛亥革命高潮一过,许多知识分子已预感到失败的阴影,“民国”的名存实亡,带来的是一种欢欣后的极度失望情绪,加之“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称帝,专制骄横,更使知识者压抑难熬,因此便以“哀情”曲折地宣泄政治上失意的情感。南社成员、曾主持过《民权报》笔政的刘铁冷,在袁氏专制下《民权报》被迫关门后就这样自白:“近人号余等为鸳鸯蝴蝶派……然在袁氏淫威之下,欲哭不得,欲笑不能,于万分烦闷中,借此以泄其烦,以遣其愁,当亦为世人所许,不敢侈言倡导也”②。 无论是认为对小说功能的反拨,还是认为在政治失意后情绪的曲折转移,这些见解,都触及到“哀情小说”在民初泛起的一些内在原因。 还应该看到的是,民国初年像徐枕亚、吴双热、李涵秋、李定夷、刘铁冷、蒋箸超等一批小说家,他们的立场是反对封建帝制而拥护共和的,我们不能像当年某些评论者那样,笼统地斥他们为“封建余孽”或“小市民”。这些小说家对袁世凯的阴谋窃国所表现的不满,在当时他们所在的“踔厉风发”的《民权报》上,就有集中体现,他们敢于首先揭露袁的阴谋行径,据经事者郑远梅的回忆:“袁氏帝制之野心已暴露,于是(《民权报》)攻击更加激烈……宋父被刺,袁氏与赵秉钧洪述祖往还手札,种种铁证,由《民权报》首先铸版披露,阴谋诡计,遂大白于天下”③。这些行动,使“袁氏忌之益甚”,致使《民权报》受到袁氏的专制迫害而倒闭。在这种令人失望的政治压抑中,这些小说家们转向“哀情”写作,避开政治锋芒,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重要的还是要体味他们的作品。在这个时期最为风靡的哀情小说中,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们不仅写男女之间情感的缠绵悱恻,更写他们为爱情的可望不可得而殉情。像《玉梨魂》写一怀才不遇的乡村家庭教师何梦霞与学生的寡母白梨影之间产生炽热的爱情,但双方都为当时无处不在的森严礼教所束缚,只能以传递诗词以诉心曲,却不敢越雷池半步。白梨影为使何梦霞留在身边,宁愿忍受感情的折磨,撮合小姑与何的婚姻。最后,梨影郁郁而死,小姑则在自怨自艾中死去,而何梦霞也参军而战死沙场。又像《孽冤镜》,它写姑苏一位在婚姻上受过挫折的世家公子王可青,在常熟泛舟遇见一美貌女子薛环娘,经朋友联络,遂订终身。但可青父亲又强行为他订了一位大官之女为妻,可青反抗无效,托人告知环娘,环娘母女得知,双双呕血而死。王可青婚后又感情不和,最后精神错乱而死。还有像《霣玉怨》,情节线索更为复杂,所写两对恋人要么“不治身亡”,要么“留下青丝一缕,不知所踪”。总之,作品的结局,都选择了决绝性的死亡,看来这并非是偶然的。但在当年新文化潮头开始跃动的时候,却被一些激进的评论家鄙薄得无所是处,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们斥之为“封建余孽”,甚至把他们的作品鄙之为“排泄物”。今天我们客观地来甄别一下这些作品,可以实事求是地说,作家们写这样的小说,不完全是无病呻吟,而是有生活的根据甚至是自身的经历和体验的(像徐枕亚的《玉梨魂》就有他个人遭遇的影子),所以,他们写的缠绵爱情的悲剧,写的为情而殉死的凄凉结局,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对封建礼教束缚无言的怨恨和无奈的控诉。这些作品在当时获得如此广泛读者的狂热追逐,能销行三十多版数十万册(如《玉梨魂》),恐怕也并不完全是为了无所事事的消闲,里面确实有一些与当时社会情绪合拍之处:对旧礼教压抑人的情感的不满,对革命未能给人以真正身心自由的悲切。这些小说无一不选择了死亡,看来也不完全是为了赚取读者廉价的眼泪,而是时代一种绝望情绪的流露。当然,一个时代的文坛如果全部被这种“哀情”所充斥,也不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后来这类小说中无数低劣的产品泛滥成灾,就统统否定他们存在的合理性。 这里我还要关注一部更重要的作品,就是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过去在新文学史上,由于它的文言写作,由于它与鸳鸯蝴蝶派的某些牵连,由于它所抒发的哀情不为日益兴起的革命文学所相容,所以它基本上难以在新文学史上占有什么位置。但我认为,这部小说在个人情感袒露中所体现的真切性、极致性,在长篇小说文体创造上所体现的个人性、开创性,对中国长篇小说的现代演进有着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 苏曼殊(1884-1918)早年曾参加过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日本东京的革命活动,思想十分激进。在他与陈独秀合作翻译法国作家雨果的《惨世界》(即《悲惨世界》)中,为了表现对旧制度的激愤情绪,可以不顾翻译应遵循的原则,抛开原著的后半部分,另作发挥,杜撰一个思想激进的理想人物,不仅抨击封建儒教,讨伐贪官污吏,而且要“大起义兵”,将那班为非作歹的满朝文武“拣那黑心肝的,杀个干净”。由此可见苏曼殊在早年思想的激进。但当他的革命行为受到家人的阻拦,又看到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依然黑暗,不禁又黯然神伤,遁入空门。他的《断鸿零雁记》(发表于1912年5月12日—8月17日《太平洋报》)就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写成的。 小说有极强的自传性质,采用的是主人公三郎第一人称“余”的叙述,三郎自幼失去母爱,未婚妻雪梅之父见其家境式微,立意悔婚,而雪梅却不肯负约。如此遭际,三郎精神落寞,决意皈依佛陀。在他三戒足俱之日,下乡化米,偶然遇见幼时乳母,得知自己生母为日本人,早已回国。为此,三郎毅然东渡寻母。后来果然在日本与生母相见,充分享受天伦之情。母亲要将其表姐静子许配给三郎,这使已皈命佛门的儿子在“出家”与“合婚”之间,发生激烈的情感冲突。三郎最终还是“力遏情澜”离开日本回国,在灵隐寺重归佛门。当他得悉雪梅为抗婚而亡,心灵受到强烈震动,遂回到乡间寻雪梅墓,但“踏遍北邙三十里”,却“不知何处葬卿卿”。 这样一个十分凄美、曲折的故事,被作者用他整个心灵和全部情感叙述得荡气回肠,催人泪下。小说所倾诉的“哀情”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糅杂式的。那种自幼失去母子亲情之痛,长大后又遭遇悔婚之痛,遁入佛门后又面对“力遏情澜”的切肤之痛,最后寻雪梅之墓未果的怅惘空漠之痛,都被作者扭结在一起而显得极强的感情力度。在这样的重重伤痛中展示的矛盾是多方面的,婚姻与金钱权力的矛盾、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佛禅与情爱的矛盾等等的复杂交错,充分袒露了动荡时代中一个精神无所皈依的心灵。 苏曼殊在《断鸿零雁记》发表后的几年里,陆续出版了《绛沙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天涯红泪记》(未完稿)等小说,它们由于充盈着浓郁的浪漫气息和青春苦闷,而广受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欢迎。有评论者认为,他的创作直接开启了“鸳鸯蝴蝶派“的先河。当时周作人也说:苏曼殊在“鸳鸯蝴蝶派”里“可以当得起大师的名号。却如儒教里的孔仲尼,给他的门徒们带累了,容易被埋没了它的本色”④这种看法有其准确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理的一面。所谓准确的,是他承认了苏曼殊确实是当时哀情小说创作潮流中的佼佼者,而所谓不合理的是,鸳鸯蝴蝶派本身并不是一个文学“联盟”,它只不过是在当时社会情绪支配下应运而生的一股文学潮流,他们的创作在作者与作者之间,在作者与读者之间,以及在创作与商业性运作之间,都是一种互动关系,难以说清是谁影响谁,谁又“带累”谁。苏曼殊《断鸿零雁记》是自我命运的有感而发,徐枕亚的《玉梨魂》其实也是自身情感经历的一种倾诉,所以我更倾向于把这股创作潮流的出现,看作是小说家们对当时社会情绪的一种感应。我们不必为了肯定某位作家而想方设法地“斩断”他与“鸳鸯蝴蝶派”的牵连,也不应因这位作家被人归入“鸳鸯蝴蝶派”中而对他的创作笼统地贬低,而是应该以具体的作家作品为依据分别其良莠。 这个时期哀情小说中的一些佳作,除了以情感的哀切宣泄了对不合理制度和压抑人的情感的旧礼教的怨恨外,在长篇小说艺术上也有许多为晚清小说所不及之处。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在长篇小说艺术上的创新尤为突出。 首先在运用第一人称叙事时真正实现了人称的“自我化”和叙事的“主观性”。 它不同于晚清小说那样,通过一个设计的人物,(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九死一生”)由这个人物来进行叙述,这样的叙述者叙述的主要是客观所“看到的事”、“他人的事”,而且基本上没有个人感情的介入。而《断鸿零雁记》中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余”(即白话文的“我”)所叙述的主要是自己“心中的事”、“亲历的事”,带有极强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性。因此,有研究者认为:苏曼殊的小说是“预示浪漫抒情小说在‘五四’时期获得长足发展的一个先驱”⑤这个评价是十分准确的。 其次,叙事的自我化和主观性特点,也带来了小说结构上与传统小说不同的新变化。它的故事叙述完全打破了线性式的传统,而是随个人情感思绪的变化起伏而展开。小说一开始,叙事主人公已经“入山求戒”,在“百静之中”“隐约微闻慈母唤我之声”,在这种情感驱动下,通过奇遇乳母,才倒叙了主人公的身世;在为筹资东渡寻母而焦虑时,又倒叙了未婚妻雪梅的家庭以及他们婚约之恶变。情节的叙写,受主人公情绪的牵制。在东瀛母子相见后叙述与静子的情感邂逅,也是在一种矛盾心绪的撞击中迂回地展开。这使整部小说结构显得灵动有致,舒张自如。 第三,小说在心理描写上也处理得十分出色。尽管作者使用的是文言,在叙事抒情上有所束缚,但文言的言简意赅,运用得精当也能起点睛之妙。作者的心理描写不是纯客观的,而是有着强烈的情感依托,是一种内心呼唤式的心理坦露。如描写与静子初见,“余不敢回眸正视,惟心绪飘然,如风吹落叶,不知何所止”;又如描写即将随母离开静子家时,通过对景物的感应来写心理:“一时雁影横空,蝉声四起”,“盈眸廓落,沦漪泠然”,“但见宿叶脱柯,萧萧下坠,心始耸然知清秋亦垂尽矣。遂不觉中怀惘惘,一若重愁在抱”。特别是对主人公在情爱与佛门之间、在对静子的怀恋与对雪梅的负疚之间矛盾心境的描写,更是心的撕裂、心的长啸:“此时正余心与雪花交飞于茫茫天海之间也”,“苍天,苍天!吾胡尽日怀抱百忧于中,不能自弭耶?”把一种陷于情感煎熬而又无法自拔的复杂心绪,写得令人痛切无比。在小说最后寻找雪梅墓未果,主人公心如木石,人归静室,但情感的波浪,仍难以遏止,“余弥天幽恨,正未有艾也”,这些心理呈示,真可谓“万叠如云”,情魂尽致,绵绵无绝。 《断鸿零雁记》在艺术上所呈现的这些特点,它的叙述情感性特征并由此而形成情节结构的灵动与开放,形成的主观性心理呈示等等,都在表明它已向现代小说形态迈开了重要的一步。加上它作品所流露的那种孤独无援的空漠心境,那种情感困顿精神无所归依的怅惘情怀,很容易与跋涉在精神苦旅上的现代人获得心灵的共鸣。过去在研究中常会因它使用的是文言不是白话,而否认了它的现代意义,但我觉得,今天我们在探讨小说创作的内在素质时,在承认它语言使用的局限的同时,更应该在其内在情感、艺术思维等因素中发掘它所蕴含的现代素质。事实上,苏曼殊的古典文化修养已经渗透进不少西方浪漫主义的情感色彩,他对拜伦、雪莱、莎士比亚创作的迷恋,被他们著作的神韵深深感染,从而化入自己创作血脉中。《断鸿零雁记》的出现,使我们获得了许多在阅读古代传统小说、甚至阅读晚清小说所没有的新感受,也使我们真切地感到,一部穿着古典语言外衣的小说,如何为中国现代小说的成长,拉开了序幕。这真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现象。 二、“五四”狂飙:长篇小说新文化视野的开启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意义,不仅已有无数文字所记载,更为近百年的历史实践所证明。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并不意味着支撑这一制度的精神大厦立刻倒塌。在“共和”体制下,专制继续横行,政治权力的无休止混战,内政外交的混乱、失败,这些现状,终于激起一批知识精英和千万民众奋身而起,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发出了要求科学、民主的强烈呼声。“科学”与“民主”从此理直气壮地进入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并且成了中国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们前赴后继奋斗的目标。 不管我们今天如何来评价“五四”这种历史行动,却不能否认,它是以不可阻挡的凌厉之势促使了民族理性精神的觉醒,促使国人作为“人”的独立意识的觉醒——哪怕还仅仅是初步的觉醒。而当这种理性精神和独立意识渗透进文学中,就自然酿造了文学的新质和新貌。 在小说领域,与这个文化潮头相呼应的,首先是短篇小说,鲁迅发表在1917年的、被誉为新文学开篇之作的《狂人日记》,就是代表。但是,作为现代文学中的长篇小说创作,却与这个沸腾、喧嚣的年代很不相称,直到“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三个年头,即1922年,才开始有被认为属“新文学”的长篇小说问世。 据一个较精密的统计⑥,从1922年到1927年的五、六年时间,发表和出版的长篇小说只有10部左右。1922年出现了两部,即: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1922年2月)和王统照的《一叶》(1922年10月)。接着有张闻天的《旅途》(1924)、杨振声的《玉君》(1925)、张资平的《飞絮》(1926)、《苔莉》(1927)、老舍的《老张的哲学》(1926)、《赵子曰》(1927)等。这些作品,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后,长篇小说的最早收获。 无疑,这是一批相当稚嫩的作品,特别是作为长篇小说来看,作家们虽然运用的不再是文言或半文不白的语言,但却几乎很少具有明确的长篇小说文体意识,许多作品就像是中篇的拉长,长者不过十四五万字,最短的则只有五万字(《玉君》)。情节设计和小说结构也无多大创意,只能说它们一律彻底抛弃了章回体而采用了自由书写,从这角度来说,作为现代长篇小说的草创,它步履的蹒跚,艺术上的“无所适从”,都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一个人刚刚挣脱千年枷锁,四肢还不知该如何伸展一样。 但是,也正因为它们是出现在“五四”狂飙后的新创,我们还是有必要仔细探讨一下它所自觉或不自觉呈现的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新素质。 强烈显示生命的独立意志,是五四后最早出现的这批长篇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些小说,从一般情节来看大体离不开爱情故事,但从其作品的深层意蕴来看,它与以往许多爱情书写的不同在于,它所体现的是一种生命的独立意志。《一叶》的主人公恋爱不就,促使他探讨人生问题:为何生命永久地如一片树叶那样飘坠在地上?他希望用爱来弥补人生的缺陷,尽管是虚无的,但却体现了一种不愿让生命像落叶飘零的人生思考。《冲积期的化石》主人公于辛亥革命后留学日本,他一方面思念亲人,感受男女分离的郁闷,对废学嬉戏的不满;而另一方面自己却在酒色中沉迷无法自拔,表现出对生命放纵的痛苦。而更明朗表现这样一种生命独立意志的,是杨振声的《玉君》和张闻天的《旅途》。《玉君》所写的是一个比较奇特的情感故事:杜平夫赴法国留学,托友人一存照顾其恋人玉君。玉君与妹妹菱君在一存照料下,相处甚好。而玉君的父亲却要将她许配给军阀之子黄培和,玉君以死相抗。一存为她选择了两条路:一是到渔岛上教书,一是筹款到法国留学。可是杜平夫回来却责备玉君与一存相爱,玉君斥杜爱的是皮肤而不是灵魂。最后一存变卖家产,资助玉君姐妹赴法留学,开始独立人生。这里所写的自然有男女感情纠葛,但却不是庸俗的三角恋,它突出的是人的独立意志,玉君的抗婚以及对猜疑她的杜平夫的斥责,无疑是要保持独立的灵魂,而一存对她的帮助,也是为了支持她获得独立生存能力,能够成为自己生命意志的个体。尽管小说人物身上有较明显的理想化,但它所体现的新时代色彩不是浮浅的,而是触及到人应成为独立个体这一作为新时代的本质特征。鲁迅当年认为这部小说的作者塑造的人物“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⑦,这种责备显然是一种偏见。《旅途》在表现对自由生命的追求中,写得更悲壮。主人公王钧凯在美国留学,在国内的恋人蕴青对他精神上无限依恋,但为孝顺母亲,从母命而与并不相爱的人结合。王在颓丧中受到深爱他的两位外国女子安娜和马格莱德影响,她们是个开放的女性,追求“力的自然,自然的力”,为追求自由生命而相继死去,由此而激起王的革命热情,王回国也在与军阀和外国联军的战斗中献出了生命。 “五四”后最早出现的这批小说,对悲剧的揭示不仅触及封建专制和旧礼教,也开始对人性弱点的关注,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这些作品大多数写的也是爱情悲剧,描写了婚姻不能自主的痛苦,反映了作者明确的反封建意识。与此同时,作者也开始注意到对人自身的思考,注意到人性弱点带来的悲剧因素。这一特点,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这是长篇小说体现新的文化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觉醒,不仅是对人作为生命独立个体的确认,也开始理性地审视自身。张资平最早的几篇爱情小说就涉及了这样问题。《飞絮》写三角恋爱,教授要将女儿许配给洋博士,而女儿却热恋一位文学青年,最后酿成悲剧,其原因除了父母之命外,还与女主人公性格的好猜疑有关。《苔莉》写两性的苦闷心理,写婚外恋,而悲剧的原因也与主人公缺乏自主意识和彻底改变命运的勇气有关。《最后的幸福》的主人公虽有追求幸福的勇气,但又滑进了性解放的歧途,悲剧也是难免的。所以我以为张资平当时的创作,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不是它写了“三角恋爱”,而是他开始思考到、触及到人性弱点这一命题,这不但对于晚清小说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跨越意义,就以五四时期的创作来衡量,也是有特殊价值的。 双重文化视野开始建立,是“五四”后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的又一重要特点。这批长篇小说的作者,大部分都有过留洋的外国生活经验,所以他们在创作中,特别是在观照本土的生活现实时,自然会多了一重视角,多了一种参照。在这方面,它与晚清小说显示了鲜明的不同点。晚清小说虽然可以写到境外生活场景,可以写到在中国的洋人、洋货,但作者的立场要么是猎奇式的展示,要么就是用墨守传统的眼光对它进行讥讽,基本没有在其参照下对自己文化的反观意识、自审意识。而这时出现的像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以及稍后发表的《二马》,都显示了作者在一种新的文化视野参照下,对“国民劣根性”的揭示与批判。“老张”的哲学是“钱本位而三位一体”,集宗教三种:回教、耶稣、佛教;集职业三种:兵、学、商;集言语三种:官话、奉天话、山东话。而以百家姓之首的“赵”为姓、以《论语》第一章开头二字“子曰”为名的“赵子曰”,则是个在大学里学过哲、文、化、植、社等学科,要成为“无所不有的总博士”。充满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人物,无论是“办学”还是“革命”,都一事无成。当然,作者以一种英国士绅居高临下的态度来着笔,使小说的基调留下缺陷。但作品以戏谑的笔法来描写这些人物的“劣质”,实际上也寄予了作者对一种自重、自强的民族意识的呼唤。在《二马》中这种双重文化视角更明显。它把小说的背景从《赵子曰》的北京公寓拉到伦敦的民宅。马则仁带着儿子马威来到英国伦敦,接手哥哥的生意,经人介绍,租住在房东温都太太母女家。小说就是在这对中国父子与英国母女之间,展开了中西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对比,表现了中国国民的封闭、陈腐、愚钝的劣根性,同时也写出了英国人的傲慢与偏见和对中国人的歧视,在揭露“国民性”中保持着爱国主义的基调。 从上述几个特点可以看出,长篇小说在“五四”文化运动高潮中虽然没有像短篇小说那样起到呼风唤雨的作用,但它在稍晚的起步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素质,它对个体生命的重视和独立意识的张扬,它对人性弱点的理性审视,它双重文化视角的建立,这些特征尽管都还只是比较肤浅地触及和生涩地显现,尤其是牵涉到社会矛盾,往往只是一种感应式的表现,说不上什么深度,但我们还是应该承认,其创作总的基调与这场新文化运动趋向是相呼应的。当然,这些属于草创期的现代长篇,其艺术缺陷也是明显的。一些作家虽有优美清新的文辞,但创作长篇却几乎没有具备长篇的文体意识,正如老舍自己所说的:“在人物与事实上我想起什么就写什么,简直没有个中心;这是初买来照相机的办法,到处照相。热闹就好,管它歪七扭八”⑧。所以在这些作品中,情节处理的突兀,人物性格刻画的粗梳,矛盾线索交错的凌乱,还处处可见。 三、人的凸现:长篇小说创作被推向新的层次 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辉煌,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文学财富,是它所塑造的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曹操、刘备、关羽、张飞,《水浒》中的林冲、武松、宋江、李逵,《金瓶梅》中的潘金莲、西门庆,尤其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晴文、凤姐等等,这些艺术形象,它们已经超出了文本本身,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中。这些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艺术形象,是长篇小说创作水准的集中体现,可以说,作品正是因它们的存在而不朽。 长篇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它的一个重要功能,或者说艺术优势,就是可以为我们塑造出血肉丰盈、具有命运感的艺术形象。在这个篇幅巨大的文学体裁中,如果只有广阔的历史和现实生活图景的展现,而缺乏感人的人的命运展示,是很难震动人心的,而命运的展示,就是人的性格展示,就是人的形象塑造。如果说晚清小说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一个低谷,其主要原因就正是在此,在于它没有为中国文学提供出哪怕只有一两个有艺术价值的人物形象。 人的凸现对长篇小说的意义,首先是因为人的生存、人的心理、人的性格成长、人生的经历遭际,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社会各种不同力的作用和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是站在社会“力的平行四边形对角线的交叉点上”。突出人的生存境况和生命过程,必然会使读者在关注人的同时,思考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种种矛盾。而人的命运起伏浮沉,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又是形成小说情节的迂回跌宕、矛盾线索盘缠有致、游弋多姿的基础,因此,长篇小说凸现人的形象,是把创作推向深度、提高小说艺术品位的一个关键。所以,在长篇小说的现代演进中,如何使人的形象在小说中凸现,自然是我们考察的一个重要角度。 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末,长篇小说出现的两部作品,即:叶绍钧的《倪焕之》和苏雪林的《棘心》,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倪焕之》,1928年11月写毕,1928年开始连载于《教育杂志》20卷1至12号(1929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全书30章,17万3千字。 《倪焕之》可以说是中国长篇小说现代演进中第一部以人物命运为线索架设艺术结构的作品。小说的内容相当贴近刚刚过去的历史和当时的社会现实,它以辛亥革命前后、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大革命失败这十多年时间为背景,以小学教员倪焕之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为主线展开故事的叙述。小说的开头是写知识青年倪焕之受辛亥革命热潮所鼓舞,抱着“教育救国”理想,随友人树伯坐船到乡间小学任职。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校长蒋冰如,需要志同道合者共同办教育,希望用教育对那个“质朴底里藏着奸刁、平安背后伏着纷扰”的小镇进行改良。倪焕之也把这次上任作为自己理想追求的开始,他和校长努力贯彻新的教学理念,策划出学习同实践结合、知识传授与游戏结合,对学生循循善诱,以诚意感化学生等一系列措施。可是,它们的作为却受到仍处于宗法制农村社会各种传统观念和黑暗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一些教员也为获取高薪而离校到公司任职。而倪焕之的女友金佩璋,在与之恋爱时,表现出新女性的进取和对教育改良的兴趣,但婚后却朝气顿失,疏离教育事业,进取之心被家庭琐事所淹没。“自立的意志、服务的兴味”都放弃了。倪焕之的理想遭到社会外部与家庭内部的双重挫折,感到幻灭与悲凉。 五四运动重新点燃了倪焕之心头未灭的火种,也使他懂得了孤立地“教育救国”的不切实际,他与蒋冰如四处演讲,表示从今以后“不但教学生,并且要教社会”。小说接着写到五四后社会思潮的变化,有人转向,有人退隐,蒋冰如当了乡董,只关心自己儿子成才,再也不关心学校和教育事业。而倪焕之由于得到革命者王乐山的启发,遂回上海投身革命。他在工人的行列中开始感到工人的伟大,感到自己不应站在教训他们的位置,而是应学习他们那种“朴实、刚健”,“不多说而用行动来表现的活力”。但是大革命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白色恐怖,特别是他所敬重的革命者王乐山的惨烈牺牲,使他刚建立起来的信念和勇气彻底被轰毁,在极度失望中他用酒麻醉自己,最后得病而亡。 小说正是以倪焕之个人命运的展示,非常真实地记录了一个追求进步的年轻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转折的最初阶段,从满怀爱国热情,投身“教育救国”,受挫后,又毅然走进工农革命队伍,最终因革命的失败,而在幻灭中结束生命的人生过程。从这个人物的命运中,我们会真切地感受到在刚刚结束封建帝制,正在向现代社会演进的转折时期现实的严酷,盘踞千年的历史蒺藜,难以靠天真的愿望自动消失;血与火的较量所带来的生命被毁,仍然是一种无尽的威胁;也使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在这种布满荆棘的现实面前,由于理想的天真不切实际,从而遭遇幻灭的心路历程。小说通过人的命运折射社会现实,特别是折射历史动荡时代人的精神伤痛,可以说达到了近代以来小说创作所未达到的深度。 《棘心》是苏雪林在1928年夏间开始写作的一部长篇。1929年付北新书局印行(原印本12万字,1957年经作者增订为18万字),销行达十余版。 这部作品也是围绕着主人公杜醒秋的个人际遇展开故事,但它带有很强的自传性质,因此个人感情色彩十分浓郁。小说一开始,写在北京女子师范学堂就读的醒秋即将送别来探望她的母亲回家乡,由此回叙了她母亲在家中备受婆婆束缚、逆来顺受的不幸人生。作者以浓重的笔调,描述主人公对母亲的依恋及对离别的难平心绪,为整部小说设下了鲜明的基调,也就是作者在作品的扉页所引《诗经·凯风》的诗句:“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凯风:南风,长养万物者也。棘心:棘一小木、丛生、多刺、难长、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夭夭:少好貌。劬劳:病苦也。——见《诗集传》朱熹集注) 小说主人公杜醒秋出生的年代,正是“皇帝已从宝座上颠覆下来,家庭尊长的地位,仍然巩固得铁桶相似”的环境,在江南小镇她这个家境殷实、传统观念却十分浓厚的家中,她自小处处受到压抑。但她有很强的求知欲望,从叔叔、哥哥们在上海带回的教科书中,使她一鳞半爪地懂得了一些历史、天文、地理新知识,也崇尚中世纪欧洲武士的尚武精神,这个在家中被称作“野丫头”的醒秋,用以死相抗的行动,终于冲破家庭的种种阻力,相继进入省女子师范和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在接触五四新文化中,她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不久,又获得赴法国留学的机会。小说的大部分篇幅,都是描写醒秋到法国后思想感情的变化。 小说对醒秋到法国后的描写,主要是围绕三条情感线索展开的。第一条情感线索是对母亲的思念,这种思念,又交织着对故乡、对故国的强烈情怀;第二条情感线索是对婚姻的矛盾心态,因与从未谋面的未婚夫性格爱好不合而深陷情感苦恼,想退婚却又怕违抗父母之命而伤害母亲的心,而违心地维持婚约又造成个人情感的受压抑;第三条情感线索是对宗教情感的变化,从理性的排拒,到情感的接受,到最后的皈依。这三条情感线索在醒秋身上错综盘缠,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由此而形成了主人公醒秋的极为复杂、常处于躁动不安的心态。西方文明固然为她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开启了她封闭的心灵,但却又把她带入虚无的精神困境;家乡遭受乱兵、土匪蹂躏,自己作为华人在异国他乡备受歧视,又更加剧了她对母亲、对故国的思念和怀恋;婚姻的无着落,生活上的孤独无援,使她的理性逐渐失去平衡,天主教的教义也就乘虚而入,带她去“求神的爱抚”。然而,入教并没有使她心灵安妥,同胞学友对她“背叛五四精神”的无情谴责以及她在五四“理性女神”面前的自我谴责,都更增加了她精神的痛苦。最后,是法兰西的灿烂文化唤起了她对美的情感的觉醒,终于放弃进修道院的念头,带着把文学当作“最佳慰情者”和“最相宜的终身伴侣”的决心,告别法兰西。 《棘心》就是这样为我们描写了一位出自封建宗法观念浓重家庭的年轻女性,在辛亥革命、五四思潮影响下,自我意识的觉醒过程以及所遇到的各种精神困扰。它非常真实、细致地展现了在那个特定时代中,一个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东方与西方的文化观念之间,在理性与情感之间,精神的迷惘、心灵的激烈碰撞和艰难的抉择。 《棘心》中的杜醒秋与《倪焕之》中的倪焕之,是处于同时代的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执着于以教育救国、改造社会,而投身革命,一个敢于冲破传统羁绊、向往现代文明,却又陷入情感漩涡中不能自拔;一个在时代激荡起伏的潮流中,从希望有所作为到最后失望而亡,一个在个人奋斗的曲折途程中,始终未能摆脱精神困扰应和时代大潮,最后选择了文学作为灵魂安妥之所。应该承认,这两种类型的人物,在那个时代都具有它特定的典型意义。它们不仅通过这样的艺术形象,从不同角度折射出历史转折期社会的复杂动荡,新与旧较量的残酷,也不约而同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精神的脆弱性。 两位作家,在塑造自己的艺术形象时,也是各有特点。叶绍钧更多是在人物的行动经历中来塑造倪焕之的,在他比较成熟的现实主义笔法中,也揉进了一些幻觉性的描写,但总的来说,呈现的是一种朴实的现实主义图景;而苏雪林塑造杜醒秋,则更多是在心理历程中、在情感袒露中来表现人物,杜醒秋的精神苦闷、心灵震颤,被作家描写得细致入微,极具感染力。如果说,叶绍钧在表现人物的思想变化和心理转换时,还有某些过度环节处理得较简单的话,苏雪林对人物心理变化的描写,却是极有层次,顺乎自然的。加上她对自然景物描写的擅长,情与景融和的优美笔法,使作品有着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浪漫情愫。 《倪焕之》和《棘心》,是现代长篇小说草创期出现的两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长篇作品,它为我们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是完整的,具有各自的文化内涵。而围绕着形象的塑造所采取的叙事方式,无论是顺叙、倒叙,都相当自如。为以人的命运为线索折射生活的长篇小说创作,进行了初步的实践,提供了最早的经验。当然,由于《倪焕之》所持的明确的创作意向:“教育救国”只是空想,改造社会,需要的是革命,是血与火的斗争。这种创作意向与当时的主流意识是合拍的,因而受到革命文学阵营的重视,在此后出现的各类文学史、小说史著作中,都把它放在重要的位置。而苏雪林则因后来在政治观念上的分歧,以及与革命文学阵营的龃龉,所以对她的这部作品往往予以忽略,或放在边缘位置,或评价谨慎。今天,我们从长篇小说现代演进的角度来审视它时,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地给予它应有的评价,承认它在我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中曾显示的成就。 总之,随着《倪焕之》和《棘心》这两部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在进入现代社会后终于结束蹒跚的步履而开始踏上新的台阶。 ①包天笑:《小说大观》宣言短引,见《小说大观》一集。 ②《铁冷碎墨》,小说丛报社1914年发行。 ③郑逸梅著:《淞云闲话》,上海:上海日新出版社1947年版。 ④周作人:《答芸深先生》,《谈龙集》,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92页。 ⑤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 ⑥陈思广:《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版,第1—9页。 ⑦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3页。 ⑧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老舍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页。标签:小说论文; 苏曼殊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百年中国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断鸿零雁记论文; 玉梨魂论文; 赵子曰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