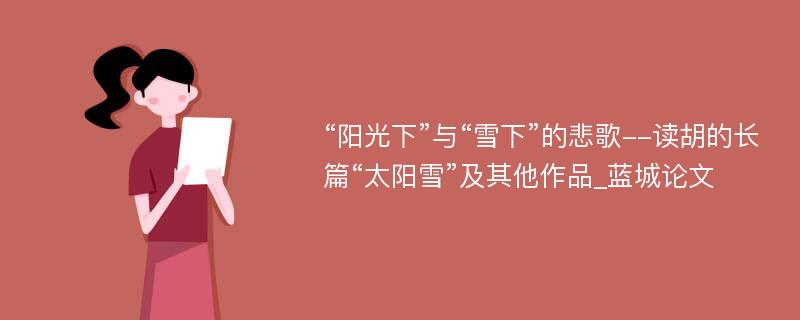
太阳雪下的悲歌——读胡小胡的长篇新作《太阳雪》兼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阳论文,悲歌论文,长篇论文,新作论文,及其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东北作家
在1993年的长篇小说年中,人们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了被媒体称之为“陕军东征”的一些小说,这也很正常。一是有媒体的倾力宣传;二是其中一些作家如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等的确实力不凡;三是其中几部作品如《白鹿原》、《废都》等均可谓特色鲜明。然而,就是在这一年,还有一部平平常常的长篇小说不经意间也成了畅销的热门书,这就是胡小胡先生的长达三十七万字的《蓝城》,一版印刷二十二万,后来的加印或盗版则更多,不可谓不畅销。我曾经在题为《站在“蓝城”外的远观》那篇短文中说到,若论《蓝城》,其厚重远不及《白鹿原》、其性描写大不如《废都》,与之处于同一档次的长篇在中国占有相当数量,可为什么只有《蓝城》能如此畅销呢?因此,我们在关注《蓝城》的同时,更可以研究一下它得以畅销的种种原因。在某种意义上说,研究《蓝城》的畅销之道或许比研究它的文学之道更有价值。这样说,绝无贬低胡小胡和《蓝城》的意思,能成为真正的畅销之作也不容易,并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
三年过去了,胡小胡给文坛又献出了一部更长(五十六万字)的长篇《太阳雪》(华夏出版社1996年12月版),它还能继续享有《蓝城》那般畅销的幸运吗?或许难,毕竟太长了,且定价已近三十元,一般的读者大约都要掂量掂量自己的钱袋和时间。然而,也算失之东隅,得之桑榆吧,《太阳雪》虽未必能如《蓝城》那样畅销,但从文学批评角度而言,却比《蓝城》有了更可言说一番的广阔空间,对一位作家而不是畅销书的写家而言,后者或许更重要也更珍贵一点。
1
从题材角度而言,《太阳雪》或可定位于都市,或可定位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后国有企业的命运,或两者兼而有之。但无论是哪一种,其难度都是显而易见的。说都市,无论是我国社会的构成还是文学创作的沿革,都市或都市文学的土壤都远不及乡村文学那样广袤、那样丰富、那样深厚。说国企改革,则更是近几年出现的新鲜事儿,当然更是一件难事儿。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近二十年,各条战线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可喜成就,国企改革自然不能例外,但相对而言,它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甚大,也正因为如此,国企改革问题才成为当前国家整体改革战役的攻坚战,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要花大力气搞好。将这样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尚未找到普遍成功答案的难题用小说形式来表现,困难自然不会小。至于将都市与国企改革这两个难点叠在一起,其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以胡小胡之智慧,当不会不知其难,知其难反迎难而上,仅是这种胆识和勇气也大可令人钦佩一番。
当然,就文学创作而言,仅有胆识和勇气自然是不够的,在《太阳雪》中,我们所读到的当然也绝不仅仅只是胡小胡的勇气。
着眼于取材,无论是都市还是国有企业在经济体制转轨条件下的命运,尽管其文学土壤说不上深厚,但也并非处女地一块,定位于都市的小说,长中短篇应有尽有;定位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国企命运的作品,长篇有没有,恕笔者孤陋寡闻,不敢妄下结论,但中篇佳作却已见出苗头,比如谈歌的《大厂》、《车间》、阙迪伟的《生路》等均已受到相当好评。因此,就题材而言,《太阳雪》并未占到什么先手,这就更需要作者的独具彗眼和另辟蹊径了。
《大厂》、《车间》、《生路》这样一批被称之为“现实主义”的作品其称谓是否准确另当别论,但这些作品无论是整体的布局谋篇还是细节的安排调度都的确是十分写实,十分质朴,作者不动声色地、近乎冷峻地通过一定企业、一个车间乃至一个普通工人的画面将国企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的艰难与希望活脱脱地再现了出来。相比较而言,《太阳雪》总体上虽也可称之为一部现实主义长篇,作者同样坦言自己“只是真实地反映这个生活、这个时代的大面貌”,但只要卒读全书,又不能不承认这部长篇在风格、技巧的构成上还是要复杂和华丽了许多。
整体象征的运用可以说是《太阳雪》的一个显著特征。我之所以使用整体象征这个杜撰出来的词儿无非是想说明作品在运用象征这一修辞格时虽然也很具体,但其寓意则是全局性的而并非某一枝节,“太阳雪”的命名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太阳雪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然景观?我们不妨想象:洁白的雪在飞舞,红日在冉冉升起,阳光和白雪交相辉映,完全是一幅如诗如画的美景;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奇异景观中,作品的主人公、名震S市乃至整个东北的国有大型企业——东北建设总公司的总经理陶兴本却孤独地喝完了一瓶衡水老白干,在寒冷的凌晨踏雪登上了四十层的金山大厦屋顶平台,他向前走了几步,然后纵身一跳……良辰美景和悲剧性的人生,巨大的反差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象征。整个事业的前景是美炒的,而主人公则是为事业作出自我牺牲的失败的英雄。再看作品的整体结构同样也是整体象征的运用,开篇伊始,便是东建四十岁诞辰的喜庆日子,虽嘉宾如云,但已讲不起排场的喜庆气氛中却夹杂着悲凉。或者说,东建四十岁来临之际,也正是它走下坡路之时,果然,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在银河大厦工程竞标中的败北,期货经营的血本无归,正在当建的金山大厦燃起了大火……一连串的厄运接踵而至,以至它的领头羊陶兴本走上了绝路。小说的“尾声”虽然为东建注射了几针强心针与兴奋剂,但效果如何却并未明示。以喜庆开局,以悲凉告终,当然又是一种整体象征,其寓意与“太阳雪”的象征意味构成呼应,造成了一种强化的艺术效果。
既然是整体象征,总有其象征的对象之所在。胡小胡在写给该书编辑的一封信中有过这样的表述:“国有大型企业在无数的成功、希望、幻灭之中走过半个世纪,成为当代经济生活中最大的‘疑难杂症’”。“而《太阳雪》的背景是一个北方大都市、一个数万人的大型国有企业。这个大企业濒临艰难之境,使小说有一种都市荒漠的苍凉”。其实,即使是撇开作者的这段表述,只要卒读全书,也不难看出国有企业在社会经济体制转型期中的前途的艰难。当然,我们不能将作品中出现的种种意象与作者对国企前途和命运的思考一一进行简单地机械地比照,“苍凉”也好,“疑难杂症”也好,自然都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反映出相当一部分曾经辉煌显赫的国有企业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尴尬处境,这是事实。也正是因为这种事实的存在,作者才要拿起笔来予以反映,予以思考。
承前所说,胡小胡的这种反映和思考需要胆识和勇气,比如写到国有企业生存的艰难、发不出工资、职工医疗费无法报销、三角债的困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屡屡处于劣势……这一切都极有可能被“左视眼”们视为“给社会主义公有制抹黑”、“为私有制张目”等等,但胡小胡全然不顾这种风险的存在,而是秉笔直书。对这种胆识和勇气我固然表示钦佩,但同时也以为这不过是作为一位称职的作家所必备的良知,尚不足以代表他艺术上的成功和出色。所谓作家,除去这种胆识和勇气外,同时还需要兼有个性和才气。胡小胡自然深谙此道,因此,在《太阳雪》中我们便读到了胡小胡在进行这种艰难的反映和思考时的一些富于个性化的艺术处理。
首先,是对陶兴本这位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作为一家大型国企的总经理,他既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又是一位悲剧性十足的人物。然而,其悲剧的结局又不是他个人的缺陷所造成。看陶兴本,很容易想起曾经出现在新时期文学人物形象画廊中的一系列改革者群像,最典型的当然莫过于蒋子龙笔下的乔光朴了。两相比较,陶兴本和乔光朴从个人魅力上看的确有很多近似的地方,比如能干、肯干、敢干,也都是那种干脆利落、说一不二的“铁腕”人物,既有大刀阔斧的一面,也有细腻入微的地方……然而,乔光朴成功了,而与乔光朴何其相似乃尔的陶兴本虽使尽浑身解数,也没能拯救他的企业,自己却最终走向了毁灭。是陶兴本人品不好吗?是陶兴本能力不高吗?是陶兴本开拓不够吗?是陶兴本魅力不强吗?都不是!于是,我们在新时期文学的改革者群像系列中,看到了一个真正彻底失败的改革者,看到了一个个人魅力十足却无可奈何、无所作为、丝毫左右不了企业命运的失败者,这不啻于宣告了那种习见的“能人治”、“清官治”模式的终结。既然指望不了“能人”,依靠不了“清官”,剩下的该是什么?作者通过对陶兴本这个性格并无多少个性但命运却耐人寻味的形象的塑造给人们留下了十分广阔的思考空间。
其次,是多重对比的广泛使用。围绕着陶兴本和他的东建,胡小胡在《太阳雪》中至少重笔设置了两重对比。其中既有陶兴本与东建和韦家昌与九建一对分属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家与企业间的对比;也有陶兴本与潘红旗、潘卫东、陶初云这两代人间的对比。先看陶兴本与东建和韦家昌与九建的对比。论个人能力与魅力,胡小胡的处理很聪明,他既没有把陶兴本写成那种只会迎合上级、碌碌无为、干干巴巴的“官人”,也没有把韦家昌刻画成投机取巧、不择手段的奸商,而是各有千秋,即使是个人的情感世界,陶、韦也各不逊色。当然,细细比较,陶兴本似乎更显大气、更招人喜爱一点。然而,就是这位从能力到魅力都多少胜出韦家昌一筹的陶兴本所领导的东建却远远比不上韦家昌所掌管的九建。在S市几百家建筑企业中,九建一举夺得国家级质量大奖“鲁班奖”,成为声名大振的明星企业,在与东建平起平坐地竞争“银河大厦”工程中,又是以九建的获胜告终。而东建则是在“层层瞒产、虚假承包、谎报利润和财务管理失控”的调查结论中几近奄奄一息。再看陶兴本与潘红旗、潘卫东、陶初云这两代人之间的对比,他们之间在具体观念、看法乃至行为上存在差异本也是正常的事儿,但很难说陶兴本就一定比下一代落后保守僵化糊涂到了哪里去,在有些方面,陶兴本的观念之超前一点也不亚于下一代,然而,在困难和挫折面前,陶兴本选择了殉道式的死亡,而潘红旗和陶初云却毅然辞去了公职,向旧体制宣战,向市场经济进军,自筹资金办起了股份制的大方设计师事务所,一个新生代的“陶经理”应运而生。这样的两重比较导致使读者不难产生殊途同归的想法。
一个人物、两重比较充分显示了胡小胡在反映和思考国企在社会经济转型期的前途和命运时的个性和艺术处理,也使得这部长篇比之于同类题材的作品具有了某种深度,这种深度我想既体现于作者不回避矛盾、直面现实的勇气,也在于胡小胡在现实中的这种艺术的思考和求索。
然而,胡小胡的思考和求索并没有就此止步,但当他试图作出更深层的理性思考时,本书的缺憾随之出现了。
2
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固有的传统观念的桎梏,致使一部分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大潮滚滚袭来之际不知所措,适应不了激烈的市场竞争,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这不仅困扰着一些企业和一部分企业职工的根本利益,也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性进程。唯其如此,国家才把国企改革的问题放到了整个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位置,提出了“转制”、“练内功”、“抓管理”、“抓大放小”等一系列宏观决策,并反复强调要下力气抓紧抓好。然而,这场变革毕竟是一场前无古人的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不是简单的几项决策和号召就能实现的。事实上经过几年的摸索和实践,国企改革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效果尚未尽如人意。于是,上至决策层下到各方有识之士都还在继续探索而且努力从更深层次上去思考国企改革的种种问题。
作为一位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况且自己的作品又是取材于国企改革,因此,胡小胡在《太阳雪》中不仅就国企在体制转轨中的现状提倡了一幅幅形象的、客观的画面,而且也试图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理性的思考,这一点在作品中的表现同样十分明显。比如借市长鲁曼普之口提出了国企改革的攻坚点究竟是体制不行还是管理不善的问题;比如借潘卫东所发出的“用旧的传统的经济模式建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就是恐龙,庞然大物也!长一个小脑袋,神经不发达,被人咬掉了腿肚子自己还不知道,生下的蛋成活率很低,气候一变化就要发烧感冒手脚冰凉瘫痪不起……”“市场经济的大潮就是今天的造山运动,是市场经济促进这种进步,淘汰了低等物种,催生了高等物种”这样大段而形象的议论,提出了国企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比如,还是借潘卫东的“陶总的死也说明,旧体制培养起来的人也救不了东建,这些人中,一部分人堕落了,而像陶总这样不甘堕落的他们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没有足够的勇气。他们的奋斗就有了更加浓厚的悲剧色彩、发人深省”的感慨将国企改革的体制问题放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
我无意否认作者的这种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理性精神,尽管这些议论和意见并未超出理论界的现有成果,但还是看得出作者试图在深层次上求索的良好愿望。要求一位作家在这些迄今尚待探索、尚待解决的大问题上有惊人的突破甚至是一家之言显然是一种苛求。因此,我的遗憾并不在于作家提出的这种思考,而在于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作者的这种处理存在着明显的创作之忌,用马克思的经典定义来说,就是多少有了点“席勒式”的味道,“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抽象性排挤了具体性,概念代替了有血有肉、生气勃勃的个人。这样的评论虽不够准确与贴切,但的确也是相类似。作者虽然是在借鲁曼普之口与潘卫东之口发出的种种议论来传递出自己的理性思考,这本身没什么不好,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是从鲁曼普之口还是从潘卫东之口发出的那些议论,其思想核心本已渗透到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和故事的发展之中,从我们前面对陶兴本形象的分析以及那两重对比中便看得一清二楚。或者说作品中种种议论的内容,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并未超出作品的人物、情节和故事的发展,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来上几段游离于形象之外的近乎赤裸裸的议论呢?而类似的处理还集中体现在《太阳雪》的“尾声”中,徜若以陶兴本在太阳雪中坠楼而死来结束,未免残酷了一些,于是作品又安排了一条“光明的尾巴”,借潘鸣放与潘卫东兄弟俩的彻夜谈心,一一交代作品的人物及故事结局,东建中的坏人被揭了出来,东建又有了生路……如此等等,似乎是为了弥补一下的这条“光明的尾巴”过于外露,作者不得不再次让潘卫东发议论,这“不过是又一次计划经济式的挽救,让你们躲开市场的冲击。你们的体制难道有什么改变?当你们再一次面临市场的时候,你们又会怎么样呢?”于是,“光明的尾巴”被掩藏起了一点点。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画蛇添足的败笔,既不能增加作品在思想层面的厚重,反倒破坏了艺术整体的和谐。尽管我能够理解作者种种安排的良苦用心,但总以为这样的处理实在有点得不偿失。
如果说作品中一些近乎“席勒式”的处理构成了《太阳雪》的一个明显缺憾的话,那么,全书枝蔓的过于杂芜与过于戏剧化的处理则是这部长篇的又一缺憾。
在反映国企于社会经济转型期的困难、前途和命运这个大主题之外,《太阳雪》还使用了大量的篇幅或详或简地、交叉地写到了好几个爱情故事,其中既有作为一条条情节线的兄弟同时追一个女人(潘鸣放、潘卫东与陶初云),姐妹先后同一个男人约会(陶初云、陶未雨与潘卫东),寂寞的“留守夫人”爱上了哥哥情人的父亲(潘红旗与陶兴本);也有以插叙形式出现的陶兴本与钱端端、钱芳芳与鲁曼普之间的情感纠葛。客观地说,这些爱情故事单个地看都有一定的可读性,其中对一些人物性格的刻画也相当个性鲜明。但总体上看,在这些爱情故事中,有的处理过于戏剧化,人为雕琢痕迹太重,而它们间交叉描述所占的篇幅又太多了一点,再加上爱情故事以外的其它枝蔓,比如陶初云寻找亲生父亲的经历完全都可以简写甚至忽略,全书五十六万字的篇幅实在有条件大大压缩,使之更加紧凑让主旨更突出一些。
最后还想指出一点,《太阳雪》的主旨是在凸现国企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艰难,其载体又是东建这样一个国有大型建筑企业,但作品中出现的主要人物却大都是这家企业的管理层以及与之相关的亲情关系,而对构成企业的另一主体——工人,除去对一个退休老劳模马龙祥在背景上写到几笔外,其余基本未涉及。作为一种选择,这样的取舍自然不是绝对不行,但即使是对管理层人士的描写,除去陶兴本写来活灵活现外,其余大都平淡,尤其是对几个所谓“反面人物”的着笔,比如金家父子、比如上级的惠石局长、下属的二公司经理吕寄生等等都过于简单化了。看起来,这只是一个对人物艺术处理的具体问题,实际上则因这种薄弱又不能不影响到整部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完整和成熟。
3
通过前面两个部分的评析,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太阳雪》是一部长处和缺憾同在,而且同样都表现得十分明显的长篇小说。作为一个读者,或也可自诩为相对专业一点的读者,我总以为这样明显的长短并存是十分遗憾的,作者本可以将这部自己“用尽心血的东西”再耐心打磨得更完整、更周全一点。当然,任何作品都可以说是遗憾的艺术。
我想,这既可视为胡小胡个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又不能完全这样简单地下结论。在目前文坛上所出现的数量与日俱增的长篇小说中,类似《太阳雪》这样长短明显并存的作品并不在少数。因此,认真地研究一下这一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对提高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或许不无裨益。
我承认,对这种原因的研究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各个作家的具体情况毕竟千差万别,不宜同一而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个性之外,是不是也还存在一些共性的因素可以提出来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深思呢?
以往人们常将长篇小说视为文学的重武器,将其作为衡量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重要标志,这样的认识在今天是否依然合理姑且不论,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长篇小说创作的艰难和不易。事实上,中外文学史上的许多著名作家在创作长篇小说中也都是倾其毕生心血,绝不敢轻举妄动,虽也有巴尔扎克、左拉这样的高产大师,但毕竟不多见。这样说并不是在刻意渲染长篇小说创作的神秘和高不可攀,而只是重申一个事实,长篇小说创作的艰难。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似乎正在越来越为人们所遗忘。在我们一些作家(或者是写家)的眼中,没什么难不难的,写来说是,不就是篇幅长一点,线索多一点,头绪复杂一点嘛,于是就出现了不仅谁都可以写长篇,而且越写越长、越写越快的畸态。应该说,这是对长篇小说文体认识观念上的问题,持这样一种轻率的认识观念,又怎么可能不出现明显的缺憾呢?这或可视为许多长篇小说出现长短明显并存之不足的共性因素之一吧。
我无意将所有存在着明显缺憾的作者都归于认识观念轻率这一类,事实上,有些作者对长篇的确也看得很重,写作前也作了不少准备,花了不少心血,写作中更是全身心地投入。但作品落成后依然长短明显并存,这就不能不提出一个艺术的全局观或曰整体观的问题了。所谓艺术的全局观或整体观就是完整地驾驭一种文体的能力,尤其是像长篇小说这样气势恢宏的文体,则更需要一种全局观或整体观来驾驭。我甚至可以武断地说,缺乏全局观或整体观,就很难创作出一部出色的长篇小说。读现在的一些长篇新作,时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有的作者对自己笔下的生活有着明显的深切体会,有的甚至就是自己的亲历,因此,作品的某些局部写来生动逼真、惟妙惟肖,着实提供了一幅幅真实形象的生活画面,但由于整体的艺术感觉一般,就导致了作品的大起大落,良莠不齐,严重者自然就是整部作品的失败;有的作者则因自己创作历史的悠久和艺术才华的横溢,在艺术的操作上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但由于对某些生活的隔膜和陌生,因而又常有苍白和虚假的地方露出,这同样导致了整部作品艺术水准的下滑。两者表现虽不同,但根源却是一个——缺乏艺术的全局观或整体观。
由《太阳雪》的得失想到了其他,话说远了。作为本文结束,还想绕回来再说一句,从《蓝城》到《太阳雪》,胡小胡经历了一次艺术的蜕变,也见出了这位作家的潜力,那么,让我们期待着他的下一部,至少不再有这样明显的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