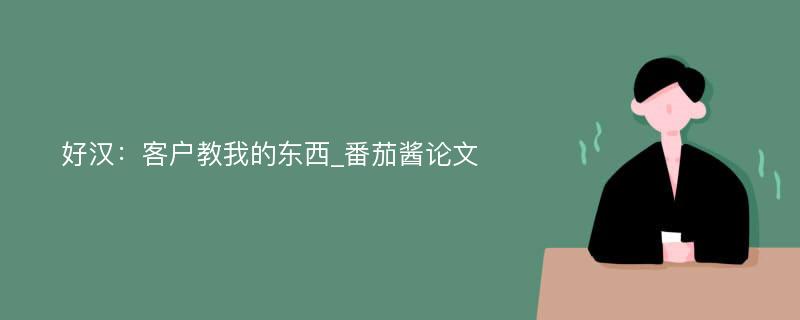
昊汉:客户教会我的那些事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会论文,事儿论文,客户论文,昊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拿着番茄的康轶,很快就在镜头前找到了感觉,不再紧张。
“从点种开始,育苗、移栽,然后采摘,在生产线加工成番茄酱。送到客户手里时,他们称赞:你们的产品快赶上美国的了。我们就非常有成就感。”康轶带着些许新疆口音说。
短短三年时间,他创办的昊汉集团,在番茄酱行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力:规模排名世界第六、中国第三,是全球番茄制品行业成长最快的企业。2008年昊汉的工厂建成投产,当年收入0.3亿元;2009年收入1.2亿元;在番茄行业低谷的2010年,收入2.96亿元。预计2011年达到10亿元。昊汉65%以上的客户是行业中举足轻重的国际性公司,在产品品质上也最有优势,“我们是中国番茄酱行业唯一一个原料追溯体系可控的公司。”
按照康轶的预估,4年之后,昊汉不但可能超过中粮屯河和新中基这两家老牌的番茄酱加工企业,还可能取代美国的Morning Star,成为年加工能力达65万吨、世界最大的番茄酱加工企业。
“我一直都觉得,番茄酱行业有非常大的行业整合的机会。”康轶说。2000年之前中国的番茄酱产量才20万吨,2010年剧增至130万吨,在世界上已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在美国之后,已经成为世界番茄酱第二大生产国。2010年中国番茄酱的出口量已经占到世界此行业贸易量的40%。但至今,中国的番茄酱行业依旧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行业集中度还比较低,很多发了财的外行都到新疆建厂,只有低价策略,没有品质可言。恶性低价竞争的结果是,从去年开始很多加工厂开始倒闭,行业整合的趋势已经很明显。
在2008年之前,康轶从事了十几年的番茄酱国际贸易,他的另一家公司博斯腾是中国最大的番茄酱贸易商。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到博斯腾的行业影响力:2005年中粮进入屯河后的新闻发布会,三个国际大客户发言,有两个大客户来自博斯腾。那时中粮屯河15%的产品通过博斯腾销售。
昊汉能够短期迅速崛起,它的客户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夸张地讲,是那些优质的——尤其是“挑剔”的日本客户——成就了它。“成就”的内容,不仅仅是订单,更是昊汉在与客户交往中,学来的理念和能力。
“一定要把产品做到客户的心里去。”这是康轶的“生意经”。在他的创业历程上,第一个重要的客户是日本的蝶理公司。这是一家日本的大型商社,1997年康轶通过意大利的一个客户联系上了它。合作是从一桶番茄酱开始的,蝶理检验后认为品质不错,就让康轶发了一托盘(4桶),再检验之后就让康轶发了一个集装箱,最终交易量达到了200吨。康轶的公司那时候成立不久,还很小,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因为当时的日本市场非常难进。
1998年,康轶通过蝶理,联系上了地扪——日本最大的番茄酱制品公司,也是全球番茄行业最有影响力的公司。和地扪的合作,让康轶的公司脱胎换骨。
为了保证产品的品质,康轶的团队带着地扪的团队,跑遍了中国所有的番茄产区。从每年3月份番茄点种开始,几乎所有的生产环节,康轶的团队都参与了。生产时节,康轶的团队蹲在加工厂直到客户订单产品生产完毕,才撤回公司。
作为一家贸易公司,康轶对销售人员的要求是,必须要了解商品的属性。“不是给客户报个价就可以,而是要给别人给不了的东西。这样才能做到客户想什么,你就能提供什么。”从地扪开始,康轶的公司已经不是那种从事简单买卖业务的贸易公司,而是对产业链进行研究的公司。
这种脚踏实地、贴身服务的结果是,当初那个只有5人的小公司,把日本前十大的番茄酱采购商都搞定了。康轶的公司从小到大,一直都有这些客户的追随。2008年,康轶决定建厂,这些日本客户全部又成为昊汉的客户。日本企业有一个特点,很少买新工厂的产品,因为产品的品质还没有得到验证。它们为昊汉破了例。
因为日本客户特有的精细特点,昊汉给他们提供的信息非常周全,包括:点种、育苗的时间、温度,施肥次数,采摘的进度。工厂里每个小时、每批次的检验报告,在第二天早上九点之前传给客户。客户还可以通过网络,随时在线看到昊汉工厂每条生产线的情况。
康轶很快把对日本公司服务的理念嫁接到欧洲、中东的客户。“客户没有三六九等,虽然价格不同、采购规模不同,但是我们的服务一定是一样的。”意大利的一个客户在拿到昊汉提供的每批次检验报告之后,完全被震住了,因为之前还没有公司给他们提供这么详细的资料。
至今,地扪还是昊汉最重要、关系最密切的客户。“我们有时候感觉就像一家人。”康轶说,隔一段时间不见面,就觉得少了什么。他每年要去日本东京的地扪总部考察、交流4次左右,地扪也会派人来考察几次。13年间,不懂日语的康轶和地扪的三任社长关系颇佳。地扪已经退休的专家中泽,2008年到中国帮昊汉建厂,帮忙降低生产成本。地扪另一位在番茄酱行业工作了42年的老专家石村,现在是昊汉的顾问,每年来中国三四次,从番茄点种开始,在关键环节指导生产。
“我们跟地扪这样的客户谈价格,根本就不是那种你报价,我砍价。而是你愿意出什么价,我什么价可以接受,彼此能为对方着想。”康轶说,“如果我卖的很高,他的企业怎么发展?我卖的低,我怎么发展?”康轶一直在琢磨,怎样能让昊汉和大客户形成一种更紧密的共同体,比如可以签订3-4年的长期协议,避免价格大起大落对双方的影响。
每逢番茄酱价格大涨,生产企业不是提价,就是降低产品品质。还在做贸易时,康轶有几次为了完成合同,不得不高价买进番茄酱再赔本卖给客户。“做贸易最重要的是讲信用。”康说,“要做得很扎实,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生产线,必须重视农业,重视产品的研发。”这也是促使他创建昊汉的原因之一。
对于销售团队很强大的昊汉来说,现在投入最大的,是番茄的种植。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番茄酱加工制造,而是一个农业产业化的命题。中国番茄酱的品质与欧美差距非常大,根源在于原料番茄的品质差异。中国的农业主要是小农经济,每亩产的番茄差别很大,原料不具有均一性,因此番茄酱的品质差异大。而欧美是现代农业,就没有这些问题。
昊汉通过与新疆建设兵团的合作,解决了小农经济的问题,甚至能满足亨氏、地扪等高端客户在农业产业化上的要求。这种与上游的良性关系并非一蹴而就。有一年番茄市价一路狂跌至280元/吨,昊汉还是按照约定的320元/吨的价位从农民手中收取番茄。“我们对待上游和下游的心态是一样的,宁可自己受一些经济损失,赢得更多的合作空间。”康轶说,“我是从新疆出来的,我也希望能够做一些对新疆农民有益的事情。”
“我们的每桶番茄酱,都能查出是哪亩地出的。”康轶说。昊汉从番茄的点种、育种、移栽、浇水、施肥、收获、加工等等,每个环节都是可控的。在日本、欧美发达国家,企业能做到这一点很正常,但在中国,只有昊汉能做到。昊汉的番茄种子是地扪、亨氏等国际客户提供的,品种与产能与国内完全不同。
受日本客户影响,康轶对细节也非常在意。昊汉的大桶番茄酱出口到国外,每只桶上都套上了塑料封套。“总不能让我们的番茄酱桶看上去还不如日本的垃圾桶干净吧。”因此昊汉的番茄酱每吨成本增加4元。日本的精益管理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你想不到的事情它们都能做到。”昊汉的每桶番茄酱都有编号,每个托盘也有编号,客户拿着昊汉提供的list就能非常清楚地知道那个桶是什么型号的产品。
康轶在昊汉亲自抓三件事:大客户,品质控制和督察审计。他对督察审计部门KPI的要求是,每个月必须查出20个不符点,包括企业和员工的方方面面,比如你为什么今天不洗袜子。他经常到工厂转悠,最关注食堂和卫生间。食堂不允许有苍蝇,卫生间不允许有异味。“一个食品企业这都不做到,怎么保证品质?”他说,昊汉要做到世界一流,必须不断纠偏,完善自己,从小事做起。
1990年,大学学医的康轶从乌鲁木齐来到天津,阴差阳错地进入了一家从事番茄酱出口的国企,成为最早一批进入番茄酱行业的人。1997年他开始创业。2008年,他开始第二次创业。谈起番茄酱他能讲上一天一夜,昊汉哪条生产线上哪个机器每秒钟弹几下,能做出什么品质的产品,他都津津乐道,也深感自豪。
康轶对番茄行业的热爱吸引了一批对行业有同样深刻理解的人,现在,昊汉的高管团队有不少人来自国内领先的食品行业。“我们这些人(在一起),为什么不做点大事,为什么不做到中国第一、世界第一?”他问道。
标签:番茄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