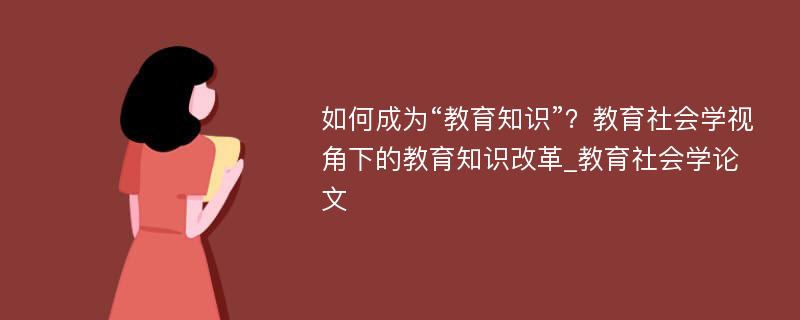
成为“教育知识”:何以可能?——教育社会学视野下的教育知识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论文,社会学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0)08-0123-07
一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教育社会学是以问题而不是以领域引导研究的。由于教育社会学与教育学和社会学的联想关系,人们通常很容易从逻辑上将它理解为跨领域的学科,由此将教育社会学理解为“教育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或者是“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研究”。这样的理解不能算错,但并不完全恰切。教育社会学拥有独立的研究取向,它假定教育现象的本质具有社会性,教育是一种社会性事件,因此教育社会学不是将教育与社会视为两个领域或两种现象,它们本属于同一事件,必须用一种“教育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眼光去看。不过眼光最终要以问题的方式呈现出来方能把握,研究者相信,寻找或者创建属于教育社会学的问题可以为我们敞开一个使某些教育现象、经验、材料的意义得以生成、显现以及理解的全新领域。
不过,在这样一个去学科化或反学科化呼声渐甚的时代,寻找某一学科独有的问题,不仅有些不合时宜甚至简直可以说有点不识实务。研究者的想法和做法恰恰相反,原因有三:其一,教育社会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本身并不缺乏学科视野的融合,它缺少的恰是学科融合之后的问题意识,包括老问题的复活与新问题的提出。对于教育社会学学科而言,问题的学科化比学科的问题化更显迫切和重要,教育社会学要寻得学科的发展更是需要以学科化的方式提出问题、确立问题、展开问题、回答问题。其二,在目前的教育领域,问题被大量的话语所遮蔽,这一点也许每个人都能感觉得到,但大多数的研究者或是实践者很不以为然。真正的实践必须在现实的紧迫性面前解决无法回避的问题,而真正的研究则要提出那些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两者都能做到诚实而毫不含糊地直面那些无法回避的问题,就走到一块儿去了。真正的实践和真正的研究通常都是毫不含糊的,不能把成问题的东西放着不管,而把不成问题的东西搞成问题,不坚持这一点往往会搞错问题。其三,如果承认教育社会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那么我们就得连带承认,它的问题并非越新鲜、越时尚就越有研究价值,不过现实中的研究局面不容乐观,很多问题还没弄清楚甚至还没进入就已经显得过时了,这让大部分的问题、概念和探讨缺少使人“惊愕”的魅力,没有了让人“惊愕”的学术究竟能够走多远?这是个问题。如果无法解决这一点往往会错过问题。
总之一句话,要么直面、要么创建学科的问题!我想首先从直面学科的老问题开始。
对于某一种“教育知识”——你可能很难下断言说它就是每个学生理所应当接受的东西,虽然我们早已对之习以为常;你也可能很难肯定它就是所有知识中最具代表性、结构最合理的知识,虽然我们常常希望如此或自以为如此。那么成为一种教育知识,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其标准是什么?规则又是什么?……显然,这是一个或一组老问题。自从新教育社会学诞生以来,上述问题就经常被摆上台面加以拷问,拷问的最终结果认为:教育知识与权力结构及社会控制原则之间具有密切联系,这种联系渗透在教育知识的选择、分配、传递与评价过程中。在总体知识中一部分知识被组织起来成为教育知识,这是一个显见的事实,正是因为太过“显而易见”,所以长期以来一直被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存在。新教育社会学将其变成了问题,反过来,这一问题也成就了新教育社会学。对这一问题通常的解释框架是“阶级”和“意识形态”,即教育知识所具备的阶级属性和内隐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以此来对应教育的不平等,以及教育知识与政治意识形态联姻后的控制特征。放在当前课程改革的背景中,问题依然存在,但解释路径却成了问题。
关于国家权力与政治意识形态对课程知识的控制特征构成了“法定知识”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两者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对立关系。这样的解释路径容易给人形成国家权力与政治意识形态铁板一块、密不透风的感觉,并且增加对国家权力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敌意。这当然不是说政治意识形态对教育的影响仅仅是一种虚构,事实上其影响是深刻的,几乎改变“教育知识的面貌”。在这一解释框架下,国家权力与政治意识形态对课程知识的控制表现为全面的总体化的控制,但是“国家”是什么呢?“国家”难道总是以作用方式一致、功能统一的身份出现吗?福柯曾提醒我们,“今天的国家可能比它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刻都不再拥有这种统一性,这种个性,这种严格的功能性,或者坦率地说,这种重要性。”①葛兰西也同样敏锐地意识到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和单一的场所的趋势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成为一个充满斗争的场所。②当然,研究者的困惑决非纯然来自上述学者们的理论启发,中国社会改革前后的现实变化也让这一困惑变得更加突显。有学者概括改革前后的中国社会是从“总体社会”向“后总体社会”转变,这种转变表现为国家权力逐步由一种无限权力转化为有限权力,国家的作用开始出现一些或明确或模糊的边界,国家的职能不再是垄断式控制,而是潜在的组织与动员。③在研究者看来,这些被动员起来的力量虽然起因于国家权力的组织和影响,但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国家力量,事实上愈来愈多的群体在奋力参与社会和政治控制,要求体现其自身的利益,分享国家的权力粉末。
同样,“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呢?从经验体认的层面看,政治意识形态的意涵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悬置和解构,要么被空洞化要么被无聊化。革命话语、政治意识形态等正愈益丧失对教育知识的影响力,除了化作若干空洞的词句,基本上退出了人们精神建构的空间,而随之登台且无处不在的是形形色色的“现代化”符号:文化、市场、消费、全球化等等,意识形态如果不是面目全非,那也至少已经今非昔比、面目难辨了。难怪有学者忍不住将它拿来与“变色龙”作比:“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一直在变化着,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随着它所出现的语境而改变。”④
“阶级再生产”一向被认为是教育社会学理解教育知识颇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它旨在说明处于高位或优势的阶层通过学校教育再生产原有阶层的价值观与文化,但它却无法解释如果同一阶层内部拥有相互矛盾的价值观念,那么究竟应该再生产谁的价值?因此如果将其放置在课程知识寻求变革的背景中,这一解释框架就不够有力,原因有二:其一,课程改革本身是要破除已有占主流地位的知识价值观,破除和确立的过程严格意义上是一个需要争取甚至斗争的过程,知识的主导价值观本身不再是一个给定的东西,而演变成一个争取和建构的过程,“谁是主流?”在改革过程中变成了一个问题,一个新旧斗争、多方协商后的结果。其二,在中国这样一个层次丰富、差距多元且处于社会整体转型背景中的阶层构成,其本身极为暧昧且变动不居,“究竟什么才算是同属一个阶层?”未必显明。研究者对课程改革原初的分析兴趣正是基于上述困惑:如果说教育知识反映了优势阶层的价值观与利益,那么自下而上的改革行动也许更能让人接受,但众所周知,这场发生在20世纪末的大规模课程改革行动恰恰相反,其自上而下的思路如此明显且从不避讳,它的动力究竟来自哪里?
指出这些,不是说“政治意识形态”和“阶级再生产”的分析工具本身是错误的,而是说如果将其视作一种现成的分析工具,容易掩盖“政治意识形态”和“阶级再生产”自身所呈现的复杂的构成性与可能的变动性。这说明:老问题需要新的答案了。
寻找新答案的努力表现为对行动者及其在知识变革中的行动观念、行动力量、行动规则的探讨。显然,行动者并不像海德格尔所描述的那样,是被从暗中扼住的抽象存在;也不是胡塞尔所谓的被剥光了感性的灵胎,不是福柯考古化石上的印痕,更不纯然是马克思所说的被总体化了的阶级意志。⑤行动者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信念、尊严、兴趣、利益、欲望、理想,他们更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甚至行动者天生就具有米歇尔·克罗齐耶所称的“策略本能”(strategic instinct),这归因于他们需要对其行动领域里诸种机遇与制约力量的感知,归因于他们对于行动中的对手行为或多或少直觉性的预期,归因于他们对其各自短期利益或长远利益的相应理解。⑥行动者是多源的、多层面的、多向度的,很难将其简单定性为某一阶级或阶层的代表,行动者的阶层背景也未必全然与其观念、实践与追求之间呈正相关的关系,同属一个阶层内部的行动者之间完全可能在信念追求迥异的前提下存有不同的主张继而倡导不同的行动,而分属不同阶层的行动者也完全可能彼此一拍即合、行动一致。将“行动者”维度引入法定知识的建构过程,正是希望从“国家”、“阶级”这些大板块结构中发现更为丰富、变化、局部、甚至异化的作用力对法定知识的影响,使得围绕“如何成为教育知识?”的答案求索更接近于事实,因为即便是纯然考虑社会因素的作用,这些社会因素也需要融注在有血有肉的行动者身上后,对课程知识的作用才更为真实、更具整合性与穿透力。
在课程改革中被动员起来的行动者借助国家力量所展开的改革行动,使得教育知识的建构过程与秩序格局忍不住让人浮想联翩:这些具备了改革资格的行动者,在实践的紧迫性与偶然性面前,在生存的考虑与策略的选择中,在群体间的利害博弈与相互妥协中,既有对控制性力量的寻求与再生产本阶层文化的可能,亦有相反力量的冲撞;既有对已有秩序的屈服与妥协,亦有充满激情与个性的困惑与努力;既有寻觅的坚持与异化,亦有变通的策略与智慧……在这种丰富、复杂的实践空间中建构出来的教育知识,不会是只有生机没有危机,只有希望没有虚妄,它很可能是个“混合范畴”或者干脆成个“四不像”。如果说政治意识形态对课程知识的解释框架生成了一种关于控制关系的理解域,阶级作用的解释框架生成了一种关于再生产关系的理解域,那么对于行动者个人或群体在课程知识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或许可以在更为动态及复杂的层面上去理解,在更为丰富与张力的空间中去探讨,而这些丰富的向度与层面需要我们在研究的具体展开和追问中将其面貌一一呈现。如果我们真诚的希望能够重思和重构中国的整个教育知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呈现这一重思与重构过程中的多种现实面向,才能在混乱复杂的改革情形中直面问题,在五花八门的繁荣中保持冷静,在暂遇的困境中寻找希望,在四散的新意中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知识更新。
二
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探讨“行动者”和“行动”,社会学理论奉为经典的“行动——结构”、“能动——制约”的分析框架并不合适,不合适表现在作为前提的这种对立关系在中国未必成立。因此用所设想的“行动——结构”、“行动的僭越”,或者干脆用被吉登斯改良过的“结构化”理论,或是被布迪厄提倡的“生成结构”理论等等作为分析思路去解释、理解当下的改革实践,总觉得非常别扭、不伦不类,甚至有点无病呻吟。过去用这样一些西方现成的概念、框架来解释局部的现象,虽然也常有隔靴搔痒之感,但因为问题本来就不痛不痒,所以这种“难受”还不够明显,但当视野向大处拓展,尤其是面对中国最深刻的教育变革时,这种智识上的无力感和无根感就变得让人忍无可忍了(或许触及的问题越宏大、越根本恰恰可能越本土、越需要地方化的理解,而不是相反)。研究者越发意识到很多分析框架和理论假设可能在前提上或开始处就已经错了。
这种“错误”不是说概念、框架原本有什么问题,研究者相信像“行动——结构”、“能动——制约”这些概念、框架用在西方社会一定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西方强调制度之间的制衡,这种制衡所形成的秩序,为行动者制造了绵密的结构之网,所以才有了韦伯所谓的“现代社会的牢笼”之感叹,人们所建立的规章、制度拆开来看对人的制约未必强硬,但是制度所织成的结构或秩序之网却是密不透风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行动与结构、能动与制约才有了紧张、有了让社会理论界津津乐道的必要;但在中国社会恰恰相反,制度、规章单独看起来对行动的制约显得较为强硬,但不以相互制衡为原则所形成的秩序,不可避免在制度与制度、规章与规章之间留有不少空隙,这些空隙使得行动有隙可乘,并且制度本身还可能是活的,有成文的,也有大量不成文的。如果说西方是通过制衡原则要求制度本身能自圆其说,那么在中国则更多要求行动者或行动本身能够自圆其说,这就给行动者留下了相当大的余地。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中国社会制度结构的制约是人们想象、捏造出来的,而只是想表明这样一种“行动与结构”、“制约与能动”关系可能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发生的,这种方式体现为一种整体性的思维与实践。
中国向来强调“天人合一”的心性、修为境界,这从中医、围棋、武术等独具中国特点的事物中可窥见一斑,这种整体性具体到行动者身上,在行动的酝酿和展开中:(1)看重“势”:“审时度势”、“见机行事”,并能“耳听八方”,兼顾“风声、雨声、读书声”;(2)关注“局”:“全国一盘棋”,“世事如棋局局新”;(3)注重“变”和“通”:强调“权宜之计”、“通权达变”、“圆熟老道”、“游刃有余”、“极高明而道中庸”;(4)发展“潜”和“绕”:如“潜规则”、“隐身份”、“绕道而行”、“另起炉灶”。⑦通过如此这般的“局势思维”、“变通风格”、“迂回策略”,使得行动与结构浑然一体、不分你我,来自“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对立与对抗不仅没有想象的那般紧张而且往往在行动中被化于无形。这提醒研究者,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思考“行动者”与“行动”,整体性视野是较为合适的,一旦不再以行动与结构的对立和弥合作为前提,也就不存在去关注行动的越轨、结构的反作用,而是直接关注行动者实践智慧的迸发、局部规则的协定、灰色地带的争夺、集体行动的筹划等。而正是立基于中国的独特文化与时空,对融合了个人与结构又不能简单还原为个人与结构的改革行动的关注,进一步印证了从行动者角度切入理解教育知识建构的意义:一方面,改革大局的存在,使得各个层面和领域的精英们意识到并拥有了执掌社会权力的可能;另一方面,行动者在行动中不断试探、体验伸展拳脚的空间,在这个被越来越多的行动者意识到并反复实践、主动寻求的行动空间中,一些看似零碎的、分散的、异质的、持续的努力正在改变着教育知识的面貌和教育秩序的格局,当然这种改变不排除异化的可能。
这些探讨可以进一步从两个维度深入:一是不同层面的主体行动及其行动博弈:个体性的精英行动、局部性的集体行动、整体性的国家行动,它们在不同范围展开,被不同的力量寻求、组织和动员,挑战了当下教育知识的秩序格局。二是不同领域的主体行动及其行动关联:官员、专家、基层教师、出版人等等在改革过程中同驱并进,发展出了行动关联的多种模式,改变了各自的角色认知,并形成了关于教育知识新的理解和生产方式。
寻求教育知识变革本身足以构成教育界局部或集体的一场亢奋和紧张,这样一场由众多人员、人员背后的力量、力量背后的组织参与的集体行动,并由此所形成的一股合力对教育知识的作用或控制,使得“法定知识”不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现成的什么东西,而很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被争夺的领域”,一个“由多种多样的声音组成的多声部”,一个“永无止境、正在进行的权宜性结果”。由此,我们已经很难辨识出教育知识的形成究竟是缘自“谁”的力量?或者说最后究竟由“谁”说了算?
我想,我们需要换一种提问的方式——
三
对于教育知识通常的追问是:这是谁的知识?它是如何呈现的?它以什么形态呈现?即就已经成形的教育知识的内容和形式本身作推论式的意义再现,再现其内容背后可能深含的意识形态或阶层密码,再现其形式本身可能裹挟的控制策略或思维限度。这样一种推论式的再现与想象性的链接,很难说没有学术建构的成分在,它遭遇的最为尴尬的拷问是:教育知识与国家、阶层的这些关联是必然如此还是存有多种可能的?如果必然如此,那么揭示和探讨它的意义何在?(对一个必然如此的关联,即使揭示的再深刻,结果还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说了跟没说一个样。)如果存有多种可能,那么是什么原因或条件让这多种可能变成了唯一的现实安排?我们在哪里丧失或错过了获得另外一些可能的机会?很显然,如果只对作为结果呈现的教育知识进行分析,无论内容挖掘得多深,形式解析得多透,依然无法回答后两个问题,因此我想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对作为结果的教育知识进行分析,而且还要对作为过程的教育知识的命运加以呈现。
于是,我们的问题变成了:成为教育知识是如何可能的?
对“何以可能?”的追问旨在对更为复杂丰富、变动不居的关系与过程予以揭示。知识的变革过程把不同的社会力量拉入了教育知识建构的舞台,这些因素和力量不是一致性、统一性,而恰恰是混杂性、矛盾性甚至悖谬性,社会因素的作用与改革现实之间既有其问题与危机也可能同时包含着希望与新意,它们以一种近乎悖谬、充满张力的关系推动实践的展开。其本身可能包含着复杂的合谋关系、多重的利益驱动、充满裂隙的意识形态运作,留下了权力斗争、力量竞逐和妥协的痕迹,在这一过程中还可能将许多或潜隐或分离的因素通过改革显露并聚集在一起,并纠集起所有的目光和力量关注它、实践它,这样的紧张、矛盾比其他任何时候更加突显,尤其在中国——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一个农业、工业、后工业社会几乎同时并存的国家,有些问题在其他国家可能是在不同时代相继发生的,但在这里却碰撞、搅和到了一块儿,各种观念的冲突——保守与变革、政治与学术、信念与利益等等交织出了非常复杂微妙的纠葛与两难、分歧与突围,敲响了改革过程多变乖张且极不和谐的合奏曲。
对“可能性”的关注,或者确切点说这一提问方式的确立,还有着研究者更为深层的寻求与考虑。教育社会学意在转向背后、揭示真相,在对真相大胆的揭示和深刻的批驳中,紧随智识上的愉悦,一种危机也悄然而至:如何在彻底解构与无情批判的地方找到突围的可能?已有的教育社会学研究显得有些无奈和无力。赵汀阳对此曾有过极到位的表述:“指出错的,却说不出对的,这种流行的批评模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正确思维,尽管指出了真相,揭露了老底,但这种釜底抽薪的批评方式令人绝望,很少有人去思考关于真相的知识必须同时是对社会负责任的知识。”⑧这一提醒触到了痛处也说出了研究者的渴望。
事实上,在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广为传播乃至深入人心之后,要坚持并完成彻底的解构与批判已不再是什么难事,恰恰相反,需要思考的是在批判与解构了的地方巧妙地坚持思考并言说其可能性。虽然研究者仍然坚信,“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从来没有因为批判力量的出现而丧失,但却往往因为缺乏这种力量而堕入社会符号秩序既有的偏见之中。”⑨但研究者对“批判”本身却越来越怀疑:如果批判只是为了彰显已然成为现实的特性本身,把它们作为需要否定的特性加以强调,那么这就是批判吗?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层面的批判而不再继续深入,那么批判也很可能会成为一种障眼法,忽视了现实本身更为复杂变动的可能性,从而使人们丧失了从这些可能性中寻求突围的意识与动力,也很难为反思与解释当下的教育知识生产、实践提供一个新的建设性视角。
自从福柯火力集中地揭示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就从来不缺乏关于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洞见,却少有知识与责任关系的承担。正是在这里,研究者倾向于秉持一种解构与重构相互承继的研究使命。解构与重构——在研究者看来,并非互不相容的选择,而是互相接界的讨论领域。解构的旨趣即便在将其发挥至极处的德里达那里,也并非全然意味着否定。“我常强调解构不是‘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它是一种肯定,一种投入,也是一种承诺。”⑩社会因素在知识生产的作用中不仅有其否定性的力量,更有其肯定性的力量与生产性的一面。我们需要做的,恐怕正是在生机与虚妄、希望与异化相互缠绕的复杂情形中,将裹挟的虚妄与异化剥离并解构,将湮埋的生机与希望寻找并重构。在实践的展开中,在批判的漩涡中,我们需要多多少少把握住一些值得信赖的和为之感动的东西。
四
对“何以可能?”的追问必然引发关于各种现实的条件、机制与力量之建构过程的探讨,建构与其说是一种视角、一种观点、一种方式,不如说它需要一种实证的态度和方法。教育社会学学科诞生的原初用意,正是为了借助社会学的实证方法以增加教育问题探讨的客观性。研究者比较认同实证加分析的研究路向,事实性资料的搜集对于接近与理解复杂多变的改革实践,其必要性自不必多说,但研究者更对理论建构抱有企图,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不止于描述事实和现象,这是其一;其二,不满足于零散的分析和解释。在研究者看来,仅仅满足于对资料的意义阐释不是实证研究的根本目的,反而会沦为亚历山大所谓的“实证主义执信”(11),从而心安理得地放弃真正的理论努力,拒绝履行作为一门学科所应发挥的特定贡献。因此,需要梳理教育社会学已有的解释框架,并对其解释能力作出判断,如果事实与理论解释之间存在出入,研究者选择怀疑理论而相信事实,这不是说轻视理论,恰恰相反,这说明事实需要新的理论解释,由此提炼概念、完善解释框架或提供新的解释框架。理论思考的努力是希望将局部问题的考察拓展向更具一般性的问题,便以把握更大范围、更为一般的问题,以此完成实证研究“以小见大”、“小题大做”的研究旨趣。
对于资料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通常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从资料中发现问题”的“由实证到理论”的路向;一是“根据问题去引用资料”的“由理论到实证”的路向。(12)不过,在研究者看来,这样的区分过于将理论解释与资料证据割裂开了看。事实上,恐怕任谁都无法否认研究的过程本身是理论与资料之间相互碰撞、相互启发、相互催生的过程。如何对待资料与理论取决于研究的目的与定位:通过研究希望提供给大家的究竟是什么?不同的研究通常扮演不同的角色,是希望提出一个新的问题还是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呢?是提供一个新的解释逻辑还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呢?即便同是实证研究,研究最终提供什么,往往也会因研究者个人喜好与追求而大有不同:有注重过程展开、事件描述的,也有注重材料分析、理论阐释的;有深挖资料提供事实证明的,也有围绕问题提供解释框架的;有方向倡导的,也有体制批判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证研究远远超出了证实理论和检验理论这种被动的作用,而是如默顿所言,发挥并充当着一种更为主,动的角色:它引出理论、重整理论、调整理论、澄清理论。(13)在经验概推与宏大理论之间发展一种中层理论,以超越粗疏的经验主义,又不致放纵想象、悬空蹈虚。
事实上,不管是哪种类型的研究,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更清楚地看清改革的真实面目,从而指出改革的希望与可能的危机,而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改革行动、面对如此动机杂呈的改革参与者,试图从改革者的参与行动之外去理解改革事件的意义和改革行动的复杂性,大概是不可想象的。一是课程知识的社会构成因素本身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地域情境的差异需要重新分析,哪些力量与因素增加或消失了,哪些因素与力量发生了新的变化或重新组合等等;二是对不同社会因素或力量本身的相互作用的分析,即各种因素与力量并非分条缕析、分门别类地作用于法定知识的生成过程中,而是以一种变动不居、更为整合的方式作用其间,在不同情势、不同场域、不同行动者所裹挟的各种社会构成因素的作用力之间充满了无数冲撞点和不稳定中心,每一点都有可能发生冲突、斗争或是妥协、异化。教育知识只是知识的教育陈述,它根据不同的教育观念与行动建构。因此知识的相对性是在体性的规定了的,把论题延伸到社会层面,知识建构的参与性质在社会共同体中,表现为一种群体分化的知识运动形式。因此面对教育知识变革,教育社会学的迫切任务是要阐明各种改革的参与群体及其行为为何最终成了各种特定的教育知识安排。在改革的空间中伴随着行动的权力关系、力量关系、利益关系等等都将一一彰显出来。面对这一变动不居的现实,面对这一可理解与不可理解相互混杂结合在一起的改革过程,教育社会学不仅需要秉持“化熟为生”的经典研究使命,将可理解的深入挖掘,更要将不可理解的乱象变得可以理解,它需要把握问题意识、着力中国视野、采用实证手段。我想改革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将为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教育社会学者们可以以此为立足点在继新教育社会学之后留心作一次跳跃了。
注释:
①[法]米歇尔·福柯:《治理术》,赵晓力译,《社会理论论坛》1998年第1期。
②[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220页。
③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④Dale,M.Stalking a conceptual chaneleon:Ideology in Marxist studies of education.Educational Theory,1986,p.241.
⑤李宪堂:《先秦儒家的专制主义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⑥[法]埃哈尔·费埃德伯格:《权力与规则》,张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216页。
⑦具体研究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孙立平《作为制度运作与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辑刊》(港),冬季卷,1997年;吴思《隐蔽的秩序——拆解历史弈局》,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弗朗索瓦·于连《迂回与进入》,杜小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⑧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⑨李猛:《如何触及社会的实践生活?》,选自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125页。
⑩[法]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页。
(11)[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73页。
(12)张静:《“雷格瑞事件”引出的知识论问题》,《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年特辑2期。
(13)[美]罗伯特·金·默顿:《理论社会学》,何凡兴等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第1-3页。
标签:教育社会学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