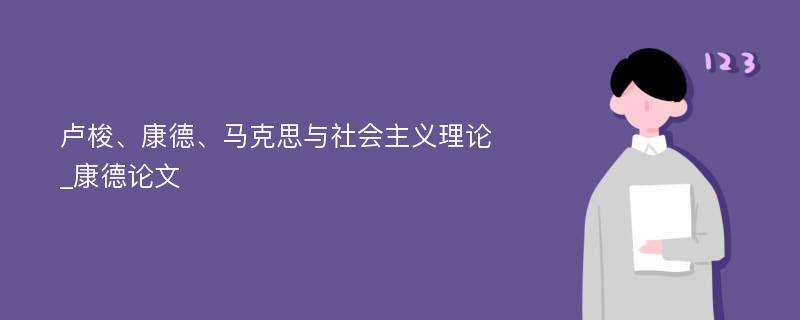
卢梭、康德、马克思与社会主义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卢梭论文,康德论文,马克思论文,社会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51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8)04-0019-09
一、引言:两种思想体系
在世界史上,两次大革命波澜壮阔,极大地震撼了人类心灵,史无前例地塑造了人类社会的精神面貌和政治面貌。这就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革命,这两次大革命孕育了两种思想体系: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两种思想体系画地为牢、势不两立,以致触发了东西方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意识形态之争,直至1989年以来苏联-东欧各国社会主义纷纷解体之后这种争论才告一段落。
两次大革命分别从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和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那里获取了灵感和动因。卢梭与马克思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两人都致力于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和规律,概括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结论,分别建立了一套石破天惊的政治思想体系,从而分别成为两次大革命的精神之父。
两种思想体系都着眼于现实的人的形象,并通过历史分析去追问人的起源: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自何处?毋庸置疑,人来自当时不同的社会境况,因此两种思想体系都洞察到了这个世界里的贫困、不平等和邪恶状态。由此出发,两种思想体系都意识到了人在这个世界里的困境;这是一个非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根本感受不到一种有人的尊严的、有价值的生活。
于是,两种思想体系便诉诸超越和升华,把人的边缘体验转变为人的理想形象,以此进行一种创造性的政治综合:在这个世界上,人应当走向何处?根据当时的社会境况和精神境况,两种思想体系都勾画了一幅未来社会的理想图景:未来社会是某种国家宪法的社会秩序状态,而这种社会秩序状态应当与人相称,能够保障人的尊严和有价值的生活。具体而言,卢梭(或康德)意义上的未来理想社会是个人充分自由的“人民民主”的公民社会或“世界公民社会”;马克思意义上的未来理想社会是社会充分正义的“无阶级社会”。
二、卢梭、康德的政治学说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提供了法国大革命的理论纲领,催生了《人权宣言》。在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中,卢梭开宗明义地写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中。”①人生而自由平等。因为自由和平等是人类的自然本性,是天赋的人权。在这个世界上,之所以有奴役,人成为法律和其他人的奴隶,是由于现代社会,是由于有了违反人类本性的社会关系,即私有制是社会罪恶的根源。卢梭的历史观一扫笼罩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的层层迷雾,揭示了一个普遍而简单的历史现象:人与人的关系史就是一部压迫史和奴役史。然而,五花八门的法律和神学教义却极力掩盖这一不平等、不自由现象,把人对人的奴役看作是合法的现象,甚至看作是神的旨意。
由此出发,卢梭揭示了一个简单而无可争辩的政治结论:“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前一样地自由。”②国家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协议。当个人联合成为一个国家时,他们的个人意志将服从普遍意志(“公意”)。普遍意志是不可转让的人民主权的基础和前提,是人民意志在真正的人民民主中的表现。卢梭提出“人民主权说”,意在表明合法性的惟一源泉在人民手中而不是在君主、贵族阶层或其他团体手中。人民的意志是惟一的法律。每一个公民既是立法者,又是法律的臣民。国家代表人民的普遍意志,主权属于人民,政府只是执行公意的机构,不是人民的主人。因此,在他看来,最自然、最合理的政府形式乃是平民民主政体。
那么,如何创立这样一个个人与全体相联合的国家呢?卢梭的回答是,通过心灵的呼唤:“自由、平等、博爱!”。这一呼唤后来成为法国大革命的革命口号,最终成为政治变革的理论纲领:废除现存的“社会关系”,根除少数人奴役多数人的不平等、不自由现象。从卢梭的“自由”(Freiheit)这一根本思想中,滋长出革命的民主思想体系。所谓“民主”(Demokratie)就是废除人奴役人的现象,以此保证一切人的权利平等的自由。
卢梭把“公民联合”看成是发展一切人的平等自由,保证个人“最大的自由”的必要手段,康德把卢梭的这一人民民主思想精确地表述为“民主原理”(demokratische Prinzip)。康德从卢梭那里继承了“人民民主”思想,但是他又通过新的法制国家学说,即“公民社会和世界公民社会”学说而超越了他的老师卢梭。康德的所谓“公民社会”(Buegerliche Gesellschaft)是共和制的民主社会。公民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尊重法律和守法。公民社会的功能是保障社会各成员的最大自由,同时确定这种自由的界限,以便最大限度地发展每一个人的自由。所谓“世界公民社会”是全球范围内无所不包的公民联盟或兄弟般的联盟,是根据理性秩序组织起来的一个伟大的、权利平等的社会。未来社会是“世界公民社会”,整个世界的目标是消灭战争,永久和平。
自由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的责任;言论自由是人民的神圣权利,是人类一切进步的必要条件。因此,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发现,在如何消除人的不自由方面,卢梭的现代天赋人权说也容易被误解:用一切人对一切人的统治来取代单个人对其他人的无限统治。因此,康德强调,一种自由的社会秩序应当建立在一种“公民社会”基础上,在这种社会中,自由不是受到任意的限制,而是通过“最精确地确定和保障个人自由的界限”来达到一切社会成员的“充分而权利平等的自由。”换言之,公民社会是按照民主原理安排社会秩序,因而自由本身受制于社会和国家,但社会和国家的前提是必须保证一切人的同一的自由。
卢梭强调“人民民主”(Volksdemokratien),完全有理由要求废除“个别人对人的奴役”,但他一味要求限制他人的相等的自由,根本不考虑如何建立一切人的“最大自由”。在康德看来,这种作法只关注自由的否定侧面而不关注自由的肯定侧面,其结果,按照这种说法,一些人不仅可以通过另一些人建立不平等和奴役,而且可以通过一切人(社会)来建立新的不平等和奴役。因此,康德的根本结论是,在“热爱自由的民主”(Freiheitliche Demokratie)这一前提下建立一切人最大可能的、权利平等的自由。
进言之,在康德那里,“热爱自由的民主”这一政治思想体系根源于人的双重现实倾向:一方面,“人具有一种要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另一方面,“他也具有一种强大的、要求自己单独化(孤立化)的倾向。”③因此,人既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又不能脱离社会,康德称之为“非社会的社会化”(Ungesellige Geselligkeit)。但是,人的“不合群性”(Ungesellige Eigenschaft)却是推动人类由野蛮进人文明的伟大动因。人的不合群唤起了人的全部能力,如虚荣心、权力欲和贪婪等,而这些倾向又孕育了围绕财富、名望、等级和统治的全部竞争、冲突和斗争。在康德看来,人与人的对抗贯穿着全部人类世界的发展,这种对抗是历史的“真正的运动性原理”,其作用堪称是赫拉克利特意义上的“万物之母”。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人性之中的全部优越的自然禀赋就会永远沉睡而得不到发展”。④
但是,当人类摆脱了自然的强制而迈向文明之后,人类应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呢?康德的回答是,要建立一个自由与秩序和谐一致的公民社会。“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起一个普遍法制的公民社会。”⑤因此,康德不仅要求废除人对人的奴役,而且要求保证每一个个人的最大可能的、权利平等的自由目标。不是寻求单纯的、空洞的自由本身,而是寻求“自由的辩证法”所引起的自由的秩序,亦即自由与秩序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为此,康德寄全部希望于尽可能完备地、合目的地发展人之中的“自然禀赋和精神力量”上。在他看来,个人的自由不是单方面的自由,而是相互的自由。围绕相互自由旋转的是一种人类学的自由辩证法,其实质是制定一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合法的“公民宪法”,以此保证社会所有成员的充分自由。在自由的秩序中,自由的辩证法能够最大限度地发展所有人的最大自由,从而避免了自由本身的毁灭。这种自由就是合目的地调整好的人的生存自由的“普遍法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的自由。自由的辩证法不仅把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联系在一起,也把个人的任意与他人的任意联系在一起。康德把自由界定为是“权利”(Recht)。那么,何谓权利?权利乃是义务的化身,而义务不是针对统治者而言,而是针对每一个成员,而且是同等地对一切人而言。人属于一个目的王国,而目的王国是一个其成员具有同等权利的共同体或共和国,其所依赖的基础是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人本身是尊严,但“自律性是人和任何理性本性的尊严的根据”。⑥
总之,康德政治哲学的主旨在于阐明建立在自由基础之上的国体,即公民社会。惟有在公民社会中,人类才有可能达到“自然的最高意图”,实现人的禀赋的全面发展。实际上,康德的公民社会就是今日人们耳熟能详的“民主”,或者通常所称说的“关于自由的民主”。
可以说,今日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均渊源于卢梭、康德的政治学说,亦即渊源于两人的“人民民主”概念和“公民社会”概念。像卢梭一样,康德也把国内公民宪法问题与外部国家关系问题结合起来,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单靠国内关系的民主程序是无法全面贯彻公民宪法的。因为“建立一部完美的公民宪法这个问题,有赖于国家合法的对外关系这个问题,并且缺少了后者前一个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⑦在“世界公民社会”的权利乌托邦中,康德勾画了世界范围内真正“有人类尊严的秩序”的蓝图。
康德充分意识到,暴力在人的本性中有着深远的根源,因此若不创造国外关系中的一种合法秩序,就无法实现国内关系中的公民宪法,也就无法保证每一个个人的最充分、最可靠的自由。正是由于暴力这一人类本性,人类作为单个的人无法长久地和谐共存,而是我行我素,沉湎于“野性的自由之中”,从而在某种合法的公民社会状态中必然出现一些“不受约束的自由状态的人”。那么,公民社会和国体如何才能确保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又能维护一切人的“伟大自由”的秩序呢?在康德看来,维持这种秩序的惟一途径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世界公民社会”:在人与人之间实行法制,在国与国之间实行协约制,从而摆脱自然状态,消灭战争。因此,康德的国体概念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标明国内关于自由的民主;另一方面标明世界范围内的关于自由的民主。换言之,他的国体概念既指明国内的充分而权利平等的合法的自由的状态,又指明一切国家之间充分而权利平等的合法的自由状态。通过区域性联合和全球联合,国体将渐渐地在外部国家关系中造成那种合法的自由秩序。康德把全球范围内的这种关于自由的秩序状态,称作“世界公民社会”。
对康德来说,通向全人类的、无所不包的合法的自由秩序状态并非必不可免,但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这种状态却是必不可少的。由于人的暴力本性,由于无休无止的战争,由于庞大的扩军备战,人类一次次被拖入破坏、倾覆、毁灭的边缘,这些可悲而惨痛的经验使得每一个国家开始用理性的眼光看待战争与和平问题,开始摆脱无视法律的野蛮状态而走向各民主的国际联盟。“这时候,每一个国家,即使是最微小的国家也不必靠自身的力量或自己的法令而只须靠这一伟大的各民族的联盟,只须靠一种联合的力量以及联合意志的合法决议。”⑧在这样的国际联盟中,战争应从人类事务中排除出去,“放弃野蛮人的那种野蛮自由而到一部合法的宪法里面去寻求平静与安全”。⑨
因此,康德认为,在世界上某种人类的理性状态不仅是“内部国家关系”的自由的民主状态,也是“外部国家关系”的自由的民主状态。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在热爱自由的民主的国家关系中,所有国家发现一种“平衡定律和一种联合的力量”,从而导致一种保卫国际公共安全的世界公民状态。“这种世界公民状态并不是任何危险都没有,从而人道的力量才不至于沉睡不醒;但同时它对于他们相互间的作用却又不是没有一条相等原则的,从而他们才不至于相互毁灭”。⑩
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中,康德表达了旨在结束迄今外部国家关系中“混乱”局面的政治意愿,即“世界的联合”,而这一意愿今天正在变成无限的政治行动。综观当今世界政治,至少在欧洲范围里,世界的联合正在变为现实,欧洲联邦或大欧洲的政治图景已经确凿不移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按照康德的理解,世界的联合是一条普遍的、人道的原理。按照这一原理,可以构想未来世界政治的宏伟前景:从欧洲的联合走向世界的联合、人类的联合。
像卢梭那里一样,在康德那里,民主政治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创造性的乌托邦,即一切人的最大而相等的自由的秩序,其实质是世界公民社会基础上的未来“国际国家”(Voelkerstaates)或“人类国家”(Menschheitstaates)。只有在世界公民社会中,自由的辩证法才能得到充分的展开,产生良好的效果,同样,只有在这种自由中,才能出现所有文明和文化的和谐发展,才能出现每一个个人之间,每一个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如前所述,康德寄全部希望于“人类自然禀赋”、“精神力量”的完备而合目的的发展上面。但是,在人类本性中战争和暴力有根深蒂固的因素,故迄今人类距康德意义上的真正的“人类秩序”状态还相距甚远。“在这最后的一步(亦即各个国家的联合体)出现以前,人性就得在表面幸福的欺骗假象之下忍受着种种最无情的灾难,……卢梭就不无道理地要偏爱野蛮人的状态了”(11)。
于是,法国大革命的包罗万象的自由伦理和激情就汇入惟一不二的历史目标:一种热爱自由的世界公民社会状态。然而,这是人类远景目标,人类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完成这一目标,而只能持之以恒,一步步地“接近”这一目标。因此,未来人类的发展,不仅需要所有社会-技术层面上的变革,还需要人类自身的道德-良知的根本转变。用康德的话来说,人要成为新人,只有通过一种类似于新创造的“再生”,以及一种灵魂的改造。这样,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思想体系既是西方世界的伦理和激情,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它为人类指明了一条现实的理想社会之路,即如何接近和实现一种热爱自由的世界公民社会。
三、马克思的“人的社会形式”
像卢梭一样,马克思也直面人的现实形象,通过探求人的社会经济关系来揭示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通过分析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马克思得出了一条公正而客观的历史结论:迄今为止的阶级社会,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一部剥削史。
在古代奴隶社会,千百万奴隶在法律上被剥夺了人的称号,在中世纪封建社会,千百万农奴和依附农失去了人身自由,而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千百万无产者则成了“无家可归的商品劳动力”。在考察社会经济关系中,马克思同样揭露了形形色色的法律思想、神学和宗教的虚伪性,作为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这类意识形态竭力把剥削现象加以合法化,或者把它美化为“神的旨意”。通过分析人剥削人的社会经济关系,马克思也得出了一条公正而客观的政治结论:“代替那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为此,必须废除剥削制度,建立无阶级社会,以此保证“最大限度地发展每一个个人的能力”,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一个个人的需要”。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这两大未来社会的价值目标。
因此,马克思意义上的“新的社会”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彻底废除人对人的经济剥削,使人成为“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13);另一方面,通过公正合理的社会关系最大限度地发展每一个个人的能力,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一个个人的需要。这是一种否定-肯定的辩证法。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概括了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着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4)众所周知,费尔巴哈曾经致力于宗教的世俗化,用人类学还原神学,进而揭示了基督教的本质,提出了“人是神的最高本质”的命题。与此相对照,马克思则致力于人类解放和无阶级社会,揭示了人的本质,提出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命题。就像费尔巴哈的宗教人类学一样,马克思的无阶级构想也被后人嘲笑为是纯粹的“错觉”,甚至被诋毁为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然而,马克思确信,无阶级社会不仅是人类的最高理想,也是必将到来的人类的“自由王国”。因为在他看来,人类所寻求的社会制度无非是使每一个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制度,也就是说,在这种社会制度中,每一个个人的能力应当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每一个个人的需要应当得到最充分的满足。进言之,这样一个人的“自由王国”就是总体的“人的社会的社会人类”(gesellschaftlichen Menschenheit der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
然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表述了一段令许多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大跌眼镜、困惑不解的话:“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15)那么,人的发展目标是什么?人的社会形式是什么?在马克思那里,人本身是对象性的存在物,所以,“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是人的自然界”。人的发展的目标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6)对于人的社会来说,这种统一意味着通过人的自我实现,也就是通过充分发挥人的自然生命力而扬弃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由此出发,马克思预先推定了一种“人的社会的形式”,即社会主义社会,以此保证每一个个人能力的最充分的发展,同时,保证每一个个人需要的最充分的满足。
那么,如何通向这一“值得生活的社会”呢?马克思的回答是,废除人对人的经济剥削,走向人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在批判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中,早期马克思把这条革命道路上升为革命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及其规律中,后期马克思则另辟蹊径,构想了“无产阶级专政”(17)这一过渡时期的社会形式,用以废除迄今为止的所有经济剥削关系。
但是,实践证明,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的设想一开始就遇到了诸多困难、挑战和考验,以致始终处于悬而未决状态之中。原因种种,归结起来有两条:第一,迄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诊断和预测并未得到应验;第二,前苏联-东欧各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完全背离了马克思本人的“人的社会的形式”的设想。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阐述了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指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并且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关系,以及阶级力量消长变化的规律,从而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私有制的丧钟敲响了,“剥夺者被剥夺”。应当承认,在早期资本主义时期,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一分析在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崩溃论”低估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适应能力和调节能力。事实上,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制度非但没有走向崩溃,反倒处于空前的繁荣阶段;其次,马克思没有料到,资本主义进程通常不是导致社会革命,而是导致社会演变和改良。例如,当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总体上趋于平缓,并且朝着劳资合作方向发展。这一“非正统的运动方式,不仅阻止了工人生活的贫困化”,也会大幅提高一般生活标准;再次,马克思没有充分考虑到,通过有效的制度干预,资本主义不仅能够应付生产过剩危机的出现,而且通过目标明确的生产调控,保证生产和消费同步增长。这一点恰恰说明了,为什么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行将灭亡的预测迄今始终没有得到应验;这一点也说明了,为什么恩格斯后来对“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做出了明确的修正:“‘无产者人数和贫困越来越增长。’这样绝对地是不正确的。工人的组织,他们的不断增强的抵抗,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造成某些障碍。而肯定增长的是,生活的无保障。”(18)然而,今天看来,恩格斯当年的预言,即“不断增长的生活的无保障”也已经失效。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劳动立法制度,并且采取逐步措施增加就业,减少失业。
在纯粹资本主义制度中,资本积聚通常造就“无产阶级”这一“未来的革命者”,并生产这一社会制度的特有的“掘墓人”。与此相对照,在前苏东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中,源于国家未支付劳动的、变本加厉的资本积聚同样造就“未来的革命者”,同样为这一制度准备“掘墓人”。换言之,这种变相剥削,一方面导致“自我奴役”的人;另一方面导致“自我奴役”的社会。一个自我奴役的人,实际上就不是本质上的人,一个其实际存在不符合其人的本质的人。同样,一个自我奴役的社会,就是一个其实际存在并不符合人类社会的真正本质的社会。在这种自我奴役的社会中,马克思所构想的人的社会的两大目标——应当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个人能力的最充分的发展,同时应当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个人需要的最充分的满足——消逝得无影无踪。事实上,在这一类苏东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诸机构既不代表单个成员的真正利益,也不体现社会本身的真正利益,而仅仅代表“新阶级”的特殊利益,其结果,造成两种严重的社会成果:第一,社会两极分化。少数经济、政治、知识新贵垄断和瓜分社会绝大部分社会财富,而大多数“普通百姓”、“普通劳动者”,即“现实的人”则被边缘化或淡出社会进程;第二,产生各种制度性、机制性、组织性腐败。在前苏联-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国家中,这种两极分化、腐败现象日积月累,愈演愈烈,最终成为其衰亡的直接导火线。
前苏东社会主义解体的历史教训表明,如果缺乏民主和舆论监督,即使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也必然导致一种新的剥削和奴役形式,即个别人通过社会来进行新的剥削和奴役。反之,如果缺乏社会正义和自由原则,即使是按照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也必然导致一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和奴役。
前苏东社会主义解体的历史教训表明,夺取政权后,这些国家踌躇不决,错失了转机,始终没有全面贯彻社会主义与民主原则,在民主领域与经济领域,始终没有兑现马克思“人的社会”意义上的两大目标:最大限度地发展每一个个人的能力,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一个个人的需要(19)。
前苏东社会主义解体的历史教训表明,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必须修正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理论,废除僵化过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引入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Sozialische Markwirtschaft)体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应是多元的、开放的,其中不仅包括公有经济,也包括独资经济、合资经济、混合经济等。与此相适应,必须调整生产关系,发挥经济杠杆作用,广泛采用物质利益原则、竞争原则,全面引入管理原则、企业生产-利润原则等等。
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建立在民主与社会公正双重原则基础上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始终面对双重意义上的蜕变危险:第一,新的奴役危险,即单个人通过社会全体来统治被解放的人;第二,新的剥削危险,即单个人通过社会全体来剥削被解放的人。
如上所述,卢梭、马克思都要求废除单个人对人的政治奴役和经济剥削,但二人都反对用新的政治奴役和经济剥削来代替旧的奴役和剥削。卢梭早就指出,在按照民主原则建立起来的新社会中,单个人能够以“全体的统治之名”,照旧自由地奴役被解放的人。同样,马克思也曾指出,在按照民主原则建立的新社会中,单个人能够以“全体的共同劳动”之名剥削被解放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原则和社会公正原则就会走向反面:民主会导致最大的不自由,社会公正会导致最大的不公正。实际上,这种所谓“民主”和“社会公正”原则与真正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完全背道而驰。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倒错现象?究其原因,在民主原则中,如果滥用社会秩序这一政治原则,那么每个人的自由的界限就不再受制于“人人自由”这一绝对界限,相反,自由的程度完全受制于社会的恣意妄为。其结果,在这种所谓“民主国家”中,一切真正民主的革命冲动都归于丧失,以致彻底否定下述民主原则:最充分而权利平等地发展每一个个人的自由乃是一切经济的、社会的、法律的和国家关系的发展目标。
马克思认为,归根结底,共产主义仅仅是到达一种“社会人类的人的社会”的必要手段,而“无阶级社会的自由王国”是通达“人的社会”的必由之路。因为只有在自由王国中,才能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力的最充分、权利平等的发展,才能保证其个人需要的最充分、权利平等的满足。因此,想要实现人的社会这一理想社会,就必须调控生产,至少要保证与个人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消费质量,还必须从质和量上保证个人物质-精神上的需要。在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经济发展与改善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经济“自由化”(Liberalisierung)和“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目标设定,这方面,社会主义的“公司”、“托拉斯”、“康采恩”等便是例证。一旦社会主义能够把“自由王国”的理想充分地、权利平等地付诸实施,就能最大限度地发展每一个个人的能力;一旦把“无阶级社会”的设想充分地、权利平等地付诸实施,就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一个人的个人需要。
从青年时代起,马克思就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深远影响,致力于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批判,要求废除一切人剥削人的经济关系,同时要求废除一切人奴役人的社会关系,建立一个没有奴役和压迫的“人的社会”。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中,马克思满怀激情地写道:“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主张,从而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0)但是,在此马克思所关注的不是一个被剥削的人,而是一个被奴役的人,不是一个忍饥挨饿的、穷困潦倒的人,而是一个受屈辱、被蔑视的人。因此,他的“新人道主义”或“人道的社会主义”这一绝对命令从一开始就不是关涉人的幸福(吃喝穿住行),而是关涉人的尊严,即摆脱奴役、侮辱和蔑视,成为一个自由、自信和有安全感的人。废除一切奴役关系,这就是青年马克思最初的关于“民主”的绝对命令。
1932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发现后,“社会主义”理论的起源和最初含义的讨论被置于新的基础之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总结性地写道:“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1)因此,在青年马克思那里,人们发现,社会主义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也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不实现民主,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不实现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民主。
四、结语: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
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了“社会公正”(soziale Gerechtigkeit)原则。尽管革命胜利后,由于斯大林-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背离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没有到达马克思所理想的“人的社会”的彼岸,最终导致全面危机,苏联国家解体。与此相对照,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产生了西方民主,孕育了西方世界的自由国家形式和社会形式。尽管这种民主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人类历史上毕竟第一次确立了“民主原则”(demokratische Prinzip)。
根据社会公正原则和民主原则,人类将继往开来,致力于康德世界公民意义上的“世界秩序”这一崇高目标,即谋求一切人最充分的、权利平等的个人自由,同时尽可能保障这种自由的界限,以便最大限度地发展每一个人的个人自由。
历史是人类自由的发展,人的天职就是实现其自由的本性。但是,“人人自由”这一民主原则的根本保证是法治国家和宪法,因为只有法制国家和立宪民主才能保证一切人的自由。正如康德所述,人的最充分而权力平等的自由不仅是“自我目的”,也是实现那个“最高人类目的”的手段。正如在人类全体中一样,在每一个个人那里,所有“自然禀赋”和精神力量都是通过斗争和竞争来达到“完备而合目的的发展”的,而这种斗争和竞争既表现在每个人的物质生活需求上,也表现在每个人的精神生活需求上。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这一“自由竞争”(Wettst reit der Freiheit)原则是一种动态的发展原则。一方面,自由竞争原则构成全部人类社会“经济基础”的基础:个体为物质生活需要展开自由竞争,其形式千变万化,但其宗旨是“物质利益”;另一方面,自由竞争原则构成人类社会“精神上层建筑”的基础:在充分而平等的社会秩序下,各种观念和理想得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断推动个体的精神生活需要,其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宗旨是惟一的、开放的“精神事业心”(immaterille Engagiertheit)。在充分发展和谋求人的自然禀赋和精神力量中,一个民主的、开放的多元社会不仅能够成为最大限度地推动文明进步的杠杆,而且能够成为个人和全人类进步的杠杆。
如果说,“民主原则”奠定法制国家的基础,为每个人最充分地、权利平等地发展个人的能力提供了形式上的平等机会,那么“社会公正原则”则奠定社会福利国家的基础,为每个人具体地实现个人自由提供了内容上平等的理念。根据“社会公正”原则,每个人都享有同等机会,从而能够最充分、权利平等地发展个人的身心能力,满足个人的身心需要。因此,法制国家和公民社会是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在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遵纪守法,实现人权,以此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在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多元化,实行市场经济,即国家对工商业实行控制而非实行国家所有制,以此保证经济增长和公平收入;在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普遍而持久的道德教育,促进公民的道德转变和良心转变,以此保证一种伦理的理想世界。
自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以来,“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两大原则渐渐深入人心,业已成为文明社会的政治、经济规划和行动的基本原则。作为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根本尺度,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是一种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社会公正没有个人自由是空的,个人自由没有社会公正是盲的。个人自由只有在社会正义中才能得到保障,社会公正只有在个人自由中才能得到实现。惟其如此,人类才能不断接近一种有人类尊严的、值得生活的社会;惟其如此,人类才有希望迈向一个热爱自由的、无阶级的未来世界公民社会。
总而言之,充分发展每一个个人的个人能力,充分满足每一个个人的个人需要,这正是马克思“人的社会”的核心思想。在实现这一伟大思想中,人类也许永远达不到总体个人自由和总体社会公正这一终极价值状态。也许,人类永远达不到这一终极状态。但是,我们相信,在未来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下,人类全部的原始禀赋必将得到充分发展,人类将获得非凡的创造能力、发明能力和技术组织能力。正是由于这一远大理想和希望(22),人类并非悲观绝望,而是悉力以赴,不断逼近这一终极价值状态。
注释:
①②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8页,第23页。
③④⑤⑦⑧⑨⑩(11)(22)Kant,I.,Schriften zur Geschichtsphilosophie,Stuttgart/Reclam1999,S.25f.,S.26,S.27,S.29f.,S.30,S.31,S.32,S.32f.,S36.
⑥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9页。
(12)(15)(16)(2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3页、第88页、第79页、第13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
(14)(17)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第21页。
(18)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0页。
(19)关于苏联衰亡的历史教训的分析,参见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57-881页。
(20)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标签:康德论文; 卢梭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世界公民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政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哲学家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