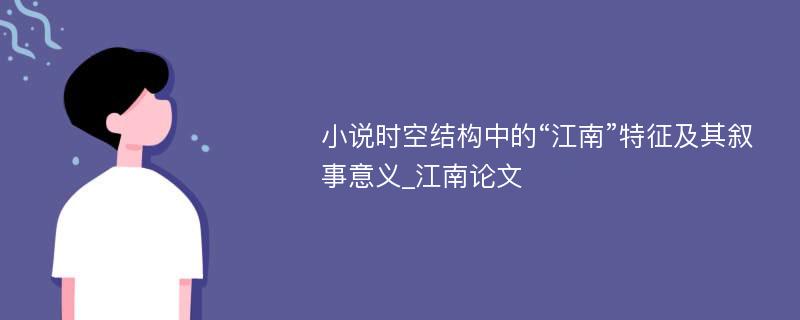
话本小说时空构架的“江南”特征及其叙事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本论文,江南论文,构架论文,特征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8)01-0135-07
话本小说虽然渊源较早,但其迅速兴起却主要是在南宋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以后,特别是到了明代,江南真正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它才进而走向全面成熟。生活在江南的话本小说家基本依据江南的地理特点、地质构造以及人文景观来构架小说时空;即使述及江北,也往往参照扛南时空“版本”进行,这就使得这一文体带有鲜明的“江南文学”性质。
一、江南人文地理叙述及其“背景”意义
从作家队伍来看,话本小说的作者大多为江南人。如对话本小说勃兴做出最突出贡献的是编辑“三言”的江南长洲(今苏州)人冯梦龙,而且他曾经多次游历过浙江,主要生活在江南。另一位高手是撰写“二拍”的浙江乌程(今湖州)人凌濛初,他30岁时便寓居南京,虽因功名原因曾一度进京,但大半生定居江南。再后,编选《今古奇观》的抱瓮老人,其生平虽难考定,但可以推断他“大约为明末苏州人”[1]514。此外,以话本小说创作扬名后世的还有,撰写《型世言》的陆人龙、撰写《西湖二集》的周楫,以及撰写《欢喜冤家》的“西湖渔隐主人”等,都是杭州人或生活于西湖。《三刻拍案惊奇》(一名《幻影》)的作者或编辑者,从其“梦觉道人”、“西湖浪子”的署名来看,他(或他们)可能也是浙江籍的文人,起码旅居过西湖。《一片情》的作者虽然也没有着落,但通过卷首序后署“沛国樗仙题于西湖舟次”来看,应当曾旅居西湖。清代,创作《无声戏》、《十二楼》的话本小说家是兰溪(今属浙江)人李渔,其足迹也主要来往于风花雪月的江南,而且还曾客居杭州十年。
从故事的取材角度来看,话本小说从不同层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情,既包含着丰厚的人文底蕴,又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首先,历史上与江南有关的名人的故事被不断地搬弄出来。据玄烨《御制诗集》卷十载,康熙南巡时曾有《示江南大小诸吏》诗云:“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这里所谓的“江左”,即江东,指长江下游包括安徽一带,相当于人们通常所谓的“江南”。关于诞生于江南这片土地上的历代枭雄,人们颇有话要说。如,五代时期的吴越王钱镠是江南一带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其发迹变泰的经历始终是浙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喻世明言·临安里钱婆留发迹》大约据《西湖游览志余·帝王都会》等记载写成,细致地向世人讲述了钱塘王“昔年盐盗辈,今日锦衣人”的人生变迁,并流露了赞赏仰慕之情,是“三言”中以“发迹变泰”为主题的系列故事的压卷之作。《西湖二集》的第一篇又是《吴越王再世索江山》,既显出了浙江人对本乡人的偏爱,又用他们心目中的“大人物”装点了这部话本小说集的门面。《西湖佳话·钱塘霸迹》再一次把这位吴越王的故事搬弄出来,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这位杰出人物的印象。同时,浙江历史的通俗化书写还集中于几个影响极大的文人墨客身上。早在唐代,著名的大诗人白居易来到这里做刺史,“三言”、“二拍”六次以白乐天为话头,引出故事,如《醒世恒言·独孤生归途闹梦》提到白居易到杭州府做太守之事;《警世通言·钱舍人题诗燕子楼》将白居易与关盼盼交往的事和后来吴越王的后代钱易勾连起来,寄托的当是怀念先贤的幽情;《拍案惊奇》卷二十八开篇也是先用白居易的两首诗以及当年他与杭东观察使的逸闻做“话引子”的;而《西湖佳话·白堤政绩》则专门叙说白居易治理西湖河堤的故事。到了宋代,浙地又来了一位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苏轼,“三言”、“二拍”约20次引其诗或说其事,如《喻世明言·史弘肇龙虎君臣会》的“入话”就是从苏学士两次到杭州说起的。在此之前,浙江的都市繁华、市民阶层的壮大曾经吸引过一位名叫柳永的市井词人,“三言”、“二拍”也有五篇引其词或书其事。如《喻世明言·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就引用这首词来铺叙渲染“杭州好景”,为写一对青年男女的恋情故事作铺垫。柳永在杭与妓女交往密切,《清平山堂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以及由此改编的《喻世明言·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等小说直接演叙了这种充满市井情调的风流趣话,才子柳永自都城汴京来到余杭县上任,他与众名妓的浪漫风情只有在当年江南这样相对开放的环境才显得谐和。
其次,宋元之后的“江南人”故事被现场性地陆续编写出来。如取自现实题材的《喻世明言·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写浙江籍忠臣沈鍊以及其子沈小霞与朝廷奸臣严嵩父子的斗争,其时空构架以江南为主。其他话本小说也往往采自江南民间传说。如南宋杭州地方一直流传着一个著名的无头案故事,称为“沈鸟儿画眉记”,宋人话本即有演述,明朝人郎瑛将其记载在《七修类稿》里。其影响之大,以至于杭州人俗话甚至用“沈鸟儿”当作“祸根”的代名词。冯梦龙将其改写而收入《喻世明言》,定名为《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使故事中的江南时空更加明朗具体。《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所叙述的故事为明代实事。据说男主人公王景隆的原型名王舜卿,河南人,《情史》有记载[2]313,但冯本中却将王景隆改为“正德年间,南京金陵城中”王家的三公子。在此,大约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和时空构架的得心应手,冯梦龙将地点作了“改北为南”的技术处理。
为了进一步说明江南人在话本小说中的具体情形,下面我们姑且以有关浙江的故事为个案作分析。在大量关于浙江的虚构故事中,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当然还是“浙人在浙”的故事,其故事时空多为地理实景。同时,“外人入浙”和“浙人外流”的故事也有许多。“外人入浙”故事的主人公大多及时“适应”了环境。如《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那个小卖油郎秦重以及花魁娘子莘瑶琴,都是在战乱中流落到杭州的“外来户”,他们的活动空间被安排在西湖周围。那些“浙人外流”故事的主人公则把时空从浙江牵引到异地,如《喻世明言·杨谦之客舫遇侠僧》写杨谦之与侠僧交往于家乡浙江,而得他安排的侠女一路帮助。况且,以浙人为代表的江南人在外地的声誉也是众口皆碑的,如“二刻”《赠芝麻识破假形,撷草药巧协真偶》中的浙江客商蒋生就在汉阳被一个店主马少卿看中,欲聘他为女婿,当蒋生因自己“是个商贾,又是外乡”心怀顾虑时,开明的马少卿回答:“江浙名邦,原非异地。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这样,江浙时空辐射到异地他乡。
宋元以后,人杰地灵、风景秀丽的江南培育了一大批市井文人,他们依托于江南人文地理优势,面向说不完的江南,推出了一批又一批话本小说杰作,其时空构架自然带有江南时代感和现场感。
二、江南节日游赏叙述及其“时机”意义
虽然中华民族的几大传统节日,如“元夕”节、“清明”节、“端阳”节、“七夕”南北共有,但风俗却不尽相同。相对于江北人过节重视伦理性的祭拜祖先或神灵而言,江南人过节更多地借机从事休闲性的“游赏”。此外,江南还有“观潮节”这样的特殊节日。话本小说在叙述中,特别注意抓住江南人的节日“冶游”大做文章,使之成为各类故事赖以展开的“时机”性时间刻度。
在江南,人们格外看重一年一度的“元夕”灯市。《武林旧事·元夕》条记载,杭人非常重视元夕节的游赏活动,“灯市”前后要延续几天时间,文化气息极为浓厚。同时还说:“山灯凡数千百种,极其新巧,怪怪奇奇,无所不有”;“至节后,渐有大队如四国朝、傀儡、杵歌之类,日趋于盛,其多至数千百队。……终夕天街鼓吹不绝。都民士女,罗绮如云,盖无夕不然也”[3]30-31。这种火树银花的热闹场景自然而然地为男男女女们浪漫的爱情营造了温馨的氛围。如《喻世明言·张舜美灯宵得丽女》的故事就发生在上元佳节的“杭州好景”之中。第一年灯夕,男女邂逅触发恋情,相约私奔失散;“又逢着上元灯夕”,勾起张舜美的思念之情,因而吟诵秦学士(今考定为欧阳修)的《生查子》词寄托感情,让世俗主题的小说去亲和风流文人的诗意,雅俗共赏。又如,《警世通言·蒋淑真刎颈鸳鸯会》写男女偷情,当事人做出了“取便约在灯宵相会”的决定,也把时间安排在那个相对自由的特殊时刻。通过比照,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所描述的“试灯”景象和《武林旧事》的记载江南元夕基本吻合。
在清明节,江北人多保持扫墓习俗,江南人往往借机外出踏春游赏,这在文人笔记和小品中多有反映。明人谢肇淛《五杂组》说:“北人重墓祭,余在山东每遇寒食,郊外哭声相望,至不忍闻。当时使有善歌者,歌白乐天《寒食行》,作变徵之声,坐客未有不坠泪者。南人借祭墓为踏青游戏之具,纸钱未灰,舄履相错,日暮,墦间主客间,无不颓然醉倒。”[4]23《武林旧事·祭扫》条说:“清明前三日为寒食节,都城人家,皆插柳满檐,虽小坊幽曲,亦青青可爱,大家则加枣固于柳上,然多取之湖堤。……而人家上冢者,多用枣锢姜豉。南北两山之间,车马纷然。而野祭者尤多,如大昭庆九曲等处,妇人泪妆素衣,提携儿女,酒壶肴罄。村店山家,分馂游息。至暮则花柳土宜,随车而归。”[3]40明人张岱《陶庵梦忆》云:“越俗扫墓,男女袨服靓妆,画船箫鼓,如杭州人游湖,厚人薄鬼,率以为常。”[5]17张翰《松窗梦语》也说:“阖城士女,尽出西郊,逐队寻芳,纵苇荡桨,歌声满道,萧鼓声闻。游人笑傲于春风秋月中,乐而忘返,四顾青山,徘徊烟水,真如移入画中,信极乐世界也。”[6]137江南人的清明游赏风俗更是为话本小说提供了生发故事的“时机”。早在《清平山堂话本》中,《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西山一窟鬼》等故事就以清明节踏青、祭祖等风俗作为故事的引子。在“三言”、“二拍”中,以“清明”为时间刻度展开故事者大约有27篇,数量特别可观。如《喻世明言·明悟禅师赶五戒》的“入话”写洛阳饱学之士李源与慧林寺僧圆泽交好,圆泽圆寂时与李相约再世在杭州相见。十年后,“源因货殖,来到江浙路杭州地方”,目睹的景象就是:“时当清明,正是良辰美景,西湖北山,游人如蚁。”小说家在利用清明这一游赏性的时间刻度来展开故事。当然,清明前后的祭扫活动以及踏青游春客观上也为男男女女的艳遇提供了方便。正如刘勇强先生所指出的,“与春情勃发相关”的清明节这一时间刻度的设置是情爱故事赖以产生的“美好季节”[7]70。《警世通言·乐小舍拚生觅偶》写多年未能谋面的一对情侣终于在这一特殊时间里迎来了见面之机。“时值清明将近,安三老接外甥同去上坟,就遍游西湖。原来临安有这个风俗,但凡湖船,任从客便,或三朋四友,或带子携妻,不择男女,各自去占个山头,饮酒观山,随意取乐。”这里写到男子刚刚跟随父亲坐定,那里就写女方出场。清明这一特殊时间加速了他们恋情的进程。另外,较好地使用清明这一时间刻度的小说尚有《喻世明言·众名妓春风吊柳七》、《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中的《孔淑芳双鱼扇坠传》以及余象斗《万锦情林·裴秀娘夜游西湖记》等。可见,在话本小说中,江南清明多被当作特殊时间刻度来牵引出“奇奇怪怪”的故事。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端午节”本来就形成于南方,因而自然令江南人特别看重。在这一天,杭人多开展一些驱除“毒虫”以及禳除灾邪的活动。届时,“道宫法院多送佩带符箓。而市人门首,各设大盆,杂植艾蒲葵花,上挂五色纸钱,排饤果粽。虽贫者亦然。湖中是日游舫亦盛,盖迤逦炎暑,宴游渐希故也。俗以是日为马本命,凡御厩邸第上乘,悉用五彩为鬃尾之饰,奇鞯宝辔,充满道途,亦可观玩也。”[3]42“三言”、“二拍”以“端午节”为故事时间者也至少有六篇。如《警世通言·陈可常端阳仙化》就将主人公的生日设置在五月五日的端阳节,然后,这一时间刻度随时出现在主人公生活的各个阶段的关键时刻:出家为僧而联想到历史上生于端午的悲剧人物;在吴七郡王端午入寺斋僧解粽子的时候,因诗写得好而受恩宠;最终因别人诬陷而大彻大悟,在五月五日圆寂之前写下《辞世颂》:“生时重午,为僧重午,得罪重午,死时重午。”无独有偶,同书的《蒋淑真刎颈鸳鸯会》也通过“端午节”生发故事,作者让浙江杭州府武林门外乡村中的那位淫荡的蒋淑真和她的性伙伴在五月初五来了一场鸳鸯会,她的丈夫张二官趁机将他们杀死。这本来似乎是事出偶然,但作者却又补叙说,与蒋有性行为而先死的两个人物曾经在蒋卧病时说:“五五之间,待同你一会之人,假弓长之手,再与相见。”这就给这场冤冤相报的故事增添了“祸福未至,鬼神必先知之”的神秘感。
除了“元夕”之外,较有地方特色的江南“七夕”也往往被话本小说家用作情节展开的特殊时间刻度。《武林旧事·乞巧》说:“妇人女子,至夜对月穿针。饾饤杯盘,饮酒为乐,谓之‘乞巧’。及以小蜘蛛贮盒内,以候结网之疏密,为得巧之多少。小儿女多衣荷叶半臂,手持荷叶,效颦摩睺罗。大抵皆中原旧俗也。”[3]43这说明杭州女儿对这一节日特别珍爱。话本小说对此也多有表现。《西湖二集》中的《李凤娘酷妒遭天谴》中间穿插写道:“杭州风俗:每到七月七巧之夕,将凤仙花捣汁,染成红指甲,就如红玉一般,以此为妙。”这不仅与《武林旧事》记载的杭人重视“七夕”的习俗相佐证,而且还丰富了它没有涉及到的内容。在“三言”、“二拍”中,至少有六篇小说以“七夕”为叙事的时间刻度。如“二刻”《硬堪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着芳名》写台州太守唐仲友在七夕开宴招待宾客,其友谢元卿让著名歌妓严蕊即席赋诗。他们饮酒娱乐,极为欢快。不料,后来此事竟成为朱熹打击异己的把柄。小说写朱熹参奏唐仲友“酷逼娼流,妄污职官”,挑起事端,基于他臆测女儿节必定发生男女欢爱。于是,“七夕”引发了一场政敌之间的较量,同时为严蕊“受刑”埋下了祸根,发挥了叙事功能。
另外,话本小说对江南仲秋节后独有的“观潮节”也多有述及,仅“三言”、“二拍”即有三次写到这一节日的故事。关于古老潮神的故事,在浙江地区广为流传,并形成一种迎潮赛会风俗。《武林旧事·观潮》:“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日至十八日为最盛。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而豪民贵宦,争赏银彩。江干上下十余里间,珠翠罗绮溢目,车马塞途,饮食百物皆倍于穹常时,而僦赁看幕,虽席地不容间也。”[3]44-45可见当时观潮的盛况。《警世通言·乐小舍拚生觅偶》的“入话”在讲述了钱塘江的来历后,又不厌其烦地用了一段文字来写“观潮”的情景:
每遇年年八月十八,乃潮生日,倾城士庶,皆往江塘之上,玩潮快乐。亦有本土善识水性之人,手执十幅旗幡,出没水中,谓之弄潮,果是好看。至有不识水性深浅者,学弄潮,多有被泼了去,坏了性命。临安府尹得知,累次出榜禁谕,不能革其风俗。
作者叙说这段文字绝非仅是为了阐释这种风俗境况,而是为了正文讲述一对青年男女的恋情故事作充分的场景铺垫。正文就是在这一场景铺写的基础上展开,而其至关重要的环节就是男子拯救了落水的女友,打破了女方父母在场的妨碍,从而使得这桩在当时很难实现的恋情最终得以告成。另如《喻世明言·任公子烈性为神》写生活在临安府城清河坊南的任珪,其妻与前情人周得在八月十八观潮日偷情,又在元宵日来相约,引发了任氏家庭一系列的误会和冲突。
杨义曾经指出,中国作家喜欢把节日“视为人类与天地鬼神相对话,与神话传说信仰娱乐相交织的时间纽结”,来发挥“独特的时间刻度”的叙事作用[8]169-171。话本小说中的时间设置与江南的风俗民情密切相关,作者借助这些风俗资料的牵引,既再现了江南一带的风土民情,又敷演出许多饱含人文色彩的故事。
三、江南水乡地貌叙述及其“场景”意义
从地理意义上讲,江南湖泊遍布,河道纵横,故而被定性为“水乡”。水上交通,无非有二:船与桥。唐代诗人杜荀鹤《送人游吴越》说:“夜市桥边水,春风寺外船。”可见,横跨的“桥”与穿梭的“船”构成一幅幅特有的江南水乡画卷。话本小说的江南品性,突出表现在其空间构架带有鲜明的水乡特点。即使间或触及江北,身居江南的话本小说家们也往往喜欢选择那些“江南化”的风物去写,如东京的“樊楼”、“金明池”,都带有江南“水乡”风味。
(一)桥边故事何其多。经检索,“三言”、“二拍”两部小说集涉及“桥”的作品大约80多篇。由于江南多水系,故而“桥”成为一道道亮丽风景,也成为话本小说空间营造的经典场景。
谢肇淛《五杂组》说:“江南无闸,江北无桥。江南无茅屋,江北无溷圊。南人有无墙之室,北人不能为也;北人有无柱之室,南人不能为也。北人不信南人有架空之楼,行于木杪;南人不信北人有万斛之窖,藏于地中。”[4]71虽然这里关于“江北无桥”的说法不合事实,但却指出了“江南多桥”的“水乡”特点。桥周围多为人口聚居地,柳永[望海潮]说古城杭州:“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桥边多为空闲地带,便于商业经营,故而店铺林立,人来人往,成为“桥市”。人多,故事自然多。宋代话本小说《错斩崔宁》中的刘贵就是生活在临安“箭桥”这个宋元以来繁华的街区里的市井“小人物”。《碾玉观音》(《崔待诏生死冤家》)写南宋绍兴年间,璩秀秀家就住在钱塘门里的“车桥”,随着情节的展开,小说还写到崔宁与秀秀逃走经过的“石灰桥”等。《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更是把一场奇缘置放于西湖“断桥”,另写到“八字桥”的雨伞。还有这样几句文字写道:“许宣离了铺中,入寿安坊、花市街,过井亭桥,往清河街后铁塘门,行石函桥,过放生碑,迁到保俶塔寺。”许宣一路行程,又经二座桥。《喻世明言·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写在新桥市上开丝绵铺的吴山,因迷上了“私妓”金奴,不顾身体“炙火”,反复“行事”,结果肚疼不适,险些丧了性命。故事展开的舞台就是一座江南化的“新桥”,而且是商业发达的“市”区:
宋朝临安府,去城十里,地名湖墅;出城五里,地名新桥。那市上有个富户吴防御,妈妈潘氏,止生一子,名唤吴山,娶妻余氏,生得四岁一个孩儿。防御门首开个丝绵铺,家中放债积谷。果然是金银满筐,米谷成仓!去新桥五里,地名灰桥市上,新造一所房屋,令子吴山,再拨主管帮扶,也好开一个铺。家中收下的丝绵,发到铺中,卖与在城机户。
市场设置在桥头或桥边,便于经营,场景热闹非凡,同时也为事件的多发创造了条件。《喻世明言·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写张舜美夜间在杭州“众安桥”上见到:“桥上做卖做买,东去西来的,挨挤不过”,于是开始了一场灯宵奇缘。
民间传说的“牛郎织女”仙话故事告诉人们:“河隔而桥通。”作为一幅幅世俗风情画,话本小说通过“桥”场景的设置,使文本内部充满了更多的商业气息和市井情调,显示了“崇商重文”的江南性。同时,为缺席媒人的男女遇合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
(二)船上故事更不少。作为由“说话”演化而来的一种文体,“无巧不成书”是话本小说叙述的一大特点,而“船”场景往往是故事赖以推进的“巧处”。据检索,“三言”、“二拍”以“船”为场景的故事几达110篇。
首先是情生客舟。话本小说叙说了许多客舟奇缘。《喻世明言·杨谦之客舫遇侠僧》写杨谦之从镇江水路出发到安庄边县赴任,得侠僧结伴同行,船行到偏桥县,侠僧特令其侄女李淑真服侍杨谦之,李淑真百能百俐,一路行程为杨谦之排除了数次险情,“客舫”成为一场奇缘赖以发生的特定场景;《醒世恒言·吴衙内邻舟赴约》的故事发生在江州船上,时狂风大作,两船暂停,一只船上的吴衙内慕美色,另一只船上的贺小姐喜俊雅,两相爱悦,吴衙内登上贺小姐之船,暗中偷情,事发后经过一番周折终成眷属,“客舟”成为青年人一见钟情的特殊场景;《警世通言·唐解元一笑姻缘》生动地再现了唐解元为秋香在苏州阊门游船上那傍舟一笑,不惜卖身为仆,寻访美人下落,终得艳遇,“客舟”成为才子情缘风流触发的特殊场景;同书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写在风景宜人的西子湖畔,白娘子为求得理想爱情巧设了“风雨同舟”的温馨场景,于是,一叶扁舟成为酿造人妖美意的特定场景。明代中期以后,“三言”“两拍”的这种空间构建传统,继续在《西湖二集》、《西湖佳话》等作品集中得以发扬光大,西湖仍然是各类奇缘生成的特殊空间。
其次是情断船头。船上“沉水”作为破解矛盾的手段在话本小说中屡有出现。一方面,“自沉”故事依赖“船”场景来推波助澜。《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就将故事的高潮起于瓜洲渡口的船上,先是浮浪子弟孙富在邻舟听到杜十娘的歌声而起歹意,李甲经不起说动薄情负心;尔后,杜十娘为了维护人格,在船头怒沉百宝箱于滚滚浪涛之中,自己也投水自尽。另一方面,“他沉”故事要靠“舟”场景来掀起新浪。《喻世明言·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叙写忘恩负义的莫稽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在登舟赴任途中,选择了采石江面将金玉奴推坠水中,企图用这种卑鄙的手段结束过去。没有“舟行”,负心者便失去了表演的空间,后面的故事便无从说起。另外,“三言”“两拍”中尚有父母插手借助船载搞隔离的婚变故事。如《警世通言·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写船户刘有才夫妇在女婿宋金患了痨症后,设计把船开到池州五溪一荒僻处,借口让宋金上山砍柴,乘机将其支开。宋金夫妇的离散聚合故事由此拉开了帷幕。
再次是家破行船。俗话说:“风波浪里冤魂多。”人们常把自己被人诱骗而身陷不良处境修辞化为“上了贼船”,可见“贼船”对人们的危害之重。在“船盗”劫财害命叙述中,“船”便作为许多公案故事的现场,造成许多美满家庭的悲欢离合。这些故事的基本框架是,某官人携家眷从水路乘船赴任,奸贼图财害命挑起事端,男主人公被扔下船,女主人公被暂时胁迫,最后分头死里逃生,历尽周折,破镜重圆。如《警世通言·苏知县罗衫再合》、《醒世恒言·蔡瑞虹忍辱报仇》等作品分别叙写了船上生祸端的故事。前者的生事地点是扬州仪真附近的黄天荡,那里是“极野去处,船到荡中,四望无际”,徐能贪财劫掠,苏知县被扔到江中,大难不死,做了市学教师,郑夫人逃到慈湖尼庵避难,19年后,全家方得聚重合;后者的降灾之处是黄州江面的船上,蔡氏全家除瑞虹外无一幸免于难,瑞虹为了复仇,忍辱偷生,历尽磨难,最后遂了心愿。另外,在《拍案惊奇》中,由文言小说改编来的两则故事也以悠悠的水域作为绵长故事空间的突破口,与上述两则故事同出一辙。《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本自唐传奇《谢小娥传》,原作对生事地点不甚强调,而改作却将生事地点交代分明,“鄱阳湖口”的“贼船”险情被生动逼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顾阿绣喜舍檀那物,崔俊臣巧会芙蓉屏》本自明代传奇《剪灯余话》中的《芙蓉屏记》,原作亦不甚强调生事空间,改作对生事地点有明确表述:在苏州一带的湖泊里,船家将崔俊臣撩下水去,而留王氏为妇,后王氏逃跑,俊臣死里逃生,终得团圆。另外,还有别种叙及家难关乎行船的小说,《醒世恒言·小水湾天狐诒书》写王生自京返扬州,遇母及家人于船,发现天狐假传书信,令母尽卖江东之产,导致家业凋零;“初刻”《丹客半黍九还,富翁千金一笑》写松江富翁潘某受丹客之骗,故事开始于他在杭州西湖见一人,“日日雇了天字一号的大湖船,摆了盛酒,吹弹歌唱俱备。携了此妾下湖,浅斟低唱,觥筹交举。满桌摆设酒器,多是些金银异巧式样,层见迭出”。结果财迷心窍,被这个丹客骗了个精光。最后,他在乞讨还家途中,行至临清码头,遇见另一大船上与丹客合伙骗他的妓女,说明究竟,他才如梦方醒。就是这样,话本小说家经常把破家之事的关键环节安排在船上,充分说明江南水乡对话本小说的叙事意义。
(三)岸边商情亦可观。明代以来,随着市民经济的飞跃发展,工商阶层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广阔,“行舟”“涉水”对他们已是习以为常。经检索,我们发现单“三言”、“二拍”即近乎90篇作品直接写到“岸”字,可见岸边故事的比例也很高。《醒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写两个小手工业者的友谊,就把他们会面的空间设置于洞庭湖的“滩阙”,施复因拾金不昧受到朱恩的接济,免去了一场风大船覆的灭顶之灾。水岸成为主人公因拥有友情而幸得摆脱厄运的重要关节。“初刻”《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更是把人物活动的空间安排在水域及其岸边,文若虚由“倒运汉”变成“转运汉”的契机,是他在百般无奈的困境中跟随他人远渡重洋,跨海贩运使之实现了一本万利。其中,“洞庭红”的出手即在岸边。在这里,水域及其岸边是一个冒险家赖以创造奇迹的乐园。“二刻”《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写程宰既得与海神幻化的美女缱绻,又在其指点下通过囤积居奇而发财致富,特别是高邮湖中的化险为夷,更是惊心动魄。这则故事简直是商人阶层的一场“白日梦”,海域及其岸边也成为他们得以“圆梦”的关键性场景。
总之,话本小说大多是江南人或旅居江南的文人创作的,他们多依照江南时空来结撰故事,即使叙及江北时空,也不会像历史学家那样进行考察坐实,而往往参照江南地貌、风俗和风物去写。既偏向于选择有江南味的风情,又写出这些风情的江南味,这就使得这一文体带有鲜明的江南地域特征。
收稿日期:2007-09-12
标签:江南论文; 杭州经济论文; 文学论文; 江南作家论文; 文化论文; 江南人论文; 警世通言论文; 西湖二集论文; 喻世明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