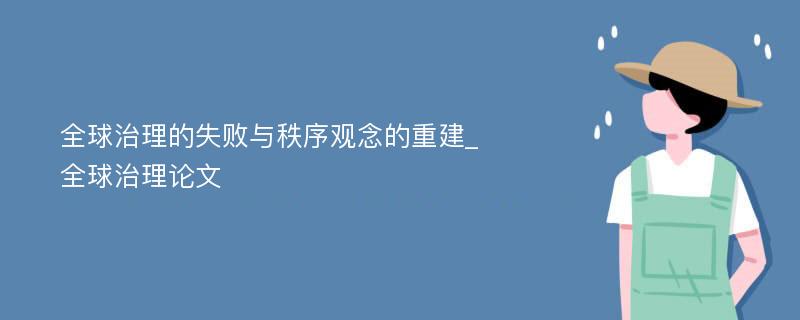
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秩序论文,理念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13-02-25]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13)04-0004-15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冷战时期那种两极对抗的体系特征消失了,同时,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也似乎失去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内战、恐怖主义、经济危机、金融失控、自然灾害、气候变化、流行疾病等等不一。①国际社会似乎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方案,但是成效甚微。跨国威胁和全球性问题都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有些甚至越来越严重。
为什么全球性问题得不到解决?常常听到的回答是失败市场(market failure)、失败政府(failed governments)、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等。经济出现问题,被解读成市场失灵,也就是失败市场;国家出现内乱,被解读为政府失灵或是国家失灵,也就是失败政府或是失败国家。实际上,世界不断涌现的全球性问题,远非任何一个国家、一家政府、一种市场的失败能够解释清楚。失败市场、失败政府、失败国家的问题可能存在,但是,在全球层面上,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可能更是“失败世界”的问题。②从整体主义观点看,市场、政府、国家都是局部因素和单位层面,如果全球层面出现问题,就需要首先在全球层面上考虑原因。本文提出全球治理失灵(global governance failure)的观点,强调治理在全球层面失去效力。如果仅仅孤立地应对一个又一个的具体问题,仅仅思考如何解决失败市场、政府、国家的问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世界仍然会在无目标的混沌中彷徨,稳定和可持续的世界秩序也很难得以建立。
一 全球治理失灵
全球治理失灵指国际规则体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务,不能应对全球性挑战,致使全球问题不断产生和积累,出现世界秩序失调的状态。冷战结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相互依存加大、全球化迅速发展、跨国威胁凸显、国际行为体多元化等都是这个新时期的重要特征。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新的世界,国际管理体系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却是严重滞后,规则背后的支撑理念也没有根本性演进。用治理国家间关系的思想理念、秩序原则和制度安排来治理全球性的国际社会,就会表现出面对挑战无能为力的局面。简言之,世界迅速变化,但制度安排和秩序理念严重滞后,这是全球治理失灵的基本原因。
(一)世界的变化
冷战之后的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有三种变化尤其需要关注,即:权力分布、安全威胁性质、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和复杂关系。首先,权力分布呈现由集中到流散的态势。③在传统国际关系中,权力是相对集中的。冷战时期两极格局的权力主要集中在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手中。冷战之后,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日益呈现流散现象,主要的流散趋向有两个:第一个是从原有大国向新兴大国流散。冷战后国际权力格局呈一超多强态势,现在这种基本格局虽未发生根本性的转折,但美国在全球权力分布中的份额比之以前明显缩小,管理世界事务的影响力明显不足。同时,世界上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却在群体崛起,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等金砖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未来世界秩序取决于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果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态势是合作,世界秩序的前景就会充满希望;反之则会出现动荡失序的局面。第二个权力流散的趋向是由民族国家流向市民社会。国际市民社会的迅速兴起,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和影响力大大增长,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它们组成跨国倡议网络,设定世界事务的诸多议事日程,传播国际规范,影响各国民意和政治进程。④信息革命以及其他新技术的发展使国际市民社会有了发挥作用的更大空间。这是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但却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世界政治,影响到国家的行动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其次,安全威胁性质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冷战之前,安全威胁主要涉及国家,是国家制造、国家认知、国家应对的威胁,是国家对国家的威胁,也就是现在称之为传统安全威胁的概念。这种威胁以占领其他国家领土和消灭对方国家为基本目的,以军事实力为主要手段,以战争为最高形式。在国际体系层面,则表现为主要国家之间的战争,尤其表现为霸权国家与挑战国家之间的战争。⑤冷战结束之后,传统安全威胁依然存在,在一些地区甚至十分严重,但国家间战争频率明显减少,在国际体系的整体层面战争的可能性减弱。同时,非传统安全威胁则明显加强,呈现出两种安全威胁并存的态势。非传统安全不是由某个国家制造,不是被某一个国家认知,也不能由一个国家应对。非传统安全不是国家之间的相互安全威胁,而是国家群体乃至整个人类共同面对的威胁。这已经不是一个国家思考如何应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安全威胁问题了,而是国家群体思考如何合力应对共同的安全威胁问题,是大家如何共同维护和改善全球公地的问题。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强大,单凭自己的实力都无法化解和应对面临的安全威胁,美国的反恐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最后,相互依存深入发展,导致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不能说不复杂,但大的阵营是清楚的。冷战之后,相互依存在经济领域首先得以扩展和深化,两个经济集团的壁垒完全打破,几乎所有经济体都成为世界经济秩序的组成部分,经济体之间、经济体与世界经济体系之间都产生了高度的相互依存态势。与之并行发展的是经济全球化。经济疆界的消除产生了真正的全球经济,每个经济体都是这个大经济的一个部分,每个部分的发展和危机都会影响到其他经济体和全球经济体系,重要经济体尤其如此。现在的相互依存是全球化条件下的相互依存,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条件下的相互依存。所以说,这种相互依存在一些重要方面改变了国际关系的内涵和性质,也导致了高度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冷战时期的敌友阵营变得模糊起来,利益性结盟不断出现,某一问题领域的同盟在另一个领域则可能就是对手。比如,中国和印度比较容易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形成一致意见,而在传统安全领域则会出现竞争。进而,不同文化、不同体制的经济体之间出现了高度的相互依存状态,并且这种相互依存会产生外溢效应,向其他领域延伸,共同安全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安全相互依存的一种形态和反映。
(二)治理规则的滞后
全球治理需要根据这些重要的变化,有效应对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如果治理思路陷入已有的、被认为是成功的治理模式及其背后的治理理念之中,⑥就无法解决当今面对的重大问题,结果只能导致治理赤字,使得正在经历重大变化的世界因治理失灵而成为失败世界。现在世界出现了“规则滞后”的现象,也就是说,全球性治理理念、原则和方式不能适应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大量涌现,规则的供应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落后于实际的需求。全球治理主要是依照现有的规则体系进行的,规则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东西,没有规则就没有治理。规则作为治理的重要保障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现行规则为什么没有解决世界面临的挑战。可以说,“规则滞后”是治理失灵的基本原因。
第一,规则滞后于世界权力结构的变化。如上文所指出的,冷战后世界发生了两种重要的权力流散趋向: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向新兴国家流散以及从国际向市民社会流散。这两种流散表现了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变化和转型。冷战期间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相互竞争的规则,一种是美国主导的,主要在西方实施;另一种是苏联主导的,主要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实施。两种规则都是以实力为支撑、以超级大国为核心的。苏联解体之后,苏联主导的一套规则体系也随之解体,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实施的主要是美国主导的规则体系。冷战之后30年,一个新的全球性现象出现了,这就是新兴经济体的群体崛起。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发展,使得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状态发生了变化。原有的规则体系虽然也在寻求改革,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将这种权力消长的因素充分考虑在内。国际体系规则要继续发挥有效的作用,就需要反映这种权力的发展趋势。金砖国家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已经也必然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日益重大的作用。同时,这些国家也会将自身的文化和理念带入国际社会,影响国际规则的改革和创新。如果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能够携手维护和发展世界秩序,有效的良性治理就可能实现;反之,如果将新兴大国视为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历史上大国政治的悲剧则可能重演。所以,对于全球治理而言,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互动关系至关重要,规则体系、规范体系的改革与创新如果能够真正融合这两种重要力量,世界才会进入有序健康的秩序状态。
第二,规则滞后于安全性质的变化。现行国际规则设计和制定的依据是部分而不是整体,大部分国际制度和规则是在以国家为唯一主导行为体的国际体系下设计和建立的。国家在当时的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据无可争议的中心地位,当时的规则设计反映的自然是这个事实。换言之,现行的规则基本上是以管理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为目的的制度设计。自从1648年欧洲国际体系建立以来,国际政治的重心是国家之间的互动,尤其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安全威胁,因为这种威胁的最高形式是战争,大国之间的问题就是世界性战争或曰体系战争。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无一不是如此。冷战虽然集中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但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没有发生变化,国家之间的安全威胁几乎占据了安全认知和安全讨论的全部空间。美苏之间一系列的战略武器协议主要是针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威胁而签订的。冷战后的世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变化就是非传统安全的涌现,不仅与传统安全并存,而且时而显得更为严重。这不是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威胁,而是国家群体面临的威胁,是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如果管理制度和规则从原本上是为了管理国家间威胁,那么对于这种新的威胁形态显然会应对乏力,全球性治理失灵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第三,规则滞后于相互依存态势的深化。世界已经处于全球性依存状态,经济的相互依存尤为明显。2008年起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欧洲、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欧元区债务危机使得中国出口下降: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的问题立即转化为中国的问题。相互依存不是冷战以后才有的事情,但是,全球性相互依存确实是冷战之后出现的新的现象,明显标志就是新兴经济体全面加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成为世界经济引擎的重要推动力。一方面,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在经济结构和行为方式上都是既有相同也有不同的地方。以发达国家为依据、为发达国家设计的国际规则,由于新的重要行为体的加入,在治理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充分性。1997-1998年东亚发生经济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法提出妥善的解决方案,致使东亚国家采取了自救的方式,东盟+中日韩(“10+3”)机制才得以应运而生。多哈回合长时间陷入僵局,世界贸易组织无力推进,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双边和小多边自由贸易区的迅速发展。这些例子说明,当国际规则无法充分实施治理功能,国家只能绕过全球性规则而进行小范围的合作,所表现出来的恰恰是全球治理规则的低效度和不充分性。地区甚至双边的治理安排如此活跃,恰恰表明了治理在全球层面的失灵。
(三)治理理念的滞后
规则滞后是人们意识到的事情,这才出现了对现有规则体系的改革倡议和改革方案。不过,改革迄今并没有重大进展,一方面是利益使然,但在更深层面上存在治理理念滞后这一更加严重的问题。如果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新兴力量正在强劲地进入世界体系,而治理世界的理念却仍然停留在旧的时代之中,规则的改革和与时俱进就难以做到,治理失灵也就难以避免。
现在的治理理念是与现代性思维相关的,其中三种尤为明显:一元主义治理观、工具理性和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一元主义治理观是一种基本认识,强调全球治理只能有一种基本的或是正确的方式,这就是规则治理。国际关系学界的治理研究议程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国际机制的研究。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对国际机制的经典定义包含了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进而,他还对规则做出了明确的定义,即“对于可为或是不可为行动的具体规定”。⑦在这一研究议程中,由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重大影响,规则治理的相关讨论也尤其突出,基本观点是由规则管理世界,以此促成行为体之间在无政府条件下的合作。⑧冷战后兴起的全球治理研究主要是沿袭了国际机制研究议程,重点也是放在国际规则上面。⑨其中,正式的规则被视为尤其重要,是秩序的基本保障。由此,因之产生的政策建议自然是如何维护、加强和更有效地执行规则。这一研究议程对后来的全球治理研究产生了最直接和最重大的影响,甚至对于其他学派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规则形成与规范形成一样,已经成为建构主义全球治理研究议程中的重要课题。⑩
规则治理因之成为全球治理研究中的主导话语。全球治理被理所当然地定义为以规则为基础的管控(rule-based rule)。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将全球治理定义为多层次——从家庭一直到国际层面——的人类活动管控体系,在这样一种管控体系中,通过实施产生跨国影响的控制达到治理目标。(11)无论是在地区层面还是在全球层面,有效规则成为有效治理的充要条件。这不仅仅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界对全球治理的基本理解,也是西方政策和战略界的重要共识。所以,全球治理研究的问题首先就是在规则这个思维框架中形成的,规则成为全球治理的唯一机制。这样一来,其他治理方式都有意无意地被压抑,基于西方现代化过程的治理实践所形成的治理理念也就成为唯一正确的治理模式,任何多元主义的治理思维都可以被忽视。当非西方国家开始成为全球治理重要力量的时候,这种一元主义的治理话语自然会受到挑战。
工具理性是规则治理的基本理念支撑。工具理性的基本内涵是将个体行为体视为理性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计算成本效益,并据此采取行动。制度现实主义往往认为,规则可以发挥作用是因为在权力已定的情况下,服从规则可以使行为体得到实际利益。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更是在理性主义框架中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制度需求理论。他没有否认二战之后的国际规则体系主要是美国霸权的产物,但也认为,规则之所以有效用,是因为国际行为体需要规则,因为规则使它们实现自身利益。规则有助于加强信息透明度、降低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促成国际合作。而合作给双方带来收益,尤其是绝对收益。(12)国家出于自身需求,为了获取自身利益,势必维持和遵守规则,这是行为体理性使然。(13)后来的全球治理研究在理论上依然遵循这一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本观念,制度主义的核心内涵——国际规则——也就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全球治理研究的聚焦点。
理性主义的规则治理理念对全球治理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基于理性主义的规则治理模式不是唯一的治理模式。当不同行为体尤其是非西方文化传统中的行为体(比如中国、印度等国家)开始进入全球治理体系的时候,自然会将自身的经验和实践带入这一体系。由于理性主义是西方现代化的核心理念而并不必然是这些新兴力量的核心理念,规则治理也不是这些新兴力量的唯一治理实践,这样就会出现互不适应、互不理解且难以达成有效协议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的利益纷争实际上反映了深层的理念差异。
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则是如何看待治理世界中不同力量之间关系的方法。黑格尔的冲突辩证法是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理论概括,认为在任何一种结构中,正题与反题是两极,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矛盾、对立、冲突的。任何两种力量、结构或是过程之间以冲突为基本取向,以消灭对方为发展前提。只有当一个主体占据主导地位,消解或是消灭另一个,这种内在的、非调和性矛盾才能得到解决,其后才会形成一种更高层次的新的合题。它的核心是通过不断斗争和冲突得以变化和进化,是“世界凭借‘既有’及其反面之间的冲突与对立,来实现自身”。在这种辩证法里,“冲突的存在使斗争成为必须,唯有尽力的斗争,才能消灭内在的逻辑矛盾”。(14)在承认这种辩证法在现代化过程中有着积极进取意义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这种进取的实现是斗争、是冲突、是一方消灭另一方。即便是在人与自然关系领域,这种思想也是影响重大,在某种意义上既实现了人征服自然的现代化梦想,但也导致了人毁灭自然的现代化野蛮。
冲突辩证法的关键在于它强调对立性和排他性。冲突辩证法虽然强调进化,但进化过程被视为一个斗争性零和博弈。冲突因此具有了本体意义,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甚至被内化为一种所谓的客观存在,人类是无法解决和调和这些矛盾的。这种冲突性在西方思想史和历史学那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被视为推动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基本动力。看一下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如以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权力理论、文明冲突理论以及英国学派所代表的国际或是世界社会理论,这种冲突性思维几乎无处不在。现实主义认为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文明冲突论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英国学派认为不同国际社会之间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现代化过程中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视其为冲突关系并以人征服自然为基本解决方式,甚至将这种征服视为人的伟大与光荣,这也反映了对世界上根本关系的冲突性认识。将冲突视为世界万物之间的关系本质和世界发展动力,这成为西方思想界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15)
当今的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两种力量:一种是原有的大国,它们是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发展成世界大国的国家;一种是新兴国家,主要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迅速成长起来的金砖国家。这种基本力量态势很容易被置于冲突辩证法的认知框架之中,也就是说被结构为“既有”和“反面”,如果以冲突辩证法和二元对立的观点来审视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势必强调其对立性和冲突性,原有大国会将新兴力量视为现行规则的破坏者,新兴大国会将原有大国视为旧秩序的维护者;原有大国试图对新兴大国实施“社会化”,而新兴大国则认为原有大国试图压制自己的发展壮大。在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导致的认知框架中,是很难就全球问题达成协议的。
二 秩序理念原则的重建
全球治理失灵的出现,说明现行规则体系不能充分和有效地发挥全球性治理功能。虽然世界成为一体,普遍的共识是国际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但真正改革现行规则体系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诚然,国家从自我视角观察问题,从自身利益思考问题,所以在全球性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可能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实例。但是,全球治理的原则及其背后的理念和范式,可能是当今世界在许多问题上面无法达成一致的更加根本的原因。
规则是至关重要的,是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但是,现行的国际规则是不充分和低效度的。这些规则本身就是为管理国际体系中的个体行为体、而不是为国际社会的整体治理而设计和制定的,所以,在管理全球公地和应对跨国威胁方面效用很低。这些规则许多是二战之后制定的,没有反映冷战以后世界权力格局和权力性质的变化,所以,滞后于冷战后变化的形势,使得新出现的问题难以得到解决。进而,这些规则不能充分反映全球高度相互依存的态势,难以解决原有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出现的矛盾和分歧,无力协调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二十国集团(G20)的成立本身就说明现有制度体系的不充分性和低效度性,但G20成立之后的运作及其难以达成一致的实际状态也反映了改革的艰难。
改革和创新之所以如此艰难,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国际规则背后的原则理念依然是过去沿袭下来的,没有反映世界的现实情况。所以,重要的是理念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建立适应治理全球而不是治理国家的新的体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一个新兴大国群体崛起的时代,需要融合各种文明治理思想的新的治理体系,重建世界秩序的理念原则。为此,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基本的秩序理念:多元主义(pluralism)、伙伴关系(partnership)和实践参与(participation)。
(一)多元主义:多样性、包容性与互补性
多元主义是第一原则。在讨论世界秩序的时候,霸权秩序或曰“霸权治理(hegemonic governance)”是一个基本的范式。无论是霸权稳定理论还是自由制度主义,都强调是霸权国建立了国际秩序,提供了国际治理必需的公共物资。因此,霸权国是国际治理必不可少的要素。比如,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维护国际制度不需要霸权,但是建立国际制度则需要霸权国的权力支撑。(16)霸权治理模式很容易被延展开来,成为一种垄断治理思维,也就是说,治理一个体系或是一个社会,需要一种主导力量。现实主义强调这种力量是霸权国的物质实力,自由主义强调这种力量是制度权力。现行的国际规则体系一直是管理国际事务的重要机制,因此,人们已经很习惯以这种理念思考问题,而忘记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真正多元和多维的世界之中。治理一个多元世界,多元主义作为一种理念是至关重要的,需要以“多元治理”的概念代替“垄断治理”或是“霸权治理”的概念。只有真正树立多元主义的思想,才能真正建立多元治理的体系;也只有建立起多元治理体系,才能针对全球性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本文提出的多元治理模式与霸权治理或是垄断治理有着根本的不同,它包含了三个基本要素,即多样性、包容性和互补性。多样性是当今世界的现实,尤其是非西方国家进入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并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多样性就更加明确地表现出来。承认多样性是构建多元治理模式的基础,也是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多元统一(unity in diversity)”不应是一个口号,而应是对现实的承认,因为任何试图将多样性变为同质性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包容性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包容意味着融合来自不同行为体的不同观念和实践,以便形成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比如,“保护的责任”是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重要理念原则,认为在一个国家无力保护国民免受人道主义灾难的时候,国际社会有责任进行干预,对其国民实施保护。同时,也需要理解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提出“保护中的责任”或是“负责任保护”的理念,因为人道主义干预不仅仅是干预,干预只是手段,而目的是和平建设和长期稳定以使人道主义灾难得到更根本的治理。包容性有助于我们分辨和界定不同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不同理念,并试图将这些理念中合理的成分结合起来。包容性治理的对立面是霸权治理,是强行实施某种单一的管理模式,也是将自己认为正确或是有益的东西强加于人。在当今日益多样化的世界上,强加于人的做法是没有合法性基础的。
互补性在某种意义上更加重要。如果我们承认世界的多元性和文明的多样性,承认强加的霸权治理不具合法性基础,那么互补就是在全球层面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互补性不仅承认世界的多样性,而且自觉地相信不同文明的理念、价值、规范不仅不是冲突的,而且是互补的;认为源自不同文明的思想和实践可以通过平等对话相互融合并形成新的合体。平等对话的实现需要通过实施互补的原则。它不仅涉及利益上的互惠,也包含理念上的相互融会。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深刻批判了文明冲突或文明优劣等持有偏见的观点,提出了“多元文明和多维文明”观。(17)比如,民主和市场是被普遍认可的价值理念和制度取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具有普遍价值的理念。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经认为东方儒家文化与西方自由市场实践是难以结合的,(18)但实际上,儒学文化圈的经济体已经以充分的经验证明两者之间不仅可以结合,而且能够促成意义重大的经济发展。
(二)伙伴关系:集体身份与关系治理
伙伴关系是第二个重要的秩序理念。伙伴关系是对全球范畴内行为体关系的一种再定位,认为包括国家在内的世界行为体不应当是现实主义世界的敌对关系,也不完全是自由主义描述的那种仅仅为利益展开合作或是竞争的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是一种关系身份的认定,它是一种基于信任和认同的关系,背后的治理理念是关系治理。
西方学者更趋于提出利益攸关方的理念,因为这是一种基于理性主义的概念。这是现有国际关系思维的主导话语,也是规则治理的基本假定。利益攸关方与规则治理的方式主要考虑到个体利益,但往往不能从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利益攸关方也强调双赢结果,但这种双赢结果是一种博弈意义上的双赢:如果一方不能够保证自身利益的实现,就不会考虑另外一方的输赢问题。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19)只是一个表层现象,即便行为体考虑的是绝对利益,这种绝对利益也必须是对自己有价值的利益。这样一来,势必产生一个高度竞争的态势,身处其中的行为体只能力求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大多数管理全球公地的谈判都是在这种工具理性环境中展开的,迄今为止,在涉及跨国威胁等重大问题上,全球治理几乎没有任何进展。
伙伴关系的概念是不同的,它的基本参照不是利益得失,而是相互关系的协调和整体氛围的营造。关系治理将全球治理视为一种对相互之间关系的塑造、协调和管理过程,将塑造关系身份视为治理的要素,将协商过程视为治理的根本所在。(20)它与利益攸关方的一个根本不同点是,关系治理的基本机制在于协调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使之朝着信任和“我们感”的方向发展,而利益攸关方的观点仍然强调个体的利益得失。关系治理作为一种有益的治理方式,可以弥补规则治理的诸多不足。关系治理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全球伙伴关系的培育与发展,伙伴关系是一种关系身份而不是一种个体身份,关系治理也总是把行为体视为关系中的行为体。(21)
关系治理更多地来自中国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国传统治理实践的组成部分,是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经过几千年实践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种治理方式之中,关系性被视为社会的一个基本概念,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是基本分析单位,治理因之也被界定为管理、协调、平衡与和谐关系的过程。换言之,关系治理将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行为体个体作为社会的关键所在,强调和谐关系是治理的重要内涵。根据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整体利益而不是个体利益就成为良治的关键目标。伙伴关系是一个关系性概念:行为体可以通过建构伙伴关系形成一种集体身份,共同应对全球公地所面临的挑战。伙伴关系从根本上否认自我-他者或是“既有”和“反面”的一分为二世界观,而是强调利益和价值的互补性。和谐关系需要相互信任,这也正是伙伴关系的实质所在。根据这些基本的观点,关系治理的理想模式是一个信任社会,其中有规则制度,也有关系认同,更有道德规范。对于国际社会的治理,规则是十分重要的,但管理和发展良好的关系也十分重要。在一个良好的关系环境中,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就会大大提升。
当今的主导治理模式是规则治理,核心是国际制度,亦即以规则为核心的治理模式。但是,其他治理方式确实存在。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外,有着其他国际体系或是类国际体系的存在,比如东亚的朝贡体系或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幕府体系。由于国际关系研究长期以来是西方学者的领地,他们的基本思想来源和实践经验是来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及后来发展演变的国际体系,所以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是在这一实践体系中产生的,难以想到其他国际体系的运作方式、实践状态以及背后的思想理念。(22)进而,规则和关系不是相互排斥的二元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二元融合。结合两者形成一种综合治理模式,可以使全球治理更加有效,也更具可持续性。(23)关系治理不可能也不应当代替规则治理,关系治理和规则治理是相互补充的两种治理方式。通过关系治理,可以培养和形成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整体治理的效度,最终形成一种既有规则可循、又有和谐关系的信任社会。
(三)参与实践:积极治理与共同进化
使国际社会成员形成伙伴关系、参与全球治理,是比仅仅惩罚违规者更加有效的治理方式。在国际关系学界对全球治理的研究中,对参与实践和伙伴感的研究甚少,因为理性主义仍然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主导话语。但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在这方面已经做过很多研究,不少研究发现,行为体参与程度越高,它们的反馈就越积极。行为体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活动与接受国际规范是密切相关的。(24)有效的治理模式是使国际社会成员参与到全球治理的过程之中,参与到国际制度设计、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塑造集体身份。现行国际社会的主导力量是西方国家,现行国际规则体系也基本上是西方国家设计和制定的。对于后来者而言,伙伴感而不是异化感是十分重要的。布鲁斯·琼斯(Bruce Jones)等人在批评小布什政府时曾经说过,“甚至对美友好的政府也反对美国将国际制度视为工具的做法,即如果符合美国利益就加以利用,如果不符合美国利益就置之不理(并在言辞上加以贬低)”。(25)这里反映的就是一种后来者的异化感:国际规则是一种主导者的权力工具,后来者只能是被规则治理的对象,这样的规则是不具合法性的,也不会达到有效治理的结果。
参与实践是奠定全球治理合法性基础的必要条件,是克服异化感的有效途径。但这种参与必须是积极参与而不是消极参与。国际关系研究中曾经讨论过“好规范/好规则”偏见,即预设现行规范都是好的,然后思考规范如何被传播到“落后”者,使它们能够接受并予以内化。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国际规则体系和规范体系的后来者被动地接受和内化已有的规则规范。这是一种消极参与,是一种最终实现“同质化”的手段。(26)有效治理需要的积极参与,不是要求行为体简单地遵守规则,而是一个共同设计和制定规则的过程,一个对话协商的民主过程,一个分担责任、分享权力、共同维护全球公地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培育伙伴感和建构伙伴关系的过程。
在积极参与的基础上,就可以出现“共同进化(co-evolution)”效应。(27)笔者曾讨论过“共题(co-thesis)”的概念。如果仅仅以正题和反题式进化观来观察世界,则会将世界看成一个处处是二元对立、冲突四伏的场所,其中任何个体行为体都以追逐自身利益为目标,都必然进入与他者发生冲突的霍布斯丛林。如果换一种世界观,则可能将世界视为一个本质上是自我和他者二元互补的社会,自我和他者处于“共题”状态,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正题反题式冲突,而是共题式进化,或“共同进化”,是双方通过互补的方式融合,形成新的合题。(28)这种参与过程不是建立同质性身份,不是要用一种话语替代、征服、消除其他话语,而是一个共同进化的过程:即自我和他者相互学习和借鉴、互为生成条件、互为变化条件、形成新的生命合体的过程。这是共同进化的根本意义,而这种意义只有通过以真正多元主义的理念参与全球治理实践和形成伙伴关系才能够体悟到。
三 结论
全球治理失灵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直接结果是从经济发展到反恐等一系列领域问题接连不断地出现,但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却无法有效应对这些问题。世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全球治理的方式却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过去的治理理念仍然主导全球治理的实践。一方面,国际社会对有效治理的需求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全球治理的机制和方式却在供应一端表现得越来越不足。这已经成为管理世界公地的重要障碍。
现有国际规则体系难以有效应对跨国问题。这并非意味着治理不需要规则,规则无疑是治理的最重要机制,但是,现有规则体系在全球治理方面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原因有很多,本文讨论了三个基本原因:这些规则不是为管理作为整体的全球公地而设计的,所以难以治理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这些规则没有充分反映国际体系中权力的变化消长,所以难以反映和管理原有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真实关系;这些规则继续以个体国家为基本的治理对象,所以难以应对多元行为体高度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
之所以治理供给落后于治理需求,一个根本原因是治理理念仍然大大滞后。支撑当今国际规则体系的最重要理念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假定个体的利己本性和制度将利己变为利他的功能,所以,几乎所有现行规则从一开始就将治理对象设定为国际社会的个体成员,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只能通过契约的方式加以解决。这种理念有很大的合理性,但在变化的世界上也表现出很大的不充分性,因为从本源上这类规则就没有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在冷战后几十年里,虽然为了应对新的挑战,针对原有规则也做了一些改进,但规则体系的不充分性却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对国际社会中的个体成员、对原有大国与新兴大国、对不同文化和文明,不能够用简单方式假定它们是冲突的二元。为了有效改变全球治理失灵状态,需要首先有一种理念革命,需要以多元主义的方式审视世界,以伙伴关系的方式应对跨国威胁,以积极参与治理过程的方式管理全球公地。多元主义不仅要求承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而且要求将不同文明价值的精髓融合起来,形成具有高度合法性的治理方式;伙伴关系要求有效管理和促进国际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以理性主义的假定为主导、将个体成员视为治理的根本对象;参与实践则要求鼓励国际社会成员以平等身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全球治理本身是一个协商过程,是一个参与和身份重塑的过程。简言之,要真正改变全球治理失灵现象,就需要以多元主义的世界观、以伙伴关系的思维方式、以参与治理过程的实践活动建构起一种真正的全球身份认同。世界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关口,如果全球性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走回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并非完全不可能。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审稿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参见Bruce Jones,Carols Pascual and Stephen John Stedman,Power and Responsibility:Building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Transnational Threat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9。
②关于“失败世界”的概念,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③参见Susan Strange,The Retreat of the State: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④Margaret E.Keck and Kathryn Sikkink,Activists beyond Borders: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
⑤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The War Leg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2001.
⑥罗伯特·杰维斯谈到一个十分重要的认知错误,就是过去的成功经验导致后来的认知错误:环境变了,但仍然依照过去成功的经验来应对变化了的环境,结果导致失败。参见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⑦Stephen Krasner,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2.
⑧Robert O.Keohan,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World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Bruce Jones,Carols Pascual and Stephen John Stedman,Power and Responsibility:Building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Transnational Threat,2009.
⑨Freidrich V.Kratochwil,Rules,Norms,and Decisions: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⑩Michael Barnett and Martha Finnemore,Rules for the Wor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World Politic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Deborah D.Avant,Martha Finnemore and Susan Sell,Who Governs the Glob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11)James N.Rosenau and Ernst-Otto Czempiel,eds.,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12)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World Politics,chapter 5;Robert O.Keohane,"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 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Westview,1989,pp.101-131.亦可参见Robert Axelrod and Robert O.Keohane,"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 in David A.Baldwin,ed.,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The Contemporary Debat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p.85-115;Duncan Snidal,"Relative Gains and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David A.Baldwin,ed.,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The Contemporary Debate,pp.170-208。
(13)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World Politics,1984.
(14)成中英:《论中西哲学的精神》,上海: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84-185页。
(15)自西学东渐以来,这种思维方式也在影响着中国近现代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75、80页。
(16)基欧汉虽然相信国际机制的存在和变化可能与权力消长没有关系,但也认为“当代国际机制的建立基本上是战后美国权力的产物,并通过美国权力得以实施”。参见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World Politics,pp.14-15。
(17)Peter Katzenstein,ed.,Civilization in World Politics:A Plural and Pluralistic Perspectiv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0.
(18)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9)Joseph Grieco,"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89,pp.485-508.
(20)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1)Qin Yaqing,"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Process:Institutions,Identities,and China's Peaceful Ris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No.2,2010,pp.129-153.
(22)David Kang,China Rising:Peace,Power,and Order in East Asi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Eric Ringmar,"Performing International Systems:Two East-Asian Alternatives to the Westphalian O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6,No.2,2012,pp.1-25.
(23)Qin Yaqing,"Rule,Rules,and Relations:Towards a Synthetic Approach to Governanc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2011,pp.117-145.
(24)颜琳:《武装组织的社会性克制:参与进程与儿童兵规范的传播》,北京:外交学院博士论文2012年。
(25)Bruce Jones,Carols Pascual and Stephen John Stedman,Power and Responsibility:Building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Transnational Threat,p.34.
(26)关于“好规范偏见”的概念及其讨论,参见Ryder McKeown,"Norm Regress:US Revisionism and the Slow Death of the 'Torture Nor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3,No.1,2009,pp.5-25。
(27)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第三章。
(28)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69-86页。
标签:全球治理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国际秩序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