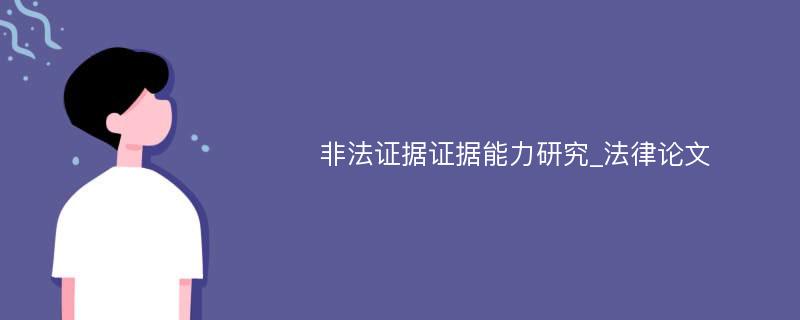
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证据论文,能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理论透析
(一)“非法证据”概念的界定
“非法证据”是我国证据理论中的特有概念,从一些学者所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来看,“非法证据”这一概念在表达上相当模糊、不一致。这是笔者在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时颇感头痛的一个问题,但从多数学者在“非法证据”所表述出的具体内涵来看,也有一些共同点, 主要有:1、这类证据都直接涉及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问题,这就明显区分于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2、 这类证据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关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一类是违法搜查、扣押而获得的实物证据。可见,非法证据是按证据表现形式进行的分类研究但也不完全取决于此,如言词证据仅涉及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实物证据仅限于通过搜索、扣押而获得的实物证据。基于上述情况,首先需要对“非法证据”这一概念作具体界定,以便于对有关证据能力问题作深入研究,避免逻辑上的混乱。
非法证据是指侦查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法而获得的证据。这一概念的内涵理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非法证据产生于收集证据的过程中。收集证据就是侦查人员发现、固定、提取与案件有关的各种证据材料的活动。我国刑诉法对如何收集证据规定了严格的程序性要求,收集证据的活动也应当遵守这些规定,依法进行。如果不顾法律的规定,虽然怀有力求查清案件事实的主观目的,但却不择手段,则构成非法行为,所获得之证据也为非法证据。第二,非法证据的“非法”是就收集证据的方法或程序而言的。我国刑诉法对收集证据的程序一般只从积极的方面予以规定,如第109条至118条关于搜查、扣押而获得的实物证据所适用的具体程序。但也有从消极的方面给予禁止性规定。如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在收集证据过程中,如违反或不符合这些规定,取得的证据被视为非法证据。第三、非法证据的收集主体是特定人员,即负有收集证据职责的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非法方法也是针对特定的对象,即犯罪嫌疑人。
根据以上对“非法证据”概念的界定,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那就是违反证据合法性并非都是“非法证据”,反之,“非法证据”都是违反了证据的合法性。这是必须理清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为便于研究,可以将非法证据的具体表现形式划分为:(1 )违反法定程序或法律禁止的方法而获得的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2 )违反法定的搜查、扣押程序性规定而获得的实物证据。在后述的非法证据证据能力问题探讨中,笔者将按此划分进行分类研究。
(二)非法证据取舍上面临的法律价值冲突与抉择
对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近年来,尤其是在这次修改刑诉法之时:学界争论相当激烈,对非法证据究竟是“取”还是“舍”?如果“取”,是全部“取”,还是部分“取”?各种观点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以为,非法证据取与舍属诉讼运作范畴,它是与一定的法律价值取向相关联的。因此,对其深入探讨,尚需上升到理念层次上加以必要剖析。在整体法律这个宏观背景下,法律价值是指可能对立法、政策适用和司法判决等行为产生影响的超法律因素。这些价值因素包括:国家安全、公民的自由、共同的或公共的利益,财产权利的坚持、法律面前的平等、公平、道德标准的维持等等。(注:参见《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920页。)可见, 法律的价值是一个多元的体系。其中,国家安全、公民的自由、公平是法律价值体系中最基本的三个方面。就刑事诉讼领域而论,国家安全主要体现于控制犯罪观,而公民的自由则主要体现于权利保障观。作为刑事诉讼法重要组成部分的刑事证据法,其通过设定一系列具体的证据规则,目的在于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为正确适用实体法提供前提性条件,以保障刑罚权的有效实现。其在法律价值这一理念层次上就是控制犯罪,维护国家安全。但是,“刑事诉讼活动,不仅是一种以恢复过去发生的事实真相为目标的认识活动,而且也包含着一种程序道德价值目标的选择和实现过程”。(注:参见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而人权保障正是体现了一定道德价值目标的基本要求。其在法律价值这一理念层次上就是保障人权、保护公民自由。就非法证据而言,某项证据对案件事实起到证明作用,采用它有助于发现案件真实,体现控制犯罪观,然而,由于此项证据的取得途径却是通过非法的手段或违反了法定程序,它的取得常常是以牺牲涉嫌者的人权为代价,如以人权保障为价值取向,其结果是舍弃这项证据。因而,对非法证据的取舍正是面临着这样一种两难选择的境地。
当两种迥然不同性质的法律价值发生冲突时,只取其中某一种价值都必然以牺牲另一种价值作为代价,因而是片面的。也是与刑事诉讼发展规律相违背的。纵观西方两大法系国家,在对待刑事证据的证据能力上总是既考虑到诉讼证明本身的需要,又考虑到诉讼证明外政策的需要,避免价值取向的单一性,以使两者得以兼顾。这直接反映了刑事诉讼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因此,寻求冲突价值之间的利益平衡,以最大限度地兼顾两者是最佳选择。那么,如何协调两种不同法律价值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使两者在合乎理性的范围内保持一定程序上的兼容呢?笔者以为,在理念层次上必须求助于公平(Justice)这一价值观。 公平,又称公正、正义。在西方法理学上,法律思想家们赋予正义以非常丰富的内涵。笔者在这里采用的“公平”理念,倾向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分配公平”,即采用那种既不站在政府立场也不站在个人的立场,而是从社会角度给“每个人以应得”(注:[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得:《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5—81页。)的公平价值观。这种“公平”应当在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之间达到某种平衡,使之不致于发生价值取向上的倾斜,乃至一方完全控制另一方,从而走向两个极端。它可以作到最大限度地兼顾两者的利益。但这种“公平”不应仅仅停留于抽象理念的高度,笔者主张表现在立法层次上,它的基本要求是证据规则的制定必须在两者利益发生冲突时,依照权衡原则,并综合考虑多种相关因素,以形成一定的客观标准。权衡原则就是杰里米·边沁提出的“两害相比择其轻,两利相较选其重”的功利主义法哲学思想。综合性因素应当包括国家的政治开明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法律文化背景、犯罪率高低、公民的权利意识等等。目前,我国有学者,从刑事诉讼目的的角度,提出了“均衡价值论”理论。(注:参见宋英辉:《刑事诉讼目的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5-211页。)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总之,非法证据的证据规则应当体现多元的价值观,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应当包括社会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应当从这些基本的价值标准来设定一些必要的证据法规则。
(三)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学说及其评析
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关于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主要有以下三类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类,“否定说”,它认为,非法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应当完全排除。其主要理由是,刑诉法已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由此推论出,使用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否则就会助长违法行为,后患无穷,也难以保证证据的真实性。(注:参见巫宇生主编:《证据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第二类,“肯定说”。它认为,应把非法手段与证据区别开来,对其违法行为可视轻节轻重予以处理追究,但非法所得的材料若与案情有关仍可采用为证据。其理由是,“实事求是”是我国证据制度的核心,我国刑诉法追求实质真实,而不是只要求形式上“合法”,即使是采用非法方法收集的事实材料,只要经过查证属实,同样应采纳为证据。(注:参见戴福康:《对刑事诉讼证据质和量的探讨》,载《法学研究》1988年第4期。 )第三类,“折衷说”,这类学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区别对待说”,认为,应当将非法获得的口供和实物证据区别开来,前者无论真实与否,均应予以排除,因为非法获得的口供,虚假的可能性极大,后者只要经查证属实,应予以肯定其证据能力。因为它与口供不同,并不会因违反法定的收集程序而改变其性质。(注:参见徐益初:《对口供的审查和判断》,载《北京政法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另一种是“原则排除,特殊例外说。”认为,非法证据原则上不能采用;但应设若干例外。(注:参见戴福康:《对刑事诉讼证据质和量的探讨》,载《法学研究》1988年第4期,第240-242页。)
笔者以为,对上述各类观点的评析,应当在充分研究西方国家,尤其是两大法系国家关于非法证据采证规律的前提下,依据上述基本法律价值的内在要求给予评判。在这里,既不能以现有法条的理解作为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的取舍理由,也不能囿于我们旧有的诸如“实事求是”的思维定势来约束自己,否则,就可能会陷入“法条主义”的泥潭,而丧失变革的动因。
就“否定说”的观点而论,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保障是其关于非法证据取与舍的唯一价值取向。其是否具有合理性,应当首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个人自由和权利保障的价值是否绝对的,唯一的?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虽然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对人权问题普遍重视与发展,个人所享有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大,但社会秩序和控制犯罪自国家产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个人自由和权利不受非法侵犯的充分保障。就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而言,如果不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凡使用非法手段或违反法律程序所获得的证据,一律排除,则难免走向极端,刑事诉讼本身所具有的控制犯罪的功能也将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在此方面,属英美法系典型代表国家的美国所走过的道路有着非常现实的经验可以总结。美国是一个崇尚个人自由和人权的国家,刑事诉讼强调正当程序。例如,根据美国宪法规定,违反法定搜查、扣押程序而获得的实物证据一律排除,这就是美国首创的“违法证据排除法则”(Exclusing Rule)。其价值取向就是把蕴含在正当程序之中的涉嫌者的个人隐私权奉为最高的刑事司法准则。 该排除法则于1914年通过Weeks V.U.S一案确定,开始只适用联邦法院。1961 年通过Mapp V.ohio一案强制各州法院统一适用。至此, 其价值取向已走向极端。然而,在这之后,此项排除规则便成为美国刑诉理论中“最具火药味”的问题之一。争论形成反对派和赞成派的两大阵营。于是,联邦法院不得不基于客观情况的考虑,通过司法判例确立了一些例外不排除情形的规则,主要有“善意例外”“必然发现的例外”“独立来源的例外”“公共安全例外”“程序性例外”等等。这些例外规则正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注:Rolando V. del Carmen,"the
exclusionaryrule and probable cause",P.56-71 in Crimial Procedure: Lawand practice,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g PacificGrove,California.)此现象正反映了美国在这一问题走向极端后迫于控制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客观需要所作出的必要的司法反应。其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吸取,也可为我国在相关问题借鉴时提供有益的参考。
与“否定说”完全相反,“肯定说”的价值取向是社会秩序,控制犯罪。这一学说基本上反映了当前我国立法和司法中价值取向的现实状况。这里,也同样引伸出一个问题,即非法证据取舍上,控制犯罪的价值观是否为唯一的、绝对的价值目标?在现代文明社会,一味片面地强调社会秩序,控制犯罪,不给个人自由留有一席余地,人们是不会满意的。关注个人自由的发展和权利保障是基于人类的天性和本能要求。很明显,在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上,单纯地强调社会秩序和控制犯罪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不可取的,在此方面,属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也有可值得吸取的教训。在法国,按规定窃听应经过法官的批准,但实际上仅有很少一部分窃听活动得到有权机关的授权,大多数窃听行为未得到同意。近年来,欧盟法院也受理一些法国公民的申诉,对因一些法院因使用窃听电话和听证程序不合法或者羁押条件恶劣作出了宣布原判决无效的裁定。这充分说明了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和发展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因此,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是明智之举。
“折衷说”中的第一种观点“区别对待说”,虽然从口供和实物证据的不同性质,收集手段与证据的因果关系方面主张不同对待,但就其价值取向来看,同样是走向了极端,而且,这种区分的实质还是强调发现案件真实,其价值取向在于单纯地追求控制犯罪。因此,这种观点与“肯定说”存在同样的缺陷。其本身也是互相矛盾的。笔者认为,这种收集证据的手段与证据本身的区分仅能在一定价值取向下作为设计具体规则的参考因素,另一种观点“原则排除,增加例外说”。就其价值取向而言,兼顾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观,笔者表示赞同。但这种学说在考虑价值均衡时将重心放在保障人权观上,不仅有刻意仿效美国做法之嫌,而且,在操作上与我国立法体例未必相适用,也就是说它能否根植于我国法律领域这块本土是值得怀疑的。
笔者通过上述评析认为,对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首先需要作出恰当的合理的价值选择,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具体证据规则。这之后,笔者将对非法证据两类情况作具体探讨。
二、非法获得的口供的证据能力
(一)西方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的共同点
对非法获得的口供证据能力的研究,笔者择大陆法系国家主要代表德国、法国,英美法系国家的英国、美国和兼具两大法系的特点的日本等对五国非法获得的口供的证据能力立法规定的考察,可以得知,各国的做法并不是完全一致,就是同一法系国家也不尽相同。这主要是由于各国法律文化背景的差异所致。但它并不妨害我们总结出以下共同点:
第一,从非法证据的取舍依据来看,尽管各国立法体例不同,但都是以法律形式作出特别规定或要求。法国、德国和日本由刑事诉讼法典作出明确规定;美国、英国则不仅由判例法形式得以确认,而且还有专门的成文法予以规定。其中,美国、日本还将其上升到本国宪法的高度来加以规定。这样,就保证了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有客观依据作为标准。
第二,从非法证据的取舍标准来看,各国立法都规定了以自白的任意性作为取舍口供证据的标准,并作为最低限度的要求。其表现在禁止使用一些取证方式,这些取证方式包括酷刑、胁迫、欺骗、引诱、不适当的长期扣留或拘禁等作用于犯罪嫌疑人身或精神上不人道行为。
第三,从价值取向来看,各国都力图兼顾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双重价值。控制犯罪价值取向表现在并非对所有取证的口供证据一律排除;保障人权价值取向突出表现在与犯罪嫌疑人个人隐私权相联系的沉默权上。美国、日本宪法都明确规定,不得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法国刑诉法典规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接受侦查人员的讯问被视为其诉讼权利。德国刑诉法典则明确规定被告人的沉默权。
(二)我国立法和司法情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1条至第98条对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诉讼程序作了规定。这些规定内容包括讯问时,侦查人员的法定人数(第91条);讯问的场所、手续,传唤、拘传的时间限制(第92条);讯问笔录的制作(第95条);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协助权(第96条)等等。而对违反这些程序性规定所获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法律没有作出任何宣称其无证据能力的规定。虽然刑诉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违背这一规定所获得的口供也没有明确其无证据能力。在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上,西方国家立法与司法都予以肯定。我国立法虽然在第43条作出禁止使用非法方法取得口供,第45条也作出“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不能认定有罪”的规定,从其含义来理解,也包含有沉默权。(注:见王敏远:《刑事被告人权利研究》,载《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但同时第93年又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不但否认了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而且还要求如实回答。据此,犯罪嫌疑人不仅不享有沉默权,而且还有如实回答的法律义务。
在司法实务中,对违反法定程序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其证据是可以采用的,只要是经过查证属实,完全具有证据能力。至于讯问时,即使发生了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诉讼权利的行为,其所获证据仍认为有效,特别是在通过口供而获得了有关有罪的实物证据,而该实物证据又不为其他证人所知晓的情况下,则更加确认该项口供的证据能力。因此这至少从司法的角度,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我国在违反法定程序获得的口供的证据能力上价值取向是单一的,即把强调控制犯罪作为唯一的、绝对的诉讼价值目标。
(三)构建非法获得的口供排除法则的设想。
基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有必要根据这类证据的采证规律和各国的普遍性做法,并结合我国国情,确立我国非法获得的口供的排除法则。
在前述西方五国中,有关口供的证据能力,在立法上都体现了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目标,在具体内容上的不尽相同正反映了各国在这双重价值目标发生冲突时,采用“公平”的价值观,依据权衡原则并根据本国国情所作出的不同选择。具体内容都是以自白的任意性作为最基本判断标准,其中,有的国家走向更远一点,如美国、法国不仅强调自白的任意性,而且注重自白的合法性。而在我国,笔者以为,以自白的任意性作为判断口供有无证据能力标准较为妥当。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因素而考虑的。
首先,在我国,关于口供证据的证据能力由于立法规定含糊,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非法证据的被采用的现象。期望在我国一步达到美国、法国那样的证据能力标准要求,这在执法人员主观上较难接受的。法律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而执法人员的诉讼观点的转变却将远远落后。事物的发展总是有个渐进的过程,人的认识的发展也是如此,试图在根本没有自白排除法则的我国跨越式地立即确定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自白排除法则,而不去理会自白排除法则的原初形态,是不可取的。(注:转引自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9页。)
其次,根据前述,在我国,由于刑事诉讼法本身对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诉讼权利的具体内容设定较少,而且,刑诉法对律师的法律帮助权又予以重重限制,要求达到自白的合法性的证据能力标准,也缺乏实质意义,因为排除证据的价值取向应当兼顾保障人权。人身权利,诉讼权利没有设定或很少设定,侈谈凡是违反法定程序就一律排除相关证据,价值也很有限。
再次,非法获得的口供排除法则的设计本身还应兼顾刑事诉讼控制犯罪上的功能。事实上,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的刑事案件的发案数一直居高不下,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事案件每年都在几十万件以上。而且近年来,一直呈现出居高不下的态势。(注:参见王敏远:《刑事被告人权利研究》,载《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8页。)因而, 如果不顾客观情况在证据能力上一味过分强调程序的合法性,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刑事诉讼控制犯罪的功能造成损害。
根据自白的任意性标准,笔者建议作如下具体设计:
第一、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相衔接,规定使用暴力、威胁、引诱、欺骗或其他不正当方法获得的口供证据应当禁止使用。
第二、刑诉法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取消犯罪嫌疑人针对讯问应当如实回答的义务性规定。这是保证自白的任意性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第三、规定对出于非任意性而获取的口供证据应认定其绝对无证据能力,并不以被告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或同意作为证据而认为其具有证据能力。
三、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实物证据的证据能力
(一)西方国家的立法和司法现状
法、德、英、美、日各国的有关法律,都对非法搜查、扣押的实物证据的证据能力作了规定。但不同于自白排除法则,西方五国对此差异较大。在立法上,法国、美国均持否定态度,而德国、日本在立法上虽然没有表明态度,但司法判例有否定的痕迹出现;英国则依据“公平”这一抽象标准,由法官自由裁量。看来,虽然同属一个法系的国家,在此问题上也存在着分岐,而不同法系的国家,在此点上却也有倾向于一致的做法。以法系特征为衡量不同国家之间的主张在此情况下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但这无碍我们发现这样一个基本趋势,即各国逐渐关注搜查、扣押实物证据过程中出现的人权保障问题。在这方面美国走在最前面,不仅强调涉嫌者的个人隐私权,而且强调程序的正当性。法国则有选择性对分割被告人的某些个人隐私权提供保障。德国判例中偶然出现排除违法证据迹象,也是基于人权保障而考虑。日本判例是从被告人宪法性权利角度予以考虑。英国的“公平”取舍标准,在司法判例中也显现出权利保障的印痕。
(二)我国立法与司法状况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09条至第118条对搜查、扣押实物证据的具体程序作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内容包括进行搜查时,必须向搜查人出示搜查证(第111条);搜查时,应当有被搜查人或其他见证人在场, 搜查妇女身体应由女工作人员进行(第112条);搜查、 扣押要制作搜查笔录和扣押清单(第113条、第115 条); 不得扣押与案件无关的物品(第114条);扣押犯罪嫌疑人的邮件、 电报的应当经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批准(第116条)。而对违反这些程序性规定, 法律没有规定其所获得的实物证据有无证据能力问题。
在司法实务中,违反法定程序进行搜查、扣押而获得的实物证据完全可以采用。就搜查要出示搜查证而言,实践中,通常做法是很少受其约束,往往是事后补办手续,甚至认为不必要。
依据上述我国立法与司法现状,在搜查、扣押获得的实物证据的诉讼程序上其特点有:
第一、法律在搜查、扣押程序上的规定过于疏漏。例如,在搜查的决定权上,没有建立起监督制约机制,侦查机关既是搜查的执行者,又是搜查的决定者。而在西方国家,一般建立起比较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直接执行人员警察没有搜查和扣押的决定权。英国、美国、日本都是由法官决定和签发搜查证;德国、法国由检察官或预审法院签发搜查证。究其原则,一般以为,搜查和扣押具有强制处分的性质,关系到涉嫌者的人身权利和自由、财产权利、个人隐私权等基本人权。如果不建立制约机制,由执行机关自行决定并执行,势必对公民的基本人权构成一些不必要的威胁乃至造成侵害。在我国,搜查、扣押都是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并执行,连起码的监督防范措施都不具备,因而在实践中,侦查人员可以滋意行动,执行搜查时,不使用搜查证情况屡见不鲜。即使有的事后补办了手续,其目的也是应付检察机关的事后监督,或出于案卷材料的需要。又如,在搜查住宅的时间上,我国立法不作任何限制。实践中执法人员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时可以闯入他人的住宅进行搜查。法国法律规定搜查时间一般不得在6时以前21时以后。德国法律规定, 夜间搜查只能是追捕现行犯或者有延误就有危险时或者在捉拿潜逃囚犯,才允许搜查住宅。从四月一日至九月三日,夜间是指从晚上九时至凌晨四时期间;从十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夜间是指从晚上九时至凌晨三时的期间。英国、美国根据习惯法,搜查原则上应在日间进行。日间是指当地时间上午六时至下午十时。日本法律规定搜查时间一般不得在日出前或月没后进行。西方国家法律之所以如何严格要求在于保障涉嫌者的个人隐私权、人格尊严等基本人权。在对刑事诉讼不构成损害的情况,不必要进行干扰,以体现权利保障的价值取向。
第二、刑诉法对违反法定搜查、扣押程序而获得的实物证据,不仅对其证据能力未作出要求,而且也完全不同口供证据,没有作出任何禁止性规定。从立法者的角度而言,正如德国著名法学教授约阿希姆·赫尔曼在比较中德两国有关搜查、扣押程序性规定时所言,中国的立法机关认为,实施搜查、没收主要是收集证据,至于实施措施时可能出现的强制性则是次要的,德国刑事诉讼法注意到这个强制性,它将没收、搜查措施与待审羁押和暂时逮捕措施直接相关联地规定在一起。(注:参见[德]约阿希姆·赫尔曼《〈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译本引言》,载《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李晶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显然,对违法获得的实物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我国采取的是强调控制犯罪的价值取向,而对人权保障价值取向却有所忽视。
(三)构建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实物证据排除法则的设想。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以为,应当考虑世界各国在此类证据的采证上的发展变化趋势,并结合我国国情确立我国的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实物证据的排除法则。
在前述西方五国,有关非法搜查、扣押而获得的实物证据的证据能力,虽然各国在立法和司法上存在差距,但总体上正呈现重视人权保障的基本价值取向,因此,我国应顺应时代潮流,在这类证据的证据能力上开始关注涉嫌者权利保障问题是为必要。而且,我国宪法和刑法都用禁止性条款明确否定了非法搜查行为。与之相适应,对违反法定程序的搜查、扣押行为规定证据禁用,有助于保证宪法和刑法切实、有效实施。但是,笔者认为,鉴于我国立法和司法的状况,有选择性地将没有搜查证进行搜查而获得的证据设定其无证据能力较为妥当。这主要基于以下因素而考虑的。
首先,这与我国立法者、司法者的诉讼观念有关。如前述,在我国立法上违法证据从来没有被承认,执法人员也缺乏起码的认识能力。观念的转变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过分强调将这类证据排除,则在实践上会难以贯彻。
其次,我国法律关于搜查、扣押程序本身对公民实质性权利设定较少,如一味强调凡违反程序的证据一律排除,将失去其实质意义。
再次,排除法则的限制程序还离不开对我国侦查机关执法人员的执法,司法资源及现时犯罪率等客观情况的考虑。众所周知,我国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近年来有较大提高,但仍不能适应严格执法的客观需要。我国的司法资源也很有限,人员少、经费缺、装备差是其突出表现。而且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刑事案件发案数高,犯罪率呈上升趋势。这些都是我国国情,片面将所有违法搜查、扣押而获得的证据排除出去,显然与我国国情不符,于刑事司法控制犯罪的功能不利。
故而,根据将无证搜查而获取的实物证据排除标准,笔者认为可作如下具体设计。
第一、规定将无证搜查、扣押而获得的实物证据排除。同时,立法上应当考虑到客观情况,规定一些例外无证搜查的情形。如,执行逮捕附带的搜查,即时追捕的搜查;被告人自愿表示同意的搜查等等。
第二、对搜查、扣押应当建立起监督制约机制,搜查扣押的批准权应当收归检察机关。因为检察机关是侦查程序中唯一的制约者和监督者。搜查、扣押属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搜查、扣押活动行使批准权是其法律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针对这类证据排除,应当规定属于相对无证据能力即在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没有提出反对使用时,这类证据也可以认定其具有证据能力。
总之,刑事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在西方国家证据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两大法系国家已形成较为系统的适合其不同诉讼模式需要的证据规则体系。而在我国,关于刑事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长期停留在诸如合法性是否刑事证据的基本特征这类命题的争论上,尚未开展系统的研究。而且,对一些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非法证据的取舍,多是就事论事,只局限于一些具体利弊的分析,缺乏必要的理论作为其支撑点。基于此,本论文以比较研究为基点,较全面地提出了刑事证据能力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并在此着重就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运用诉讼价值理论,初步探求适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获得的口供证据,以自白的任意性作为取舍证据的标准,并从立法上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对非法搜查、扣押而获得的实物证据,以是否持证搜查作为取舍证据的标准,并从立法上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标签:法律论文;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司法程序论文; 刑事诉讼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