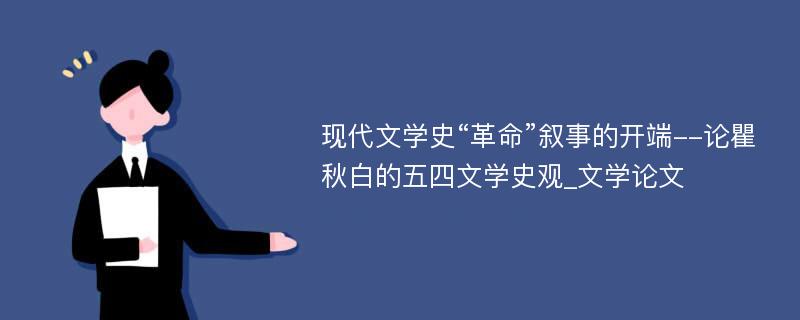
现代文学史“革命化”叙述的开端——论瞿秋白的“五四”文学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开端论文,瞿秋白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0)04-0063-04
瞿秋白生活在历史变幻的风云时代,他曾亲身经历并熟悉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人事。对“五四”文学革命和大革命时期文学运动和思潮,瞿秋白也曾一再加以评说和论断[1]。瞿秋白的这些评述,不仅影响历史后来者,而且在当时也引起过诸多论争。瞿秋白甚至以强烈批评“五四”一代作家及其文学成就的方式,试图促进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生和发展[2](P184-207),并以此体现其独特的现代文学史观。作为五四文学时期的参与者、亲历者,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先驱,在其诞辰110周年的今天,重新讨论瞿秋白对“五四”文学的评述和他试图构建的“五四”文学史观,不仅有着相当的思想研究价值,也有不凡的历史纪念意义。正如保罗·皮科威兹所说的:“要理解瞿秋白对于左翼作家的特殊评论以及他对未来的设想,必须了解他对现代文学运动简短历史以及它的革命产物的总评价。”[3](P112)
1
“五四”运动陡然爆发的时候,瞿秋白说自己是被“卷入漩涡”“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4](P25)。瞿秋白对自己参与后世仰之弥高的“五四”,其动机描述可谓非常朴素,呈现出穷学生在大时代浪潮中更为常态的被动和激情。而对“五四”时的思潮纷乱混杂,瞿秋白也有形象生动的观察和回忆,较平实展现他的心路历程,更客观传达出他对“五四”时期的体验。直到写《饿乡纪程》时,瞿秋白对“五四”时期的各种思潮也仍旧只有总体的感受和观察,但没有具体深入的研究,更没有对“五四”文学有更深入的关注[5]。
然而,瞿秋白日后的文化讨论却仍以“五四”为所有文化文学问题的讨论起点或者批判源头,原因何在呢?个中原因,可从《赤都心史》的最后两篇得到些许的解释。《生活》和《新的现实》不仅是瞿秋白思想飞跃的记录,里面有他新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生成的呈现,也是他现代思想体系生成的一个标志。瞿秋白在文中表示,他从此要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社会现象[4](P247)[6]。旅俄期间,瞿秋白用新现实观、世界观和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对“五四”进行反思,进而确定自己“为文化而工作”[4](P252)的奋斗目标。因此,日后只要是讨论到文化问题,瞿秋白总是以“五四”为起点的原因正在于此。
瞿秋白1923年扫描当时的文坛,对“五四”文学革命曾有过一个比喻:“文学革命的胜利,好一似武昌的革命军旗;革命胜利了,军旗便隐藏在军营里去了,——反而是圣皇神武的朝衣黼黻和着元妙真人的五方定向之青黄赤白黑的旗帜,招展在市侩的门庭。”[6](P312)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里,瞿秋白甚至提出“第三次文学革命”,要以“文腔革命”来开辟新的文艺战线和提出新的革命任务,把“五四”文学革命定为第二次文学革命。而第二次文学革命的前前后后,瞿秋白正是在场亲历者。因此,相关论述不仅篇幅最多,而且讨论尤为细致和充分,评论话语也特别激烈(甚至有不少过激语)。单就在这篇文章里,瞿秋白对“五四”文学的论述就不少于十处。尽管瞿秋白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真正的文学革命——“的确形成了一种新的言语”,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出他此时由于评价要力求周全,因此表述话语有点抽象,对具体文类的成绩评价标准也显得单一。关于“五四”文学,瞿秋白反复强调两点:读者少——“只有新式智识阶级”,用的言语——不是“现代普通话”。因此,很难说瞿秋白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批评是出于一种文学立场。
《学阀万岁!》里,瞿秋白再次讨论到“五四”运动的光荣,首次对新文学的不彻底进行带有激烈否定色彩①的夸张描述②:
中国文学革命运动所生出来的“新文学”,为什么是一只骡子呢?因为他是“非驴非马”:——既然不是对于旧文学宣战,又已经不敢对于旧文学讲和;既然不是完全讲“人话”,又已经不会真正讲“鬼话”;既然创造不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又已经不能够运用汉字的“旧中国文”。这叫做“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6](P176)。
瞿秋白认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不彻底,除中国社会实际生活许多原因外,还有一个次要原因是“‘文学革命党’自己的机会主义[6](P176)。瞿秋白不仅指出“五四”文学革命的不彻底性,而且认为“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都堕落为反动的旗帜[6](P179),认为不彻底性将必然导致其最终走向革命反动的结局。瞿秋白甚至断定“五四”娘家是“洋场”[6](P190)。于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瞿秋白进一步对“文学革命之中的文艺革命三大主义”展开批判[6](P198),第一次激烈地把汉字说成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毛坑”[6](P247)、“十恶不赦的混蛋的野蛮的文字”[6](P15),“必须完全打倒才行”[4](P495)。同时,瞿秋白也客观承认“真正的白话文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里面渐渐的产生出来的”[6](291)、“并不是说十四年以来的一切新式白话的刊物都是这种骡子话”[6](P344)。
而当讨论重点从“五四”文学革命从转移到“五四”式白话时,瞿秋白已经不是在讨论“五四”的文学意义,而是讨论“五四”文学的语言意义。瞿秋白迅速转向从语言变革的贡献反过来评价“五四”文学革命功绩[6](P292)。因此,瞿秋白的“五四”文学史观至少存在两次评价思路上的转折:第一次是从对“五四”文学革命评价转向“五四”文学的语言革命评价;第二次是从“五四”文学的语言革命评价转向“五四”的文学革命的评价。在他的一些论文中,这两种思路同时存在。这就导致瞿秋白对“五四”文学的评价往往出现夹二缠的混沌和片面论述的过激现象。因此,这也给后人增加不少对瞿秋白“五四”文学史观的误解和误用。瞿秋白的两次评价思路,都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彻底性作为总的评价标准。革命彻底性问题当然至关重要,因此在瞿秋白才会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半路上失败了”,并且认为“现在需要第二次的文学革命”是“原则上的问题”[6](P339)。于是,瞿秋白根据实现文学革命和语言革命彻底性的具体目标——文艺大众化和现代普通话——展开“五四”文学革命评述。瞿秋白认为“哑巴文学”是过渡期现象,提倡新文学界必须发起朗诵运动,只有“朗诵之中能茶馆里朗诵的作品,才是民众的文艺”,即“茶馆文学”[4](P376)。这无疑已经是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的先声。瞿秋白以革命历史展开的思路,论述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因为文艺问题也是阶级革命问题。为发动第三次文学革命,瞿秋白提倡文腔革命,号召“中国需要再来一次文字革命”[4](P465)、“文化革命”③。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革命——文腔革命——文字革命——文化革命,文艺大众化——汉字拉丁化——现代普通话,瞿秋白的论述逻辑渐渐趋于两个极端:一方面,越来越偏重于具体而微的语言文字;一方面,越来越强调大而化之的民族文化。也就是说,“尽管他在左翼内部属于五四新文学持极端之论者,但他以罗马字母取代汉字或绝对的白话的主张,却正位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逻辑延长线上”[7]。瞿秋白“五四”文学史观存在的两次评价思路转折,表现得异常清晰,而且呈现出极端化和可逆化的思维特征。两种思路和两个极端的绞缠论述,在此后瞿秋白的许多论著里随处可见④。
由于瞿秋白论述资源中的“五四”文学革命具有多幅面孔多种语义,所以不仅在其本人论述中有时显得驳杂,而且给相关论争带来不少含混和尴尬。在瞿秋白答复胡秋原和《文化评论》的表述里,就涉及对“五四”文学革命精神继承权和合法性的争论。瞿秋白《文艺新闻》与胡秋原《文化评论》的分歧在两点:一是“五四”有没有“未竟之遗业”;二是不管“五四”是什么,都只有为谁服务的选择问题。这是瞿秋白批判答复胡秋原的两个中心。归根到底,这里其实只有一个问题,即阶级立场的底线。瞿秋白把“五四”分成民权革命和自由主义两块,前者“应当澈底完成”但领导权应该而且已经发生转移;后者却是“遗毒”所以“应当肃清”。瞿秋白对“五四”的比喻性论述,同时带上结论的跛脚病。尽管冒着几乎忘却“五四”文学革命中文学主体的危险,瞿秋白却牢牢把握住“五四”文学革命里的革命立场和革命领导权争夺问题。
瞿秋白和胡秋原的论争尴尬,自然经不起学理的严密推敲⑤,但却经受住了政治斗争的考验。毕竟瞿秋白和胡秋原的论战时值革命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大时代,因此革命立场是所有问题最后和唯一的标杆。在瞿秋白重写而成的《大众文艺的问题》里,他以更明确、更成熟的革命叙述方式,以大众文艺为准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再度进行革命化重构。在叙述中,瞿秋白特意强化阶级斗争和对立的表述语词以及动机[6](P13-16)。
2
既然“五四”文学革命已经成为革命双方争夺历史合理性的重要资源,那就不仅要展开论争和局部重构,而且必须进行系统化的革命历史意识形态的建构。《“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堪称这方面力作。此文同时被收入《瞿秋白文集》的文学编第3卷和政治理论编第7卷。收入政治理论编时题目稍有出入,“五四”没有引号,题为《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其它完全一致。这也说明它的意义非同寻常——既有文艺思想价值也有政治思想地位。瞿秋白从革命领导权转移的角度,论述只有无产阶级才真正能够继续伟大的“五四”精神[6](P22-23)。瞿秋白还同步构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革命和“五四”接续的历史合理性。对“五四”的成绩,瞿秋白根据阶级分化的革命进化论,结合革命领导权向无产阶级转移的过程,进行再次辩证论述。此外,瞿秋白还肯定“五四”时期三个最初的革命贡献:“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里,最初发生了国际主义的呼声”[6](P29)、“最初发现了阶级斗争的口号”[6](P29)、“最初发动了白话文学运动,要想废除文言,要想废除汉字”[6](P30)。
既然否定原初的“五四”及其文学史意义,因此瞿秋白就有必要倡导“来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6](P13)。至此,瞿秋白的“五四”文学史观可谓基本定型。在新文化革命的宏伟蓝图的观照下,瞿秋白确定“五四”在革命历史叙述中的起点地位和原初意义。此后,“五四”都以此面目成为瞿秋白的话语资源。而新文化革命的具体革命目标,则是现代普通话的建立与文艺大众化的实现[6](P50)。那些“偏偏用些不文不白的新文言来写革命的文章”的做法是“‘革命骡子’的害虫政策”⑥,都是“死人”[4](P523)的力量。显然,瞿秋白以阶级斗争的革命思维来叙述中国语文、艺术历史变迁,自然有他不够体贴的地方。但反过来说,他的论述也因此获得从社会历史角度理解语言文学艺术发展变革的哲学深度。例如,瞿秋白对“五四”文学革命与文言正统之间的关系论述,就存有相当深刻的历史洞见。
也正是出于革命思维的历史重构动机,瞿秋白才给鲁迅写信论及中国文学史整理问题。瞿秋白整理中国文学史的思想前提,是相信社会历史和政治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在文学史上应有同步体现。整理中国文学史就是整理中国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历史构建和重新叙述,是为了给革命事业寻找历史合理性的支撑力量。站在整个中国文学史高度,从元曲时代到“五四”前的历史自然更重要,但当前革命更急需的是首先重构“五四”以后的历史——从“五四”说起,那么以革命思维重估“五四时期对于著名的旧小说的估量”就更为紧迫。毕竟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领导权争夺,最早也只能追溯到“五四”这个历史原点。历史总是由点到面构建起来。瞿秋白对此已经有面上的宏观把握——从“五四”到新的文化革命。但瞿秋白还需要寻找点的依托。革命的中国文学史要在“五四”到1933年的历史时段寻找符合叙述要求的点,而且必须是瞿秋白熟悉的点——这当然只有鲁迅最为合适。于是,瞿秋白花费四个白天的时间,认真选录鲁迅从1918年到1932年的75篇杂文,编成《鲁迅杂感选集》⑦。同时,瞿秋白又花费四个晚上的时间,写成《〈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从“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斗争史的革命高度来定位鲁迅,认为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6](P96)。接着,瞿秋白从政治立场、社会观察和民众斗争的肯定性角度来观照鲁迅。在瞿秋白笔下,矗立在“五四”到1933年间革命斗争洪流里的“红色”鲁迅被迅速崭新构建起来。当然,在论述中,瞿秋白时刻注意把鲁迅红色历史的起点与急需的革命历史构建起点都定在共同的“五四”。自此,瞿秋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文学史观颇成体系。“五四”是急需的、革命化现代文学史的光辉起点,“五四”文学史观自然就是重中之重。《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因此成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编写中国文学史”时具有“开路和导向价值”⑧的重要文献。
3
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上,瞿秋白是少数在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两条战线都有亲身体验的领导人。他也最早提出对中国文学史进行革命化整理的意见并亲自进行尝试。而在重构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史实践中,瞿秋白最重要的成绩便是编定《鲁迅杂感选集》并写长篇序言。瞿秋白这一举措,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树立经典,更找到革命文艺战线上的旗手。此外,瞿秋白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梳理,对其加以革命领导权争夺为主线的重新叙述,都为中国现代文学史革命构建确立了光辉起点,并以此凿定了革命文学史的思想界碑。这两项历史意识形态构建的重大工程,不仅足以让瞿秋白在中国文艺思想史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给后来的中国文学史留下宝贵的革命历史书写传统:一是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传统,一是文学史按革命史思维加以整理的传统。无疑,这也是文学史叙述上的一次造反有理⑨。
社会历史批评,是瞿秋白现代文学史观中最常运用的文学批评方法。此前尽管有对文学社会价值的讨论,但没有人像瞿秋白这样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来系统分析作家作品。而文学史的整理意见,则是瞿秋白文艺思想的革命性在重写文学史实践中的具体体现。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陈独秀提出“三大主义”建设“文学革命军”后,再次按革命要求对文学史进行的重新叙述。瞿秋白以“骡子文学”、“骡子话”来形容“五四”文学和语言,本意都在于强调其革命性不够彻底,并非源自于对文学史发展史实的切实体会。例如,陈望道就曾经不客气地批评说:“例如所谓‘骡子文学’论,便不能不令人怀疑对于‘文学革命’以来的这几年史实也是隔膜的。”[8]而瞿秋白提出用服食泻药的方式重新开展第三次文学革命和文腔革命,后来甚至致力于开展以废除汉字为最终目标的汉字拉丁化工作,认为这才是“无产阶级的五四”,如此等等,根本上都是为了革命思想里文化意识形态的建设。
瞿秋白自重返文学园地以来,始终潜在地把自己定位为文学战线上的无产阶级革命领导者。面对“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欧化文艺占据主流文化话语的情势,对民族主义极为反感的瞿秋白需要在欧化和俄化中选择自己的思想资源。然而,尽管政治实践中盲从共产国际已经给他以深刻教训,但苏俄的文字拉丁化和扫盲运动成绩却给了他文学文化变革上的启发。而与吴玉章等人共同从事汉字拉丁化的经验,加之结合上海期间对“礼拜六”等新式流行文化读物泛滥的文化现象观察,瞿秋白才最终提出“革命文艺的大众化”的文化革命目标。
从反对欧化文艺到反对民族主义文艺,瞿秋白逐渐走向“革命文艺的大众化”,完成他对新文学发展史的革命道路设计。而拟订新文学史的发展路线,自然就得对此前的文学史进行传统的接续与寻找。于是,就有瞿秋白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问题的相关思考。瞿秋白的文学史整理本质就是文学史的“革命”重写——追求对革命的文学史叙述和对文学发展史的革命重构,为新文学史的发展寻找光荣革命传统,让革命事业在文学发展领域具备历史合理性。最后在明确“我们是谁”[4](P486-490)的前提下,为革命事业的发展取得稳固的文化革命战线上的领导权。
瞿秋白的“五四”文学史观的形成过程,体现了他试图以革命叙述的模式重写中国文学史的基本意图。瞿秋白的这些努力,无形之中完成了革命意识形态下的中国文学史重构。因此,不管对于瞿秋白还是对于中国革命事业而言,尽管这都还是最初的工程,但它毕竟成为此后评述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现象的根本思路,并且影响着新文学史后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文学史写作模式,意义相当深远。
收稿日期:2010-01-10
注释:
①瞿秋白对自己表述的偏激很是清楚,茅盾曾问瞿秋白:“难道你真认为‘五四’以后十二年间的新文学一无可取么?他回答说:不用猛烈的泻药,大众化这口号就喊不响呀!那么,他自己未尝不觉得‘五四’以后十二年间新文学不应估计太低,不过为了要给大众化这口号打出一条路来,就不惜矫枉过正。但隔了一年,在论‘大众文艺问题’时,他的主张就平稳得多了。”见茅盾.瞿秋白在文学上的贡献[N].人民日报,1949-06-18.
②蒋明玳先生认为瞿秋白对“五四”以后文学的估价“就是夸张的”,并认为这是瞿秋白杂文的一种“修辞手法”(蒋明玳.文学家的政治式写作——论瞿秋白的杂文创作[A],瞿秋白研究[C],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367.)我认为瞿秋白不仅在估价上夸张,而且表述方式也是夸张的,但这不仅仅是“修辞”问题,而是瞿秋白政治思想在文艺表述上的策略共鸣。
③皮科威兹认为瞿秋白对待文化革命的态度和毛泽东有契合之处,这涉及到对中国现代“左翼”文学文化思想与延至“文革”的中国当代史的关联。[美]保罗.皮科威(Paul Pickowicz).书生政治家——瞿秋白曲折的一生[M].谭国青,季国平译.北京: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272~274.
④具体见: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A].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465~466;瞿秋白.“我们”是谁?[A].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488;瞿秋白.欧化文艺[A].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491~492.
⑤有论者往往过于喜好以文字表层逻辑的推理证明20世纪30年代诸多文艺论争的“政治性”和“非文学本位”,尽管因有大量文本依托而显得切实,但沉溺于此则有过犹不及的细碎之病。如曹清华.中国左翼文学史稿(1921~1936)[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⑥瞿秋白“害虫政策”的说法出自高尔基,类似的情况估计还很多。见瞿秋白.《“非政治化的”高尔基——读〈革命文豪高尔基〉之二》[A].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13.
⑦《鲁迅杂感选集》是否为瞿秋白独立编选似乎仍有疑问。杨之华回忆是瞿秋白独立编选。(杨之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怎样产生的[J].语文学习,1958,(1).)但鲁迅则明确说是“我们有几个人在选我的随笔”。(鲁迅.致李小峰(1933年3月20日)[A].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83.)从这个角度上说,此书编选工作贯串着政治意味和集体主义精神考量。
⑧钱璱之.瞿研小札(三则)[M].瞿秋白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6):207.此信对鲁迅文学史思想的影响目前讨论阙如。但鲁迅在1932年8月15日《致台静农》中把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评为“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鲁迅强调文学史写作史识,不知是否有瞿秋白的影响呢?
⑨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几乎都是重写,只不过重写时各自所本的主义、思想不同而已。参阅[美]宇文所安.过去的终结:民国初年对文学史的重写[J].中国学术.刘东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180~202.
标签:文学论文; 瞿秋白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革命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文学革命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