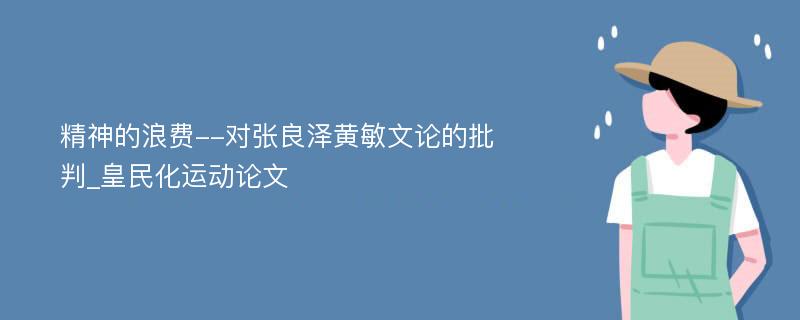
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精神论文,文学论文,张良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愤愤不平地说国民党“反共爱国主义”教育使人不能以“爱与同情”去评价“皇民文学”,恢复“皇民文学”的名誉,离开事实就不免太远了……
二月十日的《联合副刊》上刊有张良泽先生(以下敬称略)的文章《正视台湾文学史上的难题——关于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文章虽短,值得严肃商榷的地方却很不少。
张良泽说他对于在他的高中时代编过“反共壁报”,参加过“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参加过“反共演讲”,觉得很后悔。他也对于在大学时AI写作过“反共文学”,以及在七○年代研究台湾文学时,因基于他当时怀抱的中国“民族大义”而批判过“皇民文学”,深觉悔恨。
五○年代的高中生办壁报,可以办得才华横溢,但是一般地绝不可能不反共一番,因为壁报是作为学校党、安全、思想工作的核心训导处所督管的。而五○年代台湾的中学,在白色恐怖政治肃清之后,根本不存在有“反反共”的左倾思想和知识的学生和他们的斗争,学生只能跟着教官和教师反共,不存在当时中学生必须在左右、在国共、在进步与反动之间做出实践选择的问题,当然也就不存在后悔当年的无知与怯懦的问题。
至于救国团,当年凡是高中生,都不能不是救国团的团员。救国团是以高级中学为单位(大队)全员编队的。正如初中(今之国中)生皆须编入“童子军”,凡高中生莫不是救国团的团员。因此,张良泽也似乎没有理由为此扼腕乃尔。
然而参加了反共演讲,写过以反共抗俄为主题的文艺作品的张良泽,确实就比较突出了。这使我回想起我在高中和大学时代那么几个国民党积极份子学生。在被迫去听讲的比赛会场上,我看到过他们讲得热血沸腾、字正腔圆,尔后看着他们穿着浆烫过的青年服,上台领奖,神采飞扬。我也在大学时代的校刊上读过被排满文艺版的文艺学生的“反共文学”作品,生涩荒芜地写着“残暴共匪”的故事。如若从严肃对待自己的立场出发,对于已经具有行为、思想和选择能力的青年期,争取过“反共演讲”和写“反共文学”的荣誉的自己表示遗憾,则毋宁是一种值得推许的反省态度。但如果张良泽没有以为了苟活(“活下去”)和为了立志“当作家”而有不断发表作品(包括“反共文艺”)之必要为解辩,则在冷战和反共意识形态支配一切的台湾六○、七○年代,基本上也还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张良泽对于他曾以中华“民族大义”批判过“皇民文学”,深感“后悔”当初之“无知”,问题就比较复杂,应当深入探讨。
反共和皇民主义
张良泽认为,在“如今回想起来”时深为“后悔”的少时反共和批评“皇民文学”的“无知”行为,“都是三十年间接受了‘反共爱国’教育的必然结果。”办反共壁报、参加“救国团”、参加“反共演讲”比赛、写“反共文学”发表……当然和五○年代以降国民党的“反共爱国”教育有关。但是以“民族大义”“痛批”“皇民文学”的思想,却未必和这“反共爱国”教育一致。
做为一九三七年侵华战争精神动员手段的皇民化运动,是法西斯主义的日本形态。而法西斯主义的背景,在于第一次战后西欧和日本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刻化,在资本独占体利润下降,中下层资产阶级破产,农村疲惫,而林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纷扰不休,政局动荡。为了恢复和维持独占体的利润率,恢复经济发展,贫困化的资产阶级市民和农民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投向军事性独裁的国家,让国家去压迫和清除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并以极端反共右翼的铁腕统治,维持资本积累所必要的秩序。强烈的反共政策和残暴地肃清、镇压各左翼人士和团体是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政策。而领导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核心力量,正是各国、各民族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民族战线。因此,做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意识形态,恰恰是极端的反共主义。因此,“反共”教育绝不“必然”带来批判皇民主义的“结果”。恰恰相反,很有一些人主张离开中国人立场,重新评价皇民文学;主张皇民化虽然不曾把台湾人变成日本人,却使台湾人变成不是中国人而予以正面评价;主张要以什么“爱与同情”去重新“认真”“解读”皇民文学,恐怕才是以极右反共论为基点的台独论的“必然结果”吧。
至于“反共爱国”教育,恐怕也要分别哪一个阶级,哪一个集团的爱国论。杨逵被判刑十年,理由据说是“爱国过激”。彭歌指责乡土文学派“爱国过于激切”而必欲置之于死地。反对美日帝国主义之间把中国领土钓鱼台私相授受的保钓爱国运动,受到“台湾当局”彻底的镇压。日本战犯岗村宁次应蒋介石之邀,组织以日本前二十三军参谋长富田直亮少将为中心的日本右派校佐,组成“白团”到台湾秘密训练台湾军队准备“反攻大陆”。这个由日本右翼将校组成的“白团”,在战后来台秘密组训台湾军队时,有这样的誓词:
“今赤魔逐日风靡亚洲大陆。崇尚自由和平,深知中日合作之切要之中日两国同志,皆以为此乃为亚东反共而联合、为共同防卫而崛起,相互密切合作,为防共而精进之秋也。
“兹日方同忧共谋,欣然应欲打倒赤魔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之招聘,期为中日恒久合作之础石也。”
此外,日本战犯岸信介、儿玉誉士夫,右派政客藤尾正雄等人,一贯是蒋介石的座上客。今天,有一群日本右派学者,也是出入“总统府”的上宾。今天的国中新编教科书,充满着对日本在台殖民历史之美化、正当化与合法化的叙述。因此,愤愤不平地说国民党的“反共爱国主义”教育使人不能以“爱与同情”去评价“皇民文学”,恢复皇民文学的名誉,离开事实就不免太远了。真正的事实是,在青春期间狂热地度过“皇国少年”的一代,自台湾光复以后,从来不曾像今天那样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言论上昂扬得意过。
作家形成和机会主义
其次,不妨谈一谈“要做一个作家”,是不是一定要无原则地“活下来”和“发表作品”。
台湾遭受日本殖民统治长达五十年,在现实上,这是在一九三七年日本开始其强权的“皇民化”运动之前,即日本在一八九五年割占台湾的一刻开始,就一直推行将台湾人同化于日本的政策。但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都以抵抗同化,保住汉族种姓来回答殖民者的同化压力。一八九五年就开始的台湾农民反占领斗争,以及坚持到一九一五年的抗日武装游击斗争、一九二○年代到一九三○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都是台湾人民为保卫民族主体性而在高压下一仍坚持抵抗的历史。从文学上说,坚持以白话汉语写作,一生坚持不著和服只穿唐装,在作品中表现出磅礴坚强的、对民族和阶级压迫抗议,蔚为以赖和为代表的日据下台湾现代文学家光荣的历史传统。看来,“要做一个作家”的“条件”,未必一定要为了苟活而屈从,未必一定要发表违背原则、屈折于权力的作品。从赖和到吕赫若的台湾文学家,既使在压迫最苛酷的时代,都不曾稍露屈服的奴颜媚骨。说到“发表作品”,人们也会想起在压迫着严密控制下犹冒险秘密写出反抗的心声,隐而不发,迨敌人溃败后才将作品公诸于世的吴浊流。台湾文学史上,不为“活下来”而失节,不为“发表作品”而写违背原则,讨好权力的文章的人比比皆是,而他们又个个都是从艺术上、思想上都能过关的,令后世景仰的真正的作家。
皇民化歇斯底里的机制
一九三七年,日本向中国发动野心勃勃的侵略战争。在此之前,日本人没想到有朝一日必须调动台湾的人力和物力供侵华战争驱策。日本当局有鉴于据台四十余年而绝大多数台民一仍怀抱强烈的汉民族意识,而开始强化对台民的强制同化,由国家权力发动全面压服性的同化运动,收夺汉语、中文的使用,强力推行日语;禁止台湾的一切汉族系民间宗教,把日本神道信仰强加于人;禁止台湾人的传统生活惯习,提倡日本式的生活、衣食和习惯;鼓励弃绝汉民族祖先传用的姓名,提倡“创氏(姓)改名”,改用日本式姓名。在另一方面宣传皇国史观,宣传所谓“日本精神”和“大和魂”,但在具体的政治、社会、民族关系上,仍然保持甚至实质上强化向来的殖民地歧视构造。
现代资本帝国主义以其强大而残暴的现代化武装显示出来的暴力,以其现代化交通、运输、产业、教育、法政和文官制度等向其殖民地呈现种族、政治、社会经济、文明和权力上绝对的优越性,造成对殖民地强大的威慑,以遂行其政治支配和经济收夺。这种暴虐的统治,一方面激发殖民地人民的抵抗,但也更多地造成被殖民人民和知识分子深刻的民族劣等感,对自己民族种性、文化和传统,怀抱深层的厌憎和自卑,丧失民族主体意识,对自己民族的解放、进步和发展,抱持绝望、悲观的态度,并从而对“文明开化”的殖民统治者表现为奴颜媚骨、卑屈驯从。这是从十九世纪末向全球迅猛扩张,统治了全球百分之七○以上的人口,而在二十世纪五○年代初迅速瓦解的殖民帝国主义对广泛殖民地人民造成的深刻的心灵和精神的创伤,流毒为害至于今日,是殖民主义在政治压服、暴力统治和经济掠夺之外另一个荼毒广泛久远的罪行。
一九三七年的“皇民化运动”,正是日本殖民统治在政治压服、经济掠夺外,对台湾民众的精神加害的著例。日本当局,一方面巧妙地利用了殖民地台湾人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民族劣等感、民族自我厌憎感和对于自己民族文明开化的绝望感(而这些都是苛虐的殖民地统治和殖民地意识形态所造成),另一方面则在“皇民化运动”中,突然开启了“内台一如”、“皇民炼成”之门,宣传只要人人自我决志“练成”“精进”,可以锻造自己成为“真正的日本人”,从而摆脱自己做为殖民地土著的“劣等”地位。这一套殖民者对被殖民者大规模精神洗脑的装置,于是促发了相当一部分台湾人“皇民练成”的歇斯底里,今日回顾,令人辛酸悲忿。
皇民文学的经纬和主题
而“皇民文学”运动的发生,有这经纬:在一九三七年皇民化精神洗脑运动的延长线上,在日本进一步准备向祖国华南和南洋扩大侵略战争的一九四○年,成立“大政翼赞会”于日本。同年,在殖民地朝鲜、“满州”分别成立相呼应的“国民总力连盟”和“兴亚奉公连盟”。一九四一年台湾成立在总督府领导下的“皇民奉公会”,在全台自中央以至行政末端成立支部、分会等,把报纸、广播、戏剧、电影全面组织和统辖起来,为侵略战争宣扬动员。
在文学界则先成立“台湾文艺家协会”于一九四二年,并选荐作家张文环、龙瑛宗参加“第一届大东亚文学会议”。一九四三年,进一步把台湾作家纳入“台湾文学奉公会”,推派周金波、杨云萍参加二届“大东亚文学会议”。同年十一月,召开“台湾决战文学会议”,以“确立本岛文学的决战态势,把文艺杂志摆到战斗位置上”为会议主题。西川满的《文艺台湾》和张文环的《台湾文学》皆废刊而统合为全面支援侵略战争的《台湾文艺》。
现代台湾文学,是在日据下台湾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二十余年的历史中诞生、成长和成熟的。一九三一年的大检举,全面镇压了台湾抗日社会运动,但文学战线一仍在镇压的火线上疏散出来的战士们坚持下,在三○年代艰困条件下,继续擎起抗争的火炬。然而到了一九四○年以后,一切抗日运动被一扫而光,军部法西斯的“皇民化”运动,以强权和威压向岛屿的四面扩张。
在殖民地台湾,“皇民化”运动欲达到两大目标:一是彻底剥夺台湾人的汉民族主体性,以在台湾中国人的种族、文化、生活和社会为落后、低贱,而以日本大和民族的种族、文化、社会为先进和高贵,提倡经由“皇民练成”——思想、意识形态的“皇国民化”改造,语言、姓名、宗教、文化的日本化改造,从而彻底厌憎和弃绝中国民族、中国人的主体意识,把自己奴隶化,对天皇国家输绝对的效忠。
上述皇民化运动的第一个目标还仅只是一种手段,以达成运动的第二个目标,那就是以奴隶化、经过彻底精神洗脑、彻底破除了台湾人的民族主体之后的台湾人,供日本侵略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圣战”驱策,鼓动以精纯的日本人,为日本侵略战争“义”无反顾地充当炮灰,为天皇国家和意识形态效死而不稍悔!因此,皇民化运动展开后越四年许!就宣告征召台湾青年为“陆军特别志愿兵”(一九四二),翌年,征“海军特别志愿兵”,四四年宣布在台湾实施征兵,四五年实施。
而为皇民化运动服务的台湾皇民文学,正是为皇民化运动的这两大目标服务。
周金波写的《志愿兵》,写的是一个只有小学毕业,出身平凡、质性素朴的台湾青年高进六(自改姓名为“高峰进六”),对皇民化思想,比一般的资产阶级台湾知识分子有更深一层的体会。他深信神秘的“祭政合一”论(即神道信仰与皇国政治的一体性),深信神道的击手之仪足以使人“为(神道)诸神所引领”,从而益发“接近(大和)众神”,甚至借以触摸到“大和心”、“体验到大和之心”。和知识分子张明贵的怀疑论形成对比的高峰进六,决志要依所信而活,终于以血书明志,应征为“特别志愿兵”。
周金波主张抛弃理性,却除知识分子的怀疑论,从神秘的日本神道信仰入手,去“触摸”和“体验”大和民族的心灵和精神,借以使自己从卑污的台湾人种脱蜕而出,成为高贵的日本人,然后以血书志愿应征,充当帝国侵略的鹰犬。
为了背叛自己的民族主体,把自己改造成日本人,陈火泉的自我斗争就更加披肝沥胆了。他的长篇小说《道》(道路)表现了一个力争在天皇信仰中把自己转变成日本人时,近于哀嚎、呻吟的民族自卑、自我憎厌、和对于“天业翼赞”的无限忠心和信仰。小说的主人翁狂热地想要戮力蜕变为日本人,但对于自身体内流动着的台湾人的血液这个自然的限制,感到绝望和怀疑。他对自己呐喊:
“菊花就是菊花。真正的花就数樱花。但牡丹花终于也能算是花吗?做为岛民的我,终究会成为皇民吗?终竟也是个人吗?”
因为生而为(低贱的)台湾人,因此力争通过精神的精进修练,达到“与大和心交流”而成为日本人,但又对于身中流动着的毕竟不是大和民族“高贵”的血液而深为苦闷。在终于向日本当局提出应征为志愿兵时,小说的主人如此吟咏明志:
“愿为日本臣民,而此身猥非日本骨血,伤悲宁过于此?
今为圣君之盾牌,吾辈欢欣勇猛以效死”
他并且为他战死后的墓碑上预写了这样的墓志铭:
“青楠(小说主人翁的雅号)居士生于台湾、长于台湾、而以日本国民死。”
“青楠居士,日本臣民也。居士为翼赞天业而生,为翼赞天业而劬劳,为翼赞天业而死。”
自己践踏和羞辱自己的民族主体意识,以令人震惊的民族自卑感和自我憎恶,不惜以自身为皇国的侵略战争而破碎与毁灭,来求取获得殖民者民族的认同。
以“皇民练成”为魔咒,造成人人蜕化为光荣的日本人的集体幻觉,并在魔咒幻觉的驱使下,向着毁灭性的战争狂奔。这就是“皇民化运动”的真髓。而“皇民文学”正是这邪恶道场的共犯和帮凶。
从全面看,皇民文学是日本对华南、南洋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时,做为战争的精神、思想动员——“国民精神总动员”机制的组成部分而展开。皇民文学运动,是同时期皇民教育、皇民戏剧、歌谣运动的一部分,目的在集体洗脑,使殖民地人民彻底抛却和粉碎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化和认同,从而粉碎自己民族的主体意识,在集体性歇斯底里中幻想自己从“卑污”的台湾人蜕化成光荣洁白的“天皇之赤子”,在日本侵略战争中“欢欣勇猛以效死”,“以日本国民死”;“为翼赞天业而死”。
愤怒的回顾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在皇民化运动下,总共有二十万七千余台湾青年分别以“军属”、“军夫”和“志愿军”、战斗员等名目被征调投入战争。战死、病殁、失踪者计五万五千余人,伤残两千人。另外因受皇民思想欺骗过头,在南洋、华南战场中误信自己是真皇军而犯下严重屠杀、虐杀罪行,在战后国际战犯审判中被判处死刑者二六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者一四七人!
一九四五年,战败的日本拍拍屁股走人,在台湾留下满目心灵和物质的疮痍。驱策台湾青年奔赴华南和南洋,成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加害者——和被害者的主凶,当然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的权力。但是,对于殖民地台湾出身的少数一些文学家在那极度荒芜的岁月中,认真鼓励鄙视自己民族主体性,鼓励青年“做为日本人而死”,从而对为屠杀中国同胞和亚洲人民而狂奔的营为,后世之我辈,应该怎样看待?
从反省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立场,尾崎秀树在评论陈火泉的小说《道》之余,有这沉痛的感慨:
“……然则,陈火泉那切切的呐喊毕竟是对着什么发出的啊。所谓皇民化、做为一个日本臣民而生、充当圣战的尖兵云云,不就是把枪口对着中国人民、不也就是对亚洲人民的背叛吗?”
因此,重读陈火泉的皇民小说之余,尾崎有这痛苦的呻吟:
“当我再读这生涩之感犹存的陈火泉的力作时,感觉到从那字里行间渗透出来的作者的苦涩,在我的心中划下了某种空虚而又令人不愉快的刻痕,无从排遣。
尾崎秀树并且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对于这精神上的荒废,战后台湾的民众可曾以全心的忿怒回顾过?而日本人可曾怀着自责之念凝视过?只要没有经过严峻的清理,战时中精神的荒废,总要和现在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
尾崎的《旧殖民地文学之研究》,正是怀着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深刻反省和“自责之念”,在日本右翼至今喧嚷“自由主义史观”,指谪主张反省战争责任的史论为“自虐史论”,从而美化日本侵略历史和殖民地历史的日本右翼思潮氛围中,早早敢以“春秋之笔”、“仗义执言”的力作。而正是像尾崎这样,坚决不肯以“爱与同情”为言,去美化、去正当化日本侵略历史对中国和亚洲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物质、生命和精神的加害的日本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存在,使我们对中日和亚洲人民之间真正的和平、正义与团结的展望怀抱了希望。
冷战和颠倒
怎样对待在“决战文学”旗帜下,在日本法西斯最张狂的时代,台湾文学家的思想和实践?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不是三、五年,而是五十年。长达半世纪殖民统治,是渗透到生活细节的日日夜夜的五十年。五十年间,台湾人民给日本人纳粮缴税,不少的人不能不从事日帝统治体系下的下层公教职务,尤其在台湾成为日帝南侵基地和军事要塞的四○年代,全岛岛民在严峻的战争动员体制下,更是无所逃于日本战争机器的淫威。当时的文人、知识分子,在权力下,写些配合时局的小文章,参加一些战争动员的活动和会议,在所不免。因此,国民党到台时,宣布了在台湾地区不清理汉奸问题的方针。纯就政策而言,不能不说是十分贤明的政策。但照顾到台湾殖民地化历史的特殊条件而抑止历史清算以增进民族团结,到后来成为“台湾当局”在台湾光复后急剧升高的国共内战和国际冷战态势中,改而残酷肃清台湾的抗日各派,反过来与日据下汉奸豪族(所谓“五大族系”,又皆在战争末期台湾皇民化运动的领导机关中担任要职)相温存,且以日帝下累致的巨富为基础,在战后“内战—冷战”构造中发展为庞大的集团资本,享受不能仰视的权力和财富的结果。而五○年代以降,“台湾当局”和日本旧军部、反共右翼政、商、学界千丝万缕的网络,被在八○年代末“台湾化”后的台湾当局继承和进一步发展,甚至也在少数一些台湾战后留日学界中发展成对日占台湾史加以美化和正当化,宣传和当年伪满“建国”论如出一辙的各种建台湾为“新而独立”的“民族论”和“国家论”的运动。但这已是余话了。
抵抗者和奴隶的分际
然而,即使在疯狂的“决战”期,台湾人民和作家也绝不只是消极地在战争体制的淫威下屈从而已。以文学界为例,最突出的例子是杨逵。他积极参加日本军政当局组织的皇民剧运,却大剌剌地写《怒吼吧,中国!》。利用日帝和英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宣传中国农民抗击美英帝国主义的热潮。明里符合当局抗击“英美鬼畜”的国策,暗中宣传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之英勇。此外,他也写《驱逐登革热》。按日语“登革热”的“登革”,与日本传说中的恶灵“鞍马天狗”的“天狗”同音。剧本借描写台湾贫困农民扑灭登革热的运动,从而对台湾农村以高利贷和地租压迫农民的地主“李天狗”加以无情的批判。作品中浸染着鲜明的阶级意识,其在屈折中表现出来的令人会心的坚强的抵抗,今日读之,犹为之动容!
而至于吴浊流之冒险在日本军政的枪尖下秘密从事抵抗的写作,是世所周知的。
因此,对待“日据时代台湾作家”“写过……《皇民文学》的历史事实”,不能只看一个作家的一时,主要地也要看他的一生。看一时,也要分辨是积极主动地为虎作伥,还是消极的、面从腹背的言动。有人找到杨逵一篇似在呼应“时局”的短文,几乎如获至宝,大喜过望,仿佛这就足以为“日据下谁不写皇民文学”找到有力佐证。然而,杨逵不惮于门争和抵抗的一生,岂可因战争末期一篇面从腹背的短文,而与周金波、陈火泉之流相提并论?赖和不惮于在剧作、生活、社会活动上坚拒同化,力保民族尊严,不惮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光辉的一生,岂可因他临终前甫自缧绁中重病出狱、心灵一时的凄绝和软弱所写的短文,而硬将他与奴颜媚骨、“忘祖背宗”之辈同日而语!而吕赫若在皇民文学运动沸沸扬扬之际,把“时局”的主题大剌剌地摆到一边,兀自去刻划与战争无关的台湾传统生活的风俗百相。在宣传全面同化于日本的皇民运动主旋律下,刻画台湾生活习俗和风情,就是对皇民主义的批判,有重大意义。
再次,“写过所谓的皇民文学”的台湾作家,本身对于自己成为问题的、当时的作品与思想的态度,也各有不同。
周金波始终不曾稍悔当年皇民思想。在近年一次台湾文学研讨会上,他在日本学者前,坚持以日语发言,发言内容,基本上与当年皇国青年的周金波无轩轾之分。这是坚持皇民有理的顽固态度。
陈火泉对自己的《道》,则采取辩解的态度。他说他所表现的是为当时“时代环境”所逼的言行。小说的主旨,在于促使读者对日据下“被凌虐、被损害”的台湾同胞一掬同情之泪,云云。
不论陈火泉的说辞说不说得通,战后的陈火泉的态度,和周金波者毕竟有所差别。至于为林瑞明教授认为较之陈火泉有“台湾人主体意识”的王昶雄,战后在自己汉译的《奔流》中,多处修改,声言日文版本受当时日本当局检阅时横遭窜改,以适合“时局”标准而与原作失真。王昶雄改订汉译文本的做法固然引来争议,但在对待皇民主义上,显然他是有一定的羞恶之心,视同自己的耻部。这与周金波的坚持大和主义、与陈火泉的强辞饰辩,在性质上又有不同。至于龙瑛宗、杨云萍、黄得时,他们在战后的许多言论,已足表现对那精神荒废时代的自己的言动的悔意,此处实不忍细说,但其对待自己当年皇民主义言论的悛悔态度,又与周、陈不同了。
而张良泽此次译刊杨云萍、龙瑛宗的“皇民文学”“作品”未审有没有征得当事人的同意(虽然二老目前已经相传有衰老到痴聩的程度)?否则,恣意公刊当事人或其子女未必同意公刊的旧时文章,是对二老的“爱与同情”呢,抑或是残酷的二次伤害?
十六年后的回答
一八九五年,强权割台成为定局的条件下,台湾绅商官僚组织了一个抗日临时政权“台湾民主国”,“阳为独立,阴奉大清”。
经过五十年殖民统治,日本人培育了一批与殖民者同其利益的,协力派精英豪绅。迨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一些亲日派台湾绅商豪族阴图与驻台日本军部勾结,倡台湾之独立。但这一回是阳为独立,阴奉日本帝国。
同一年,尾崎秀树有这样一个难忘的体验。一个和青年尾崎同一队的台湾人“学徒兵”向尾崎道出他对光复的想法。这台湾青年说,经过了五十年的日本统治,台湾的生活、文化水平已经高出中国,台湾已经没法儿跟着(落后的)中国走了,只有第三条道路——台湾独立,从而和日本、中国平等交往……
当时,尾崎哑然无以为对。十六年后(一九六一),尾崎在他的论文《决战下的台湾文学》中,对那位台湾籍同学做了回应。尾崎秀树写道:
……回答这问题,只能说日本的殖民统治所造成的伤痕无乃太过深切。只有把日本对殖民地台湾的这一笔亏欠镂刻在心版上的时候,我才有资格回答那位台湾籍的同学。同时,我也想对我这位同学提这么一个问题:
“对于曾经做为日本军之一员的你自己,你是怎么想的?”
在我遣返日本的第二年,发生了二二八事变。
过了几年之后,听说在台湾中南部武装蜂起于二二八事变的民众中,有不少台湾人原日本军人。而且听说特别是曾被征召到海南岛作战的台籍原日本军人,战斗尤为骁勇。
“当这些从战场上回来的台籍旧日本军人或军属,拿起武器在事变中崛起之时,到底受到多少日本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影响?
当我听说了有一些台籍原日本兵在二二八事变中蜂起时,我痛烈地想到上面这个质问,是我们日本人必须向你们作答,却至今一直不曾解答……
殖民者破坏被殖民者的主体性、剥夺被殖民者的语言和文化,对被殖民者强加思想、意识形态的同化,特别有效地使被殖民精英认同、同化于殖民者的史观、世界观、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而当殖民者离去,这些精神的歪扭依然顽强、长时期滞留下来。
五十年的殖民地统治,四十年代的皇民化运动,使一些殖民地精英妄以为自己在殖民地中现代化、蜕变成文明开化的人种,妄以为台湾的文化生活因殖民统治而高于中国,从而必欲抛却自己的祖国,企图独立。
早在六○年代初,尾崎秀树在对日本殖民主义深刻地进行自我批判时,就看到所谓台独运动正是日本殖民主义在台湾遗留下来的“心灵的殖民状态”这个严重的创伤。一九五○年代,弗·范农以“黑皮肤、白面具”之论,早已提出了被殖民者(“黑皮肤”)在心灵上受到殖民者意识形态荼毒(“白面具”)的深刻的分析。
精神的荒废
(一)国民党长年以来的“爱国”主义(中华民族主义)教育,是一切基于(中华)“民族大义”“痛批”“皇民文学”的根源。
(二)然而,在现实上,“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或多或少都写过所谓的‘皇民文学’”。
(三)因此,“新一代的(台湾文学)研究者,应该扬弃中华民族主义”,不可“道听涂说就对‘皇民作家’痛批他们‘忘祖背宗’”;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以“爱与同情”的“认真态度”去“解读”皇民文学作品。
这就是张良泽的皇民文学论的逻辑吧。
否定、鄙视、憎恨被殖民台湾人(中国人)的主体性,把自己改造成日本人,使自己像一个日本人那样地效忠和崇敬日本天皇,终于做为日本人而效死——这就是四○年代台湾皇民文学的主题的真髓。
而主张对这样的文学不要以被殖民者的主体性(“民族大义”)加以批判和反省,企图以“反共爱国教育”论,以“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或多或少都写过所谓的‘皇民文学’”为言……,对皇民文学无分析、无区别地全面免罪和正当化的本身,正是日本对台殖民统治的深层加害的一个表现——长年以来未曾加以清理的、心灵的殖民地化的一个鲜明的表现。
“……只要没有经过严峻的清理,战时中精神的荒废,总要和现在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
每当在生活中眼见触目皆是的、在文化、政治、思想上残留的“心灵的殖民化”,尾崎的这一段话就带着尖锐的回声,在心中响起。
久经搁置、急迫地等候解决的、全面性的“战后的清理”问题,已经提到批判和思考的人们的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