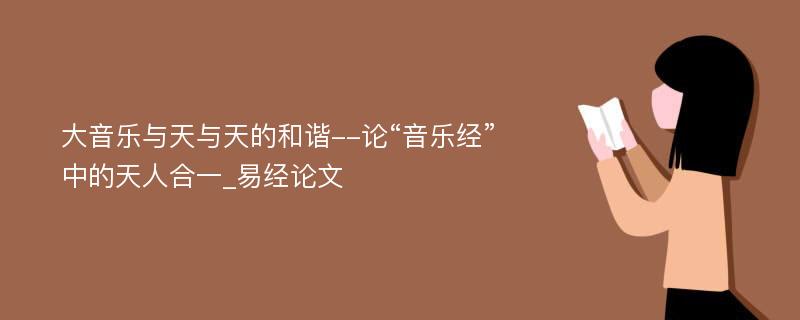
大乐与天地同和——论《乐记》天人相谐的和合神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人论文,大乐论文,同和论文,天地论文,乐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和合是中华民族永恒鲜活的文化精神,凝聚着古人对宇宙天地和社会人生的深刻体验和理性思考,反映了人与自然互相敬畏、互相促进、共存共荣的美好愿望与追求。作为中国第一部文艺美学典籍,《乐记》的内在灵魂就是和合,它所体现的宏大的视野和开放性,彰显出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命意识和博大情怀。
一、承上启下:和合哲学视野中乐的阐释
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和合思维在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文化渊源。《周易》一书已蕴涵了和合思想的重要萌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以致后世谈和合颇有言必称《周易》的意味。《乐记》自始至终渗透着浓郁的和合精神,它所阐发的“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等,实质上是对《周易》和其他经典著述和合思想的承接和弘扬。
和合理论上的萌芽是《周易》里“中”的表述。在《周易》里,表示褒义的词汇最重的是“吉”和“亨”,但是由于吉和亨表示的只是人们的愿望和祈求,并不具有方法论的意味,故对后世的哲学和思维方法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与此不同,《周易》里“中”字的使用虽只有12次(其中家人卦中的“在中馈”是指家中饮食之事),却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其一,这些带“中”的卦都是褒义的,正如刘大均先生所言,这些称“中”的卦辞,“它们都是吉卦、吉爻”[1](P30);其二,“中”在哲学和思维方法上具有方法论的含义。《周易》里讼卦中的“中吉”,师卦中的“师中”,泰卦中的“尚于中行”,复卦中的“中行独复”,益卦中的“中行告公”,夬卦中的“中行无咎”,丰卦中的“宜日中”、“日中见斗”(丰卦中有两句“日中见斗”)、“日中见沫”,中孚卦中的“中孚”等概念,基本上都具有褒义色彩,是一种肯定性的价值判断,充分体现了周人的尚中思想。与使用“中”字的次数相比,《周易》中使用“和”字仅有两处:兑卦有“和兑”之说,“和兑”即和悦;中孚卦有“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这里的“和”是指应和之意。《周易》全书未见“合”字的用法,可见,在《周易》中,“和”字还不具备后世的“和合”之意。因此,从“和合”的发生学角度来看,应该说,《周易》里“中”的概念对我国古代哲学尤其是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和合、和谐、中庸等,都是我国古代非常重要的哲学概念和重要的思维方式。同样,这一思维方式对音乐美学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陈晹《乐书》序云:“臣窃谓古乐之发,中则和,过则淫”,说的就是音乐的中和之美。
明确提出“和合”概念的是《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这里的“和合”即中和。张岱年先生认为,用两个字表示,称为“和合”;用一个字表示,则称为“和”[2]。在古代汉语中,“和”具有丰富的含义,在不同的语境中主要有中和、和顺、谐和、和平、温和、调和等义;“合”主要有相合、符合、合同、融洽之意;而“合同”又有会合齐同与和睦之意,如《乐记·乐礼》:“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孔子也说:“天地不合,万物不生”[3](哀公问第二十七)。子思在《中庸》中明确把“中”与“和”融合起来:“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由此,“中和”上升到了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升华为天地宇宙和社会人生运行的理想图式。而“中和”也就是和合。
显然,《乐记》的和合思想肇始于《周易》,并且是以《周易》的和合思想为先见的。《乐记》虽然篇幅凝练,却以敞开的视域、通融万象的姿态,阐释了和合的深厚蕴藉,可谓论见迭出。诸如“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乐以和其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乐和民声”;“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
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乐者敦和”;“合生气之和”;“平和之德”;“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反情以和其志”;“和顺积中”;“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审一以定和”;“中和之纪”;“四时和焉”等等,另外,还谈到“和敬”、“和顺”、“和亲”等。《乐记》行文凡谈到“和”字的有20多处,而用“合”字近10处。由此可以见出,一部《乐记》,其主旨与核心就是和合,是从文艺美学的视角进一步深化和彰显了中国古代天人相谐的和合文化思想与内涵。
伽达默尔以他百岁长者的智慧,认为中国语言具有形象性,而诠释学需要一种幻想力或想象力,大家200年后可能都要学汉语。《乐记》的语言不仅具有形象性,而且具有高度的想象力,尤其《乐记·乐论》运用整体思维和模糊思维,以意象化的语言集中阐释了“大乐与天地同和”与“乐者,天地之和”的和合美学思想,展示了中国古代特有的哲学智慧和诗性智慧。《乐记·乐论》有两段表述十分充分的文字,其一:“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其二:“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孔颖达《礼记正义》认为,“‘大乐与天地同和’者,天地气和,而生万物。大乐之体,顺阴阳律吕,生养万物,是‘大乐与天地同和’也。”另外,《乐记·乐礼》曰:“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以上所述,既有古人的感悟和体验,又有以整体思维和模糊思维为特征的诗性探幽,其和合思想与审美愉悦相互渗透,融合在宏大的开放性视域之中。同时还应看到,中国古代先人的和合思考是伴随着对客观事物内在规律的不断探索而深化,一方面,“和合是世界万物产生最终的原因和根据,具有形而上学存有的性质”[4];另一方面,和合也表现为客观事物存在和运动的重要形态。诚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所言:“我们所知道的规则与和谐,常常局限于经我们考察了的一些事物,可是有更多的似乎矛盾而实际上却呼应着的法则,我们还没有找出来,它们所产生的和谐却是更惊人的。”[5](P33) 《乐记》所阐发的,正是这种已广泛渗透到事物的原因和存在运动之中的“和合”。从中国音乐发展史的角度看,这种阐发更是一脉相承,“中国传统音乐作品,无论是民间音乐、宗教音乐、文人音乐和宫廷音乐,都强调‘中和’”[6](P261),所以,明代徐上瀛在《溪山琴况》总结的“二十四况”包括和、静、清、远、古、淡、恬、逸、雅、丽、亮、采、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也把“和”视为首况,认为“和为五音之本”。
二、天地之和:天人相谐的和合精神
《乐记》所强调的乐为“天地之和”,是一种至高、至大、至广的富有极大包蕴性的大乐观,体现了宇宙自然万物运动的和谐平衡,与《礼记》“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3](郊特性第十一) 可谓不谋而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方民族的和谐世界观。泰戈尔在《人生的亲证》中,在阐释印度自然环境对印度的影响时,还高度赞扬了印度古代先哲对人类精神与宇宙精神之间的这种伟大和谐的亲证。可见,追求和谐“是东方各民族共同的传统精神”[7](P73)。而且由于和谐中蕴涵着美,所以,怀特海指出:“美的完善被规定为就是和谐的完善”[8](P88)。《乐记》以天地为思维之两极,以乐礼相比、相对,避免了以管窥天的遮蔽和具体事物的制约,拓展了审美视野,这种宏大的视野所追求的是天地宇宙自然的和谐统一,也是一种超越狭隘的感性经验和个人心理的升华。这不仅在当时具有深广的社会认知意义和审美价值,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研究音乐美学乃至生活美学、生态美学,依然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在和合的哲学视野中,事物既有宏观的、中观的,也有微观的。和合作为一种认识和处理事物关系的方法论,尤其应该从大处着眼,以宏观的视野审视天地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惟如此,才能把中观和微观的事物统领起来,从根本上克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在《乐记》中,作者在不同的语境中都谈到了大和合观的问题:“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9](乐象);“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翼奋,角觡生,蜇虫昭苏。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则乐之道归焉耳!”[9](乐情) “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 ”[9](师乙) 显然,这都是以天地宇宙自然为认识对象和审美对象,把宏观的天地与中观和微观的万事万物熔铸于和谐运转的图式之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阴阳调和、刚柔相谐、动静互补的中庸把握。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地是万物之母,“天地感而万物化生”[10]。《象传·泰》:“天地交,泰”;《象传·否》:“天地不交,否”。这段话旨在说明,天地只有相交,才能达到和谐;反之,天地不相交,则无法达到和谐。《乐记》所表现的大和合观充分展示了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并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美学思想。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十八》载公孙弘对策曰:“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公孙弘所论与《乐记》“乐者,天地之和”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周敦颐《周子通书》乐中第十八:“心达于天地,天地之气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则万物顺”;张载《张子全书·礼乐》则说:“声音之道与天地同和,与政通”。这些阐发也明显受到《乐记》的影响,又反过来可以对《乐记》的和合思想作很好的注释。
荣格认为,人类先天地具有一套心理机制,能够容纳祖先遗传下来的生活与行为模式,从而使人类的集体经验获得在心理深层的积淀。荣格这种观点虽有偏颇之处,但也给人以不少启发。从中国古代思维模式的角度看,“天”和“地”作为中国古代经典中反复出现的“原始意象”,虽然不能归结于荣格所说的人类先天具有的一套心理机制,却是在代际相传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成为一种特殊的、神秘的、令人敬畏崇拜的对象。“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一致”[1](P10),也就是说,在天人感应、天人互动的历史进程中,“天”和“地”都被社会化、人化、文化和神化了,所以人们在长期的历史承传中,崇拜和敬畏天,就再也自然不过了。而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古代的先贤们拥有大智大慧,他们在敬畏和崇拜天地的同时,并没有消极地屈从于天地,而是在“明于天地”的基础上,以积极的心态去建构天地之间的和谐关系,建构乐(人)与天地之间的和谐关系。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六:“圣人之遗言曰,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盖言性也。大礼性之中,大乐性之和,中和之情,通乎神明”。王安石这段话颇得《乐记》之主旨。
《乐记》对于天地人和谐关系的建构,在理论渊源上亦可看作对《系辞》的承接和开拓。《系辞》非常明确地说:“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像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以说,《系辞》这段表述是中国古代很典型的“模仿说”。模仿天地自然,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然,与天地之间建构和谐的关系,而且这种和谐关系是动态的,是双方经过相融相谐所达到的新境界,它蕴涵了真(“明于天地”),体现了善(“百物不失”,“百物皆化”,“百化兴焉”),追求着美(“大乐”),集三者于和谐统一之中。在《乐记》看来,“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9](乐礼) 这也说明,乐为“天地之和”,并非纯粹没有矛盾、没有斗争,而是要经过“地气上齐”与“天气下降”的相互渗透,要经过“阴阳相摩”、“天地相荡”的运动,要经过“雷霆”和“风雨”的交融,还要历经春夏秋冬的变化和日月的照耀。如此灵动的感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生不息、万物萌动、化育成长的生命图画,这才是真正的乐,是真正的天地之和。不惟宁是,在今天,《乐记》所蕴涵的和合美学思想恰恰为现代农业和现代畜牧业所证明,同时也为当下视域中的生态美学和生态农业提供了启迪。
事实上,《乐记》所蕴涵的大和合观,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的音乐理论有某些相通之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天上的星体在按照一定轨道运动时,能够演奏出和谐的音乐,“音乐和节奏体系既按数字排列,就必然体现天地和谐并与宇宙相应”[12](P6),而整个宇宙就是一首和谐的乐章,创造出一部天体的音乐,此“天体音乐”是行星运转而产生的音乐,人类虽不能直接听到,却能够心领神会。这与《乐记》所说的“大乐与天地同和”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换一个角度来说,从音乐发生学的视角看,音乐最早的发生虽然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但最基本的是模仿自然,这也是世界音乐史上的共识。中国的先人们在长期的农业文明中生存和发展,人们接触最多、最广的就是大自然。他们处于天地之间,深刻感受和体验到人类的生存和生命的意义,与大自然浑然一体,力求并且也必然能够感受到宇宙天地、自然万物运动的节奏和秩序。在古人的视界中,宇宙天地、自然万物在运动中的节奏和秩序是有所节制的,这不仅符合真的规律,客观上有利于宇宙万物欣欣向荣、繁盛成长,而且也符合善的需求,蕴含了和合之美。宇宙天地、自然万物的和合运动所体现出来的节奏和秩序,如天与地、阴与阳、刚与柔、动与静的对立与统一,还有诸如四时的变化等等,这本身就具有高与低、动与静、张与弛的音乐节奏感;许多最具有原始意味的节奏和音响,如四季交替、风雨雷电等,不仅客观存在着,而且已经成为激发人们音乐灵感的永不枯竭的动力和源泉。刘敞《公是先生七经小传》:“古者制乐,皆有所法也,或法于鸟,或法于兽。其声清扬而短闻者,皆法于鸟也。其声宏浊而远闻者,皆法于兽也。”陈幼慈《琴论》:“夫音韵者,声之波澜也。盖声乃天地自然之气,鼓荡而出,必绸直而无韵,迨触物则节生,犹之乎水之行于地,遇狂风则怒而涌;遇微风则迁而有文,波澜生焉。声音之道亦然。”声音之道与天地化生万物之声可以相通,乃至相同,这正是人文化成与自然神韵渗透融合,由此,也就不难理解陶渊明何以能够在没有琴弦的琴上弹琴,而悠悠然自我陶醉了。
三、乐法天地:中国古代的大乐观
“乐法天地”,这在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中是一个非常需要关注的话题。所谓乐法天地,就是乐应该效法天地,以天地自然为师。在人类与自然互动互存的关系中,乐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社会与审美实践活动,以天地造化为师,究其实质,这既是一个艺术的“模仿说”问题,又是一个实践的方法论问题,因此,前者可以归结为文艺学和美学;后者可以归结为实践哲学和社会学。但是从隶属关系来看,乐法天地的根基或者说是社会动因,恰恰就是以天地造化为师所蕴含的实践方法论;而乐法天地所揭示的这一艺术创造原理,却正是人类实践活动以天地造化为师的美学显现。惟有把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才能够更好地阐释乐法天地的美学价值和实践价值。
乐法天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样有着丰富的理论资源。《象传·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象传·坤》:“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能够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民族精神,尤其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生命历程的重要精神支柱,其深层的原因正在于古代君子效法天地,追求天地之序,注重万物的和合与生机。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看来,天地运行不但遵循着真的规律,而且也呈现着生机勃勃的善和美,由此出发,君子效法天地显然是合情合理并且符合审美的直觉和体验。《系辞》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话的主旨就是“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即以天地造化为师。与此相联系,《桓谭新论》曰:“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乐记》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实质上也是强调只有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才能使礼乐兴盛,“礼乐偩天地之情”。在中国,重视乐法天地,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审美化,完全符合古代素朴的美学思想,体现了浓郁的人文情怀,正如袁济喜先生所言:“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生生不息,是因为其中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它以人为中心,将人与自然,人与审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13],从而共同构成了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宇宙人文系统。
问题在于,在实践层面上,古人何以要乐法天地呢?如果我们拨开当下视域的遮蔽,就不难发现,从更普泛的意义上说,效法天地、以天地造化为师,这充分体现了人类在天人关系中的能动性。追求天人关系中的相谐相融,已经是中国古代社会所普遍认可的公理,因而也是那时最具普适性的公共视域。我们再来看今天,随着工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高楼大厦和信息技术共同构成了城市化的时代特征,一方面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繁杂与喧嚣;一方面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网虫”。人们置身于大都市,仿佛与大自然一天天地疏远了、隔离了,即使栽树、养花、铺草坪,也难以让人们产生回归自然的感觉,以至于不得不千方百计去寻找人与自然
的那种天然的联系。与当下视域不同,在古人的视域中,大自然不仅是他们生存所需要所依赖的客观环境,而且在人们的心理和情感上,他们也可以与大自然息息相通,甚或将大自然看作学习和模仿的对象。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认为,人心要和天道相辅相成,“人和人可以通过感性达至共鸣,也可以跟自然、跟生物、跟无生物进行共鸣。即使是无限遥远的星球,对我们也可以进行有感情的联系”[14]。杜维明先生所说的共鸣和联系,实际上是指人与自然在沟通中通过移情,进而达到感情的共鸣。当然,这离不开综合的历史条件,对于古人来说,人类最早的审美对象就是天地宇宙、自然事物,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天地之和既是生存的理想状况,也是朦胧的美的理想”[15](P148)。
还应指出的是,东方的“乐法天地”体现出来的天人相谐,与西方古希腊的“模仿说”、与现代的仿生学有着相通和相同之处,是一种实践的方法论,具有现代实践哲学和社会学的意味。首先,乐法天地作为一种艺术起源的“模仿说”,与古希腊的“模仿说”有着惊人的相似、相通和相同之处。在中国诸多的音乐起源学说中,乐法天地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而在古希腊的艺术起源学说中,“模仿说”最早肇始于赫拉克利特,中经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德谟克利特的不自觉润色,集大成于亚里士多德。在中国古代美学中,“模仿说”在理论上最早可以追溯到《系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君子以天地自然造化为师,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乐记》看来,乐是按照天的道理来创作的,乐如果不合天的道理,就必然导致音调偏激或不和谐。另外,从实践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类模仿自然不需要交任何“学费”,可谓事半功倍,这一点德谟克利特也说:“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模仿禽兽,做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16](P4—5) 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先天就具有音调和节奏感,所以人先天就具有模仿的本能。虽然亚氏的表述与赫氏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看到了模仿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其次,从实践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一般社会实践还是艺术实践,“模仿”无疑是人类一种重要的行为方式,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重要确证。众所周知,艺术领域有天鹅舞、孔雀舞,体育领域有蛙泳、蝶泳、猴拳、螳螂拳,科技领域鲁班发明了锯,达·芬奇根据鸟的飞行设计出飞机模型。考古人员通过研究还认为,人类酿酒和饮酒也是从鸟类那里学来的。这些都是很典型的模仿自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模仿也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任何个体都要以天地自然为师,以社会和他人为师,融通与和合几乎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它广泛地贯穿于宇宙天地与社会人生的诸多方面,这都需要学会模仿。而就艺术与大自然的关系,或许更可以说,“艺术家的内心生活和大自然的生活之间有一种亲缘关系。因此,大自然不仅是艺术家的避难所,也是力量、灵感和觉醒的源泉”[12](P60)。这姑且可以看作是艺术的仿生学。
在《乐记》看来,天地之和也就是天地相和,所以,才能百物不失、百物皆化,正所谓“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9](乐礼)。乐之所以兴,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天地之和所构成的万物育焉、百化兴焉的和谐律动。因此,我们不妨说《乐记》所说的“大乐”,是人们以艺术的方式自觉模仿天地宇宙万物的杰作,是人们永恒所追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