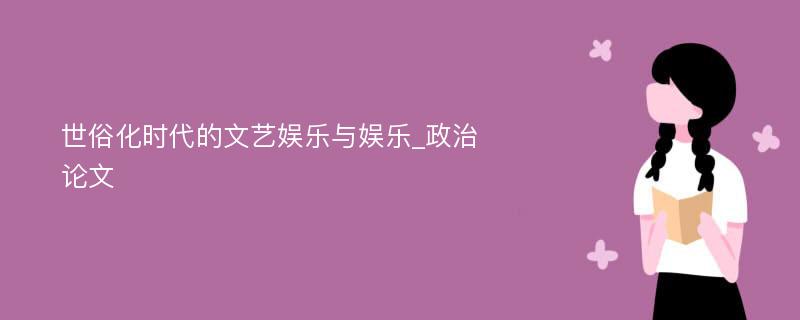
世俗化时代文艺的消遣娱乐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娱乐性论文,消遣论文,世俗论文,文艺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不同的社会与文化形态中的“乐”与“教”的关系
虽然在几乎所有时代、所有社会文化形态中,文艺的消遣娱乐功能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不同时代与不同社会文化形态中,文艺的训导劝谕性与消遣娱乐性,即所谓“教”与“乐”之关系是不同的,各自的角色、地位也不可同日而语。
从不同的时代来看,古代社会中“教”重于“乐”,“乐”从属于“教”,在所谓“寓教于乐”或“文以载道”的提法中,“乐”本身没有合法性,它要从对于“道”或“教”的依附中分得一些合法性;而在现代社会中,世俗化的趋势使得“乐”从对于教的依附中解脱出来,有了独立的地位与意义。
从不同的文化的形态来看,宗教文化、政治、伦理文化都是重“教”而轻“乐”,“乐”是从属性的,没有本体的、独立的意义;而世俗文化、大众文化、市民文化则或是“教”、“乐”并重、或是“教”、“乐”分离、或是在“教”重于“乐”的幌子下实际上是“乐”重于“教”。
今天看来,把“教”与“乐”关系设置为支配与被支配、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不能成立的。“乐”不应从属于“教”,“教”也不应当统治“乐”。文化与艺术中“教”与“乐”的等级秩序与宗教社会或政治社会的权力秩序是相互勾联的,是从属于权力秩序的。政治权力或宗教权力对于文化权力及道德伦理的绝对支配性,是“教”与“乐”的等级关系的合法基础。因而在“道”与“文”的等级中实际上还有一个政或教(宗教):政—道—艺(文)。同样,在“乐”从属于“教”的背后,还存在一个支配一切的宗教的或政治的权力。贺拉斯本人就与罗马的教皇、贵族关系十分紧密。将教与乐的等级秩序这样加以还原以后,可以暴露出“寓教于乐”这个命题的统治本质,以及它所隐含的权力的运作机制。正因为这样,当古代的宗教文化与政治伦理文化秩序解体以后,“教”对于“乐”的统治合法性也就不再存在了。
二、当今中国世俗化社会中“乐”的意义
今日文艺的“乐”(即消遣娱乐性)的意义,可以概括为“解神圣化”(当然是政治化的所谓“神圣”,是为专制统治提供合法依据的“神圣”)的功能。如上所说,在宗教性的神权社会的或准宗教化的政治社会中,“教”是一种宗教的或政治权力的合法化机制,因而解构“乐”对于“教”的依附性和从属性,也就解构了“教”的神圣性以及“教”所支撑的宗教或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神圣性。结合中国的实际,解放后30年“教”已堕落为意识形态的驯化,“教”本身的独立性也荡然无存。正因为这样,消解了“教”与“乐”的从属关系,实际上也就消解了“教”背后的支撑系统——官方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文艺的消遣娱乐的政治与文化的功能在今天就表现在这里,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结合当前的人文精神的讨论,我想重点谈谈这个问题。
人文精神的话题引发大陆文化界热烈关注是在1993年的下半年(王晓明等人在《上海文学》1993年第六期上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在此之前,“人文精神”的提法早已有之,但无人回应。指出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1993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经一段时间的停滞以后重新起步并以更快的速度加快的一年,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社会的世俗化、商业化程度的加深以及相关的文艺的消遣娱乐性的空前的突出。这一世俗化潮流在文化界的表现就是被称为“痞子文人”的王朔的大红大紫和各种大众文化的兴盛。我以为这是引发人文精神讨论的最直接的原因。这样,中国的人文精神的出场就有了与西方的人文主义的出场完全相反的语境:西方人文主义是针对神权社会而提出的,其核心是从天国走向人间,从神权走向人权,世俗化及人的非神圣的欲望正是其最为核心的诉求;而中国90年代的人文精神则是作为对于世俗化及人的非神圣的欲望的高涨趋势而提出的,其核心是从人间回到天国,以终极关怀、宗教精神拒斥世俗诉求,拒斥文艺中的所谓“轻松”、“逃避”、“玩”,实际上也就是拒斥文艺的消遣娱乐性(张承志:“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用道德理想主义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主义拒斥文艺的市场化、实用化与商品化。明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当然他们自己并没有用“世俗化”或“消遣娱乐”这些个词,但在他们所批判的玩文学、回避沉重沉溺于轻松,在他们所提倡的生命意识、生命体验、生命的沉重、痛苦与神圣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对于消遣娱乐的排斥。
由于今日文化艺术中的消遣娱乐性(尤其是在以“乐”为本位的大众文化中)与世俗化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所以关键在于我们对世俗化应当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与评价,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才能解决如何评价文艺的消遣娱乐功能的意义的问题。在西方,世俗化的主要意思是解神圣化,宗教与人们的日常世俗生活脱勾,世俗政治与教会权力脱勾,民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不再与一种神圣的精神价值相关联,人们不再到生活之外去寻找生活的合法化依据。社会活动的规范也脱离了宗教的源头,由法律取而代之,意识形态问题是大众参与讨论的而不是由教会垄断的。这样宗教就不再是公共生活中的普遍性的规范,而成了个体的精神信仰。这是西方现代性的核心内容之一。在中国世俗化所消解的不是典型的宗教神权,而是准宗教性的集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于一身的专制王权。尽管如此,在向市民社会转换、健全法制、肯定人的日常生活诉求并使之从准宗教化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教条中解脱出来这些方面,中国的世俗化社会变迁仍然有着与西方相似的一面。所以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必然凸显出大众对于生活幸福本身的强烈欲求,凸显出文化活动解神圣化以后的多元化、商品化、消费化的趋势以及相关的消遣娱乐功能的强化,文化成为对于人的世俗欲望的肯定。
从西方的语境来看,针对着世俗化的文化批判话语是在西方社会世俗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业已经过40余年的长足发展之后出现的,在这么漫长的历史阶段中,西方的世俗化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解构神圣化的使命,它已成为西方社会文化中的绝对主流,并表现出了种种问题(如神圣解体以后精神价值、精神家园的迷失,价值的多元化导致的价值相对主义等)。而中国的世俗化才10多年的历史。由此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质问:西方的文化批判话语是否适合于中国?中西方世俗化的历史定位如此不同,它们的文化功能与政治意含又怎么可能一样?中国文化的世俗化是否已经充分地完成其解神圣化的使命?一旦把握住了这一历史的错位,就不难发现,西方的文化批判话语在分析中国问题时的适用性是极其有限的。如果不经转换地搬用过来,就会批判得片面、批得不得要领,甚至批错了对象、提错了问题。如果我们承认世俗化是中国当今的社会文化转型,亦即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不管世俗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文艺的市场化、商业化和消遣娱乐性本身会有多少负面的东西,也不管它有多少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虚无主义、混世主义,我们都不应该从道德理想主义、审美主义或宗教价值出发全盘拒斥它的存在,这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而只能是在肯定其历史意义的前提下对之加以优化。我坚持认为,当前以消遣娱乐为本位的大众文化具有消解政治文化与正统意识形态的作用。当然这不是说大众文化采取了直接的、面对面的、严肃认真的姿态对政治文化展开了批判,而是说它的繁荣在客观上冷落了政治文化,大量的大众文化产品覆盖了大众的文化阅读空间,从而使得政治文化的影响力大大降低。这难道不是一种不应忽视的消解力么?从大众文化的本质看,消遣娱乐对它来说是具有本质规定性的,我们不能要求它以精英文化的方式传“道”(精英知识分子之“道”),或者与正统意识形态对抗,这无疑是取消了它的存在。
三、“乐”在中国特殊语境下的畸变
现在参与人文精神讨论的另一部分人,如王蒙、李泽厚等,对于世俗化、对人的欲望、对文艺的消遣娱乐性采取了基本肯定甚至拥抱的态度,体现出与道德理想主义者很不相同的价值取向(李泽厚说:“大众文化不考虑文化批判,唱卡拉OK的人根本不去考虑要改变中心什么东西,但这种态度却反而能改变一些东西,这就是……对正统体制、对政教合一的中心体制的有效的侵蚀和解构。”)。我体会他们理解的人文精神更合乎西方的人文主义的意思。他们强调世俗化是对先前的政治社会与专制主义的否定,充分肯定人自身的价值,关注人的存在,而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这种关注不是什么空喊终极关怀、宗教精神,也不是一味的沉重、痛苦,而是实实在在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尤其是让他们从专制主义与物质馈乏中继续解放出来,而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中,像王朔那样的调侃与嬉戏、玩文学、玩人生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解放之途。如果说,在一些人文精神的倡导者的眼中,王朔的调侃与嬉戏是对生命意义的遗忘、对沉重的存在的逃避、是价值虚无主义,那么在王蒙他们的眼中,王朔的这种调侃与嬉戏以及大众文化中对于感官刺激的追求,则是对政治与文化的专制主义的一种有力的解构。其实,争论的双方都只看到了王朔的一个方面,把这两者合起来才是完整的王朔。这一分析也适用于王朔以外的其他大众文化。当前的大众文化表现出了对于官方意识形态与精英文化的双重疏离,因而具有双刃剑的性格。基于这一思考,我提出人文精神论者与世俗化的拥护者应当握手言和。
当然,在对于世俗化、物质欲望及感官刺激的欢呼中也不是没有值得警惕的误区。必须指出:世俗化决不只是商业化、市场化,更不是游戏化、痞子化、精神侏儒化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滑头主义的同义语。它实际上应当包含新道德、新规范、新价值的建构。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化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反观中国的世俗化,对于旧价值的破坏虽然痛快淋漓,但新价值的建构却远远不如人意。从这个意义说,人文精神论者指出的世俗化与大众文化的“粗鄙化”倾向是一个不可否定的事实。
这里的关键是:中国的世俗化本身就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出现的,与西方极不相同。从小处说,90年代的世俗化的历史语境是:80年代末现代启蒙随政治风波而俱去,中国社会进入了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陷于冷冻、经济的市场化畸形膨胀的历史时期,这种局面一直延续至今。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大众文化与世俗化从政治的大逃亡一头扎进了经济的大合唱,文化与经济联手,而面对政治则表现出了它的软弱与妥协(当然这有客观的历史原因)。事实证明:从《渴望》开始的大众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存在着极大的妥协性,这是不可否定的,我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今年八月号对此作过详细分析。这就使得中国当前的大众文化的现代意义大为削弱。可是,我看到现在的人文精神论者与世俗化的批判者很少是从这个角度谈问题的,拥护大众文化的人对此也很少谈及。从大处说,中国的世俗化与大众文化是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三重语境中出现的,因而是一个极其混杂的价值与文化形态。它一方面带有解神圣化的现代意义(尽管可能不是有意识的),同时也体现出了对于传统前现代享乐主义的纵向承受以及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横向移接,在此,人文精神论者批判的“处世哲学”、“滑头主义”、“玩文学玩人生”、“虚无主义”、“认同废墟”、“逃避沉重与痛苦”,的确抓住了大众文化的一些负面性。这些负面性也使得中国社会文化的世俗化不像西方的世俗化那样带有更多健康向上的现代精神、开拓精神与规则意识。而对此,世俗化的拥护者也是缺少分析的。
由以上分析可知,对于中国的世俗化与大众文化、对于文艺中消遣娱乐性的凸显,必须充分考虑到它的方方面面,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评判尺度是历史主义的还是文化哲学的,它的具体指向及其局限性,明确自己所指的是世俗化的哪个维度,而不要用化约主义的方法把对象简单化。只看到它的解构专制主义的现代意义,或只看到它的后现代的游戏人生与虚无主义,都是相当片面的。总的说来我对大众文化与世俗化的态度是优化它而不是拒斥它,也不是拥抱它。其核心是批判其前现代的陋习,警惕其后现代的误区,强化其现代性的革命精神。
然而人文精神论者与道德理想主义者在批判世俗化的时候,恰好没有分清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与对于后现代性的批判。他们常常笼统地把中国的大众文化与世俗化归入后现代文化的范畴,然后不加转化地将西方的批判理论(如对现代文化的批判、对传媒霸权主义的批判)用于批判中国的世俗化与大众文化。这样不但批判的准确性与力度大大削弱,而且不应当地忽视了世俗化与大众文化的进步意义。
标签:政治论文; 人文精神论文; 大众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艺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宗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