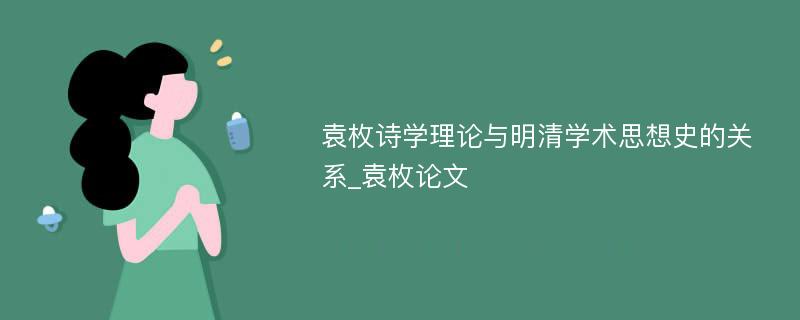
袁枚诗论与明清学术思想史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思想史论文,学术论文,关系论文,诗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袁枚的《随园诗话》及《小仓山房诗文集》等,是他诗学思想的渊薮,如分类梳理则可以见出他的诗论在学术思想史意义上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
其一,他的诗学可以归结为论才、论学、论艺三个方面的整一理论。关于“才”的论述又可进一步阐发为论性灵或论性情,是其诗学的主脑,如其所述的“才者情之发,才茂则情深”。(《李红亭诗序》关于“学”的因素,他赞同李重华(玉洲)的见解,录其所论的“凡多读书,为诗家最要事。所以必须胸有万卷者,欲其助我神气也”。(《随园诗话》补遗卷一,二条)然而,袁枚又极为厌恶博学者之好卖弄,好用典,好以考据入诗的陋习,因而每将“性灵”与“学问”对峙。他主张的是善于读书,实际上讲求的是“诗人之学”而非学人之诗。袁枚对诗“艺”的论说亦不少,比较集中的则在其《答祝芷塘太史》中。他说作诗当留意者约为六条,其中的二条、三条、五条,则分别涉及选题(“山川关塞离合悲欢,才足以发抒情性,动人观感”),炼句(“百炼之钢千炉才铸一剑”),选韵(“非响者不押,非稳者不押,非清脆者不押,非在眼前者不押”),修辞(“情欲信,词欲巧”、“春秋时郑国词命先草创,后讨论,再修饰而润色之”)。因而可以将这一书信文字看成袁枚较为完整的“诗艺”之论。其中,性灵为纲领大要,有超乎文艺学的重要意义。
其二,尤可注意者,是袁枚在其诗论中对妇女乃至村童牧竖、奴仆婢妾等人物的才情多所称颂,其中出语令人意外之处比比皆是。兹举数条如下:
1.诗境最宽,有学士大夫读破万卷,穷老尽气,而不能得其阃奥者。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此诗之所以为大也。(《随园诗话》卷三,五○条)
2.余游南岳,往谒衡山令许公。其仆人张彬者,沅江人,年二十许,见余名纸,大喜,奔告诸幕府,以得见随园叟为幸。既而许公召饮,命彬呈所作诗,有“湖边芳草合,山外子规啼”“远岫碧云高不落,平湖萤火住还飞”之句。果青衣中一异人也。(《随园诗话》卷十三,七二条)
3.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善取之皆成佳句。随园担粪者,十月中,在梅树下喜报云:“有一身花矣!”余因有句云:“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余二月出门,有野僧送行,曰:“可惜园中梅花盛开,公带不去!”余因有句云:“只怜香雪梅千树,不得随身带上船。”(《随园诗话卷二,三条》)
至于其余论录女子诗、秀才诗及少年诗者,更是不胜枚举,这在同时代诗论、诗话中是非常罕见的。钱钟书先生对此评论道:“故随园此书,无补诗心,却添诗胆。所以江河不废,正由涯岸不高;惟其平易近人,遂为广大教主。”(注:《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5页。)所言不无讥诮,但亦认可袁枚诗论“平易近人”,深得广众之心。这种广采兼收,不轻蔑低贱的做法,也包容着思想史上的消息(容后详议)。
其三,袁枚诗学立足的学术基础,在于他不崇宋儒,更轻篾所谓汉学。因此他诗论中所列的弊病如忌模仿古人,忌俗学,忌卖弄书本知识,忌持律过严,忌叠韵、次韵,忌假道学(注:《答李少鹤书》,《随园尺牍》卷八。转引自《清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湾成文出版社,第480页。),忌求名心切等等,其中尤为所忌而反复审论的则在于忌以考据入诗。袁枚在这方面的批评也最为激烈。其言曰:
近之诗教之坏,莫甚于以注夸高,以填砌矜博。捃摭琐碎,死气满纸,一句七字,必小注十余行,令人舌绎口呿而不敢下,于性情二字,几乎丧尽天良。(注:可见其《再与沈大宗伯论诗书》中为王次回艳情诗之辩护及对《诗经·关睢》的解释。)
又称:
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其次,则骈体文,尽可铺排,何必借诗为卖弄?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惟李义山诗,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驱使,不专砌填也。余续司空表圣《诗品》,第三首便曰《博习》,言诗之必根于学。所谓不从糟粕,安得精英是也。近见作诗者,全仗糟粕,琐碎零星,如剃僧发,如拆袜线,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虑吾说之害之也,故续元遗山《论诗》,末一首云:“天涯有客号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注:《随园诗话》,卷五,三三条。)
其言最尖刻处甚至及于考据学者的人品:
考史论经,都以故纸堆中得来,我所见之书,人亦能见;我所考之典,人亦能考。虽费尽气力,终是叠床架屋,老生常谈。有如贾人屯货,胥吏写供,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就使精凿异常,亦使他人观览,与我何与?况词章之学最古,始于六经,盛于三传,皆殷周贤圣之才;考据之学最后,始于郑马,盛于邢孔,皆汉唐龌龊之士,甚至戴圣、欧阳歙尽赃吏矣!其拘牵附会,穿凿侜张,殊非“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之旨。不过天生笨伯,借此藏拙清闲则可耳。有识之人,断不为也。(注:《寄奇方伯》,《随园尺牍》卷八。转引自《清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第480页。)
以上所列袁枚诗学中之三端,即重性灵,平视卑贱者,排斥伪道学及考据学对诗歌的不良影响,实际上都与明清时代学术思想史有着相当深切的关联,并不是诗学、诗艺中的细枝末节问题。大略而论,袁枚诗学的特质当从“外在机缘”与“内在理路”两个方面细致考求,但因篇幅所限,我这里论述的重心偏于“内在理路”的脉络上。
而在“内在理路”爬梳中,袁枚文艺学思想与颜李之学的关系实为一大关节点。
在近人中。郭绍虞先生是提出这一问题并予以讨论的学者。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袁枚之文论》中有相当深入的探讨,在这一节的末尾郭先生曾感叹道:“真想不到颜李学派乃与性灵派之文人发生关系。”(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64页。)初读绍虞先生所论袁枚与颜李之学的关系时亦曾产生误解,以为称袁枚是“颜李学派的信徒”未免牵强,担心绍虞先生受50年代思想改造的影响,非要为“清初新兴的市民阶级的影响”找出文学上的落实者,也担心绍虞先生只寻求程廷祚与袁枚的“往还颇密”这一孤证,难以坐实袁枚在思想上的确受到“宗主颜李学的程绵庄”的影响。然而在仔细阅读《袁枚之文论》一节并参较其他学术史著作后,却认识到绍虞先生慧眼高明之处。
要之,在于研究不可死做。如果强以所谓“影响研究”为本,细致考求程廷祚对袁枚的影响在何时何处,则必为穷钻牛角而无所得。如果呆板地平行比较颜李与袁枚论学宗旨、治学、取径的异同,则又必定发现颜元讲求的是“兵、农、礼乐”三事,主张学者身体力行,而反对专门著书作文,这与袁枚一生自甘文士诗人,沉潜于诗文之中显然相互冲突而不能相容。
因此,这里不能拘泥于表层文字异同的考究,而必须向深层学理推进求其是否可能会通。以期获得较为深切圆通的理悟。
钱穆先生曾言:“夫学术之异同,难言之矣,而学术之流变,尤为难言。”(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3页。)论袁枚诗论与颜李之学的关系既有异同的比较,又有流变的叙说,其难不言自明。以下将就异同及流变两点而分论之。
袁枚论学与颜李的相异之处,主要在于对程朱的评价上。颜元视宋儒尤其是程朱一系为大敌,声称“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究其缘由,主要来自个人早年经验、历史教训及康熙时代士人风气之反省。颜元早年治学曾经历若干变换,从神仙导引术至陆王,又至程朱。后来因为居丧时严守《朱子家礼》,每天进食及哀哭都遵朱熹书中的规定计时而为,结果因抑情和减食致病几殆。其后,颜元校之以古礼,察觉朱熹擅改古礼之误,进而省悟程朱、陆王均受禅学、俗学浸淫,遂上溯周公、孔子,讲求六德、六行、六艺及四教,而自成以事功力行为特色的儒学系统。面对历史的惨痛经验,颜元将宋、明两朝亡于异族的缘由,归结为宋儒、明儒之弊,简言之,即为“无用”二字。他认为宋儒自高身份,视汉唐为“杂霸”,虽自命为继承中断千年之道统的圣贤,却在国家危难之机,既不能建“扶危济难之功”,又不能出“可将可相之才”,遂使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难道可以因此称宋代为“多圣贤之世?”颜元又说:“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艰,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凄然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惶久之。”(《存学编》)在颜元看来,已往之历史已不可追回,然而康熙时期程朱之学转盛,一时间以言“格物穷理”为风尚。颜元曾经对李塨说:“予未南游时,尚有将就程朱,附之圣门支派之意。自一南游,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也孔门敌对。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颜习斋年谱》)所谓“禅子”、“虚文”即是颜元所说的:“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与桐乡钱晓城书》)既然视宋儒为大敌、大害,颜元对程朱所倡导的主静,多读书,好著作的“尊德性”、“道问学”的主张也一一加以排拒,称读书非但无用,且如吞食砒霜,是自害自戕的行为,而对著述文章,则称“文章之祸,中于心则害心,中于身则害身,中于家国则害家国”。(《颜习斋年谱》)颜元所创的“读书无用”论及“读书有害”论,为当时石破天惊之语。他所主张的“兵、农、礼乐”诸事也的确可以导致有别于空谈心性的功利实学,开出经世之新途。然而颜元用语激烈,持论极端,不能恰如其分地剖析宋儒、明儒的功过。因此其学说在当时仅传一代至李塨。自李塨起至王源、程廷祚之辈,力行于兵、农、礼乐的主张已声息渐消,而别寻他途,回到了读书与著述的传统路径上。然而颜李之学的精神有如地火虽不彰显却依然延续。
袁枚论宋儒及论颜李,有数端可以列举:
一、对宋儒的评论能持两端而执中。但对后儒过分尊崇宋儒之论与道统说则攻之不遗其力。袁枚在这方面的零星议论较多,专论者则集中在《答尹似村书》、《再答似村书》、《与程蕺园书》、《再与蕺园书》、《宋儒论》及《书大学补传后》等中。
袁枚对宋儒的批评约有这样几点:1、对朱熹的直接批评。袁枚认为《大学》一篇,虽出于《戴记》,但“意义周匝,绝无隙漏”,先言“治平齐修诚正之先后”,又虑“蹈思而不学之弊;故以致知格物次之”,又恐蹈博而寡要之弊,故又以物有本末知所先后晓之,而且以听讼一章证之,其始终条贯,灿若列星,传固未尝缺也。”但是朱熹节外生枝,著《大学补传》附于正文之后,并在其中强作解人,反而导致失误。袁枚对朱熹的批评集中在两点上:其一,朱熹对“格物致知”加以补充,说:“所谓格物致知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理也。”(注:见《四书五经》,中国书店,1985年版,上册,第12页。)袁枚认为说得过分,“因为天下物无尽时”,这样无穷尽地一物一物格过来,何时方能致知?其二,朱熹自己也约略知道即物穷理的过程漫长或至于遥遥无期,则又有所补充承诺:“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注:见《四书五经》,中国书店,1985年版,上册,第12页。)袁枚对这一补充解释尤其不满,认为这种“一旦”的承诺“杳无年月”,不知何时所期。更为严重的是朱熹所谓的“一旦豁然开朗”,恰恰“坠入佛氏参禅顿悟之邪径而不自知”,而且这又开启了“陆王创为良知之说”与《大学》本义大相牴牾的弊端。(注:以上袁枚所言,均录自《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0~1811页。)
2、对宋学在当时影响的批评。在《与程蕺园书》中袁枚称:“黄氏《日抄》称吕哲习静,其仆夫溺死不知。张魏公(张浚,作者按)自言有心学,符离之败,杀人三十万,而夜卧甚酣。宋学流弊,一至于此。”(注:以上袁枚所言,均录自《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63页。)
3、对道统论的批评。对道统论的抨击也可以看作是间接批评朱熹。因为朱熹在他的《大学章句序》里公然声称,这一《大学》之明法由曾子作为传义,“及孟子没而泯焉”,直至“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孟氏之传。”(注:《四书五经》,第2页。)这无异于公倡宋儒继统之说,袁枚对此最为厌恶。
二、袁枚对宋儒、宋学亦有赞扬、肯定的意见,例如他说:“总而论之,汉、唐、晋、宋诸儒,俱有功于孔子,俱为仆所敬畏。宋儒立身,亦卓卓可师。”(注:以上袁枚所言,均录自《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62页。)《宋儒论》的立足点在于否定一切“过尊”与“过攻”。他说:“过尊者迂,过攻者妄。此吾宋儒之论所以作也。”(注:《小仓山房诗文集》第1606页。)在论文中,袁枚首先肯定宋儒对佛、老之学仪神易貌,创立心性学的功劳。这是对过攻者的回答。其后袁枚又认为宋儒虽然努力,但没有超越颜、闵、思、孟诸前贤,于圣道仍未能至,也难免有不符圣心而毫厘有失之处。这是对过尊者的回答。其最终结论是:“后世学者未必能胜宋儒,亦未必不如宋儒。要唯是其言,而不必迂拘墨守;非其言,而不必菲薄诋诃。则所以论宋儒者定矣,所以论汉、唐、晋诸儒,亦定矣。”(注:《小仓山房诗文集》第1607页。)
三、正是在讨论宋儒的功过中,袁枚涉及对颜李学术的评议。
程廷祚与程晋芳在书信往还中对颜李之学有激烈的争辩,廷祚遂将书信寄交袁枚,这才有了这封《与程蕺园书》及《再与蕺园书》。在袁枚看来,程晋芳“守宋儒太狭,诋颜李太遽”,对程廷祚多有袒护。袁枚一则认为“道颜、李讲学有异宋儒者,足下以为获罪于天,仆颇不谓然”,觉得颜、李对宋儒的激烈批评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如果宋儒能像子路那样闻过而喜,则必定欢迎颜、李的批评。而且,颜、李对宋学的批评正切中要害,所以袁枚说:“宋学流弊,一至于此。恐周、孔有灵,必叹息发愤于地下,而不意我朝有颜、李已侃侃然议之。”袁枚论颜李学的重心则在称赞“其论学性处,能于朱、陆外别开一径。”当然,袁枚对颜、李也有所批评,称其“文不雅驯,论均田封建太泥”。两相比较,可以清楚地见出袁枚的倾向。对颜、李的批评只在局部论点,只在文风,而对其肯定则在总体,在于其开辟创新的精神。
回顾以上所述的颜李之学的要旨以及袁枚对宋儒与颜李学的评论,大约可以概括为如下诸点:
第一,颜李以宋儒为大敌,宋学为大害。而袁枚则不作如是观,但其中埋藏若干曲折未发之意。例如,袁枚不否定颜李对宋儒的批评,而且他了解这种批评的实质和意义。这种不否定是以代宋儒言“闻过则喜”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或者是以肯定颜、李能在朱、陆之外别开生面的方式传达暗示的。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并不引证、不重复颜李对宋儒锋芒毕露的批判。或许可以说,袁枚乐于以较为沉默的方式坐观颜、李之成。但袁枚论朱熹思想似儒实禅,论宋学流弊至于丧失人性,至于误国,却是在要害处深刺一刀,与颜、李之批评在实质上颇有一致。
第二、袁枚不可能完全赞同颜元的禁绝读书著作的倾向,他以文士、诗人自我定位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因此他断然不会苟同颜元关于文章之祸“害心”、“害身”、“害国家”的立论。袁枚自己的一生证明他与颜、李学的分野之一正在于如何看待诗文、章句之学。
在这里,一个非常奇特的逻辑终于浮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颜李之学的大旨是曲曲折折的,一步一步地演变成袁枚所追求的目标。
这一奇特的逻辑又大致展开为两种途程。其一,是颜元学说的自然流变过程。颜元至57岁时才走出穷乡僻壤,但仍然坚持不讲学,不著述,以访友论学为活动的中心,游历的范围大致以河北南部及河南为限。他在62岁时曾应肥乡县漳南书院之聘,期待在书院形成实践他理想抱负的基地。但由于一场洪水的来临冲毁了书院屋舍,遂告归还乡以至终老。李塨则21岁时即从学于颜元。从他一生行为看,抱定的宗旨是:身体力行实践颜学;通声气,广交游,以传颜学之道。于前者,曾先后应当时浙江桐乡县令郭金汤与陕西富平县令杨勤之聘,往两地协助治理县政而有成效;于后者,则结交南北著名学者如万斯同、王源、方苞、阎若璩、毛奇龄、程廷祚等,在学问上多所切磋,也因此逐渐转向著述与考据。尤其自结识毛奇龄后,更陷入治《易》考《古文尚书》的学术漩涡中而一发不可收。其间尤可提出的是李塨曾经选编《陶渊明集》、《韩昌黎文》,已经同当时学者渐趋一致。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习斋北方一老儒,而其驱迈之气,实欲扫除千古壁障。今恕谷求以明习斋之道,而不免沾染南方学者考古穷经之习,即已不脱书生气局矣。移步换形,貌存神离,自信不坚,引外为重,宜不足以转捩一世之视听也。”(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5~236页。)至程廷祚,虽然依旧推崇颜李恢复三代学教戒规,叹服其摧陷廓清之力量,但也愿意调停程朱与颜李的对立,认定宋儒是圣贤之徒,不可以妄加讥评,又认定颜李能在大是大非处立论,可谓先圣之功臣,宋贤之益友。(注:参见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2~133页。)再至袁枚,则是较为纯粹的诗人、文士了。另一途程,则属于暗中消息,隐隐然有一学理的脉络,使袁枚相通于颜李之学,极而言之,也通向阳明之学。
至于颜李学说与阳明学在学理逻辑上的关连,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此有极详备而精当的分析,发明王阳明的“拔本塞源”之论与颜元思想的相通、相合乃至相异而可互补的论述。袁枚思想和阳明学相通消息于以下数端可见。
其一,良知之说,以一己之心性为是非的标准,不假外求。袁枚诗论的核心即是一己的天赋性情或曰性灵,亦不应外求。
以下以并行方式罗列袁枚论诗与阳明论学之若合符节之处:
袁枚
若夫诗者,心之声也,情性所流露者也。
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
诗宜自出机杼,不可寄人篱下。
近日有巨公教人作诗,必须穷经读注疏,然后落笔,诗乃可传。余闻之,笑曰:且勿论建安、大历、开府、参军其经学何如,只问“关关雎鸠”、“采采卷耳”是穷何经、何注疏,得此不朽之作?(注:以上袁枚所言分别出自《答何水部》,《随园诗话》卷五,三三条,《答王梦楼侍讲》,《随园诗话补遗》卷一,七条。)
王阳明
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性,自然灵昭明觉者也。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
夫舜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或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以而为之邪?(注:以上王阳明所言分别出自《大学问》(《全书》)以及《答聂文蔚》、《答罗整庵少宰书》、《答顾东桥书》,参见《象山语录·阳明传习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第68页与第46页。)
以上袁枚所论为性灵之诗,阳明所论为良知之学,所论对象有所不同,而究其旨要又确有相通之处。王学的宗旨原本就是要打消种种中间的障壁,以直觉顿悟方式发明本心,体认圣道,从而否定了格物致知、即物穷理、读书问学的道路,也就相应地突出天赋情性的尊贵,为文学理论上的主情说奠定了心学的基础。而袁枚诗论的中心也恰恰在于强调天赋才情的自然灵动与活泼可爱,反对一切限制拘束性灵的陈规戒条。作为诗人,就必须自出机杼,甚至是师心自用,不需要依仗道统,也不需要穷经读注而寄人篱下。正如阳明所说,大舜的不告而娶,不必有前人拟定的准则,不必寻求祖先的典籍为依据。而只须求之于己心,求之于良知。袁枚也几乎是运用同样的论辩方式,以《关雎》等作为最有力的例证,质问初始的诗歌又有什么经典的仗恃、注疏的依据。在王阳明看来,只有良知才是权衡轻重,判断是非的标准,而一切在本心之外的尺度则都是虚假的、累赘的、不可靠的。在袁枚看来,则是:“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注:《随园诗话补遗》卷一,一条。)唯有性灵才是诗歌创作的源泉和动力,而一切在性灵之外的东西,只不过是第二义的,从属性的,只可以扶助性灵,而不能遮蔽或妨害性灵。
其二,持良知之论,必有平等之心;而主性灵之说,也必趋于消解尊卑之别。
袁枚诗论,尤其是《随园诗话》的编选原则,多年来招致了许多的指责批评。直率者,称之为“滥”;浅薄者,则斥之“为富贵人家作犬马”;宽厚而善解者如钱钟书先生则谓“江河不废,正由涯岸不高;惟其平易近人,遂为广大教主”。所谓“平易”,所谓“近人”,事实上均立足于众生平等的观念之上。所以钱钟书先生借唐代张为《诗人主客图》以白居易为广大教主用以形容袁枚,正是在不经意中道出了事情的真相。其实就在当时袁枚弟子梅冲就因蒋士铨称其师为诗佛而特意写过一首《诗佛歌》。其中有“佛之慈悲罔不包,先生见解同其超“一心之外无他师,六合以内皆布施”等句,赞扬其师袁枚本人虽然不信佛乃至排佛,但的确有慈悲心肠。他曾经引用当时名臣兼大学者李绂的名言为自己编选《随园诗话》的意图做过说明:“李穆堂侍郎云:‘凡拾人遗编断句,而代为存之者,比葬暴露之白骨,哺路弃之婴儿,功德更大。’何言之沉痛也。余不能仿韦庄上表,追赠诗人十九人。乃录近人中其有才未遇者诗,号《幽光集》,以待付梓。”(注:《随园诗话》卷十三,一条。李绂之学术与事迹及其对袁枚的影响,也不可小视。其行为有所不同,但都有当时罕见的豪杰之士的气概。)袁枚之赞后生新进,赞穷士寒儒,赞闺阁才女,都不是随意而为的。尤其他对女子的同情甚至偏护,更是对宋儒倡导的纲常道理的冲击。与阳明精神有相通之处。
王阳明的平等思想,倒并不在于人们所熟悉的“满街都是圣人”这类王畿的夸大之词,而是他自己常说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唯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答顾东桥书》)“与愚夫愚妇同的,是所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传习录》下)这些话语中显露的,是人性中固有良知、善端的观念,在此原无贤愚不肖之分,区别只在能“致”与否。应该说,这一天赋人性良知良能的平等观,正是阳明哲学的重要基石,而在这一平等观更得到了“天地万物一体”的世界观的支持。阳明说:“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传习录》上)由阳明学说看袁枚的诗学,可以看出袁枚所主张的,其实是性灵平等的观念。性灵的平等,是讲人性内涵的平等,在此也没有贤愚、尊卑的差别,但这还不是袁枚诗论的核心。同样,性灵也有“致”与“不致”的区分。在袁枚看来,能致性灵者,性情的自然发露就可以有好诗佳句,虽然身为寒士、为女子、为野僧、为粪夫、为童子少年,在其致时,也应一视同仁,在他的诗话中录而存之。袁枚录李穆堂言,表现出他有相近于“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的思想,这也正是他搜集“有才未遇”者诗作为《幽光集》的道理,恰恰又一次证实了他自述的“然则诗话之作,集思广益,显微阐幽,宁滥毋遗”的原则是有本有原的。
需要有所说明的是,对袁枚诗学思想中所包含的这些因素也不应当过分拔高,生硬联系到诸如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思想自由等等现代概念范畴上去。说到底,袁枚只是乾嘉时期的一名诗人。他的志向、他的兴趣、他的事业并不在儒学的发明上,而是沉浸和投入于诗歌文学之中。然而他在乾嘉诗坛上的所作所为却充盈了一股豪杰之气、壮士之情。这种豪杰气概不但是袁枚,而且在王源、李贽、颜山农、何心隐、黄藻、王畿直至王阳明本人身上都可以见到,俨然形成一条脉络。这虽然不是文艺学史所应专注的题目,却是学术史与文艺学史交迭的有趣事例。
其三,主致良知之说,必重视教育尤其心灵教育;而袁枚持性灵之诗论,亦不忘兴观群怨的宗旨。
看阳明学应当对王守仁本人与王学末流有所区分,不能视阳明为空谈心性之徒,更不能将后学末流的弊病栽在阳明头上,以为王学为诬世惑民之学。阳明学前人讨论甚多。这里,仅就其重要论述涉及教育主张之处,略加引述。
其一,申述教育在其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宇宙观中的地位,其说为: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由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有我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
其二,对中国历史长时期陷入功利争夺而导致学术分裂而同趋于邪路的状况做出总结概括: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猖,孔孟既殁,圣学晦而邪说横……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遂以芜塞。……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是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若是者,纷纷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蹊,莫知所适……间有觉其空疏谬妄,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奋,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止……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注:以上引文均出自《答顾东桥书》,见《阳明传习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第49~52页。)
其三,注重于童子教育,强调歌诗的启蒙陶冶、宣泄洗涤的作用。其言曰:
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洩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阳明传习录》第78页。)
阳明对当时之儿童教育有深切的了解,对那种“鞭挞绳缚,若待拘囚”而使儿童“视学舍如囹狱”“视师长如寇仇”的教育方法十分痛恨,因而主张以歌诗启蒙的情感教育、快乐教育,使儿童在诗歌、礼节、读书的教育中如沐浴“春风时雨”而枝条畅达。
袁枚一生所关注的事情极多,但是对儿童教育似乎少所议论。略有关系的则可见之于他的《祭妹文》与《书院议》。前者为凄婉真挚的名篇,其中对幼时与三妹同诵《诗经》之作的往事记忆尤为深切:“余九岁憩书斋,汝梳双髻,披单,温《缁衣》一章。适先生户入,闻两童子音琅琅然,不觉莞尔,连乎则则。此七月望日事也。”(注:《小仓山房诗文集》,第1436页。)在《书院议》中则对当时书院制度有所不满,称书院中“教士者加苛焉,是视士不如兵也”。他所向往的,是书院中二三十人,“师师友友,弦歌先王之道以自乐”。在这些片言只语的议论中,可以揣测袁枚的教育态度和其诗学宗旨一样,中心在于强调情感的关键作用,强调真实之情感动人的功能。在《书复性书后》文中,袁枚不赞同李翱的尊性而黜情之论,而称:
夫性,体也;情,用也。性不可见,于情而见之。见孺子入井恻然,此情也,于以见性之仁;呼尔而与,乞人不屑,此情也,于以见性之义。善复性者,不于空冥处治性,而于发见处求情。(注:《小仓山房诗文集》,第1640页。)
转而论及诗歌,自然更以情为中心,而又特别重视诗歌“兴”的感发作用,其言有:
1.圣人称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
2.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诗可以兴。”两句相应。惟其言之工妙,所以能使人感发而兴起,倘直率庸腐之言,能兴者其谁耶?(注:以上两条,分别见于《随园诗话》卷十二,二四条,《随园诗话》补遗卷一,一条。)
袁枚论性情并不盲目将情性等量齐观,在《书复性书后》中将性与情视为有“上中下”之分别,而尤其强调“情欲信”即情感的真实性。尤可注意的是,袁枚论真情时,称引王阳明所论,显然视之为同道。其言曰:“王阳明先生云:‘人之诗文,先取真意。譬如童子垂髻肃揖,自有佳致;若带假面,而装须髯,令人生憎。’”(注:《随园诗话》卷三、七条)
以上所述,虽然迂缓曲折,但终究可以看见阳明学与袁枚诗论在重视情感、重视兴会感发方面的相通之处。所不同的是,阳明为一代大宗师,其学理精深博大而呈现宏阔壮观的体系;袁枚的意见散见于其文、其诗话议论之中,不免吉光片羽,未成条理严密的架构,但分疏而综合之,也可以见出其中自有关联条理。
袁枚诗论注重通达而不偏执,对阳明之学议论不多,也不顶礼崇拜,但是从深处发掘,阳明的良知之学力主功力而必兼性情,则与袁枚性灵诗论的主旨大要相会。因此而可以断言,论学术之是非与流变,不能只以文字表面上排比勘校,而应特别重视内在精神的相通相契,甚至于持论者自身不自觉之处挖掘之。适度运用此方法,无疑是研究深入之一重要途径。
标签:袁枚论文;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文; 小仓山房诗文集论文; 大学论文; 明清论文; 文化论文; 随园诗话论文; 四书五经论文; 思想史论文; 宋儒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