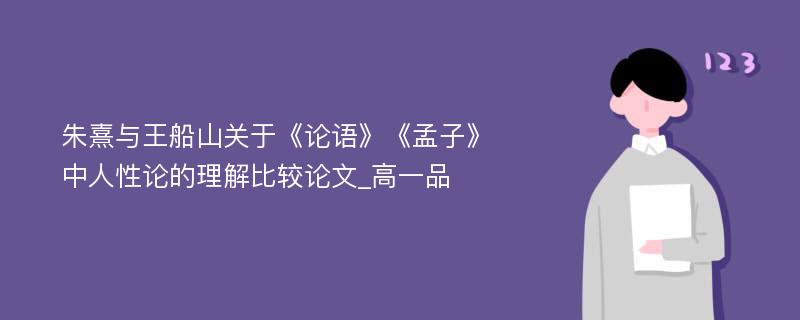
高一品
(黑龙江省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150086)
[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论语》与《孟子》中朱熹与王船山对孔、孟二人人性论的理解,说明其各自所持“性善论”与“性近论”的差异,并通过二者自身体系中的本体论基础对其人性论进行分析。最终指明朱熹理论的内在矛盾性及王船山对朱熹思想的批判继承关系。
[关键词]《论语》 《孟子》 朱熹 王船山
一、引言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对《论语》、《孟子》等内容进行详细注释与分析,王船山在《读四书大全说》中也对《论语》、《孟子》等先秦著述进行解读,而本文立足《论语》与《孟子》的文本,分析二者在其各自的著作中对孔、孟人性论的理解,并通过其自身理论中的本体论基础分析其选择性善论与性近论立场的原因。
二、《论语》中的人性论
通过《论语》中“有教无类”一句,朱熹认为,人性皆为善,如果有不善出现则是因为后天的习染,所以只要对人进行教化,则人人均可恢复善性,“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四书集注》,卫灵公第十五)可见,朱熹肯定人性皆善,而人的有善有恶并不是因为他们“性”的不同。而对于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一句,其认为,存在善与恶的差别的人性不是性之本,而是“气质之性”。气质之性的善恶是受后天的习惯的影响的,而性之本是“理”,理是无不善的,因而人性如同孟子所讲是皆善的。可见,朱熹认为气质和习惯对人的善恶影响很大,且其接受了二程关于人性的思想,认为人性分为性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性理之性无不善,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因而其认为孔子的性相近是指气质之性而不是性理之性。实际上,虽然朱熹在对《论语》文本进行解释时遵照作者原意,说明后天养成的“习”对人的善恶影响更大,但在朱熹自身的理论中,其认为气质及其所产生的私欲对人的善恶形成的影响大于习。
不同于朱熹,王船山认为,孟子的性善论与孔子的性近论差别并不在于是针对性理之性言,还是针对气质之性言,而是在于孟子是从人性的本源言性善,而孔子是从现实的人性言性近。
王船山认为,从善与性生成的时间性的角度,《易传》中,善在先而性在后,而“性善”中性在先而善在后。并且,一方面,在“继之者善”的对比下,船山认为孟子的说法是“以继之者为性”。另一方面,此种“成之者性”是二程所称,构成具体人的“气禀之性”,即与“天命之性”相对的“气质之性”,是气之本体气化而凝聚成的固定形体中的性。对此,船山曾将形成人的气划分为“天地之气”、“形质之气”、“形后之气”。其中,“天地之气”即为气禀成形以前的阶段,此一阶段对应孟子称为“善”的性,属于“继之者善”。而二程的气禀之性则对应以“天地之气”为材料的“形质之气”凝聚的阶段,因而二程所谓性是成之者性。实际上,对于性与气质的问题,船山反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元人性论,且反对朱子性寓于气质之中的说法。首先,朱熹所认同的二元人性论是基于其认同“性即理”的观点,而在其理论中,理又是作为独立于气而存在的实体,因此存在依于理的天地之性与依于气的气质之性的区别。而在王船山的理论中,理并不是可脱离于气而独存的,而是作为气的规则、条理、属性而存在的,因而其人性论是一元的。此外,其认为性寓于气质之中的叙述方法应用“气质中之性”的提法代替。“性寓于气质之中”或“性在气质之中”说明气质是性的外在的居所,这种外在性说明其是可替换的,但对人而言,人的性与人的形质是不可变换的内在关系。两种说法之间的差别类似于“哲学在中国”与“中国的哲学”的区别。可见,朱熹与王船山在人性论上观点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其对理气关系的态度。
王船山在《论语说》中,对孟子性善论的解释为:“推其所自而见无不一,故曰‘性善’。”(《读四书大全说》)船山认为,孟子此种“性”实际上是指性的源头,而不是各个具体的人性的善,因作为源头的“命”是无不善的,所以性善也具有合理性。而作为“性之本体”的性的“善”,并不是在具体存在者中,与恶相对的善。其认为以“诚”说明属于天道存在的“性”更为妥当。孟子以善表述性,是根据各个具体的可见的人性做出的判断,只能说明“性之定体”,即已完成的、人所展现出的性,而未能到达“性之本体”,即本源性的性。因而此种观点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而以“诚”论性则是王船山将天道论与人道论相结合的一种体现,“诚”是其用于表述天与属于天道存在的属性的范畴,而以“诚”表述性,说明其将“性”认作与天具有相同属性的存在,人性的仁、义、礼、智与天道的元、亨、利、贞相对应。诚作为一种本源性的存在,作为善的前提,将善赋予人,使善存在于各个个体存在者之中,成为诚的结果。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单一的源头需要分殊为“多”,成为各个具体的人性。人性既然是分殊的结果,则必然不再是同一的,而是各异的,但由于其源头是共同的,因而其差异应相对较小,所以可归结为孔子的“性相近”说。如上述所提及,船山认为孟子的善应作为命的规定性而不是性,在《周易》中,命属于“继之者善”,性属于“成之者性”,成之是指形质。形质形成后性随之凝聚。质秉承由命而来的性,但已经不再是源头的“一”,而是各个相近的万殊。因而不能说性善而只能说性近。
三、《孟子》中的人性论
朱熹在《孟子集注》中,对“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一句进行分析,认为人性是禀受于天的,因而是至善而无恶的,如同尧舜的人性,而世人之所以未能达到尧舜的圣贤境界是因其被私欲所蒙蔽。所以人与圣贤的本性都是相同的,差别只在于圣贤能够充分发挥和实现其本性,而普通人则沉迷于私欲而丧失其本性。因此,人若想要实现善,不必向外探求,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喜、怒、哀、乐未发是善,发而皆中节为善,只要进行道德修身即可实现善。
关于《孟子·告子》中孟子与告子人性的论辩,朱熹认为,告子所称“生之谓性”之中的生是指生物的知觉运动,是来自于天之“气”的,属于形而下的范畴,而性则是指能生发仁、义、礼、智、信的存在,是来自于天之“理”的,属于形而上的范畴。在朱熹的理论体系中,理与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础。人禀受理以成其本性,禀受气而成其个体生命,其在理气论的基础上以“性——生”二元论解释人与动物的区别。人与动物相同,都是禀受了气才形成其自身,因此告子认为二者并无差别,而人是禀受了仁义礼智信的全体,因而性为全善的,而动物只禀受了部分的性,因而各个动物之性中是有恶的,由此人与动物相区别。所以,朱熹认为,告子与孟子对于人性与动物性是否存在区别的问题产生分歧的根源在于告子以气为性而孟子以理为性。此外,朱熹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只在于是否禀受了全部的理,也在于二者禀受的气是否是正气,只有人能禀受正气以致禀受理的全体并使得理的全体存在被自身所保有的可能。而要真正实现使本性保持理的全体则要进行戒慎和慎独的修养功夫。
对于《告子》篇中,孟子与告子关于人性的论辩,王船山认为,人性在根本上不能比拟于物,凡是把性比拟于物都是未曾“见性”,“知性”。 而对于朱熹将孟子与告子的争辩理解为告子是以气为性,将气质之性理解为本然之性的观点,王船山认为,此观点说明朱熹认为本然之性为善而气质之性有不善。而王船山并不认同性本善说,而是认为气本善。王船山认为,告子的错误在于其只知道气之用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而不知道气之体为全善。在王船山理是气的运行法则,理气一元的理气论基础上,其认为,人与动物的善与恶的区别在于,人的理善,所以人的气无不善,而动物的理不善,则动物的气不善。此处理即为性。王船山在对人与物的理气善恶的分殊的基础上,强调天道的理气善恶,在天道观上,气决定立而不是理决定气,气本身是无不善的。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理解,太极生两仪,两仪即为阴阳,阴阳变化交合,生成万物,从而产生了善与不善的划分。最初,两仪为善,阴阳即为善,而阴阳即气,因而气为善,此种善即为体之善。但此种气的善只能限于变合之前,在进行变合的动作,即经过体展现为用的过程,由于变合自身没有方向,因而不能保证变合的结果仍为善。且天自身没有意志,没有选择善与不善的能力,只能顺应变合自身的发展。因此,天道在变合后,生成善的结果即为人,生成不善的结果即为动物。
此外,对于性的善恶与情、才的关系,朱熹认为,《孟子》中“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孟子·告子上》一句可理解为,情是性的发用与表现,为情本只是可为善的,所以由性所表现的性是善而无恶的。朱熹用性情的体与用的关系将孟子此句理解为由情证性,以用证体的思想。而“指其发于性者言之,故以为才无不善。”(《孟子集注》)说明朱熹认为根据孟子性本善的观点,而才是出于性的,因而才为善。在此基础上吸收二程关于才是禀受于气的,因而不同的人表现出才的强弱差别。因而其认为孟子的才是天地之性的表现,所以是为善的,二程的才气质之性的表现所以是有不善的。虽然气质的禀受有不善,但并不会改变性本身的善。反之亦然,虽本性为全善,但如果不进行修养气质的功夫,则会导致性的善不能全然展现。
王船山则通过天道的理气论证才情的善恶。王船山认为,理是引导于善的,气是实现善的,理与气是形而上的,才与情是形而上的,理气的善是本原、本体,理气为善则才与情为善。“情以应夫善者也,才则成乎善者也。”(《读四书大全说》)情是响应性的善的,才是成就善的,才与情是善实现的条件。但是,才与情只是具有为善的可能,并不是必然为善,情本身没有确定的方向也没有意志,而才只是作为成就善的材料,但不是善的完成。在宇宙生成,阴阳变化交合后,生成善的结果即产生善的才情,反之则产生不善的才情,情与才自身没有选择的能力,因而只是在气为善体的基础上,以理进行引导,以实现形而下的情与才的善,而最终此种现实的善是无法与气的本善相等同的。
四、结语
实际上,按照气异理异的原则,即人禀何种气即得何种理,则导致气质之性对人的性的决定作用而不承认本然之性。反之,若承认本然之性,则说明人性的不善是因本然的纯善之性受到不善的气质的蒙蔽。因而,与气异理异说相对应的本体论基础则为气本论,说明气是第一性的,理不是气中的某种实体、本体,而只是气的条理、属性。气对于人性的影响也是第一性的;而气质蒙蔽说则对应理本论,说明理是第一性的,理是作为气中的一种实体存在的,理对于人性的影响也是第一位的。因而,通过朱熹对《论语》、《孟子》中人性论的分析,说明其认同气异理异说,而实际上此种观点所要求的本体论基础是气本体论。因此,通过朱熹的人性论与本体论可见,其理论内部存在一定的矛盾性。而王船山对孔、孟人性论的分析说明其以气为本体,且具有使“理学思维去实体化”
参考文献
[1]陈来.2013.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胡适.2013.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一品(1994-),女,汉族,黑龙江哈尔滨,硕士研究生,黑龙江大学,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的倾向,是对朱熹思想的批判的继承,既延续了其基本的问题意识,也在其自身启蒙背景下对其有所发展。
论文作者:高一品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7年8月上
论文发表时间:2017/9/8
标签:孟子论文; 朱熹论文; 之性论文; 人性论论文; 气质论文; 论语论文; 人性论文; 《知识-力量》2017年8月上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