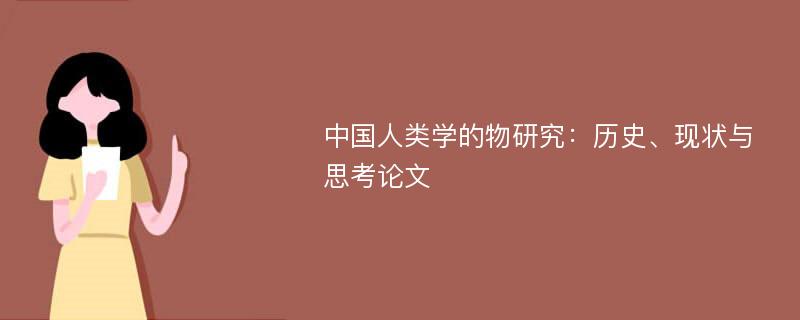
主持人语: 本栏目选用了3位青年学者的论文。马佳的论文对中国人类学物的研究作了阶段性的梳理,指出了长处与不足,并对这一课题在中国的未来做了前瞻。王欣的文章讨论西双版纳城市化进程中的“再地方化”实践与族群关系,以敏锐的洞察力总结当地居民和外来移民以自己的逻辑创造出一种既保证了地方特色和经济利益,又能发展“边疆建筑文化”的模式。张雨男的论文则梳理、分析、讨论了国内外研究鄂伦春社会文化的成果,全面地展示这一小民族在世界人类学研究中的位置,指出了现代以降边缘民族社会文化变迁主要靠的是外在的能动性力量,包括生计方式的改变,定居和公路、铁路的修筑等。3篇论文皆具开拓性,值得一读。——范可
中国人类学的物研究:历史、现状与思考
马 佳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4)
摘 要: 物/物质文化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之一。物研究提供了一种认识他者与洞悉社会文化世界的路径。中国人类学的物研究从民物收集整理开始,到当前以物的社会生命史研究为主流,大致经历了4段时期。每段时期中的研究内容、目的与理论方法亦有相应特点及变化。对之进行历史性的梳理与呈现有助于认识自身的长处与不足,展望未来的发展及对学科的贡献。
关键词: 物质文化;人类学;物研究
人类学对物/物质文化的研究由来已久。从哈登(Alfred Cort Haddon)在托雷斯海峡关注的艺术品,到马林诺夫斯基(B. K.Malinowski)在特罗布里恩群岛关注的项链臂镯,再到当代米勒(Daniel Miller)关注的手机[1],物(质)是一个涵盖面较广的概念,从哲学的层面上来理解,它指“存在”(较为抽象与泛化),从日常生活层面来理解,它指与人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一切实体存在,如居所、饮食、服饰、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等。对人类学而言,物(质)通常指具象实体层面上的物。“物(质)”之后的“文化”一词表达及透露出人类学看待与研究“物”的一种具有历史渊源且延续至今的视角——这些“物”都是被人类文化所引导的行为所制——制作及使用这些“物”表达或者说展演出人之观念与行为,即“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物进行研究“必然是对他者性(文化)的一种研究”[2]。对物的研究是理解人类自身社会文化的一种路径,因为正如人类学家米勒所言:“物质文化正是我们所研究的人群赖以创建他们自身真实世界的具体方式。”[3]人类学对物质文化的认识逐渐往深度发展着,而同时,物质文化研究也拓展着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论。从受猎奇心理驱使热衷于古物异物收集,将物作为文化阶段排序的标志,到将物视为意义的载体,再到关注物的能动性,物质文化在人类学各理论流派中扮演着不同的功能角色,也以此反观着人类学研究内容、目的及理论变化[4]。
20世纪初人类学传入中国后,随着该学科的生根、发芽、成长,对物质文化的研究亦被国内学者依据自身的情况,吸纳、借鉴、进行着。20世纪70-8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是在人类学、博物馆学、艺术学、历史学等学科基础上形成的一个跨学科领域,身处其中的不同学者依据各自的学术背景贡献各自的力量。西方物质文化研究(含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之来龙去脉与现状,已由西方学者做了详细呈现与论述,其研究理论与方法趋于系统性。(1) 此类研究可参见Arjun Appadurai, eds.,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Daniel Miller, 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Consumption ,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ied, 1987; Daniel Miller, eds., Why Some Things Matter , London: UCL Press, 1998; Han Woodward, Understanding Material Culture ,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7; Dan Hicks and Mary C. Beaudr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 studies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Daniel Miller, Stuff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0. 受西方物质文化研究热的影响,近几年来中国学者对物质文化的关注度增强,发表与出版了一些论文与会议论文集,但偏重引介西方物质文化研究的概念、内容及部分方法论,尚未成自己的体系。(2) 可参见韩启群:《物质文化研究——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物质转向”》,《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尹庆红:《英国物质文化研究》,《思想战线》2016年第4期;[美]托马斯·施莱雷恩:《美国的物质文化研究》,宋向光译,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考古学研究4》,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垚:《物质文化研究方法论》,兰州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白文硕:《“物的传记”研究》,兰州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孟悦,罗钢主编:《物质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徐敏,汪明安主编:《物质文化与当代日常生活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引介固然重要,但探究本国的学术传统也尤为重要。中国人类学应对物质文化研究做出贡献,前提是认识到自身研究的特长与不足。目前,尚无人对中国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含内容、目的、方法论做历史性地梳理与总结。本文欲做这方面的尝试。限于能力与知识储备量,只能试图对历史及当前中国(大陆)人类学的物研究进行宏观层面的梳理、呈现与分析,并进行相关思考与展望,期翼能引起学界对此一研究的关注与重视。
一、 20世纪前半期的物质文化研究
人类学是20世纪初从西方渐进引介入中国的。书籍的翻译、学术机构的陆续成立与相关学术研究的开展标志着中国人类学学科之诞生[5], 1926年蔡元培先生在《一般》杂志上发表《说民族学》一文,较为正式地界定了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对象——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记录或比较的学问[6]。与西方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异地的,如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地的土著们不同,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一开始就是内部的“他者”。他们是由被称为蛮、夷、狄、戎等演变而来构成中华民族的各少数民族,以及生活于农村的农民。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中、东部学校及研究机构的西迁,人类学以处于西南、西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及他们的文化为研究对象。其重要的主旨之一是通过对族源、族性的考察研究,论证中华民族的形成,维护疆域与国家之统一。作为民族文化之一的物质文化亦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并展开了一些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研究常分散于边疆民族调查、民物(民族文物、民俗文物)的搜集、人类学博物馆筹建等工作中。如颜复礼、商承祖、杨成志、江应樑等人类学前辈从1928年7月始,先后对广西与广东两地的瑶族进行调查研究,其中一部分调研涉及到瑶族的住处、衣饰、房屋材料、屋内陈设、日用器具、工具、道路桥梁等物质(物质生活)[7]。师承美国人类学家拜耶的人类学前辈林惠祥先生于1929年-1935年到台湾,对高山族进行调查研究,顺带收集民物标本,其中涉及高山族之生活器物、劳作工具、住所、衣服、食物、工艺品等物质文化,在《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文中有详细的记录描述[8]。林先生认为,所谓物质文化泛指人类基于发明创造能力制造的一切物品及制造技能,如取火使用的工具、食物的种类及如何烹饪与保存、衣服、住所、狩猎工具及方法、畜牧,驯化的牲畜品种、种植业、种植的作物、石器及制作方式、金属物、陶器、武器、交通工具及使用方法等[9]。杨成志先生(1902-1991)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物质生活或物质文化”是指“人类为‘生存需求’而创造出来的一切物质需要而言,包含(1)生活上的需求,如衣、食、住、行及器具;(2)工作方法或生存方法,如渔、猎、牧、农、工、商各业;(3)获得财富如工资、赢利、田地、房屋、财产及其他”[10]。依照这些界定与归纳,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类学前辈们已将民族物质文化/生活,诸如住处、设备、饮食、衣饰、日用器具、工具、手工业、技术等文化事项设计成问题格的形式,并运用实践于相关调查中[11]。但是,此期物质文化研究之目的多还仅是对民族物质文化事项的收集、记录、罗列与描述,以突出其特殊性,将其作为标本与材料,“以做文野的比较”[12],并未与整体文化相联系,几乎无理论关照。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及40年代为中国人类学从创立到发展的辉煌时期,直接师承当时西方著名人类学家的中国学者归国后,结合国情与学术传统,创生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比如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厦门大学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为基地,以凌纯声、徐益棠、林惠祥、杨成志、戴裔煊、江应樑等为领军人物的“南派”,就将历史研究传统与人类学相结合,使用历史文献、民族学(田野调查)及考古学材料对边疆民族族源进行研究。此派受德奥传播论、美国历史特殊论及法国民族学派影响,对民族起源历史与民族文化事项较为关注,注重历史考据,同时也擅长文化细节的调查与描述。文化史、民族史和人文地理是该派的主要研究内容[13]。物质文化研究亦是这一学派的特长领域。研究者一般以物质文化在时空上的起源、形成,及传播、变迁来复原与探讨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据此展开对具有某类文化特质的文化圈及文化区域的划分与思考。如戴裔煊(1908-1988)采用史地学的方法对存于中国西南的 “干兰”这一住宅形式之名称、类别特征、分布与传播地进行历史考证与论述,且认为“干兰”可以用来确定一个有着共同文化特征的东南亚的文化圈之存在[14]。与之相似的是凌纯声对中国古代树皮布文化的研究[15]。这一由某文化特质(物质文化)引申出来的区域视野与文化史研究方式,在功能学派鼎盛之时,及中国人类学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后,便黯然消色了,对中国人类学的理论建树不失为一种损失。与“南派”相并行的中国功能学派,即“北派”的人类学前辈们,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人多以汉族农村(农民)为研究对象,更关心中国的现实问题,试图通过微观的社区调查研究,深度分析中国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尽管这些人秉持着物质文化作为某社区文化整体一分子的观念,他们认为物质的意义依它在人类活动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它所关联的思想,及所有的价值而定[16],如社会人类学家、功能论的引介者吴文藻先生(1901-1985)已洞察到了蒙古包与蒙古族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碍于调查时间短暂,未能深入分析[17]。但是,该派对诸如饮食、居住、交通、服饰等物质文化的调查与书写,更多价值在于制作出一个体现功能论思想的完整民族志文本[18-20]。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了解边民历史与社会现状的研究目的影响,中国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多是收集、罗列与描述那些稀有的、未曾见过的、所谓的土著/边疆民族之物。这些物被作为遗物、证物与标本来收集与叙述。1930年代中期后,历史学派发端出了物质文化史的研究范式,功能学派意识到了物质文化与社会文化整体及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二、 1950-1980年代初期的物质文化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代直至1980年代初期,受意识形态与苏联民族学派的影响,中国人类学逐渐被狭义的研究民族历史与发展规律的民族学取代,研究对象由早期的“文化”变为“少数民族”,研究内容(任务)围绕着少数民族族别问题、少数民族社会性质、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少数民族宗教信仰4项进行[21]。其中,有关物质文化调查研究并不像20世纪前半期那样事无巨细地动情描述,更不需用来论证文化的功能及文化的整体性,它带有强烈的目的性与应用性。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至今,中国人类学得以恢复、重建与发展。总体趋势是研究视野逐渐开拓,成为其研究对象及内容中的文化事项越来越多,突破以往较狭隘的民族研究视野,除了深化专门研究领域,如亲属制度、宗教仪式、经济,政治外,还产生了交叉领域,如历史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应用人类学等。跨学科的综合趋势越来越明显[29]。物质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在这种态势中得以某种程度上的发展。此期物质资料的生产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不再是研究与讨论的重点,研究者更加关注物质所承载与反映的文化意义,专门讨论物质文化研究价值与介绍理论方法的文章及书籍出现于学界。
MIN Mi-ke, ZHOU Peng, ZHU Min-hui, SONG Xian-min, ZHENG Hong-liang
施药后2 h,螺虫乙酯、B-enol的原始沉积量分别为0.54 mg/kg、1.71 mg/kg。以施药后时间、残留量绘制螺虫乙酯、B-enol在猕猴桃果实上的残留消解动态曲线。消解动态符合一级动力学模型,消解方程分别为ct=0.562e-0.170x(r=0.836)和ct=1.689e-0.108x(r=0.584),消解半衰期分别为4.08 d和6.39 d。施药后螺虫乙酯、B-enol 23 d转化率分别为78.38%和62.35%。
尹绍亭先生摸索与总结出一套研究少数民族农具的方法论。他曾说研究农具这一物质文化,我国学界过去存在汉族中心论,另外就是套用进化论解释模式,文化多样性被进化论代替,农具自身的文化,它们的多样性并没有很好地得以呈现与研究。为破除进化论的禁锢,首先,研究方法就要改变,不仅仅参阅现有的那些汉人精英书写的文献,更重要的是到选定的村落做田野调查,先做普查,再重点调查,然后再与其他地域进行横向比较研究。调查过程中,应参与观察制作与使用的过程,认真测绘记录。(7) 尹绍亭先生就他本人的农具研究之缘起和过程,有过以上内容的叙说。笔者依据2014年3月18日的录音整理。 他认为在未能够提出理论,未能与西方进行理论对话的时候,我们应该从解决自己的问题出发,做扎实的田野调查,至少在方法上要有所建树。
三、 1980年代中后期至 21世纪初的物质文化研究
从1950至1964年,为摸清国内少数民族现状、进行民主改革、及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政府先后进行了民族识别与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工作。在以政府、政治服务为核心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中,民族学家们本着“务实”的态度,对边疆民族的历史、民族社会、民族经济进行了调查与记录,物质文化包含其中,内容涉及到各兄弟民族(当时的称呼)的生产工具、生计方式、交通工具、服饰、住所、手工艺等。“物质文化”被放置于“物质生活与习俗”“文化与生活习俗”“生产方式”“经济”“服饰”“手工业”的撰写目录下进行呈现与分析,其中尤以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的记录、描述与分析为重点,(3) 参见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鄂伦春族社会历史调查》《珞巴族社会历史调查(一)》《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赫哲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黎族社会历史调查》、《佤族社会历史调查》等。 并以此作为此判断与划分各民族社会经济形态的材料与依据。其原因是,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不因精神、心理因素、英雄主义等,而是由生产力推动。生产工具的改进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工具与技术是衡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指示器。据此,国家要求民族学者“应该记录下落后的生产工具及使用情况,帮助国家来改进落后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及改造不利于生产的种种条件”[22]189。“要通过直接的观察、调查、访问去研究各个民族及各民族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所进行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并把这些生产活动看作是各个民族中的各种社会现象、各种制度、观念的物质基础。同时用这个基础去解释各民族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因”[23]。可以说,受马克思主义“物质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论,尤其是苏维埃民族学派的巨大影响,归属到物质生产资料中的物质文化受到相比20世纪前半期时的更多关注。民族学者还将它作为了构成/划分经济文化类型具体要素中的重要一项,(4) 经济文化类型是由苏联民族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居住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之下,并有着近似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中国学界将其借用,并有所发展,使其成为了一种学说或方法论。 如将生活于东北大小兴安岭及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的交汇处,有相同的生计方式——渔猎兼采集,有相似的生产工具——弓箭、鱼叉等,相同的生活器具——桦树皮制品,冬季使用相同的交通工具——雪橇的赫哲族、鄂伦春族与部分鄂温克族划为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于物质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从而为民族学对于人类社会物质文化的起源和特征的研究提供了一条科学的认识途径[24]81。20世纪90年代兴盛于国内的生态人类学在这一认识途径的基础上深度思考了人(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1982年,宋兆麟先生(1936-)在《论物质文化在民族学中的地位》一文中,专门介绍了民族学与物质文化研究,尽管用“民族文物”代替了“物质文化”,但却指出与肯定了物质文化反映民族历史、社会制度和宗教方面的学术价值[30]。这是国内民族学界较早系统论述物质文化学术研究价值的论文。之后,《世界民族》(民族译丛)1986年第1期上登出了一篇由苏联民族学家C·A托卡列夫写的《民族学研究物质文化的方法》(原载于《苏联当代民族学和人类学》1974年,第Ⅰ集)。该文介绍了民族学者如何研究物质文化中的饮食、服饰和建筑3大块的内容。C·A托卡列夫认为,因为民族学是研究“人”而不是研究“物”的学科,所以,在面对一个物质文化现象时,民族学家感兴趣的往往不是物质本身,而是物与人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民族学家看来,人们围绕某物而产生的关系,即人们之间受物质资料调节的社会关系,往往更为重要[31]。20世纪90年代初,由林耀华先生(1910-2000)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将文化一章分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类介绍与论述,并指出,人类生活必需的衣、食、住、行都属于物质文化的组成因素,深入研究这些文化因素是民族学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是1990年代初国内民族学界较系统介绍物质文化的书籍[24]406-430。此后,中央民族大学的潘守永撰文《物质文化研究:基本概念与研究方法》,刊于2000年的《中国博物馆馆刊》。该文介绍了物质文化的概念、研究内容及基本理论框架[32]。之后,潘守永在此文基础上撰写了由国内人类学者庄孔韶主编的《人类学通论》一书中的第六章“物质文化研究”,总括了物质文化的概念、基本理论框架、主要研究对象。该章节内容引介了国外学者的一些重要观点,如认为事实上物质文化的研究主要是关于物质客体的文化表述的研究,所以它不仅研究物质客体本身,还要研究物质文化背后人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人的认知问题[33]152。物质文化研究一般包括物品性质(历史、质地、制作与功能等)、物品的识别和描述、物品的比较分析、物品的文化分析和解释等内容。这些步骤是环环相扣、不可分割的,前4步是具体方法,最后一步是目的[33]155。潘守永还在该章节末尾总结了国内物质文化研究涉及的主要对象,包括生计方式与生计类型、生产工具与技术文化、饮食文化、交换与商业文化、服饰文化、交通与行为文化、建筑文化与居住类型,并对这些研究的基本路径做了说明和介绍[33]164-169。此书是当时国内对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对象、方法及理论介绍得较为完整的导论性质书籍。
触发国内物质文化研究从“物质”转到“文化”层面的原因与西方人类学理论范式的转变密切相关。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掀起“语言学转向”与 “文化转向”,符号、仪式、神话成为文化分析的核心。在文化人类学界,结构主义、文化生态学、象征人类学成为主流理论学派。研究文化的目的不再是探寻社会文化维系整合的功能,而是探究其后的文化语法、意义体系。如格尔茨所言:“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34]受此转向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国内的民俗学、人类学学者开始运用象征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民族文化中的某些象征符号或某些单一民族的文化象征现象进行研究[35],其中便包括了被视为承载着民族文化意义的物质文化。进入21世纪初,中国人类学界涌现出诸多以饮食文化、宗教祭品、宗教器物、建筑、服饰、艺术品等“物”为内容,用象征作为理论工具进行分析与论述的著作。如《苗族服饰:象征与符号》(李鹖国,1997)《中国象征文化》(居阅时、瞿明安,2001)《隐藏民族灵魂的符号——中国饮食象征文化论》(瞿明安,2001)《沟通人神——中国祭祀文化象征》(瞿明安,2004)《弦外之音——中国建筑园林文化象征》(居阅时,2004)《云装秘语——中国民族服饰文化象征》(邓启耀,2004)《钟铃象征文化论》(庾华,2004)《汉画像的象征世界》(朱存明,2005)等。可以说,象征理论为中国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经久不衰的理论范式。
20世纪年代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末是中国人类学受创曲折发展时期。中国高校学科建制改动,社会学系、人类学系被取消,民族学研究内容被部分移入历史学(民族史)中。这段时期专项物质文化研究的任务交给纯粹的考古学家和在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考古学家,如宋兆麟、汪宁生、李仰松等前辈调查了苗、瑶、侗、壮、傣、佤、鄂伦春等少数民族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交通工具、住所、冶铁技术、造纸术、制陶术等物质文化[25]250-254。李先生认为佤族原始制陶术为民族学提供的制陶材料对研究和复原古代社会情景提供了不少材料[25]250-254。汪先生以傣族制陶术为据,谈论我国远古制陶的几个问题,认为“傣族原始制陶术,对研究人类制陶技术的演化、对复原各地出土陶器的制法和用途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26]。民族考古学学者多把少数民族物质文化视为人类历史演化过程中的“活化石”,用他们的技艺实践过程及结果印证考古发掘的物质事项。这些民族考古学家都有一个相似的学术经历——学历史学(考古学)出生,在后期的民族史研究与田野调查中渐渐走近狭义民族学。即,他们的学术积淀发轫于历史系下的考古学。可以说,是民族史研究范式的独断与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的机遇触发了民族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从而成就与延续了中国民族学界物质文化研究的一种与史学、考古学密切联系的研究径路。
由前三部分的呈现与分析可以看到,从人类学传入成长于中国的那天起,无论是以文化为研究对象,还是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拥有长时段历史事实及丰富历史文献资料的特点及优势均促发中国人类学与历史学密切联系在一起,物的文化史书写早在民国学者的笔下已呈现出来。播化论、历史特殊论、法国民族学派的共力作用促生了中国人类学的历史学派,作为文化特质、文化标志的物质文化已被运用来论证中国南北间、东西间,乃至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太平洋岛屿的历史及空间上的联系。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历史学保护下曲折发展的民族学,尽管被限于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论述少数民族的历史(社会形态的演变史),但是,作为经济基础、生产方式重要内容的物质文化依然有一定的时空维度。由此,可以说,物的文化史研究乃是中国人类学的一种传统,故当物的社会生命理论进入中国后,它很容易“嫁接成活”。只是,有一点值得思考,究竟物的社会生命理论能否完整地呈现与诠释出类似中国这样古老国家中的某些物的全部生命历程?对古代中国而言,它存在着内外、前后、左右、上下的关系,这些关系使它成为一个文明的复合体,而文明的本质是超越社会体系的[44]。如此,对古代中国而言,仅在社会(内部)是无法全面理解物的生命历程,还需要在外部,在内外、上下等关系丛中才能完整理解物的生命史。在中国做物研究,不仅要将其放置在历史长河与广博地域空间中,更为核心的是,要看到它身处其中的一系列结构性关系,或者说是围绕因物的流动而产生的一系列结构性关系,这是理论与方法论的一个突破口。总体而言,尽管当前中国人类学物研究有发展的态势,但是与西方将近约三四十年的积淀与发展不同,中国物的人类学专题研究尚还方兴未艾,理论与方法依然是其硬伤。
四、近年来的物研究
抢救性纪录整理依然进行着,而同时,物质文化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本世纪物质文化研究的两条道路,后者让人类学家看到了物研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独特贡献。如果以台湾人类学者黄应贵主编的《物与物质文化》(2004年)传入并影响大陆人类学界;2006年7月,由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论中心、西南民族大学、北大蒙养山学社共同召开的以“人类学与物质文化”为主体的学术夏令营活动,或是孟悦、罗钢主编的《物质文化读本》(2008年)为标志,那么约从21世纪头十年中后期起,中国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的内容、目的、理论方法在西方物质文化转向——一种反思物(客体)与人(主体)决然对立、隔绝关系,回归物自身、肯定物人互为主客体关系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下发生着变化。
1) 升降施工平台各部件之间采用螺栓连接,且数量众多,将螺栓连接简化为固定连接,并不影响分析结果[9]。
受之前的结构主义、解释人类学及1980年代兴起的实践理论之影响(实践理论试图统合结构和阐释,即力图消解长期以来的主客体对立、个人与结构的对立关系。)20世纪80年代国外物质文化研究在以伊恩·霍德(Ian Hodde)为代表的一批后过程考古学者、英国物质文化研究代表人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克里斯·蒂利(Chris Tilley)及美国人类学者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等人的努力下发展出了各自的理论及研究径路,如物的能动性、作为分类的物质文化、物的社会生命等[39]。物与人共同构成了社会,共同参与了文化或文明的进程,人通过周遭之物认识、建构自己的身份,表达自己的感情等观点被提出。其中,阿尔君·阿帕杜莱在他主编的《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视野中的商品》一书中,提出“商品,一如人,拥有社会生命”[40]的命题。阿帕杜莱将商品视为是其社会生命中的某一阶段,所有的物都有成为商品的潜质,这与所处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规定有关,一个经历丰富的物会经历着“商品化”与“去商品化”的生命历程(轨迹),研究者所要做的是考察这些物的“生命转折点”,以此关注到商品化,去商品化的路径、方式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这本出版于1986年的论文集的突出贡献在于,使人类学对物的研究回归到了物自身,(5) 物质文化研究的路径转变,经历了物作为客体,以此来研究社会进化,社会功能、社会结构、文化符号系统,物只是用来证明社会结构和社会存在的附属物,没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对物的重新认识,从莫斯的“物人不分”社会象征理论起源论中找到引申之路,肯定物自成一格的研究价值。由此,开启了由物为切入点,研究社会文化及人的心性的路径。除了阿帕杜莱外,英国人类学家丹尼尔·米勒,提出了“人物互动促成社会文化进程”的文化理论。参见黄应贵主编:《物与物质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中华民国九十三年五月(2004年),第2页、第3页。 并进行了视野及方法论上的新尝试。阿帕杜莱在“面向物的人类学”(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things)中提出:“我们不得不跟随着物本身,因为它们的意义就蕴涵于它们的形式、用途以及轨迹之中。只有通过对这些轨迹的分析,我们才能解释人用于激活物的存在的人的活动及其计划。由此,甚至在理论上说,是人的行为给予物以意义,但从方法论的视域下,却是运动中的物,说明了人以及社会内涵。”[41]这一视野与研究径路被引介运用于中国(6) 孟悦、罗钢等主编的《物质文化读本》和《消费文化读本》两本书较早集中介绍了国外近年来物质文化研究代表人物论著的部分章节及一些经典论文。阿帕杜莱的《引言:商品与价值政治》及科普托夫写的《物的文化传记:商品化过程》被全文翻译登出,此为该书对中国物质文化研究的贡献。参见孟悦、罗钢主编:《物质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8页;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4-427页。 ,近年来中国人类学界出现了一些以“物的社会生命”为研究径路与分析脉络的论文及专著,如《山参之“野”:关于意义与价格之生成的人类学研究》(孙晓舒,2012)《延伸的平行线:滇越铁路与边民社会》[42],《葡萄的实践一个滇南坝子的葡萄酒文化缘起与结构再生产》(郑向春,2012)、《茶叶的流动:闽北山区的、物质、空间与历史叙事(1644-1949)》(肖坤冰,2013)等分别对滇越铁路、滇南葡萄酒、闽北茶叶进行研究,并以这些物为切入点,研究铁路与少数民族的互动;研究葡萄酒在经济、政治、社会脉络中文化意义的生成;研究茶叶对当地历史的建构作用等。舒瑜以物的社会生命为研究理论,梳理了诺邓盐业的兴衰史,同时将盐置于帝国文明与边疆文明互动中来讨论,由“盐”史探究了边疆纳入帝国的区域政治史[43]。可以说,“物的社会生命”研究路径影响到该书出版之后,直至今天有关物的人类学研究以及人类学对社会文化历史进程的研究。当前中国物的人类学研究特点突出为将物的社会生命与地方建制史、区域社会文化发展史、区域贸易史、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史等相勾连讨论。且不仅如此,这一研究径路与理论也影响到了国内的艺术学、文化史学、经济史学、社会史学等研究领域。物的社会生命(史)在当前中国人类学界引起这么大的反映,值得思考。其原因之一,恐怕与中国人类学与史学密切结合的传统有关。
传统意义上,物质文化仅指有形实体,与人工制品同义,但随着人类学科和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物质文化的范畴已经涵盖了具象与抽象的物质客体,“由文化决定的行为所改变的那些自然环境”也一样被理解为物质文化[37],甚至包括了人类自身(身体)。物质文化研究(MCS)的方法逐渐呈现出2个重要的特点:首先是提倡物的“过程”观,强调关注物的运动“轨迹”和“重新语境化”;其次,有着强烈的跨学科性,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形成一定程度的交叉[38]。对人类学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作为人类文化类别的物质文化,对其进行研究在于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的起源、发展历史以及人类的社会文化。1980年代之后,尤其是21世纪近几年,物质文化研究价值更突显在对方法论与理论的增益上,它使人类学者重新审视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重新审视人与物的关系,重新认识社会文化构成。最大的贡献在于,使得人重寻“谦卑”,反思“人类中心主义”,进而反思人类学的本体论与认识论。
还需提到的是,此期与象征理论运用相对的是抛开理论,通过田野调查,采用“细描”与“白描”手法呈现与论述民族物质文化的另一种研究方法,见于尹绍亭先生(1947—)主编的《云南物质文化》丛书,包括《农耕卷(上、下)》(尹绍亭,1996)《采集渔猎卷》(罗钰,1996)《纺织卷》(罗钰、钟秋,2000)《生活技术卷》(唐立,2000)《少数民族服饰工艺卷》(刘琦,2004)。作者运用历史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图像法等对云南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中使用的劳作工具、生活器具的外观、内部结构、功能、分类、制作和使用源流等方面做了细致入微地描述和呈现。对纺织、制陶、造纸、制糖、榨油等动态的生产过程及生产技艺亦做了图文并茂的详细描述。丛书作者持生态人类学的立场,认为物质文化乃是人类在物质上和社会上适应环境的产物,是人与环境互动的参照物[36]。不再忙于下决定论式的结论,摆脱验证理论正确性的束缚,回归到一种扎实的物质文化调查、纪录、整理与书写方式,其透露学者面对又一次涌入中国的诸多西方理论的迷惑与对囫囵吞枣状态的反思。更深的原因在于,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与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生发于民族物质文化日渐消失的速度与程度中的焦虑使民族学家意识到 “抢救性纪录整理”依然迫在眉睫。
五、思考与展望
由以上的呈现及论述可知,中国物/物质文化的人类学研究经历了将物作为民族文化标本,作为社会发展标志而进行历史考古式样的具体描述阶段,而后是探究符号物意义的阶段,近来受西方物质文化理论与方法论的影响,渐渐出现了“回归物自身”(Return to the thing)的本体论思考,物的能动性、物的文化史受到关注。可以说,从进化论、历史唯物论、到象征理论,再到当前物的社会生命,每个阶段每种物质文化/物的研究理论,乃至于物的概念,我们都从他处引介而来,在本土使用着,期翼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文化问题,如中国近现代化进程,明清消费文化的兴起,民族认同,传统文化的续存,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发展等等,诚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早在前辈学人论述“人类学/社会学本土化”议题时,理论与方法论引介及使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已被肯定,但引介中及之后,还需要“本土化”的过程也得以讨论直至今天。那么我们的物研究理论与方法是什么?这一领域的研究是否应该对学术界做出独特的贡献?
20世纪70年代末,受到重创的中国人类学学科开始得到恢复。尽管此期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人类学界依然以1950年代以来的研究内容,如少数民族社会形态、民族史为研究重点及热点[27]。物质文化研究的路数依然为就少数民族物质文化自身的记录与描述,强调物质基础、物质生活对民族社会形态、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但是,此期,民族学者已开始反思之前的研究,如吕光天指出“过去我们比较重视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的研究。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很不重视少数民族社会的上层建筑、特别是民族心理状态的研究,我们的材料中比较薄弱的是关于家庭、婚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精神文化和衣、食、住等物质文化的材料。这是不全面的。今后还要填补:(1)婚姻和家庭制度史的研究;(2)还应对服饰、建筑、哲学思想、文学艺术、风格、节日等进行研究”[22]202-203。严如娴、宋兆麟在所写的《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一书中对摩梭人住屋的研究已开始结合住俗、家庭形态与家庭生活方式进行呈现与分析[28]。总体而言,因政治原因,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的中国人类学,唯物论与进化论成为其主要理论范式,在原始社会史研究、经济文化类型研究、民族史3大研究领域中,物质文化举足轻重,被视为是民族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文化),也真就只有了“物质”,没有了“文化”。物质与文化的分离为中国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欠缺它该有的文化深度与广度埋下了伏笔。因为,犹如我们后期意识到的,民族社会文化进程(历史)亦不单是物质性的历史。文化不是经济基础(物质)“决定”的反映物,它是人的观念及行为实践。
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奋斗过程中,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选择性地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它的意义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红色文化主动地有机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功能,创造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激发群众接受理论知识的积极性,使抽象的理论通俗化,让红色文化体现在各种形式中,渗透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在潜移默化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实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红色文化的自觉接受,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完成“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花期授粉:猕猴桃的花期一般为7~10天,“贵长”“红阳”等品种必须借助人工授粉或蜜蜂授粉可以弥补自然授粉不足。
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通过研究青铜器及其上的纹饰,呈现与分析中国上古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贸易、宗教,且对中国青铜时代与社会的若干主要特征做整体性的讨论。他认为研究青铜时代的每一方面,小自一件器物或它上面的纹饰,大到整个的中国政制,都得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它本身的性质;二是它与其他方面的关系[45]1982年版前言2。据此,他发现那些作为巫术法器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在造成或促进政权集中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而提出了中国文明区别于西方文明的世界学术性观点[45]二集前言5。我们如何来理解物与其它方面(物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以探究中国文化/文明的本质及变化,或者说通过研究中国文化/文明的深层结构(内部之间、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给予“物转向”“物回归”一些立足于本土的,有别于西方的诠释?王铭铭教授认为“回归于物的世界之努力,(应)落实到人的观念、历史的叙事及思考的方式上”[46]17。从物切入(以物质文化作为研究径路),可达中西文化/文明的深层结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物研究的独特贡献,可能在于物人不分,互为主体,见物见人,见人见物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上[46]150-191。在“观物见人”中,学者能够深刻地洞察到社会生活的微妙层次,能发现所谓的“无意义之物”的“隐藏意义”[46]133。
我们并不是物质文化匮乏的国家,相反,五千年文明积淀,使我们拥有巨大的物质文化宝库,只是说,诚如赵园先生所言:“大陆学界关于古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从来不乏坚实的研究成果,如《东京梦华录笺注》就涉及大量与北宋物质文化有关的内容,只是没有相应的理论视野与所谓的‘问题意识’,这一方向上的研究,其意义未被阐发而已。”[47]的确,先人前辈们留给我们的书籍记录,如《天工开物》《格古要论》《金石录》《陶雅》《考工记》《瓶史》《长物志》《饮流斋说瓷》等足以证明。我们现在恐怕需要做的是,其一,激发问题意识,即通过物的研究,究竟要试图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而非就物论物;其二,立足于田野调查,与西方理论进行对话;其三,对前辈学人的研究内容与方法进行梳理与总结;其四,就是对中国的传统物观、物观演变过程及当前的物观进行回溯、呈现与分析。
物的世界,毫无遮拦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是只被动地接受着它的功能呢?还只是一眼瞥之,任其在脑中留下印迹即可?我们如何去观看它?如何通过它去解密文化密码?如何发现它与人之间的积极互动?如何将它与更久远的历史、更宽广的社会相联系,而以此带出更大的意义,值得每一位人类学研究者去思考、实践与探询,中国人类学的物研究任重而道远。
本研究样本仅由某市农村的3所中学的278名初中学生构成,所得结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以后可扩大样本量,还可进一步关注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及相关情况。
参考文献:
[1]Heather A. Horst and Daniel Miller, eds., The Cell Phone :An Anthropology of Communications , Oxford: Berg Publishers, 2006.
[2]孟悦.什么是“物”及其文化?——关于物质文化的断想[C]//孟悦,罗钢.物质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7.
[3]Daniel Miller. Why Some Things Matter?[C]// Daniel Miller. Material Cultures: Why Some Things Matter ?. London: UCL Press, 1998:19.
[4]马佳.人类学理论视域中的物质文化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 2013(4):83-92.
[5]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48-54.
[6]蔡元培.说民族[J].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 1950(9):19.
[7]杨成志,等.瑶族调查报告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
[8]林惠祥,蒋炳钊.天风海涛室遗稿[M].厦门:鹭江出版社, 2001:87-157.
[9]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60-134.
[10]杨成志.广东北江瑶人的文化现象与体型研究[C]//杨成志,等.瑶族调查报告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195.
[11]凌纯声.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G]//凌纯声,林耀华,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3:17-31.
[12]蔡元培.何谓文化[C]//中华书局.蔡元培选集.北京:中华书局, 1959:160.
[13]王铭铭.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181.
[14]戴裔煊.干兰——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研究[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
[15]凌纯声.树皮布印文陶与造纸印刷术发明[C]//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之三,中华民国五十二年(1963).
[16]马凌诺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17.
[17]吴文藻.蒙古包[C]//吴文藻,陈恕,王庆仁.论社会学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420-431.
[18]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57-131.
[19]费孝通.江村经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0]林耀华.凉山夷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21]费孝通,林耀华.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C]//杨圣敏,良警宇.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百年文献.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150-174.
[22]吕天光.三十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发展[C]//杨圣敏,良警宇.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百年文献.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23]梁钊韬,陈启新,杨鹤书.中国民族学概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63.
[24]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7.
[25]李仰松.从瓦族制陶探讨古代陶器制作上的几个问题[J].考古, 1959(5):250-254.
[26]汪宁生.傣族的原始制陶术——兼谈中国远古制陶的及几个问题[C]//汪宁生.民族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9:202.
[27]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下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8:320.343.
[28]严汝娴,宋兆麟.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4:151-168.
[29]王铭铭.25年来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对其成就与问题的思考[G]//王铭铭.中国人类学评论.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7(1):11-20.
[30]宋兆麟.论物质文化在民族学中的地位[J].民族学研究, 1982(1):275-282.
[31]C·A·托卡列夫,李苏幸.民族学研究物质文化的方法[J].民族译丛, 1986(1):23-28+35.
[32]潘守永.物质文化研究:基本概念与研究方法[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2000(2):127-132.
[33]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3.
[34]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上海:译林出版社, 1999:5.
[35]瞿明安等.象征人类学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1.
[36]尹绍亭.物质文化·农耕卷(上下)[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
[37]Jame Deetz, In Small Things Forgotten: Anthropology of Early American Life, New York: Anchor Books/Doubleday, 1996:35.
[38]韩启群.物质文化研究——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物质转向”[J].江苏社会科学, 2015(3):73-81.
[39]Dan Hicks. The material cultural turn: Event and effect[C]//Dan Hicks and Mary C. Beaudr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 stud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25-26.
[40]Arjun Appadurai. Introduction: 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 [C]//Arjun Appadurai, eds.,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3.
[41]阿尔君·阿帕杜莱.商品与价值的政治[C]//孟悦,罗钢.物质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13.
[42]吴兴帜.延伸的平行线:滇越铁路与边民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43]舒瑜.微“盐”大义——云南诺邓盐业的历史人类学考察[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0.
[44]王铭铭.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3-70.
[45]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46]王铭铭.心与物游[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47]中华书局编辑.奢华之色——新书恳谈会会议记录(摘录)[J].书品, 2011(2):6.
Material Culture Study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History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inking
MA Jia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 650504, China )
Abstract : Material/Material culture is one of the objects of Anthropological study. Research on material culture can provide a way to know the others and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world. Start with the collection of folk objects, and nowadays mainstream with the social life of material studies, material culture study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has experienced four periods. The research content, purpose,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each period also have corresponding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es. It helps ours to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nd to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discipline by historically combing and presenting material culture.
Key words : material culture; Anthropology; China
中图分类号: C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1X(2019)06-0041-10
收稿日期: 2019-08-27
作者简介: 马佳,女,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民族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传统手工艺。
[责任编辑:王 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