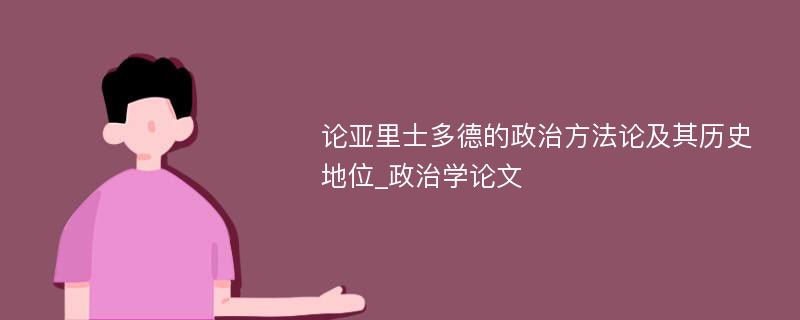
试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方法论及其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里士多德论文,方法论论文,政治学论文,试论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方法论原则,具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征,也含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从本质上说,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主要有:以自然主义为特征的历史“溯源”方法;以回避本质为特征的形式比较方法;以“设疑求解”为特征的思辨分析方法。他的政治学方法论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其历史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在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亚里士多德被公认为政治学之开先河者。他所创立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对后来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总的方面看,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充满了矛盾,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具有二元论和折衷主义的思想特征。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对于政治学的研究。他的政治学方法论原则,无疑具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特征。但是由于他尊重经验事实,立足于政治实践的研究,所以含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合理因素。
我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方法论原则主要有:以自然主义为特征的历史溯源方法;以回避本质为特征的形式比较方法;以设疑求解为特征的思辨分析方法。笔者虽然在这方面知识浅薄,但有兴趣试图做一些粗略的分析,提出一点看法,以就教于读者。
一、关于以自然主义为特征的历史溯源方法
这一方法,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由胚胎追踪其形成的发生学的研究方法即“溯源”方法,二是由部分而及于全体的整体分析方法。亚里士多德说,这是他所“惯常应用的方法”②。他首先应用这一方法,考察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他认为,国家即政治团体是“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③。这种社会团体是由较低级的社会团体即家庭和村坊逐步发展和演化而来的。因此他说,对于国家像对其他任何事物和任何问题一样,只要“追溯其原始而明白其发生的端绪,我们就可获得最明朗的认识。”④依此方法,他认为,国家这一政治团体最初起源于家庭。家庭是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的基本形式。家庭是由于两种关系结合的产物,一是男女关系,二是主奴关系,这两种关系都是纯粹出于生理和生活需要的自然关系。为了适应更广大的生活需要,人类由若干家庭联合又进而组成一种较为高级的社会团体,这就是村坊。村坊最自然的形式是由一个家庭繁殖而衍生的聚落,因此有些人就称聚居的村坊为“子孙村”。随着村坊的进一步发展,若干村坊组合在一起就成为城市(即城邦国家),这样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社会团体就发展到了终点。
亚里士多德说,这种由家庭到村坊再到国家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完全是一种合目的的自然的演化过程。国家的产生和形成完全是为了人类本性发展的需要,国家的产生过程也就是人类本性完成和实现的过程。因为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是自然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只有国家才能达到人类的至善;只有在国家中人类才能过上最优良的生活。因此人离不开国家。那种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如果不是一只野兽,就是一个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从个人到国家是一个由不完全到完全、由根本意义到十足意义上的人实现其本性的过程,国家的生活是人的本性的完成。“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⑤
以上,就是亚里士多德运用发生学的方法所揭示出的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这种溯源分析的历史方法,如果从逻辑的角度看,也就是由部分而及于全体的分析方法。
从逻辑的角度看,亚里士多德首先是把国家这个复杂的整体分成若干组成部分,考察每个组成部分特有的性质,然后联系这些部分的不同组合,分析整体的形成和活动。他说:“研究每一事物应从最单纯的基本要素(部分)着手”⑥。政治学术“恰好像在其他学术方面一样,应该分析一个组合物为非组合的单纯元素——,我们在政治学的研究中,也要分析出每一城邦所由组成的各个要素而一一加以考察”⑦。由于这种分析,我们就能比较清楚地阐明各种社会团体及其人物之间的差异,并进而弄清国家的性质。但是他又说,考察部分又必须立足于事物的整体性,因为“整体总是超过部分”⑧。在他看来,从发生程序上来看,城邦后于个人和家庭,但是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就本性来说,全体必然先于部分”⑨。所谓“先于”,就是“优于”,就是说惟有在国家中,个人、家庭、村坊等才是完整的政治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了整体是有机体的观点。他多次拿国家与活的有机体相类比,认为部分统一于整体是有机的统一,而不是绝对的划一。他批评了柏拉图的绝对划一的整体观。因为柏拉图主张在国家中子女公育,妻子公有,财产公管,一切绝对统一。亚里士多德说,这种划一不符合城邦的本性,它所导致的结果实际上只能是城邦的灭亡。部分与整体的统一是有差别的统一。从这一原则出发,他坚决拥护个人权利,特别是私有财产权。他反对柏拉图的“共产制”,拥护私有制,认为私有制符合对自己的天赋之爱的个人本性。只有维护个人权利,实行私有制,才能实现个人的本性,免除国家中的恶,使之兴旺起来。
由上可见,亚里士多德运用历史溯源方法阐述国家的产生和形成,认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在当时来说,虽然还缺乏事实的根据,但毕竟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具有辩证法的合理因素。这与他的老师柏拉图相比,应当说是前进了一步。但是也应当看到,亚里士多德是从生物学的纯自然主义的观点出发来解释国家的产生和形成过程的。他认定国家是自然发展的产物,仅仅服从自然的法则而非社会法则,这样就又表现了他对待历史的非历史主义的倾向,反映了他的历史方法的唯心主义性质。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界的发展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服从于不同的发展规律。亚里士多德主要考察的是希腊城邦国家。针对这种国家,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⑩“一夫一妻制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11)随着劳动生产率和私有制的发展,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而被炸毁,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这才是国家产生的真正过程。恩格斯又说:“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12)这就是说,国家的本质也不是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一个追求至善的政治团体,而是一个阶级压迫的机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观点是一种超阶级的观点。另外,他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合目的性的观点,也是片面的。应当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人们的目的意志只有合乎社会发展的规律才能得以真正的实现。离开规律性奢谈目的性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
其次,他把人的本性的发展与国家的产生和形成联系在一起,认为人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动物,这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不自觉地触及到了人的社会性方面,具有唯物主义的合理因素。他的这一观点受到了马克思的称赞和肯定(13)。
但是,他虽然看到了人的社会性的一面,然而他对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的理解是错误的。他提出,人类之所以比蜂类或其他群居动物所结合的团体达到最高的政治组织,就是因为在各种动物中独有人类具备言语的机能。只有借助于语言,才能辨别是非与善恶,家庭和城邦的结合则正是这种义理的结合。根据唯物史观,用有无语言和理性区别人和动物,从一个侧面说是正确的,但是把它作为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却是唯心主义的。因为真正能够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就是以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而结成的生产关系为基础和核心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二、关于以回避本质为特征的形式比较方法
据说,亚里士多德一生曾收集和编订过158种城邦的政治体制。他在认真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有目的有意识地进行理论总结,寻求他认为“最好而又可能实现人们所设想的优良生活的体制”(14)。所以,比较分析方法是他从事政治学研究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方法。
亚里士多德首先阐述了对于诸种政体进行分类和比较的一般标准,主要是两点:一是利益标准,二是最高权力执行者的人数标准。依据这二者的统一,他把政体分为两大基本类型,其一是正宗的或正确的政体,其二是变态的或错误的政体。他说:“依绝对公正的原则来评断,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的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15)。他又说,最高权治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要是旨在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或平民群众的私利,那就必然是变态政体。”(16)
依据上述原则,他把正宗政体划分为三种,即君王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相应于上述各正宗政体,也有三种变态政体,即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他不仅对各种政体的性质作了“比较周详的研究”(17),而且又依据各种不同的具体原则,把每种政体又分成若干类型,进行了细致的对比研究。他认为在所有的政体中,僭主政体是最坏的政体,因为这种作为君王政体的变态政体,以个人利益为依归,实行专制独裁。平民(即民主)政体是较好的政体,因为他作为共和政体的变态政体,倡导自由和平等的精神,人人都可以轮流充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担任公职没有财产定额的限制,官吏由选举产生并实行任期制等等。但是最理想最好的政体,他认为是共和政体。共和政体之所以最好,是因为在共和政体中是多数人为了公共利益而进行统治,一切其他政体都是对共和制的程度不同的偏离。共和政体集寡头和平民政体的优点于一身,同时又弃其各自的极端,以中产阶级为基础并由其执掌政权,就能免除党派之争,不会出现内讧,而有助于实现政治的安定。更为主要者,他认为共和政体崇尚法制,主张以法治国,法治胜于人治。因为“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18)。只有按照法律办事,才能做到正义即公平,免除个人情感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比较分析,比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前进了一步。苏格拉底在谈论各种国家组织和统治形式时,虽然也力图区别出它们的特点和结构的不同,也进行了具体的比较分析,但是,他进行分类和比较的标准是混乱的。另外,苏格拉底通过各种政体的比较分析,把当时存在的贵族制和较为温和的寡头制说成是由良好法律统治的完善国家,而较多地批评了民主制,特别是批评了民主制统治者的不称职和民主制采用的“多数人决定”的原则。柏拉图提出了五种国家制度即贵族制、财阀制、寡头制、民主制、僭主制,对之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认为最正确、最好的政体是由优秀的人和高贵的人统治的贵族制度,其余四种都是错误的政体。他认为,由于人的本性的变质,上述几种政体形式会发生改变和更替,这种改变和更替呈现出内在的周期性循环;这种循环是一种退化和堕落。柏拉图对此的论证,多半是从心理学、神话学的角度出发,显示出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虽然也有些是以政治、历史提供的事实为依据的,但从总体来看,则是牵强附会、生拉硬扯,纯属主观臆断,所以他所绘制的政治生活及其形式更替的变动图是虚假的,不可信的。亚里士多德对政治体制的比较研究,更多地是以经验事实为基础,而且在全面性系统性深刻性方面大大超过了他的前辈。
但是,他们之间的区别毋宁说是次要的,因为他们的比较分析都是从形式出发的,讲的都是国家政治组织形式如何不同,而回避了对国家本质的分析,这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则更为突出。因为他讲得很明确,政治体制就是一种体现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制度,“是全城邦居民由以分配政治权力的体系”(18)。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体是受国体决定的,国体决定国家的本质。所以对不同国家制度的比较研究首要的是进行国体的比较,揭示出不同国家制度的阶级本质。亚里士多德虽然也声称他要找出不同国家制度的本质特点,但在他那里只是一句空话。因为他所阐明的各种政体从本质上都是一个,即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他所说的当政者,不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都不包括奴隶在内,奴隶只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亚里士多德回避对不同国家政治制度本质的分析,完全是由他的奴隶主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
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近乎形式主义的比较分析,来自于他在哲学上对形式与质料关系的某种错误理解。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提出质料、形式以及二者的结合(个体)都是实体,另一方面又强调形式是最后的最根本的实体,是现实实体。他认为,实体除了具有主体或基质的含义外,更重要的是还具有本质的含义。而形式是决定某物成为某物的真正原因。因此形式较之质料、较之质料与形式的结合更为根本、更为重要,形式是第一实体。这种哲学观点应用到政治学的研究上,政体自然就上升到国家本质的高度,而真正的本质则被掩盖起来。
三、关于以设疑求解为特征的思辨分析方法
亚里士多德从事政治学的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从经验事实出发,具有现实性;一是注重理论的分析,具有很强的思辨性。他所运用的思辨分析方法,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对话式的论战方法相比,前进了一步。他在提出一个问题后,进行一连串的设疑,又进行一个一个的解答,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论辩,最后得出他认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些结论在我们看来可能是荒谬的,但它确实是经过一番认真的论证而得出来的,并不是武断的。
例如,为了说明奴隶是天生的自然奴隶,主奴关系是一种自然关系。他首先设置了一个疑问,说:“另一些人却认为主奴关系违反自然。在他们看来,主人和奴隶生来没有差异,两者的分别是由律令或俗例制定的:主奴关系源于强权,这是不合正义的。”(20)接着是亚里士多德的反驳,他认为,奴隶只是一种工具和财产,只不过是一种有生命的会说话的工具和财产而已。作为一种工具和财产,自然应当从属于主人。他说,奴隶的性质和本分就在于:“(1)任何人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的人格而从属于别人,则自然而为奴隶;(2)任何人既然成为一笔财产(一件用品),就应当成为别人的所有物;(3)这笔财产就在生活行为上被当作一件工具,这种工具是和其所有者可以分离的(即买卖——引者注)”(21)。他还说,主奴关系如同灵魂和肉体的关系一样,身体从属于灵魂和灵魂的情欲部分受治于理性及其理智部分,总是合乎自然而有益的。究竟应当如何看待法定奴隶和强迫奴隶呢?他并不否认这一客观事实的存在,也不得不承认主奴关系源于强权这一理论是有一定理由的。但是他认为不能根据力量的强弱来划分主人与奴隶,象在战争中胜利的一方俘虏战败者为奴隶那样,就会使不应当成为奴隶的人成为奴隶,这是不正义的。区分主人和奴隶的标准只能是德行和理智,而这都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他说:“我们还是维持尚善的宗旨,认为主奴关系应该以善良和卑恶为准则。”(22)
不难看出,他的方法确实是辩证的,但结论也确实是荒谬的。对此,列宁指出,亚里士多德提出此类问题是由于“唯心主义的胡说而发生的绝顶天真的‘困惑的’问题和怀疑”。指出这是“关于基本的东西、即概念和个别东西在这个问题上陷入毫无办法的混乱”(23)。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寻求、探索,它接近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但是,亚里士多德(他到处,在每一步上所提出的问题正是关于辩证法的问题)的逻辑学却被变成僵死的经院哲学,它的一切探索、动摇和提问题的方法都被抛弃。而这些提问题的方法就是希腊人所用的那一套试探方式,就是在亚里士多德学说中卓越地反映出来的质朴的意见分歧”(24)。亚里士多德用辩证的方法而得出了荒谬的结论,这也和后来的黑格尔一样,要从根本立场方面去找原因。
亚里士多德的思辨方法还表现在他运用辩证法的范畴对社会政治问题进行分析。例如,他曾运用因果分析的方法考察了各种政体倾覆的原因及其挽救和保全的措施。亚里士多德生值希腊奴隶制社会的危机时期,他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始终关注着各城邦国家的盛衰兴亡。他说:“因果相循,凡初因有错误的后果必恶”(25)。他从一般原因和具体原因、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具体分析。然后他提出:“考察清楚了政体所由破坏的原因,我们就可凭以找到加以保存的途径。相反的原因应当得到相反的效果;破坏和保存便是由相反作用所引起的相反结果”(26)。据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挽救和保全的措施,抽象地看,他的措施是有意义的;具体地看,则是为了挽救奴隶制的。
另外,还有一点应当指出的,就是他在进行思辨分析的时候,很强调事物的“度”。他说:“我们都认为万事都是过犹不及,我们应该遵循两个极端之间的‘中庸之道’”(27)。强调“过犹不及”,注重适度原则,这具有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但是,这里掺杂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因为他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处处都强调中间成分在各个方面应当占优势,舍此皆为偏激。例如他认为共和政体就是中间政体,善德就在于行中庸,财产应当是小康水平,中产阶级组成的国家是最好的国家等等。他的这些思想在现实中是很难行得通的,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以上,是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方法论的一个概述。从总体来看,他的方法有不少合理的因素,但是在根本上则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因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28)。这才是考察社会政治问题、国家和法律问题的唯一科学的方法。亚里士多德只是在政治问题本身兜圈子,或者离开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以他不可能真正揭示出问题的本质和找到解决问题的真正途径,这不仅是由于他的方法论原则的局限性,同时也是他的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尽管如此,我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应当低估他所创立的方法论原则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可以说,在政治学说史上,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大思想家没有一个能绕过亚里士多德的创作遗产的,也没有一个能直接地或间接地回避自己对亚里士多德的态度,他的历史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尽管把亚里士多德放入地狱,但是仍然把亚里士多德尊崇为“知识者之师”,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方法运用于自己神学政治的研究,托马斯·阿奎那就是一个典型。例如在对待国家起源的问题上,阿奎那就采取了亚里士多德的以自然主义为特征的历史方法,以此论证了国家是由于人性中彼此依靠过同伴生活的自然需要而产生的。尼可罗·马基雅弗利被称为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始祖,他克服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政治化和阿奎那的政治伦理化的泛政治学和泛伦理学的缺陷,但是他仍然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方法。他把注意的中心放在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生活的动态的论述方面,充分运用了因果分析的方法。
卢梭和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进行了根本改造,但他们都没有离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当代西方的一些学者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社会政治问题进行实证主义的分析,从表面上看,好象与传统政治学的研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路,但实质上仍然与亚里士多德一脉相承。总之,他们在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方面,既发扬了亚里士多德的优点,同时又继承了他的缺陷,从本质上看,终究都没有能够跳出历史唯心主义的窠臼。
注释:
(1)(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9、425页。
(10)(1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5、60、168页。
(1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3页;第12卷,第734页。
(23)(24)《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6、417页。
(2)(3)(4)(5)(6)(7)(8)(9)(14)(15)(16)(17)(18)(19)(20)(21)(22)(25)(26)(2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0、3、4、7、10、4、173、173、43、132、133、134、169、109、10-11、13、17、235、265、433页。
标签:政治学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地位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唯心主义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