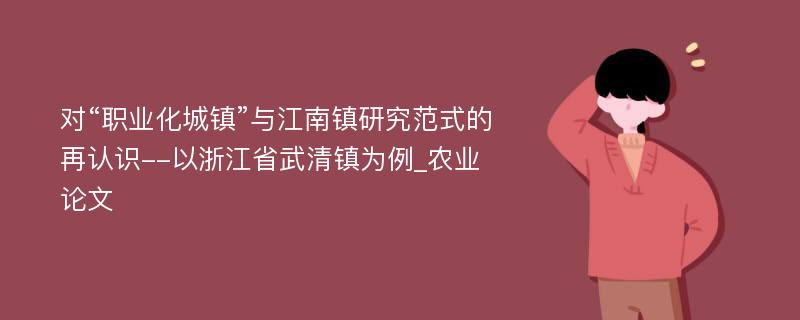
“专业市镇”与江南市镇研究范式的再认识——以浙江乌青镇个案研究为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镇论文,再认论文,乌青论文,范式论文,江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在江南市镇研究领域中,关于“专业市镇”的学术范式日见引人注目。其基本内容指明清以来,在人地关系紧张等因素的影响下,专业化的经济作物区兴起,该地区经济作物种植比例一般认为达到了60—70%。随着种植业的专业化,农村地区商品交换需求扩大,专业化的交换中心即市镇应运而生。这种经济结构一直延续到了近代以后。范式的归纳,对于特定研究领域有着相当的指导意义。但范式的强化,有时也不免带来矫枉过正的弊病。本文以被学术界普遍认作蚕桑业市镇的乌青镇为例,来讨论专业市镇这一学术范式的科学性。文章首先界定了乌青的乡脚范围,然后对其乡脚范围的农业经济结构作了深入分析,认为其蚕桑的比例达到三成,可视为上限。其次,对“存于农村经济之上”的市镇及市镇经济的专业性,也作了进一步验证,试图说明乌青镇作为一个农村地区的商业中心,经济结构是比较全面的,它实际上扮演着两方面的角色:本地区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集散地,与本地区农民生产、生活资料采购批零兼营的商业中心。其中蚕桑业固然是本地区农村经济中在粮食作物之外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若说它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进而规定了市镇经济的“专业性”,则恐怕有夸大之嫌。乌青镇的例子说明,“专业市镇”的学术范式由于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江南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有特色的内容,因而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可是随着范式的强化,以及学者在应用这一范式过程中的一些误解,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矫枉过正”的弊病:一是过分强调市镇经济的专业性,而忽视了其作为农村地区一般性商业聚落的特性;二是由于范式强化的影响,不少学者常常努力地将他们的研究对象纳入某一特定专业市镇的类型,以致在有关江南市镇的研究中,出现明显的“泛专业化”的现象。
一、“专业市镇”范式的确立及其影响
近年来,关于江南市镇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任放的新作《20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注:文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68—182页。)比较全面地总结了近百年中国学术界关于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学术史,其主要内容,就是关于江南市镇的研究。任放指出:傅衣凌先生于1964年发表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注:文载《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后收入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奠定了迄今为止以江南市镇为研究主攻方向的学术格局”。傅文第一次完整使用了三个关键词: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严格匡定了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叙事结构和学术话语,并提供了必要的文本范式”。其归纳很是准确,但可略作补充:傅先生在此文中还提出了另外一个基本概念——专业市镇,也为后来研究的深入起了指导作用。傅先生指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依据于当时社会生产,即商业、手工业、商品生产、货币流通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并成为全国性国内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乌青、南浔、濮院、盛泽等地,“即和丝织业有密切的关系”。“有些市镇和棉布业的发达也有关系,如枫泾……等市镇即是”。他认为:“象这一类新兴的专业市镇,在江南地区是很多的。”(注:傅衣凌前揭书,第230—231页。)
十余年后,台湾学者刘石吉即以“专业市镇”为核心概念,刊布了其成名作《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注:此文分上、中、下三篇,连载于《食货月刊》复刊第8卷之6、7、8三期(1976年)。后收入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刘石吉描述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农业结构变迁“都已发展至高度的专业化”的情况,确立了农业生产专业化与本地区城镇化过程中的“各种专业性市镇应运而生”之间的逻辑联系,并提出了明清江南市镇的丝业及丝织业、棉业及棉织业、米业等基本专业类别。
此后不久,江南市镇经济研究在中国大陆进入任放所说的“繁盛阶段”,“专业市镇”这一概念几乎为所有涉及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所接受,并在他们的论著中被强化,最终作为一个学术范式而得到确立。概括这一范式,可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
其一、自明清以来,江南地区在人地矛盾等背景因素的促进之下,农业经济结构产生变迁,以棉花与蚕桑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由于劳动收益明显高于传统的粮食作物,种植的比重日渐扩大,以至出现专业化的趋势,从而在某些地域形成具有特色的经济作物区。一般认为清代松江府及太仓州所属各县是棉业区的中心,越往西部,则棉花种植越少。在这些地区棉花种植的比例,刘石吉前文已根据史料,推定“平均则达百分之六、七十以上”。蚕桑业集中在苏州府及杭嘉湖地区,刘石吉认为它已成为这一带民众的“主要生计”。(注:刘石吉前揭书,第2、70、16、33页。)此后有关学者的研究,进一步提出了粮、桑之间的种植比例:“十分之七栽桑、十分之三种粮”。(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页。包伟民数年前所主编的《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也采纳了这一说法,参见此书第56—62页。)其它各类经济作物发展的情况,也有不少讨论。
其二、随着农业经济专业化,江南农村商品交换的需求扩大,作为农村交换中心的市镇“应运而生”;而且,由于农业经济的专业化特性,各地市镇也相应地具有了各自的专业特性。(注:可参见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第126页;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等。)
其三、市镇的专业类别在学者们的笔下日趋多样化。在刘石吉所提出的丝业及丝织业、棉业及棉织业、米业等专业类别之外,樊树志在其论著中进一步将江南市镇经济细分为十余种类型,增添了交通业、盐业、编织业、竹木山货业、冶铸业、窖业、刺绣业、烟叶业、制笔业、制车业、榨油业等专业类别;陈学文根据他对明清浙江嘉兴府市镇的研究,提出了十三种专业类别,除上述之外,新增的如有建筑器材与日用品业、五金用品业、油漆工艺与玩具生产业、生姜销售地、盐业生产地、海港兼外贸港口等等。(注:樊树志前揭书,第248—261页;陈学文:《嘉兴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收录于陈氏:《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其他学者在各自的论著中所提出的分类,虽或不如樊、陈两氏那么齐全,但都努力将研究对象纳入一定的专业类别,则是一致的。(注:例如乐承耀等:《明清时期宁波府市镇的发展》(《浙江学刊》1994年第3期,第34—39页),即将宁波的市镇,划分为丝织业、绵织业、造纸织席业、渔业、竹木山货业等专业类别。)
其四、由于农村经济的连续性,直至20世纪中叶,上述关于明清江南专业市镇的认识,仍基本适用。换言之,关于江南市镇的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妨从明清延续到近代。(注:参见包伟民前揭书第一章(30—91页)。)
1998年,单强发表《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一文,(注:文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第118—133页。)明言在刘石吉、樊树志关于专业市镇概念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讨论“专业市场”问题,给出了迄今为止关于专业市镇最为清晰的定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密,乡镇市场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即乡镇以一种主要产品为中心,形成‘一镇一品’的格局,以生产促进流通,以流通带动生产,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良性循环。”基本概念的提出与范式的归纳,对于特定研究领域有着相当的指导意义。但范式的强化,有时也不免带来矫枉过正的弊病,所以反复地验证它,是必要的。目前学术界对明清以来江南农村经济专业化趋势的描述,是否存在脱离实际的现象?当我们强调市镇经济的“专业化”、甚至将其定义为“一镇一品”的同时,是否忽视了其作为一般农村商业中心而存在的意义?我们对上述范式的应用,是否存在泛化的现象?这些都是我们在梳理了专业市镇学术范式的学术史之后,需要认真思索的内容。
本文试图以对浙江乌青镇的个案研究,来验证上述的思考。
以乌青镇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主要出于资料的可行性与案例的典型性这两方面的考虑。乌青镇由于存世文献相对集中,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在资料上近乎唯一可行的研究对象。即便如此,本文在分析中仍不得不经常引用其附近地区的资料作为旁证,来补充其本身记载的不足。此外,如前所述,从傅衣凌先生以来,关于江南专业市镇的主要研究者如刘石吉、樊树志等,均将乌青镇归入蚕桑丝织专业市镇的范畴,所以本文以此作为分析对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二、乌青镇及其周边农业经济结构
乌青镇在历史上位于三府(湖州府、嘉兴府和苏州府)六邑交界之处,它源起于唐代的军镇,(注:朱辛彝等纂:(民国)《乌青镇志》卷3《沿革》,1936年刻本。)到北宋已经演变成一个比较繁荣的农村商业性聚落。镇区夹车溪水(即市河)分成两部分,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分为乌镇和青镇,河东为青镇,属嘉兴桐乡县,河西为乌镇,属湖州乌程县(今湖州市)。1949年,两镇合并,通称乌镇,隶属嘉兴市桐乡县。就市镇经济而言,两镇历史上一向“实同一聚落”,(注:朱辛彝等纂:(民国)《乌青镇志》卷15《祠庙·张偘重修土地庙记》。)所以一向合称“乌青镇”。
南宋以后,由于战争的影响,乌青镇发展几经盛衰。到明代中后期,乌青镇已经形成了雄视一方的巨镇格局。万历年间(1573—1620),镇区纵7里,横6里,周26里,分7个坊,乌镇5坊,青镇2坊。此后镇区面积与坊区数目都有所增加。从清代前期起镇区人口称“烟火万家”,“巨丽甲他镇市”。(注:董世宁:(乾隆)《乌青镇志》卷2《形势》,乾隆二十五年刻本。)“名为镇而实具县郡邑城郭之势”。(注:(民国)《乌青镇志》卷5《形势》。)所以有学者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乌青镇是明清江南诸市镇之冠……。”(注: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第134页。)
近年来,有关论著对施坚雅(William G.Skinner)所提出的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八个市场等级的划分办法,提出了不少修正意见,(注:参见前引任放文。)但不管根据哪一种体系,乌青镇当属本地区农村的商业中心,是没有问题的。作为一个“存于农村经济上面的市镇”,(注:施火星:《乡土重建的一个实验:记实干中的菱湖建设》,(上海)青树出版社1948年版,第2页。)其全部活力就是来自于周围的农村经济。那么乌青镇这个农村中心市场的辐射范围有多大呢?
所谓市场辐射范围,即市镇提供商品和服务范围的大小,学者们一般用“乡脚”或是腹地来表示,每一个市镇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乡脚地区,也就是与市镇发生商业联系、大小范围不等但数量相对固定的村落,这些村落并不一定非得与市镇产生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在乌青镇志中与乡脚的概念相近的称呼为“四乡”,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无法具体说明其范围。对与乌青镇相邻、同样作为农村商业中心的市镇的距离作一分析,也许是一可行的思路。在乌青镇东北分布着檀丘市,东面有新塍,南面和东南面有濮院、屠甸、梧桐,西南面有石门、琏市,西面和西北面有双林、马要、东迁,北面有南浔、震泽、严墓等,这些镇市距乌青镇从14里到40里不等,因而乌青镇的乡脚范围,当为它与这些相邻市镇之间的一部分村落,是可以确定的。根据(民国)《乌青镇志》卷14《乡村》所载民国初年乌、青两镇的自治区疆域,乌镇下设6个乡,管辖21个村落,青镇和炉镇共同成立为区,下设22个乡,辖60多个村落。这些村落分布于乌镇以北的较少,最远的水路相距不过10里左右,而主要分布在青镇以南地区,距离远的与市镇水路相距达40里左右,如位于青镇东南的妙智、正家笕等村即是。(注:(民国)《乌青镇志》卷14《乡村》。)大致看这一自治区疆域边界均介于距上述各市镇路途的中段,总体格局是北狭南广,因为位于乌青镇西栅以北30里的地方分布着与乌青镇同等规模的南浔镇,而在青镇以南,同等距离之内却不存在较大的商业中心。所以民国时期,乌青镇的商业实际上多集中于青镇。这与我们调查估计的范围大致相当。因而我们推断,民国时期乌青镇自治区内的村落基本上就是乌青镇的乡脚地区,即所谓的“四乡”,正是在这些村落与市镇发生长期、固定经济联系的基础上,才有了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笼统讲,维持乌青镇如此规模的市镇经济,大致需要半径为10公里左右的乡脚圈。由此反观,乾隆(1736—1795年)《乌青镇志》卷17“乡村”所载村落,数量达数百个,反映的应该是当时设于镇上的湖府督捕同知一职的治安管辖范围,实际上也就是当时乌青镇的乡脚地区。
在上述乌青镇的乡脚范围内,分布了如小乌镇、陈庄这样的村市,当属基层市场的范畴。此外水路距青镇南栅14里还有炉头镇,虽名为镇,规模不大,有“筷长”炉头之称,(注:《桐乡县文史资料》第6辑《炉头访古》,桐乡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1987年编印。)实际也是基层市场。这些基层市场为周围范围不大的一些村落所提供的商品与服务,大都来源于乌青镇,(注:参见(民国)《乌青镇志》卷21《工商》。)它们的存在,正是乌青镇商业经济职能的发挥和作为这一地区商业中心地位的体现。
上述这一乡脚范围内农业经济的特色,是决定乌青镇作为农村市场的专业类别的基础。但出于资料的原因,下文考察的视角,不得不扩大到其农村经济具有共性的苏州、杭嘉湖地区。
自南宋以来,乌青镇所在的杭嘉湖地区蚕桑业不断发展,到了明代中后期,已经出现明显的专业化趋向,前引学者的论述,有桑与稻争地、桑七稻三的估计,其文献根据,主要来自地方志的记载。例如明人徐献忠记述湖州一带农村经济,谓“田中所入与蚕桑各具半年之资”。(注: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12《风土》。呈兴丛书本。)天启《海盐县图经》对本地农村有“桑柘遍野”的描述,(注:许瑶光等:(光绪)《嘉兴府志》卷32《农桑》;引天启《海盐县图经》,光绪四年刻本。)清代谢肇浙在《西吴枝乘》中描述湖州,也说“尺寸之堤必树之桑”、“其树桑也,自墙下檐隙以暨田之畔池之上,虽惰农无弃地者。其名桑也,不曰桑而直曰叶”。(注:宗源翰等:(同治)《湖州府志》卷30《舆地略·蚕桑上》,光绪九年重校刻本。)但这些记载所反映的关于当地稻作与经济作物之间种植的比例数据,十分含糊。如前引的“各具半年之资”,如“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注:张大纯:《姑苏采风类记》卷51,转引自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16页。)如“烟火万家”,与历代文献都可见到的诸如“十人之中,农民仅居其五,而士工贾与异端游惰之民以及异端之工贾,亦居其五”之类议论相似,(注:靳辅:《文襄奏疏》卷7《生财裕饷第一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数据并无严格统计学意义,只可引作旁证。所以,前人关于明清以来江南农村稻桑比例——乃至专业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不妨重新验证。
现存关于当地明、清近代田、地比例的一些统计材料,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根据王社教新近研究的统计,明代中后期松江府田的面积占耕地总数(包括田、地、山、塘等)的84.96%,田和地总数为4398195亩;嘉兴府田的面积占耕地总数的90.26%,田和地总数为4150186亩;湖州府田占耕地总数的82.06%,田和地总数为3333784亩;杭州府田占耕地总数的79.10%,田和地总数为2825546亩。苏州府的统计数字缺如,但是从其所处地势来看,稻田的比例至少不会低于杭州府。如果仅从田与地的比例来看,整个明代水稻的种植面积要远远超过蚕桑。王社教估计,明初苏松常嘉湖五府的水稻种植面积约占整个耕地总面积的85%。到明代后期出现了桑争稻田的现象,上述五府水稻种植比重下降到66%。(注:王社教:《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6、97、320页。)水稻种植比例虽下降到六成有余,由于还存在豆麦等其它粮食及经济作物,蚕桑的比例估计达到三成,可视为上限。
其他一些记载可以印证上述估计。据20世纪20年代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对蚕桑经济区吴兴县(即湖州府的归安和乌程两县)农村土地情况的调查,平均每户农民使用各种田地9.78亩,其中稻田为6.61亩,桑地为2.84亩,即稻占七成,桑占三成。(注: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1928年印行)第四章“土地问题”,第103页。)30年代,嘉兴县的稻田面积为1134317亩,占耕地总额的86.1%,(注: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1935年编印:《中国经济志》第1册,第33页。)则蚕桑至多占14%。考虑到30年代当地蚕桑业有所衰退的因素,(注:参见包伟民前揭书,第56—62、292—297页。)可能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蚕桑的比例还要略高一些。又据档案记载,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浙江省吴兴、桐乡、崇德、嘉兴、海盐、平湖、德清、嘉善、海宁、长兴等蚕桑业较发达的10县区,耕地面积及水稻种植指数可列为表1:
表1 吴兴、桐乡等10县区耕地面积及水稻种植指数统计 (单位:亩)
数据类别
面积 百分比(%) 备注
耕地面积 5928978
100.00 1948年统计数据
1948年水稻种植面积527344888.94
1953年水稻种植面积
417312470.39
种植面积系据双季早稻及单季中、晚稻合计而成
资料:据浙江省档案馆藏《浙江省农林水利参考资料》(全宗号J116-3-4)第五节。
水稻之外,大、小麦、大豆、玉米、甘薯、油菜子等旱地作物也占了相当的面积,(注:各类粮食作物合计种植面积为9066398亩,超过了耕地面积本身。由于复种指数不明,很难估计单季种植面积,但由此可见蚕桑面积不大,是可以肯定的。估计蚕桑面积当在15%以下。)蚕桑种植的比例看来是比较低的。根据《浙江省蚕业改进所1950年春蚕工作总结报告》,当年全省蚕丝收入在主要蚕区尚占农民经济收入3/10左右,较战前(1936年)约减少2/3。(注:《浙江省蚕业改进所1950年春蚕工作总结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全宗号J116-4-37。)如此,战前浙江省主要蚕区农民经济收入中来自于蚕桑的,或者可达五成。由于蚕桑在种植面积与产出的比例上要高出稻作,蚕桑的土地种植面积,看来不会超过总土地面积的三成。这与前引调查资料所提供的数据相吻合。由此,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稻桑种植比例三七开的估计是合理的。这主要指的是浙江蚕桑区的情况,其它地区蚕桑种植比例更不可能太高。此前学者的一些估计,疑有失实之处。
稻作经济之所以长期在上述蚕桑专业区占着很高的比例,除技术、市场等因素之外,还存在其它一些重要的因素,不应忽视。首先、从事蚕桑业需要比稻作更多的劳动与资本的投入,无疑是制约其扩展的一个因素。据李伯重的研究,明清时期蚕桑业总计一亩桑地上的劳动投入(包括种桑、养蚕、缫丝三个环节所需人工)至少为93个。而种稻一亩所需的人工为11.5个。前者为后者的8倍有余。同时,一亩桑地同样包括上述三个环节所需资本(包括肥费、蚕具费、桑秧费、蚕炭费、蚕种等)为2.935两白银(不计盘费即搬运费),而一亩稻田的资本投入为0.635两白银,前者是后者的4至5倍左右。
其次、蚕桑与稻作收益的比差,也不如前人所强调的那么高。据李伯重的估计,乾隆年间每亩桑田缫丝所得为约银11两左右,同时期江南地区水稻的亩产量平均为米3石左右,以平价1两白银1石为准,则每亩田收入为3两白银。如果扣除资本投入,那么一亩桑地可得8两左右,而种一亩稻的效益为2.4两左右。(注:李伯重:《“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农史》1985年第1期。)如果按稻七桑三的比例,则农户的家庭收入中蚕桑(田地以十亩计,不包括织业)为24两左右,而稻作收入为16两左右。两者的收入相比实际上差距不如学者们所说那么大,而两者的劳动集约程度却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即从劳动效益看,蚕桑业明显低于稻作。据周中建近年的研究,江南地区农民植桑收入,在1919年为粮作的83%,蚕桑业鼎盛的20年代为89%,到1936年,仅为39%。(注:周中建:《近代苏南农村比较利益论析(1912—1937)》,《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第65—72页。)这恐怕也是稻作经济比例一直较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产业的风险因素不容忽视。相比于更具自给自足色彩的稻作经济,明清时期江南的蚕桑业已经与市场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受市场的支配和调节,风险性要大得多。同时,在传统技术条件之下,栽桑育蚕易遭受病虫害,其风险也较稻作大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到20世纪前期,江南地区蚕桑改良的主要内容,首推蚕种改良与蚕病防治的原因。(注:参见包伟民前揭书,第291—321页。)所以粮食生产实为中国传统农民的“养家之本”和最后的保障,绝不会轻易抛弃。
第四、还应该注意到的是,江南农业生产的发展一向有着多样化的倾向。宋代人称“茶盐蜜纸竹箭材苇之货,无有纤钜,冶咸尽其身力”。(注:《曾巩集》卷17《分宁县云峰院记》,中华书局点校本。)明清以来则更甚,不少地方的农村经济构成中,除稻作和蚕桑以外,还出现了第三种、第四种经济,它们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甚至与之并重。民国二十三年菱湖一带农村地区农户全年总收入中,渔业收入位居第三,仅次于稻作农业和蚕桑业。(注: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第二章《农家人口与家庭经济》,第35页。)青镇所隶属的桐乡县,其经济作物的种植除了蚕桑以外,还包括菊花和烟叶,两者的栽种历史长达300多年,(注:《桐乡文史资料》第5辑《晒红烟》,第30页;《杭白菊》,第34页。桐乡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1986年编印。)。至清末民初均出现了广为种植的局面,年产量相当大。(注:(民国)《乌青镇志》卷20“土产”。)
因此,我们在充分认识到明清以来江南地区蚕桑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其发展水平的估计恐怕还应力求更客观、更全面,避免以偏概全的失误,尤其需要注意不要被传世文献中缺乏统计意义的、夸张性的记载所误导。
三、乌青镇商业结构分析
所谓市镇是存在于农村经济之上的,是指市镇作为周围农村地区的商品交换中心,一方面为周围农村地区提供生产、生活资料方面的商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又作为周围农村地区各种农副产品的集散地,以此维持农民的购买力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市镇的商业机能主要就是由这两方面因素构成的,市镇经济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这是前文所概括的关于专业市镇学术范式的一个基本内容。前人研究,多见对市镇经济某一侧面的描写,尤其注重于如“商贾辐辏”、“百货骈集”等渲染性文字的征引,能够具体、细致地分析某一特定市镇商业全部内容的,则尚未见到,因此常令人有窥一斑而不能见全豹之憾。(民国)《乌青镇志》卷21《工商》,胪列了20年代后期乌青镇工商各业的全部内容,达63种之多,反映的当属清末民初乌青镇的经济构成,可供深入分析。今据以列为表2:
表2 清末民初乌青镇市镇经济构成表
行业类别 行业数量 行业名称
集散型商业 16桑叶业、桑秧业、丝吐业、丝业、茧业、绵业、绵绸业、茧壳业、米业、布业、烟叶
业、猪羊业、羊毛业、烟业、羊皮业、茶叶业
其它商业及服29①木业、竹业、桐油业、窑货业、颜料杂货业
务业 ②衣业、绸缎洋布业、洋广货业、鞋帽业、山货业、草席业、药材业、酱酒业、南北货
业、茶食业、襄饼业、茶酒肆业、菜馆业、八鲜业、旅馆业、花爆业、纸箔业、水作业
③电器业、西医业、钟表业、照相业、煤油业、西药业
金融业
2典业、钱业
手工业 14竹器业、藤业、冶业、造船业、油车业、糖坊业、染坊业、碾米业、磨坊业、浇造业、
香作业、铜锡业、印刷业、银楼业
交通信息业
2航业、民信局业
其中“集散型商业”17种,反映了市镇作为农副产品集散地的职能。除桑丝、米、布等业外,还有烟叶、猪羊、羊毛、羊皮等业,是乌青镇产业“多样化”的表现,占了地方经济一个不小的份额。以上这些农副产品大部分被销往外地或者供出口,如蚕丝,乌青镇四乡无机户,细丝都供出口,粗丝售于杭、绍、盛泽等内地机户,绵绸则销往江苏、上海、宁波、绍兴等地;羊皮、羊毛则是通商以后农村经济中新增的内容,完全供出口;蚕茧销往外地;烟叶销往江淮一带。其余产品的一部分销往外埠,一部分在本地区销售。
“其它商业及服务业”又分三类:第一类为竹、木、桐油、窑货、颜料杂货等业,反映了市镇从外地输入生产资料,以服务于当地村镇经济的职能;第二类为百货酱酒成衣茶饼旅馆等各类批零兼营商业及服务业,其主要服务对象为乌青镇乡脚范围内的农民;第三类显然是近代开口以后新兴起的各类商业与服务业,与第二类性质无异。
“手工业”的情形略为复杂。前面所列商业、服务业中,如成衣、水作等,其实也包括了手工作坊的成份。“手工业”类所列各业,如浇造、香作、铜锡、印刷等,看来大多是为本地村镇居民服务的,而竹藤冶船以下各业,却是当地村镇——主要是乡脚范围内村民——的手工副业。或者通过来料加工,由市镇商行将其产品分销外地,来赚取加工费,如竹木藤冶等即是;或者加工本地农产品,其产品供本地销售或外销,如碾米、磨坊、油车等即是。市镇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手工业大多具有季节性,基本上是在收获季节后才能展开经营,这些手工业作坊往往与店铺相连,不仅从事生产,而且兼顾销售。市镇中传统行业亦工亦商,前铺后坊,是常见的形态,如冶业、造船、磨坊、糖坊、铜锡、香作、银楼等,有些除了零售外还兼营批发业务。所以实际上大多数手工业也兼具商业的性质,构成商业经济的一部分。
“金融”与“交通信息”两类,行业数目虽不多,其重要性却不容忽视。金融业所涉及的具体行业分为两种,即典当和钱庄。典当业务的对象除了村镇民众外,同时也对镇上商铺开展借贷业务;而钱庄的业务对象基本上是镇上的商家,甚至包括一部分当铺。这两种行业直接以金钱往来为业务,需要有雄厚的商业资本来支持,经营这两项业务的往往是家财以十万、百万甚或千万计的富商,尤以来自南浔的富商为主。典当与钱庄虽然并不直接参与商品的交换,但是却通过向镇上商铺放款的形式来间接参与商品交换,因而对市镇商业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其兴衰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市镇商业的繁荣与否。乌青镇“典业在商业极盛之时相传有十三家之多”。
交通业对市镇的发展规模和镇区形制、商业经济的发展水平等具有决定性影响,尤其是交通的发达与否直接关系到市镇商业经济的发展。乌青镇作为苏杭嘉湖水网区域的一个商业中心,与其作为水运交通网络中的关节点密切相关,这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乌青镇作为其周围农村的交通中心,另一方面又作为构成苏杭嘉湖地区水网交通的中心环节之一,充当着周围农村与外部区域进行商业交流的中介。尤其是后者,对乌青镇商业经济的发展比前者更有意义。如果乌青镇仅仅作为周围农村的交通中心,那么或者只能作为农村基层市场而存在,正是因为它具备了后者的交通地位,才使得乌青镇发展成为名义上属于中间市场实际上具备中心市场规模的市镇。清末民初乌青镇每日经由的快船、航船及轮船等,近40个班次,其航线远及上海、苏州、杭州、嘉兴等地,充分显示了它在苏杭嘉湖地区交通网络中的地位。
以上所征引的资料,充分体现了乌青镇作为农村地区商业聚落所具有的普通商业机能。全镇共有各类行业63种,其中批零兼营的商业与服务业29种,手工业19种。在16种集散型商业中,与蚕桑业有关的为8种,其余8种所反映的地方农副经济是多种多样的,如米、布、烟叶、猪羊、羊皮、茶菊等等,其在地方经济所占比例也相当可观。且这些集散型商业基本属季节性经营,如茧行负责收购鲜茧和干茧,乌青镇一带育蚕有夏、秋两季,蚕茧也有夏季和秋季之分,所以茧行在小满(5月)开市,营业期主要在夏秋两季,丝行也是一样。在它们歇市的日子里,维持市镇商况的是其它批零兼营的商业与服务业。
由资本市场所反映的各业地位比例,也并不说明有哪一个待业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而是各具相对重要性。江南地区早期从事丝蚕贸易都依靠牙行,到后来才出现了专业经营的丝行、经行,但无论是哪一种经营形式,所需资本都有限,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商业中介机构,以赚取佣金为目的。在丝业贸易鼎盛时期,市镇丝行以18‰的比例来收取佣金。(注:以上均见(民国)《乌青镇志》卷21《工商》。)丝行最多时达十余家。至于茧业贸易,其兴起缘于机器缫丝的出现和发展,因此历史不长,兴盛期是在二三十年代。茧行所需资本较大,多者十几万元,少者二、三万元,(注:《中国经济志》第1册,第37页。)乌青镇最多时有16家。但丝茧业贸易很不稳定,完全受市场支配,因而只持续了两三年时间,平时不过在四、五家。
市镇其它行业,首先是金融业(即典当行和钱庄),其所需资本无疑要比丝业和茧业多得多。尤其是钱庄,直接为市镇其它行业提供资本借贷,因而其商业资本量在整个市镇待业中首屈一指。此外,需要资本投入量比较大的待业还包括烟叶业,清代咸、同以前据称“行销于江淮等处,帐款动以数万计”;油车业中的桕车业:“投资较大……须买桕籽千担,需费五六千元,成为一挡,徐恒裕东号向于冬令做两挡”;桐油业:“徐恒裕营业最久,远近著名,批发门市均售,营业较大,陆三泰、杨永升、杨坤元诸家皆赖乡庄,交易亦繁,故往时桐油一业营业亦钜。”米业、药材业等等,商业贸易规模也都不小,批零兼售,不逊于丝茧业。(注:(民国)《乌青镇志》卷21《工商》。)
由此可见,乌青镇作为一个农村地区的商业中心,其经济结构是比较全面的,它实际上扮演着两方面的角色:本地区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集散地,与本地区农民生产、生活资料采购批零兼营的商业中心。据以上分析推断,蚕桑业固然是本地区农村经济中在粮食作物之外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若说它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进而规定了市镇经济的“专业性”,则恐怕有夸大之嫌。
※※※
“专业市镇”的学术范式由于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江南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有特色的内容,因而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可是随着范式的强化,以及学者应用这一范式的种种欠周全,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矫枉过正”的弊病,应该注意。如下几个方面尤为突出:
其一、过分强调市镇经济的专业性,而忽视了其作为农村地区一般性商业聚落的特性。许多学者在分析市镇类型时,都已强调了存在着作为贸易集散中心与作为商品供给中心这样不同的市镇类型,(注:参见前引任放文,尤其文中所引之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等论文。)却常常未能注意到在绝大多数作为中间市场的江南市镇,这样两种功能事实上是并存且互为依赖的。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一个作为中间市场的市镇的商业繁荣,更多的需要依靠其对周围农村地区“保障供给”的商业功能。有些学者在其一般性的理论归纳中有时也能考虑到类似的情形,但当他们需要对某一特定市镇作出类型区分时,却常常非此即彼,失于周全,忽视了市镇作为一般性商业供给中心的作用,这显然是范式强化所带来的弊病。
其二、由于范式强化的影响,不少学者常常努力地将研究对象纳入某一特定专业市镇的类型,以致在有关江南市镇的研究中,出现明显的“泛专业化”的现象。从傅衣凌先生大致提到的丝织业与棉绢业两种类型,到刘石吉的三种类型,再到樊树志、陈学文的十余种类型,种类越分越多,其中有一些类型的界定不能不说失于勉强。
其三、如乌青镇的个案所显示的,明清以来,江南农村——乃至依存于其上面的市镇——发展起多种经济,是普遍现象,学者在套用专业市镇学术范式分析某一特定市镇的专业类型时,由于所关注侧重面的不同,难免会顾此失彼,产生差异,强调了其中一个侧面,而忽视了另一个其实也是十分重要的侧面。有时甚至会产生互相矛盾的现象。即如本文作为典型个案分析的乌青镇而言,就有学者既将其视为“丝绸业市镇”或“交通枢纽型市镇”,又在自己的同一研究中明确指出,乌青镇“不同于那些主要作为商品经济发展产物而出现的专业市镇”,而是一个“日益完善其经济职能的市镇的代表”。(注: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第104、105、132页。)这不能不令人感到茫然。
范式其实不过是一种观察问题的视角与分析问题的工具,绝非可让人依葫芦画瓢的样板,更不是必须亦步亦趋的规则。如果我们在自己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能更周全、更理性,专业市镇的学术范式必将继续帮助我们加深对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