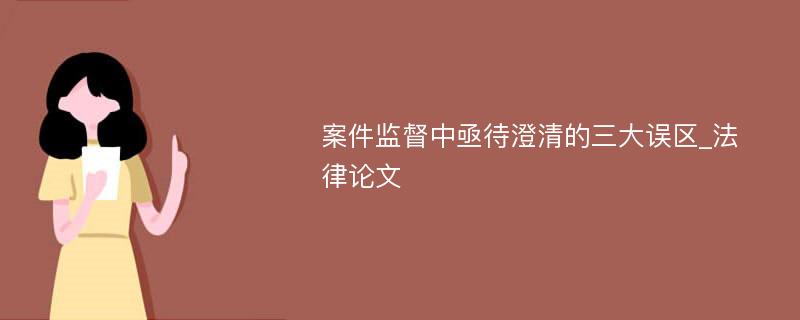
个案监督亟须澄清的三个误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案论文,亟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学界对人大的个案监督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据统计,以此为研究主题的文章大约有200篇。一些有影响的期刊还针对个案监督问题举办了专门的笔谈。(注:就个案监督问题进行专题笔谈的主要有《法学》1999年第1期、《人大研究》2000年第1期、《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2期、《人大研究》2003年第3期。)这些文章对人大应否享有个案监督权的基本立场是针锋相对的。同时,立法机关内部也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其表现之一是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对审判、检察机关重大违法案件实施监督的决定(草案)》议案,该议案虽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但每次都因争论过于激烈而被迫中止审议。(注:参见蔡定剑:《人大个案监督的基本情况》,《人大研究》2004年第3期。)
笔者研读上述文章之后,认为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个案监督的学者,似乎在个案监督的定义、个案监督是否合宪、国外是否存在类似于我国个案监督的立法例这三个问题上存在误识。因为所有研究个案监督的学者对于上述三大问题的回答要么失之准确,要么有待于进一步论证,要么因语义不一致而导致了不必要的争论。有鉴于此,本文拟对上述三大问题进行研究,以澄清一些不太准确或者应该进一步明确的认识。
一、个案监督的定义
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进行任何学术争鸣的前提。“因为可能争论者使用的虽是同样的概念,他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却很不相同,他们不是在同样的层面上争论,没有形成真正的交锋,甚至实质的观点没有多大差距,或者在歪曲对方观点的情况下‘得胜回朝’。这样的争论是一种不会使知识增值、倒可能使知识贬值的争论。”(注:何怀宏:《公正的正义——解读罗尔斯〈正义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笔者认为,个案监督之所以在学界产生如此激烈的争论,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没有给个案监督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因为赞成者和反对者在相互反驳对方观点时,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在同一层面上使用个案监督这一概念。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这些学者甚至相互指责对方“偷换概念”。(注:参见李静美:《个案监督,毋庸置疑——就“个案监督”问题与何兵先生商榷》,《人大研究》2003年第3期。)下文中笔者将对目前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对个案监督所下的三种定义进行评介。
第一种定义是:“所谓个案监督,顾名思义,就是对某个具体案件的办理情况进行检察督促。”(注:彭生发:《个案监督是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必然要求》,《人大研究》2000年第7期。)第二种定义是:“个案监督是指人民代表大会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重大的、可能是违法的案件实施的监督。”(注: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03页。)第三种定义是:“所谓个案监督,就是人大及其常委会或其授权的专门机构根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为了维护司法公正,保证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接受人民群众、社会团体、当事人及媒体的申诉启动监督程序,并由此而启动司法机关内部的审判监督程序,由司法机关自身对可能存在错误判决的案件进行审查、纠正的一种法定程序。”(注:刘旺洪:《论人大对司法的个案监督》,《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比较上述个案监督的三种定义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是非常明显的:第一种定义的外延最为宽泛,人大及其常委会无需任何理由,即可对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机关正在审理的案件或者已经审结的案件进行监督,且监督的手段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第二种定义的外延也比较宽泛,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对象包括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监督的理由是“可能违法”,监督的手段可以采取任何方式;第三种定义的外延似乎又失之过窄。因为按照这种对个案监督概念的理解,个案监督的范围仅限于法院已经生效的、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个案监督的途径是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行使监督权来启动法院的审判监督程序。显然这种对个案监督概念的理解局限于三大诉讼法已经明确规定的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情形,并变相否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各级人大及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以下简称《代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效力。因为上述几部法律、法规中都明确规定各级人大代表有权依法提出对本级人民法院的质询案,且质询案的对象既包括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也包括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如果将个案监督的对象限定在已经生效的错误判决,且只有通过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方式来行使监督权的话,那么实质上就是否定了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本级法院的质询权,缩小了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限。所以,仅仅将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个案监督权限定为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是不妥当的。
通过比较上述个案监督的几种定义还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对个案监督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可谓存在天壤之别。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有学者甚至认为,个案监督的提法本身就是不确切的,因为它包括不同的监督情况。(注:参见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页。)由于定义含混是造成目前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争论个案监督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对个案监督的概念进行明确定义就显得尤为必要。
笔者认为,个案监督就是指人大及其常委会如果发现法院违反诉讼程序审理案件或者作出的生效裁判可能存在错误或者审判人员徇私枉法、收受贿赂时,通过行使监督权要求法院予以纠正并依照法定程序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对个案监督的定义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人大及其常委会启动个案监督权的理由限于生效的裁判确实存在错误、法院违反诉讼程序审理案件、审判人员因受收贿赂而徇私枉法。由于目前没有明确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启动个案监督程序的理由,因此,各地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行使监督权时各行其是,缺乏统一的操作标准。如各地人大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地方个案监督条例中出现了“错案”、“可能发生错案”、“重大违法案件”等多种表述,但“错案”、“可能发生错案”、“重大违法案件”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应该如何理解?显然,上述任何一个对个案监督定义理解的歧义性必然会造成实践上的诸多弊端。例如,一些地方采用较为宽松的“可能发生错案”标准导致法院审理的案件大量涌入人大及其常委会,浪费了司法资源,使得人大异化成一个具体负责审理案件的机构;另一些地方采用“重大违法案件”作为启动个案监督的标准,显然有定义失之过窄的嫌疑,因为这会将法院的一般违法行为排除在个案监督的范围之外。
第二,个案监督权在行使过程中只能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集体名义进行,单个的人大代表不能行使这种权力。之所以要禁止人大代表个人行使个案监督权,其主要理由是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本质上是一种民意机构,它行使职权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因此,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行使个案监督权时只能以集体的名义进行。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由于我国民意机构实行合议制,其监督权只能集体行使,即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常委会来行使,从而使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具有集体监督的性质。”(注:何华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解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页。)具体而言,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对法院行使监督权时,特别是要作出某种决定、指示、意见、建议等,都必须以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的形式作出。人大专门委员会进行监督时,也要获得授权。事实上,只有以集体的名义行使监督权,才能防止个别人大代表擅自干涉法院的独立审判权。目前,由于立法上对个案监督的含义缺乏统一的规定,实践中人大在行使个案监督权时,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个别人大代表假借监督之名为亲戚、朋友谋私利;有的先入为主、偏听一方当事人的申诉意见就对案件作出结论,以个人的名义或者怂恿其他的人大代表对法院施加不正当的影响,责令法院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再审改判,从而造成更大的司法不公。事实上,上述这些做法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人大的形象,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一些学者纷纷撰文反对人大对法院行使个案监督权。当然,如果人大及其常委会委托具有专门法律知识和审判经验的人来行使个案监督权应该允许,因为这种做法与个别人大代表私自对法院施加压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第三,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行使个案监督权时不能干扰法院的独立审判权。我国目前并不是奉行类似于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政体,人民代表大会虽然是国家唯一的权力机关,但在国家机关内部还是存在权力分工的。国家权力机关并不能直接行使司法权力,而是将司法权委托给法院行使,同时,司法权运作的基本规律也要求法院只能独立自主地行使审判权,不应受到来自任何机关的不当干涉。因此,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行使个案监督权时,不能影响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如果人大及其常委会认为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和裁定存在错误,既不能宣布判决和裁定无效,也不能直接予以改判,只能以行使个案监督权的名义要求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进行审理和裁判。其二,对于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应该根据情况的不同区别对待:人大及其常委会如果认为法院对案件的实体问题判断不准,既不能要求法院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审理和裁判,也不能就实体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只能等判决生效后建议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予以重新审理;如果认为法院违反程序审理案件,人大及其常委会应该以行使个案监督权的名义要求法院立即予以纠正,并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其三,如果人大及其常委会发现审判人员涉嫌受贿或者故意枉法裁判,无论案件是正在审理还是已经审结,人大及其常委会都可以立案调查。如果查证属实,人大应该依法将涉嫌犯罪的法官予以罢免,并移交检察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个案监督是否合宪
赞成与反对人大行使个案监督权的学者对个案监督是合宪还是违宪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赞成者认为个案监督是有宪法依据的。其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从该条内容看,《宪法》并没有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时不受来自权力机关的干涉。(注:参见黎藜:《人大行使个案监督有宪法依据》,《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2期。)与此相应,《地方各级人大及政府组织法》第44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之一是“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因此,人大对法院行使个案监督权是有宪法和法律依据的。(注:参见胡建成、苏梅芳:《接受人大的个案监督有利于保障司法公正》,《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2期。)反对者则认为个案监督违宪。其理由是:首先,国家机关之间的职权必须进行合理的分工,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不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误解,而主张人大行使个案监督权实质上是使人大集立法权与司法权于一身。(注:参见卞建林、姜涛:《个案监督研究——兼论人大审判监督的合理取向》,《政法论坛》2002年第6期。)其次,1982年《宪法》已经从逻辑上否定了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权。因为《宪法》第7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从该条的立法原意来看,立法者已经意识到审判权、检察权与行政权的运作存在本质差别,为了保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独立自主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应该弱化人大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因此,人大不应该对法院行使质询权(人大对法院行使质询权是个案监督的一种形式)。换言之,《宪法》已经从逻辑上将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权给予了排除。(注:参见童之伟:《理顺关系、摆正位置——评人大代表质询法院引起的争论》,《法学》1997年第9期。)最后,《宪法》第62条第14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战争和和平问题。”同时《宪法》第67条明确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但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来就没有对军事委员会的具体工作进行过监督。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院的审判工作也应如同对待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一样,不得进行所谓的个案监督。(注:参见何兵:《“个案监督”质疑》,《法治时代周刊》2002年4月8日。)
从目前学界对个案监督是合宪还是违宪的争论来看,显然认为其违宪的理由占据了上风。笔者认为,人大对法院行使个案监督权是有宪法依据的,但是上述认为个案监督合宪的学者尚未针对违宪论提出有说服力的反驳。有鉴于此,下文中笔者将深入论证个案监督合宪的理由。
第一,上述认为个案监督违宪的学者的理由之一是1982年《宪法》的本意是要弱化人大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因为1982年《宪法》制定者们的意图之一是希望能够强化人大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对此,我们考察1982年《宪法》和1954年《宪法》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规定即可看出(1976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都是在国家的政治气氛不太正常的情况下制定的,因此,笔者予以忽略)。1982年《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而1954年《宪法》第78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对比1982年《宪法》与1954年《宪法》关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规定可以看出,1982年《宪法》只规定了法院行使审判权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却没有包含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而1954年《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在行使审判权时,不受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的干涉。换言之,1982年《宪法》在保障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力度方面不如1954年《宪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彭真同志对此的解释是,这样修改有利于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对司法的监督。(注:参见蔡定剑:《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因此,认为人大行使个案监督权违背宪法制定者希望弱化人大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的理由是没有根据的。
第二,人大的个案监督权与人大直接行使审判权不是同一概念,因此,认为人大对法院享有个案监督权并不是说国家权力机关之间不应该进行合理分工。无论是将我国现行的政权组织形式定性为议行合一还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法院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对其负责,受其监督。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权理论学说中可以看出,强调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力至上是其核心内容。《宪法》只规定人大依法对法院的审判活动实行监督而没有规定监督形式,因此,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权理论以及《宪法》的规定来看,这种监督方式可以采取包括个案监督在内的任何一种。当然,笔者也认为对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进行合理的分工是必要的,人大也不应该直接代替法院行使审判权,但是人大的个案监督权与人大直接行使审判权毕竟是本质上截然不同的概念,不宜将二者等同。因为按照我国宪法学界的通说,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由其产生国家的“一府两院”,并将本应由其行使的行政权、审判权与检察权委托给行政机关、法院和检察院行使,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权力的最终承受者,对行政机关、法院和检察院的行政活动、审判活动以及检察活动依法进行监督。因此,这种监督与直接行使权力是完全不同的。同时,如果按照上述学者的结论,人大对法院行使个案监督权就是人大代替法院审判案件,那么,必然会得出这样一个逻辑命题:如果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家的行政机关采取包括质询在内的任何一种监督方式,就是在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并进而推论出这也会导致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不存在分工。显然上述学者也不可能接受这一必然的逻辑结论。因此,在笔者看来,如果将人大对法院享有个案监督权等同于人大在代替法院行使审判权,并由此推论出个案监督会导致国家机关之间权力不分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
第三,以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对中央军委的具体工作进行监督从而推论出人大也不应该享有对法院的个案监督权似乎有转换概念之嫌。因为中央军委的工作与法院的审判活动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军队必须步调一致,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自井冈山土地革命时期开始,我们党就牢牢地树立了党指挥枪的观念,强调党对军队工作的绝对一元化领导,因此,人大及其常委会通常没有监督军委的工作。况且,军队工作大多涉及国家的军事秘密,如果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够对军委的工作进行监督,前提条件是军队的工作都必须透明,这样国家的军事机密就有可能泄露。同时,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军队的具体工作进行监督也不具有现实性,因为现行法院体制是按照行政区划来设置的,地方法院由地方人大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而各大军区却不是由地方人大产生的,因此,地方人大无权监督各大军区的工作。当然,强调党对军队工作的领导并不是说法院的审判活动就可以离开党的领导。党是领导我们一切工作的核心力量,但是这种领导对于法院的审判工作而言,主要是一种组织上和政策的领导,而不是过多地干涉法院的独立审判活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已经开始反思党委过多地干涉司法工作的教训。1979年9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指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做法。”(注:转引自强世功:《法制的观念与国家治理的转型——中国的刑事实践(1976—1982)》,《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1986年7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必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再次重申:“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保证司法机关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注:转引自张憨、蒋惠岭:《法院独立审判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页。)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也指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这表明党中央已经充分意识到法院的审判工作和军队的军事工作是截然不同的。
第四,如果说《宪法》没有明确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院可以行使质询权的话,那么,在《宪法》颁布之后由全国人大制定的三部法律则明确赋予了人大的上述权力,这三部法律与《宪法》的立法本意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人大对法院行使个案监督权是符合宪法精神的。
诚然,从1982年《宪法》第73条的规定来看,《宪法》并未赋予全国人大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人大对地方人民法院和地方人民检察院进行质询的权力。但是在通常情况下,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只能对国家和社会生活进行原则性规定,具体的操作条款则由一些部门法规范来调整。这些部门法如果与宪法的立法精神相一致,那么,它们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就具有了宪法依据。实际情况是,在《宪法》颁布之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相继制定或修改了三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人大可以对法院行使质询权。这三部法律、法规依次是1987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议事规则》、1992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代表法》、1979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后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多次修改的《地方各级人大及政府组织法》。其中,《代表法》第14条规定:“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一个代表团或者30名以上的代表联名,有权书面提出对国务院及其工作机构和‘两高’的质询案,县以上地方各级人大代表还有权依法提出对本级‘两高’的质询案,县以上地方各级人大代表还有权依法提出对本级‘两院’的质询案。”《地方各级人大及政府组织法》第28条、第47条也规定了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一府两院”提出质询案的程序以及相关的人数要求。
考察上述三部宪法性法律、法规的内容,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大对法院行使质询权是符合宪法精神的。因为这三部宪法性法律、法规同《宪法》一样,都是由一套立法班子——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而且这三部宪法性法律、法规既与1982年《宪法》制定者关于强化人大对法院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立法意图相吻合,同时也与制定我国《宪法》的指导思想相一致。故笔者认为,人大对法院行使质询权完全符合《宪法》和相关组织法的规定。由于质询权是人大个案监督权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因此,可以认为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院行使个案监督权是有宪法依据的。
三、国外是否存在议会监督法院的立法例
关于个案监督亟须澄清的第三个误识就是国外是否存在与我国相似的立法例。目前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个案监督的学者都认为:国外特别是西方法治国家没有议会监督法院审判活动的实践,也没有与个案监督相似的立法例。例如,对人大行使个案监督权持异议的学者指出,任何法治国家都没有议会监督法律审判工作的先例,因此,个案监督不符合国际惯例。(注:参见何兵:《“个案监督”质疑》,《法治时代周刊》2002年4月8日。)而赞成个案监督的学者也认为西方法治国家没有议会监督法院的立法规定以及类似于我国个案监督的立法例。这些学者认为:“虽然在西方奉行三权分立的法治国家中立法与司法、行政三足鼎立,其司法机关一经设立,便具有不受其他机构和个人控制的较为完全的司法独立。即在西方法治国家没有议会监督法院审判活动的立法例,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大及其常委会不能行使个案监督权,因为我国奉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唯一的权力机关,人民法院处于派生的地位,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因此,在我国人大应该享有对法院的个案监督权。”(注:钱明龙:《个案监督应消除的几个误区》,《人大研究》2003年第3期。)
笔者在认真查阅国外议会与法院关系的相关资料之后,认为这些学者对国外议会与法院关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西方法治国家,议会对法院还是享有不同程度的监督权的,同时在西方学者眼中,司法程序“归根到底需要公开性,尤其是新闻和议会的监督保障。”(注:[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事实上,在西方很多法治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和韩国,也存在类似于我国个案监督的立法例。下文中,笔者拟对国外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的议会监督法院审判活动的立法例进行评介,以澄清上述已为学界普遍认可而又失之准确的认识。
1.瑞典的议会督察专员制度
瑞典是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国家,议会既负责制定法律,同时还监督政府和法院是否依照法律行使权力。瑞典议会对法院和政府的监督是通过议会的督察专员制度来实现的。所谓议会督察专员制度,是议会用来监督法院和行政机关是否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行使权力的一种制度。督察专员们由议会选出,其职责是根据议会下达的指示对法律和法规的适用进行公开的监督。(注:参见[瑞典]本特·维斯兰德尔:《瑞典议会监察专员》,程洁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第21页,第57页,第47—56页。))瑞典的《议会督察专员指令法》第2条明确规定了议会督察专员的监督范围为:所有国家与地方机关、全国性机构和地方当局以及法院。通常情况下,普通民众如果认为法院的判决和行政部门的决定不公正、不适当,就可以向议会督察专员办公室申诉,通过督察专员制度获得有效的救济。
在督察专员与法院的关系上,从瑞典的督察实践中可以看出,督察专员的主要精力是集中在法院的审判活动上。督察专员监督法院审判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确保法院按诉讼程序审理案件并在合理的时间内审结案件。在个别情况下,议会督察专员还可以对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提出异议。例如,当督察专员发现法院的判决超出了法律许可的处罚程度或者超出了自身的权限时,就会行使监督权。(注:参见[瑞典]本特·维斯兰德尔:《瑞典议会监察专员》,程洁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第21页,第57页,第47—56页。)督察专员在监督法院的审判活动时享有很大的权力:他可以出席法院的所有会议,并有权查阅任何法院的会议记录与案卷,每个被监督的法官都有义务提供议会督察专员所要求的相关资料,即使这些资料属于国家秘密。如果议会督察专员认为某个法官有过失行为,通常会给法院写信并提出批评意见。如果问题非常严重,议会督察专员可以建议对负有直接责任的法官予以处分,或者追究该法官玩忽职守的刑事责任。如果决定追究玩忽职守的法官的刑事责任,督察专员同时还要扮演公诉人的角色,所有的检察官都有义务协助督察专员完成指控法官违法的任务。
当然,议会督察专员在监督法院的审判活动时不能影响法院的独立审判权。瑞典的《政府组织法》第2章第11条明确规定:“无论公共权力机关(这里指政府)还是议会,都不得决定法院如何对某一特定案件进行审判,或在其他方面如何适用一项法律原则。”(注:参见[瑞典]Hans Hegeland:《瑞典议会:作用与工作程序》,艾志鸿等译,载王晓民主编:《议会制度及立法理论与实践纵横》,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页。)统计数据显示,1992年7月1日至1993年6月30日,议会督察专员对法院提出警告或者批评的案件共9起。在所有这些案件中,议会督察专员都没有对法院具体审理案件时应该如何适用法律或者取证发表意见,只是针对法院违反诉讼程序办案以及超过法律许可幅度的实体判决进行监督。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学者们认为,瑞典的督察专员制度很好地解决了司法独立与议会监督法院之间所可能产生的冲突。(注:参见[瑞典]Hans Hegeland:《瑞典议会:作用与工作程序》,艾志鸿等译,载王晓民主编:《议会制度及立法理论与实践纵横》,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页。)
瑞典督察专员制度赢得了来自国内外的一致赞扬,西方一些法治国家也纷纷在立法中移植该制度。首先,从瑞典国内的情况来看,对督察专员制度可谓是好评如潮。虽然目前还没有关于议会督察专员所采取的督察措施的效果的实证调查数据,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普通民众对该机构的存在是相当满意的,因为经常有投诉人在收到督察专员签署的认可令之后立即回信表示感谢,并对投诉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表示高度赞扬。从瑞典国内学者对督察专员的态度来看,虽然学界对督察专员制度存在争论,但是争论的问题却不是要不要废除该制度,而是应否赋予督察专员更大的权力。因为“在瑞典,公众对有关议会督察专员的争论从未对该机构的存在提出质疑。相反,问题往往涉及能否授予督察专员‘更尖锐的牙齿’。”(注:参见[瑞典]本特·维斯兰德尔:《瑞典议会监察专员》,程洁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第21页,第57页,第47—56页。)其次,瑞典的督察专员制度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国家都在学习、借鉴、移植瑞典的督察专员制度。自从瑞典的督察专员制度产生以来,世界各地的学者、律师和政治家对其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督察专员每年都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许多次访问,这些访问者的目的都是为了了解、学习督察专员制度的成功经验。同时,很多西方法治国家已经将督察专员制度在其国内立法中明确规定下来,如芬兰于1918年、丹麦于1953年、挪威于1963年也建立了类似于瑞典的督察专员制度。迄今为止,全世界约有55个国家建立了类似于瑞典的督察专员制度。另外,在新近独立的国家以及经历过集权制度、试图建立某种民主制度的国家中,人们对这类审查与监督机关也很感兴趣。(注:参见[瑞典]本特·维斯兰德尔:《瑞典议会监察专员》,程洁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第21页,第57页,第47—56页。)
2.日本和韩国的国政调查权制度
日本的国会既是立法机关,也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依法对行政权和司法权进行监督。日本议会的监督权是通过国政调查权来实现的。所谓国政调查权,按照《日本国宪法》第62条的规定就是:“两议院可以各自进行有关国政的调查,为此可要求证人出席并提供证言和记录。”(注:转引自张建伟:《刑事司法体制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413页,第413页。)日本学者所有关于国政调查权的研究,几乎都是集中在“司法权独立”的问题上,即国政调查权是否会影响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以此为轴心,日本学者对国政调查权的目的、范围以及如何防范其影响司法独立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关于国政调查权与司法权的关系,《日本国宪法》第76条规定,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只受宪法和法律约束。既然司法独立是日本的一项宪法原则,则不妨碍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就是日本国会行使国政调查权的前提,“哪怕是稍有一些违反司法权独立那样的调查,也可解释为是不允许的”。(注:转引自张建伟:《刑事司法体制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413页,第413页。)具体而言,国政调查权在行使过程中应该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对于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通常不允许国会以国政调查权的名义进行监督,但如果法官的审判活动明显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其性质严重到必须立即罢免其法官职位,且如果此时国会仍然置之不理势必影响司法公正时,则可行使国政调查权。当然,即使在这种情形下,国会也应该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注:参见杨建顺:《日本国会》,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第153页,第275页。)其二,对于法院已经审结的案件,国会可以对判决本身以及量刑是否恰当行使国政调查权。(注:参见杨建顺:《日本国会》,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第153页,第275页。)著名的“浦和充子”判例是国会对法院已经审结的案件行使国政调查权的经典判例。1949年3月2日参议院制作了“浦和地方法院关于‘浦和充子’案件在事实认定和量刑上都过于轻率”的报告书,以此纠正了法院的错误判决。虽然事后最高法院和一些学者对参议院的上述行为进行了批评,认为这种做法侵犯了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但参议院法务委员会却认为国政调查权是国会的一项独立权限,对法院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进行调查,是国政调查权作为一项独立权限的内在要求之一,本身也不会对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注:参见杨建顺:《日本国会》,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第153页,第275页。)总之,虽然日本最高法院和学界并不赞成议会的国政调查权可以针对法院已经审结的案件,但是从其立法及判例来看,国会是可以监督法院已经审结的案件的。
鉴于日本的国政调查权能够很好地解决国会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冲突,1980年韩国也在其宪法中第一次将国政调查权确立了下来,同时其1987年的宪法还进一步明确了国政调查权的目的、调查方法及范围等操作程序。对于法院的审判权,国政调查权的范围主要包括大法院规则、宪法法院规则、法院预算的运用、法官的人事安排、程序规则以及审判是否迅速进行等事项。韩国同日本一样,司法独立也是一项宪法原则,因此,国会在行使对法院的国政调查权的过程中不得影响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对于法院的审理和裁判活动是否可以行使国政调查权,韩国现行立法的规定与学界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立法上明确规定,国政调查权属于国会独立的权限,国会可以对法院的审理和裁判活动进行独立的调查;而学者们则认为,如果允许国会对法院的审理和裁判活动进行调查,有可能侵犯法官的独立审判权。换言之,在韩国,虽然学界反对国会针对法院的审理和裁判活动进行调查,但是立法上还是赋予了国会这项权力。不过,国会在行使这项权力时应该遵循以下四个方面的规定:第一,对法院正在审判的案件,不得以法官的诉讼活动作为调查的对象;第二,对法院的审判内容只能进行合法性而不是合理性调查;第三,不得对正在审判中的案件要求法院提出司法上的文书;第四,禁止针对特定个人是否有罪进行调查。确定上述界限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司法独立的价值,从而形成国政调查权与司法独立的良性互动。(注:参见韩大元:《韩国国会》,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121页。)
3.美国和英国的做法
美国和英国没有采取类似于瑞典的督察专员制度以及日本、韩国的国政调查权制度,但为了保障议会能够对法院审判权的行使进行适度的监督,也采取了一些相关的措施。例如,美国为了使法院的审判活动能够按照议会制定的法律来进行,同时也是为了使议会能够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必要的监督,一直比较注意议会与法院之间的积极联系与沟通,如在基层法院和巡回法院两级设立了法院与议员的非正式沟通渠道。为加强沟通的质量和持续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和美国司法联合会建议在联邦法院设立一个常设的委员会,由联邦政府、立法和司法部门的人员担任其成员,其职责之一就是对联邦法院审理的有关案件进行研究并定期向联邦法院提出建议。(注:See Stephen G.Breyer,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40 Saint Louis University Law Joural,pp.989—996(1996).)英国议会虽然对法院正在审理的未决案件不能发表任何评论,但英国一直奉行议会至上原则,实行两院制,贵族院实际上是国家的最高司法机关,其议长同时是贵族院首长、首席大法官和内阁成员,而英国的法院系统由贵族院议长办公室直接管理。同时,针对一些特殊的案件,议会也可以直接行使审判权。在特殊情况下,如果议会无法容忍法院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还可以通过事后重新制定溯及既往的立法来矫正该判决。显然,上述做法可以保证议会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某种程度的监督。英国议会监督法院审判活动的另一途径就是通过议会来直接行使审判权。由于此时行使审判权的议员既是法官又是立法者,为了避免由此所可能导致的程序不公,2000年下议院一名资深贵族法官指出,议员法官在遇到下列两种情况时应该回避:一是案件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纷争色彩;二是议员法官此前就对与该案相关的问题发表过自己的意见。(注:参见张越:《简述英国议会与法院的关系》,《人大研究》2004年第10期。)总之,无论是美国的司法联合会还是英国的贵族院,都是一种保证议会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适度监督的切实有效的途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笔者主张人大及其常委会应该享有对法院的个案监督权,但也认为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行使这种权力的时候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即不得妨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我们应该借鉴瑞典的议会督察专员制度以及日本、韩国的国政调查权制度的有益经验,制定严密的规范人大行使个案监督权的操作程序,尽量将个案监督对司法独立所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