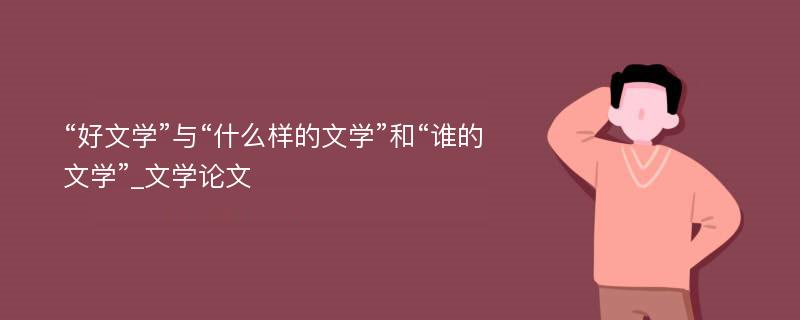
“好的文学”与“何种文学”、“谁的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谁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久前南方一家有影响的报纸组织了一次有趣的讨论,主题是“一部作品赢得热爱和 尊敬的理由”。记者向几位当红的中国作家提出了如下问题:“如果没有外在的提示, 比方获奖、畅销等,我们凭据什么去发现和喜欢一本小说?……换一种表达方式:一部 作品赢得热爱和尊敬的理由是什么?”韩少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优秀的作品 一定是透着心血的,一定不是冲着热闹而去的。”王安忆的回答要“文学化”一些:“ 有几个男作家的作品我很喜欢,作品中有一种‘温柔’的特质,那是一种温柔的情感。 比如张炜、张承志、史铁生,台湾的陈映真,还有西方的米兰·昆德拉……需要说明的 是,我判断作品的好坏从来不以深刻、价值判断的先锋为标准,而看感情是否饱满…… ”(注:《南方周末》,2002年8月8日。)
让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些个性纷呈的答案,而是记者提出的这一问题本身。韩少功和王 安忆显然都没有提供让我们满意的答案。我们可以承认“优秀的作品一定是透着心血的 ”,却不能说“透着心血的作品”一定是优秀的,谁都知道作家对文学的态度与文学作 品的好坏根本是两码事。而王安忆说史铁生“温柔”大体说得过去,说张炜、张承志乃 至陈映真“温柔”就恐怕难以服众了。王安忆在这里显然在自说自话,她无意为“好文 学”确立标准。然而,问题在于,如果连韩少功、王安忆这样的超一流作家也无法为我 们提供“好文学”的标准,那么作为文学研究者的我们如何去判断一部作品的“好”与 “坏”呢?面对每年900部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我们依据怎样的标准对它们进行阅读、评 判和选择,甚至将它们中的佼佼者写入文学史呢?
“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从90年代开始重新变成了一个让文学研究者、作家乃至读者 感到困惑的问题,显示文学研究者形成于80年代的依靠“50—70年代文学”这一“他者 ”确立的以“个人性”、“文学性”(纯文学)等为标准的文学共同意识发生了分裂。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80年代的那套文学话语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和解释这个今非昔比的世 界。事实上,只要不是深怀偏见或特别懒惰的人,都不难发现今天我们置身的世界发生 的剧烈变化。改变的不仅仅是环绕我们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还有我们由此产生的 对民族国家/全球化、东方/西方、自我/群体关系的认知方式。在这些变化中,“文学 ”的改变尤其惊心动魄。虽然不乏死活不愿意离开80年代的教条主义者对这些变化充耳 不闻、视而不见,仍然一如既往地挥舞着“个人性”、“文学性”(纯文学)这些陈腐的 兵器,演出一场又一场狂热而又滑稽的风车大战,然而,更多的研究者却在开始睁开眼 睛,重新打量我们置身的这个新的文学—社会空间,在艰难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中, 重新思考文学乃至文学研究的意义。在“普遍性”遭到普遍质疑的90年代的语境中,研 究者对于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原理”,对于丝毫不加语境限制地使用“文学” 范畴开始失去信心,因而几乎是必然地导致对“何种文学”,“谁的文学”这样的“文 学史”问题的不懈追询。
80年代文学场域中最重要的关键词莫过于“个人性”(或称“个体性”、“个体化”、 “个性化”等)。这一时期的文学叙事借用屡试不爽的“传统”与“现代”、“文学” 与“政治”的对立确立了“个人化写作”与所谓的“集体—政治写作”——“公式化” 、“模式化”的文学的对立。文学研究者真诚相信的一种“事实”和“真理”,即真正 有意义有价值的文学必然是“个人”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批评家乃至文学史家肯定 一部作品的最重要的理由,是指称这部作品“真正”——或者说“终于”回到了“个人 ”。与此相对应的是,“50—70年代文学”由于其强烈的社会性和政治性以及由此导致 的“模式化”或“公式化”特点,被理所当然地视为“非文学”,或被理解为政治对“ 文学”与“文学”赖以存在的“个人”的扭曲和强暴。对“50—70年代文学”的批判与 控诉成为80年代文学确立主体性的基本前提,它与思想文化领域“告别革命”的诉求相 呼应,从8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精神信仰和知识内核。然而 ,这种将知识转变为信仰的认知方式中隐含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在80年代初期 ,文学研究中——其实远远不是仅仅在文学研究中的这种“个人化”立场还因为对左翼 文学表达的“一体化”政治的解构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那么,面对90年代以后的文 学与社会现实,继续宣扬无边的“个人化”,将在具体历史语境中获得的知识普遍化, 却可能在反对一种政治的同时,丧失对历史的批判和对现实的想像能力,进而演变为对 一种压抑“个人”和差异的、以建立同质化、一体化为目标的政治的辩护。在不可遏止 的全球化过程中,“个人”由80年代的“抽象主体”逐渐向“利益主体”转换,“个人 性”也悄悄向“私人性”演化。环绕着“私人性”这一语词周围的,已经不再是“自由 、平等、公正”这类精神色彩浓郁的语言氛围,而是由欲望、身体这些打着“个人”旗 号其实又是最不个人的、被高度殖民化的生活世界。具体地说,成为90年代文学环境的 社会生活的主要问题早已不是“过度政治化”的问题,而是“过度私人化”的问题,或 者说,主要不是“个人”或“私人”受到“左翼”政治压抑的问题,而是“全球化”以 “个人”为名压抑和排斥“公平”、“平等”等“集体叙事”和“宏大叙事”的问题, 用甘阳的话来说,“当少数人正在疯狂掠夺多数人的财产并且日益威胁多数人的基本保 障时,我们却听到许多人在那里摇头晃脑地谈什么‘多数人的暴政’”(注:甘阳:《 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载《知识分子立场》,2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作为“对革命激进主义的反省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且开始在走向反面”的最为直 接的表现,是“个人”的权力已经在开始压抑甚至强暴“不个人”的权利。在这一意义 上,90年代的那场无疾而终的“人文精神”讨论不过是以多少带有反讽意味然而又是异 常真切的方式表达了知识分子对这一变化了的中国现实的艰难回应——所谓的“反讽意 味”指的是人文精神的倡导者对自己的立场缺乏自觉,90年代让他们怒不可遏的不符合 整体性的“人文精神”的东西其实正是他们在80年代亲手从潘多拉的盒子中释放出来的 “个人性”。“人文精神”讨论正是以这样一种缺乏自觉的方式展开了知识分子对80年 代的反思,并进一步开启了90年代末期的更著名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 再度展开了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现代中国知识场域的重构。
90年代以来文学—社会环境的变化使我们不能不思考“个人性”这一范畴的有效性。 其实,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在理论世界,“个人性”都不是一个可以被当成信仰而超语 境使用的概念,这个内部充满了紧张与冲突的范畴实际上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就 文学研究而言,即使是在现代西方文学理论中,“个人化”也从来不是“好文学”的惟 一标准。譬如说在艾略特那里,好的作家恰恰是“非个人化”的,“于是他就得随时不 断地放弃当前的自己,归附更有价值的东西,一个艺术家的前进是不断地牺牲自己,不 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注: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载《艾略特诗学文集》,4 、4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艾略特认为判断一位好作家的标准在于他的作品 中是否具有“历史的意识”——当然,他这里的“历史”指的是欧洲的历史:“历史的 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 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注:艾略特:《传 统与个人才能》,载《艾略特诗学文集》,4、4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而在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中,好的文学恰恰是模式化的。模式化—类型化的文学常常具有潜在 的深层意义模式,常常具有深刻而不可替代的社会化的文化意义,它以幻想的形式,隐 喻地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内在生活的秘密,告诉我们特定时代(包括“话语讲述的时代” 与“讲述话语的时代”)以及特定文化传统中那种固有的困惑与关怀。“原型批评”则 将这些在作品中反复的意象或叙述母题称为“原型”,用弗莱的话说,这些原型是具有 可交际性的,它作为一种典型化的结构因素,把一部作品与另一部作品联系起来,把一 位作家、一部作品与整个文学传统、文化精神联系起来。批评一方面追索这样一种原型 ,另一方面又从追索到的原型中思考一位作家的创作与民族文学传统的整体意义,洞悉 我们置身其中的文化精神……
由此可见,文学作品的好与坏常常并不由作品本身决定,而取决于评价作品的理论和 方法,更取决于我们讨论这些文学的语境。——如果我们因此承认“个人性”本身并不 是“好文学”的理由,那么,是否我们也应当因此放弃将“模式化”、“公式化”的文 学视为“坏文学”乃至“非文学”的偏见呢?
在80年代的知识中,与“个人化”异曲同工并与“个人性”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的另 一个关键词是所谓的“纯文学”。“让文学回到文学”成为了与“让文学回到自我”同 样著名的口号。在这里,“文学”的他者是“政治”。只是与文学的“个人性”原则一 样,如果说“纯文学”这一观念的提出在80年代代表了一种对抗主流政治的积极意义, 那么,在90年代的语境中,当“纯文学”——按照80年代的理论,即所谓“纯个人”的 文学——成为完全形式化的写作乃至完全“私人化”的“身体写作”和“下半身写作” 的旗帜,成为诸如“我爱美元”的宣言、占有女性的幻想、私人生活的展览等的辩护词 以及用以表达和强化个人对社会问题无能的时候,当文学“让纯文学马车驾着个人的下 半身飞奔”(注:薛毅:《开放我们的文学观念》,载《上海文学》,2001年5期。), 使“文学”在脱离了“左翼”政治的控制之后投入商业化、市场化——这一体积更为庞 大的“右翼”政治的怀抱,共同构建出另一种更具压抑性、更加难以摆脱的新主流意识 形态的时候——或者说,当许多人以“纯文学”为名鄙弃文学对弱者的同情与关怀、对 不合理的现实的批判等对公共领域的关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一边气壮如牛地以80年代 的口吻宣称自己是一个具有人道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一边又坚持这种一点都不“人道 ”、一点都不“公共”的超时空的“纯文学”理想呢?
在90年代仍然坚持“纯文学”理想的人的确需要一种非凡的漠视现实的能力。人们仍 在说“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彻底的态度,当然是审美的态度,把上帝的还给上帝,凯撒的 还给凯撒”(注:刘克敌:《重建文学史形态:必要与可能》,载《文艺争鸣》,1996 年4期。),人们仍在重谈将文学史从政治中剥离出来的高调……这些“文学研究者”在 抒发自己的“高论”时是如此理直气壮,他们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安徒生童话里那位指出 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小孩,仿佛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明明知道有一种“文学”的批评却有 意不用,这样的推论之所以荒诞,是因为这些“文学研究者”从来不以同样的方式反问 自己,那就是他们能否指出在“新时期”以来(“新时期”以前不用说了因为肯定不会 有)的中国文坛上,谁进行的批评是与政治无关的“文学”批评?或者追问在将“政治” 彻底从文学史剥离开后“文学史”还能剩下什么?
80年代的“纯文学”观念的出现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然而,这一“合理性”只能在 斯皮瓦克的所谓“策略上的本质论”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如果将其理解为文学的不变的 “本质”,将其理解为超历史的哲学范畴,那么,“纯文学”观念有过的正面意义就完 全取消了。事实上,只要稍稍具有一点文学史知识的人,都不可能幼稚到会相信存在一 种与时代、与政治完全无关的“纯文学”。“纯文学”观念进入中国以来,从来就没有 固定不变的意义。它是历史机缘的产物,其含义依据特定的历史—政治环境确定,表达 出不同的现实—政治诉求。即使是在“纯文学”喊得最响的“五四”时期和所谓的“新 时期”(即80年代),“纯文学”的政治性同样昭然若揭。“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家的确 曾以“纯文学”为旗帜反对旧文学的“文以载道”,但他们反对的并不是“文以载道” 本身,而是反对传统文学载的“道”,反对的目的是为了使文学成为传播新文化、建构 新政治的工具。用格里德的话来说:“文学革命从其发端就是更广阔范围的思想改革运 动的工具。”(注: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9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 5年版。)而“文革”后的“纯文学”概念完整地重现了“新文学”的策略,那就是文学 是政治不要紧,要紧的是要表达“正确的”政治。80年代出现的文学论争以及所谓的“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文学主潮,无一不是以“文学”为名而大肆张扬的政治理 念。由此不难发现,作为一个本土的、国家性社会文化建设运动的一个环节,“文学” 从来不是独立于政治的自主意识,而是一种对应并维护了中国现代性的历史经验的制度 。它在现代中国的每一次显形,都以特定的社会政治诉求参与了某种“想像的共同体” 的建构。“文学”的斗争从来就不只是“文学”之间的斗争,而必然是——只能是文化 与政治的斗争。因此,不应该把“文学”剥离出具体的历史进程和权利关系,而应该把 “文学”历史化,——或者说将“文学”作为话语对待。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 不会再以是否与“政治”有关作为判断“好文学”的标准,而是转而追问这种文学表现 的是“何种政治”与“谁的政治”。具体到90年代以后的文学研究,则应当对时至今日 仍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地鼓吹“纯文学”的人提出类似的问题:你们今天的“ 纯文学”抗拒的是“何种政治”,张扬的是“谁的政治”?
概而言之,当我们不再把“个人”、“文学”这些概念视为超历史的形而上学范畴, 而是将这些概念历史化,探询这些概念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的不同意义的时候——或者 更进一步,当我们不再以为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只是“我”与“作 品”之间的透明关系,而是清醒地意识到“我”和“文学”之间横亘着数不清的批评方 法,所谓的批评其实是我们在使用批评方法进入“文学”的时候——即我们充分意识到 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其实是文学教育的结果的时候,对文学“好”与“坏”的价值探讨才 可能进入更加有效的知识探讨,对文学的批评与批判才可能同时意味着对自我的批判与 反思——同时意味着对自我与现实关系的重新体认。或许只有以此为前提,我们才能够 真正重新建立起我们与“文学”乃至历史和现实的有效关联,在想像——也就是意识形 态的斗争中获得社会和文化的新空间和新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