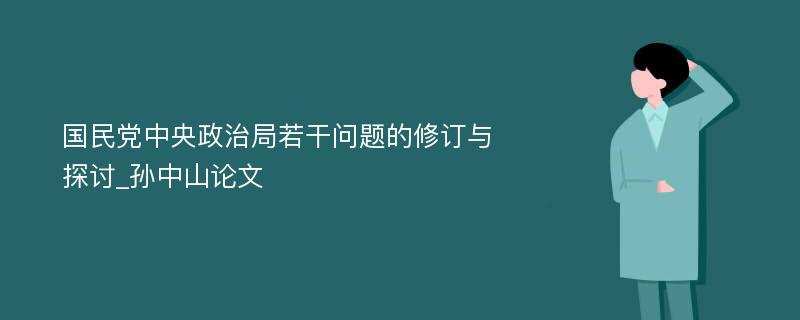
国民党中政会若干问题的订正与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党论文,若干问题论文,中政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0)03-0080-06
《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发表的王奇生撰《中政会与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轮替(1924-1927)》(以下简称《轮替》),有数处论述涉及到笔者发表于《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演变述略》(以下简称《述略》),因而引起了笔者的关注。笔者认为,该文涉及到笔者《述略》的四处论述欠妥,值得商榷,除此以外,该文还存在其他问题,所以特撰此文,就该文涉及到笔者《述略》的论述发表商榷意见,同时也就该文存在的其他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一
《轮替》涉及到笔者《述略》的四处论述,都是程度不同的否定或者批评。笔者细读了该文后,觉得这些否定或者批评都是站不住脚的。
下面逐条分析这四处论述:
第一处:《轮替》第一部分第八段称:“后来的看法,认为中政会最初只是备孙中山咨询的一个辅佐机关,没有法理职权和明确责任,其权力实际有限。这一说法不尽符事实。”这一批评针对的对象,包括笔者的《述略》。笔者认为,这一批评是有问题的。
问题之一,笔者的《述略》并没有认为中政会最初“没有法理职权和明确责任”。《述略》在论述中政会建立之初的权限时,写有如下一段话:“胡汉民在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3次会议提出《政治委员会对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权限案》,规定:(一)关于党事,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按照性质由事前报告或事后请求追认;(二)关于政治及外交问题则由总理或大元帅决定办理。根据这一提案,中政会虽有议决党事之权,但关于政治外交问题,则需在议决后,由孙中山最后决定方能执行。”这段话已经根据胡汉民的提案阐明了中政会建立之初的法理职权和责任。《轮替》对此的批评是不符合事实的。
问题之二,《轮替》批评中政会建立初期“其权力实际有限”这一看法时,提出的基本依据是中政会实际地位重要,“孙中山所指派的中政会委员,都是其最信赖的左膀右臂和忠实追随者。而中政会的实际运作,也显示它是一个比中执会更核心的权力机构”。但笔者的《述略》并不否认中政会建立初期实际地位重要,相反早已指出:“中政会成立时,孙中山共任命了七名委员,他们是: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伍朝枢、邵元冲。他们都是孙中山的左臂右膀和忠实追随者。这说明,中政会初期虽然权力有限,但其地位的重要性不可低估。”笔者认为,中政会建立初期实际地位重要并不能否认其权力有限。为什么这么说?这是由孙中山生前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的权力基本上集中于他一人之手,不论是国民党中执会,还是中政会,权力都是有限的。从中政会的实际运作情形来看,它当时的确能够就一些重大问题做出决策,其实际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超过了国民党中执会,但这并不能改变孙中山大权独揽的事实。在孙中山大权独揽的情况下,中政会的实际地位不管怎么重要,它的权力都必然是有限的。所以,如果以孙中山逝世后的中政会作为参照物,说中政会建立之初权力有限并无不妥。
第二处:笔者在《述略》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国民党中政会成立后,紧接着又组成军事委员会,“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专理党务,中央政治委员会筹划政治上的大政方针,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军事。后来,中政会的性质及职权虽几经变化,但这一格局大体未变”。《轮替》对这一观点也进行了批评,其原文是:“一般的说法,孙中山设立政治委员会的目的,是出于军政、党务分工办理的考量。因为在政治委员会成立后,又议决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这样一来,似乎形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党务,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政治,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军事之分工格局。不过,在政治委员会成立初期,其职能之分工并不如此清晰。”
对《轮替》的这种批评,笔者觉得需要指出如下数点:第一,笔者所说的在国民党中政会、军事委员会成立之后,“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专理党务,中央政治委员会筹划政治上的大政方针,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军事”,只是指国民党内一种基本的分工,这种分工从一开始就是非常清晰的,因为孙中山建立中政会、军事委员会的指导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军政、党务须分工办理。第二,这种分工并不排除国民党中执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处理政治、军事问题,也不排除中政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处理党务、军事问题。如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对于时局宣言》、《接受总理遗嘱宣言》、《对于党军校及军队之训令决议案》,就涉及到政治、外交、军事问题。如果认为中政会除了政治外不再处理任何党务、军事问题,中执会除了党务外不再处理任何政治、军事问题,它们之间的分工才算清晰,那么这是对国民党中执会、中政会、军事委员会之间的分工做了过于机械的理解。不仅在中政会成立之初没有如此清晰,就是后来也从没有达到过这种“清晰”的程度。第三,《轮替》批评笔者观点的一个主要依据是胡汉民在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3次会议的提案(提案的内容见前文)。但笔者认为,该文作者明显误读了这一提案。该提案的确显示中政会能够处理党事,但该提案同时又明确规定,中政会处理党事时,必须“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必须按照事件的性质向中执会“事前报告或事后请求追认”。而关于政治及外交问题,则没有这样的规定,而是规定由兼任中政会主席的孙中山决定办理。这说明党事是中执会的职责范围,政治与外交是中政会的职责范围,中政会虽能议处党事,但超越了它的职责范围,所以必须对中执会负责,事前报告或事后请求追认。
因此,中政会成立之后,中执会负责党务、中政会负责政治、军事委员会负责军事这样一种分工是明确的,并不存在不清晰之处。《轮替》的批评是对这三者之间的分工做了一种机械、简单的理解,并不能够成立。
第三处:笔者在《述略》中对孙中山逝世后至大革命失败前的国民党中政会的性质有如下一段论述:“此后,不仅国民政府,而且国民党中央的许多重大事情都由中政会讨论决定,然后再交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中政会的这一地位,在大革命失败前,基本上没发生过变化,因此有人认为它当时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党政最高机构’。”
《轮替》对笔者的这一段论述也进行了批评,其原文是:“以往有学者认为自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一直到1927年宁汉合流以前,中政会始终是国民党的‘党政最高机关’,其地位基本上没发生过变化。这一看法显然不确。”笔者不同意这一批评,理由如下:
孙中山逝世后,中政会迅速演变为国民党的最高党政机关,集党政权大权于一身。此后,中政会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关节点:一是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的召开,二是1926年7月中央政治委员会改组为中央政治会议,三是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三个重要的关节点都没有能够动摇中政会作为国民党党政最高机关的地位。
首先,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后,中政会的地位没有下降。国民党二大闭幕后,紧接着召开的国民党的二届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轮替》认为这一条例“明确了中政会与中执会的隶属关系”,并“将中政会的职权限定在‘政治指导’方面”,旨在限制中政会的权力。但实际上,这一条例并没有这种意图。中政会是中执会的下属机构,在中政会成立时即已明确,该条例只不过对此再次加以确认而已。至于中政会的职能,也是一开始就定位于“筹划政治上的大政方针”,即处理政治问题。因此,这一条例在对中政会的定位和定性上,并没有作出新的改变,当然也就并不存在限制中政会权力的意图。
事实上,从国民党二大后中政会的组织和人员构成情况来看,中政会的权力应该是有增无减。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推选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伍朝枢、孙科、谭平山、朱培德、宋子文等9人为政治委员会委员,陈公博、甘乃光、林祖涵、邵力子4人为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同时选举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蒋介石、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9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对比这两份名单,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三巨头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都既是政治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中常会委员。从这一点看,中政会与中常会的地位可以说不相上下;第二,中政会与中常会的人数,都是9人。从这一点看,中政会与中常会的地位也可以说不相上下。第三,中政会的4名候补委员中,有3名是中常会委员。也就是说,有部分中常会委员只能作中政会的候补委员。从这一点看,中常会的地位又略低于中政会。
此外,有材料显示,这一时期的中政会,不仅是政治上的最高机关,而且也议决国民党的重大事项。如1926年5月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闭幕式上解释提出整理党务案的原因时说:“我此次向政治委员会建议,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第二次全体会议,完全是以党员的资格来建议的,决不是以军人的资格要来解决党内的纠纷。”[1]589这不仅显示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是由中政会决定的,也显示中政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最高机关。
其次,1926年7月中政会改组为中央政治会议后,其地位没有下降。1926年“3·20”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逼迫汪精卫出走海外,提出整理党务案,对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的权力加以限制,开始逐步控制国民党的军权和党权。在此过程中,蒋介石为了削弱鲍罗廷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和影响,对受到鲍罗廷控制的中政会确有加以限制、甚至取消之意。1926年7月5日他在国民党中执会会议上提出将中政会归并于中常会的建议,就体现了这种意图[1]605。蒋介石希望通过将中政会归并于中常会,来加强中常会的权力,但归并的结果,是重新组成了一个其性质相当于中政会与中常会联席会议性质的中央政治会议。1926年7月6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规定“政治委员会应于中央常务委员会同开一政治会议,以代政治委员会之会议”。7月13日,国民党第40次中常会作出决定,政治委员会改为政治会议,并推汪精卫等21人为政治会议委员[2]。中央政治会议组成以后,原来的政治委员会固然不再存在,但中常会也名存实亡。中央政治会议不仅取代了原来的政治委员会的地位和职能,而且也取代了中常会的地位和职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党最高党政机关。这种结果,说明蒋介石并没有达到取消中政会,加强中常会权力的目的。原来的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摇身一变为中央政治会议,不仅继续存在,而且由于其性质相当于中政会与中常会的联席会议,其权力有增无减。
最后,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中政会的地位也没有下降。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名称,并对中政会的职权进行了限制。但由于中政会行使最高职权的传统,以及中政会的组成人员以中常会成员为主,因此中政会的实际权限并没有降低。
综上所述,从孙中山逝世到大革命失败前,中政会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关节点,但其作为国民党最高党政机关的地位始终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根本变化。《轮替》对学术界的这一传统看法的批评是不能成立的。
第四处:笔者的《述略》在谈到1926年7月中央政治委员会改组为中央政治会议的意义和影响时有如下一段论述:“中政会的改组,‘其意义在将中央常务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合并为一’,以统一最高领导。改组前的国民党中政会,虽然实际上已成为政治上的最高决策机关,但名义上仍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所做出的决策须经中常会批准。改组后的中政会,由于中常会成为它的一个部分,因此权限更加增大,甚至超过中常会。”
《轮替》对笔者的这一段论述也进行了批评,其原文是:“有学者认为,此次中政会改组,‘其意义在将中央常务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合并为一’,因而权力更大,甚至超过中常会。实际上,两会并非完全合并为一,中常会仍然独立存在。而中政会改组为政治会议后,意味着中央常务委员可参加政治会议,而一般的政治委员却不能参加常务委员会议。而且人数增多以后,政治决策的机密性与运作的灵敏性均将受到影响。”
这一批评也是有问题的。首先,“其意义在将中央常务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合并为一”,并不是笔者提出的观点,笔者在《述略》中已经注明了其出处。《轮替》对笔者进行批评时,不注明其原始出处,给人的感觉是它出自笔者的《述略》。该文这样张冠李戴,笔者虽然感到荣幸,但并不赞同这种不实事求是的做法。
其次,中政会的改组,实际上意味着中常会与政治委员会合并为一。前辈学者所说中政会的改组,“其意义在将中央常务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合并为一”,侧重点在指出中政会改组的实质,而并不涉及中常会本身的存废。不论中常会是否存在,这一论断都是成立的。因此,《轮替》所说的中政会改组后,“中常会仍然独立存在”,虽是事实,但并不能推翻前辈学者的这一论断。
再次,由于中央政治会议成为国民党内公认的最高职权机关,因此中央政治会议的委员能不能参加中常会,都不影响到中央政治会议的职权。至于中央政治会议比政治委员会人数增加,这对中央政治会议的地位和职权,基本上是一种正面的影响。因为所增加的是中常会的成员,这是提高了中央政治会议的地位,而不是降低了其地位。
二
《轮替》另外还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直接关于中政会的,但它们是该文在论述中政会的时候出现的,笔者为了论述的方便,姑且也把它们看作与中政会有关的问题。它们是:
1.如何看待国民党的“党治”?
《轮替》的结尾,对国民党的“党治”体制有如下两段论述:
法无定规,权随人转,一切都在“党章”、“党纪”、“党权”、“党治”、“党统”等旗帜和名义下进行,一切又以实力较量和权力权谋为依归。党的规章和形制虽是外来的、现代的,而实际运作与权力递嬗的潜规则及其政治文化土壤则完全是本土的、传统的。
从早期中政会的组织与人事演变中,我们不难看出,传统“帝治”向现代“党治”的转型,变的更多是外在形式,而不变的,则可能延续在中国数千年的深层政治文化之中。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仅仅关注制度本身是不够的。“法治”的背后其实仍是“人治”。
这两段论述是有问题的。
首先,“现代‘党治’”本身就是一个站不住脚的提法。“帝治”肯定是传统的,但“党治”是不是就是现代的?显然不是。“党治”是现代才有的,但却没有现代性可言。政治现代化的趋势是民主化,但“党治”与民主、与“法治”是根本对立的。作者把“现代‘党治’”作为与“传统‘帝治’”相对立的概念提出来,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党治”与“帝治”相比,有根本的进步。但实际上,这两者虽有形式的不同,在专制这一点上却并无本质区别。所谓的“现代‘党治’”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
其次,作者在第二段论述中,显然把所谓的“现代‘党治’”看成了“法治”,这对“党治”和“法治”都是一种误解。所谓“法治”,最基本的要求是任何政党、任何个人的行为都必须受到国家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而不应该凌架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国民党的“党治”显然是与此相悖的。对于国民党的“党治”的实质,孙中山曾说得很到位,这就是“把党放在国上”。这一点,该文曾经提到。在一个“把党放在国上”的体制里,能有所谓的“法治”存在吗?对于“党治”或者叫“以党治国”,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决反对的。早在1941年4月15日,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这篇文章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并认为“以党治国”是国民党的遗毒,我们要反对这种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3]10~12。所以,把“党治”与“法治”等同起来,是一种错误的理解,是没有弄清“法治”的真正内涵所致。
第三,国民党中政会存在的“法无定规,权随人转”等问题,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国民党向“党治”体制的转型不彻底,而是因为“党治”实质上仍然是一种“人治”,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治”所产生的,国民党即使彻底实现了向“党治”体制的转型,这些问题依然会存在。
2.镇压商团叛乱的“革命委员会”究竟有没有成立?
《轮替》有一个注释,对1924年10月孙中山为镇压商团叛乱而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有如下论述:“1924年10月初,孙中山在鲍罗廷的鼓动下,还一度打算成立一个名为‘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机构,这一机构可能位于政治委员会之上,其权力比政治委员会更为核心、更为集中,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并加大‘以俄为师’的力度。但不知何故最终未能正式成立。”
这段论述的依据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蒋介石年谱初稿》。笔者查阅了《蒋介石年谱初稿》,的确没有关于“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的有关记载。但这是不是就能成为判断“革命委员会”未能正式成立的依据呢?回答是否定的。
其实,如果细读《蒋介石年谱初稿》的有关记载,就会发现“革命委员会”其实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简称。《蒋介石年谱初稿》1924年10月9日记载:“又奉总理手谕:令迅即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这一记载的下面,收录了两封函件,一封是蒋介石致孙中山,“函请总理应准胡、汪加入革命委员会”。函件称,“今日鲍顾问来校就商革命委员会之人选问题,其语意甚不愿展堂与季新加入”,“此中期期以为不可也”,“中以为必须展堂与季新之名列入为妥”。第二封是孙中山给蒋介石的复谕,表示:“革命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1]243把“又奉总理手谕:令迅即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一记载与上述两封函件的内容联系起来看,基本可以断定,所谓“总理手谕”就是孙中山为成立“革命委员会”给蒋介石的复谕,所谓“令迅即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就是孙中山复谕中所说的“革命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因此,所谓的“革命委员会”,实际上另有一个名称叫“革命军事委员会”。
关于“革命委员会”或“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历史资料甚少。但从笔者接触到的资料看,下述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革命委员会”于1924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以孙中山为会长,以许崇智、廖仲恺、汪精卫、蒋中正、陈友仁、谭平山为全权委员。这从《蒋介石年谱初稿》的下述两条记载可以看出:
1924年10月10日记载:“是日,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总理为会长。”[1]246
1924年10月11日记载:“大元帅特派许崇智、廖仲恺、汪精卫、蒋中正、陈友仁、谭平山为革命委员会全权委员。大元帅令革命军事委员会用本会长名义,便宜行事,弭平商团事变,并立即设法收回关余。”[1]246~247
这两条记载,第一条反映出“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24年10月10日成立,以孙中山为会长,但没有组成人员名单;第二条反映出“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但没有说明“革命委员会”以谁为首,首长的名称是什么。如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是两个不同的组织,一般不可能同时存在这样的缺漏。而且,这两条记载的缺漏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它们的内容可以互补。这样的缺漏实际上正好说明,它们是同一个组织。因此,《蒋介石年谱初稿》中虽然没有关于“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的记载,但关于“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的记载实际上也就是关于“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的记载。所谓“革命委员会”最终未能正式成立的说法是错误的。
第二,“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孙中山曾要求付托以“政府全权”。这说明它是一个孙中山为镇压商团叛乱而成立的临时机构。
“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二天,孙中山致电广东省长胡汉民称:“密刻,仲恺到,并接电话,知省中已有非常之变,我以北伐重要,不能回省戡乱,请立即宣布戒严,并将政府全权付托革命委员会,以对付此非常之变,由之便宜行事以戡乱,则小丑不足平也。委员为汝为、介石、精卫、仲恺、友仁、平山,我为省(疑为“会”字之误,笔者注)长,兄不在列者,留有余地也。接电即发表,切勿犹豫致误为要。”[4]448
这则电文说明,“革命委员会”是孙中山为对付商团叛乱这一“非常之变”而采取的非常措施,其性质是在戡乱时期临时行使政权全权,其目的在于让其能够“便宜行事以戡乱”。作为一个临时机构,其性质、地位和作用是不能与政治委员会相提并论的。
第三,“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曾于1924年10月14日任命胡汉民为代理会长,廖仲恺为秘书[4]448。这一事实说明两点:其一,“革命委员会”确经正式成立,不然不可能有所谓代理会长之说;其二,胡汉民代理会长后,“革命委员会”实际上失去了它的本来意义。因为当初孙中山之所以提出成立“革命委员会”,就是认为胡汉民长于调和,不长于彻底解决,而希望撇开胡汉民,成立一个能够“快刀斩乱麻”的行动机构,以解决商团叛乱的问题[1]243。孙中山任命胡汉民担任代理会长,说明他实际上放弃了通过“革命委员会”来领导镇压商团叛乱的想法,“革命委员会”名存实亡,在镇压商团叛乱中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3.国民党全代会与国民党中执会是不是两个并列的“最高机关”?
《轮替》第一部分第一段称:“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以俄共党章为蓝本,制定新的党章。新党章规定,党的‘最高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全代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简称‘中执会’)。以后国民党党章虽历有修改,此一规定基本未变。这意味着国民党中央在法理上有两个并列的‘最高机关’”。该文最后一部分还提到,在国民党的法理上,全代会、中执会、中常会与中政会,在某种意义上都具有最高权力机关的性质。作者以此来说明,国民党最高权力处于分割状态,各权力机构关系紊乱,运转失序。
笔者认为,国民党中政会成立后,国民党最高权力时而统一,时而被分割,各权力机构关系紊乱,这是事实。但如果说国民党全代会与中执会是两个在法理上并列的最高机关,则是错误的。国民党全代会与中执会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所谓并列,应该是这两个机构同时存在,同时发挥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否则也就谈不上最高权力被分割的情况。但是,关于国民党全代会与中执会的关系,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党章说得非常清楚:“本党最高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但闭会期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5]92~94也就是说,国民党全代会和中执会并不同时扮演最高权力机关的角色,从法理上说,全代会召开期间,只有全代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没有第二个最高权力机关;全代会闭会期间,国民党中执会被授权行使最高权力机关的职权,全代会则不发生作用。国民党全代会和中执会既然不同时发挥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就没有理由说它们是并列的两个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党中执会与中常会的关系,也是同理,它们也不是并列的最高权力机关,而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
国民党中央权力机构关系紊乱,主要是由于中政会的建立而造成的。中政会建立后,逐渐演变成国民党的党政最高机关,行使本不属于它的最高权力,使其实际地位与法理地位发生冲突,从而造成了国民党中央权力机构关系紊乱。
[收稿日期]2009-06-20
标签:孙中山论文; 胡汉民论文;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论文; 革命委员会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央机构论文; 国民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