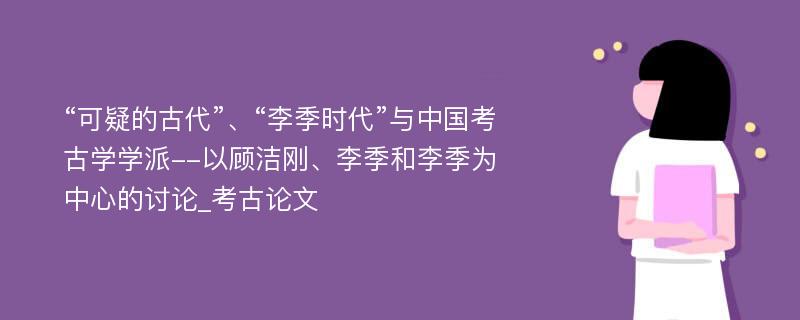
“疑古时代”“李济时代”与中国考古学的学派问题——以顾颉刚、李济和苏秉琦为中心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论文,考古学论文,学派论文,中国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査晓英在近期论文中援引张光直的话说到两点:“就中国考古学说来,我们仍旧生活在李济的时代。”“1950年以前,中国考古学最主要的特征是民族主义。”①而另外有学者则称,在尚未出现能够超越或取代“苏秉琦学术思想”的新学说之前,中国考古学正处在“苏秉琦时代”②。笔者拟以李济等前辈的事功为中心,有选择地梳理中国现代考古学史,引出对于学派和时代的讨论。 一、疑古思潮和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兴起 顾颉刚(1893-1980)曾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掀起了新一轮的“疑古思潮”,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影响③。不过,这一派对古史的“破坏”作用要远远甚于“建设”作用。“破”后如何“立”,成了个问题。“古史辨”推翻了旧的古史体系后,新的可信的古史只有建立在考古发掘所得新材料的基础之上,这几乎是当时许多学者的共识。顾先生也深有自知之明,他几次提到,凡事不可能一人包揽,当和他人分工合作。“所谓华夏民族究竟从哪里来,它和许多邻境的小民族有无统属的关系,此问题须待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的努力”(《古史辨·第四册序》)。他称自己“希望替考古学家做扫除的工作,使得他们的新系统不致受旧系统的纠缠”(《古史辨·第二册自序》)。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资深著名考古学家夏鼐(1910-1985)在《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一文中对古史辨派的评价则是: 他们批判封建主义的旧史学是对的。但是他们所想建立的仍是资产阶级的新史学。他们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又没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立说的基础。他们所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无法建立一个站得住的中国上古史新体系。不过,他们对于封建主义的旧史学的摧陷廓清的功绩仍是不可抹杀的。他们扫除了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的道路上一切障碍物,同时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④。 曾悉心研究20世纪疑古思潮的沈颂金博士(1964-2003)认为:“可以说,以古史重建为宗旨的考古学得以在中国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古史辨派。古史辨重在破,考古学偏于立,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因果关系。”⑤ 不过也有人研究此段学术史、分析过“古史辨”派的困境。例如,山东大学的李扬眉博士认为,顾颉刚的古史研究自始至终都具有鲜明的“思想史”特质。他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探究上古史料的生产、组织、构造和流变等等,最终目的是要从“中古期的上古史说”中勘探出“真正的古文籍”,从而尽可能地达到对上古史的客观认知;只是他所援用的方法事实上仅能在“史料”范畴内发挥效用,根本无力将他引领到“史事重建”的层面。而顾颉刚以史料为本位的致知取径恰恰主要来源于他所反叛的经学传统,因此他的古史研究未能真正脱出传统学术的范式⑥。 其实,当时不论是“信古”派还是“疑古”派,都采用一种循环论证的方法,以传世文献评判传世文献,而李济等人所倡导和践行的是,利用新出土的考古资料来重新评判传统文献,以文献研究与考古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重新评估整个中国古代文明⑦。安阳殷墟的发掘和事后的大量研究成果,切切实实地“把早期中国文明的历史推早了六七百年至一千年”⑧。 20世纪70-90年代,包括银雀山汉墓竹简等带文字的考古新发现剧增,人们对于传世古籍产生了新看法。李学勤等学者指出,需要重新认识学术史,认识到“古史辨”的副作用,即,它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李学勤还提出“走出疑古时代”⑨、进行“释古”⑩。总的说来,90年代的中国考古学家们,在处理传世文献方面更为成熟,也比较充分地认识到了考古学的局限性。对于李学勤等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的观点以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些阶段性成果,张忠培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11)(12)(13)。 二、安阳殷墟和“李济时代”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1896-1950)起了重要作用。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旨趣》里的宣言语出惊人:“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之后,所里成立的考古组首选安阳殷墟作为田野工作地。安阳自此成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14)。截至1937年的十五次发掘中,李济(1896-1979)是最重要的领导人。晚年他曾以英文发表了他最后一部专著《安阳》,书中回顾了安阳发掘前前后后难忘的历史(15)。 纪念殷墟发掘六十周年前后,世风与1950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语。长期在安阳工作站从事考古的郑振香为《殷墟的发现与研究》所写的“前言”里提到: 殷墟的发现将我国的信史提前到3000多年以前,提高了我国先秦文献的史料价值。也是对当时疑古之风的有力反驳……我们研究殷墟文化的后学者们绝不会忘记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老一辈考古学家……他们不仅为殷墟考古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通过殷墟发掘……使中国考古学这一新兴学科取得了应有的地位(16)。(下划线为引者所加) 在李济的著作中,与安阳殷墟有关的论著占很大比重。这位被弟子张光直(1931-2001)称为“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17)始终关心中国上古史的研究(18)。不过,李济的殷墟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重建中国上古史也不是李济终生的唯一追求。以张光直在选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时的思考,他把老师的主要贡献归结为四方面,一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个人类学途径;二是现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初期发展方向;三是殷墟发掘与中国古史;四是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19)。 张光直对于李济考古学的成就做了归纳总结的同时,也指出了他受时代局限所留下的不足:“……得到材料以后,应该如何去整理材料,我们却在他的著作中找不到有系统性的理论性的指导。李先生在资料里抓到了许多关键性的问题,但他并没有很明白地指点出来这许多问题之间的有系统、有机的联系。很可惜的是,李济先生没有给我们留下一本考古理论、方法论的教科书。”(20) 李济暮年曾有一个编写《中国上古史》的巨大计划,1972年出版了由他主编的《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一本》,他本人执笔撰写了其中的第一章“史前部分”(21),其思路的高屋建瓴在此及一些文章里有所体现,在深受他学术思想影响的学生张光直的有关文章里也有表露。简单地说,李济主张的是:不把对中国问题研究的视野局限于中国的范围。例如,李济晚年在台大讲课时曾经讲到,彩陶在中东与东欧自公元前1000年-前4000年有数千年的历史,彩陶文化可能经安诺一带传入中国……许多人说我主张中国之彩陶起源于豫北,我实从未曾作如是之主张。我只曾说,豫北是中国彩陶最为发达之地。我相信彩陶虽发达于中国,而其制造观念的来源,则极可能来自西方……中国之历史文化在考古学上可以确认的以商为最早。商文化立基础于彩陶黑陶文化。但其中之铜器、文字及车等,已发展到相当高的阶段,却为彩陶黑陶文化中所无。此三种文化之来源如何?我个人所知,在西方古文明,车、文字、铜器均早于中国一千年以上,但是否由而传入中国?若谓为传入中国者,则系统?(22) 张光直后来的见解基本沿袭乃师的,这可以从《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一文里读到,而这篇文章作者标明是呈献给李济作为纪念的(23)。文章中张光直明确提出在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里的整合研究方式。他的另一部大作《商文明》,同样题赠“献给李济教授”,在书的开篇就是“绪论:探索商代历史的五条途经”,显现了他研究方法之别于传统的鲜明特点(24)。在上述文集里的另外一篇论文《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中,张光直则明确表示,研究中国的考古问题,视野不能为现在的国界所拘束。凡此种种,与“中华寻根式”的思路及操作方法,均有差异。 至于“李济的时代”一说,源出自张光直1981年在《世界考古学》期刊(英文)上《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一文的论述。张光直称: 在我看来,李济个人的研究取向和成就在以下方面具有特别深远的影响:他一生坚持以使用第一手的科学取得的经验材料(而非过去写在书上的教条)为信仰和立论的依据;他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以可定量的有形的东西为基础;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出发,对考古资料所作的解释;他不把对中国问题研究的视野局限于中国的范围。我们不可能在此对李济漫长而又多产的考古生涯的每一侧面详细评述,然而,仅仅罗列这些方面就足以表明,就中国考古学说来,我们仍旧生活在李济的时代……总之,尽管新中国的考古学家有理论上的自觉,大致说来,在方法论方面,他们还是满足于沿用从李济及其同时代的中西方考古学家那里学到的方法,来处理考古资料(25)。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李济在1949年之后“离开了中国考古的主流”(26),“李济的时代”之说,除了批评“主流考古”存在的某些欠缺外,在进行总体特征概括方面总显得有些苍白。 三、夏鼐身后的苏秉琦时代 新中国几十年来考古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苏秉琦(1909-1997)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兼任考古教研室主任,几十年来培养了大批考古人才。他对建立考古学的“中国学派”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考古学研究的“中国学派”有什么特点,苏秉琦的两位高足,俞伟超(1933-2003)和张忠培表达了他们的理解: 我们理解,第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考古材料出发,运用考古学的方法,仔细观察与分析考古现象所呈现出的矛盾,具体地研究中国境内各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内容的社会面貌及其发展阶段性; 第二是在科学发展基础上,运用由我国学者所发展了的考古类型学方法,分区、分系、分类型地研究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通过考察我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研究中国这一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研究这一总过程中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 第三是这种研究,以揭示历史本来面貌作为目的,对促进人民群众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民族团结思想情感,有着重要的作用。由这样的指导思想、方法论和目的性三方面结合在一起的考古学研究,正是新中国所特有的;何况其研究对象,又是世界上一个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面积的、独特的、包含着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并各有其完整发展系列的考古学遗存。 多少人的血汗浇灌,终于培育出了“中国学派”这一新种。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大量考古实践,正是生长出“中国学派”的土壤;从实际出发的比较分析、综合概括,则是“中国学派”出现的催化剂(27)。 苏先生被公认为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人之一(28),他创立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说(“满天星斗说”)(29)和国家形成的“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和“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30)(31)(32)。李伯谦认为:“苏秉琦先生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为指导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典范。”是后来“满天星斗说”等的理论基础(33)。朱乃诚则对苏先生学术体系的形成做了梳理(34)。 俞伟超曾经忆述过一桩逸事。1981年,夏鼐看到了苏秉琦刚发表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1979)后,到考古所苏秉琦的办公室里,对苏先生还有安志敏先生以及俞伟超说:“你(面对秉琦师)的文章很有意思,和你(转而面向安志敏先生)的看法不一样,你是讲大一统的。可惜这篇文章没有附图,别人不容易看懂。”(35)对于苏秉琦这一理论创新,夏鼐无疑是有足够的学术敏感和深刻认识的(36)。 夏鼐是1950年来直到他逝世为止中国大陆考古学的领军人物。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中国考古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37)(38)。透过不久前出版的《夏鼐日记》,我们可以了解一段跌宕起伏的社会史、了解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尽管夏鼐成就卓著,但是,如今大陆考古学界没有提出“夏鼐时代”一说。毕竟,那是一个“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集体主义至上时代。21世纪初,唐际根在一篇与西方考古学家(《剑桥中国史·商代考古》作者贝格雷)商榷的论文里提及作为新中国考古领导人的夏鼐时有如下一席话: ……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只有极少数的考古学家尝试过运用考古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解释,绝大多数的中国考古学家都在埋头于发掘、整理田野资料。那时中国的考古工作主要由夏鼐先生主持和安排,夏鼐先生严格要求中国的考古学者只发表材料,而不允许随意性解释。翻开当时的《考古》或《考古学报》,发掘简报或报告占了绝大多数。许多简报或报告的作者在报告的结语中写上了自己对材料的解释,但发表时大都被删除。我相信夏鼐先生是有意识这样做的(39)。(下划线为引者所加) 夏鼐不同意苏秉琦关于“我国的考古工作及考古学发展已进入一个新时代”的判断,在1984年3月13日的《日记》里逐条反驳了苏秉琦的观点: [苏秉琦说]我国的考古工作及考古学发展已进入一个新时代,它的主要标志是:一、已有相当数量的一批比较系统而不是零星的,扎扎实实的而不是草率的田野考古工作、工地和原始资料(鼐按:这只是相对而言,“新时代”是质变而不是量变。从量变到质变,什么数量才算是“新时代”呢?)。二、已经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鼐按:曾问过这与所谓“中国学派的考古学”是否一回事?所谓“特色”是体系的特色,或仅只内容是中国材料,犹是中国特色的历史,即中国史。他说这是后者)。三、已有一批在建国后新培养成长起来的专家学者(鼐按:要有新人,是必要的,但有新人并不便是新时代,还要新人的学术思想及拿出的成果,是否足以代表)(40)。 研究《夏鼐日记》的近代史所学者宋广波撰文说道:夏鼐晚年,特别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在学术问题上,即使是老朋友提出的学术观点,他只要有不同意见,也会直面提出来。在上面这个例子中,宋广波觉得“夏鼐的观点更符合历史实际”(41)。 我们还注意到夏鼐在1979年写的一篇回顾新中国考古学历程的综述文章里表达的观点,即,如今中国的考古学与解放前的一个很大不同是,三代以下的考古也占有了突出的地位: 考古学在最近三十年中与狭义的历史学(利用文字记载以研究历史)的关系结合得更为密切了。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这时开始受到应有的重视,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是三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进展的另一个标志。解放以前的中国考古学主要是史前学,其次是属于原史时代的殷虚研究。当时受过训练的考古学家几乎都是从地质学或人类学方面过来的。便是受过考古专业训练的,他们所受的训练也几乎都是史前考古学方面的。另外一批学者,则是由古史研究、古文字学和古器物学方面过来的,是在书斋中培养出来的。所以除了殷虚以外,连殷周时代考古学也是被忽视,发掘工作做得很少,更说不到秦代以后的考古研究了。解放以后的三十年间,我们除了继续开展史前考古学之外,还做了大量的历史时期遗存的调查和发掘。这些工作提供了大量的考古资料,使我们有条件可以着手编写中国的历史考古学,而不再是“古不考三代以下”了(42)。 以此而论,至少在夏鼐看来,恐怕仅局限在新石器时期和文明起源阶段的研究内容并不足以涵盖整个中国考古学。看来,夏鼐之于苏秉琦未必就是行使学术霸权,不做学理解说。 张光直后来在他的大作《古代中国考古学》(43)的“中文版自序”里谈到,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开始使中国考古学摆脱中原中心的巢穴,使区域考古和由之而来的许多文化交流演进等问题,成为研究的对象”。诚所谓“旁观者清”,张光直在另外的地方指出,夏鼐掌握着话语权,所以他在世时(1985年前)苏秉琦的说法是不容易听到的(44)。的确,苏秉琦大量理论性、思想性强的讲话和文章几乎都是在1985年之后到1997年他逝世之前发布的。 不过,我们也需注意到顾颉刚辨析古书、推翻非信史方面蕴含的思想前瞻性(45)。他那“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46),在20世纪晚期考古发现剧增的现实中得到了验证,或许可以被看作为苏秉琦提出的“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文明起源多元说”的思想先驱。 与李济相似,苏秉琦也有重建中国史前史(上古史)的雄心,在这方面发表过多篇论文,还主编过《中国通史·远古时代》。但两人有明显的不同取向。同样的宏阔,我们觉得苏先生比较偏重传统史学,富有民族寻根色彩,也有较重的哲学气息;而李先生则多跨学科的特征,并不时地把中国当作世界一部分来思考,也就是查晓英所说的矫正民族主义的“正当的历史观”。 四、考古学界对于中国现代考古学学科史的一种分析 陈洪波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学术流派及其嬗变》里称,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主要存在科学考古、传统考古和马克思主义考古三个流派。建国后的中国考古学,先后以“史语所传统”和“中国学派”为主流,它们的兴替深刻地反映出时代的变迁和学术自身的演变。当代中国考古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新特点,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向“史语所传统”回归的倾向(47)。 我们认为,这样的分析尽管粗糙(48),但还不失为一个可喜的开端。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而言,“学派”问题是值得开展讨论的,而且应该放宽视野,进行“跨文化比较”式的思考。中国的考古学如此,人类学和民族学也是如此(49)。 五、讨论:学术流派和一国的学术传统 在民族学/人类学中,同样不乏关于“学派”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尽管“中国功能学派”(也被称之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燕京派”“中国早期社会学的社区学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享誉海外,但不少研究者都认为它只是中国人类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派别。许多研究者指出,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形成了研究取向有别的两大类型,被称之为“南派”与“北派”(50)(51)(52)。其中,“北派”注重理论,提出一些比较系统的见解,更强调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南派”则着重历史研究,力图以人类学的理论方法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并给国内各民族以系统的分类(53)。另外,李绍明先生在近年经潜心研究后又提出中国人类学中尚存在一个“华西学派”(54)。 有学者曾于2008年尝试提出存在以费孝通等人为代表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功能学派”或“民族学的中国学派”的看法,引起了圈内同仁的关注(55)。但该派的具体特征有哪些,除了乔健关于费先生“历史功能论”的总结之外,尚缺乏系统论述。我们也就难以由此体味“学派”概念本身的规定性以及“学派建构”的必要条件。 在此问题上,西方学者的观点和做法或许值得借鉴。 研究社会学史的Szacki曾在梳理社会学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区分出四种意义上的“学派”:一是学术机构或制度意义上的“学派”,通常指称享有共同的兴趣、假设、主题等并在一个制度或机构框架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群学者,强调学术机构对于拥有共同观点的社会学家的团结作用;二是心理认同意义上的“学派”,类似于“参照群体”的概念,强调的是学者们相信他们构成一个“学派”的心理联系,制度意义上的“学派”同时也是心理认同意义上的“学派”,反之则不一定;三是类型学意义上的“学派”,其划分仅仅依赖于研究者在理论、观点、方法等方面的相似性,可以包含从未一起工作过、从未相互援引过、甚至不曾知道彼此的存在的学者;四是“国家学派”,即一国的学术传统,主要涉及到特定国家的文化传统、社会历史环境及其对学者们的研究兴趣、理论观点、研究方法等的影响,通常与该国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流派有所关联(56)。对于第四种意义上的“学派”,Szacki只是简单提及,但他明确提醒我们:此种语境下的“学派”概念只能从比喻性的意义上来理解(57)。 尽管Szacki并未给出一个关于学派本质及其构成要素的严格界定,但他的研究依然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框架。比如,Kempny在研究曼彻斯特人类学学派时,就分别从学术机构或制度、心理认同、类型学三个方面检视了该派之所以成其为一个学派的具体表现,并将该派的总体特征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扎根非洲;二是以罗得斯-利文斯顿研究所和曼彻斯特大学社会人类学系为制度场所;三是牛津学缘;四是田野民族志导向的研讨会;五是独特的方法,即拓展个案法;六是多元理论取向(58)。 若以“国家学派”而论,巴特等人关于英、法、德、美四国人类学传统的梳理和概括(59)对我们也有参考价值。他们无一例外地关注了国家情境对于该国人类学发展路径的重要作用,但绝不在独特的国家情境和独特的人类学国别传统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而是重点强调在国家情境影响下所形成的具有延续性和持久影响力的学科制度、学术谱系、理论范式、方法路径等,并认为后者才是人类学国家传统的本质特征。对于个人魅力型学术领袖的讨论也遵循同样的逻辑。 总之,相较于西方的研究,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学派总体特征概括方面所做的工作尚待加强,对“学派”概念的多重含义尤其是负面意涵(60)的明确讨论似嫌不足。曾经的“中国学派”也好,“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也罢,都是和当时特定的国家情境和智识背景相联系的;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断裂和重新发展之后,如今是否存在一个“中国学派”,如果存在的话,其总体特征是什么,与20世纪前半期的学术传统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何在,这些都是值得仔细研究和深入讨论的问题。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在发展路径及其特征、趋势等方面都必然会受到我国独特文化传统和历史情境的影响,因此,人类学/民族学的“中国传统”这个方向应该是可以讨论并朝之努力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借鉴巴特等人的做法,处理好“国家传统”与国家情境、有影响力的学术流派、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学术大家之间的关系。 注释: ①查晓英:《“正当的历史观”:论李济的考古学研究与民族主义》,载《考古》2012年第6期。 ②赵宾福:《苏秉琦与中国考古学派》,载《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1期。 ③依朱佳木的归纳,顾颉刚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创建古史辨学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开辟了中国古史研究的新局面;是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开拓者;是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造就了“禹贡学派”,为我国历史地理学培养了整整一代人才。参见朱佳木:《顾颉刚先生治学生涯的启示——在纪念顾颉刚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本文无意对顾先生做全面评价。 ④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载《考古》1979年第3期。 ⑤沈颂金:《试论“古史辨”与考古学的关系》,载《齐鲁学刊》2003年第5期。 ⑥李扬眉:《颠覆后如何重建:作为思想史家的顾颉刚及其困境》,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9期。 ⑦李济曾对“古史研究的新运动”有所批评。他在《〈城子崖发掘报告〉序》(1934)中写道:“我们固不惜打破以中国上古为黄金时代的这种梦,但在事实能完全证明之前,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也只能算一种推到伪史的痛快的标语;要奉为分析古史的标准,却要极审慎地采用,不然,就有被引入歧途的危险……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谎账。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材料,一步一步地分析它们构成的分子,然后再分别去取,积久了,我们自然会有一部较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可写。”参见李济:《李济文集》(第2卷)第20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⑧李济:《李济文集》(第5卷)第18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⑨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第1-19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⑩张京华认为,李学勤本人对于“疑古时代”的阐述并不系统充分。“疑古”若作为对于材料的考订而言,乃是先于“释古”的第一步工作,两者是平行发展的关系;而“疑古”若指一种思潮,则是应该加以肯定,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的。参见张京华:《“信古、疑古、释古”论评》,载《学术界》2007年第3期。 (11)(12)(13)张忠培:《浅谈考古学的局限性》,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2期;陈宁:《“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载《社会科学报》2003年11月27日;杨春梅:《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载《文史哲》2006年第2期。 (14)中国考古学的另一只摇篮是北京周口店。我们注意到曾经师从贾兰坡先生的陈淳对此的不同见解。他认为:“由于殷墟发掘与典籍的吻合,使得中国考古学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没有再在完善和改进自身理论方法上下功夫……却在史学的学科定位上裹足不前,将印证史籍看作是具有最大成就感的工作。所以,虽然殷墟研究是标志中国考古学起步的一项值得称道的重要成就,但是,以解决问题和揭示因果为精髓的科学探索而言,它却成为一个十分不幸的开端”。参见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第60-61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 (15)李济:《安阳》,[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19、22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17)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第16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张光直特意声明,这个“派”乃是“研究方式”或“研究方法体系”的简称。 (18)(21)黄海烈、蒋刚:《考古学与中国上古史重建》,载《古代文明》2009年第3期。 (19)(20)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载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第417-44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22)陈星灿:《张光直课堂笔记所见李济晚年在台大教书的片段》,载《中国文物报》2005年3月11日。 (23)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第4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24)这五条途径是:“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卜骨和卜甲”“考古学”“理论模式”。张光直充分注意到了理论在研究中的重要性,所以在注重历代积聚的丰富资料的同时强调运用中介理论模式,以期获得有益于从支离破碎的材料中恢复整个社会系统的规则。参见张光直:《商文明》第55-56页,张良仁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5)(26)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陈星灿译,载《考古与文物》(西安)1995年第3期。 (27)俞伟超、张忠培:《编后记》,载《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第316-31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28)陈畅在《三位中国考古学家类型学研究之比较》中提到的三位学者即李济、苏秉琦和邹衡。参见陈畅:《三位中国考古学家类型学研究之比较》,载《四川文物》2005年第6期。 (29)陈星灿在论及中国文明起源范式演变的文章中提到一个有趣现象:外国学者往往能很早跳出中原中心论的模子,明确提出多元论,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他们没有或少受中国传统史观的影响。参见陈星灿:《考古学对于认识中国早期历史的贡献——中外考古学家的互动及中国文明起源范式的演变》,载《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 (30)(31)(32)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第225-234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苏秉琦:《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载《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第132-134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30-16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33)李伯谦:《中国考古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重读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札记(提纲)》,载《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 (34)朱乃诚:《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和尚待研究证实的两个问题——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载《东南文化》2008年第1期。陈淳对苏秉琦的理论持一定的批评态度。他说:“我国目前的大部分考古研究和报告都采用描述的形式,其中类型学的分类和分期无非解决‘什么’和‘何时’的问题,而考古学文化的确立和区系类型的总结也是解决‘谁’和‘何处’的问题……如果考古研究要突破罗列性的描述,就必须提出探索性的问题,对考古现象问‘为什么’”。“从思维方式而言,苏秉琦的区系文化类型有点像美国考古学20世纪上半叶流行的‘文化区’或‘文化圈’的模式,将文化区和民族区相对应。但是苏秉琦的6大文化类型区系尚不足以解决汉族与其他民族文化历史演变的问题。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苏秉琦的理论无疑是一种创造和突破。然而,由于受传统思维的影响,这种理论也有明显的时代和学术上的局限性”。参见陈淳:《考古学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加拿大考古学家特里格(1937-2006)在其名著《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中提及苏秉琦模式时有这样的一番话:“自1980年代初起,苏秉琦提出了一种与马克思主义‘社会进化法则’相一致的模式,视特定文化在中国不同地区肩并肩发展起来。这一模式要比老式的北方核心-周边模式更好地解释了区域文化差异的大量证据……在中国,民族团结仍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苏秉琦的系统陈述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历史学阐释倾向之间以及当代中国中央与各省利益之间构建了一个平衡”。参见[加]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205-206页,陈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5)俞伟超:《本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里程碑》,载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36)在《夏鼐日记》里记录了考古所的王仲殊和安志敏都认为“中国学派”一称的提法很不恰当。参见夏鼐:《夏鼐日记》(十卷本)第325-32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7)(38)[日]樋口隆康:《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载《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王仲殊、王世民:《夏鼐先生的治学之路》,载《考古》2000年第3期。 (39)唐际根:《考古与文化遗产论集》第10-11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40)夏鼐:《夏鼐日记》(第9卷)第33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1)宋广波:《从〈日记〉看夏鼐的学术人生》,载《中国文化》2011年第2期。 (42)夏鼐:《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载《考古》1979年第5期。 (43)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3页,印群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4)张光直:《二十世纪后半的中国考古学》,载《古今论衡》(台北)1998年第1期。 (45)顾颉刚在《答刘胡两先生书》里提及“在推翻非信史方面,我以为应具下列诸项标准……”此即其中两项。参见顾颉刚:《顾颉刚集》第9-1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46)顾颉刚:《顾颉刚集》第1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47)陈洪波:《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学术流派及其嬗变》,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48)言其粗糙,至少该文未能充分注意到史语所的传统带有被某些研究者诟病的“证史倾向”。参见陈淳:《安阳小屯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纪念殷墟发掘八十周年》,载《文史哲》2008年第3期。 (49)胡鸿保、张丽梅:《一个新传统的形成:民族工作的拉动与苏维埃学派的影响》,载《中国民族学》(第5辑)第58-68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 (50)(51)(52)龙平平:《中国民族学早期情况概述》,载《思想战线》1986年第5期;李亦园:《民族志与社会人类学》,载周星、王铭铭:《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下)第833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第3版)第433-440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53)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第3版)第433-440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54)李绍明:《略论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载《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55)杨圣敏:《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民族学卷)第42、340-34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6)比如,英国人类学的国家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功能学派所塑造的。参见张丽梅、胡鸿保:《功能学派与英国人类学的国家传统》,载《思想战线》2012年第4期。 (57)Szacki,Jerzy.“‘Schools’in sociology”.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1975(14). (58)张丽梅、胡鸿保:《曼彻斯特学派述要》,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59)[英]巴特等:《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60)Szacki指出,“学派”概念经常伴随着一些负面评价,因为“学派”的存在意味着这门学科还处于库恩所说的“前科学阶段”,尤其是心理认同意义上的“学派”,很容易为了护卫创立者的学说而无视合理的反对之声。参见Szacki,Jerzy.“‘Schools’in sociology”.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1975(14).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倾向于将社会人类学视为自然科学一个分支的拉德克利夫- 布朗就对“功能学派”的说法避之唯恐不及;特立独行、以“绅士”自居的利奇也不大愿意被归为某个“学派”,尽管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功能主义者”。参见Leach,E.R.“Glimpses of the Unmentionable in the History of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84; Leach,E.R.“Writing Anthropology”.American Ethnologist,1989(1).标签:考古论文; 顾颉刚论文; 张光直论文; 中国考古学论文; 李济论文; 上古时代论文; 文物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人类学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古中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