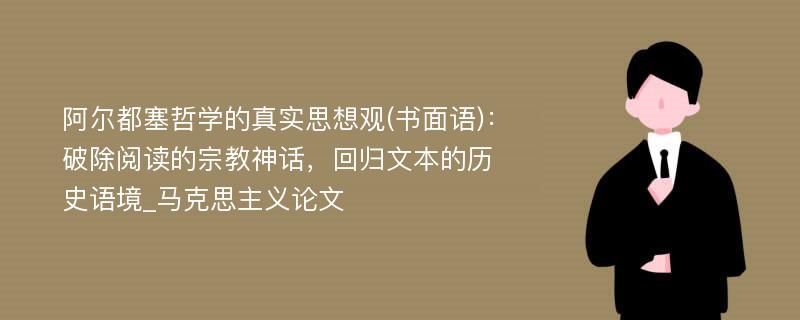
阿尔都塞哲学的真实思想意境(笔谈)——破除阅读的宗教神话,回归文本的历史语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语境论文,阿尔论文,意境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2)4-0007-18
一提到阿尔都塞,国内多有学者将其定位为西方“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这个评价并不准确。其实,阿尔都塞的意义与贡献在于,他竭力将作为意识形态(或 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科学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他毕生致力于将马克 思主义从强大的意识形态襁褓中解放出来,用严格的科学的方法即学术规范的形式,来 保卫马克思主义之本来的科学思想面目。用时下的行话说,阿尔都塞的确是要“思想淡 出,学术深入”!
应当说,阿尔都塞的功劳并不在于提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写作方式,或者发 现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或者批判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在于他为我 们历史地科学地深层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与历史形成过程,提供了一种 重要的研究方法——回归马克思哲学的原初思想语境与客观历史语境。
阿尔都塞认为,“回到马克思”,并不等于(也根本不可能!)要直接同马克思进行对话 。因为作品的诞生从来是以作者“主体之死”为代价的(罗兰·巴特语)!我们所能遭遇 的和对话的永远是历史性的文本而非作者本人。“种种事实表明,思想的主人在交流与 辩论中却似乎并不出场。不仅通过其思想与著作表现自己的具体个人不出现,而且在现 有意识形态环境中表现自己的真实历史也不出现。思想家被他的著作所掩盖,人们通过 著作只能看到思想家的严谨思想;具体的历史也被当时的意识形态论题所掩盖,人们所 能看到的只是意识形态的体系。”(注:参看[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4页、第45,55页。)
阅读马克思文本的最大的意识形态神话或障碍是,将马克思表面上的结论与语录句句 当作自明的“真理”,把马克思的思想当成是“现成的”、“有典可稽”的结论。这实 际上承认了观念的独立性与永恒性,实际上将马克思哲学思想当作与时间地点条件无关 的、“永恒在场”的“绝对真理”;将马克思本人理想化为“永垂不朽”的思想主体。 主张“永恒真理”,把“必死的”此在主体的“理想性”形象同一个理想化的、全知全 能的绝对主体混为一谈,“这些都是哲学问题内的长久以来仍未彻底肃清的基督教神学 残余。”(注:参看[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64页、 第158,171,176页。)把马克思哲学文本当成“现成在手”的教义,这等于暗中假设有 一个“本来的”马克思思想面目——我们可以发现或者可以揭开这个“本来的”面目。 这种“直接”阅读是一种宗教式信念支配下的、无反思无批判的直接“观看”,即把书 面的语言变成直接的、明显的真理,把现实当作有声的语言,把世界变成无字“圣经” 。世界是上帝的化身,通过语言,上帝或者真理便呈现在我们面前。客观实际(真理)、 上帝(主体)与语言(文本)三位一体,是同一个东西!
事实上,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实际性不是一个现成东西的僵硬事实那样的事实性 ”,“实际之为实际的‘它存在着’从不摆在那里,由静观来发现”。“‘看’不仅不 意味着用肉眼来感知,而且也不意味着在一个现成东西的现成状态中纯粹非感性地知觉 这个现成的东西。”“解释奠基于一种先行掌握之中。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 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 行给予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准确的经典注疏……喜欢援引‘有典可稽’的东西 ,然而最先的‘有典可稽’的东西,原不过是解释者的不言自明的、无可争议的先入之 见。”(注:参看[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64页、第 158,171,176页。)也就是说,当面对马克思的文本时,如果我们直接地、不假思索地 将其中某个观点当作是“真正的”“马克思的”观点时,这其实是将我们自己的“先入 之见”强加给马克思(国内不少学者就是用教科书的“先见”来“反注”马克思的文本) !这种不反躬自问自己的思想前提与知识结构、直接阅读马克思文本的方法,显然是“ 非法的”、“有罪的”!而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一开头则从另一角度坦率地承认 ,任何哲学方式的阅读都是一种“有罪的”阅读,因为我们都是带着自己的偏见,都是 在一定视野下阅读文本。我们不是上帝,也没有上帝能够保证我们避免误读。任何阅读 都是“误读”。
任何文本的阅读或者“看”,都不是发现或者复原那个所谓真理“本来面目”的过程 ,而是新的文本的生产过程。任何作品都不是现成可读的。它们的意义都是在一定语境 下产生的、因而也只能在一定语境下才能呈现出来的。任何阅读都是作品本身与读者在 特定语境中的一种动态融合。任何阅读或者“看”,都不是主体用眼睛看到某个“现成 ”东西,而是读者在自己已经具有的、“无意识的”思维框架(或问题式)支配下对文本 结构的一种重新构造——新的语义的再生产过程。“读”与“看”某物,不是我们去看 与读某个对象,而是某个对象在先行于我们自身的“无意识结构”中的“自我呈现”。 我们“读”、“看”某个文本不是“看”它的表面的、自觉的观点与意识,而是对产生 这些观点的无意识的思想前提的反思。于是,“看”与“读”就变成了我们用自己的知 识结构去“提问”与“透视”某个文本得以产生的“知识结构”与思想前提的过程。“ 看”就是“看”的结构条件的行为,就是问题式领域所内在的对它的对象和问题的反思 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看”就失去了它的神圣阅读的宗教特权。“看”就不过是把对 象和问题同它们的存在条件连结起来的内在必然性的反思,而对象和问题的存在条件又 同它们的产生条件联系在一起。“看”不再是主体的眼睛或者精神的眼睛去“看”理论 问题式所决定的领域中存在的东西,而是这个领域本身在它决定的对象或者问题中自己 看自己,因为“看”不过是领域对它的对象的必然反思。(注:参看[法]路易·阿尔都 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第17—1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照此来看,阿尔都塞所倡导的“回到马克思”,并不是要回到马克思当年所自觉表达 的某某基本观点与结论那里去。这些是人所共知的观点,谁都可以随意甚至“非法”地 引用引伸的观点。“回到马克思”,不是回到马克思某一个最初的基本观点,然后再加 以“过度诠释”而创立一种新的体系学派,或者从“微言”中引出所谓“大义”来。我 们面临的任务是回到马克思当年写作与思考的初始的语境与原初的思想视野。我们所关 心的,并不是马克思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主体的自觉一致的自我意识与公开的思想立场 ,不是关注作为“能指”的书写文本,即自觉意识层面的东西;而是自觉意识所遮蔽的 “所指”,即马克思形成与表达思想的无意识前提—结构;不是在前台展示的公开发表 的文字,而是保存在思想实验室中的文字。在这种阅读视野中,我们不把马克思看作是 一个具有前后一贯自觉意识的作者—主体来研究,不把马克思哲学思想史看成是马克思 自觉表达出来的连续不断的观点发展史,而看成是自觉意识即公开发表的学术语言背后 所掩盖的各种相互冲突的著作话语结构的转换生成谱系。用福柯的话说:“问题是要在 没有一种目的论能预先限制的不连续性中分析思想史”(《知识考古学》语)。它关心的 不是统一、连贯、自觉的思想观点发展完善过程,不是一个注定要成为马克思主义创始 人的马克思那样的、带有目的论色彩的个人完整叙事逻辑,而是处于无意识、自发乃至 于近乎“精神分裂”状态的“无主体”的、文本重叠、话语冲突的“地质层次”。再说 一遍,这里并没有一个前后观点一贯的、自觉连续的思想主体的马克思;这里并没有一 个统一的连贯的、作为自我意识与观念主体的抽象的“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 本质体现和肉体化身的“马克思”;而只有处于具体语境下的、读着各种不同著作与各 种话语系统打交道的、具有着具体的阅读心理与生活感受的、处于各种阅读无意识结构 支配下的“偶然存在的”马克思,或者说只有一个肉体化的“定在的”或者“偶在的” 马克思!“马克思的命运是由一些具体思想家之间的辩论所决定的”。“马克思开端的 偶然性在于,他诞生时被包裹在一块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而他成功地从这块沉 重的襁褓中解脱了出来。”(注:参看[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 书馆,1984年版,第44页、第45,55页。)总之,马克思哲学并不是一个“冷藏”无数 真理的“体系”,而是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马克思的“当代性”特征就在于,他 经常是同时在用有本质差异性的多种文本交错写作,让这些文本之间发生尖锐的冲突, 然后揭开一个又一个神秘的意识形态胡说的迷雾,让我们真切发现客观存在的彻底的唯 物主义与彻底的辩证法的现实。
进一步来看,分析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单位,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时代、著作、概念、主 题,而是“话语”,即实践中的思想的无意识结构与实践的语言体系,是支配着马克思 自觉思想观念背后的那种无意识的深层次的语言结构,是各种权力—话语结构。阿尔都 塞称之为总问题或者问题式(problematic)。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意义在于,他在批判自 己思想先驱的理论框架或者问题式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问题式;马克思是在颠覆德国 古典哲学的人本主义问题式或者理论总框架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 架。
理解某个文本不是要相信它的每一句话,而是要理解它所提出的与回答的问题。我们 理解一个文本时总是带着自己的问题来阅读,总是把文本当作是对自己的问题的一种回 答;我们阅读与理解某个文本时,总是想拆构瓦解掉对方的理论框架——用自己的语言 “胃口”,把对方的思想观点素材“消化”到自己的问题式中。“因此,精神科学的逻 辑是一种关于问题的逻辑。”“谁想寻求理解,谁就必须反过来追问所说的话的背后的 东西。他必须从一个问题出发把所说的话理解为一种回答,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所以 ,如果我们返回到所说的话背后,我们就必然取得问题视域才能理解文本的意义。”“理解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个问题提出问题。理解一个意见,就是把它理解为对某个问题的回答。”“谁想理解,谁就可能如此强烈地对于所意指东西的真理犹豫不决。他可能如此强烈地偏离事情的直接意见转而考虑深层的意义,但并不把这种深层的意义认为真实的,而只是把它当作有意义的,以致于真理可能性仍然处于悬而未决状态——进入这样一种悬而不决之中,就是提问的特有的和原始的本质。提问总是显示出处于悬而不决之中的可能性”(注:参看[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475页、482、481页等处,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正因为如此,任何文本(包括马克思的)都是在这种“悬而不决”的动态的问—答过程中,在动态的语境融合下,无限地、开放地呈现与生产着自身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