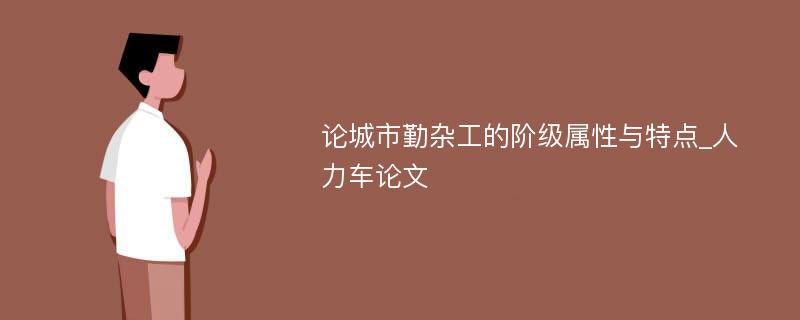
论都市苦力工人的阶级属性与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苦力论文,阶级论文,属性论文,工人论文,都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2375(2008)05-0100-05
都市苦力工人与产业工人一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过去人们只把关注的视角投向产业工人,甚至把产业工人与工人阶级等同起来,而把都市苦力工人置于“被遗忘的角落”,并忽视了对都市苦力工人的研究,有关研究文章更是凤毛麟角。这种状况显然与近代社会庞大的都市苦力工人队伍及其所起的作用是极不相称的,也是极不公平的。本文试图从阶级属性、结构分布及特点方面对都市苦力工人进行探讨,以期使人们从整体上认识、了解都市苦力工人,同时也希望借此唤起人们对这部分生活在社会底层工人的重视。
一、都市苦力工人的阶级属性
近代中国都市苦力工人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随着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发展而不断发展起来的。
但是,都市苦力工人的提法则出现较晚。从现有资料来看,都市苦力工人的提法始见于毛泽东在1926年3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粪夫清道夫等亦属于这一类”。[1](p8)在1928年出版的《中国劳动年鉴(第一次)》中,王清彬进一步明确了都市苦力工人的属性和范围,“我国工人,大多数恃筋肉劳动为主,除少数有技能者外,概可称为苦力”,惟社会上一般所称苦力, “系指无规定工作之负力工人而言”。[2](p625)都市苦力工人主要指码头搬运夫(工人)、人力车夫(工人)、粪夫(掏粪工人)、清道夫(清洁工人)等在城市“恃筋肉劳动”而“无规定工作”的血汗工人。
那么,都市苦力工人具有什么阶级属性,它与产业工人是什么关系?
工人阶级是一个历史概念,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产物。工人阶级是不占有生产资料,完全或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并获取工资为生的劳动者的集团,也叫无产阶级。但是,关于工人阶级,人们最初一般把它与产业工人等同起来,称之为工业无产阶级。20世纪初,国际上对工人阶级较为通行的定义有两个:一个以生产技术的熟练程度为标准,把工人阶级只限于被机械化工业雇佣的工人;另一个是限于以企业的规模大小为标准,低于一定规模的企业工人不算。[3](P95)20世纪80年代依然有人把工人阶级范畴只限于产业工人,也就是说,只限于物质生产领域生产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者。
然而,这种把产业工人等同于工人阶级的观点,使工人阶级的概念狭隘化,像码头工人、人力车工人、粪夫、清道夫等尽管使用的生产工具比较简单,但他们同样是雇佣劳动者;同时,剩余价值的产生不等于剩余价值的实现,从事事务性劳动、商业劳动、服务性劳动的劳动者,也被迫更快、更多地为资本提取和转移剩余价值服务。从资本的生产观点来看,这种非生产性劳动的职能实际上也是生产性的;从劳动对社会有用性的角度来衡量,非物质领域的劳动也是维持劳动者生命、保护劳动力和发展家庭所必须的社会分工。
法国学者谢诺在《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中结合中国工人运动史的实际情况,认为以生产技术熟练程度及企业规模大小的标准对工人阶级的定义“都不标准,不能采用”,“如果把机械化程度很小的小矿的矿工和船舶码头的装卸工,或者上海广州等城市中的中小印刷厂和小铁厂的工人都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中国的工人运动史就不完整。因为早在1919年之前,矿工和码头工人就曾有过罢工,并且显示了相当的组织力量”。谢诺认为“根据经济标准对工人阶级的定义,远比上述两种说法更为恰当”,工人阶级应该“包括所有在大型和中型资本主义企业以及和资本主义生产有密切联系的交通运输业中劳动,本人没有生产工具,也不占有劳动产品,完全依附于雇佣主的工资收入者。不论他们是机械化程度很高的纱厂工人,或者是主要使用原始工具的矿工,或者是轮船上的水手、码头工人、铁路工人、或一般搬运工人,都属于谱写中国劳工运动史的工人。除此以外,工人阶级还包括各种市政公用事业,如电讯、自来水、公共交通等所雇用的工人。甚至人力车夫,虽然他是个体劳动性质,也应包括在内”。[4](P95-96)
因此,工人阶级中不仅包括产业工人,而且包括码头搬运工人、人力车工人、粪夫、清道夫等都市苦力工人。因为都市苦力工人“除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5](P8)都市苦力工人的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丧失了生产资料,或只有很少的生产工具,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其特征和马克思所描述产业工人的情形几乎完全一致:“他们除掉自己的劳动力,除掉劳动的手和头,再没有别的东西可卖了”。
二、都市苦力工人的结构与分布
据1924年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的血汗工人约有3200万之多”。[6](P52)近代都市苦力工人主要分布在交通运输、清洁卫生等行业。
在沿海沿江一些有轮船通航的城市,码头工人是都市苦力工人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他们主要依靠体力为船舶装卸货物。1920年“上海黄浦江两岸,从16铺抵杨树浦10多华里的地方,差不多尽是轮船码头”。这些码头上有很多为轮船“起货、背包、扛棒”的码头小工,“约略计算起来,这类小工在3万上下”。[7]汉口的码头工人“上自龙王庙、下迄洋火厂,有4000余人”。[8]此外,广州、重庆、大连、南京等沿海沿江港口城市,都有为数不少的码头工人。1929年,李达在其所著的《中国革命概观》一书中,依据英文《中国年鉴》的资料推算,全国城市码头工人约有30万人。加上其他搬运工人,1950年统计的全国 50个城市中,共有搬运工人568584人。
除码头工人外,近代中国城镇一般都有人力车工人。人力车是一种用人力挽拉、供人乘坐的单座车辆,大约在1874年从日本传入中国。拉人力车的人,通常被称作人力车夫、黄包车夫、人力车工人,简称车夫或车工。
人力车传入中国后,很快遍及各地。据1920年调查,上海租界和华界“专在市面上运送”客人为业的人力车,共约11800辆,人力车工人“总计共有35000人上下”。此外有包车车工约15000人。[9]两种车夫合计,共约5万人。北京的人力车“不下7、8万辆”。南京“开黄包车行90多家,拖黄包车的约有7500人”。据1928年出版的《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记载,20世纪初,北京有人力车工人约55000人,成都有7000-8000人,广州有7000-8000人。到20世纪30年代,人力车数量继续呈上升趋势。据20世纪30年代后期伍锐麟、白铨的统计,“全国28个城市共计车夫459359人,这绝不包括全国,因为28个城市之外,较小的或市或乡镇,也多有人力车夫的存在。如果完全计算在内,则当在50万以上。”[10](P379)
都市苦力运输工人除了搬运夫、人力车夫外,还有小车夫和挑夫、轿夫等,人数也很多。
近代中国都市苦力工人中,还有从事清洁卫生工作的清道夫和从事粪便收集工作的粪夫或清洁夫。例如,1920年上海南北市及租界共有运粪的清洁夫5000余人;公共租界工部局雇有清扫马路及园林工人600余人。武汉也有为数不少的粪夫,1909年武汉共有粪夫1125人;1949年汉口、武昌还有肥料工会,其中汉口肥料工会有会员1832人。1930年,北平约有4000多名粪夫。据实业部20世纪30年代初调查,京津两市计人力车夫20万人,粪夫、水夫、澡堂工人等苦役27000人。[11]
挑水工人也是近代几乎所有城市都有的一种苦力工人。清末的成都,“上千这样的劳动者每天从河里挑水,外加400多人从2500多口井水中取水,把饮用水送到人们家中”。从1881年英国商人建立上海自来水公司开始,到1908年,广州、汉口、武昌、南京、北京等城市相继开办了一些自来水厂。但是,自来水厂规模有限,供水不多,一般居民用水主要还是依靠工人挑水。没有开设自来水厂的城市更是依赖挑水。20世纪20年代末,重庆市区尚无自来水设施,以挑水为生的约有2万余人。
人数众多的都市苦力工人是近代都市人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日本外务省1907年编的《清国事情》第一辑记载,“武汉三市的工厂使用的职数不下3万人。特别是百货集中的汉口……苦力据说达九、十万。”1927年上海有苦力工人约12万人,1936年苦力工人总数上升到14万人,到1949年上海解放,各类苦力工人共16.7万余人。有些城市的苦力工人数量甚至还超过产业工人,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除了洋车夫和粪夫,见不到什么劳工社会”。[12](P189)
三、都市苦力工人的特点
通过对都市苦力工人劳动生活状况的仔细分析,不难发现,都市苦力工人具有如下特点:
1.劳动的简单性和生产工具的简陋性
劳动分为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复杂劳动是指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具有一定技术专长的劳动者才可以胜任的劳动。简单劳动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需要经过任何专门训练的、一般劳动者都可以胜任的劳动。产业工人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主要运用机器进行生产,有一定的技术要求,这说明产业工人的劳动属于复杂劳动;同时机械化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因而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中最有前途的部分。
都市苦力工人的劳动主要是肩扛、背驮、手拉,用力就可以完成,不需要专门训练,所以属于简单劳动之列。劳动的简单性决定了劳动工具的简陋性。人力车是人力车工人所使用的载客工具,相当简陋。车座夹在两根扶杆中间,人站在中间用力挽拉。码头工人除了一块破烂的搭肩布和杠棒、绳索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劳动工具。武汉粪夫工具“极为简陋,主要是以人力用粪瓢舀粪和用粪桶挑粪,粪板车极少”。清道夫的劳动工具也就是扫帚和筐子。
劳动工具的简陋反过来又使都市苦力工人在劳动中要付出较多的体力和汗水,有人称他们的劳动是“牲畜式的劳动”。码头工人要完成货物搬运,“只要求体力好,有力气,不要求别的”。[13](P109-110)人力车工人的劳动“殆完全用筋肉力,所需之智慧极低微”。
所以,从劳动工具方面来看,都市苦力工人代表了落后的生产力,是工人阶级中逐渐衰退的部分。
2.分布上的分散性及行动上的流动性
在分布上,产业工人表现出集中的特点,且大都集中在大中型企业中。1894年全国雇佣500名工人以上的工厂矿山共有39个,有工人6万左右,占当时全国工人总数的60%。产业工人的这种集中,随着近代中国企业的发展而愈益显著。这种集中使得产业工人组织起来比较容易。
但是,都市苦力工人就不及产业工人集中。汉口华界地区人力车数量,根据1918年汉口警察厅调查,“计贸易车与包车共为1056乘,车行43家”,如果按每辆车由2人拉计算,人力车工人人数大约为2200人左右,每个车行大约只有工人51人。上海码头工人“做工,不是像工厂一样的集中,他们是零碎分散在广大的地区工作”。[14](P645)他们分散在各条船上或各个仓库里。当时,“招商局及周家巷有200人,太古码头有210-220人,怡和码头有220-230人,日清宁绍两公司有600人,鸿安公司亦有140-150人”。[15]各码头、仓库的工人似乎不少,但是“相互之间很少联系”。
从中国工人阶级产生的历史中可以发现,无论是产业工人,还是都市苦力工人,都与农村有着密切联系。但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产业工人中已经形成了一部分“不再到农村去”的经常工人。30年代“经常工人”已经占了较大比例,如青岛内外棉纱厂工人,来厂以前属于纺织业和其他工业的占63.2%。这种稳定性使得产业工人参与改善劳动条件、劳动待遇斗争的积极性较高。
与产业工人不同,都市苦力工人总是与农村保持着密切联系。码头工人、人力车工人、粪夫、清道夫等苦力工人从农村来到城市;但是他们又常因各种原因与农村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大多是流动的临时工,这些人“是真正的农民—工人。1940年的一次调查显示,能在上海干满3年的人力车夫不足30%,而只有2%能干满5年”。[16](P312)抗战时期的上海码头工人“只是把在码头上出卖苦力做一个暂时混饭的地方,工作一些时候走了,又有新的来补充”。都市苦力工人的流动性,不仅表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流动,还表现在由于工作的竞争性强,因此也就存在工作地点变动和工作种类的变动。
都市苦力工人这种分散性及流动性不仅不利于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当然也不利于进行组织。
3.行为、生活习惯上的散漫性和“流氓式”
产业工人绝大多数从事专业程度较高的生产劳动,这种劳动需要彼此之间协作配合才能完成。这种工作性质有助于产业工人团结协作的集体意识及组织纪律性的养成。
文化程度低,就业压力大,工作不稳定,经常变换工作和工作地点,分散劳动,与农村的密切联系等特点,容易使都市苦力工人养成不良的生活习惯,甚至染上近乎流氓式的习气。《上海生活》1940年12月一篇报道就描写了人力车工人不良的生活习性:他们的智识既是那么浅陋,他们的头脑又是那么简单;而对于这五方杂处繁华的上海,竟将他们原有的纯朴天性汩没了,濡染成一种欺诈、贪狠、野蛮的习气。所以,上海居民,无论男女提起人力车夫莫不痛首疾心,对他们表示不出一丝好感……他们的弊病和恶劣的印象,一时也说不尽。[17](P91-98)
据《新青年》杂志的调查,都市苦力工人中,赌博、喝酒和嫖妓是最常见的娱乐。武汉的人力车工人在劳动之余经常到小茶馆“谈天、玩牌、吸烟、喝酒等等”,还“在茶馆打纸牌、打麻将,每桌4人,每人2角或5角不等,进行‘雀战’和牌按翻得钱,钱完算一局,再抹再出钱,”有时从天黑赌到天亮。对于矛盾的处理,都市苦力工人往往野蛮地一“打”了之,表现出近乎流氓的习性。
行为、生活习惯上的散漫性和“流氓式”大大损害了都市苦力工人的社会形象。例如,“上海居民,无论男女,提起人力车夫莫不疾首痛心,对他们表示不出一丝好感”。[18](P91)
4.社会地位低下
在都市社会中,人力车工人、粪夫、清道夫等苦力工人是职业人群中地位最为低下的社会群体。昆明人除非走投无路,否则决不愿干清道夫这种职业。人手不够时,警方只得“让违警拘役人员参与清扫”,清道夫无形中成为低人一等的贱民。天津的清道夫也“被视为贱役”。对于粪夫,“一般人全都认为他们的职业是鄙贱的,不但不表示一点同情,且加以轻视的态度”。[19](P96)上海的车夫和粪夫“是最最底层的行当,没有人看得起,没有人理睬”。“他们贫穷孤独,天天蜷缩在阴暗角落里,只有在酗酒和赌博中,才能找回他们的乐趣和自尊,就连茶馆也没有粪夫之份,都嫌他们是臭头”。[20](P73)武汉的码头工人被称作“码头夫”、“荒气”、“披麻袋的”、“臭苦力”。长沙的码头工人被店主商人看不起,“被买办、洋人喊叫做苦力,受打受骂,忍气吞声”。[21](P148)
[收稿日期]2008-0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