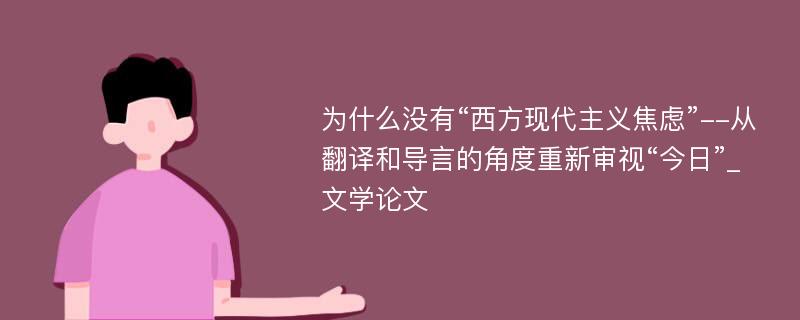
为何没有“西方现代派焦虑”:从译介的角度重估《今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派论文,焦虑论文,角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今天》与“现代主义”
《今天》在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位置自不待言。① 学界对《今天》的认识也一直和当代文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纠缠在一起,比如“文革地下诗歌”、“现代主义”、“纯文学”和“文学/政治”等等。其中一个最具影响力的定位是把“朦胧诗”视为当代中国现代主义(或中国“现代派”)② 文学的源头和重要代表。这种观点早在1980年代初“朦胧诗”论争时就被提出,当时虽然很多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朦胧诗”作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诗歌)的重要一环的位置最终还是被确认了下来。体现在具体的研究成果中,就是把“现代文学”中的所谓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和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时期”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作“整体观”,再加上19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文学新潮(“先锋小说”和“第三代诗歌”),勾画出了一个脉络清晰、起伏有致、现代之后又有后现代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发展”史。除此之外,对《今天》的认识还有一种略有差别的杂糅说,即认为以《今天》为代表的“新诗潮”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等多种风格的混合体。一种比较典型的说法是:“即使在层次较低的以浪漫主义为主要倾向的诗人身上,也夹杂着某些现代主义因子;同样,哪怕是主要倾向为现代主义的诗人,也不是一个完全的现代派,而是夹杂着某些浪漫主义色彩。”③
近些年,随着学界对“文革地下诗歌”的发掘,特别有关“白洋淀诗群”、“黄皮书”、“灰皮书”等等的回忆和叙述日渐丰富,学界更愿意把《今天》和“文革地下诗歌”并置在一起,将前者从“朦胧诗”、“新诗潮”等等极其含混的指称中单列出来,强调二者在作者构成和文学理解上的差异,以“提高”或“还原”《今天》的文学史地位。其中一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是:“(《今天》的)‘组织基础’乃是70年代的‘白洋淀诗群’和与其关系密切的北岛、江河等人。从‘X小组’、‘太阳纵队’,到‘白洋淀诗群’、‘今天’,有一条现代诗的连续文脉可循。而《今天》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成熟的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群体的出现。”④ 还有学者从阅读书目中看到了“文革地下诗歌”和“朦胧诗”之间的风格分疏:“‘白洋淀诗群’的回忆文章往往刻意强调他们所受到的西方‘现代派’文艺的影响,而在‘朦胧诗’论争中得到命名的重要诗人如北岛、舒婷、顾城等那里,这种‘影响的焦虑’则很少涉及。即使在舒婷直接谈读书的文章中,列出的也主要是雨果、普希金、泰戈尔、拜伦、济慈等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作家。可以说,‘朦胧诗’杂糅了19世纪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与20世纪的现代主义风格。”⑤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成果都对《今天》(包括“文革地下诗歌”)和“朦胧诗”等研究有所推进,但均未溢出原有影响研究的框架。即和之前的研究类似,在定位相关的文学现象时,均把它们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作为最重要的阐释依据。至于前后观点上的差异,大致与研究者对文本特征的不同体认和对影响史实的掌握情况有关。在这些研究中,尽管“文革地下诗歌”、《今天》与“西方现代派”的关系被进一步坐实或强调,但仍然疑窦重重。比如“文革地下诗歌”和《今天》的“西方现代派”情结何以到了“朦胧诗”人那里却淡化了?要知道,“朦胧诗”的倡导者们最重要的辩护策略就是将之看做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在“朦胧诗”的接受过程中讲述“黄皮书”、“灰皮书”的故事应该说正当其时;还有就是,把舒婷作为特例是有说服力的,在她本人“主动坦白”的书目中⑥ 确实没什么“西方现代派”,但如果把舒婷的书目放大为“朦胧诗”的书目,进而认为正是这种阅读资源的限制才使“朦胧诗”人没有“影响的焦虑”却不足信——同时有“文革地下诗歌”活跃分子、《今天》主编和“朦胧诗”代表诗人这三种身份的北岛就无法纳入此种研究理路⑦。本文并不打算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解释,而是想从原有的研究框架中跳出来,借助《今天》(1978-1980)原刊来分析《今天》择取文学资源时的态度,重新讨论“现代主义”视角在研究《今天》时的优先性,并由此对《今天》的文学理解作出新的阐释。
二 《今天》的视野
《今天》创刊号上有这样一段话:“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不再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真正地了解自己的价值,从而避免可笑的妄自尊大或可悲的自暴自弃。”⑧ 这段话被广泛引用,往往被人们看成《今天》追寻西方现代文学尤其是“西方现代派”的宣言,1980年代中期以后“文革地下诗歌”和《今天》的当事人对“黄皮书”、“灰皮书”等的回忆,似乎更佐证了这种判断,却很少有人直接分析这种“横的眼光”究竟看到了什么。
这需要具体考辨《今天》发表的长期被人们忽视的译作。因为对于有着“创世纪式”⑨ 热情的《今天》来说,在那些冒着极大风险印制出的珍贵版面上发表的非原创性(即译介)文字,对于理解《今天》的自身期许和文学想像有着重要价值,理应作为他们十分看重的精神给养和文学范例来加以审视。
《今天》的译介不多,全部9期刊物里有3期发表了11篇(首)译介类作品。其中“创刊号”发表了西班牙诗人阿莱克桑德雷(《今天》译为卫尚·亚历山大)的3首诗,并附以吴歌川的绍介文章《西班牙诗人卫尚·亚历山大》,一篇英国作家格林厄姆·格林的小说《纯真》,还有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今天》译为亨利希·标尔)的文章《谈废墟文学》和“译后记”;第2期发表了苏联作家叶甫根尼·叶甫图申科的小说《鸡神》,还有两篇编译类文章,分别是对“俄国象征主义诗歌和亚·布洛克”与西德“四·七”社的简介;第9期上是美国作家小库尔特·冯尼格特的小说《步入永恒》。
从这份译介目录看,《今天》的译介和“文革”后的中国文坛一样,也有着“诺奖情结”:共刊发了五位外国作家的作品,其中就有两位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莱克桑德雷和海因里希·伯尔),阿莱克桑德雷是“刚刚”(1977年10月6日,《今天》1978年12月23日创刊)获奖就被关注;此二人“待遇”也比较高——都发在创刊号上,且都是作品并附作家介绍的方式。虽然不知道译者所用的原始材料,无法考证翻译时的归化或异化的程度如何,但还是能从作家的介绍中发现翻译的主题化倾向。在译者吴歌川笔下,阿莱克桑德雷是一个诗人英雄:“在精神上永不屈服……而成为西班牙精神生活的堡垒”;“半世纪来,在战乱扰攘、生活不安的情况下,他都要尽其有限的精力,献身于诗的写作,他认为那是‘最深刻最精确的表现方法’。他立志要用毕生的力量,和全人类打交道”;“他心目中的诗人,是一个从脚底上升的力量,来为地球上的人类说话的人。诗人写出来的诗,应该是肯定的”。尽管对两位作家的介绍中分别提到,阿莱克桑德雷是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诗人,伯尔是西德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艺术手法“基本上遵循了旧有的现实主义传统,但同时也采用了一些现代派艺术手法”,不过,在所有的译介文字中,“超现实主义”和“现代派”都没有被详加阐释。也就是说,在诺奖得主之外,选择他们的原因和“西方现代派”关系不大,而是作家的形象和他们对文学的理解有着与《今天》相契合之处。
除却阿莱克桑德雷和伯尔,格林厄姆·格林、叶甫图申科和小库尔特·冯尼格特三人《今天》上各有一篇小说被译介,但无论是文学风格还是小说技巧均中规中矩,看不出和“现代主义”有什么干系。唯一值得重视的是支波编译的《俄国象征派诗歌与亚·布洛克》⑩ 一文。这篇文章是把俄国象征派视为“西方现代派”加以介绍的,文中详加描述了象征派的历史和四种特征,并特别介绍了诗人布洛克。似乎这篇文章可作《今天》重视“现代主义”的例子,但细读该文会发现,文中对“现代主义”的态度恐怕会让那些把《今天》看成当代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源头的人大跌眼镜。文章提到,布洛克的独特之处在于:“现代派诗人有种坏习气,就是超越诗歌所特有的界限,而堕入离奇怪诞和反复诉说的五里雾中。但布洛克却尚未失掉和人世的联系,他的诗充满了人世的音响和芳香,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是一位“探索自己真实道路的诗人”。相对于1980年代中期对“西方现代派”的追捧,这里对“现代主义”的态度可谓相当“保守”,甚至让人想起当时站在文学新潮对立面的批评家那套“客观”、“扬弃”或“批判地继承”之类说辞。
文章最后总结道:“对我们来说,布洛克的诗歌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是现代的图画。在这些画面里,捕捉着现代精神的复杂的形象。但是,由于多数人不可能在同等程度上感受到他所描述的体验,这种意义上的现代精神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他和所有的诗人一样,把自己最接近、最熟悉的事物触发出来的精神幻象当作整个人类的精神生活。然而,不论这里有多少谬误,都不足以贬低作为现代诗人的真诚自白的价值。”很显然,这里出现的“现代的图画”、“现代精神”、“现代诗人”和《今天》别处提到的“现代更新”、“现代艺术”、“现代手法”等概念不能简单归结为“现代主义”一家,“现代主义”充其量是《今天》所热切寻求的“现代”文学中的一种,是一个重要的、可资参考的但绝不是毫无挑剔和足以成为文学未来的概念。
此种对待“现代主义”的态度非《今天》所独具。当时社会上一些和《今天》的处境类似的前卫文艺团体和文艺活动,都有着一种蓬勃的探索热情和强烈的形式更新欲望,但同时又对堕入某种现成的和单一的整体解决方案保持警惕。对于这些艺术同行的作品和动向,《今天》都给予了及时的关注。夏朴为“新春画展”(由稍后成立的“春潮画会”主办)写的评论中提到(11),这次展览如“非洲的植物园”一样“纷纷扬扬”,有学院派、印象派、表现派和野兽派。但他同时指出:“一些思想变态的人确实搞过十分低级的常识,赢得过资本主义舆论界的喧嚣。但是,支离破碎的断片绝不是艺术发展的主导倾向,绝不可以抹杀艺术的革新和探索。”在文章中,夏朴对“现实主义”发起了激烈攻击:“我们尊重前代大师们的现实主义因素和技巧,我们更要尊敬他们探索时的自信和顽强。我们要发展的艺术观,发展的艺术。那么,让我们的作品中不再是历史的回光返照,而代之以现代的真实、代之以未来的理想吧!”但是,和1980年代被普遍接受的——无论是倡导者还是批评者——以“反(非)现实主义”为特征的“现代主义”相比,夏朴对“现实主义”的批评并没有导致完全对立的艺术观诞生。这从夏朴对这次展览的批评可见一斑:“我们不希望作品中那种对生活的麻木和对生活的卖弄,两者虽然在艺术风格和形式上水火不容,但却是一个枯树上长出的两个空果。严格地说,这是艺术家对生活不认真不严肃的产物,个别作品里有这样的倾向。”钟城对“四月影会”主办的《自然·社会·人》展览进行了热情的评论,虽然他在文章里特别强调了用“直觉”表现摄影者美学观点的重要性,但他也认为,“作为一个集体影展,它缺乏一种强烈的个人风格彼此区别。虽然影展的整体效果显示出它比以往影展的丰富。这首先表现在题材上:众多的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一种题材,并且手法又惊人地相似。我们不能希望摆脱一种狭窄的道路而又共同走入另一条不宽的道路”。(12)
三 海因里希·伯尔的象征意义
为了更清晰地呈现《今天》的文学视野和文学态度,下文将重点分析《今天》非常重视的海因里希·伯尔的译介情况。《今天》的“创刊号”翻译了海因里希·伯尔的名文《谈废墟文学》,配发的“译后记”介绍了伯尔的生平、著述和文学地位;第2期还特别追发了伯尔所属的“西德‘四·七’社”的“简介”。这则“简介”透露出了《今天》选择伯尔的用意所在:“这批作家关心现实的政治问题。他们作品的题材主要取材当代或近代生活,很少以历史题材为主要内容。战前,人们常常责备德国作家过于脱离政治。但今天肯定不会有人再这样说了,有人甚至认为,他们太‘政治化’了。这批作家深刻体会到‘政治是人民的良知’,因而用自己的笔反对战争和促进人民之间相互理解作出了贡献”,“在他们的作品中,作家总是从明哲和□□(原刊系油印,此处字迹模糊——引者注)的态度对待现实。在小说的形式上,多采用内心独白手法。经常用‘小人物’的经历、思想和他个人的决定来表达我们时代和我们生活中的重大题材。因为我们的社会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而他们的状况非常具有象征意义”(13)。伯尔是《今天》唯一被译介过两次的作家,“四·七”社又是《今天》上介绍过的唯一一个文学团体,可以说,这一译介对同样作为文学团体的《今天》来说也“非常具有象征意义”。
《谈废墟文学》是伯尔一篇曾被广泛引用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伯尔阐述了他对于“废墟文学”的理解:“人们并不是在责备我们曾参与这场战争,把一切都夷为废墟;显然是在怪罪我们看到了这一切;我们没有把眼睛蒙上,还继续在看……我们认为,将同时代人诱骗于田园诗中是一种残酷,一旦从梦中醒来,将是可怕之极,难道我们真的要玩一场捉迷藏的游戏吗?”其中,伯尔对狄更斯的描述颇为动人:“他有一双很好的眼睛,一双人的眼睛。它通常不是完全干涸的,但也不是泪汪汪的,而是有一点湿润……他的观察是如此敏锐,以至他能够描写他的眼睛所没有看到的事情——他没有用放大镜,也没有用倒置的望远镜,因此他很准确地、但又保持一定的距离去观察事物,他没有蒙上眼睛。”在德语里,“观察”除了指视觉的范畴之外,还有“洞察”、“看透”的意思。伯尔认为,作家在观察时,应该有这么一双“人的”、“不受贿赂的”和“湿润的”眼睛。他可能看到幽默,也可能看到一点都不幽默的废墟。并且,伯尔还将这样的“观察”推向了那些正在兴起的建筑物——“没有人住在建筑物里,而是人在被管理,作为保险经纪人被管理,作为国家爱的公民、城市和居民,作为那些付钱的或放债的人——有无数的理由,人们正是为了这些理由而被管理着的”。伯尔提醒人们,不仅要记住那些战争的后果,还要去探讨战争的发生以及像舞台背景一样的社会场景中那些以日常生活形式存在的权力机制的运作。在此意义上,战争所能提供的不再仅仅是对战争本身的反思,而是呈现出这样一个反思舞台背景一样的社会场景的契机,作家的任务就是要使人记住:“人不仅是为了被管理而生存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毁灭,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也不是那些细枝末节方面的,人们无法自诩在几年之内就能治愈它们。”(14)
参照《今天》上发表的作品,会发现伯尔的思考在1970-1980年代文学的“转折”处就已获得深度回应。《今天》创刊时的背景和二战后的德国有些相似,“其时正是‘伤痕文学’时期,正是这个民族开完刀麻醉药过了喊痛的时候。《今天》没有直呼其痛,它镇静地看着伤口,思索着怎么会挨这一刀,研究这鲜血的色泽和成分,动了灵思,这正是《今天》的气质所在”。(15) 《今天》“创刊号”第一篇作品的题目就是《在废墟上》。这是一篇典型的以文革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署名“石默”,即《今天》的发起人和主编之一北岛。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历史学家王琦,他在“文革”中的处境极其糟糕:作为“老牌英国特务和反动权威”被批斗,女儿与之断绝了关系;他的剑桥同学也是现在的同事被迫害致死的惨象如在眼前,历史系主任、哈佛社会学博士吴孟然也遭受了侮辱——“曾引为自豪的白发被交叉地剃了两道深沟,乱蓬蓬的,落满了灰尘,像把降过霜的枯草”,而这些都很可能是他的明天。无意识中,王琦走到了圆明园。在王琦眼中,这片“石头的废墟”就是中国的历史,这让他顿获认同之感:“历史不会停留在这片废墟上,不会的,它要从这里出发,走到广阔的世界中去”,“一个历史学家,死在自己的历史面前是无愧的”(16)。王琦相信时间与历史总会呈现出另一面,眼前看到的只是真相被遮蔽,包括他女儿在内的那些“革命小将”们都会在某一天“觉醒”、“洗手不干”和“后悔”的,而到那时候,他现在的自杀将被赋予意义,“废墟”将会变成“历史”。正当他准备上吊时,一个小姑娘出现了。当王琦听到小姑娘说“我爹死了,上月初六,让村北头的二愣、栓柱他们用棍子打死了”时,他似乎突然意识到这个小姑娘的天真可爱与她说起父亲的死亡时的“毫无表情”是如此清晰地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的,特别是她说起的父亲的死因——“我爹偷过生产队的西瓜”——完全可以视为一种对历史的解释,也完全可能会被他一直念兹在兹的亲人所接受。这让他悲痛不已,也让他最终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他原本打算容忍历史的残暴把最后的审判交给时间,但他陡然发现更可怕的是那残暴会自动生成历史叙述;“废墟”不会长出活的评价,现实却有听上去严丝合缝的措辞;“废墟”并不天然具有价值,而需要不断地被揭开、晾晒和质疑。他要返身走回现实参与对“历史”的争夺,不让自己和他人真实的身体感觉被一些简单的说法所覆盖。把这样一篇大有深意的作品刊发为首篇,可见《今天》对“废墟”意象及文学、人在历史中的位置等等所持有的复杂看法。这或许就是《今天》看中伯尔的原因,在同期的译文中,伯尔表达了对“作家的政治”的理解:“作家要面对过去,为的是从过去中探索当前的秘密;作家面对当前,并要解放当前;作家支撑着未来,并要揭示其秘密,以使当前知道,要做何等样的准备。”(17)
《今天》上曾发表过一篇名为《试论〈今天〉的诗歌》的文章,作者辛锋以“《今天》的诗歌何以在这样一个时代产生”设问,他的回答是《今天》的诗人“在这样的冷落面前开始思考他们生存的意义了。这种思考是绝大多数生存在这个时代的人都经历过的。它要求每个人做出回答,但是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是无法回答的。因为原有意识的逻辑已经不能再起作用了,就需要人在精神上的再创造来作出回答”,《今天》要做的,是“真正的再创造中国的新文明和新文学艺术,而不象过去那样留有过多的模仿的痕迹”(18)。这里“再创造”显然不能理解为因无知而导致的狂妄——事实上即使是狂妄无知也不可能真正拒绝所有的文学资源,而是一种充分自信的主体状态。这群经历了“文革”的青年“尝到了幻灭的苦果”(19),让他们轻易地相信任何一揽子计划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不仅包括政治方案,还有诸如“现代主义”这样颇富诱惑力的文学方案,他们要用自己的方式面对历史和现实,试图探索出一种新的文学。因此,那种一直颇有市场的“文革”后“西方现代派”是中国当代文学必然选择的神话并不怎么靠得住,是对历史连续性过于崇信的结果。至少在《今天》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文学期刊上,并没有把“西方现代派”作为最高的文学范本。北岛等人当时没有“西方现代派”焦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与此——在《今天》时期他们虽然非常渴望一种“现代”和“新”的文学,也有向西方文学学习的内在冲动,但对他们来说,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的文学样板可以对应于他们的文学追求。《今天》“创刊号”上迪星的《瘦弱的人》表达了对“新”的看法。这篇小说用一个“瘦弱的人”来隐喻现世的问题,他已经被医生“判决”为“先天性贫血症”,即便是输血也不能重获生机,他发现街上“这无数张迎面而来的无声的脸,和他一样苍白,一样瘦弱”,活力之源只在那些新生的婴儿身上。
结语 “从野兽变成家畜”
可是,在后来的文学史上,《今天》还是成了“现代主义”。甚至一直到今天,“现代主义”神话仍然在控制着有关《今天》的回忆方向、研究预设和阐释限度。个中缘由,和《今天》杂志原刊的不易搜求有关,造成一些未经证实的说法被来回转引;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1980年代中后期以后,那种以“现代主义”为核心的文学观念被体制化之后,要想进入文坛,就必须借道“现代主义”,而到了更重“学问”的1990年代,这种文学观念进一步被学科化,在各类文学史研究中,《今天》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位置则被进一步强化和细化。这也大大影响了当事人的回忆——或者如刘禾说的那样,回忆也是一种边缘化的文学史写作形式(20) ——“黄皮书”、“灰皮书”成了文学史和回忆录的兴奋点(也就是后来所谓的“西方现代派焦虑”:“‘白洋淀诗群’的回忆文章往往刻意强调他们所受到的西方‘现代派’文艺的影响”(21) ),甚至一下子成了“文革地下诗歌”和《今天》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文学资源和精神给养。在批评家看来,用“现代主义”(或“现代派”)来描述《今天》不啻一种赞赏——本文开头提到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说”和“杂糅说”都有此意——可又有多少人认真地揣度过《今天》那种更为复杂的文学追求所蕴含的意义呢?或许在1980年代以来的“现代主义”神话建构中,这是《今天》必然的文学史命运。(22)
《今天》主编北岛在近年的一个访谈中回答提问者关于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问题时,不客气地说:“你把很多问题都混在一起了。‘西方’、‘本土’、‘现代主义’、‘现代性’,这些深奥复杂的概念就像牢笼,让我们从野兽变成家畜。”(23) 对这种用概念来简化《今天》的不满不是现在才有,只是一直没有被更关注“现代主义”的人们所注意。《今天》的成员之一徐晓记录了1985年《今天》遭遇“现代主义”的情形:
“我清楚地记得,1985年冬天,我踩着积雪到北京大学参加学生会主办的艺术节,北岛、芒克、多多、顾城被邀请在阶梯教室里讲演,当学生们对现代派问题、朦胧诗的概念纠缠不清时,北岛开始回忆《今天》。我不知道坐在讲台上的《今天》元老和主力们当时有怎样的感受,大学生们对这一话题的茫然和冷淡深深地刺痛了坐在听众席上的我,我觉得受了伤害,并且为这些无从责怪的学生感到悲哀,我甚至想走上讲台,讲述我们当年承担的使命和风险,我们所怀的希望和冲动……那时离《今天》停刊只有四年……”(24)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现代主义”、“浪漫主义”抑或是“现实主义”,这些曾经赋予《今天》及相关文学现象的标签,在其对应的语境下都发挥过很大的作用:要么参与了“文革”后新的话语空间的开创,要么象征着学术研究的新进展。但随着前者的作用越来越不明显,学界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在《今天》原刊及文本上,将文本、史料与文学史叙述关联起来作出更加贴近的描述。本文从译介的角度对《今天》与“现代主义”关系的描述,并不是要刻意地否认二者可能存在的关系,也对《今天》是否属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之类问题没有兴致,而是希望借助这种清理提醒学界在研究《今天》时,能在“现代主义”视角之外探寻更多其它的可能,这不仅对研究《今天》具有重要意义,还会为人们揭示1970-1980年代“转折”之际的文学的复杂面向提供不可或缺的参照。
注释:
① 除了在一些文学史著作有“专节”的位置外,还不时有作家在讲述自己的成长历程时向《今天》“致敬”。可参见本文作者与小说家格非的对话《文学史研究视野中的先锋小说》(载《南方文坛》2007年第1期)和对诗人韩东的访谈《只有“今天”,没有“朦胧诗”》(载《星星》2005年第9期)。
② 在1980年代,“现代派”和“现代主义”两个概论在使用中并未被区分。由于引文中经常出现混用的情况,也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然沿用这种方式。
③ 王光明:《艰难的指向——“新诗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新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④ 陈超:《打开诗的漂流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85页。
⑤(21) 贺桂梅:《后/冷战情境中的现代主义文化政治:西方“现代派”与80年代中国文学》,《上海文学》2007年第3期。
⑥ 舒婷:《生活、书籍与诗——兼答读者来信》,《福建文学》1981年第2期。
⑦ 北岛曾提到他印象最深的“黄皮书”“包括卡夫卡的《审判及其它》、萨特的《厌恶》和艾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等……”。见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9页。
⑧ 《致读者》,《今天》第1期。
⑨ 洪子诚:《朦胧诗新编·序》,洪子诚、程光炜编选《朦胧诗新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⑩ 支波编译《俄国象征派诗歌与亚·布洛克》,《今天》第2期。
(11) 夏朴:《采一束鲜花献给春天:评中山公园〈新春画展〉》,《今天》第2期。
(12) 钟城:《〈自然·社会·人〉巡礼》,《今天》第4期。
(13) 程建立编译《西德“四·七”社简介》,《今天》第2期。
(14) [德]海因里希·伯尔:《谈废墟文学》,程建立译,《今天》第1期。
(15) 韭民:《〈今天〉短篇小说浅谈》,《今天》第9期。
(16) 石默:《在废墟上》,《今天》第1期。
(17) 笔者的《海因里希·伯尔的中国遭遇》一文对海因里希·伯尔的中国接受情况有详细的分析,暂未刊。
(18) 辛锋:《试论〈今天〉的诗歌》,《今天》第6期。
(19) 毕捷:《评〈思绪〉的思想性》,《今天》第5期。
(20) 刘禾:《持灯的使者·序言》,《持灯的使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Ⅶ页。
(22) 与《今天》命运相似的还有其“派生出来”的“一个组织”(北岛语)“星星画会”。在2007年12月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的“星星画会”回顾展上,无论是画展的海报、主持人的介绍还是当事人的回忆,“现代主义”都是对“星星画会”最明确的定位。可资对比的是,1960年代开始不公开创作的“无名画会”也颇有成绩,1979年还曾与“星星画会”同时展览过,也处于权力中心(北京),却没能引足够的重视,抗拒“现代主义”的收编是原因之一。参见高名潞《无名画会——拒绝媚俗的悲剧前卫》,收入高名潞主编《“无名”:一个悲剧前卫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8页。
(23) 朱朱:《北岛访谈》,《今天》2007年冬季号。
(24) 徐晓:《〈今天〉与我》,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385页。
标签:文学论文; 诗歌论文; 朦胧诗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西方诗歌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读书论文; 北岛论文; 现代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