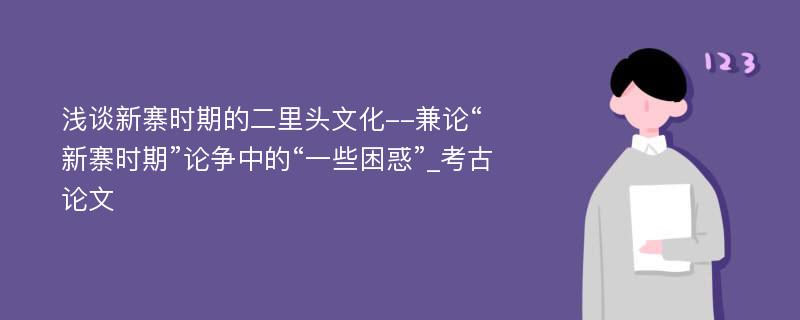
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兼评《来自“新砦期”论证的几点困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论文,困惑论文,文化论文,新砦期二论文,新砦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法 K871.2 文献标识码 A
发表于《中国文物报》的《来自“新砦期”论证的几点困惑》一文[1](以下简称《困惑》),对《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中关于“新砦期”从1997年试掘提出以后,通过1999年第二次试掘再次得到确认的事实,提出几点“困惑”。事实上《简本》只是公布科研成果的结论,不是详细公布试掘的原始资料。要完全依靠《简本》上公布的有限材料去认识“新砦期”的全部内涵是不现实的,只“认真学习”和“研习”《简本》所公布的材料也是明显不够的,由此而产生“几点困惑”也是可以理解的。由于夏文化研究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家与文明这样重大的学术问题,因此笔者也认为很有必要对“新砦期”的能否成立,加以讨论,以期对正确认识“新砦期”有所裨益,不妥之处,望方家指正。
众所周知,新砦期二里头文化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通过对新砦遗址试掘以后提出的[2],迄今已有20余年。在这段时间里,相关论文也有发表[3]。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的提法,已经为学者们所采用,这是有目共睹的。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为慎重起见,于1999年对该遗址再次作了试掘[4],目的是检验这种提法是否可以成立。通过第二次试掘再次证明,“新砦期”确实是能够成立的。
为说明这个问题,下面先来对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的情况作一简要的回顾。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对密县(今新密市)新砦遗址进行首次试掘,发现有一组灰坑的打破关系,即H5打破H6和H11。H5、H11是二里头文化早期灰坑,H6是龙山文化晚期灰坑,还发现有两者相迭压的地层关系。新砦遗址二里头文化早期的遗物,包含有相当数量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与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期文化有些区别,有它独特的风格,具有介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遗址第一期之间过渡的形态。有此类特征的遗物,在豫西地区的其它遗址中也多有发现,如临汝煤山遗址[5]、柏树圪垯遗址[6]、洛阳东干沟遗址[7]、登封告成王城岗遗址[8]、北庄遗址[9]、禹县瓦店遗址[10]等,说明它具有一定的分布范围。同时,在煤山遗址中也发现有此类性质灰坑打破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灰坑以及地层相迭压的关系。因此,它们之间相对年代的早晚关系是清楚的,文化方面的差别也是明显的。同时,它与二里头遗址第一期文化的区别也是明显的,表现出时间较早的特点。所以试掘者将其另立一期,称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
新砦遗址的新砦期二里头文化,遗迹有灰坑和瓮棺葬等。灰坑形状有圆形、椭圆形、袋形、锅底形和不规则形等几种。瓮棺葬的葬具为深腹大罐,口向上,底微偏东北,罐内置婴儿骨架,头向上,面向西。遗物也比较丰富,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锛、石凿、石铲、石刀和石镞,还有一定数量的有段石锛和有段石铲。石刀多为弧背长方形,两侧平直,中部有孔,制作规整。石镞有扁三角形、三棱形和圆锥形三种,后两种有铤,刃很锋利。骨器和蚌器数量相当多,器形主要有镞和锥等,还有陶制的纺轮和网坠。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泥质黑陶不多,棕褐陶占一部分,有相当数量的涂黑衣陶,磨光陶少见。以轮制为主,器壁较厚,陶色不甚均匀,器体较小,制作不如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工整。陶器的折沿较平或微内凹,唇缘稍圆或略方,内侧明显有折角,直领较高,口部不外侈。罐、瓮类的器腹下瘦,鼎、盆类的器腹下广,多为平底,盛行鸡冠形耳,环带状耳较少。纹饰以方格纹和篮纹为主,次为绳纹、弦纹、阴线纹、指甲纹和刻划纹,以及附加堆纹,纹理较为清晰。器类主要有鼎、深腹罐、甑、甗、盆、平底盆、澄滤器、钵、圈足盘、三足盘、大口罐、高领罐、豆、杯、碗、壶、觚、瓮、缸和器盖等。器形自具特色,有别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及二里头遗址第一期的陶器。
下面再着重对新砦期几种主要器类的特征予以介绍:
鼎 分乳头足罐形鼎、扁三角足罐形鼎和扁三角足盆形鼎三种。乳头足罐形鼎,宽沿外折,口部微敛,深腹下广,圜底,器足稍大,壁饰篮纹或方格纹。扁三角足罐形鼎,平沿外折,敛口,圆腹下广,器足宽大,饰绳纹。扁三角足盆形鼎,口沿稍窄,口部微敛,浅鼓腹,饰不明显的斜篮纹。
深腹罐 皆夹砂灰陶,数量较多。一种是敞口,宽沿,圆腹较深,下部内收,小平底,饰篮纹或方格纹。另一种是宽沿外折,深腹较圆,下部较瘦,小平底,饰方格纹。
盆 平折沿,器腹较深,下部圆鼓,平底圆角,饰浅横篮纹,腹上部有一对宽耳。
澄滤器 一种半圆形,敛口,厚沿,圆腹,圜底。饰方格纹或篮纹,器壁较厚,内壁刻有辐射状凹槽。另一种,稍束颈,腹较浅,平底。器壁较薄,饰篮纹或方形纹。
三足盘 侈口,厚缘,腹较浅,壁较直,平底。足底连接处偏里,横断面"C"形。腹及足饰弦纹。
钵 口沿内卷,宽肩,浅腹,斜壁,底较大。
碗 敞口,方唇,斜腹较浅,平底稍大。
器盖 握手粗而短,盖面较平,折肩,直壁口微外侈。
如上所述,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从地层上说,是介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遗址第一期之间的;从陶器的形制来看,也有明显的承袭关系。虽然三者的陶质都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泥质黑陶占一部分。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磨光陶较多,黑衣陶较少,器壁较薄,陶色均匀,陶质坚硬,器体较大,器形工整;后两者的黑衣陶较多,磨光陶较少,器壁较厚,陶色有的不甚均匀,陶质尚坚硬,一般器体较小,器形不及前者工整。三者的纹饰比较相似,明显的差别是二里头文化第一期增加了一定数量的压印花纹,为前两者所不见。方格纹的变化是由多到少,篮纹则由少到多,纹理由深变浅,由清晰变模糊。三者的器类基本相同,差别是新砦期不见二里头文化第一期盛行的圆腹罐、捏口罐、尊和甗等。二里头遗址第一期文化则不见新砦期盛行的乳头足罐形鼎、钵和敞口斜腹碗等。根据地层关系与器物形制的变化,可以看出,新砦期是介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遗址第一期文化之间的遗存。虽然它包含有相当数量的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但似乎更接近二里头遗址第一期文化,所以试掘者称它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增补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遗址第一期文化之间的缺环,将以嵩山为中心的四周平原地区的古文化发展序列,基本上联系起来,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有人坚持夏王朝是从偃师二里头文化第一期开始的,不承认“新砦期”的存在。但偃师二里头文化的渊源来自何方?又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位置与文献上记载“禹都阳城”并不相合。与夏代纪年为公元前21~前16世纪,也不相合,因为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期的C[14]测定标本的年代数据是从公元前1900年开始的。与文献记载的夏代始年尚相差100余年。以上存在的问题,正好由于“新砦期”的发现,将偃师二里头文化第一期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联系起来,因而得到顺利的解决。
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在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如登封、密县、禹县、临汝和洛阳等。经C[14]测定标本的年代数据,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约为公元前2132~前2030年;二里头遗址第一期文化约为公元前1900~前1800年;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约为公元前2000~前1900年。《夏商周年表》公布的夏代纪年为公元前2070~前1600年。因此,可以认为,河南龙山晚期和新砦期二里头文化是夏代早期的文化遗存,二里头遗址第一期至第三期文化为夏代中、晚期的遗存。
上述事实完全可以证明,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确实是客观存在的。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为慎重起见,于1999年对新砦期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试掘,这无疑是对1979年试掘成果的一次复查和验证。试掘的成果,已经通过试掘简报公布[11]。试掘者根据层位关系及器物形制变化,将新砦遗址出土的陶器群分为三组,这三组器物的划分,不仅得到地层关系的支持,而且某些同类型的器物还有形制演变的逻辑关系。即器物的演变与地层关系是相符合的。从而表明上述三组器物群,可能代表新砦期前后相衔接的三个发展阶段。
现让我们对这三组遗存的内涵予以介绍:
第一组 以H223、H227、H109为代表,位于T2和T6的最底层。出土陶器以H227为例,陶质以夹砂灰陶为主,次为泥质灰陶,再为夹砂褐陶和泥质褐陶。纹饰以方格纹为主,篮纹次之,绳纹很少。常见器形有夹砂罐、罐形鼎、小口高领瓮、豆、钵、碗以及双腹盆、甗、圈足盘、器盖等。其中以夹砂大口罐和中口罐最为常见,器形多为鼓腹折沿方唇,沿面内凹,内折棱突出。壁饰清晰的方格纹。钵、碗多见清晰的同心圆纹。双腹盆为敞口折壁,折壁呈钝角,豆为粗柄。出土三足盘一件,器壁甚薄,深腹平底,下附三个瓦形矮足,呈现早期风格。
第二组 以H147、H101、H220为代表,层位关系晚于第一组。出土陶器以H101为例,陶质以泥质灰陶为主,次为夹砂灰陶,再为泥质褐陶。纹饰以篮纹为主,次为方格纹和附加堆纹。鸡冠耳开始出现,绳纹较第一组增加。第二组器物组合与第一组无大变化,区别在于有折壁器盖大量出现,夹砂罐和鼎的唇部多为圆唇,与第一组同类器流行方唇的作风有明显不同,纹饰印痕变浅,且较散乱。鼎、罐和缸的口部开始流行子母口作风。
第三组 以H6、H29为代表,从层位关系上看,都属晚期单位。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泥质黑灰陶次之,以及泥质浅灰陶和泥质黑皮陶等。夹砂灰陶比例下降。纹饰以篮纹为主,方格纹次之,再是绳纹、弦纹和附加堆纹。陶器组合与第二组无根本变化。差异之处是鼎、罐类的唇沿上施一周凹弦纹或将唇部加厚,与二里头遗址第一期的同类器相似。还有尖圆唇、圆折沿施整齐细绳纹的深腹罐,深腹近折壁的豆,两侧捏花边的鼎足,瓦形足三足盘,施附加堆纹的大口尊,侈口尖圆唇、腹壁饰散乱篮纹的小口高领瓮,侈口弧壁尖圆唇澄滤器等均与二里头遗址第一期的同类器相近或相同。
从以上三组的情况表明,第一组与第二组之间的差异大于第二组与第三组之间的差异,所以试掘者将第一组划为新砦一期,将第二、三组归为新砦二期。新砦一期属于豫西地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即王湾三期,新砦二期介于豫西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遗址第一期之间,试掘者称为新砦二期遗存,即新砦期二里头文化。试掘者还着重指出:1999年新砦遗址试掘的重大收获是对新砦二期遗存的确认,再次证实二里头文化的确是在豫西龙山文化晚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1999年第二次试掘的结论与1979年第一次试掘得到的结论是完全相同的。即证明新砦二期遗存即新砦期二里头文化是确实客观存在的。是一种介于豫西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遗址第一期之间的过渡性质的文化遗存。它填补了两者之间的一段空白。这一新的科研成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探讨早夏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下面让我们对《困惑》一文提出的四点所谓“困惑”来作点讨论:
在第一点“困惑”中说:“《夏商周代断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六《夏代年代学研究》中明确指出‘河南龙山文化又称王湾三期文化,是分布在豫西地区,在年代上早于二里头文化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这本来是一句完整的句子,《困惑》将它强行从中间割断分开,插上一段“(笔者按:王湾三期文化只是河南龙山文化内涵构成中的一部分,两个概念不能等同)”。这就叫断章取义,节外生枝。因为这是一句完整的句子,意思是指豫西地区在年代上早于二里头文化的一种考古学文化称为河南龙山文化或王湾三期文化。完整的意思并无大错,内行人都能明白,不会产生误会。《困惑》说:“令人费解的是,这张用来说明新砦期上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下连二里头一期的图上所列器物群均将出土地点和地层单位隐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夏商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公布的是一份高层次、综合性很强的科研成果,而不是一份普通的试掘简报,因此,将器物群的出土地点和地层单位省略,是《简本》的性质所决定的,是正常的。而将省略说成“隐去”则是明显不妥当的,因为,该图所用的原始资料都是真实可信的,并不存在要将出土地点和地层单位“隐去”的必要。如果《困惑》确实想搞清楚的话,尽可以去将有关的原始调查发掘资料找来进行“研习”和核实的。如果核实的结果发现有不妥当之处,尽可以具体指出来错在何处,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困惑》先是贬低别人“隐去”,后是随便将这张典型陶器形制演变图说成“丧失其科学性和可信性”,能服人吗?这话说在一个搞考古工作者的嘴里,确实是有点“令人费解的”。
在第二点“困惑”中,是将1999年试掘简报公布的第三组,以H6、H29为代表,改为“T6(2b)(或2B)”,不知是什么原因?并将T6西壁③层,误写为⑧层,在这错误的前提下,反而倒过来问试掘者“怎么能够说明H6(三组)一定晚于H220(二组)呢?”众所周知,本来③层之下晚于⑤层是最简单不过的,还用得着“困惑”吗?此外,《困惑》将一份内部参考刊物《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来与1999年公开发表的新砦遗址试掘简报相提并论,混为一谈是不对的。一般利用别人的资料,都是以公开发表为准的。内部资料与公开发表资料如有矛盾之处,都以公开发表的资料为准的,这是一种基本常识。所以本来是《困惑》自己的问题,却给试掘者扣上一顶“因其全面、客观和科学性的欠缺,尚难以证明其所作出的结论”的大帽子,这公平合理吗?
在第三点“困惑”中说:“以1999年新砦遗址发掘材料为主要支持点的《豫西地区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典型器形制演变图》(《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78页图十五),却对上述发掘报告所分各组代表单位中的器物一件未选(笔者按:不排除选用1999年新砦遗址发掘所获材料中未发表者的可能性存在)。”《困惑》以上所说并无道理,因为既然已经标明这是一张《豫西地区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典型陶器形制演变图》,当然应该反映整个“豫西地区”的考古资料,至于是否选用新砦遗址试掘简报中各组代表单位中的器物也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关键是只要能够客观如实地反映出整个豫西地区三种遗存的“典型器形的演变”关系就足够了。众所周知,考古学在选择同一时期的典型器物作标本时,是可以采用“桥联法”的。同时在这张“图上所排器物至少选自豫西地区的密县新砦、登封王城岗、临汝煤山和偃师二里头等4个遗址。”这不正好说明这是一张真正的《豫西地区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一期典型器形制演变图》吗?为此,《困惑》却发表一通议论说:“通常是采用以该文化典型遗址若干具有分期意义的典型地层单位所包含共存器物群分析为标尺,通过对该文化其他主要遗址的编年成果这一系列最终排定完成的。”难道现在这张典型器形制演变图,与《困惑》所说的有实质性的分歧吗?至于《困惑》所说的这张“《豫西地区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典型陶器形制演变图》在没有交待清楚新砦遗址本身文化序列和文化性质、没有交待清楚所选标本遗址与新砦遗址的内在文化联系的情况下,采用广袤的豫西地区不同的遗址、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类型中按需要挑选一些器物组成具有特殊意义的器物群,有悖于学术界通常运用的考古学文化分期研究方法。”请问《困惑》:这种说明用在一张《简本》的典型器物图上合适吗?这么多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对一张《简本》的典型器物图来说,要求是否有点过份了?虽然《困惑》对别人提出一些不实事求是、不合乎情理的条件和要求,但就在《困惑》这篇文章中,却出现一些不应该出现的差错?如《困惑》说:“已经公布的1999年新砦遗址H6器物群组合(罐、豆、钵、缸、刻槽盆、刻槽罐、盖)”。请问这件“刻槽罐”是一件什么器物?我们为什么从来没有看见过?从以上情况说明“证据不足而难以成立”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困惑》者自己。
第四点“困惑”,是关于如何正确运用C[14]测定年代的问题。众所周知,只有学会正确运用C[14]测定标本年代数据的方法,才能发挥C[14]在考古学中应有的重大作用。这次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展过程中,测年技术与考古学相结合,改进样品制备及测试方法,采用大量的系列标本,并充分运用标本的文化分期和样品之间的先后顺序等考古信息,在进行日历年代校正时与树轮曲线的扭摆进行匹配拟合,从而建立了高精度的C[14]年代框架。把重要的古文化遗址尤其是夏商遗址的绝对年代进行排列,这已成为考古学者多年努力的研究成果。从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表》可知夏代的纪年为公元前2070~前1600年,二里头遗址第一期文化为公元前1900~前1800年,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第一段即王城岗遗址的二、三期为公元前2132~前2030年。二里头遗址第一期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之间的这段缺口,约有100多年,完全有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立足的余地。所谓新砦期二里头文化“难于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之间找到足够的时空立足”之说,纯属主观臆测之辞,缺乏确凿可靠的根据,本不可信。众所周知,通常采用C[14]测定标本的年代数据,都是采用一系列年代数据的平均值,因为C[14]测年尚有误差,所以既不采用最大年代数据,也不采用最小年代数据。更重要的是,使用C[14]测定年代,也不能代替考古学上的地层学证据和器物形制学的证据。也就是说考古学的地层关系和器物形制的变化证据是最直接的、最可靠的和最科学的。我们只能依据地层关系去定出相对年代的早晚,而不能倒过来随便采用一些过时的C[14]测定的年代数据去怀疑、排斥、否定最新公布的C[14]年代数据以及无视地层学上的证据。如果地层学与C[14]测年发生矛盾时,我们应该从C[14]测年方面去寻找原因,而不能相反去怀疑、否定地层学上的客观证据。否则会出现舍本求末的现象,颠倒主次关系,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来的。地层学、器物形制学与C[14]测定标本年代数据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不是相互排斥的。
考古学是一门实证性很强的学科,科学讲实事求是。缺乏亲自参加田野考古工作的实践经验,缺乏对出土器物形制学的感性认识,又缺乏“认真学习”、全面掌握已经发表的试掘资料和专题论文的研究成果,没有全部领会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最新科研成果,包括C[14]的测年在内;不是抱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虚心求教的态度。仅仅因为是个人产生的“困惑”,就去批判、否定、抹杀“新砦期”这一来之不易的重要科研成果,得出所谓“欲信不能”、“至少在目前条件下做出这样学术结论的时机并不十分成熟”等错误判断,是不可能的。事实证明,“夏商周断代工程”作出的结论的基础是牢靠的,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晶,因此,具有权威性。要想动摇、全盘否定、抹杀它,恐怕为时过早。而真正的科研成果,将在综上批判、反对声中经受住考验而站稳脚跟。
综上所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为夏代的早期文化。夏代的早期文化,不是从偃师二里头文化第一期开始的。偃师二里头文化第一至三期是夏代中晚期文化。新砦期发现的重要学术意义,在于填补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期之间的一段空白,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期之间的缺环联系起来,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制定科学的《夏商周年表》之夏代纪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收稿日期 2002-0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