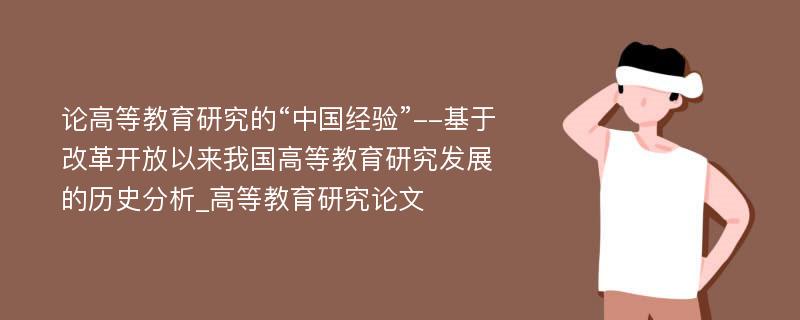
论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经验”——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教研究发展的历史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高等教育论文,高教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64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3-8418(2008)03-0001-04
通过近三十年中国高教研究发展的历史分析不难发现:中国高教研究之所以后来居上,异军突起,不仅归功于改革开放和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而且得益于中国高教研究工作者在开创这项崭新事业道路中探索出来的若干宝贵经验。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经验凝聚着中国高教研究工作者的精神、勇气和智慧,不仅对中国高教研究的繁荣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世界高教研究的发展也有独特的贡献。
经验之一:以学科建设促进高教研究发展
当1978年潘懋元等学者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开创中国高教研究事业之时,西方的高教研究已历百余年之磨砺。作为典型“后发型学术”的中国高教研究是追随西方模式,还是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成为摆在中国第一代高教研究工作者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
众所周知,西方高教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相对崭新和欠发展(undeveloped)的研究领域”,即使将来也只能作为一个多学科研究领域,“不会以一个独立学科(a separate scientific discipline)的形式出现”[1]。而中国高教研究从一开始就另辟蹊径,通过建立专门的高等教育学科来带动整个高教研究事业的发展。历史证明,这条道路适应了中国国情和中国高教研究发展的实际需要,对于中国高教研究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首先,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使中国高教研究迅速取得“合法”地位,制度化进程大大加快。
从社会科学发展史看,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往往只有取得政治——建制上的合法地位,才有可能得到较快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社会科学百废待兴,各类新兴研究领域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蹒跚起步的高教研究要脱颖而出,就必须尽快取得“合法地位”,即成为国家承认的正式学科。因为,在中国,学科是国家管理和调控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单位,是行政建制在科学研究中的体现,其意义超出了研究范畴和教育范畴。一个研究领域往往只有成为正式学科,才能被纳入国家学术管理序列,才有可能在大学设置,才有可能取得政府评审的学位点,才有可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下去。
不难想象,倘若中国高教研究只是像西方那样的“多学科研究领域”,而从未成为专门学科,其后来的发展情形肯定不容乐观。中国高教研究起步伊始就备受争议,举步维艰。中国第一个高教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刚刚成立的时候,除了个别教师外,学校不少人对高教研究并不理解,有人甚至冷嘲热讽:“教育研究是师范大学的事情,综合大学搞什么教育研究。”[2]当时全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不少学者认为“一般教育理论适用于各级各类教育,似无新立学科的必要[3]。但潘懋元等中国第一代高教研究工作者不畏艰难,为高教研究奔走呐喊,终于建立了崭新的高等教育学科。
事实证明,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无疑是确立高教研究“合法地位”的关键因素。1984年高等教育学科正式建立后,各种怀疑之声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全国性高教研究的热潮。以高教研究机构的创建为例。1983年5月,全国805所普通高校中尚有2/3的学校没有高教研究机构。1984年后,各地纷纷采取措施加强高教研究工作,形成了一个新建高教研究机构的高潮。1987年全国已有高教研究机构700多个,比1983年增加近500个,即平均每年就有100个左右的高教研究机构在各地高校建立起来,其发展速度之快在世界高教研究史上绝无仅有[4]。其原因除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对高教研究需求增加外,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
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加快了中国高教研究的制度化进程。从“非制度化”阶段转变到“制度化”阶段是高教研究的质变表现之一,只有“制度化”才能使高教研究具有赖以存在的稳固基础和得到持续发展的保障。1978年以后,中国高教研究制度化的核心工程是建立高等教育学科,但建立一门学科是系统的、复杂的工程,不仅有学科之名,还有学科之实;不仅要形成教育学的分支或形成一类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还必须建立学科研究的规范、规则、范式,建立包括学会、专业研究机构、图书资料、专门出版机构及专业刊物等社会建制在内的学术共同体(academic community)。因此,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不仅使高教研究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而且有力地带动了高教研究机构、组织、队伍、成果的大发展,促使这些制度化指标在80年代末攀升至世界第一。中国从此成为“高教研究大国”。
其次,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提高了高等教育理论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推进了高教研究的科学化进程。
尽管“开放社会科学”、“学科壁垒消融”、“多学科研究增值方式”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界的热门话题,但并不能就此断定学科范式已无法安身立命,因为“科学史上每一个主要时期都是以多种相竞争的范式共存,即没有一个范式能占据霸权地位为特点的”[5]。多学科问题研究范式的价值虽毋庸置疑,但该范式在整合研究兴趣多元性等方面存在缺陷。尤其目前的多学科研究,主要是有关学科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各自进行的研究,对同一问题缺乏多学科的协同研究。这不仅会导致对高等教育整体和全局把握的欠缺,也有可能导致对高等教育一些关键问题,特别是人才培养等教育内部问题的忽视。同时,高等教育问题是典型的复杂问题。解决这类问题,既需要通过多学科研究深入各个层面,追求“局部的、片面的深刻”,也需要对多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整合,从而达到综合性、整合性思考的效果。也就是说,“复杂性所要求的教育研究范式,不仅是后现代的多元,而且还强调整合”[6]。
高等教育学科作为专门研究高等教育的学科,必然以整个“高等教育”作为“问题域”。它既关注宏观领域的高等教育发展,也关注微观领域的人才培养;既研究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也探讨高等教育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讲,高等教育学科研究范式具有多学科问题研究范式无法替代的作用:从高等教育的全局来整体把握高等教育问题,整合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从而更好地探索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建立相对完整和系统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
劳丹(Larry Laudan)指出,“科学的主旨在于解决问题”,理论的合理性与进步性“与它的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密切相关”[7]。从方法论的角度考虑,建立以高等教育为问题域、整合多种理论的高等教育学科有可能提高高等教育理论解决问题的有效性,从而提高高教研究的科学化程度。当然,这要以高等教育学科形成成熟理论体系为前提。如果说,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推进了高教研究制度化进程只是中国特殊国情下的产物的话,那么从理论视角分析得出的高等教育学科整合多种理论和范式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普遍性。如果这个功能得以完善的话,高等教育学科将来未必为中国所独享。
经验之二:以开放姿态推动高教研究繁荣
尽管中国首创了高等教育学科,并按照高等教育学科的理论开展研究、培养专业人才,但高等教育学科并未成为中国高教研究的惟一范式。30年来,中国高教研究从未把自己封闭起来,始终保持一种相对开放的姿态。这是中国高教研究保持长期繁荣和活力的重要原因。正如有学者所言:“高等教育学自创立至今,之所以能发展如此迅速,从学科内部看,就是学科共同体有意识地使学科研究处于开放状态”。[8]笔者认为,中国高教研究的开放姿态具体体现在研究队伍的开放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以及借鉴国际先进理论的主动性等多个方面。
首先,在研究队伍的开放性方面,中国高教研究遵循“来者不拒,一视同仁”的原则。
无论是教育专业的“科班出身者”,还是其他专业的“半路出家者”,甚至“业余爱好者”都可以加入高等教育学科行列,都可以在学科领域发表自己的观点,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成果赢得同行的尊重。
这与其他社会学科的情况大相径庭。从社会科学发展史看,不少社会学科正是为了争夺学术的“垄断解释权”才建立起来的,因而需要“通过同一性的作用来设置其边界”,以“构成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9],为了和“业余爱好者”的活动区别开来,社会科学家所讨论的大部分论点都是用相差无几的词语来表达。而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从建立开始就没有为所谓“垄断解释权”进行过任何努力。相反,争取尽可能多的“业余爱好者”加盟高教研究队伍一直是这个新兴学科的不懈追求。
也许,有人会批评中国高教研究队伍过于“庞杂”,但谁也无法否认中国高教研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是这支“庞杂”的队伍。事实证明,大批其他学科的教师和干部的加入既是高教研究繁荣发展的标志,也是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不仅因为来自其他学科的人员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原来的专业学科背景和研究方法来进行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而且,高教研究的发展离不开高校广大教师和干部的支持。因为“理论的源泉来自实践,只有广大有实践经验的教师与干部支持了,参与了,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才能有生气”[10]。
其次,在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方面,中国高教研究推崇“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气度。
创建高等教育学科,不唯高等教育学科“独尊”;重视高等教育学科范式,不忽略其他相关学科范式和方法对高教研究的意义。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高教研究界就注意到高等教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1984年出版的第一部《高等教育学》在探讨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时就已经主张:“正确认识高等教育学同其他有关学科的关系,掌握并运用有关学科的信息,交流渗透,交互为用,以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发展,这是研究高等教育学的前提条件”[11]。近十多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对高等教育问题的探讨越来越需要借助不同学科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多学科研究方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2001年由潘懋元主编、10位学者共同参加编写出版了《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该书用历史学等11个学科的观点和方法对高等教育进行了研究,掀起了国内高教研究界多学科研究的热潮。
在教育研究领域中,多学科研究方法首先由高等教育学科提出并非偶然。由于高等教育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密切关系,使得高等教育学科与其他学科知识间更可能存在着一个连续的谱系,更容易产生学科知识之间的“视界融合”。这是高等教育学科理论发展生生不息的源泉。因而“在借用其他学科领域的方法上,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在这一点上,它很可能走在其他教育学科的前面,从而为整个教育科学事业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12]。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建立了专门的高等教育学科,中国高教研究是高等教育学科研究与其他多学科研究的结合,两类研究范式的相互配合,既避免了高等教育学科可能出现的“就教育论教育”倾向,又克服了多学科研究可能出现的忽视教育规律之弊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高教研究多样化范式的运用上为世界高教研究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第三,在借鉴国际先进理论的主动性方面,中国高教研究实行“主动借鉴,洋为中用”的战略。
在坚持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前提下,根据中国高教研究自身需要,主动引进和借鉴国外先进的高等教育理论成果。
改革开放之初,尽管当时与国外的交流相当有限,但中国高教研究界就已经注意到借鉴外国高等教育理论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纳伊曼的《世界高等教育的探讨》、阿什比的《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阿特巴赫的《比较高等教育》、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伯顿·克拉克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和《学术权力》等外国高等教育名著先后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受到广大高教理论工作者的重视和欢迎。90年代以来,高教研究领域的国际交流更加频繁,外国更多的高教研究成果被引进。2001年,王承绪等学者组织编译的一套“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出版,所选12部著作皆为国际高教研究的经典之作。此外,克拉克·克尔的《大学的功用》、伯顿·克拉克的《高等教育系统》、阿特巴赫的《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等名著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由于起步晚、国际化程度不高,中国高教研究在世界高教研究领域仍然处于“边缘地带”。如果不能主动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主动借鉴国际先进的高等教育理论,中国高教研究势必进一步边缘化。30年,中国学者对国外高等教育理论的主动借鉴,极大地提高了中国高教研究的理论水平,加快了中国高教研究的国际化步伐。同时,正因为中国学者对国际高等教育理论是主动借鉴而非被动接受,使我们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同时,能够根据中国国情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有所发展和创新,从而为世界高等教育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近年来,中国学者对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修订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经验之三:以服务实践引领高教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学科建立之后,中国高教研究工作者并未故步自封、陶醉其中,而是积极运用新兴的高等教育学科理论来解决高等教育实际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高教研究不是“学科指向”,而是“实践指向”:无论是高等教育学科建设,还是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其目的都是为了服务实践、服务决策。30年来,中国高教研究工作者正是通过服务实践、服务决策引领了中国高教研究的方向。
改革开放之初,提高高校教学水平成为高等教育领域拨乱反正、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因而这一时期高教研究界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高校教学改革。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步开展,大量出现的高等教育新问题需要从理论层面进行深入的思考,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成为高教研究的重点,在民办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地方化、高等教育横向联合、校长负责制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与此同时,高教研究界组织了高等教育思想的大讨论,传统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思想、高等教育人才观、高等学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高等教育价值观等理论问题的研究深化了人们对高等教育改革的理性思考。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高等教育问题研究日趋活跃,服务实践、服务决策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高教研究与高教实践的关系更加密切。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大学素质教育、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与知识经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建立一流大学等课题陆续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
特别令人振奋的是,近年来已经有更多的研究成果为政府部门所重视和采纳。如果说90年代中期以前高教研究成果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还比较有限的话,那么近十年中国高教研究的许多成果已经逐渐被决策部门重视和采纳,有的研究还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最近几年政府关于推行大学素质教育和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决策都深受高教研究的影响,“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这两个对中国整个教育发展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策,正是受教育研究工作者研究的启发而产生的”[13]。
从以上对不同时期高教研究重大课题的回顾不难发现,中国高教研究热点问题的转移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进展是基本同步的。服务实践和决策引领了中国高教研究的方向,为中国高教研究的发展注入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也许有的学者对高教研究界追逐现实“热点”,特别是与行政决策日益密切的关系不以为然。但笔者认为,这不仅符合高教研究的“实践性”、“应用性”特点,也反映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相互依存的趋势。作为应用性特征鲜明的高教研究若不能与教育实践、教育决策建立起相互依存的亲和关系,就很容易陷入“知识乌托邦”而一事无成。
潘懋元教授说过,如果我们“故步自封,不去接触火热的高等教育实践,就会由于钻牛角尖走到死胡同”。“‘坐而论道’实际上既无助于理论联系实际,也无助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14]。中国高教研究之所以在短短30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新兴领域发展成为繁荣而庞大的事业,正是因为它与中国高等教育实践有天然的亲和关系;也正因为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都以服务实践为鹄的,两者才能相互交融,相得益彰,共同促成中国高教研究今日之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