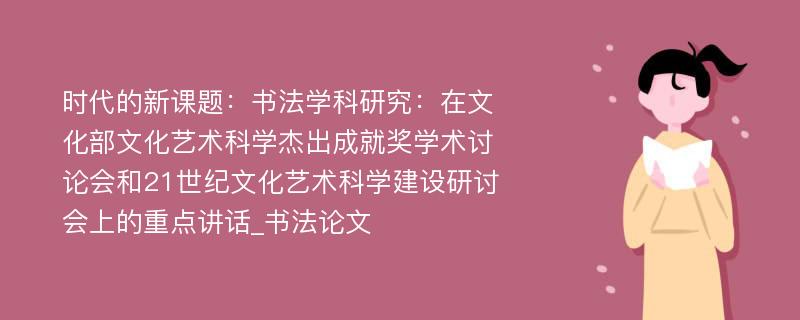
时代的新课题:书法学学科研究——在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大会暨21世纪文化艺术科学建设座谈会上的重点发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艺术论文,文化部论文,科学论文,成果奖论文,书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从事书法艺术研究的生涯中,书法学学科研究,一直是我始终予以最重点关注的学术领域。本来,在我从事的艺术理论研究中,有书法、中国画、篆刻、词学、比较诗学、日本书法与中日绘画交流的诸课题(注:近二十年来,我在书法、中国画、篆刻以及日本书法方面已出版的专著有37种,其中以书法方面的著作为最多。牵涉到书法史、书法美学、书法教育学、近现代书法史、日本书法史、中国画形式美学、篆刻史、篆刻美学、词学流派、比较诗学等方面的内容。但书法学学科研究则是我投入精力最多的一个研究领域,并且还具有系列化的优势:以论文、著作、专栏、研讨会、文库丛书、笔谈等各种形式组成一个立体的多侧面的研究成果群。),即使是限于书法这个老本行,也有书法史、书法理论史、书法美学、近现代书法史、书法教育学暨教学法,书法创作理论……书法学学科研究,本来是一个没有现成参照的、新创建的(也许它又意味着不够成熟的)尝试性研究科目而已。但不管我在做哪方面的研究,比如在书法史学研究中强调史观的统辖功能乃至形成“史观学派”,又比如在书法美学中倡导书法的美学构架、更甚或在书法教育学中的研究分科设置与课程结构性、以及教学法的实施诸内容;再或者是在近现代书法之理论意识与思辨立场转换与古典书论的随感录的不同区别;又或者是在创作理论中追究书法的认识论基点、价值观立场、方法论模式(注:关于书法学学科研究对书法创作的贡献,可参见拙稿《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总纲》中的第六章:〈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的评判标准〉;第七章:〈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的理论基础〉;第八章:〈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的教育支点〉。详见《学院派书法作品集》第20—27,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1版。)……几乎每一项研究一上升到抽象的原理层次,即必然地会落入“学科研究”所设定的基本框架内容中去而概莫能外。由是,在我的切身体会而言,书法学学科研究,既是我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的学术目标,是一项“百川归海”式的终极意义上的研究课题群,但同时,它又是书法研究中的方法论、认识论的起点与基础,是进行任何课题研究时必须的思想武器与方法前提。掌握了这个“武器”,则不仅限于书法,还可以把它引伸向篆刻(注:关于篆刻,我们已尝试召开过一届“全国‘篆刻学’暨篆刻发展战略研讨会”(1997天津),并有论文集,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1997年第1版。)、引伸向中国画(注:关于中国画,我们也于1996年12月在天津举办过一届“全国‘中国画学
’暨中国画发展战略研讨会”,并有论文集由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基本上与书法学学科研究在方法上是同一个思路。);引伸向任何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一
从1979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师从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先生之时,老教授们对我谆谆教诲,即是学书法必须以一门学问打基础,我也曾经像陆维钊恩师那样,选择宋代词学作为我的打基础的学问,以后又自学过一段古文字学和古文献目录之学。但似乎,最能作为基础的学问,应该是书法(篆刻)自身的学问——比如书法史,书法理论等内容。于是忙理论研究,写了许多单本著作,也写了许多报刊连载。在我的艺术生涯中,搞创作的时间远不如理论写作的时间花费多,这是因为书法创作在过去是写文人字,完成一件作品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如绘画创作中主题、构思、形式、技巧那样的时间。而读书做卡片找资料写文章爬格子,倒是需要实实在在地投入时间的。
我的硕士一年级学年论文是《蔡襄研究》(注:《蔡襄研究》,是我在1980年作为学年论文提交给研究生导师陆维钊、沙孟海教授的。后被收入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书法家小丛书〉系列,书名改为《蔡襄》,详见该出版社1988年第1版。),而学位论文则是一部10万字的《尚意书风郄视》(注:《尚意书风郄视》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共10万字。毕业后先在香港《书谱》连载了一年(1984),以后则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1990),在该书的[后记]中,我曾详细地讨论了书法史研究中学科立场,以及思潮史研究在学科构架中的定位问题。),正是在学位论文中,由于讨论的是宋代书法乃至整个书法史上的“思潮史”问题;而早在1981年,还很少有人会去关心这样的问题,但正是不那么“实际”的、略带空泛抽象的史学课题,反而促使我意识到在书法研究中,其实有一个“方法论”和“思辨能力”的因素在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对这样的因素稍加延伸,就会牵涉到书法的学科建设问题。书法向来是写字与文人风雅,在过去并没有人想到书法也有“学科”、“学科意识”、“学科框架”、“学科建设”……等问题。于是我的这种感觉,只是停留在“研究方法反思”的单一层面上,还没有形成自觉的“学科意识”并且也并不认为“书法学科”的提法有多少必要性与急迫性。
但随着书法理论著述的日渐增多,我开始慢慢意识到“学科”这个陌生的名词对于书法的重要性。在为各书法报刊撰写的专栏或连载文稿时,我也有意识地以学科式构架的立场来处理每一个栏目,尽量使它能包容书法的方方面面的成果与思考,其结果是在1990年出版了这批专栏稿的合集《书法学综论》(注:《书法学综论》,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但相对而言,因为是报章的短篇简册,离真正的学科研究所具有的思辨性格与深度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只能说是一个前期的“练兵”而已。此外,1992年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有意组织出版一套书法类的丛书,我被邀出任主编,并定名为《书法学文库》(注:《书法学文库》,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版,共7册。由我主编。计有《书法生态论》(卢辅圣著)、《上古书法图说》(沃兴华著)、《书法文化丛谈》、(姜澄清著)、《近代书苑采英》(陈祖范著)、《书法技法意识》(陈方既著)、《书坛旧闻》(郑逸梅著)、《印人轶事》(刘江著)。本来还有一册《海外书学论文选》,因故未能出版,至今仍引为憾事。),第一辑计划出版8种,在这套丛书的选题、组稿、出版等从确定大致思路到具体操作的过程中,在我本人而言则又是一次对书法学科应该包括的方方面面的内容与构架的重新省视与思考。它,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前奏”性工作并对此后的学科研究起到了极重要的孕育与催化的作用。
1990年7月,在贵阳召开了第三届全国青年书学研讨会。作为青年书法理论家协会主席的我,在主持会议之际,正遇上江苏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前来组稿。鉴于当时书法理论还是不太受重视,也鉴于我们在做理论工作的学者们已深切地感受到需要有一个完整的学科框架以及作为它的样板的学术著作的推出,于是定名为《书法学》。这可以说是第一次把“书法学”这个学科名称,以真正意义上的学科构架形象推向社会。为了共同编撰这部著作,受邀参编的十几位撰稿者共同聚会了好几次。对《书法学》这部著作、以及它所代表的书法学学科内容与方法——进行了反复地论证与驳难。其坦诚与激烈程度远远超出当时一般学术研讨会的气氛(注:关于《书法学》编写过程中的热烈的讨论场面,迄今仍是记忆犹新的。可参见《书法学》下册〈后记〉所记载的当时情况。请见该书下册1471-147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版。)。作为主编的我,也因此一机缘,对自己积累日久的思考作了一遍大清理,并且为了对各章提出了修改意见,又不得不对每一章的具体内容进行深入思考。可以说,一部120万字的上下册《书法学》的编写过程,不亚于一个专题性的书法学学科建设研究班,许多含糊的知识要在这时澄清,而许多零散的知识又要在这里序列化。这,就是我们当时从事书法学学科研究的最大收获——它使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学术出发点:一个几千年来古典书论和民国书学研究甚至80年代以前所没有的,只有这个时代才有的出发点。
当然,这样的出发点肯定是超前于时代,因此也是不容易为人所理解的。就是在《书法学》出版后风靡书坛,一年之内连续印刷三版达12000部,甚至连我们也觉得意外:纯理论著作怎么会有如此好的图书市场——之际,我们也听到了大量的非难、不屑与愤愤不平。有认为“书法学”这个提法毫无必要,也有认为书法是不能有“学科”的,还有认为这一举动纯属沽名钓誉的;更甚至还有指它为花样文章、毫无学术价值的……种种不一而足。毋庸赘说,一个几千年来没有过的“学科意识”的不被理解,本来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但正是这种种反应,促使我去思考一些更深的问题:书法学学科建设,是一项开拓创新的学术工程。但是把它仅仅限于塔尖上,成为少数专家学者孤芳自赏的雅玩;还是把它作为一个时代的理论课题,使它走向大众、至少是走向书坛中对理论思考有关注热情与关注能力的书家层面中去呢?事实上,一部纯理论的、思辨型的、没有一张书法图版的《书法学》上下册第一版在短短一年中即印了三次,达12000部,即表明这个书家接受层面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并且它证明:书法界需要这方面的成果。或反过来说:这样的成果对当前的书坛可以拥有指导意义与产生影响力,只要它本身的质量过硬。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其后的研究生涯中对书法学学科研究进行了有意的推动与倡导。
第一、是联合中国教育学会书法专业委员会、《中国书画报》社,在近十年间,共同举办了三届“全国‘书法学’暨书法发展战略研讨会”(注:第一届“全国‘书法学’暨书法发展战略研讨会”,于1993年在天津召开。第二届于1995年在湖北宜昌召开。第三届于1998年在北京房山召开。)每届投入资金十多万,每届都出版论文集(注:第一本《书法学论文集》1995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二本《书法学论文集》1995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三本《书法学论文集》1998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参与研讨会的作者,有作为基本研究队伍的,也有偶尔介入这一学科研究课题的。经过三届研讨会,已聚集起了约60—70人的学科研究的基本力量。这,是一个扩大学科研究接受面的举措。
第二、是使既有的书法学学科研究向纵深发展,比如我们以书法“学科”为核心,分几个方面进行有计划的引导与展开,如(一)书法学学科构架的几种既有方式的类型分析;(二)书法学学科构架的其他可能性;(三)书法学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四)书法学学科研究的分支(如史学、美学……)研究;(五)书法学学科研究与其他艺术门类(如绘画、音乐、戏剧、电影……)之学科研究的水平评估;(六)书法学学科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将来。期望以此一系列措施,使书法学学科研究真正成为当代书法界的一门“显学”并能成为这个时代独有的标志。
第三、鼓励个人对书法学进行著述,并使它从学科研究的理论立场走向教育,使它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后继者。比如,在《大学书法教材集成》15册中(注:《大学书法教材集成》共15册,它们分别是:《大学书法专业教学法》《大学篆书临摹教程》《大学行书临摹教程》《大学草书临摹教程》《大学隶书临摹教程》《大学楷书临摹教程》《大学书法创作教程》《大学篆刻创作教程》《大学师范书法教程》《中国书法发展史》《中国书法批评史》《日本书法史》《近现代书法史》《书法美学通论》《书法学概论》。分别由中国美院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三家出版,自1995年到1999年全部出齐。总字数达6500000字。),我即单独著了一部《书法学概论》(注:《书法学概论》内分为[书法学引论]、[书法哲学]、[书法史学]、[书法美学]、[书法文化学]、[书法社会学]、[书法心理学]、[书法形态学]、[“书法学”学]等九章,书后附[书法学研究文献汇编]、[书学学科研究年表简编],大致囊括了书法学学科研究在这十几年中最主要的成果与基本文献。)共45万字。它是作为大学书法专业所用的教材,在课堂中面对大学生们进行授课的——连[思考题]、[作业]、[参考文献]也一应俱全;但它又是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而成立的。并且,在著述时,我有意识地使它与1992年出版的我主编的《书法学》在体例上、内容上都拉开距离。我个人以为这也正代表了我对书法学学科建设的深化的努力。此外,在书法学的各分支学科中,也已拥有一大批质量上乘的优秀论文(注:这方面的论文,可参见三册《书法学论文集》中所载,约有20余篇有代表性的论文,并且从1993年到1998年的这五年间,论文的水平也越来越高。)。甚至,我们还组织理论家们撰出了书法学学科研究的“文献汇编”与“年表”(注:[书法学研究文献汇编]收集了刊发在各报刊和三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最有价值的成果,和三次论文集的序跋、目录等,基本上可以涵盖书法学学科研究的各个方面的最高水准的成果。[书法学学科研究年表简编](胡湛编),则以时间为脉胳,梳理了自1985年到1998年这15年间书法学研究所走过的道路,可当作一部大事记来读。请参见拙著《书法学概论》第496-675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版。)。这样的资料工作,也许会对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书法学”带来极大便利。
第四、使书法学学科研究扩展至相近的艺术门类。比如在主持三届“全国‘书法学’暨书法发展研讨会”之同时,我们还以同样的思路,主持了一届“全国‘中国画学’暨中国画发展战略研讨会”,“全国‘篆刻学’暨篆刻发展战略研讨会”,也都出版了论文集(注:《“全国‘中国画学’暨中国画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集》由天津美术出版社1996年出版。《“全国‘篆刻学’暨篆刻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集》也于1997年面世。)。我们向来有“美术学”的概念,但却难有“中国画学”的概念。因为“中国画学”要澄清概念即不容易:比如“中国画”这个概念的产生与由来,“中国画”与“水墨画”的关系、“中国画”与“中国绘画”的关系、“中国画”与“文人画”的关系……至于它本身的学科架构,也与书法相类,并无现成的模式可供参照。因此我们的“中国画学”研讨会,也起到了荜路蓝缕的推扬作用,为中国画研究提供了较新的思路。至于“篆刻学”则更是印学界还未有认真思考过的陌生的新东西。其中牵涉到的“篆刻”与“金石”、“篆刻”与“印章”、“篆刻”与“篆”的篆书规定的关系,以及篆刻艺术作为视觉艺术的展示方法竟然不是印石(本物)而是印蜕(钤盖物)等等,在一个学科立场看来,都是极有探究价值的内容。故尔可以说,从书法学学科研究出发,我们还可以在诗、画、印等传统文化艺术领域中获得更为广泛、积极的回响。
以学术著作、论文集、丛书文库、学术研讨会等诸种形式聚集起来的“书法学学科研究”的成果群,在目前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并且它的纯思辨的理论成果,还伸延向同为传统艺术的中国画与篆刻,甚至还伸延向书法创作,成为“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成立的理论基础。由此可以表明:这一学科研究在当代的崛起与存在是合理的,并且是拥有前瞻地位的。在今后,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还可以使它向更精深、更专门化,同时也更具有书法发展的预见性的方向推进。全国性的“书法学”研讨会还要一届届地举办下去;至于撰述出版方面,也还会有更多的成果涌现出来。
二
回顾这将20年来对书法学学科研究的持久投入的足迹,我在以下三个方面有着深刻的体会:
(一)书法理论研究应该作为时代的前导,理论家应该有“敢为天下先”的雄大抱负与志向,立志为我们这个时代创造业绩。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大变革的时代,是一个可以充分施展才华、创造业绩的时代。书法在解放前,是没有什么艺术地位,仅仅限于文人雅玩而已,在建国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书法也是被冷落,受贬斥,是作为“封建主义的那一套”被鄙弃的。正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这20年,史无前例的“书法热”波澜壮阔、风起云涌,使多达上亿的人民大众投身于其间。这是书法从未有过的时代机遇,如果还是因循守旧,颟顸迂腐,不去努力振作,那是太有负这个时代了。更加之生逢明世,整个国策的开放,和江泽民主席倡导“知识创新”与举国上下的响应,为书法发展和理论发展形成了一个绝好的大气候。当代有成就的书学理论家,就应该有这样的抱负:在书学理论研究中探寻“知识创新”的各种可能性,使书法的“知识创新”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成为书法史在当代独有的新的历史内容,通过“创新”来创造出几千年古人所未能梦见的新的业绩。
“创新”的重点在于“创”——“创”前所未有之“新”,这就要求理论家们在选择课题进行研究投入之时,首先要有勇气有意志“敢为天下先”;敢于对古人的既成模式提出挑战。应该说:在书法这样的传统艺术门类中提“创新”将冒相对更大的风险,因为书法的传统积累超强超厚,在其中进行那怕是稍微的改革都会有一败涂地的可能性。但古典书论那种片段式、随笔札记式的论述方式,又与今天日新月异的书法思维相去甚远;至于在内容上的强调有序性与结构性,更是古典书论相对缺乏的——在书法学学科研究中,我们对创新的把握,首先即落实到这两点上:在内容上强调“纵构架”的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理论,从技法理论到书法艺术哲学原理;和“横构架”的书法哲学、书法史学、书法美学、书法文化学、书法社会学、书法心理学、书法形态学的并列展开,以此来表现作为学科构架的有序性:这正是书法理论之“新”和我们致力于此的“创”的着眼点。至于在方法上,则强调逻辑思辨、实证考订、文献资料汇集……等等之间的统辖关系,使书法学的研究方法本身也具有严密的秩序与因果——这些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之“构架”,都是古代书论即使是晚至民国甚至是建国以后直到70年代末都不曾有过、或即使偶尔有之也只限于片断而未能形成有序结构的。要想建立这样一种学科研究的形态,不但要冒着大多数人在专业上不理解因而拒绝接受的风险,甚至还要面对人们既有思维习惯、文化意识、知识结构所产生的陌生感并由此而引出对人们(书法家们)思想方法与知识结构进行改造的任务,毫无疑问:这简直是一个改造一代(书法)人思想的、远远超出书法理论一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如果新的书法学学科理论的研究,至少在书法界能引出如此的震荡,则说当代书法理论通过前所未有的学科研究,达到了古代书论所无法想象的无所不在的时代效果;谓为是“书法学”——知识创新的时代成绩,不亦宜乎?
至少在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书法理论领地里的任何一个分支内容课题,是拥有像“书法学学科研究”这样的无比生发力、扩张力和延伸力的。是则引它作为时代的标志,自然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必然的时代选择。如果我们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或敢于倡导的胆魄,那我们是太愧对这个伟大的时代了。
(二)书法学学科研究,应该尊重博大精深的既有传统,并具有扎实的理论准备,只有这样扎根于民族文化的丰沃土壤,才会保证它立于不败之地。
书法理论研究本来已经有相当丰厚的古典形态的积累。这是当代书法理论、甚至是未来书学“创新”所依赖的根基——只要我们不是盲目地把它当作“目标”,那么应该说:作为根基,它不但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还是今后书法理论“知识创新”的一个最有效的参照。于是,谙熟古典书论,并对它有深入的发掘与足够的把握,使之成为作为“创新形态”的书法学学科研究的一项基本功,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
但仅仅有这个前提还是不够的。没有对书法理论从功能到立场的重新定位,我们还是可以对书法学这样的新课题茫然不知应对。古典书论只能解决一个基础问题,但并不能教给我们在当下这个时代的方法。于是,从1986年开始,我们即对书法理论的功能立场进行重新厘定:
(一)古典书论是附庸于创作,今天的书学则是独立于创作;
(二)古典书论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技法作解释,而今天的书学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书法家提供思考方法与开拓新思维;
(三)古典书论是后喻文化式的现象总结,今天的书学则应该是前喻文化式的预想与创新;
(四)古典书论依附于人,故可以想到哪记到哪,随笔札记式的散漫并不算失败,但今天的书学则自有独立的框架,不是书论随人的好恶轻重随心所欲;而是作为人的书论家必须严格遵守书法学的科学规范,相对而言,是人服从于理论科学的规定。
像这样的对当代书学理论——“书法学学科研究”的基础功能作如此明晰的定位,正表明我们是站在时代的立场上对从古典到现代的书学理论进行全面的把握与反思。可以说:没有这样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对比思考,我们即使匆匆忙忙地打出一个“书法学学科研究”的旗号来,也是无法获得真正的收获并体现出时代价值来的。回忆自从事“书法学学科研究”以来的15年间,在书论界被倡导最有效,也最具冲击力的,正是这个“理论的独立价值”口号的提出——理论不是创作的附庸,它具有独立价值;理论是实践的前导而不仅是事后的整理;理论思维也是创造性思维(注:这是我于1986年在山东烟台召开的全国书学讨论会上提交的《关于当代书法创作层与理论层的构成分析及背景探讨》论文中的一个观点,后来被引用在《中国书法》1987年第3期梁扬撰文《理论之树常青——谈“陈振濂旋风”》一文中作为结束语,以后在许多理论讨论中都有引用这一观点的例子。)——它是我们对这个时代书法理论地位、功能、立场的基本定位。正是在这样的定位之下谈“书法学学科研究’,我们才会发现它的价值所在;若不然,若仅仅是附庸,没有独立价值,仅仅限于事后的整理,则要“书法学”学科这个概念作甚?如此抽象的被指为“泛泛不着边际”的学科研究能帮助我们写好毛笔字吗?更推而论之,书法不就是写好字嘛?要那么多名堂管什么用?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名句;“笔墨当随时代”,这是石涛等人的宣言,以之看书法理论,则当然也是一代有一代的“书论”。这个时代的书学成果:书法学学科研究是很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一项。之所以敢如此自信地说,正是因为古典书论中没有“学科”的概念,而新的书法学学科研究的现有成果中,可以窥出无处不在的传统基础的有力支撑。它,不同于古典书论,但又是古典书论在现代的逻辑伸延。它根植于古典书论;但又超越(而不是轻率否定)古典书论。
(三)书法学学科研究,是一项时代的系统工程,只有时代的配合和社会的综合支持,才会使它真正成为时代的标志。
以学科研究为出发点的“创新”的当代书学,在起步伊始即受到了来自有识之士层面的认真关注。以我作为倡导者的亲身经历,我认为来自协会团体、大学、出版界和社会如书法理论界的四个方面的支持,是使“书法学学科研究”能获得时代成功的最重要保障。
A、从中国书法家协会开始,到书法教育委员会,以及各书法团体、组织,对书法学学科研究给予了重要的支持有时甚至是亲身参与组织活动。比如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学仲,副主任刘正成等,都对书法学学科建设有过极中肯的建设性意见。沈鹏同志、刘正成同志还与我专门就书法学学科建设问题组织过专场学术对话,(注:关于沈鹏先生与我的对话,是起因于1999年7月7日在杭州我们的学术交谈,后被整理成《沈鹏先生与陈振濂先生关于当前书法理论研究的对话》(姜寿田整理),文长15000字,即将发表。关于刘正成先生与我的对话,则由朱培尔整理录音成《刘正成与陈振濂关于书法学科理论研究的对话》,刊发于《中国书法》1997年第1期。)学术委员会也曾组织过书法学学科建设的专题座谈会。此外,最值得大大记上一笔的,是中国教育学会书法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路棣同志,他与我一起策划组织了三届“全国‘书法学’暨书法发展战略研讨会”,一届“篆刻学”、一届“中国画学”的学科研讨会。出了五本论文集,这可以说是对当代书法学学科建设所能作出的最重大的贡献:从调动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配合、从策划构思到组织运作到学术定位,无不反映出这位古稀老人甘为人梯、愿做我们学科研究的坚强后盾的博大情怀。此外,最早尝试进行学科理论研究的第一代先行者如姜澄清、周俊杰、张铁民以及参与《书法学》著述的青年理论家们,也是各社会团体、组织中人才介入书法学学科研究的最典型的例证。
B、在大学开设《书法学概论》的课程,并以“书法学学科研究”作为主脉胳,是中国教育学会书法专业委员会主持的“大学书法教材集成”中《书法学概论》教材编写的基本思路。正是有了这样的基本思路,我才会在这部著作中附了两个内容:第一是“书法学研究文献汇编”,第二是“书法学学科研究年表简编”。在我所服务的中国美术学院,也把“书法学学科研究”作为四年级的授课内容之一。像这样的较有理论水平的授课能得以在大学课堂里实施,显然是基于“书法热”的遍行天下和书法高等教育体制的建全,它应该是当代书法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通常而言,一门学问能在大学里被系统讲授,则必然是该门学问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与具有时代性的标志。目前的“书法学学科研究”得到来自大学与高等教育的支持,这对于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理论而言是弥足珍贵的,它可以保证“书法学”在今后的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美好前景。
C、书法学学科研究,还得到了来自新闻出版界的鼎力支持。不但在报刊上已有过对《书法学学科研究》的全年连载文稿(注:1994年,我应湖北《书法报》邀撰写了一年的《书法学学科研究》的专栏稿,共分26期,全年连载。以后则被收入《书法学概论》单册著作中,作为第一章《书法学引论》的基本内容,详见该书第1—66页。),还有像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书法学综论》、《书法学文库》系列,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书法学》上下册,以及此后的三册《书法学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书法学概论》等等。这些系列成果能在近10年间鱼贯而出,使书法学学科研究真正成为一门当代书学中的“显学”;这些著作的化身千万,又吸引了更多的来自学术界的目光,并催化出新一轮的学科研究的大潮。可以想象,随着今后的成果越来越丰厚,我们还可以在更高的学术起点上对“书法学”进行更有深度的学术思考。
D、来自书法理论界的关注与支持,也使得书法学学科研究获得不断的动力。三届学术研讨会,每一届都有相当多的研究家投入,出席会议发表论文的都在50人左右。其中有一部份研究家是一以贯之,以“书法学”为主攻方向;也有一些是随机的:此进彼出,学术视点在不断转移——正是这种既有稳定核心、又有吐故纳新的健康的学术机制,才使得书法学学科研究有了历久弥新的魅力。可以想象,在目前开放的文化政策的支持下,今后作为时代创新主课题的书法学学科研究,以及篆刻学、中国画学的学科研究,还会吸引更多的参与者。这是书法学学科研究富于生命力、富有未来的象征,也是书法理论研究拥有时代的鲜明标志。
“书法学学科研究”还处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它还远未到结出丰硕成果的阶段。今后我们的任务是:在研究目标定位、研究内容分布、研究方法检讨这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使它在保持学科建设的抽象形象的基础上,对现实拥有更切实的指导意义,对当代书学也能具备更明确的牵引作用,即使对未来的书法发展,也能拥有更准确的预期功能与掌控功能。能进行这样的研究课题的选择,主要还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恩惠、得益于“书法热”的推扬、得益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更确切地说:是得益于国家富强之后对“知识创新”的大力倡扬的高瞻远瞩,我认为只要有这样的大氛围,我们致力了十几年的书法学学科研究,是一定会拥有未来的。
1999年9月22日于浙江省政协八届八次常委会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