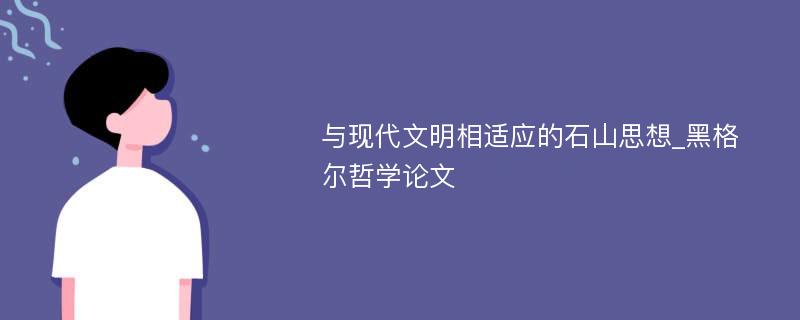
与现代文明接轨的船山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明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当今之世,仅凭个人的一家之言,就能取得“显学”的态势,而且正面肯定的声音,远大于负面批判的声音,尤其在以“意识形态”挂帅的时代,只问政治上的正确而不论学术上的是非,那些在思想史上被公认的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纷纷被一波波的文化运动,以及反传统、反封建,批儒批孔的声浪推倒的时候,明清之际的船山(王夫之)却能屹立不摇,不但通过种种严苛的思想检验,还能取得左右共识,如今更成为两岸三地学者认同的最后一位理学家。既是承先者——“对于中国封建文化和古典哲学作了总结”(冯友兰语)。又是启后者——“具有近代新世界观萌芽”(侯外卢语),不能说不是一大异数。
所谓“异数”,当然包括了船山其人其学所遭遇的幸与不幸,如冯友兰在晚年著《中国哲学史新编》所述:“王夫之的著作很多,大部分是在湖南西部深山中写成的。当时没有流传下来,这是不幸。因此也没有受到清朝当局的注意,如其不然,以其坚决反清的态度,在清初的几次文字狱中可能被消毁,他的家族必然受到迫害,这又是不幸中之幸了。他的全部著作一直到清朝末年才被刻板印行,影响及于全国。当时中国革命正处在排满的阶段,他的著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的著作在过去一、二百年之间好像是在养精蓄锐以待在适当时机发挥生命力量。他的著作对于中国封建文化和古典哲学作了总结,可以为继承人所凭藉,这是他的最大贡献。”(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册,第298、297~281页,人民出版社版。)
又船山的思想也与他的著作同样遭受到不幸中之大幸的命运,据萧萐父《船山哲学引论》提到:“船山的早期启蒙思想经历了清初一百多年的窒压之后,终于以符合时代需要而逐渐被发觉再现,流播海内,成为‘万物昭苏天地曙’的‘南岳一声雷’。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思想家,都先后吸取船山浓烈的民族爱国主义思想,镕铸成自己的批判武器。鼓吹变法维新的梁启超,曾把黄黎州、王船山等清初诸大师的学说比做‘蓦地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觉醒转来’的电光火石;力主种族革命的章太炎,则把船山著作视为‘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的思想号角。五四以后,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朦胧地意识到明清之际的哲学启蒙思潮是自己的思想先导。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首先提出‘清代思潮’,‘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文艺复兴绝相类’,肯定船山思想‘发宋元以来所未发’,‘是为宋明哲学辟一新路’。其后,又有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及王孝鱼《船山学谱》,稽文甫《船山哲学》,张西堂《王船山学谱》诸论著相继问世、踵事增华,试图用新方法新观点对明清思潮钩玄提要,对船山哲学疏理评判。这些研究成果,比之过去简单地把船山看作一位民族主义者进了一大步。”(注:萧萐父:《船山哲学引论》,第156~157、222、297、160~162、166页,江西人民出版社版。)
由以上所述,可见船山之学在清代整整被埋没了一百多年,直到清末才乘势而起,主要原因乃是客观情势起了变化,为了排满,而兴起了民族运动与民主思潮,这时才发现原来船山思想中有著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反专制的主张,一夕之间成了大家竞相研究讨论的对象,并且推崇他说“五百年来,学者真能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谭嗣同《仁学》卷上),而这种转变的趋势,也正符合船山对历史发展的看法,所谓“殆已得理,则自然成势”。正因其得“理”,具有丰富的思想体系,才能成“势”,取得“今之显学”的地位。
二、黑格尔与王船山
除了时间上船山学的晚出为“不幸中之幸”外,就地理环境言,船山生在中国也成了另一种“不幸中之幸”,如牟宗三有一篇短论,就直接将西方的黑格尔与中土的王船山相提并论,而且替两人定位说“依照传统的标准说,都不算是好的哲学家,而却都是好的历史哲学家。”因为他们的“具体领悟力”都很强,除了哲学之外,他们还能讲关于历史、国家、法律、艺术等方面的学问。但是在西方黑格尔并不能引起哲人的注意,因为西方的哲学传统是以逻辑思辩为方式,以形上学知识论等问题为对象,所以对于黑格尔讲得最精彩的人文世界、价值世界,那些具体的或实际的哲学方面表现,完全不受重视。
相反地,王船山在中国,虽然他的学问也沉寂了一两百年,而一旦被发现,立刻引起注意,牟先生指出说,原来这方面的学问即中国所谓“内圣外王”之学,是“大人之学”的“大学”。而船山所继承的正是由孔孟到宋明儒者的传统,其思想路数,则是继承了张横渠的规模而向下发展。要知儒家虽讲内圣外王,但大多著重内圣一面,至于如何从内圣开出外王,一直是儒者要面对的问题,而船山在这方面最显精彩,难怪牟先生对他推祟备至,赞美他“才气浩瀚,思想丰富,义理弘通”。说他“论历史,亦古今无两”。“尤其遍注群书,见其心量之广。由其心量之广,见其悲慧上下与天地同流,直通于古往今来之大生命而为一。”并认为船山最大贡献,即通过他具体的解悟,发现史不离道,道即在史,然后“据经以通变,会变以归经”。直透“道德的精神实体”,而见历史为精神表现的发展史,建立起真正的历史哲学,正视人文世界、价值世界之真理。(注:牟宗三:《黑格尔与王船山》,《生命的学问》第170~180页,台北三民书局版。)
其后唐君毅论王船山也与牟著所见略同,将他与黑格尔相提并论。在《王船山之人文化成论》一文中,谓“黑格尔在西方成理性主义的潮流以心统理,更言客观之心,客观之理。”并强调“黑格尔特重理性之经验意识,而表现为客观精神与历史文化矣”。而以中国哲学言之,只有结束明清之际的大哲王船山,与黑格尔的综合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之流相类。他说“惟船山生於宋明理学极盛之时期之后,承百年理学中之问题,入於其中,出乎其外。於横渠之重气,独有会于心。知实现此理心於行事,以成人文之大盛者,必重此浩然之气塞乎两间,而两间之气,亦即皆所以实现此理者。则人道固贵,天地亦尊。德义固贵,功利亦尊,心性固贵,才情亦尊。由是而宗教,礼、乐、政治、经济之人文化成之历史,并为其所重。而人类之文化历史者,亦即此心此理之实现,而昭着于天地之间,而天地之气自示其天地之理,天地之心者也。故船山之能通过理与心以言气,即船山之所以真能重气,而能善引伸发挥气之观念之各方面涵义,以说明历史文化之形成者也”。最后唐先生赞曰:“以此观黑氏与船山之言气言存在,必重精神之存在,文化之存在,言历史能扣紧民族精神之发展而言,以招苏国魂为己任,则黑氏船山,敻乎尚已”。并预见两人对中西文化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曰:“然处今之世,逆流上溯,而西方欲救黑氏以下以唯物思想以言历史文化者,盖当由黑氏而上溯。而在中国欲救清儒之失,不以考证遗编,苟欲民生为已足,而欲建立国家民族文化之全体大用,则舍船山之精神,其谁与归。”(注: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第665~667页,香港新亚研究所版。)难怪萧先生在介绍唐君毅对船山哲学之阐释一文中表示惊讶,他说:“自清末船山学流行以来,论者多矣。阐释如此之深,辩析如此之密,评价如此之高,实为罕见,唯熊十力、侯外庐书中对船山思想多所揄扬,差可比拟。”(注:萧萐父:《船山哲学引论》,第156~157、222、297、160~162、166页,江西人民出版社版。)
三、马克思与王船山
冯友兰在三十年代初写的《中国哲学史》中,只轻描淡写地把船山看作一个理学家。但是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因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所写的哲学史,他把船山的地位推到了宋明理学的最高峰。将船山思想划到唯物主义一面。而且解读船山晚年自作的墓志铭,铭文说:“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於兹丘,固衔恤以永世。”他认为这四句话的前两句表示船山一生的抱负,后两句表示他最后的悲愤。第一句表示他积极参加民族斗争,第二句表示他继承道学中的唯物主义的传统。他在民族斗争的锻炼中接受和发展了唯物主义,言下王船山乃先知先觉,两百多年前就知道唯物主义将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所以担当起这一承先启后的重责大任。(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册,第298、297~281页,人民出版社版。)
至于正式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船山思想的是被尊为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侯外庐,他在1942年写成的《船山学案》即作出了船山“是中国历史上具有近代新世界萌芽的杰出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评断。
侯著首先指出,船山思想具有启蒙的意义,盖船山思想正是旧制度“天崩地解”,新因素“破块启蒙”的反映。在政治观点中,“个人自觉,产生了他的近世人本主义思想,对于当时现实的批判。”经济方面,“颇具洛克的近代思想,更接近于亚当史密斯之国民之富的观点。”在哲学思想史中,这种时代精神升华为船山的具有启蒙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他在世界观、人性论、知识论、历史观等各方面改造了中国古代学术传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近代启蒙意义的命题,批判理学、解放知识,“开启中国近代的思维活动”。
进一步指出船山是一位“推故而别致其新”的杰出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使用颇丰富的形式语言成立他的学说体系”,建构了中国哲学史上最宏大的与辩证法相结合的朴素唯物主义体系。他一方面比较自觉地排斥、批判唯心主义路线,“尽其能事地痛斥佛老二氏的世界观”;一方面比较自觉地坚持、贯彻唯物主义路线,其“世界观乃是基於存在的实在,而不是高谈性命”,在他看来,是否承认物质世界是不依赖感觉、思维的客观存在,是‘异端’、圣学之大辩。”(注:萧萐父:《船山哲学引论》,第156~157、222、297、160~162、166页,江西人民出版社版。)
该书最后特别阐明船山的历史观,说:“他的自然进化史观,便是他的人类社会历史观的基础理论。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和自然史演变相等的,而有其具体的法则。”因此船山在历史理论中提出了“理”、“势”范畴,试图把自然史观中的唯物主义思想推广到人类史观。如果说,他在自然史观中主张“理为气之理,故由气的秩序见理。”那么他在人类史观中则谓“理为势之理,故由势之必然处见理”,即在历史的发展中没有不依靠“势”而存在的“理”,也没有不依靠理存在的“势”,强调“把握到理势的统一,以说明客观的合法则运动”,固而反对宋明理学“以天理的一成型范而概历史的发展。”(注:萧萐父:《船山哲学引论》,第156~157、222、297、160~162、166页,江西人民出版社版。)
以上所论,证明船山不同于宋明所谓“天理史观”特别把“理成势”和“势成理”两方面结合起来分析,就是企图说明历史发展是一个客观事实发展的必然过程。故坚决反对在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设置“王命”、“道统”、“天理”等各种唯心史观。
这一片面的看法,当然也引起了质疑,如稽文甫的船山研究即对船山的历史观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其中含有神秘思想,他说:“船山当然有许多反对泥古,通权达变的议论,可是一拉扯到他所谓‘贞一之理’和‘相乘之机’就神秘了。”这个“贞一之理”也称为“天理”,不仅历代典章制度的因革损益都是“天理”的表现,就连每个朝代的治乱兴亡里面也都有个“天理”在作主宰。照船山看来,汉祖唐宗都是应运而出“继天立极”,是那个“贞一之理”的体现者。一部历史就是一部天理实现史,这可以说是一种天理史观。
所以他严格的指出说:“本来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所有旧唯物主义者虽然对于一般宇宙论具有唯物主义的见解,可是一涉及人类精神现象和社会历史方面,总不免离奇古怪地陷入唯心主义的迷雾,船山在这些地方也并不特别高明。”(注:稽文甫:《王船山学术论丛》第56~57页。)
四、论“气”—概念的究竟义
五十年代以来,受到大陆学者高度肯定苏联日丹诺夫对研究哲学史所下的马列定义:需恪守哲学史中的阶级分析法,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史中的一条贯穿线,而冯友兰即根据这条线的指示,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作了严格归类,将各哲学家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如宋明理学家中张载是“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思想,而以张载继承者自居的王夫之所著《张子正蒙注》一书,进一步发展了张载的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说:“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处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张子正蒙注》卷一)他又说:“虚空者,气之量,弥沦无涯而希微不形,则人见虚空而不见气。凡虚空皆气也,聚则显,显则人谓之有;散则隐,隐则人谓之无。神化者,气之聚散不测之妙,然而有迹可见。性命者,气之健顺有常之理,主持神化而寓于神化之中,无迹可见。若其实则理在气中,气无非理,气在空中,空无非气,通一而无二者也。”(《张子正蒙注》卷一)所谓神化和性命,在张载的《正蒙》中,意义不很明确,可以有唯物主义的了解,也可以有唯心主义的了解。王氏在这段注解中,明确了这些范畴的唯物主义意义。气之聚散,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这些形式有无限的差别,这就是所谓“不测之妙”。也因为“不测”,所以称为“神化”。气之聚散必遵循一定的规律,这就是“理”。这些规律是神化所遵循的,就在“神化”之中。道学中的理学一派认为理先于气而存在,超於气之上而存在。王夫之的这段注解,认为理就在气中。
又说:“太和之中有气有神。神者非他,二气清通之理也。不可象者即在象中。阴与阳和,气与神和,是谓太和。”(《张子正蒙注》卷一)又说:“理只在气上见其一阴一阳,多少分合,主持调剂者,即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二》这就是说,气的聚散并不是杂乱无章的。阴阳配合有一定的分剂,阴阳变化有一定的秩序条理,这都是应当如此的,这就是“气之善”,也就是气之“神”。这就是说物质运动有一定的规律,这些规律就是理。它就是说物质运动有一定的规律,这些规律就是理。它就在气之中,并不是“虚托孤立”,象理学所说的那样。(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册,第298、297~281页,人民出版社版。)
反观新儒家的看法就完全不同,如牟宗三在他所著的《心体与性体》中,论到张载,即坚定地说:“横渠以天道性命相贯通为其思参造化之重点,此实正宗之儒家思理,决不可视之为唯气论者。”不过他也不讳言因为张载描述“太和”、“太虚”等,有关“道”的语言,“气”的意味太重,容易引起误会,而把他看作“唯气论”。试看牟著对张载《正蒙》首段的疏解:“太和所谓‘道’。中函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其来也,几微易简;其究也,广大坚固。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於简者坤乎?散殊而可象力气,清通而不可象为神。不如野马絪缊,不足谓之太和。语道者知此谓之知道。学易者见此,谓之见易。”牟宗三说;“此为太和篇之首段,大体是根据易传重新消化而成者。是以‘太和’为首出,以‘太和’规定道。‘太和’即至和。太和而能创生宇宙之秩序即谓为‘道’。此是总持地说。若再分解地说,则可以分解而为气与神,分解而为乾坤知能之易与简。”
并提出几点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例如“以‘野马絪缊’来形容‘太和’,则言虽不窒,而意不能无偏。盖野马是气之事,若以气之絪缊说太和、说道,则著于气之意味太重,因而自然主义之意味亦太重,此所以易被人误解,是唯气论也。”又说:“故‘太和’一词必进而由‘太虚’以提之方能立得住,而不落于唯气论。‘太和’固是总持地说,亦是现象学的描述地说。而其所以然之超越之体,由之可以说太和,由太和而可以说道者,则在太虚之神也。”最后再强调说:“横渠由野马絪缊说太和、说道,显然是描写之指点语,即由宇宙之广生大生,充沛丰盛,而显示道体之创生义。故核实言之,创生之实体是道。而非游气之絪缊即是道也。如此理会方可不致使横渠成为唯气论者。”(注: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437~439页,台北正中书局版。)
以上厘清了张载被人误解为唯气的地方,再看为张载《正蒙》作注的船山思想就可以明白分辨他究竟是唯心主义还是唯气论的唯物主义了。
船山注解太和说:“太和本然之体……太和之中,有气有神,神者非他,二气清通之理也。不可象者,即在象中。阴与阳和,气与神和,是谓太和。……生其变化而有滞有息,则不足以肖太和之本体。”(《张子正蒙注卷一》16~17)页“太和,和之至也……阴阳异撰,而其絪缊於太虚之中,合同而不想悖害,浑论无间,和之至矣。未有形器之先,本无不和,既有形器之后,其和不失,故曰太和。”(同上,15页)此处由“太和本然之体”及“太和之本体”二句,可知船山足以“太和”一词,来做为宇宙本体之称谓的。而由“阴与阳和”、“气与神和”、“和同而不相悖害”与“和之至”等句,则可知:所谓太和系强调本体自身的性能与成分之无上,极至的和谐状态。故船山说:“生其变化而有滞有息,则不足以肖太和之本体。”而这表示宇宙本体之无上和谐状态的太和,是必须透过气来理解的。而且它根本就是气。换言之,在船山眼中,太和与气只是“同指而异名”,它们根本就是表述同一本体的不同称谓而已。(注:陈立骧:《王船山天道论性格之衡定》,台北《鹅湖月刊》第328期,2002年10月。)
五、结论
以上笔者简单地用二分法介绍了五十年代以后大陆哲学界与港台新儒家对船山思想的看法,发现对同一个船山学,有两极化的各自表述的现象,其中最大的分歧,除了尊黑尊马不同的路线之争外,根本差异在两者不同的历史观;即以精神表现为主的历史观与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唯物史观,更重要的差异是对宇宙本体的看法,到底是气还是天道、天理等根源处的追究,即可判定是属于唯物论还是属于唯心论不同的阵营,形成一种“各尊所闻,各行所知”的对立情况。
从正面来看,可以说是因为船山学的内容过于庞大,如有人将它比喻为一座宝库,有人将它比喻为一座矿藏,总之,都是用来形容它的丰富渊博,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尤其船山遍注群经,借注疏来发挥自己的思想,虽然每部书的论述都精彩透辟,但整体来看,很难见出其系统的必然性,所以不容易精准的把握,而发生见仁见智的歧义。
从负面来看,则是“天崩地解”时代造成的不幸,学者必须选边站,港台新儒家为了救亡图存,而积极研究船山学,希望借船山思想开启从内圣,到外王的途径。认为“通过船山具体的解悟力,提起历史意识、文化意识、建立真正的历史哲学,正视人文世界、价值世界之真理,乃当今开辟生命理想之途径,以抵御唯物史观之唯一法门。”(注:牟宗三:《黑格尔与王船山》,《生命的学问》第180页,台北三民书局版。)
而大陆学者普遍把船山定位为“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说他“明确肯定太和絪缊之气是实体,这肯定虚空皆气,就是肯定世界统一性在于物质性。这固然是发挥张横渠的学说,但比横渠所说更为详密。“王船山批判唯心主义者关于本体的虚构”,以及“指斥道家和佛教唯心主义者是妄立一体而消用以从之,这个批判可以说非常深刻。”(注:张岱年:《玄儒评论》第20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版。)
总之,双方都借船山思想作为攻击批判对方的思想武器,这种以意识形态或政治正确为诉求的言论,并不合于现代尊重学术独立的精神。今天船山学早已与现代文明接轨了,但是船山学的研究,何时才能步入现代化呢?
标签:黑格尔哲学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哲学史新编论文; 张子正蒙注论文; 读书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哲学家论文; 王夫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