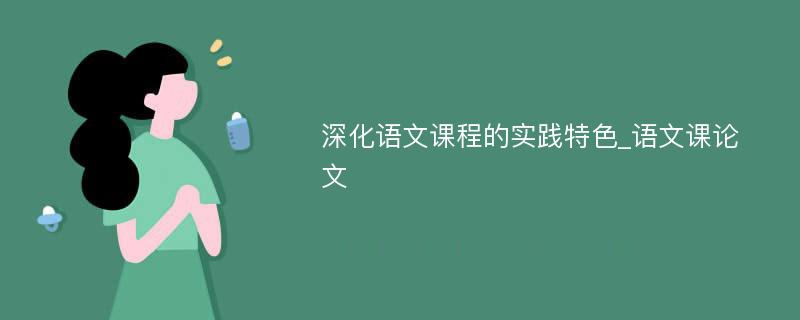
深化语文课程的实践特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性论文,语文课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相比而言,《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2011年版课标)对于课程性质的规定,由原先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修订为“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课标组专家巢宗祺指出,2011年版课标对语文课程性质的界定主要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说明课程内容和目标应聚焦于“语言文字运用”;第二,说明语文课程的“实践性、综合性”特点。简言之,语文课程是一门学生学习如何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实践性课程。[1]因此,深化语文课程的实践特性是语文课程建设的关键问题。
一、语文课程强调实践性的学理分析
2011年版课标不但在“课程性质”中明确提出了“实践性”,而且在其他部分也不断地强调该特性。例如,在第一部分讲如何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特点时指出,“应该让学生多读多写,日积月累,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体会、把握运用语文的规律”;在“课程设计思路”中,“语文课程应注重引导学生多读书、多积累,重视语言文字运用的实践,在实践中领悟文化内涵和语文应用规律”;在第三部分“实施建议”的“教学建议”中指出,“重视学生读书、写作、口语交际、搜集处理信息等语文实践,提倡多读多写……让学生在语文实践中学习语文”。
为什么要强调语文课程的实践性?这是由语文课程的独特个性所决定的。语文课程作为母语课程,我们认为,言语性是其区别于其他课程最为显著的特性。[2]学习语文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被祖国的语言文字进行同化的过程,对祖国语言文字的掌握和实践水平决定了学生的语文素养的高低。语文素养的高低既有实用的成分在内,也有文化的成分在内,但都是语文的言语实践性所派生出来的特性,因此言语实践性是语文课程最为本质的属性。西方语言学领域将语言现象划分为“语言”和“言语”,并进一步区分了二者的关系。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一种特殊规范;而言语是一种个人活动,是个人意志或智力的行为。[3]基于此,李维鼎等学者进一步认定,“语文课”本质上就是“言语课”,[4]其中“言语作品”是教学内容的主体,“言语活动”是教学活动的主要形式等。因此,学习母语的最好方法是“被语言说”,通过听、读、说、写等言语实践活动,提升学习主体的语文素养,这是一个动态的言语范畴,而非静态的作为抽象分析的语言范畴。而且,言语活动所有的价值和内涵都“主客一体”地附加在了言语实践当中,言语产品中承载了文本作者、教材编者、教师及学生等共同的精神家园。换言之,只注重作为规律和本质的语言科学范畴而离开了言语实践活动的语文教育是背离了语文课程的基本特征和规律的。
把“言语实践性”作为语文课程的基本性质明确地提出来,不仅是对语文教育规律的客观真实的反映,而且是充分认识言语教学、加强言语教学、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根本保证。我们认为,当前语文教学令人不够满意的是,好多中学毕业生往往字写不正确,书读不顺畅,话说不明白,文章写不通顺,语文知识也较贫乏,总的来说,就是缺少实际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未能在语文方面奠定扎实的基础。所以语文教师要千方百计地将教学的重心落实到充分、完善地发展言语实践的教学上来。[5]语文课程的言语实践特性决定了在语文教学当中,我们应当尤其强调“听、读、重读、抄写”[6]等。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实践性并非将语文教学简化为“训练”,用解释学大师利科的话来讲,言语哲学是一个主客未分的世界,人类通过书写确立了生命的表现。教学对话的过程是对人类精神和文化的追寻和相遇,在言语实践中,包含着情感的熏陶、审美的提升、人格的健全、文化的传承等等语文课程培养的目标,因此,言语实践中贯穿和渗透着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多维目标,且这是一个不可割裂、浑然一体的过程。
二、语文课程实践性的内涵与特征
我们认为,所有的课程都具有实践特性,而语文课程的实践性是以语文知识为中介,涵养学生的言语能力、思维能力、审美情感等的系统的实践活动。2011年版课标明确将“实践性”作为语文的课程性质之一。对“语文实践”内涵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我们认为其实践特性的内涵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特性:
第一,语文实践是学习主体言语涵养的过程。语文课程的言语实践性是语文课程最为本质的属性,这既指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听读说写”能力,同时也指在言语涵养的实践当中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凝聚力和创造力的过程。这其实是一个“主客一体”的过程。从后现代哲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学习语言文字过程的实质也是被语言文字同化和格式化的过程,因此,在学习者进行言语涵养的听读说写实践过程当中,蕴含着母语教育中的文化意蕴和精髓;在提升学生的听读说写等运用和驾驭祖国语言文字实践能力的同时,也是传承和弘扬母语文化的过程,言语实践将语文的多重价值凝固到了教学当中。
第二,语文实践是学习主体语文思维培养的过程。从思维的类型和品质来看,语文包含有言语形象思维、文章逻辑思维和语感直觉思维等等,都以其独特的方式区别于其他课程的思维培养。因此,在听读说写的实践活动当中,在感性认识尤其是记忆表象和想象的基础上,以文字、语言、材料、主题、结构、文体等为对象,将语文思维的凝固形式转化为学习者同化顺应的心理结构之中。缺乏思维引领的语文教学实践将变成教条式的机械记忆。语文思维客观存在于教育活动的始终。语文独特的言语形象思维、文章逻辑思维和语感直觉思维等思维活动的发展、思维水平的提高,是学生个性成熟与健全的标志。
第三,语文实践必须以语文知识为中介。张志公在1985年《关于改革语文课、语文教材、语文教学的一些初步设想》的讲话中,提出了“按照知识与实践的合理关系组织语文课”的设想,并指出“不能把语文课搞成一门纯粹的知识课,而是以知识为先导,以实践为主体并以实践能力的养成为依归的课”,这一论述准确地道出了语文课知识与实践的关系。语文课程知识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名物知识,如作家作品、常用字词、文学典故、文化常识等,这是让学生明白“是什么”的知识;二是方法知识,如造字方法、修辞方法、阅读方法、写作方法等,这是让学生掌握“如何是”的知识;三是理论知识,如文学理论知识、古代汉语知识、审美鉴赏知识等,这是让学生通过探究“为什么”的知识。[7]的语文课变成了道德教育课,在形式热闹中忽略了语文知识,殊不知,语文知识是培养学生言语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基础。就语文知识本身而言,它是思维和智慧的结晶,而其形式是静态的、现成的。但在教学当中,应把知识看作认识的过程和求知的方法,这是现代动态的知识观。[8]因此,以语文知识为中介的语文实践是在引导学生或理解“是什么”的名物知识,或探究“如何是”的方法知识,或在发现“为什么”的理论知识的过程当中,理解和建构其学习主体的语文知识,从而将知识转化为学生的素养。
三、语文教学中的实施策略
在具体的教学当中,应该始终注重把握教学是指导和促进学生言语能力的生成和发展的原则。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关注文本,言语积累。2011年版课标中反复强调,语文课程的建设“应继承我国语文教育的优良传统,注重读书、积累和感悟,注重整体把握和熏陶感染”,并且确定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所要达到的刚性要求:认识3500个左右常用汉字,背诵优秀诗文240篇(段),课外阅读总量应在400万字以上等。这都突出了语文言语积累的重要性。
在现实教学当中,有的老师偏重于对语文静态知识的讲授,而忽略文本的阅读和言语的积累,这是偏离了语文学习的核心的。如果在教学当中忽略文本,那么言语积累便失去抓手,学生所学习的语文知识往往成为空中楼阁,有骨架而无血肉,有理论而无实践,从根源上忽略了学生语文学习的言语生成原则。例如一位老师讲授初中课文《范进中举》,用了五幅具有代表性的插图概括全文剧情发展,进而引导学生分析人物命运和特点。用看似便捷的方式替代了文本阅读的过程,由于忽略文本,使得语文学习一直停留在言语实践的“外围”,学生没有得到言语历练和熏陶。因此,教师在学生文本生疏、阅读有限的情况下只注重客观知识教授的做法,甚至通过大量做题试图找到“举一反三”的规律,这就是古人所讲的“躐等而上”。结果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得到的却是似懂非懂、一鳞半爪的印象。[9]厚积薄发、注重博览、关注文本和言语积累是回归语文教学的言语实践本性的良方。
其次,注重诵读,知言养气。知言养气,源于孟子的“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到唐代韩愈讲求“气盛言宜”,到清代桐城派的“因声求气”,都强调了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言语实践对学习主体精神的促进和升华价值,是我国传统语文学习方法的典范。“言”即是文辞之美,“气”即读者阅读文章所产生的与作者、文本之间的精神共鸣。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认为,“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惜抱轩尺牍·与陈硕士书》),意思即是说学习古文,必须要放声诵读快读,再慢读,久而久之便能自己悟出其中的意味;如果只是默默看书,那么终身都是外行人。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琛先生回忆他的启蒙教育时曾讲过,开始读书,只教孩子读,读会了就背诵;到了节日,如端午、乞巧、重阳等,要温书背书;年终要把一年来读过的书全部背出。张元善先生认为这叫“立体的懂”,其关键就在于“熟读背出,把所有的书都全部装在脑子里”。[10]即便不能做到对经典篇目的全部背诵,一定数量的言语积累的“坦途”无疑还是诵读。通过背诵才能够真正掌握语言的表达形式和所指的内容,内化为学习主体的语文素养和能力,进而在实践当中举一反三。王力也讲:“背诵是传统的好方法,可以加强感性认识。通过熟读和背诵,对古代汉语能有更多的体会,不但古代的词汇和语法掌握得更加牢固,而且对古文的篇章结构和各大家的风格,也能领略得更加深刻。”[11]
例如一位老师讲授《出师表》第二课时,学生通过第一节课的学习已经对文章熟读成诵、烂熟于心,因此在老师引导学生对文章的思想情感进行分析理解时,学生便水到渠成、信手拈来了。学生每提出一个观点,都能够纯熟地引用《出师表》原文加以论证支持,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与作者、与文本的对话”。最后老师和学生分工合作朗诵了全篇,无论在情感和气势上都达到了审美的境界,使得《出师表》的精神意蕴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
第三,涵泳体察,精思笃行。“博览”和“诵读”的过程也蕴含着语文教学“涵泳”“笃行”的方法。涵泳体察,这是一种整体的言语理解策略,是以学生语文素养的发展为旨归的语文教学方法。它不像近现代过分强调科学性的语文教学方法,对汉语语言机制和文学作品进行肢解性解读。如对词性、句式的科学分析;文学课也上成了结构分析课,过分关注语文知识的客观性而失之偏颇。
“涵泳体察,精思笃行”,是力求言语的“内部”与“外部”的统一,力求在“言尽”与“意达”之间的张力关系中探其精微,建立起学习者与作者、教材编者、文本之间对话的“理解场”。曾国藩在《谕纪泽》中讲道:“涵者,如春风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善读书者,须视书为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在他看来,解说文义是容易的,而深入涵泳、体察是真正的读书之法。这里将读书比喻为春风、清渠对花和稻的润泽,也即教育的“化之”境界,非常形象地描绘了语文教学主客一体、不落两边的交融状态。这里的言语实践性是立足在学生自身对言意关系的内在体认上的。例如语文课《故都的秋》,很多老师在分析文本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理解秋的“悲凉”;但通过对文本的涵泳体察,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悲秋”的背后是对“故都的秋”深深的眷恋和热爱,以及他对于美好事物的执着与况味。因此文末写道:“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这正是身处乱世而恬淡自若的知识分子积极心态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