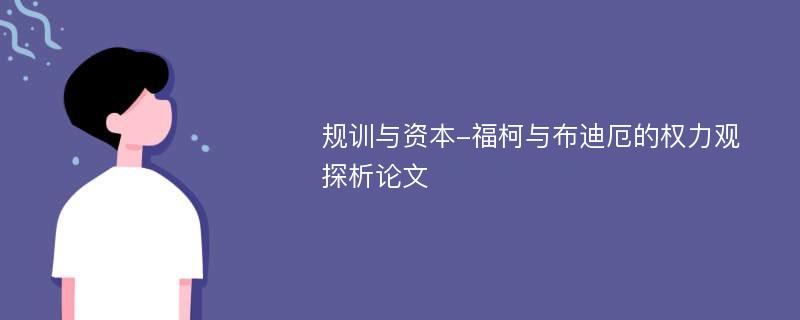
规训与资本
——福柯与布迪厄的权力观探析
施 超1,2
( 1. 上海杉达学院 管理学院, 上海 201209; 2. 台湾政治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台湾 台北 11605)
摘 要: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权力问题一直是传统政治与社会理论关注的焦点。与传统权力理论不同,福柯和布迪厄的权力观为我们提供了颇有洞见的备择理论。福柯提出一种现代微观权力观,他指出权力是“关系性”的策略,权力是“生产性”“规训性”的,权力无处不在,且权力与知识为合作共生之关系。布迪厄则发展出了一套关于实践与象征权力的理论,把权力阐释为具有特殊积累法则、运行法则与转化法则的资本形式,并证明了在现代社会,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对立作为一种基本的权力区分机制在发挥着作用。
关键词: 权力; 福柯; 布迪厄; 规训; 资本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权力”始终是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从霍布斯(Thomas Hobbes)到马克思(Karl Marx),再到韦伯(Max Weber),权力问题一直是传统政治理论与实践关注的争论焦点。只是,在大部分学术讨论脉络下,权力更多地被视为毋庸赘述的概念在沟通着学者们的理论表述,即人们甚少对权力及其周边术语做深入讨论,而是止步于理所当然的直觉理解。然而,20世纪下半叶始,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福柯(Michel Foucault)对传统的宏观统治权力理论进行批判与解构,他反对将权力视为可以被拥有的东西,反对将权力问题化为君主、国家或主权问题,而是以权力关系及其运作路径作为自己的研究中心,并发展出自己的微观规训权力观。而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则发展出了一套关于实践与象征权力(symbolic power)的社会学理论,他引入资本的概念,把权力阐释为一种具有特殊的积累法则、运行法则与转化法则的资本形式,赋予了权力概念更多的实践经济性和文化象征性。
日本兵坐着马车,口里吸烟,从大道跑过。金枝有点颤抖了!她想起母亲的话,很快躺在小道旁的蒿子里。日本兵走过,她心跳着站起,她四面惶惶在望:母亲在哪里?家乡离开她很远,前面又来到一个生疏的村子,使她感觉到走过无数人间。
一、 两种传统权力观
现代传统权力的分析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利益—冲突模式,另一种是权威—媒介模式。利益—冲突模式的代表人物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秉持A-B式的权力观念,他的“三维权力观”(the three-dimensional view of power)一直使用“A以何种方式来影响B”的句式。权威—媒介模式的代表人物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阿伦特(Hannah Arendt)。帕森斯认为权力是“能够为有效的集体行动调动资源的一般化媒介”[1]314,阿伦特则更强调要将权力与支配事务分开,必须超出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来考虑权力。在此种权力观中,权力与集体而非个人保有根本性的联系,它通过符号化和合法化的两个过程转变为一种集体的权威,从而成为有效的权力。并且,权威—媒介模式在进一步发展权力的沟通观念中开始逐渐摆脱对带有主观色彩的价值规范的依赖。卢曼指出:“权力的沟通媒介理论与其他权力理论的最显著差异就在于这一理论对权力现象进行的概念化是基于符码与沟通过程之间的差异,因此并不将权力作为财产或能力而归于某一方,而是将权力看作沟通媒介。”[2]116
这两种权力观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共同的局限性:首先,它们都将权力与政治领域挂钩,这虽然是大众眼中盛行的政治观,却与亚里士多德的开创观念大相径庭。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中,作为政治的动物——人所生活的城邦,其意涵远远不仅限于今天所说的“the political”,而是具有更广泛的意涵,即社会成员进行社会互动的舞台,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今天所谓的“the social”。亚里士多德大概并不会同意今天的学术体制将权力问题仅仅留给“政治学”领域。权力和统治都是渗透整个社会生活的实践问题,而无论是利益—冲突模式还是权威—媒介模式都忽视了这一点。其次,这两种权力分析都与精英和领导权的判定关联,涉及谁有能力掌控政治议题及形塑他人的意志,并且它们都将权力视为主体的一种“财产”,将其与“占有”“拥有”联系起来,利益—冲突模式将权力看作可以归于一方的“控制单位影响反应单位行动的能力”,权威模式将其视为归于集体的“协同行动的能力”[3]。这种“所有物”的分析思路和“能力”思路将权力分析深深禁锢在“原因—力”[注] 受牛顿机械力学思想的影响,将因果关系中的原因理解为一种力(force),将有待解释的社会现象看作是这种“原因—力”所产生的效果(effect)。 的观念上,阻碍了学者们从“关系—运作”的角度来研究权力。
二、 规训——福柯的微观权力观
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认为:权力、知识和主体构成福柯哲学的三维,其中,权力问题是理解福柯思想的关键。从早期的考古学到中期的系谱学,“权力如何运作”一直是福柯的研究中心。“考古学时期,在《疯癫与文明》和《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就已经构思出后来在《规训与惩罚》中发展成熟的权力微观物理学。”[4]福柯对权力的诠释在哲学史上是有独创性的,他的权力观是一种微观权力的生产性面向。福柯关心的问题不是“权力是什么”,“由何处产生”,而是“权力如何被运作”,“权力运作的效果是什么”,对于权力,福柯并没有给出一个完全准确的定义,尽管他对权力的见解相当丰富,就是因为他认为分析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比给权力界定一个抽象概念更重要。不过,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福柯关于权力论述的相关特性来理解其权力观的独创性。
(一) 权力是“关系性”的策略
福柯认为,如果要不带成见地了解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就要建立一种非经济的权力分析视角,他指出:“并没有真正的‘理性’的经济理由来迫使囚犯在监狱中工作,囚犯的工作并不为任何经济目的服务”[5]。因此,不管从利益的角度,还是从所有物的角度来诠释权力都是不妥的。从所有物角度来看,人们经常说“A有权力”,是指A有权利以某种方式处置它并通过处置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或利益,也就是说,权力成了物权。另一种情况下,当人们说“A有权力”,意味着把A视为权力的化身或代理人,这又使等级垄断以隐蔽的方式进入权力理论。因此,无论是哪一种理解,都只将权力看作某主体所占有的力量而并没有真正去分析权力机制。
其次,福柯的权力研究中另一个突出的创新即为“知识—权力”理论。传统权力观大多认为权力是压制知识的,此前的学者大多持批判的眼光进行权力分析,认为真理或知识会像光一样照亮社会的阴暗角落,相信能透过揭示权力来展现社会支配的真相。然而,在福柯看来,“知识的起源或影响永远不会是无辜/天真(innocent)的”(John Forrester 217)[9],权力与知识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合作共生的。一方面,知识体系需要相应的权力体制加以落实;另一方面,权力关系的运作依赖知识体系提供养分,且知识体系可以增强权力实施的效果,使权力具有合法性,即“知识为权力的运作建构了行动和干预的基础”(Barbara Townley 521)[10]。福柯尤其将这一论证的矛头对准精神病学、临床医学等“非精确科学”。
而福柯则突破了权力的所有物观念和政治系统的牢笼,使用技术、策略(strategies)、手法等术语来分析权力,强调权力运作的实际过程,并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权力。在福柯看来,权力关系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权力关系总是与“第三者”相关。在互动中,A-B的行动包含了各种偶然性因素,而不同的第三者(即A-B互动的外在变量)以何种方式改变着A-B互动的可能性是权力分析要讨论的问题。二是这种第三者对互动过程的影响是一个“历史”现象,与时间有关。权力关系绝非“一次性”交易,它不是当下的关系,而是历史的关系。A-B的“互动链”上每一次出现的不同第三者都会将无数其他社会成员带入权力关系之中[3]。因此,权力并不是某个主体所拥有的“能力”或“财产”,而是一种关系性的策略,我们应该关注权力作为一种关系“线”是如何穿梭在社会互动中发生作用的。简言之,发挥权力作用的既不是某个个体,也不是某个据点要地,权力从无数的点出发,在诸多关系线中根据其生产机制发挥作用。
(二) 权力不是压制性的,权力是“生产性”的
根据表4中数据计算,单层干燥模式总体样品终水分含量均值为9.33%;双层干燥模式II下,总体样品终水分含量均值为7.77%,各层物料最终湿基含水量无显著差异(p>0.05);而干燥模式III下,总体样品终水分含量均值为8.68%,B层与A,C层物料终水分含量差异显著(p<0.05),与双层干燥相比,干燥的均匀性较低。在干燥能耗方面,双层模式能耗最低,能较为充分的利用热能,过薄或者过厚都会增加能耗。
在《资本的形式》(The Forms of Capital )中,布迪厄指出在他的理论框架下,“资本和权力,这两者是同样的东西”[13]。不同于马克思的资本,布迪厄把资本的概念扩展到所有的权力形式,包括经济资本(财产权)、文化资本(如教育文凭)、社会资本(关系网络)以及象征资本(合法性)。“资本是累积的劳动,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施为者(agents)或其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或活的劳动形式占有社会资源。资本需要花时间去累积。”[13]虽然布迪厄也说“资本是积累的劳动”,并将时间因素纳入社会结构之中,近似于劳动价值论并带有历史制度论的味道,但是他的资本概念主要关注的还是权力,并不区分资本主义的劳动形式与非资本主义的劳动形式。布迪厄在资本的研究领域的关键贡献就在于扩展了权力资源的劳动类型,并提出不同形式的资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一定的比率相互转化。
(三) 权力不是国家中心的,不是宗主性的,而是“规训性”的,权力无处不在
福柯强调,在权力议题的讨论上应突破国家机器、政治和司法模式,我们要从权力发挥作用的微观、局部性行动/经验(如家庭、监狱)来探究其无处不在、统包全局的实相。
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有部分高校旅游专业在进行教学时,依然采用灌输式的教育方法,导致专业知识索然无味,难以吸引学生对教学的注意力,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专业水平的提高,降低了旅游专业优秀人才出现的几率。所以教师应该积极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对现代化的信息技术进行应用,促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提高,并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专业综合能力[4]。
权力不是宗主性的,宗主权的运作机制是征收,国王征收物品、人力和工具,同时国王也进行花费,但国王的花费永远比不上征收,产生了他和臣属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然而,现代权力是规训性的,规训性权力征收的不是物品或一部分时间,而是整个身体、全部的时间。规训权力的发展路径类似“蜂巢分蜂”(essaimage)的现象[注] 指蜂群离开业已饱和的蜂窝,去别处再建立另外的群体。 :由原先的宗教领域逐渐过渡到殖民、军队、工厂和城市。最后,在一层层的权力机制移居(migration)过程中,几乎整个社会都被规训权力所填满[7]。由此,宗主权社会过渡至规训权社会。
在《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中,福柯指出:“权力无处不在,不是因为它让每件事笼罩在它之内部,而是因为它来自各地”[8]93。 “一个规训社会的形成,其原因不在于权力的规训方式取代其他方式,而在于它渗透到其他方式中,尤其是使权力的效应能够抵达最细小、最偏僻的因素,确保了权力关系细致入微的散布。”[6]215-216在规训性权力的新形态下,福柯强调应多做权力的“上溯分析”,它从现代社会多层文化中的“细微机制”开始,“它来自下面”,它是“毛细管状”的,遍布整个社会肌理,在社会各部分之间不断流动。这种权力之微观物理学(microphysics of power)重点分析了各局部微观权力——诸多散布在社会空间中的“微小实践”。
(四) 关于权力运作机制背后的技术与知识
如前所述,福柯的确是想要分析权力机制和经济、政治制度之间的交互影响,但他也并没有建立一套关于权力的普遍性理论,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必须透过各个领域的案例才能厘清。福柯最终的立场是:在权力机制背后有一套有效工具——观察方法、登记技术、探讨和研究的程序等,用来构成和累积知识。因此,规训权力的发展和运作是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特殊的知识技术的出现以及人文科学的发展而来的。
首先,规训的力量贯穿在各项纪律之中,规训权力的主要功能是“训练”,而不是挑选和征用,规训造就个人,个人既被视为操练工具,又被视为操练对象,而且,规训得以成功实施依赖于一系列社会控制技术组合——逐级监控、检查和规范裁决。其中,检查把可见状态转换为权力的行使,也把个体引入文件领域,“书写权力”作为规训机制的一个必要部分建立起来,如此,以文牍为技术手段的检查使每个个体成为“个案”。此时,个案既是知识的认知对象,又是权力的运作支点。这一整套技术手段是福柯在研究监狱问题时发现的,但它不仅仅可以用来改造囚犯,也逐渐从监狱扩散到学校、工厂和军队,并最终遍布整个社会,就像边沁(Bentham)所设想的那样,成为现代社会的一项广泛采用的权力技术,也正因为此,福柯才称现代社会是一个“规训社会”。
(141)尖瓣扁萼苔 Radula apiculata Sande Lac.ex.Steph.余夏君等(2018)
综上所言,福柯的权力观使得“权力关系比我们之前看到的更为狡猾(cunning)和无孔不入(pervasive)”[9],但也在学界引发了很多争论:一方面,福柯的权力观开启了对权力微观运作机制的新探讨,通过对身体的规训力量对消费社会与消费文化间接产生了影响;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福柯进行了批评甚至全盘否定的评价,例如有学者提醒人们勿把福柯的权力无处不在的假说,错误地理解为好似它等于现代管制装置的无所不能。的确,说权力布满社会,并不意味着社会中的每件事物,都负担了权力的烙印作为一个确定的特征,这难免具有泛权力论的倾向。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遗忘福柯》(Forget Foucault )中表示,他不由自主地想知道福柯是否仅是在他的微观政治安排中使国家小型化,“权力概念在这个层面仍然适用吗?它不也是一个全球概念的小型化吗?我不确定微观安排是否可以被描述为权力”[11]19。在鲍德里亚看来,福柯关于权力的新版论述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权力原则依然不变,他认为这是一个“傲慢但过时的理论”。而针对福柯的权力观是否真的“反政治学”,也有学者辩驳道:“福柯的行动者在一个空间内以其作为互惠行为者的能力来引导他人,这与控制或强制关系不同,它们仍然对建立新关系和可能更具‘政治’形式的社会行动的可能性保持开放之态度”[12]。
传统的权力分析基本属于“压抑说”,总是强调权力消极否定的面向。但福柯通过对监狱和性的研究发现,权力应该是一种生产性的实践。他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中指出:“我们应停止从消极面向来描述权力的作用,如认为其是‘排斥’‘压制’‘审查’‘分离’‘掩饰’‘隐瞒’的。事实上,权力是生产的,它生产现实,也生产客体领域和真理仪式。个体及从它身上获得的知识都属于这种生产。”[6]194亦即权力得以作用的原因是它做出某事物的效果而非压制某事物的能力,正如监狱的存续是它能做出某事物的效果而非压制犯罪的能力,即权力是生产之事而非能力之事。即使压抑是事实存在的,也只能作为权力的附属效应,权力所能压抑的——即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它的“产品”。福柯这种正面性的论述主张并非认为权力一定就是好的,而是强调权力不仅仅是负面的压制、命令或禁止,它更多的是能产生各种具有积极效应的技术或策略。例如,他在分析“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on)时指出:全景敞视建筑有一种增益作用,它的目的是加强社会力量——增加生产、发展经济、传播教育,使社会力量得到增强。全景敞视建筑方案在下述条件下能保证权力的生产性扩充:一方面,权力得以在社会基础中以尽可能微妙的方式不停地运作,另一方面,权力是在那些与君权的行使相联系的突然、不连贯的形式之外运作[6]207-208。
三、 作为资本的权力——布迪厄的权力观
相比较福柯的蔑视利益和泛权力论的倾向,布迪厄的权力观则有较强的实践性,与政治和经济也有较强的亲近性。布迪厄认为,必须避免一般的权力理论,因为它会重新召唤传统哲学、政治科学的本体论,对权力的批判必须始终置于时间、空间和主体领域,并且必须高度反思其生产条件、限制和可能的影响。布迪厄提出了一套关于象征(或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的理论,这套理论要解决的是社会结构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的重要问题。布迪厄在对阿尔及利亚的农民、大学教授和学生、作家等群体的研究中发现:分层的社会等级与政治系统能够在代际之间进行维持与再生产而没有受到强有力的抵抗,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研究资本、资本的运作及其不同形式的转化如何把个体与群体纳入相互承认的竞争与自我延续的统治等级体系而得到解释。在布迪厄看来,所有的文化符号与社会实践——从饮食习惯、服饰风格、生活品位,到宗教、科学以及语言——都体现了强化社会区隔(distinction)的功能,而为了社会区隔而进行的斗争,就一定涉及个体、群体以及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问题。在布迪厄的权力分析中,资本(capital)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他把权力阐释为一种具有特殊的积累法则、运行法则与转化法则的资本形式,把权力的争夺比作社会游戏(game),他就是要找社会游戏的规则(rule),而资本就是一个最好的切入口。因此,他的研究焦点集中在社会化如何把个体与群体置于一个竞争的等级体系中,斗争的场域如何使个体与群体为了争夺有价值的资本而斗争,施为者(agents)[注] 布迪厄使用agent(施为者)而不是subject(行动者),意为个体没有那么独立自主,会受到结构的影响,但是个体的行动又有一定的弹力,甚至是可以改变结构的。 如何通过各种策略获取利益,以及他们如何在采取行动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再生产/复制着社会的结构。
(一) 作为“资本”的权力
4.3 死体可燃物自身含水量较低,可燃性完全受外界环境制约,主要由当地的气象因子决定,可燃性动态变化明显,分别对应不同的火险等级。
(二) 资本的形式及其转换
1. 资本的形式。布迪厄反对经济主义把一切都简化为经济学,他强调实践经济的一般科学必须努力掌握各种形式的资本并证明某些法则。于是他区分了资本的四种基本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注] 事实上,按照布迪厄的理解,资本的形式不止这四类,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社会领域找到更多不同形式的资本。 。
文化资本的概念,最早是布迪厄在研究中将其作为一个理论假设用以解释不同社会阶级出生背景的个体是如何获得不同学术成就的。他指出,文化资本以三种不同的状态存在:首先,它以具体的状态(embodied state)——即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dispositions)的形式存在。该形式的文化资本是转换成个人惯习(habitus)[注] Bourbieu用的不是habit,因为habit只强调结构面,会把结构视为理所当然,忽视人的能动性。而habitus有内化的结构,面对不同的情形,人会有不同的行为反应和展现,即能动性。意为有一个倾向,这个倾向构成一个结构,而各agent的倾向会牵涉到他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它是夹在structured structure和structing structure之间的,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惯习产生了适应客观环境的策略,即使这些策略既不是明确针对有意识追求之目标的结果,也不是由外部原因进行机械决定的结果。 的外部财富,它无法通过礼物或馈赠、购买或交换来及时性传递。文化资本最有力的传递逻辑在于文化资本客观化所需要的时间及其积累,那些具有强大文化资本家庭的后代,其资本积累的时间覆盖了整个社会化过程,即文化资本是资本继承性传递之最优隐蔽形式。其次,文化资本以客观化的状态(objectified state)呈现,诸如文学、绘画收藏、艺术品等,在物质性方面是可以传递的。再次,文化资本以体制化的状态(institutionalized state)存在,比如“学术资格”的形式。相对于政治经济权力,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具有一定自主性,即教育系统按照一定的合法化标准,吸纳和训练能够进入这一系统的人员,从而保证教育系统再生产的控制权,并生成了距离政治干预与经济制衡的相对自主性。但是他似乎忽视了社会建构性“里比多”(libido)的变迁——社会认可和赞许的阶层流动标准在今天越发多元和嬗变,因此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1)经过室内处理剂优选,研究出了一套抗120℃的环境友好型钻井液体系,该钻井液体系具有良好的抑制性、润滑性及油层保护性能,能够抗钻屑及水污染,经检测体系无毒。
目前将三位女作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几乎没有,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介绍、回忆文章。如杨静远《让庐旧事(上、下)——记女作家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11-12],文章回忆了抗战时期,武汉大学搬到乐山时袁昌英和苏雪林、凌叔华的一些旧事;秦春燕《修为人间才女夫——〈让庐日记〉中“珞珈三杰”》[13],以杨静远的《让庐旧事》为基础,重点放在“三杰”的情感问题上;陈学勇《珞珈三杰》[14],在简单介绍了袁昌英、苏雪林和凌叔华各自的成就后,记叙了三人的友谊,并将她们从性格、婚姻、人生归宿等方面进行了简略的比较。除此之外,几乎没有文章论及三人,更不用说是综合三人与外国文学关系的学术研究了。
印度国父圣雄甘地曾警示人们:地球可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无法满足人类的贪婪。联合国提出的《21世纪议程》也指出,地球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不适当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导致环境恶化、贫困加剧和各国发展失衡。若想达到适当的发展,需要改变消费方式,以最高限度利用资源和最低限度产生废弃物[22]。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到适度消费,要根据经济能力和合理需要理性购物、理性消费、适当消费。少买不必要的衣服,加强旧衣利用;适量选购食物,杜绝餐桌浪费;理性选购住房,避免严重的资源浪费。总之,从抑止过度消费入手来减轻生态环境所承受的压力。
这套关于资本的理论隐含着对权力的想象,布迪厄曾引用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的话指出,既然资本/权力能够以各种形式存在,那么资本/权力就可与能量进行比拟。按照这样的逻辑,资本就具有了扩散性,我们不仅有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也有宗教资本、政治资本、国家资本等等;但若资本/权力的形式被划分得很精细,我们就会倾向于发现权力无处不在——这恰恰是布迪厄本人所反对的权力的极度扩散。事实上,“布迪厄把自己的作品区别于福柯的恰恰在于:他比福柯更有自觉,只强调权力集中于特定的机构或领域,当然,他还是给予了经济资本一定的优先性。经济资本处于所有其他资本类型的‘最根本处’,说到底是经济资本使时间的投资成为可能,并经此而使文化资本的投资成为可能”[16]92。一定条件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是可以转化的,但经济资本似乎更容易转化为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不过,某些商品与服务可以通过经济资本直接获得,但某些商品与服务只有通过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才能获得。布迪厄还承认,文化资本的隐蔽性传递也存在缺陷,由于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学术资格——既无法像贵族头衔一样代际继承,也无法像货币期权一样随意转让,故而文化资本遵循着比经济资本更具隐蔽性同时也更具风险性的传递。
2. 资本形式的转换。如果说经济学倾向于从物的层次看待投资问题,布迪厄则从社会学的角度,退回到时间层次上提出了一套关于各种资本形式转化问题的理论。布迪厄对资本转换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马克思的价值学说,他指出资本形式的转换可以通过施为者积累的劳动时间来衡量。这就意味着,时间的注入不是浪费,而是积累,投资不是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经济学的层次),而是能量出现和消失的关系,只有某种时刻的“暂时消失”,不存在浪费的可能性。而资本不同类型之间的可转换性,是施为者致力于资本再生产和社会空间地位再生产的策略基础。
关于象征资本,布迪厄在《实践论纲要》(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中给出了三种不同的定义:“首先,它等同于荣誉或声望,即在其他群体眼中的社会地位;其次,象征资本相当于对经济和文化资本——当它们的属性、重要性和功能被主流分类所隐藏时——的再认;最后,象征资本是一种信用形式。”[14]此后,斯沃茨(David Swartz)曾试图提炼此概念的核心含义——即“不同资本形式(处于认知和认可领域)的公认权威验证”[15]83。但这种正式的抽象并没有考虑到其实际运用中的变化和细微差别。因此,布迪厄对这一概念的弹性使用被视为在不同经验脉络下多元应用的结果,其重要应用之处体现在下文将谈到的“象征斗争”。
(三) 资本分布、流通与权力斗争的空间——场域
“场域”(field)是布迪厄著作中的经典概念,他倾向于将场域视为一个开放式的概念,用以修正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他从关系的视角界定了场域——“在各种位置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network)或构型(configuration)”[17]133。通俗来讲,场域就像游戏,“斗争”是场域的核心特征,进入游戏的行动者虽彼此对立,但他们都认为游戏是值得参加的,在社会游戏中,每个行动者有自己的“主牌”,不同种类的资本之间的等级次序随着场域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归根结底,一种资本的价值取决于某种使这项技能得以发挥作用的场域的存在:各种资本既是所有者斗争的武器,也是游戏者角逐的对象,且每种资本只在特定的场域中发挥效应,它能使其所有者在特定场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因此,特定的资本形式就类似于权力场域运作中的“入场费”[17]135-143。
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与对某种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密切相关,而网络通常与会员制相关,能为会员提供所需的资源、支持和声望。布迪厄提出,某个施为者占有多少社会资本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他能有效运用的网络规模,二是网络中每个与之联结的施为者所占据的资本数量。会员制团体中的个体能从团体获得全方位的益处,既有物质利润,又有象征利润。事实上,不管是在未分化的传统社会还是分化的现代社会,在劳动力市场中各项机会与资源的获取都高度依赖于以教育资格为形式的文化资本和以网络为形式的社会资本。
场域也是一个“空间”,其“强”或“弱”还是“独立”或“支配”,取决于它如何从位置与其立场之间呈现出同质性。此外,“我们还必须将场域视为与其他场域相关以了解其独立和渗透的程度”[18]。至于场域中的施为者,他们是资本的主动承载者并具备基于其在场域中的位置及占有资本量而积极行动的倾向,也就是惯习。因此,惯习取决于塑造每种游戏感的场域,惯习的每个方面都会产生形塑该场域施为者行动的实践意义和模式。此外,场域斗争会使位于统治地位的个体与被统治地位的个体互相对峙,即斗争通常发生在场域中已确立有利地位的施为者与新来者之间。布迪厄借鉴了韦伯对牧师与先知之间的对抗之描述,把这种冲突称为捍卫“正统者”(orthodoxy)与倡导“异端者”(heterodoxy)之间的冲突。比如,在学术界存在“文化的掌管者”与“文化的创造者”之间的对抗,前者是知识的合法化系统的再生产者,后者是新知识系统的创造者。不过,这两种策略之间是辩证的关系,一种策略的实施会产生另一种策略,挑战者在斗争中产生着自己的异端,当挑战者斗争成功成为正统,它紧接着就会接受来自新的异端的挑战。当然,这只是适用于整个社会空间的一般性命题,事实比这里论述的要复杂得多。
(四) 社会空间与象征斗争
围绕经济资本或文化资本而进行的争夺也必然是一种象征斗争,象征斗争的目的在于占据资本区分符号,或为了维护或颠覆这些区分的分类原则。因此,生活空间即各种属性的空间,本身不过是在象征斗争的一个固定时刻的状况,社会空间中不同位置的占据者无论有无区分意图,都借助这些特征互相区别[19]390。
预制光缆采用预制舱内集中配线方式时,由于集中转屏柜的预制光缆根数较多,若直接将光缆余长收纳在屏柜周边光缆槽盒内或集中转屏柜下方,对空间要求较大,且日后检修、维护困难。针对该问题的余长收纳方案有两种:
布迪厄在《区分》(Distinction )中提出了与场域紧密联系的空间和象征斗争的概念,社会空间(social space)是区域(region)在其中分划的地理空间。位居此空间的施为者、群体或制度之间越接近,它们的同质性便越多,反之,距离越远则同质性越少。而施为者之间的空间关系是他们在资源分布中所占领的位置(positions)之间的关系,施为者根据他们所拥有的资本总量和资本结构被分配到整个社会空间中。个体、群体、机构和家庭等常利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以维护或强化自己在社会空间中的地位并进行斗争。
在布迪厄看来,被统治阶级只是以被动或陪衬的身份加入象征斗争中,尤其是加入为了给值得占有的属性和合法的占有方式定义的象征斗争中,而区分属性将其外观赋予不同的生活风格。例如,在文化方面,作为对所谓“高雅”的认可,觊觎支配着之前最高雅的属性的获取,因而觊觎有助于维持象征财产市场的紧张程度,迫使受到普及威胁的高雅属性持有者永无止境地到新属性中寻求稀缺性的证明[注] 这里,布迪厄受到尼采对精英主义与文化信仰机制的看法的影响,即文化的真正秘密在这里:数不清的人为获得文化而斗争,为文化而劳动,表面上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但实际上仅仅是为了允许少数人的存在。 。这种需求在本质上是无穷无尽的,因为构成这种需求的被统治者的需要无限地相对于一种区分重新为自己定义,而这种区分总是从否定方面相对于被统治者为自己定义。至于象征权力何以存在,布迪厄指出,象征权力会成为构造权力(power of constitution),它是一种保全或改变在社会世界中运作的联合与区分、结合与离异、聚合与游离之客观原则的权力,是维护或转化现行之性别、国家、区域、年龄与社会地位的分类方式的权力,而这一切都是借由那些用来描述个人、群体与制度的字词而运作的。即象征权力是利用字词制造事物的权力,象征权力的最高形式是制造群体的权力。而谈到“群体”,我们就不得不讨论一下布迪厄建构的“阶级”。
与马克思和韦伯不同,布迪厄把阶级界定为“社会空间中具有相似的生存状况与相应倾向系统的个体的不同组合”[20]。这种社会空间的观念,让我们在面对社会阶级时,能够超越实在论与唯名论的选择。布迪厄提醒我们象征斗争的策略原则存在于有分类能力的和被分类的词语系统结构相对于资本分配结构的独立性中,个体或群体会通过选择最有可能提高社会承认度的标签与头衔来强化自己的职业知名度与社会荣誉。比如“运动疗法医师”,他们期望这种新标签使他们与按摩师区分开来并使他们接近医师。这些策略力求保证区别性差距之恒定的自行车追逐赛,其作用是支持一种有名无实的持续“通货膨胀”。因此,阶级权力实际上是一种命名权力,分类斗争的中心是使用群体分类并把它们强化为一种官方的与合法的名义与分类的能力。由此,布迪厄就把阶级行为的可能性与象征权力的积累联系在了一起。
其实,这种对个体竞争的分析反映了布迪厄的职业特征及其偏好的研究领域,教育与文化是最重要的个体竞争与区分的例子。虽然个体对教育文凭的竞争在战后有上升的趋势,但这似乎更适合一个关于高雅文化霸权的强有力的假设。若这套理论被用来分析其他一些更具文化多元主义的国家处境,它的解释意义就会大打折扣了。比如在以货币力量为主导的高度分化的美国,高雅文化与象征权力似乎就没有像在法国那样发挥支配性的作用。因此,布迪厄的这套以资本为中心的权力理论缺少对于不同社会的特殊性以及它们之间重要结构差异的更加细致的讨论。
四、 辩证理性的“权力”
不管是福柯的“规训权力”还是布迪厄的“资本权力”,两者都摒弃了“实在论”的思考方式,都反对询问权力属于谁,权力从哪里来,是谁在统治等问题。并且,福柯与布迪厄在以下几点的分析视角上存在一丝不谋而合:第一,福柯认为权力是“关系性”的策略,强调要关注权力作为一种“关系线”是如何在社会互动中发生作用的;布迪厄则用权力“场域”来指社会位置之间存在的力量关系,这种力量关系确保它们的占有者握有一定量的资本并使他们跻身于对权力的争夺之中,这也是“关系”的方法,强调施为者之间关系的不可见性而非这些施为者们的可见性。只是,“布迪厄的关系方法必须在特定时间以及特定过程的变化和转换中予以检视”[18]。第二,布迪厄分析权力的经典概念是“场域”和“游戏”,每个场域中的个体都有自己的“主牌”;福柯虽然没有直接用“场域”“游戏”来注解权力,但他对布迪厄的观点应持肯定之态度,例如福柯也曾指出:“社会不可能在没有权力关系和权力游戏的情形下存在。权力关系网络在个人之间、在家庭内部、在教育关系中到处运作,这种对权力关系的分析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场域”[21]。
福柯的微观权力观突破了传统权力观的“牢笼”,推动了相关政治哲学与社会理论的发展,但是他过于强调规训权力的微观运作,忽视了国家宏观权力的运作机制,同时悬置了“权力由谁控制”的根本问题,完全不顾权力关系的阶级属性,易陷入泛权力论的境地。正因为这些局限性,福柯的权力反抗策略最终只能局限于个体的生存美学层面。相比较福柯并没有为“权力”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因为他认为概念界定不如研究“权力如何运作”来得重要——布迪厄则是通过“资本”的概念为权力下了定义。可以说,布迪厄的概念也不是为了对应于内在连贯、可以普遍化的形式规范而设计,相反,它是实用地从经验研究中以及与相互对立的知识观论争中塑造出来的。布迪厄一直强调要超越“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要把它们统合到一个更大的框架中去建构一种认识论。客观主义是实证主义倾向,是关注人类行为的统计学规律性的知识形式;而主观主义致力于辨认意义并揭示主体借以产生意义的认识活动。布迪厄的概念——诸如场域、施为者、结构、位置、社会空间——都展示了相似的策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研究特征是“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constructivist structuralism)或结构主义的建构主义(structuralist constructivism)”[20]。布迪厄寻求建构一种关于实践的理论,这种理论综合了物质的(实践的)与象征的(符号的)两个方面,因此强调社会生活的基本统一性。他重视社会生活的象征方面与物质方面的关系问题以及结构与能动性的关系问题,他强调个体在场域中的权力斗争与流动性,也承认经济资本的优先地位,已经比福柯有较强的兼容性与实践性,却也甚少论及劳工、工厂和国家,如果他能更多地关注工厂和国家,那么他或许会看到权力斗争的集体与组织的面向。
总体而言,在一个把传统权力分析模式作为学者们诠释、继承与对话对象的时代,福柯和布迪厄的权力观为我们提供了颇有洞见和吸引力的备择理论,尤其是布迪厄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在现代社会中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对立作为一种基本的权力区分机制在发挥作用。法国哲学家巴什拉(Bachelard Gaston)说过:“科学知识是‘辩证’知识,它虽不能抵达最终的真理,但它能作为一种纠错过程持续进行下去。”[16]36辩证理性可以把原有的理论置身于一个更广的概念空间,这个概念空间既能论证原有理论的力量,也能洞察它的局限。这个辩证的思维模式能够包含若干不同的理论,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它们或在一定的逻辑水平上是矛盾的,但是,一旦被置于更大的概念空间,它们就处于互补的关系中。既存的知识可以不是被拒绝而是通过一种重新的审视而被周延。在这种重新审视中,新的知识领域被开启,于是迫使我们对原先不加反思接受的东西进行重新认识与评价。对于“权力”,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 1 ] TALCOTT P.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ety[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7.
[ 2 ] NIKLAS L. Trust and power[M]. Chichester: John Wiley and Sons, 1979.
[ 3 ] 李 猛.福柯与权力分析的新尝试[M]∥黄瑞祺.再见福柯:福柯晚期思想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104-139.
[ 4 ] 徐国超.权力的眼睛——马克思与福柯权力观比较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3.
[ 5 ] MICHEL F. Power and sex[M]∥ LAWRENCE K.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1988:110-124.
[ 6 ] MICHEL F.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7.
[ 7 ] 林志明.权力与正常化:由“精神医疗权力”迈向“不正常的人”[M]∥黄瑞祺.再见福柯:福柯晚期思想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181-209.
[ 8 ] MICHEL 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M]. New York: Pantheon, 1978.
[ 9 ] FORRESTER J.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and the individual[J].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2017, 19(2): 215-231.
[10] BARBARA T.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and its relevance f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3, 18(3):518-545.
[11] BAUDRILLARD J. Forget foucault[M].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7.
[12] KEVIN S J. Foucault and the telos of power[J]. Critical horizons, 2017,18(3):191-213.
[13] PIERRE B. The forms of capital[M]∥ RICHARDSON J.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1986: 241-258.
[14] STEVEN L, STEPHEN Q.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universal: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bourdieu’s theo-ry of symbolic power and the state[J]. Theory and society, 2017, 46(5):429-462.
[15] DAVID S. Symbolic power, politics & intellec-tuals: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16] 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迪厄的社会学[M].陶东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
[17] 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 猛,李 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18] DIDIER B. Pierre Bourdieu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wer of practices, practices of power[J].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2011, 5(3):225-258.
[19] 皮埃尔·布迪厄.区分[M].刘 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20] PIERRE B.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J]. Sociological theory, 1989, 7(1): 14-25.
[21] MICHEL F. The ethics of care for the self as a practice of freedom[M]∥BERNAUER J, RASMUSSEN D. The final foucault. Cambridge: The MIT Press,1988: 1-20.
Discipline and Capital —An Analysis of Foucault and Bourdieu ’s View of Power
Shi Chao1,2
(1. College of Management,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2.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11605, China)
Abstract : Since Aristotle, the issue of power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ie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power, Michel Foucault and Pierre Bourdieu’s view provided us with an insightful alternative theory. Foucault proposed a modern micro-power view and pointed out that power is a “relational” strategy, is “productive” and “disciplined” and exists everywhere. Bourdieu developed a theory of practice and symbolic power, interpreting power as a form of capital with special accumulation rules, operational rules and transformation rules. He also proved that the opposition between cultural capital and economic capital plays a role as a basic mechanism for distinguishing power in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 power; Michel Foucault; Pierre Bourdieu; discipline; capital
中图分类号: C91- 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04(2019)03-0037-09
收稿日期: 2019-02-10
作者简介: 施 超,讲师,台湾政治大学博士研究生,从事社会学理论、人口社会学研究。
DOI: 10.13317/j.cnki.jdskxb.2019.031
(责任编辑 张向凤)
标签:权力论文; 福柯论文; 布迪厄论文; 规训论文; 资本论文; 上海杉达学院管理学院论文; 台湾政治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