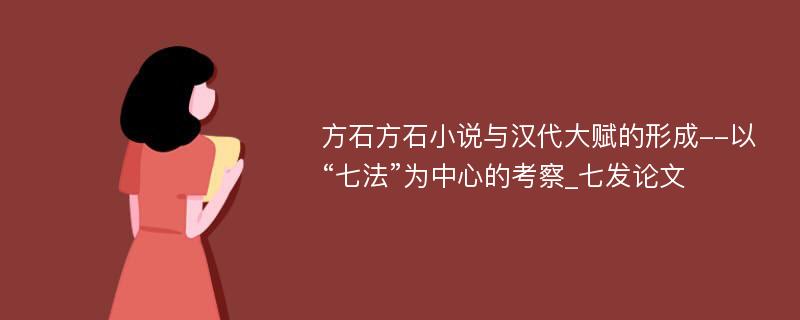
汉代方士小说与散体大赋的形成——以枚乘《七发》为中心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体论文,方士论文,汉代论文,说与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10)24-0170-04
关于汉代散体大赋体制的形成原因,古今学者论述很多,一般认为与统一、强盛的大汉帝国,文人对现实生活的尽情铺陈和炫耀,以及楚辞的铺张描写有密切关系。[1]122-129这些说法从时代特征和艺术手法入手,看到了散体大赋形成的外部原因,但与散体大赋的体制、内容的形成或无直接关系。汉大赋中奇秀的生活图景的展现虽与大汉的繁盛有关,但与大赋体制的形成并无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大汉帝国的强盛不一定必然形成长篇巨制的文章,唐代就是以简短的格律诗为成熟标志。汉赋与楚辞虽都喜欢铺采骋辞,都有驰骋夸张的描绘,但一是虚幻的神话图景,一是眼花缭乱的现实图景,两者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认为,枚乘的《七发》是骚体赋向散体大赋转变的标志性作品。《七发》描写内容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后来马、扬、班、张的叙述方式和表现对象,通过对《七发》内容的考察,我们可以窥测散体大赋从内容到体制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
汉赋名家枚乘《七发》的主题,主要以刘勰和李善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后世学者多在此基础上征引发论,虽略有不同,但都归于讽谏。《文心雕龙·杂文》曰:“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刘勰告诫膏粱之子不要纵欲,正是文章之显意,符合枚乘的原意,只是所说简略,没有点明内涵。到唐李善注《文选》则点明其隐喻之义:“《七发》者,说七事以启发太子也。……枚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发》以谏之。”李善认为枚乘写《七发》的目的是劝谏梁孝王,不知有何事实依据,大概是受汉赋由“虚辞滥说”到“卒章见志”的基本结构以及传统儒家诗教思想的影响,其道德化评价非常明显。但从文义看似乎并不能证明其说。
对于《七发》所说七事,一般的论者都认为,作者对音乐、饮食、车马、宫苑四方面的描写正是太子平时养尊处优、耽于声色生活的极端化的写照,作者正是借吴客之口极力渲染从而达到否定的目的,以警世人,进而为后文张扬“要言妙道”起到铺垫的作用。挚虞《文章流别论》曰:“《七发》造于枚乘,借吴、楚以为客主。先言‘出舆入辇,蹙痿之损;深宫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宴安之毒;厚味暖服,淫曜之害。宜听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导引,蠲淹滞之累’。既设此辞以显明去就之路,而后说以色声逸游之乐,其说不入,乃陈圣人辩士讲论之娱,而霍然疾瘳。”如果这样理解,则有两个问题无法解释:一是作者全篇极尽辞采,纵横杂陈,而真正讲到要言妙道时却写得极为简略、概括,草草收尾,显然无法体现启发导引作用,给人以结构不谨严的印象。二是作者的跌宕之词中对“至悲” “至美”等内容极力夸扬,未见片言贬损之意。虽然吴客在每陈一事后,总是问太子“能强起观之乎?”太子也总是曰:“仆病未能也。”好像是在说明这些声色生活是太子“玉体不安”的根源。可是,当吴客讲完田猎后,太子面有悦色,“阳气见于眉宇之间”,显然吴客之说已见成效。倘若如此夸夸其谈而竟无一点效果,恐怕听者早就昏然欲睡了,何况是病入膏肓的太子呢?
其实,这篇文章的主旨作者在篇末已经明确点出。吴客曰:“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能够讲述“要言妙道”的是“方术之士”,而这些方术之士除墨翟外,都是养生学派所尊奉的宗师。[2]如果我们把文义与时风联系起来看,枚乘所说的能够辨析天地万物是非的“要言妙道”应该与当时的黄老道家思想密切相关。他对放纵耳目之欲导致“伤血脉之和”的批判,希望通过精神上的疗救匡正人们由于纵情声色带来的伤身、伤性之疾,体现了汉初黄老养生观念。枚乘炫采之笔夸饰的内容正体现了他对养生的独特理解。
枚乘的《七发》作于汉初黄老学说最为盛行的文景时期,表现出非常成熟的养生思想。文章一开始借吴客之口阐述了导致太子疾病的根由:“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世俗的声色享乐生活是侵害生命的毒药,长此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这种惜命贵生的思想在秦汉诸子作品中经常论及。《吕氏春秋·本生》言:“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相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贵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贵富者,由重生故也。”枚乘显然是在《吕氏春秋》上的进一步扩展。《淮南子》对养生有更详细的阐述。《泰族训》说:“七窍交争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浇其身,夫调身弗得治,奈天下何?故自养得其节,则养民得其心矣”,主张“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使在己者得,而邪气因而不生。”出于“贵生”的目的,枚乘提出了解决太子疾病的根本办法就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自刘勰论出,之后的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作者对音乐等前四个方面故意夸张渲染正是为了明其害,“始邪末正”,以唤起人们的注意,从而对后文正论要言妙道起铺垫、烘托的作用。这一认识实际上曲解了枚乘力陈声色、车马的本意。枚乘在对前六方面一一渲染之后,都有一个准确的概括,分别称它们是天下的“至悲”“至美”“至骏”“靡丽皓侈广博之乐”“至壮”“怪异诡观”。作者反复用一个“至”字其实就是强调,它与一般世俗的声色享乐是有本质的不同的。“至”在老庄思想里有独特的含义,“至人”是指达到了“道”的境界的人,是神人或圣人。所以枚乘所夸耀的音乐、饮食等并不是一般意义的音乐或饮食,而是非世间所能享受到的达到了玄妙境界的快乐,是可以使人“伸伛起躄,发瞽披聋”的要言妙道,而绝非是引人病入膏肓的毒药。
汉初以黄老清静之术治理天下,黄老之学蔚然大兴,盛极一时。西汉初期的帝王、诸侯都非常痴迷黄老,景帝和窦太后尤甚。《史记·儒林列传》说:“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武帝虽以儒术治天下,但也喜黄老,尤喜鬼神之道。由于帝王的倡导,很多官员、士人也热衷此道,著名的人物有陈平、田叔、黄生、邓章、司马谈等人。此时的方士们也喜欢研究黄老,如司马季主、严君平等,都是以方士身份而研究黄老之学的人。《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说:“(严)君平卜筮于成都市……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依老子、庄周之旨著书十万余言。”他们不但研究黄老,还以老庄之书教人,这是方术和黄老之学结合的开始。为了迎合帝王的喜好,方术之士纷纷以“异术”干谒帝王,希望求得富贵利禄。《后汉书·方术列传上》云:“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史记·封禅书》载,武帝时栾大以方术侍上,“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同篇又载,武帝东巡海上,“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这些方术之士为了干禄,编造了大量的“诞欺怪迂之文”,夸大自己方术的效异和价值,因此形成了汉代的方士小说。
汉代的小说,《汉书·艺文志》“小说家”中记载的数量众多。其中可确定为汉代小说的作品,大多出自方士。《封禅方说》十八篇,班固注云作于武帝时。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时曾有许多儒者和方士言说封禅之事,《封禅方说》“盖即当时诸儒及方士所言封禅事也”。《虞初周说》943篇,班固注称其作者虞初是“方士侍郎”。其他如《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 《艺文志》颜注称应劭曰:“道家也,好养生事,为未央之术。”养生是方术的主要内容,此二书的作者应该也都是方士。[3]从内容看,方术之士的谈论多从历史故事、神鬼怪异传说引申发挥,阐述封禅、却老、房中、神仙之术。由于是待诏王侯时需要准备的应对材料,促使他们积极编纂、加工使情节更加生动。
二
方士小说中的故事经常与散体大赋中所描绘的内容有一定的联系,这在《七发》中表现特别突出。
枚乘所列举的音乐等之所以与一般的世俗声色不同,我们从他所描述的那些与众不同的人或物身上也可以看出,而这些人或物在汉代的方士小说中经常出现。枚乘在炫耀“至悲”之乐时称他要用“龙门之桐”制作的琴,“使师堂操《畅》,伯子牙为之歌”。师堂就是春秋时期著名的乐师师旷,他精通音律,《洪洞县志》云:“师旷之聪,天下之至聪也。”传说师旷鼓琴,可通乎神明。《汉书·艺文志》载小说《师旷》六篇,并注曰:“见春秋。”由此知,《师旷》六篇应该说从春秋史书中辑录而成的。现存春秋史书中只有《左传》记载了师旷故事。其中与音乐有关的是师旷歌南风事。“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此故事说明了师旷善听音。而《风俗通义·声音》明确注引《春秋》曰:
师旷为晋平公奏清徵之音,有玄鹤二八,从南方来,进于廊门之危,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则延颈舒翼而舞,音中宫商,声闻于天。平公大说,坐者皆喜,平公提觞而起,为师旷寿,反坐而问曰:“音莫悲于清徵乎?”师旷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闻乎?”师旷曰:“不可。昔黄帝驾象车,六交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后,虫蛇伏地,大合鬼神于太山之上,作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听之,听之,将恐有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闻之。”师旷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云从西北起,再奏之,暴风亟至,大雨沣沛,裂帷幕,破俎豆,堕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室侧,身遂疾痛,晋国大旱,赤地三年。[4]
《太平广记》也有相似记载,这个故事具有神异色彩,师旷甚至具有驱遣鬼神的能力。师旷所弹的乐曲《畅》是尧时圣乐,说明师旷音乐不是普通的靡靡之音而是“至德”之乐。伯子牙是春秋晋国之琴师,被后人尊为“琴仙”。据《吕氏春秋·本味篇》记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时而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摔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由师旷弹琴,伯牙为歌,自然是世上绝妙的音乐,飞鸟、走兽、昆虫皆听得痴迷了。所以,此乐堪比仙乐!
实际上,师旷之乐在汉代确有被神化的倾向,汉代保存下来的墓室画像石也有相似的故事内容。四川雅安高颐阙上有《师旷鼓琴》音乐故事图像,就是根据这个故事创意而作。画面上两人:师旷凝神弹琴,晋平公掩面而泣;上有两只飞鹤低头下翔,延颈倾听;下面有各具形状的昆虫似作欢跃状。整个画面生动感人。[5]师旷故事出现在墓阙中,说明师旷在汉代已不是一个普通的乐师,而是在另一世界里被尊崇的“乐仙”,身份发生了明显变化。
饮食中谈及的伊尹和易牙也都不是普通的厨师。《艺文志》有小说《伊尹说》二十七篇。其中与饮食有关的故事在《史记》《吕氏春秋》里都有记载。《史记·殷本纪》曰:“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吕氏春秋·本味》记载则极为曲折详尽,讲述伊尹出生于空桑之中,以及向商汤极陈“五味调和”之道,虚辞滥说,颇有小说的味道。而《艺文志》说《伊尹说》“其语浅薄”,则吕不韦可能取材于古小说。王齐洲引严可均云:“此疑即小说家之一篇”;又引梁玉绳《吕子校补》云:“《汉志》小说家有《伊尹说》二十七篇,《司马相如传》索隐称应劭引《伊尹书》,《说文》栌字、耗字注亦引伊尹之言,岂《本味》一篇出于《伊尹说》欤?”[6]不过,吕氏在“五味”说后用来比喻“天子之道”,还属可观之词:“天子不可强为,必先知道……天子成则至味具。”这里的“至味”与“道”等同。《史记》在引述时去除了其中荒诞不经之说,只留下了其中的“王道”之论。关于易牙的辨味功夫,《淮南子》《列子》皆引孔子言曰:“菑、渑之水合,易牙尝而知之。”《淮南子》又曰:“昔者齐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饵之。”刘向的《说苑》也有此说,而刘向自称其《说苑》部分辑录自当时的小说。这些大概可说明易牙故事被作为小说于汉初广泛流传。由伊尹、易牙烹饪的当然是天下“至美”的饮食。
至于论“车马”时提到的王良、造父,《荀子·王霸》:“王良、造父者,善服驭者也。”造父是汉代小说《穆天子传》的重要人物,他曾经为周穆王驾车西上昆仑拜见西王母,并随周穆王四处征讨。传说其驾车日行八百里。《史记》也载:“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只是没有小说中记载的神异特征。伯乐故事《淮南子》《列子》中都记载了其高超的相马技术,明显具有小说的味道。
除了《七发》列举的这些人物多出自汉代小说,具有神奇的技艺外,那些自然景象的描绘也都超越了现实世界的实景,具有想象的、虚构的神奇色彩。事实上,枚乘所要表现的并不是现实的生活,而是仙化的情景。“宫苑”中所说的景夷台,李善注《文选》引《战国策》说:“鲁君曰,‘楚王登京台,南望猎山,左江右湖,其乐而忘死。’”而接下来的描写珍禽异鸟、佳木修林、皓乐美姬,皆世间之少有,宛若极乐的仙界。对于《七发》中宫苑、田猎的描写,范文澜认为与楚辞《大招》有关。“详观《七发》体构,实与《大招》大致符合。”[7]《大招》本是为死者招魂的祝辞,引导死者的灵魂回归肉体。所以其内容一般要极力夸耀世间的享乐生活,但是实际上招魂所描述的内容本身并不表现社会的阳间生活,更不是墓主生前生活的写照,它反映的是墓主对阴间生活的一种理想追求,因此人们把所有的美好的享乐生活都寄托在了对死者的祝福之中。但是枚乘把它转化为对世间理想生活的描绘,通过方术之士的夸诞神奇的故事表达对理想的长乐养生生活的赞美。
所以,《七发》先陈音乐之妙、饮食之美、车马之盛、巡游之乐,次陈田猎之壮、观涛之奇,非指一般意义上的声色,而是借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神化的人和物来表达养生的观念,并无否定之意。关于前六方面所发,龚克昌也质疑“如果真的是日常生活的养尊处优、放纵腐化而引起的疾病”,那么优美哀伤动听的音乐、紧张雄壮的校猎、惊心动魄的波涛,“不是正可以修身养性、强健体魄”[1]304-314?看到了枚乘对前六发的肯定态度,不过他认为这其中包含了更深的讽谏意义,似有拔高原意之嫌,是受传统道德化评价思维模式的限制。
三
事实上,枚乘之所以虚构了一幅幅浪漫神奇的画面,与他本身就是方术之士是分不开的。枚乘曾先后游于吴、梁,客从于王侯,善言辩,好夸诞,其辞虽没,但从其子枚皋“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或可见一斑。但《七发》所表现出的对养生的深刻理解则毫无浮夸嫚戏之处。
作为由骚赋向散体大赋过渡的作品,《七发》对之后汉赋的内容和体制影响至深。之后的司马相如延续了枚乘驰骋文辞的特点,并加以进一步发扬,文意更加张扬,虚构想象更浓,“腴词云构,夸丽风骇”,这在他的《子虚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司马相如对楚王田猎和宫苑生活的描绘读来更有飘乎若仙的感觉,子虚最后称楚王“乃登云阳之台,怕乎无为,儋乎自持,勺药之和具,而后御之”,依然有养生之说的影响。不过,司马相如对楚王的行为由夸赞转向了否定,称子虚“奢言淫乐”是“彰君恶”,表达了他对汉初借养生而实纵欲行为的批判,从而使汉赋开始转向伦理化的批判倾向上来。更重要的是,这其中无意间涉及的对诸侯的批判之词被急于建天子之威的汉武帝偶然发现,不禁发出“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的感叹。在黄老之说导致自由主义肆意泛滥的背景下,司马相如自然受到武帝的重视和重用,为中央王朝摇旗呐喊,而司马相如也不负众望,继而写出了《上林赋》歌颂天子声威,从而使辞赋走向“与古诗同义”的颂赞的诗教传统上来。之后的班、张之作皆承讽喻之说,形成了汉赋的基本主旨。
通过对枚乘《七发》等汉初赋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汉初流行的方士小说逐渐渗透到赋体创作中,对散体大赋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从题材上看,散体大赋的描写基本围绕音乐、饮食、田猎、宫苑等展开,这些多为方士小说中夸说的内容。西汉的方士小说多与神仙养生之术有关,所以它的内容总是与声色六欲相关。由于汉初帝王喜好神仙养生之术,所以附从在帝王身边的人多是精通养生的术士。这些方士小说往往敷衍历史故事,加以神异化,以广视听,引起帝王的注意,而内容上则倡导贵生重道。上面所举的西汉小说都反映了这一内容。汉初推行休养生息,承平日久,法度废弛,声色享乐生活盛行,因此,散体大赋在形成初期与方士小说在题材上具有一致性,都围绕养生内容展开。枚乘引用了当时流传的小说故事,旨在对时俗流弊提出忠告,而他也借小说故事在赋中首倡“至乐”的养生观念,这种观念与老庄所言的“大音”“大象”一脉相承。《老子》第十二章指出了情欲之害:“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方,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只有超越世俗之乐,达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才可以超越情欲之害,达到养生的目的。这才是真正的要言妙道。只是这种“至乐”的观念在司马相如那里已经显得模糊了,至于班、张则完全系于世俗生活的描绘。但即使是在现实生活的描绘中依然经常可以看到方士小说素材的影子。
方士小说夸诞、想象的特征也逐渐为散体大赋所吸收。方士小说故事往往夹杂着神异的描写,师旷的音乐竟然可以驱使玄鹤、招致风雷,可谓出神入化。而枚乘的描写也很夸张,至悲的音乐使“飞鸟闻之,翕翼而不能去;野兽闻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蝼、蚁闻之,拄喙而不能前”;江潮使“鸟不及飞,鱼不及回,兽不及走”。司马相如虽是现实生活的描写,但也给人神奇的感觉,写田猎则如流星动雷,写美女则“若神仙之仿佛”,其对上林的描写宛若人间仙境。司马相如无论从题材和铺写手段上都吸收了枚乘的特点并加以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了散体大赋“辞翦荑稗”“铺采摛文”的体制形式。
因此,从内容看,大赋吸收了方士小说养生的题材;从素材上看,方士小说故事大量出现在大赋的体物描写中;从艺术上看,方士小说的夸诞、想象扩展了赋的篇幅,增强了赋的浪漫色彩,形成了散体大赋“丽以淫”的风格。
